关于女性友谊和命运——“那不勒斯四部曲”和埃莱娜·费兰特的女性意识(一)

《我的天才女友》
近年来,关于女性的话题越来越受人关注。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也使得女性的困境和诉求在公众平台上引发讨论。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包括四部小说,有人称之为“女性史诗”,它通过两位女主人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和抗争,传递出女性间的一种力量,也探讨了女性命运的复杂和深度。
神秘的意大利匿名作者
大家可能对这套作品并不陌生,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位匿名的意大利作家,“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她在中国最知名的作品,也可能是她在中国唯一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2016年底到2018年夏天,99读书人通过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将“那不勒斯四部曲”翻译成中文,每半年出版一本。这套书出版后引起一些关注和讨论,很多读者朋友并不陌生。这套书可能确实刷新了我们原先对很多文学话题的认识,包括对女性友谊、女性命运,女性和知识的关系,女性和原生家庭的关系,甚至女性和自己的身体等一些问题的思考。费兰特在书中对这些问题做了毫不粉饰的尖锐剖析,倾注了对女性命运的深沉关注。这也是她的书在意大利等欧美诸国出版之后,引起特别大反响的原因。
关注这套书的朋友可能知道一个记录片,叫《费兰特热》,导演在全球追踪很多承认受到费兰特影响、为这套作品欲罢不能的作家、艺术从业者以及各行业的普通读者,让他们分享对这套书的看法。这套作品包括这个纪录片最奇特的地方在于,作为主角的作者是永远缺席的。我们在中文版出版时也向大家传递这样一个概念,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书一旦写出来就不需要作者,它会走向自己的道路”。2016年出版第一本书时,我们的海报也向读者传达了作者匿名以及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版过作品的信息。但是我希望读者在拿到这套书时对这个故事、这个作家本身有一个充分的认知。她并不是一位一夜成名的作者。她的成功也不是出于偶然或者幸运。
费兰特的写作从1992年就开始了。1992年,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凡人的爱》。十年之后,就是2002年,她出版了第二部作品《被遗弃的日子》。这两本书已经在意大利拍成了电影。2006年出版的《暗处的女儿》讲述两位女性和她们的女儿在夏日海滩上发生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并不是灵感突然乍现,费兰特大概经历了十几年对写作、对自身、对文本、对女性在文学当中的地位等问题的艰苦思索,才为写出这样一个荡气回肠的女性史诗做好铺垫。。
费兰特在匿名写作的大概25年时间里,一直经由出版人居中协调和转达,通过书信或者邮件的方式回答媒体的问题,后来辑录成《碎片》一书。从《碎片》中,可以看出作家整体的思考或者写作力度。费兰特的早期作品并不像读者习惯认为的那样——一位作家的早期作品是不成熟的,可能跟后面有很大的割裂。我们想通过出版更多的作品来证明“那不勒斯四部曲”其实有她个人非常深厚的思考储备和写作训练。《碎片》里甚至收藏了很多宝贵的片段,是费兰特写作过程中尝试去突破,但最终未出版的一些段落。
费兰特匿名写作,全球有很多媒体关注她,《纽约书评》2016年曾做过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通过出版社追查作家的身份,在当时的国际出版界引起轩然大波。出版界对费兰特的匿名决定非常赞成,这是一个作家最为神圣的决定,与名声没有关系,从《碎片》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家:她承认自己是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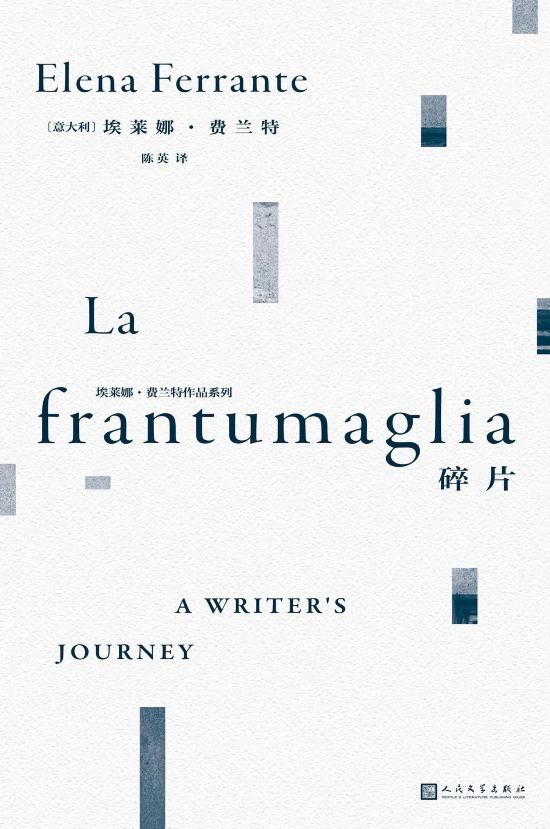
《碎片》中文版
费兰特是怎样形容自己和书的关系呢?《碎片》中有她在采访中的一段话,“写完一本书后,就好像对内心的挖掘太过深入,我会迫不及待地想从远处看着这本书,想恢复完整的自我。我发现出版一本书会让人松一口气,因为书印出来之后,就会走上自己的老路。起先是这本书跟着你、缠着你,出版之后,轮到你跟在它后面。但是我决定不跟在它们后面,我的想法是,假如我的书进入了流通领域,我没有任何义务跟着它们走完全程。”之后她又把这个问题深入了一点。“说得更具体的一点吧,我之前进入了那本书,现在我再也进不去了。那本书也无法再次进入我,我只能保护我自己不受它的干扰,这就是我现在做的。我把这本书写出来,就是为了摆脱它,而不是成为它的囚徒。”
作家这个想法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费兰特别开生面地强调了作家与文本之间的一种关系,不是通过文本收获名声、财富。而是坦诚自己跟文本之间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张力,她不想被书控制,进而影响到此后的作品。作家在做这个决定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外在的干扰、噪音甚至破坏。通过出版社追查作家身份是一个例子,另外就是满天飞的各种流言。有一个北欧的记者问她:“很多知名媒体和知名人士尝试揭开您的身份,按照一位知名文学评论家的说法,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位女作家,他说您甚至还可以是那不勒斯的一个男同性恋者。您觉得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费兰特是这么回答的:“我很欣赏您提到的这些作家,我的书能够被归在他们头上,我觉得非常荣幸,包括认为我是一个同性恋,我也不觉得古怪。这证明了一个文本经常能够包含很多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这个回答说明了费兰特跟自己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也足够让我们领略,她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的作家,是如何看待自己跟大众、跟小说,甚至跟出版界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在当下的出版生态里非常少见。
到2019年下半年,据费兰特的出版人公布,她的小说在全球已经被翻译成超过45个国家的文字,“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千万册。费兰特是对的,一本书只要写出来,足够好,它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读者。
竞争又依存的女性友谊
我们为什么要讲“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女性的生命是怎样呈现在文本中的。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是,“那不勒斯四部曲”跟费兰特之前的三部长篇小说《凡人的爱》《被遗弃的日子》《暗处的女儿》不同,这些小说里的女性并没有收获具体的友谊而主要是在为身份焦虑,为自己与故乡的关系,与女性的关系,与婚姻的关系焦虑。她们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存在。费兰特的出版人也意识到这点,问她,女性友谊作为文学的新主题出现,是不是让你的叙事很不平常?如果我们回想自己的阅读经验,会发现“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没有任何关于女性友谊的文学传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或世界的文本会让我们对女性友谊有一个真实的感受。
费兰特的出版人说,在之前的小说中,费兰特讲述的也是孤单女性,她们没有其他女性可以依赖倾诉。费兰特回答说,您说的对,之前的那些角色都是独自面对自己的问题,她们没有任何其他女性可以求助,可以获得支持。但是2004年的《暗处的女儿》中,有女性角色打破了这种孤立的状态,和另外的女人建立了惺惺相惜的关系。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莱农这个角色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她的故事和情感结构都是与儿时伙伴莉拉纠缠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用“女性友谊”来形容“那不勒斯四部曲”,与费兰特之前作品中的女性友谊不一样——她第一次让女性可以有另外一个女性去支撑和依赖,这也是小说打动我们的原因。无论女性或男性其实都长久忽略了女性之间那种非常奇特的支撑关系。“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女性友谊,没有比费兰特自己说的更为动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小说当中,一段友谊里面,性格更强大、更丰富的那个人,会让软弱的那个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但是在莱农和莉拉的关系当中,处于弱势的莱农,从自身的从属位置当中获得了某种才智,这让莉拉失去了方向,心晕目眩,这种过程很难描述,但是也正是这一点让我着迷”;“可以说,在莉拉和埃莱娜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事件显示了一个人如何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汲取力量。但要记住这一点,这并不仅仅表现在她们帮助彼此的层面上,同样也体现在她们互相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知识,甚至消耗对方的力量。”
这是她2011年出版《我的天才女友》后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的回答,通过这些描述,可以推断费兰娜到底想呈现什么样的友谊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比现在很多关于爱情的文本中的决裂都更让人心潮澎湃,甚至更有力量。很多人读完都非常震颤,这个震颤伴随着每一页——有一个可以支撑的人,你们之间是竞争但又依存的关系。
无论是读小说还是看看HBO改编的前两季,我们非常容易将莉拉和即莱农两个人脸谱化,会觉得莱农在智力上处于弱势,或者在勇气层面上明显不如莉拉,但是她获得的机会又远远超过莉拉。在四部曲里面,莱农离开了那不勒斯贫穷的社区、龌龊的家庭、粗俗的文化环境。身在底层的莉拉则留在了那个城市,但是她却依然用本质的强大智慧,或者说对社会的判断,试图去颠覆规则,莉拉最后的命运是走向——也不能叫失败,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界限消失”。
费兰特是怎么样形容这种关系的呢?她说莱农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她知道社会召唤什么样的人,知道要跨越自己的阶层需要做什么。她选择了通过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她说莉拉是更底层的,更发自肺腑的。当面对朋友莱农以及所谓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时,我们却往往为莉拉的整个生命和生活感到振奋,并更容易偏好莉拉进入世界的方式。借用费兰特在《碎片》中的提醒,埃莱娜勤奋,对自己要求很高,她积极地参与了世界,每次都能找到需要的工具改变生活,最终成为知识分子。
整本书其实就是莱农的自述,她一直在书里强调,好朋友是被自己抛在身后的。但整个叙述会不停地被莱农的各种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中断。在叙述中,她的恐慌或她真正的弱势定位,来自于她认为自己通过知识建构的资本、地位和生活结构都非常脆弱,是非常虚伪的认知,与自己有某种不相干的感觉。而莉拉其实表现得比她更为活跃、更加激烈,更彻底地参与这个世界,所以说莉拉是更底层、更发自肺腑。但是莉拉最后会真的离场,并且把舞台交给莱农。
不是严格的镜像关系
《我的天才女友》中发展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叫“界限消失”,在莉拉那里,界限最后真的消失了,因为她想打破生活。生活有各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外壳,让城市变得不再是城市,家人也变得不再是家人。我们会觉得“界限消失”是一个新造的陌生词汇,但其实它可能在既往的文学艺术中有一些轻微的痕迹。比方说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女朋友》当中,有一个中产阶级女性角色,说了一句话抱怨自己的生活空虚无聊——她说我特别希望自己消失,不留下任何痕迹。
《女朋友》是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但这句话在21世纪的一部小说中找到了呼应。一个人要抹除界限,要抹除自己的痕迹,这就是莉拉的生活哲学。这种生活态度根本上是非常激烈、非常彻底,甚至是爆裂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莱农跟莉拉这两个角色的对立,其实是一种本能的行动力,与社会强加的所有秩序之间的对立。但是小说家也一直提醒我们,用镜像关系分析这种对立或这部小说,是失效的。
因为两位主人公不是严格的耦合关系,这其实反映出一种更深刻的写作策略。四部曲中,看起来是莱农回顾自己跟莉拉从10岁到60多岁的友谊、两个人的一生,以及从意大利包括全球从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技术爆炸的巨大社会变迁。但其实它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个人是另一个人严格的对应。莱农在描述自己生活的时候,暴露出她不可信的一面。第三部中,有一段话描写她们的中年阶段。莱农当时出版了一本书,特别高兴,她参与了当时意大利的很多左翼运动,或者知识分子试图与劳工阶层互相融合的座谈会和讨论,志得意满;她也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试图描述自己生活得挺好的。莉拉说了一句话,她非常粗暴地对莱农说,每个人想怎样描述自己的生活都可以。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愿意试图描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样子。
她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像一种力量的不断游移。这是作家强加的一种修饰策略。我们觉得莱农这个人物变得虚弱,甚至觉得她在自我反思的时候,已经快要崩溃了。书中写了无数次她崩溃的瞬间,她回顾往事,想到自己一生的经历,要怎么样描述一个个阶段,她的想法,她的成就,但是很多时候她的怀疑都是来自于最可怕的生活现实——她的一切都不如她的朋友。这并不是嫉妒的原因,而是一个实打实的比较,她明白按照某一种另外的标准,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值一提,自己写的所有书也好,那些发在报纸上的文章也好,都不如她的朋友在工厂里打工,参加跟资本家作对的那些血淋淋的实际工作,或者是低俗的那类东西来得更为有效。所以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当莱农崩塌的时候,我们会想迅速攀附住莉拉这个角色。我至今都没有办法去向读者传达,读这套书时所体验到的在不同视角和声音间切换产生的魅力到底来自于何处。
伪装成爱的嫉妒
费兰特说,当莉拉的步子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时,读者会紧紧抓住莱农;但是当莱农迷失的时候,读者又会对莉拉产生信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个人的友谊并不是我是你的翻版、你是我的翻版,而是一种力量的时刻流动与生成。她们其实并不是在参与一种对称的人生,两人的人生绝对不是对称的,而是两种不同的自我成长,去生成、去变化的一种可能。从10岁到60多岁,在两个人情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内核是她们的互相嫉妒。她们成长在一个街区,10岁认识,但是却因为不同的际遇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小说里,跨越了阶层的莱农看似非常嫉妒朋友莉拉——她所学的东西,所参加的运动或喊出的的口号,都不如朋友的生活来得轰轰烈烈,来得动荡。这个动荡是一个褒义词,体现出一个女性的生活是有能量的。
对嫉妒这一主题的评论,《纽约书评》总结得很好——“那不勒斯四部曲”精彩而又持久地探索了嫉妒这种最为致命的情感。因为人们有时候会将嫉妒伪装成爱,我们当然不能说莉拉和莱农的关系只有嫉妒没有爱。这个小说最迷人之处也是来自两人之间的嫉妒与爱的界线非常模糊,甚至会在瞬间转化。我想熟悉莱农心理过程的读者非常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她可能在上一秒钟还在为莉拉的才智、大胆、粗俗感到愤怒,觉得莉拉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但是下一秒钟,她又会站在莉拉的角度去想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莱农后面所有的形容都是一种强烈的友谊和爱。第四部中,在莱农生命晚期,她最小的女儿和她非常疏离,她说莱农这辈子只有读书、写作,好像真正爱过的人只有莉拉阿姨。
我想这段话,还有《纽约书评》分析嫉妒与爱之间那种非常隐秘的关系,可能帮助我们思考女性彼此之间情感上的张力。这种张力不单体现在她们相互支持、无条件地站在对方角度的态度上,还体现在最令读者兴奋的部分,即她们两个如何从情感和智力方面互相超越对方。这是特别重要的。
(本文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版的编辑索马里在上海图书馆讲座的精简版整理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