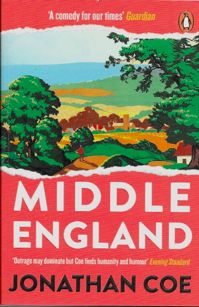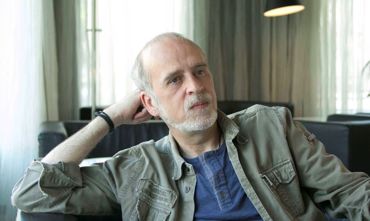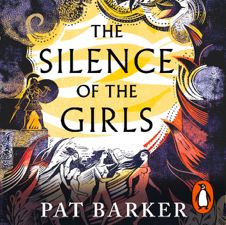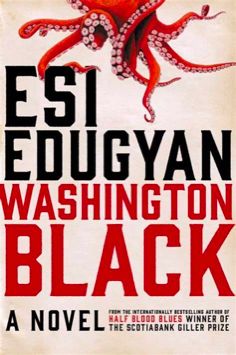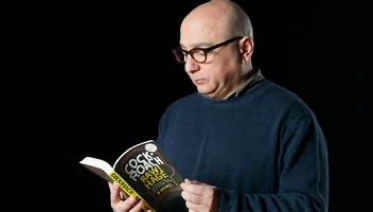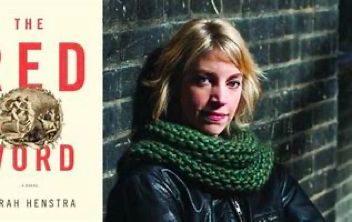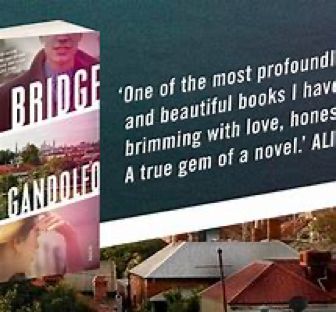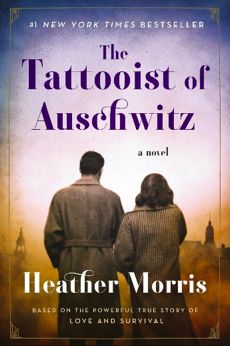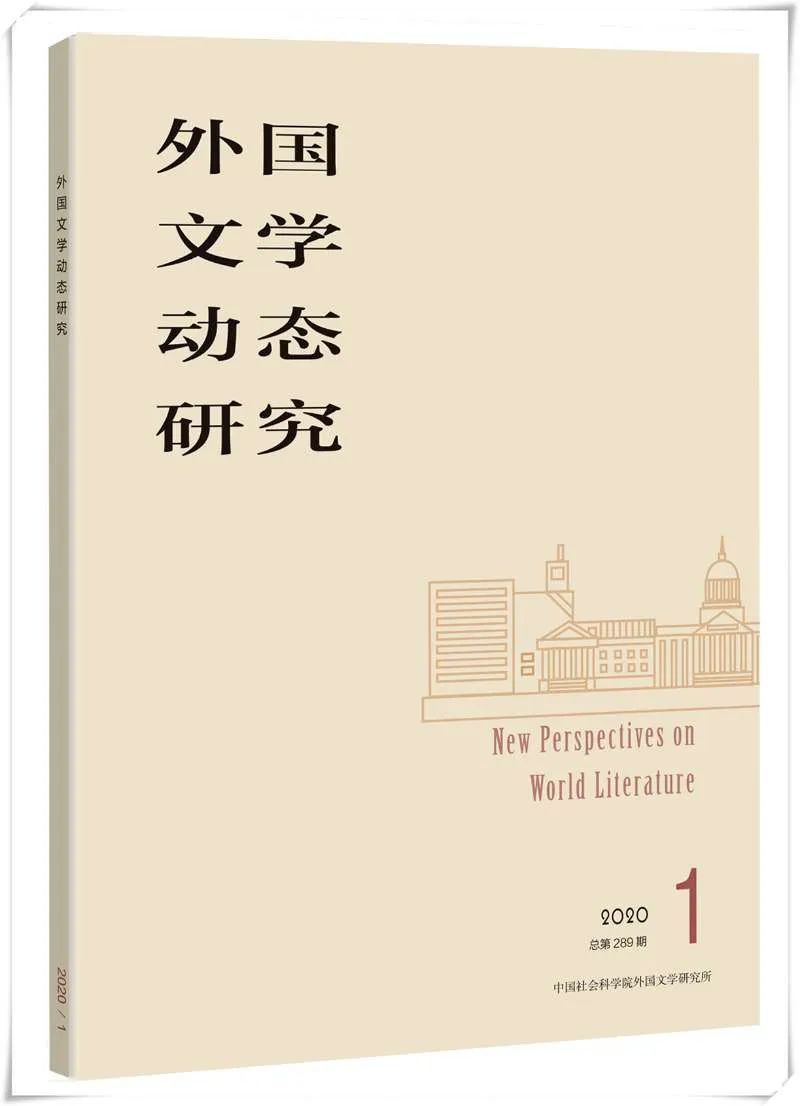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年度研究 |英语文学疆域的拓展 ——2018年英语文学概述
英语文学疆域的拓展
——2018年英语文学概述
芮小河,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 2018年度的全球英语文学出现以下趋势:通俗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界线模糊,科幻小说等进入主流文学;脱欧事件作为本年度英国小说最重要的背景,催生了科幻文学等通俗类型文学的变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文学、族裔文学方兴未艾,丰富了两国的民族文学资源;各种新的文学声音带来了英语文学在主题、类型、内容与形式上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带动了英语文学的疆域拓展,文学在不断被重新定义。
关键词 英语年度文学研究 脱欧 科幻文学 疆域 多种族文学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4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
往期阅读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关注我们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社科期刊网
扫码关注我们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