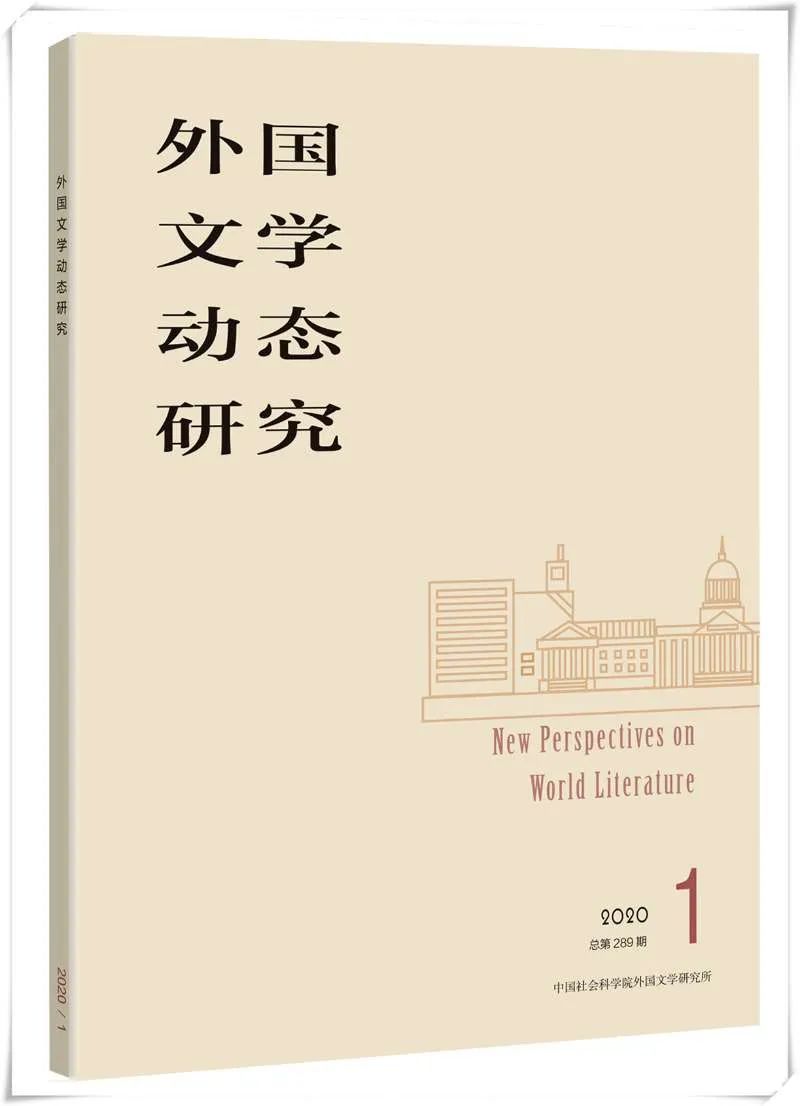诺贝尔文学奖 | 汉德克与老庄哲学 ——试析彼得·汉德克萨尔茨堡创作期作品中的道家哲学影响
汉德克与老庄哲学
——试析彼得·汉德克萨尔茨堡创作期作品中的道家哲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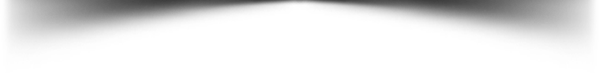
李睿,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德语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德语语言史、德语语言哲学、德语话语语言学等研究。出版发表学术著作、译作、论文数种。
内容提要 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代奥地利德语作家彼得·汉德克崇爱老庄道家哲学。本文尝试梳理汉德克在萨尔茨堡创作期作品中的道家哲学影响痕迹,指出汉德克作品以“回归”作为最终和解状态的追寻历程,为读者展示了一个“虚己”的过程,契合道家哲学中所谓“反/返”与“大归”的概念;其作品中描述的主人公寻找自我、回归自我、实现自我的“去主观化”过程与老庄哲学所谓从“有我”到“丧我”的转变具有一致性;从汉德克的“重温”美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老子》所谓“复”的道家哲学思想。
关键词 汉德克 道家 老子 庄子 萨尔茨堡

一、萨尔茨堡读老庄
2016年,在其中国之行中,汉德克难掩自己对老庄哲学的崇爱之情:“我特别喜欢读《老子》这本书,还有庄子。”汉德克作于萨尔茨堡的随感集《于崖窗前,晨》(Am Felsfenster, morgens,1987)中的笔记显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创作童话《消逝》(Die Abwesenheit,1987)期间,他曾认真钻研过《道德经》和《南华经》。事实上,汉德克在萨尔茨堡期间创作的诸多作品中几乎都可见老庄哲学的影响痕迹。

(作家彼得·汉德克,图片源自网络)
《老子》和《庄子》正是汉德克在萨尔茨堡期间曾细读过的两本道家哲学著作,对汉德克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语世界中对道家经典的专业研究大约在1912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1910年出版了《庄子之语与喻》(Die Reden und Gleichnisse des Tschuang-Tse),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于1911年翻译了《道德经:老子有关意义与生命的书》(Tao-te-king. 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和《庄子:南华真经》(Dschuang Dsi. Das wahre Buch vom südlichen Blütenland)。卫礼贤翻译的《老子》和《庄子》是德语世界影响最为深广的译本,改变了过去由赫尔德(J. G. Herder)和耶稣会主导的、对以道家哲学为代表的“欠发达的”“(与基督教文化相比来说)停滞的”中国文化的偏见。在卫礼贤译本问世之后,德语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逐渐走向客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道家哲学在德语世界开始受到好评,并对黑塞、德布林、布莱希特等重要德语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子》和《庄子》在德语世界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哲学乃至信仰的经典著作。汉德克八十年代初在萨尔茨堡期间阅读的《道德经》和《南华经》应该也是卫礼贤的译本(《蒙》: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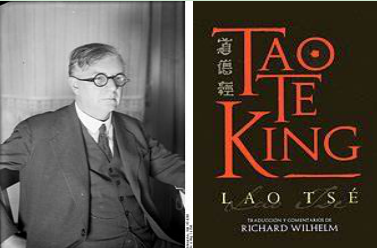
(汉学家卫礼贤及其翻译的《老子》,图片源自网络)


二、汉德克游乎“无何有之宫”
汉德克曾在《于崖窗前,晨》中记录,在创作童话《消逝》期间,他曾认真阅读过《道德经》和《南华经》。这部童话的标题“Abwesenheit”可以追溯到《庄子·杂篇·则阳第二十五》篇末少知与大公调对话的最后部分,这一部分讨论了宇宙论的一些问题如万物起源问题。其中“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是季真的主张,他认为万物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并不是起源于某种力量的作为。因此,卫礼贤将“莫为”译为“die Abwesenheit einer solchen Ursache als Ursprung der Welt”(“万物起源之原因的缺席/不存在”)。有学者认为,汉德克以卫译“莫为”中的“Abwesenheit”一词来命名自己这部童话,有可能是受到当时正在阅读的《南华经》的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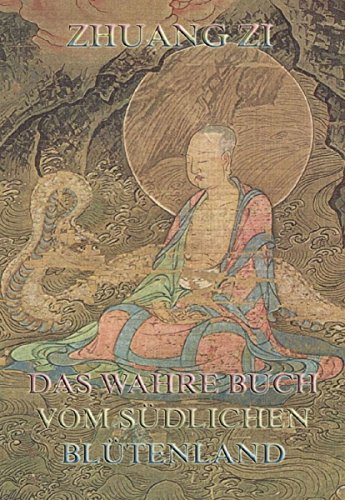
(卫礼贤翻译的《庄子:南华真经》,图片源自亚马逊官网)


三、“吾丧我”:《消逝》中的道家思想
童话《消逝》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四位主人公——长者、女子、士兵和赌徒——似乎无缘无故逃离了各自的日常生活,聚在一间火车包厢里,开始了一次时间和目的地都不确定的旅行。这是一列不同寻常的火车,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特殊人群,他们中有流亡者也有朝圣者”(Abwesenheit:71)。途中火车行经多站,几乎不再有人上车,却不断有人下车。四位主角继续前进,虽然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并不明确,但随着火车的行进,越来越清楚的是,此行是一次带有修道性质的追寻之旅,就像书中那位长者所吟唱的:他相信,在那里——“虚空之基”(Abwesenheit:83)——将见到万物回归自我。然而,“那里”却并非神圣之地,亦非通都大邑,它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毫无名气”,甚至只有一个特征:“它本身空无所有,其周围却到处都有点什么。”(Abwesenheit:82)这种描述让人不难联想到老子中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无何有之乡”,在长者看来,那就是“虚空的世外桃源”(Abwesenheit:82)。汉德克在长者对“世外桃源”的浅吟低唱中,再次引用了《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中的“名者,实之宾也”,来赞美他所信仰的那个最爱的小地方:“Der Name ist der Gast der Wirklichkeit!”(Abwesenheit:81)如前所述,这句话也出现在汉德克于1987年3月在萨尔茨堡书房“崖窗”前记录的随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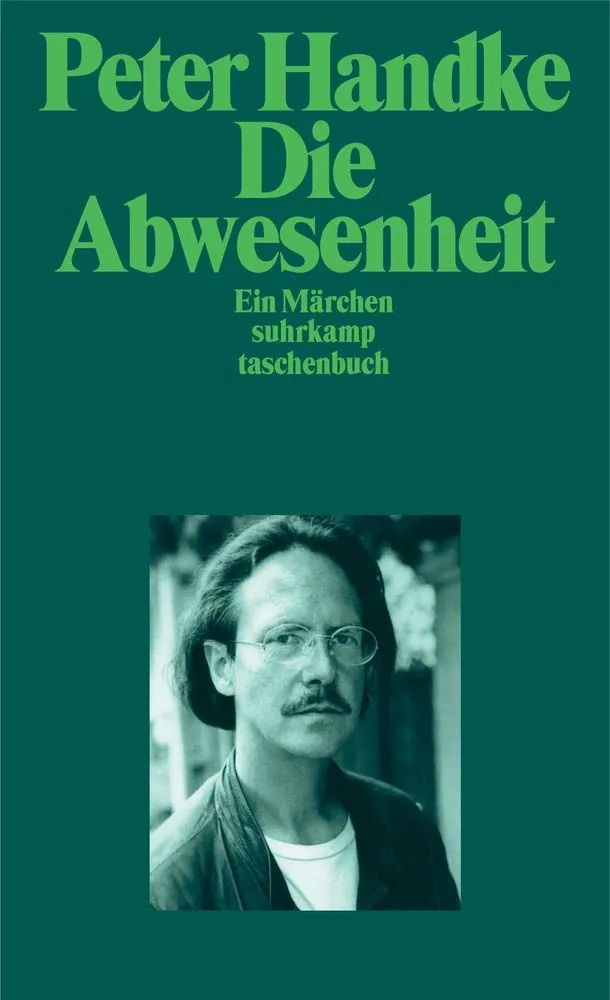
(彼得·汉德克的《消逝》,图片源自网络)
《大宗师》主旨在于写真人悟道的境界。所谓“大宗师”就是“宗大道为师”之意。“悟道者色若孺子”这一段出自《大宗师》第四章,是借南伯子葵与女偊的对话,讲述学道的过程(《庄》:197)。南伯子葵是庄子笔下的隐士,女偊为得道之士。南伯子葵问女偊说:“你的年龄很大了,却面如孩童,这是为何?”女偊答道:“我闻道了。”(《庄》:220)汉德克在这里借用了庄子的意象和思想,将长者写成如得道的女偊一般“色若孺子”,兼有长者的智慧与孺子的天真,合二为一,方可得道。汉德克在其创作于同一时期的随感集《重温之想象》中也有可资类比的笔记:“我是如何日日衰老,然后转天又变年少(然后再衰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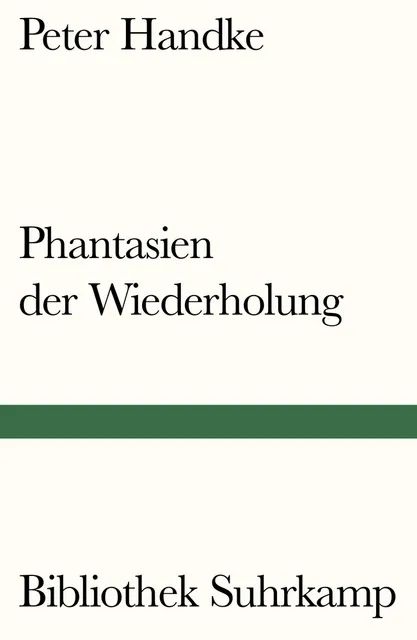
(随感集《重温之想象》,图片源自网络)


四、“大归”与“复”:汉德克的“重温”美学
按照张晖的解释,“道”在大千世界中将自身显示为按照“大-逝-远-反(返)”模式进行的循环运动和变化迁转。第一阶段“大”为整体性尚存、万物尚未彼此分离的理想状态;第二阶段“逝”是整体性不断消逝、逐步分化的过程;第三阶段“远”可被视为“多元化进程的遁点/消失点”或“碎片化的急遽升级”;最末阶段“反/返”则成为了达致“生命圆极”的“骤变”或者说“逆转/突变”的转折点(《蒙》:46)。但是,此“返”并非是一种“怀古情结”(Nostalgie)或“倒退心理”(Atavismus),而是体现了老庄哲学的二律背反与汉德克的辩证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进步’恰恰就是‘退步’,或者至少应被视为倒退的诱因。通过这样一种向前发展,人们修得了返璞归真、万有归一的正果。巨涡般的世界历史亦如是旋转运动,如螺旋而非如封闭的圆周。”(《蒙》: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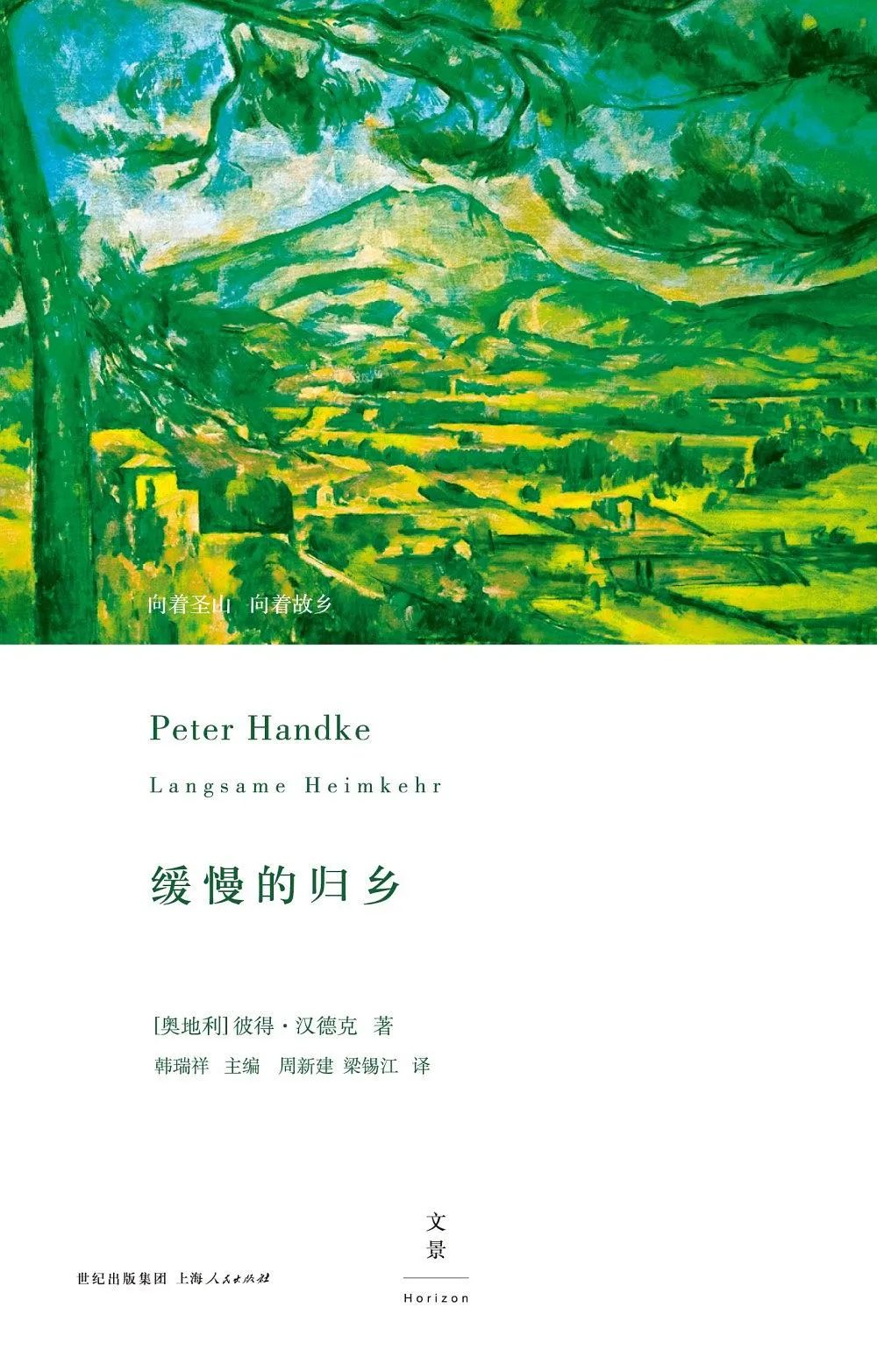
(《缓慢的归乡》中译本,图片源自豆瓣)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2期“专题·诺贝尔文学奖”,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
往期阅读

扫码关注我们
投稿邮箱
wgwxdt@aliyun.com
 | 社科期刊网 |
扫码关注我们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新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