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研究 | 似真还假的“回忆录”:华莱士遗作《苍白之王》的虚构性与非虚构性
似真还假的“回忆录”:华莱士遗作《苍白之王》的虚构性与非虚构性

万晓蒙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叙事学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小说,现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习。

内容提要 《苍白之王》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对虚构自传体叙述的成功尝试。在作品中,他巧妙运用虚构性与非虚构性的修辞叙事,展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税局税务审查官经历的厌倦、自私、冷漠等精神危机。非虚构性的“回忆录”强调历史性的传递,令读者置身历史,聚焦现实;以夸张和超自然现象为主的虚构性手法又使故事从现实脱离,意在展现现代生活中一直存在的人性弱点与社会问题。两种修辞手法融合交错,有效地表现了华莱士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怀和对大众的娓娓劝诫。
关键词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苍白之王》 虚构性 非虚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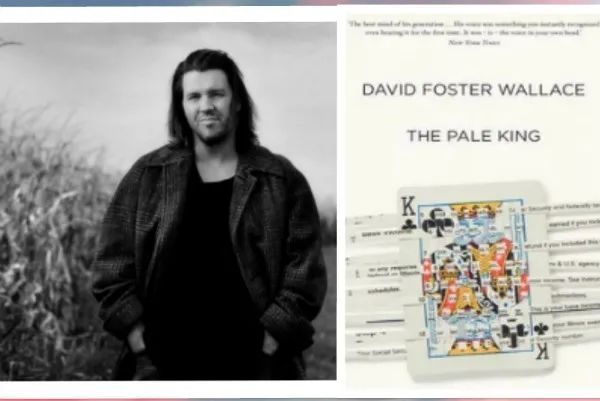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及其《苍白之王》,图片源自网络)

一、作为虚构性与非虚构性混合体的《苍白之王》
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将虚构性概述为“虚构世界的发明,这种发明以文本、戏剧(表演)或视觉(和视听)的形式呈现,目的是给受众以娱乐消遣、智力刺激和(道德)教化”。修辞叙事学家理查德·沃尔什将叙事虚构性(fictionality)定义为“一种用来沟通价值、衡量选择、传递信念与意见的载体”,强调其作为“载体”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作用。詹姆斯·费伦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虚构性话语与非虚构性话语,他认为,前者是作家主动构建的现实替代物,目的是让观众察觉到自身从现实的出离,后者则受现实约束,离不开对事实的传达。叙事虚构性与非虚构性并没有本体论上的明确界定或区分,二者的最大差异体现在实际的沟通目的上。因此,(非)虚构性话语及相关理论能提供独特的视角,令读者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作者与读者沟通的方法,是批评实践的得力工具。
费伦在阐释叙事虚构性时特意强调,“有时(虚构性话语的)使用者会故意模糊虚构性与非虚构性的边界”,华莱士的《苍白之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部作品是华莱士唯一一部回顾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体是虚构的作者“大卫·华莱士”编纂的关于国税局的回忆录。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里根执政时期,国税局变得“不像简单的政府部门,而更像利益驱使的生意,对社会公平渐失关注”。这位“华莱士”在离职后意图将在职时收集的有关国税局的资料不加修饰地展示给读者,其个人叙述中穿插了采访稿、对话记录、独白、新闻稿等多种文本,作者在其中娴熟地切换虚构与非虚构话语,实现不同的沟通目的。正如布莱恩·麦克黑尔所言:“《苍白之王》某种程度上是一部伪回忆录……(华莱士)竭力断言其真实性,但又狡猾地破坏读者的信任。”这部小说是非虚构与虚构话语的“混合体”:非虚构话语主要表现为非虚构文体和叙述者的自传式叙述,诚恳地将“华莱士”所掌握的事实和盘托出;虚构性话语则更多体现在超现实的叙述形式中,突出回忆录的故事性和艺术性。

(美国国家税务局,图片源自网络)
史蒂芬·伯恩认为,“批评华莱士留下的文字并不是要否认迈克尔·皮奇为读者整合其内容的工作,而是要认识到这部小说的混合性特质,并且去思考我们要以何种方法从其雏形衍生出更深刻的洞察”。从修辞叙事的视角来看,非虚构性与虚构性叙事手法的交错使用正是其混合性特质的重要方面。作为非虚构话语的接收者,读者可以切身体会小说叙述者“华莱士”构筑的“真实”历史,这种“代入感”让读者进入历史,感受历史,对相关社会问题进行历时性反思。但当虚构性话语出现造成“出离感”,读者就进入旁观的“上帝视角”,以此为鉴,思考其隐喻含义,分析出真实作者华莱士所传达的警告和劝诫。虚实感受的切换带给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也折射出作者的两层沟通意图:既要关注真实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的遭遇,更要跳出历史,举一反三,认识到跨时代普遍的人性弱点。

二、非虚构的“回忆录”与“自传”
初读《苍白之王》,非虚构文体传达的“真实感”扑面而来:1980年11月17日的新闻报道(“国税局一工作人员四日前死亡”)、国税局的内部简报、“国税局人事部十条法则”,还有言辞不加修饰的梦境复述、没有任何指示词的对话转写稿,这些非虚构特征明显的叙述穿插在“华莱士”的回忆录中,如同散佚的档案,高度模仿了人为记录的随意性和不完整性。
让-马里·舍费尔认为,非虚构文体是作者用来传达历史性和真实性的一种“事实性叙事”,这种“事实性叙事”区别于虚构叙事的一大特点就是“主张指涉性的真实”,意在指涉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非虚构的话语“打开一个内部场景,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品味把玩’变为‘息息相关’”,它意在映射读者所在的世界里真实发生的事情,比虚构性话语更具影响力和批判性。“华莱士”的非虚构叙述正是希望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八十年代国税局中西地区税务审查员病态的精神状态与人际关系。比如第二十三章令人不寒而栗的梦境转述:
我看到一排排被扭曲、缩小的面孔,带着模糊的表情,如远处的火光闪烁。我看到成年人的平静的无望,也看到难以言表的遗憾。状态较好的一两个人面露迷惘。其他很多人面无表情,像硬币上的头像。在他们周围,办公室的雇员们为无穷尽的琐事而忙碌,……这个梦里,我的灵魂教会我厌倦。那时我不知道那是厌倦,我当时很担心,很焦虑。(Pale:253)
这一章是某位心理疾病患者的童年回忆,匿名的独白与前后文毫无联系,显然作者不想让读者把这部分“作为小说来体验”。细致的场景复现和情感描述令读者更多地接收到“真实世界的信念”,而主动去探索让不谙世事的孩子产生此类梦境和感受的原因。讲述者回忆,自己的父亲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高强度的工作,鲜少参与家庭活动,家庭关系名存实亡。想到自己未来可能重演父亲的角色,“我感受到的厌倦乏味无限激增,这种情绪甚至已经超出厌倦,变成了担心”,但我又“记不起在担心什么”(Pale:253)。儿童的认知有限,既缺少社会经历,又无能力进行系统的思考。童年记忆的部分缺失也是非虚构性话语与读者互动的一种方法,读者需调用自身经验,从现实角度为故事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补充。叙述中,随着年龄增长,“我”出现了心理障碍,最终为社会所同化:“当我开始为自己在家庭话剧中的角色负责时,父母的话、父母的感受都变成我自己的了。”(Pale:254)上一代经历的焦虑和厌倦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孩子,而毫无变化的社会环境终会将孩子们变成上一代的复制品;盲目投入工作导致的漫无目的的生活态度腐蚀着每一代人的生活,形成恶性循环。
《苍白之王》中多种非虚构文体的采用皆有与上两例类似的效果,借用读者对纪实性文体的信任和接受来传达“客观史实”,通过读者对其历史性与真实性的认同,拉近故事与读者的距离,叙述者仿佛只是按下了几十年前的录影带的播放按钮,以“史实”与读者进行诚恳的沟通。多种非虚构文体看似随意拼凑,对国税局无一字微词,但都间接指向美国官僚主义。政府部门像对待机器一样压榨职员,“上级”占绝对优势,“下级”无力反抗,以致整个社会对压力之下的人性扭曲习以为常。在这部“录影带”里,人物的自我缺失,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冷淡一代代地传了下来。轻描淡写、毫无感情的非虚构叙述与叙述者意图反映的严重社会问题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促使读者去发现叙述者对当时政府的控诉和对人类本性的呼唤。同时,小说中提及了此类社会问题的遗传性,也促使读者进行历时性的反思,考察其所处的尊重人性、人权至上的时代是否依然有人忍受着工作压力对人性的腐蚀,在厌倦无望中受到心灵与身体的双重折磨,进而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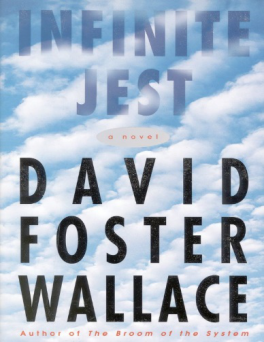
(《无尽玩笑》,图片源自网络)
除了非虚构性叙述之外,华莱士还设置了一个突出的叙述者:前国税局审查官“大卫·华莱士”,他自称是回忆录的收集者和《苍白之王》这部作品的作者,还特意注明这个省略中间名字的“大卫·华莱士”是他的笔名(Pale:295),诱导读者相信叙述者真的就是创作了《无尽玩笑》和其他作品的作者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本人。这种以作者声音进行的自传式叙述在后现代小说作品中并不鲜见,其效果就是“让读者很难断定叙述者只是一个虚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作者”。读者在阅读这类文本时即使“知道”讲话的“我”是虚构的,也倾向于给文本的叙述声音加一个熟悉的身份,以达到共情效果。而且,在《苍白之王》中,叙述者“华莱士”的自白在整部作品中占据重要部分,内容包含其自身经历、国税局见闻,甚至社保号码和家庭住址等详细隐私信息,突出表现了一个丰满、立体的叙述者形象。因此,“华莱士”以读者熟知的华莱士的身份作长篇独白,能令读者感觉亲近可信,从而接受这部分的非虚构性。相比非虚构性叙述这种从纪实性文体本身的接受模式来构建的非虚构话语,来自叙述者的作者自述是引导读者在感情上产生共鸣的另一种非虚构话语。其中,被刻意安排在书的中间,以“作者在这里”(Pale:66)开头的所谓“序言”颇有深意:
首先,请翻回去看这本书的法律免责声明,……开头写着:“本书所有人物、事件纯属虚构”……根据免责声明定义,序言是虚构的,也就是说,序言可以说假话,因为它在免责声明确立的范围内,受特殊法律保护。我需要这种保护来告诉你,下面所讲的,在现实中真实无妄,绝非虚构。(Pale:66—67)
这位作者似乎有些难言之隐,需要法律保护才敢打着“虚构”的幌子讲出真相。进一步的坦白和揭露隐藏在这一章的大段注释里:“因为出版商最后一刻的谨慎决断,这篇序言现在被后移七十九页,放到文本中间了。”(Pale:67)出版商为何如此小心翼翼呢?在下一条注释里似乎能找到更多答案:“本书出版商,作为一间注册的美国公司,对于任何对国税局表示轻蔑的苗头或‘教唆’作者违反财政部员工保密协议的可能都谨小慎微,原因显而易见。”(Pale:68)国税局是美国最大的官僚机构,掌握着每个美国人的社保号码和银行账号,有权对任何人提出上诉,令他们自身难保。《苍白之王》中的“华莱士”和出版商意图揭露国税局内部的种种异常,但又受制于国税局的权力而如履薄冰。“华莱士”迂回的叙述行为是作家华莱士构筑非虚构性现实的另一个方法。他对官僚主义压力下人物心理的洞察和再现,一次次冲击着读者的认知,几可以假乱真。史蒂芬·泰勒·马尔什指出,华莱士处理复杂的自传叙事结构时,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叙述其他人需要自我牺牲”。小说中的“华莱士”不仅牺牲了展示自我的空间,也将自己的人身安全置于险境,“为了别人,伤害自己,来使读者认识到《苍白之王》中多个人物无限的内在性格和多变的经历”。“华莱士”几次跳出来对话读者,以假乱真的身份和有血有肉的情感表达让读者在他的导引下从文中“华莱士”所在的故事世界跨越到读者所生活的真实世界,二者的界线逐渐模糊,仿佛小说中的世界真实存在。
那么,这位“华莱士”不惜自我牺牲都要向读者传达的是什么呢?从两处“作者在这里”的叙述来看,他想说的是自己在回忆录作者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税局工作人员双重身份下经历的社会和人性问题。“华莱士”在和读者直接沟通时,又是假名又是免责声明,可谓处处留心,时时在意。但他还是忍不住直接痛斥国税局的官僚主义:“我对他们(官僚机构)又恨又怕,将他们看作巨大的、毫无人情的折磨人的机器。”(Pale:260)直白地道出了对国税局等政府部门凭借职权横行霸道的暴行的愤怒。甚至连这句话也带着一条注释:“记住,这句话只说在那个时代末尾,……现在已经和《摩登原始人》动画一样早就过时了。”(Pale:260)这句话真的“过时”了吗?或者这只是“华莱士”避免被国税局找到把柄的手段?其含义不言自明。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华莱士”一方面想揭露真相,一方面又不想自身受到牵连和报复。其内心多个声音的相互作用都原封不动地展现给了读者,想宣扬正义又怕自身难保,只能采取折衷的委婉手段,在捍卫伦理规则与保护自身利益的两种动机下权衡斟酌,进退维艰。国税局受政府直接管辖,本应该是最遵守道德与社会规则的地方,然而在“华莱士”笔下,却是一手遮天的吃人机器。审查官们超负荷工作,被压榨的同时还“被沉默”,一旦公开了国税局的劣迹就很可能遭到报复。国税局为了替国家赚取利益无所不为,其行为早就跌破了伦理道德的底线,可以说,这样的官僚机构比冷血的机器还要可怕。
博斯韦尔认为,《苍白之王》的大部分现实描述都带有“共情认同”的效果,读者会主动将自身代入故事,“放弃外部位置,将自己放入叙述世界中”。共情认同所必需的,正是非虚构话语通过模拟人们现实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所带来的真实感。华莱士用叙述者现身说法的方式,映射了从政府机构到个人心态的方方面面。非虚构的话语毫不掩饰地传达了叙述者的失望和矛盾,其内容坦诚平实、贴近生活、深入人心。回忆录的记录部分采用非虚构文体,强调了宏观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事件,而文中的“华莱士”推心置腹的自白则大幅增强了真实性和可信度,用叙述者“真实的”主观看法与读者沟通,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普通大众的痛苦与困惑公诸于世,希望读者关注社会环境可能存在的弊病,也更希望读者能意识到人群中现在可能依然存在的价值观扭曲与精神危机。

三、假“回忆录”与假“作者”的虚构性
尽管虚构的“华莱士”在《苍白之王》中用尽各种方法证明叙述的真实性,但从现实来看,作家华莱士从未在国税局任职,该作品的叙事虚构本质无可置疑。而且,华莱士所采用的虚构性话语也足以使读者坚信这部作品只是虚构小说。《苍白之王》中的虚构性话语穿插于非虚构话语之间,产生了丰富的沟通效果,作者以非虚构话语真诚坦白,与读者推心置腹之余,又加以虚构性话语“表演”种种夸张离奇的场景,令读者在欣赏其独特“文采”之余有所反思。就虚构性话语来看,文中不时会出现后现代风格的怪异叙述手法或者与客观事实相悖的事件,制造读者的“出离感”,表面上增加了阅读乐趣,但根本上仍是为其道德主题服务。比如第二十五章中国税局办公室的场景,由“克里斯·弗格翻了一页。霍华德·卡德维尔翻了一页。肯·瓦克斯翻了一页”(Pale:310—311)等冗余的动作描述组成,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夸张重现。当是时,国税局大量工作依然靠人工完成,纳税申报单都是用麻袋装,审查官们做着大量重复的工作。华莱士近乎笨拙的无意义细节堆砌,向读者传达了这项工作的枯燥乏味。重复的动作和冗长无意义的情节颇具后现代美学特色,令读者不明就里,自然地切换到虚构接收者的角度,完全置身事外去对比历史与虚构,进入一种“远程交际模式”,“暂时不受自我指涉和实际情况的束缚”。在此,读者对故事中国税局审查官们的“枯燥”(dullness)和麻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就不难想象审查官们的“像被榨干一般灰白的脸”(Pale:103),“像烧煤工人被熔炉熏到接近失明的眼睛”(Pale:104)。根据“华莱士”的说法,“国税局是首先意识到(迟钝、麻木)这些特质的好处的政府部门,他们可以借此避开公众抗议和政治反对派,令人费解的愚钝是比保密更有效的挡箭牌”(Pale:83)。枯燥而繁重的工作令审查官们逐渐失去理性判断,失去反抗的意识,沦为被美国政府操纵的机器,陷入精神上的“存在主义生存危机”。

(《摩登时代》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1985年,国税局开始以计算机代替人工审核,类似的情景早已不复存在。华莱士以后现代叙述形式构筑的虚构性叙事,更大程度上隐喻了从八十年代到现在都隐伏在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现实中的厌倦可能并不致命,不为人所关注,但华莱士将这种精神危机夸大,用看似荒唐的叙述突出这种消极的体验,其意义已超出模仿真实,更多地是要影射真实事件所隐含的精神危机,达到超越历史语境的警示作用。《苍白之王》隐喻的精神危机并非只在为官僚机构工作时产生,二十一世纪的很多生活场景中都能见到类似的问题。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人们每天忙于处理来自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介的各种类型的信息,不停地做出筛选和判断,恰恰和国税局审查官们不停“翻页”审查的状态有几分相似,疲于处理信息时产生类似的消极厌倦心态也不足为奇。但不同的是,信息时代人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远超过审查官。人们在信息的海洋中疲于应对,为厌倦感、空虚感所折磨,失去了应有的活力。正是出于对此情形的担忧,华莱士才会以史为鉴,给现代读者一个委婉的提示,希望大家主动寻求解决方法来适应和改善生活中的厌倦,重构完整的自我。
《苍白之王》还讲述了一些离奇古怪的事件,这些虚构性叙述将人性的缺点放大、突出,给读者以感知上的刺激。比如徘徊在审查官办公室的两位特别的“幽灵”,其中一位便是在工位上死去四天才被发现的布卢姆奎斯特。有趣的是,“他不打扰你,也不会用令人发毛的眼光盯着你。你会有种感觉,他只是喜欢呆在那。……多数审查官接受甚至喜欢布卢姆奎斯特的来访”(Pale:316)。枯燥的工作令这位尽职尽责的审查官失去了完整的自我,他不仅在自己的工位上工作至死,甚至死后都离不开这个地方,灵魂只能回到原来的办公室,仿佛还想继续生前的工作。布卢姆奎斯特令人感伤,更令人感慨:国税局的工作剥夺了他最珍贵的理智与感情,到死都未能解脱。布卢姆奎斯特的幽灵并非个例,故事中婴儿的反常状态更令人震惊。一位审查官在描述其小组经理曼斯哈特先生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时反复重复“凶狠”(fierce)一词:“它表情凶狠,行为凶狠,连盯着奶瓶或奶嘴的眼神也是凶狠、富有侵略性而令人恐惧的。”(Pale:387)令人震惊的是,它还学会了小组经理的官腔:“(它)清了清嗓子引起我的注意,仿佛是警告我工作不要走神一样,然后凶狠地盯着我,说:‘那么——’……我不由自主地像回复所有上级领导那样,说:‘不好意思,什么事?’”(Pale:393)
本该天真无邪的婴儿成为父亲曼斯哈特言行的映射,令人畏惧,这也侧面反映出曼斯哈特在高压之下扭曲的生活状态。国税局的工作销蚀了他的同情心,只知道通过“凶狠”的态度来迫使员工机械地工作,使双方都更加痛苦。讲述者“我”的条件反射更为讽刺:婴儿本不足为惧,“我”却不经思考就为其古怪言行所控制,仿佛已形成机械的条件反射。“机械化”不仅限制了审查官的工作能力,还令他们的思维模式化、简单化,以至于想机械地照流程处理生活中所有问题。或者说,税务审查工作占用了他们过多的精力,对于生活中的其他事,他们只想迅速地用最少的精力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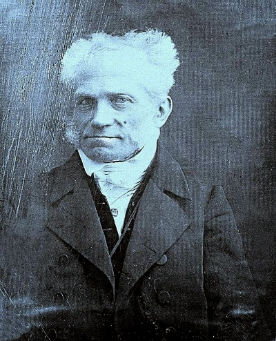
(亚瑟·叔本华,图片源自网络)
根据叔本华的定义来看,《苍白之王》所表现的大量强制工作是现代传统中厌倦产生的基础。小说中另一个极端人物,对人“病态地慷慨”的国税局员工斯泰赛克似乎比别人看得更透彻:“如果你对厌倦免疫,那真的无所不能。”(Pale:438)这恐怕也是华莱士使用虚构性话语时想传达的:现代社会有太多因素使人厌倦,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难以回避,然而,在厌倦中安于现状不作为,只会让情况更糟。他虚构的这些奇闻异事,成功地让读者“认识到话语使用者从现实范围的脱离”。修辞叙事学认为小说会激发读者的两种意识,读者首先会将“自身投射到故事世界观察者的位置”,而且“不仅知晓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出来的,也意识到它们被虚构出来必有其原因”。在领略了真实的“回忆录”之余,读者也会逐渐发现,《苍白之王》虚构的怪异事件不只是影射八十年代的史实,也试图与当下人们厌倦生活、懒于思考的现实产生共鸣。因为人们不仅在处理过载的信息时疲于应对,更难在各种信息传达的不同价值观冲击中站稳脚跟。很多人因为厌倦而拒绝思考,遇到问题只知道寻求简单的解决方法。他们或盲目从众,或固守传统惯例,很容易在不断寻找可依靠的参照物中迷失自我,最终成为没有独立思考的“机器”。华莱士的虚构性话语表面荒唐怪异,实则是在以史为鉴,将国税局的故事作为范例与读者沟通并加以警告。带有魔幻色彩的事件不再只对特定历史阶段有意义,其虚构性令读者的注意力从叙述情节的“史实”转移到其符号性内涵——华莱士利用虚构性修辞手法所表达的机械化、超负荷的工作方式以及人们在社会环境影响下伦理价值扭曲、人性异化的现象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时期均有发生。二十一世纪的读者在庆幸这些夸张的事情没有真正发生在自己的世界之余,应从更客观的视角看待《苍白之王》虚构的怪异事件,进而举一反三,反思自身是否经历着相似的厌倦和压力,是否能有效地“对厌倦免疫”,避免自身沦为冷血的“机器”。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1期“作家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
往期阅读


扫码关注我们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投稿邮箱
wgwxdt@aliyun.com



社科期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