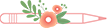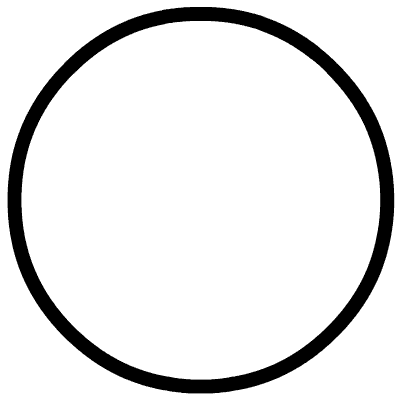重读 | 论吉拉尔的俄狄浦斯阐述

杨俊杰 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最近发表的论文有《博尔赫斯的雨村:读小径分岔的花园》(《读书》2020年第3期)等。

内容提要 1966年的“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国际会议是近数十年理论风潮的重要起点,德里达的参会报告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后结构思潮的开端。本文试以吉拉尔的参会报告为中心,指出吉拉尔虽与德里达不乏相通之处,但当时已然走在一条独特的道路上,他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悲剧当中读解出的“内介绍”和“替罪羊”机制,便体现了他与解构主义迥然不同的旨趣。
关键词 吉拉尔 俄狄浦斯 法国理论 内介绍 替罪羊


德国耶拿浪漫派赢得世界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国学界的关注与推崇,据说斯塔尔夫人的介绍居功至伟。类似地,法国后现代理论家们赢得世界声誉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美国学界的认可与推广,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科中心于1966年10月举办的“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国际会议尤其功不可没。德里达在会上发表了《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这一日后影响巨大的著名报告标志着后结构或曰解构思想的隆重登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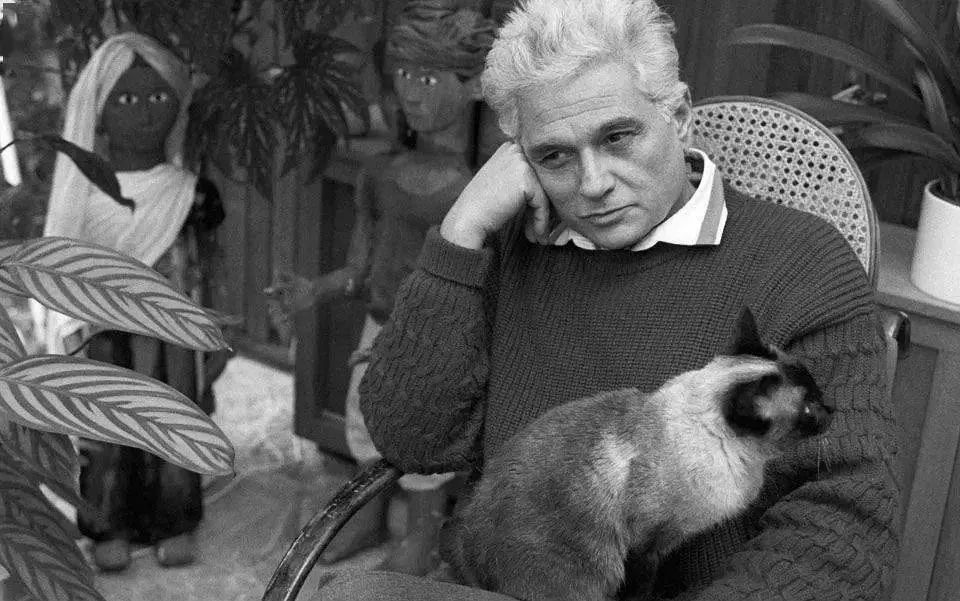
(德里达,图片源自百度)
2016年,以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为契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科中心与巴黎第十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合作举办了纪念活动,相关论文不久后合编成霍普金斯大学的《现代语言丛刊》(Modern Language Notes)2019年12月的专刊。德里达的报告是整个纪念活动的焦点,其他与会人物也多半因德里达而被关注。比如有研究者以“差异”概念为中心,以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的《暴力与神圣》(1972)为基础,对吉拉尔与德里达的相通之处进行解析。本文则直接返回1966年那场会议,重读吉拉尔那篇对俄狄浦斯悲剧进行阐述的报告,尝试指出吉拉尔当时虽与德里达颇多相通,但其实根底处旨趣迥异。吉拉尔的俄狄浦斯解读,自那时起便已有其深长意味。

吉拉尔参会报告的题目是《忒瑞西阿斯和批评家》,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进行了研讨。这一悲剧故事简单说来就是追查者最终发现自己是凶手。吉拉尔也是如此看待这一悲剧,可采用的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在俄狄浦斯看来,他所追查的凶手一定是“别人”,必定不是“自己”——为对“在俄狄浦斯看来”表示强调,吉拉尔的用语是“他的别人”(his Other,也可译为他的“他者”)、“他的自己”(his Self)。吉拉尔认为,俄狄浦斯最初把自己设想成有能力进行中立、客观、科学、理性判断的人,最终却认识到自己并非如此。他所以为的那位“他的别人”,原来是真正的“他的自己”。原先那个客观的“自己”,不过是主观想象出来的“自己”而已。同时,吉拉尔又从盲人先知忒瑞西阿斯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事件,忒瑞西阿斯早已捕捉到了俄狄浦斯的“真相”,早知道俄狄浦斯绝没有“外在于”罪行。对忒瑞西阿斯来说,俄狄浦斯是“他以为他自己不会是的那个人”,他不是“他以为他自己是的那个人”。忒瑞西阿斯在与俄狄浦斯冲突时指出,俄狄浦斯的“真实的存在”与俄狄浦斯“关于他自己的看法”存在着差别、乃至对立。
对俄狄浦斯来说,凶手应当受到惩罚。他咒骂凶手将过上悲惨不幸的生活,未曾想这些指向别人的咒骂竟落到自己身上。在与忒瑞西阿斯出现冲突时,俄狄浦斯又咒骂盲人先知眼瞎、没头脑,咒骂最终也落在他自己身上。用吉拉尔的话来说,这些咒骂的语言来自俄狄浦斯所设想的“他的自己”,指向其所设想的“他的别人”,指向某位“别人”。吉拉尔又结合语言学的术语进行解析,指出俄狄浦斯这些语言作为“能指”,与其观念(设想)当中的所指原本形成一个结构。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意味着这些语言失去效力。在与观念性、想象性的“所指”(即“别人”)脱离以后,这些语言依旧是“能指”,并找到新的所指(即俄狄浦斯“自己”),形成新的结构。忒瑞西阿斯曾回敬俄狄浦斯说:“你这会骂人的可怜虫,回头大家就会这样回敬你。”按照吉拉尔的思路,忒瑞西阿斯的回敬应被理解为,他作为俄狄浦斯的分析者、“批评家”,已然清楚地看到俄狄浦斯的语言将脱离观念而形成新的结构,并且忒瑞西阿斯的回敬实际已将俄狄浦斯的语言同别的东西(俄狄浦斯本人)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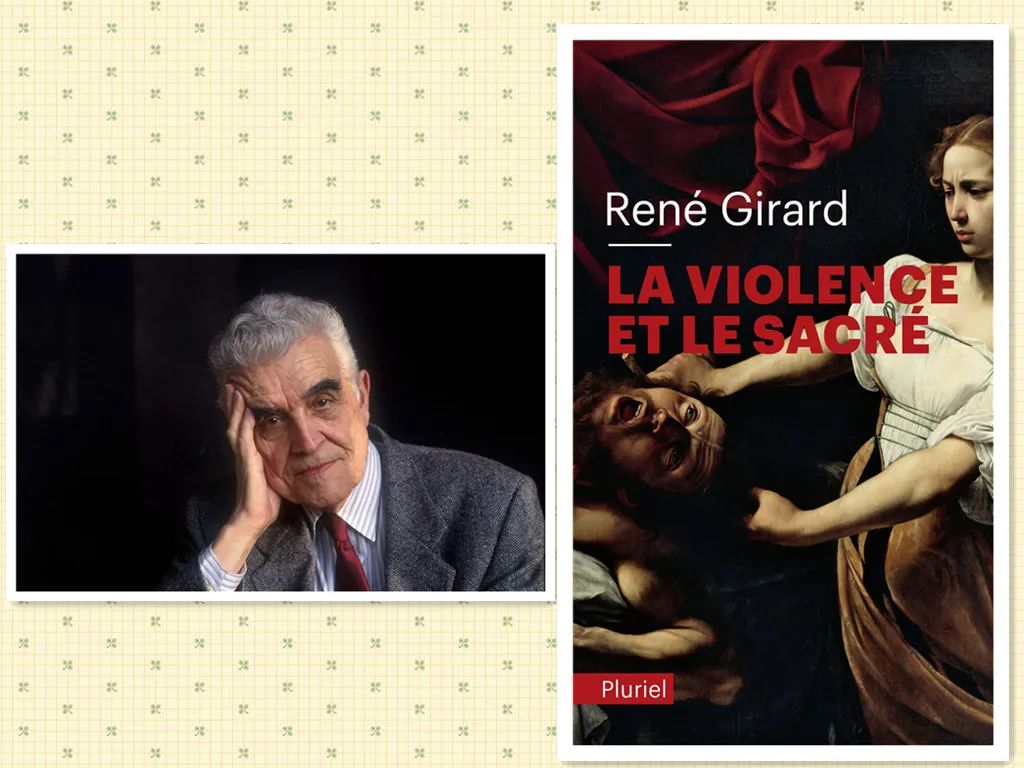
(勒内·吉拉尔与《暴力与神圣》,图片源自Yandex)
需要提到的是,吉拉尔又进一步发挥说,最近几十年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对文学作品采取的分析模式,与忒瑞西阿斯对俄狄浦斯所做的“分析”相通,都主张“语言所指的东西,在说话人清晰的意图抑或隐含的意图的外面、甚至是反面”(“Tiresias”:18)。也就是说,当时正盛行的文学解析都是努力让语言脱离人物、让文本脱离作者,为人物、为文本寻求新的结构。差别仅在于,精神分析理论总往“性欲”方面寻找,社会学理论总往“社会经济”方面寻找。固然林林总总,却都是到文本与作者之间原有结构的“外面”寻找、建立新“结构”。对于这种以寻找新结构为旨趣的“结构化”文学解读模式,吉拉尔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原始结构遭遇轻视,甚至会被移动、破坏,才有了所谓的“结构化”,进而建起新结构。这种使文本与作者脱离的做法,吉拉尔甚至呼之为“虚无主义”(“Tiresias”:19);而他倾向于选择的文本诠释策略,则是界说“作品的统一性”,界说“作者有意设计的组织性”。文本诠释的旨趣在于将作者与文本之间原先存在的结构找回来。吉拉尔既不愿与(法国)那些结构主义式文学分析共舞,又与(美国)破除“意图谬见”的新批评迥异其趣,这无疑是一种并不讨巧的选择。

寻找、确认“作品的统一性”,恰是吉拉尔此前已经在做的工作。他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1961)第一章里以“三角欲望”为关键词,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司汤达的《红与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远的丈夫》等进行阐述,试图整理出一条西方现代小说的发展线索。就《堂·吉诃德》而言,我们通常都把堂·吉诃德看成理想主义者,把桑丘看成现实主义者。在吉拉尔看来,这种区分如此重视两位人物之间的差异,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并未捉住问题的实质。更值得留意的事情其实是两者的相似性。堂·吉诃德追寻骑士道,是由于他把骑士小说里的完美骑士阿马迪斯视为榜样,阿马迪斯所做的事就是他要做的事。用吉拉尔的话来说,堂·吉诃德想做的事及其欲望的形成,是阿马迪斯“介绍”给他的。同样地,桑丘愿意追随堂·吉诃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向往海岛总督职位,这一欲望的形成又恰来自堂·吉诃德的“介绍”。整部《堂·吉诃德》情节或有离奇、拼接的嫌疑,但两位主要人物守持着各自那份因“被介绍”而形成的欲望,总能使小说不失其统一性。
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当中,吉拉尔从俄狄浦斯与忒瑞西阿斯之间的冲突里同样找到了“介绍”与“被介绍”的关系。吉拉尔指出,这部悲剧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完满的“相互性”(reciprocity)。通俗地说就是,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彼此彼此”:忒瑞西阿斯回敬给俄狄浦斯的话最终被证实是正确的,俄狄浦斯的确“眼瞎”“没头脑”;然而,俄狄浦斯起先这样骂忒瑞西阿斯同样也是正确的,因为忒瑞西阿斯也是“眼瞎”“没头脑”。正如俄狄浦斯没有料到他本人是罪人一样,忒瑞西阿斯也没有想过他对神谕的解释有可能是错误的,且最终也会被证实是错误的,实际上,“并没有哪位神灵在通过他讲话”(“Tiresias”:20)。在吉拉尔看来,所谓忒瑞西阿斯认为、知道俄狄浦斯就是“污染”,其实只是忒瑞西阿斯自认为、自以为知道。忒瑞西阿斯没有想到,他自以为是真相、被他当成真相的东西并不就是真相,而纯粹来自于他与俄狄浦斯之间“火热的争论与战斗”,来自“欲望相碰时的叠加”(“Tiresias”: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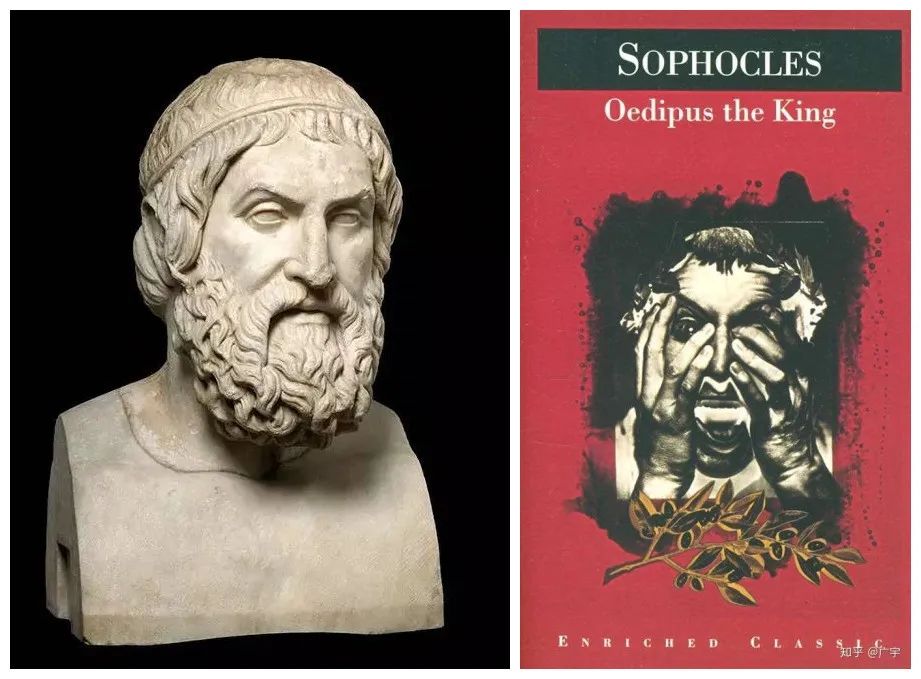
(索福克勒斯与《俄狄浦斯王》,图片源自百度)
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里,“介绍”(médiation)被吉拉尔区分为“外介绍”和“内介绍”。“外介绍”指介绍人(介体,médiateur)系被介绍人(主体,subjet)所望尘莫及、为被介绍人所膜拜的关系。阿马迪斯之于堂·吉诃德、拿破仑之于青年于连,均是如此。“内介绍”则指介绍人、被介绍人间距离较小,被介绍人在接受介绍、指引后对介绍人想做的事产生兴趣,与介绍人构成竞争,从而形成冲突的关系——其中常有想象的成分,却因想象而化为现实。在吉拉尔看来,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对于“内介绍”所引起的冲突都做了精彩刻画。以《红与黑》为例,开篇便有着典型的“内介绍”:德·雷纳尔市长聘请于连当家庭教师,是由于他设想瓦勒诺会聘请于连,而并非完全出于对自己孩子的成长关心。就聘请之事而言,瓦勒诺不啻是德·雷纳尔市长想象出来的介绍人,这位被介绍人在想象中与介绍人激烈竞争、冲突着,而精明的于连老爹仿佛洞若观火,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才向市长先生索价成功。
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之间因“内介绍”而出现的冲突,吉拉尔在此前一篇详论俄狄浦斯的会议论文《一种关于俄狄浦斯王的分析》(1965)里也有过翔实的探讨。吉拉尔指出,以前听得最多的是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有着显著差异:俄狄浦斯是理性推崇者,忒瑞西阿斯是神意占卜者。人们经常以差异为着眼点,佐以个人立场,或欣赏俄狄浦斯,或支持忒瑞西阿斯。用吉拉尔的话来说,在这些解读者眼中俄狄浦斯不是“高于”忒瑞西阿斯,就是“低于”忒瑞西阿斯。但他强调说,文本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并非差异,而是差异的消除。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都想成为神谕的终极解释者,“相互”视对方为竞争者、介绍人——相互“内介绍”的双方,对吉拉尔而言是互为“副本”(double)的。俄狄浦斯回顾斯芬克斯往事,嘲笑忒瑞西阿斯不曾“借鸟的帮助、神的启示”解决问题,最后反倒是他“不懂得鸟语,只凭智慧就破了那谜语,征服了它”。这段话是吉拉尔所倚重的重要文本依据,不啻是将俄狄浦斯与忒瑞西阿斯之间一直以来的矛盾公开化:俄狄浦斯视追查真相为己任,原来不只是出于“王”的职责,携往昔破解斯芬克斯谜语之余威,他已然设想自己最有资格成为智慧化身、真相掌握者(凭借理性)。忒瑞西阿斯被请来对神谕进行解读,他便会视其为对手、且是从前击败过的对手。经吉拉尔如此解读,则有理由认为俄狄浦斯在欢迎忒瑞西阿斯时所说的赞美之词,恐怕另有意味。激烈的冲突,就是在这种相互“内介绍”的机制里发生的。
至于忒瑞西阿斯对神谕的解释为何错误,吉拉尔强调说,神谕是“生命的话”(Verbe de vie),其真实内涵是使人活。然而神谕难懂,于是需要解释。解释者们对神谕进行解释的结果,却总是使人死。拉伊俄斯在得到神谕以后,甘愿残害亲生骨肉,这大概就是他对神谕的解释。克瑞翁在向俄狄浦斯传递神谕内容以后,把赶走“污染”解释为找到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要赶走或者杀死他。而后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又相互指责,认为对方是凶手或与罪行有牵连。所有这些人物如此这般解释神谕,都是“残害”“割裂”“破坏”神谕,把神谕“变成一个死的东西,变成死亡载体”,“就像所罗门断案里的那个小孩,那位恶毒的妇人愿意把他劈成两半”。对吉拉尔而言,忒瑞西阿斯的解释首先错在认定一个具体的人是“他的别人”,认定这位俄狄浦斯就是城邦必须要赶走的“污染”,俄狄浦斯也与忒瑞西阿斯并无二致,他们在对神谕做出解释时出现了同样的错误,又因相互“内介绍”而形成冲突。

辅之以吉拉尔1965年的会议论文、1961年的专著,我们不难看出其1966年的参会报告从“相互性”的角度对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的冲突进行分析并非随意为之。这关联着他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内介绍”机制的揭示,亦关联着他对这部悲剧“作品的统一性”的寻找与确认。但也有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亟需得到解答。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神谕的内容既然是赶走“污染”,吉拉尔如何能够将之界说为“生命的话”?
关于这一点,吉拉尔在1965年发表的期刊文章《从小说经验到俄狄浦斯神话》里提出,宜将《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这两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结合起来理解:过错被揭发、被赶下王位的俄狄浦斯,神奇地成为一位能够带来祝福的人。俄狄浦斯神话故事、悲剧情节的结局便成了俄狄浦斯的祝福,能够带来祝福的俄狄浦斯大概也须被理解为是一位被祝福的俄狄浦斯。如此说来,俄狄浦斯的结局就是祝福与被祝福,正如吉拉尔所说:“那些可怕的预言最终带来的,不是诅咒,而是祝福。”被祝福、又带来祝福的特点唯独在《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当中得到清晰呈现,但对吉拉尔来说,《俄狄浦斯王》便已然包含着这一结局和内涵——之所以既被祝福、又带来祝福,是由于俄狄浦斯终于看到并接受了真相,终于成为一个智慧的“明眼人”(尽管这时已然眼瞎),而这正是《俄狄浦斯王》呈现的结尾。吉拉尔的思路便是:《俄狄浦斯王》所呈现的俄狄浦斯,不单是俄狄浦斯的“倒下”,更是一位因倒下而重获新生的俄狄浦斯。假如把俄狄浦斯的故事一味理解为俄狄浦斯的倒下,则神谕会被看作是一种关于他倒下的预言。倘能看到俄狄浦斯的重生,神谕的内涵必然是关于俄狄浦斯因倒下而重生的。神谕的真实内涵之为“生命的话”,内在逻辑便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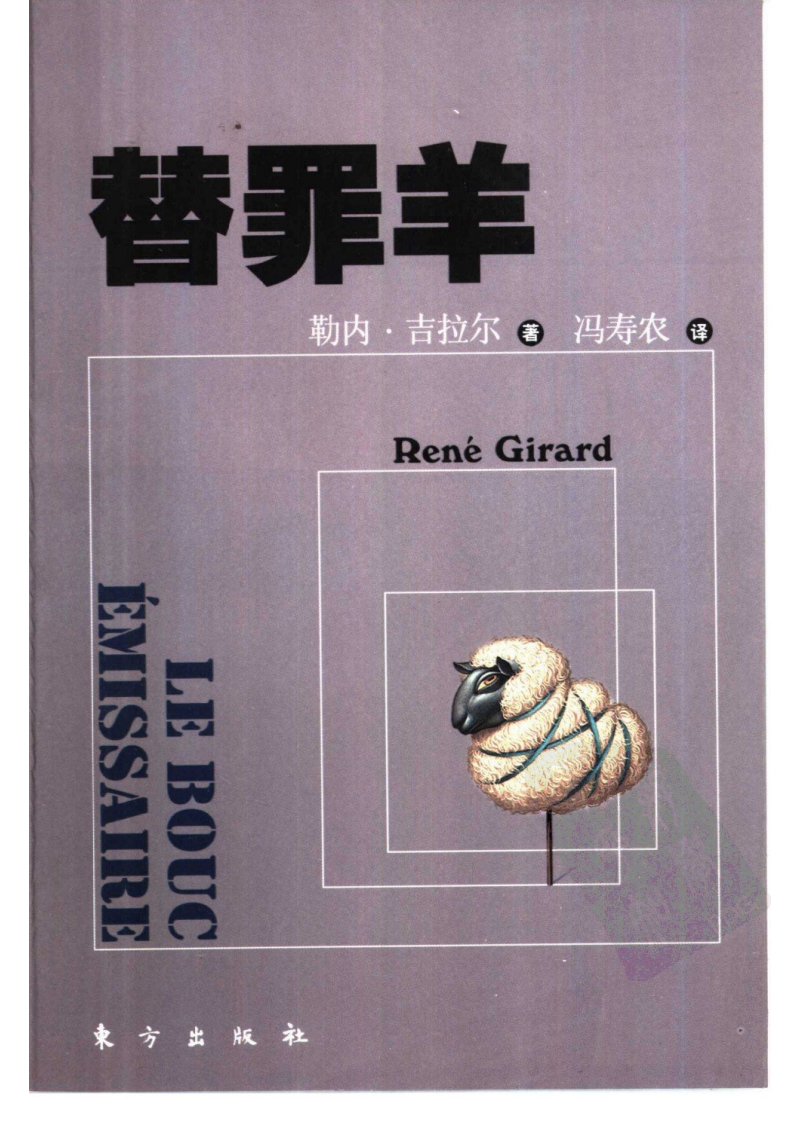
(《替罪羊》,图片源自百度)
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假如神谕的真实内涵确实就像吉拉尔所说那样是“生命的话”,是“使人活”,那么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为何会把神谕解释为一种“使人死”的东西,为何会把赶走“污染”解释为有一个罪犯需要惩罚?若以“内介绍”、竞争抑或“相互性”为依据,推论似乎应该是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都想着要战胜对方,按理当不必把对方说成是罪人,甚至欲置对手于死地。这种“归罪”乃至“致死”的欲望来自何处,还有必要得到进一步说明。吉拉尔对此也有阐述,那便是在《暴力与神圣》(1972)、《替罪羊》(1982)中揭示的最为人称道的“替罪羊”机制。俄狄浦斯的神话以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文本,正是其相关理论阐述的重点内容。吉拉尔1966年的参会报告未曾谈到俄狄浦斯作为替罪羊,自然也未谈到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在“归罪”欲望方面的相似。但其1965年的论文《一种关于俄狄浦斯王的分析》却早已详细谈及于此:神谕本是赶走“污染”,克瑞翁将之解释为捉拿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且未引起任何争议,俄狄浦斯亦不曾往别的方面去想,忒瑞西阿斯进行占卜又同样以之为前提——在吉拉尔看来,进展如此地没有争议,恰恰表明替罪羊机制已深入人心。

吉拉尔从“替罪羊”的角度解读俄狄浦斯悲剧,并非没有争议。就西方古典学界而言,有学者出版著作形成呼应、决心重读索福克勒斯,亦有学者撰文对吉拉尔提出批评。这里无意于替吉拉尔辩护,亦无暇作辨正,而只试图强调以下两点。其一,吉拉尔在1966年之时,已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形成具有一定系统性的阐述。理解吉拉尔的俄狄浦斯阐述,应回到1966年及以前的相关文章。其二,无论吉拉尔的俄狄浦斯阐述是否正确,其自成一说当系无可辩驳。更何况,他的阐述已然自觉地在与当时盛行的(他所理解的)“结构化”文学解读拉开距离,且与那被称作“解构”的德里达式解读有明显相通之处。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对柏拉图哲学及其文本着意强调哲学家与智者之间差异的论说进行了拆解。吉拉尔在阐释俄狄浦斯故事内涵时,也恰在做着同样的工作。俄狄浦斯、忒瑞西阿斯的差异为其所拆解;两者间的界限不只变得模糊,吉拉尔甚至基于“内介绍”和“摹仿性的欲望”把两位人物说成是互为“副本”。其所拆解者,还有俄狄浦斯、克瑞翁的差异。按照吉拉尔的思路,他们同样互为“副本”。两人之间的“竞争”,同样鲜明地体现在他们的冲突里。
这种拆解差异、提撕“同一”的解读手法,并未止步于解读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吉拉尔那里,这也是解读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甚至辨认伟大文学作品的重要手段,《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书便针对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做出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差异的“假象”俯拾皆是,伟大作家对它的拆解也可细心体会。单就俄狄浦斯悲剧的阐述而言,吉拉尔甚至将差异的“假象”问题延展到替罪羊话题。对于寻找、确认替罪羊的个人、群体而言,替罪羊不啻是大写的“别人”。俄狄浦斯矢志寻找“别人”、寻找“他的别人”,却发现“他的别人”不是别人而就是他自己——主体性的谎言被戳破。他找到了智慧,成为智慧的人,代价却是他“认同”自己是替罪羊,而这就意味着认同自己与“大家”存在着差异,认同自己就是大家眼中的“别人”,认同自己是大写的“别人”。但对吉拉尔来说,替罪羊是一种被当成“别人”的东西,而非真切的“别人”。对忒瑞西阿斯和克瑞翁来说,俄狄浦斯实际上并非“别人”,只是他们有意愿要把他设定为“别人”而已,正如俄狄浦斯也曾想要把忒瑞西阿斯、克瑞翁设定为“别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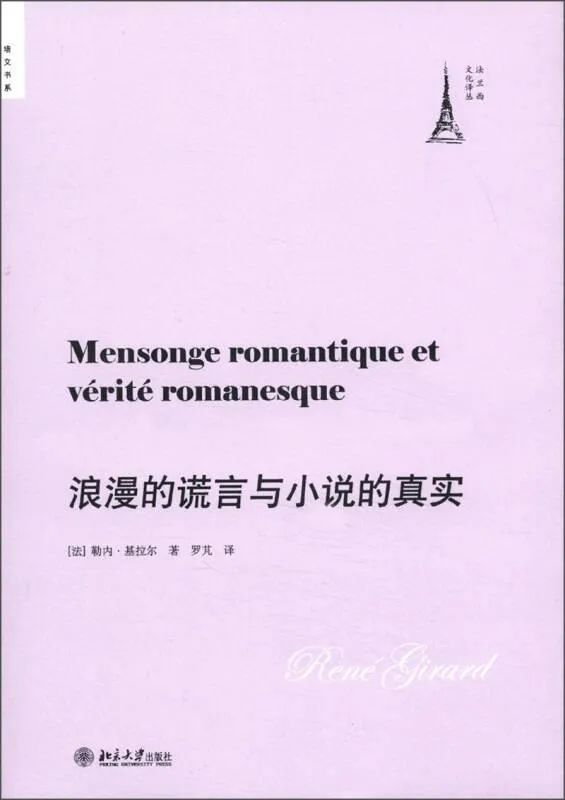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图片源自百度)
自1966年以后,吉拉尔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被理解为走在了更深入地揭示、更敏锐地反思替罪羊机制的探索道路上。《暴力与神圣》对多种原始宗教进行摸索,对更多希腊悲剧作品进行探究,指出替罪羊机制古老而且普遍。《替罪羊》则进一步指出,基督教的新约福音书清晰地记录着耶稣以替罪羊的身份被杀戮。耶稣受难叙事对吉拉尔来说,最要紧的信息是耶稣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耶稣被当作替罪羊,却并不认为自己有罪,这俨然与索福克勒斯笔下俄狄浦斯的悲剧、欧里庇得斯笔下伊菲革尼娅的悲剧形成了鲜明对比。俄狄浦斯、伊菲革尼娅认同自己是替罪羊,他们相信城邦、军队的灾难是由于他们有过错,相信只要他们作为替罪羊被惩罚,灾难就能消除。对吉拉尔而言,这意味着这些悲剧仍有着神话的底色,不曾揭露替罪羊机制的粗暴与残酷,而“我们不能再将福音书当作另一种神话,因为它照明了神话”。吉拉尔还指出,耶稣固然揭穿了迫害者的面相、揭示出迫害的真相,固然坚信自己的无辜,却依然主张宽恕、原谅;真相与宽恕之间如此联结,与索福克勒斯笔下克瑞翁、忒瑞西阿斯抑或俄狄浦斯以真相的名义、以被误读的神谕内涵为依据而进行迫害形成了对比。
简言之,吉拉尔1966年那篇措辞较为隐晦的会议报告,其实已将对文本诠释的独特理解传达了出来,已对其所概括的“结构化”或结构主义文本诠释路径提出了批评。假如以德里达参会报告为解构的起点,则可看到吉拉尔当时亦走在与解构相通的道路上,却又自有其重心。他的道路最终通向西方古代思想传统,对西方基督教正典进行接纳。吉拉尔由关注文学、关注俄狄浦斯神话开始,由关注文学“作品的统一性”、关注神话与文学里的“相互性”开始,渐次发展为揭示、反思替罪羊机制。其拆解、破除差异,并不停留于拆解、破除本身,也不是以拆解、破除传统为旨归。他从西方古代的思想传统里找到了其所珍视的信息,并坚信将有益于理解神话与文学,理解我们正置身于其间的社会与世界。西方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群星璀璨,吉拉尔的学术追寻当有其一席之地。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2期,“重读”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回 顾
点击图片,进入微店订阅
投稿邮箱
wgwxdt@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