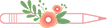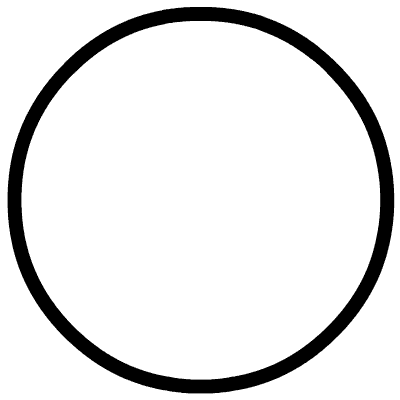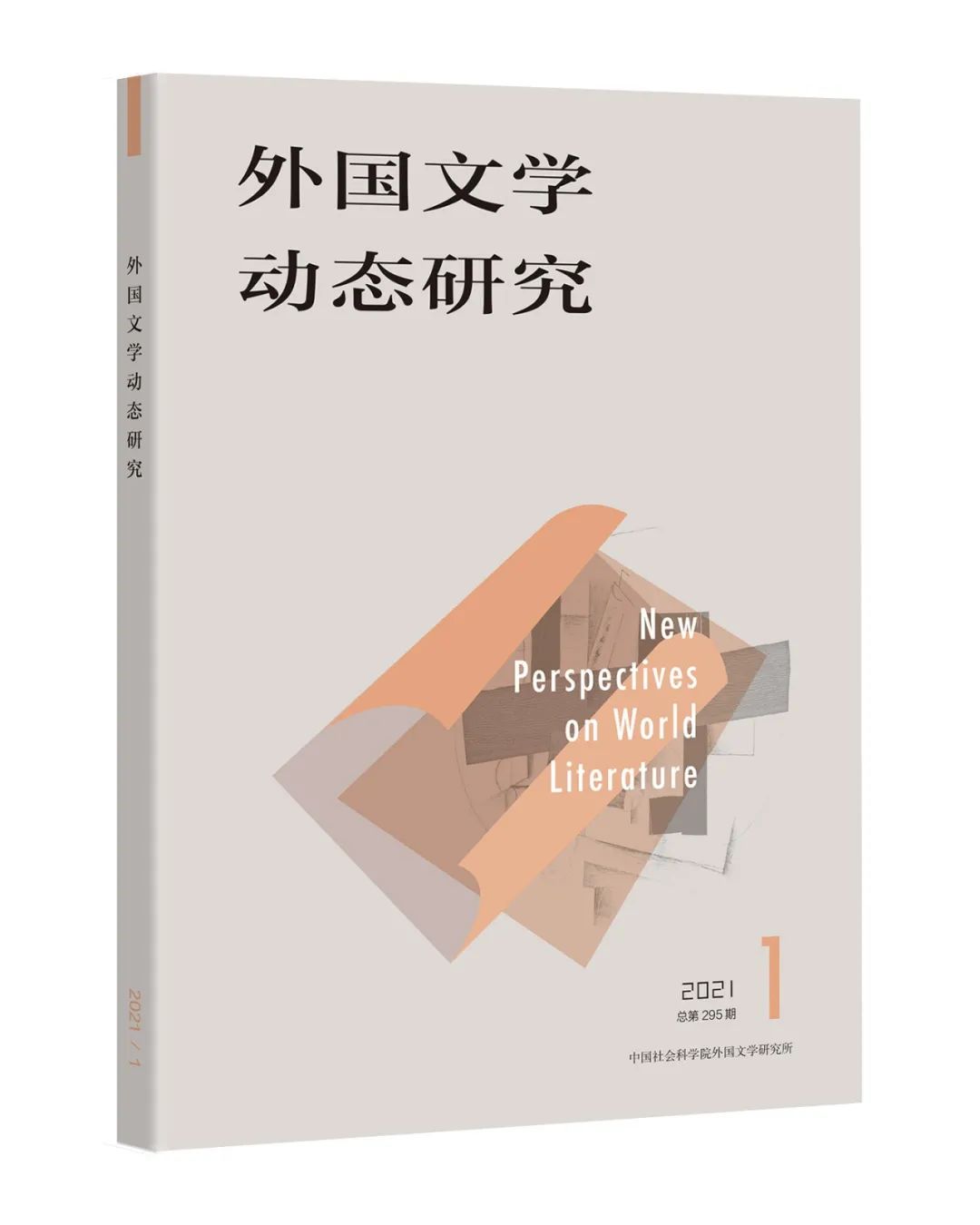重读 | 理念·寓意画·思维方式——从“思想图像”的语义流变看本雅明思想图像写作的三个面向


姜 雪 博士,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中国社科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德语文学及文学理论,近期的研究重点是本雅明的思想图像写作。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梳理“Denkbild”(思想图像)一词在德语史中的语义流变,考察本雅明的思想图像本身就内在于该词多重语义中的写作特点。理念、寓意画和以“图像思考”为核心的运思方式蕴含了本雅明思想图像的三个不同面向:思想图像是与本雅明的认识论理想相契合的思维方式;尽管有别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但它却是本雅明以剥去假象的具体经验来建构客观哲学星丛的尝试;尽管题材与主旨都不同于寓意画,但它却是本雅明以图像性的文字实施批判的现代“寓意画”。
关键词 本雅明 思想图像 理念 寓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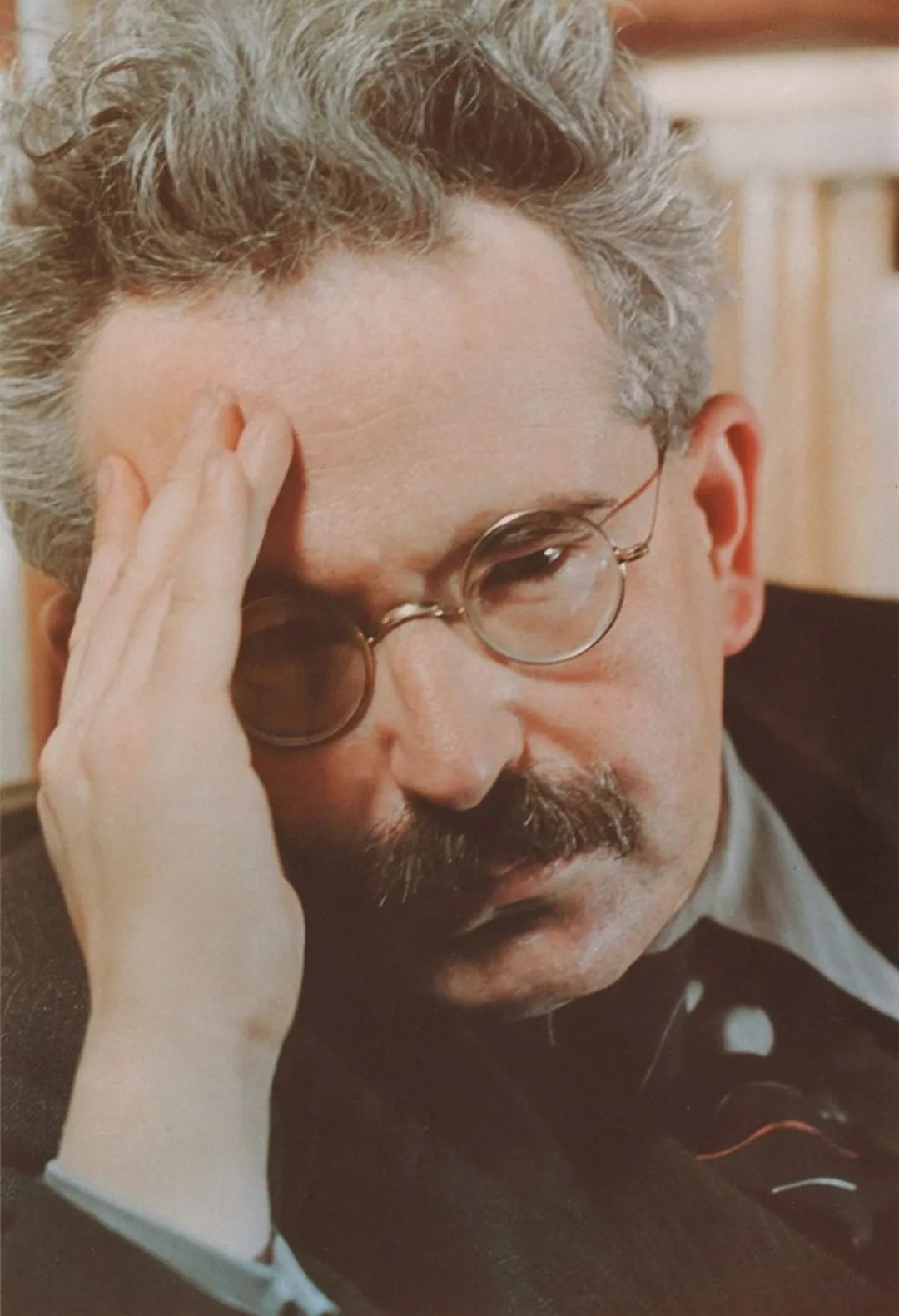
(本雅明,图片源自Yandex)
“思想图像”(Denkbild)是本雅明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它既指称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也代表一种独特的运思和写作方式。由于该词在语义上的巨大张力,它甫一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就令人争论不休。回溯“思想图像”的词源发展可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该词早期历经一系列学者的阐释,词义从纪念物延伸到寓意画,从表达普遍概念的神话图像发展为将直观和理念有机统一的认知方式;再到20世纪初被认为用来指称柏拉图理念论意义上突出显相的“理念”;及至本雅明,它被用来作为混合了箴言、梦境、即兴语录等一系列短篇散文的标题。“思想图像”一词在其演进过程中发展出的语义内涵,已内在地哺育了本雅明思想图像写作的几个方面。理念和寓意画蕴含了思想图像作为文哲交融的文学类型的旨归与表现形式,而与概念思维相对的思维方式则是探源这种写作方式的核心所在,故本文拟以这三重语义初探本雅明思想图像的写作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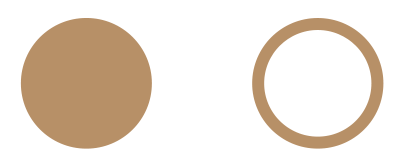
德语文学界在20世纪初首次围绕“思想图像”之来源与词义展开了争论。从1968年舒尔茨对“思想图像”一词所做的词源学考察中可知,此番争论由诗人博尔夏特的评论《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第七个指环〉》(1909)引起。博尔夏特用几乎占据了半页篇幅的脚注批评格奥尔格借用了毫无必要的荷兰语“denkbeeld”和“eeuw”,且毫不掩饰对这舶来品的鄙斥。他首先认为格奥尔格借用了“毫无智性的不纯正的荷兰语”,其次认定其意在以该词赞颂为“艺术理念之本质”献身的马拉美,但是“马拉美和格奥尔格都表明,他们所思考的艺术理念之本质并不比柏拉图的更普遍,也就是说,他们明白,艺术理念全都只与图像(Bild)有关,而与思想(Denken)的关联比无还少”。因此,博尔夏特认为不仅格奥尔格借用外来语是毫无必要的,而且他对这个词的意义使用也是错误的,其中“并不比柏拉图的更普遍”道出了“denkbeeld”在荷兰语中的真正意指——柏拉图理念论意义上的“理念”(Idee)。据舒尔茨考证,“Denkbild”在格奥尔格时期无论是在德语口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非常鲜见。所以对该词的论辩一时间十分激烈,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该词是否从荷兰语舶来;该词到底更强调“理念”还是“图像”,以及格奥尔格对该词的使用是否恰如其分。

(马拉美,图片源自Yandex)
与博尔夏特针锋相对,当时的论者如博克认为“Denkbild”在德语中古已有之,温克尔曼和赫尔德都曾使用过,因此说格奥尔格借用荷兰语只是妄加揣测。克鲁斯曼(P.G. Klussmann)则指出,“Denkbild”通过名词构词法直接道出了柏拉图的核心术语“Eidos”所包含的另一面,那就是图像与外形(das Bild-und Gestalthafte);但他认为诗人对该词的使用略嫌用力过猛,理由是该词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更强调图像性的一面,而不能充分凸显马拉美所重视的理念(l’ idée)的一面。
“denkbeeld”和“Denkbild”在构词上的相似性,以及格奥尔格与荷兰诗人的友谊和他对荷兰文化的了解,都足以令博尔夏特确信“Denkbild”是借鉴了荷兰语。为探源词义,舒尔茨列举了《荷兰语词典》中“denkbeeld”的词条义项,最重要的前两条是:“(1)由思考产生或形成的被视作是图像的思想;(2)在观念或概念的意义上,人的思维活动就某一事物而形成的图像。”由此可见,“denkbeeld”的词义本身具备一种居间性,连接起了本来处于对立状态的思与像,二者可以双向运动,从任意一方走向另一方,而不会冲破概念涵括的范围。舒尔茨隔空回应道,格奥尔格正是在替代理念的意义上使用了“Denkbild”,且该词恰恰强调了被克鲁斯曼认为是被弱化了的内容,即马拉美关于诗歌创作的理念;格奥尔格之所以不用“Idee”而用“Denkbild”,是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加生动,更加地远离概念,更加地适宜。这里“适宜”无疑是指用“流血”(blutend)和“思想图像”(Denkbild)来形象化地喻称马拉美为之现身的理念,比用抽象语汇譬如“奉献”和“理念”(Idee)更加适宜于诗歌语言。
综上所述,几位论者基本都是在认定“Denkbild”指称“理念”的前提下,围绕其到底是更强调抽象还是图像展开了辩论。即便是博尔夏特,也是断定格奥尔格在表达理念的意义上使用“Denkbild”后,批评其对马拉美艺术理念的认识是错误的。由于柏拉图的“Eidos”本义为“所见之物”,即心灵所见的显相或外观,而“Denkbild”恰恰通过其词形体现出理念在视觉上的“显像”之义,因此“Denkbild”就在指称与具体事物相对的客观理念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构词法兼及了理念的另一方面,而“Idee”则纯粹成为了符号和概念,其词形已偏离了其意义本源。“Denkbild”在格奥尔格的所有作品中共出现过五次,大多不超上述讨论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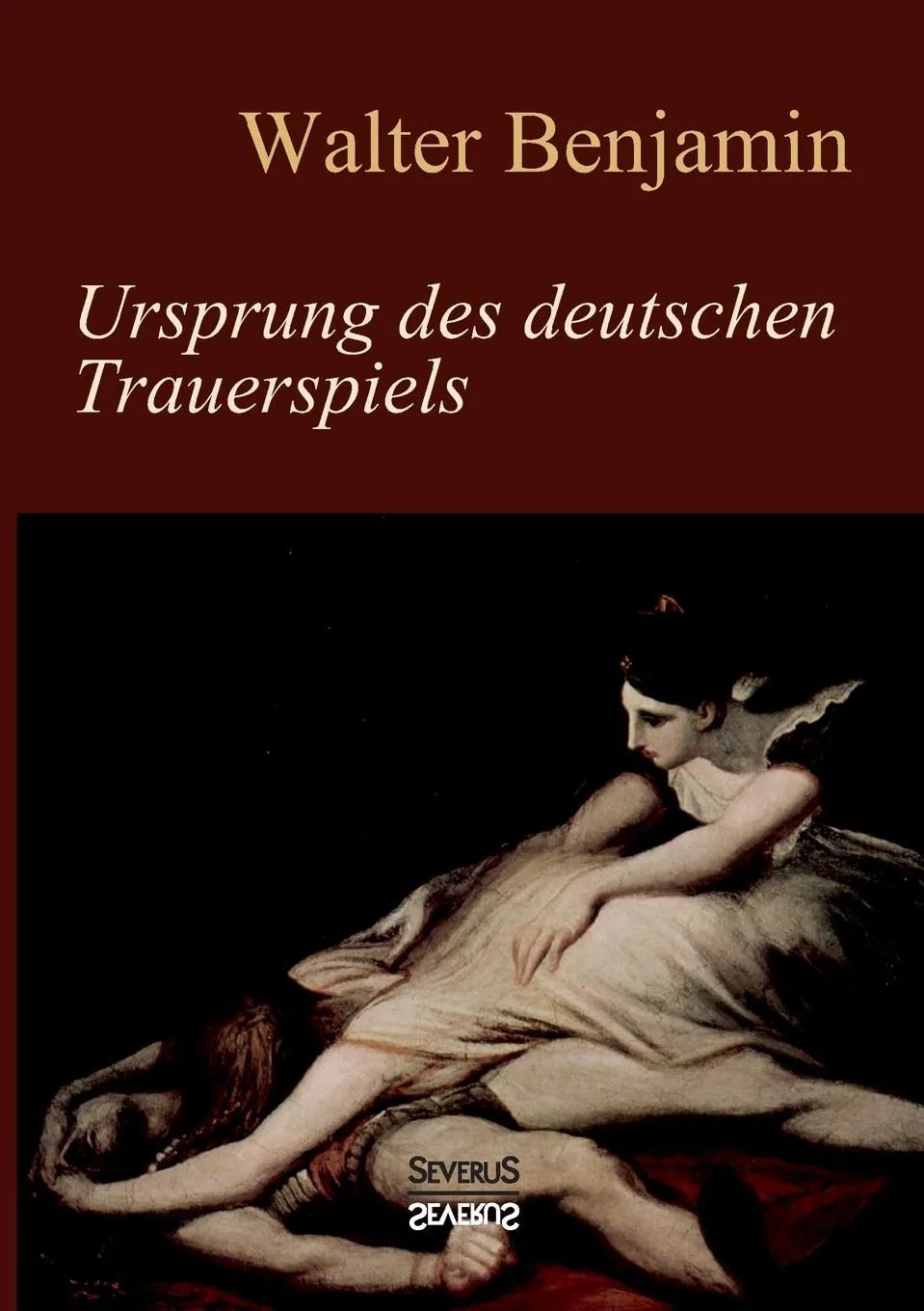
(《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图片源自Yandex)
本雅明对“思想图像”一词的使用到底是从格奥尔格还是从对巴洛克寓意画的研究(详见本文第二部分)中来,由于缺乏实据不得而知。但本雅明的思想图像也包含了抽象和具象的两极,正如其构词所示,它“包含一个具体的事实情况(图像)和一个与之相关的反思(思想)”。《单行道》就是这样一部用图像的方式或称图像化的文字把本雅明关于政治、宗教、社会批评的思想表现出来的典例,是本雅明从纷繁芜杂的经验世界中重现事物之本质构型(Konfiguration)的尝试,或说,是在马赛克般的图像并置中“建构形象化的哲学星座(Konstellation)”,这与他同年出版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的“理念”的意蕴是一致的。在该书序言《认识论批判》中,理念被规定为是对某种关联的赋形,“在这样的关联中仅此一次的极端情况物以类聚”,“普遍之物就是理念,而经验之物……是一种极端情况”。理念与经验之物亦即现象的关系就在于,现象并没有像合并同类项一般被归并到理念中,而是在不丧失其具体性和特殊性的情况下,处在与其他现象元素的关联之中,而这样一种关联的构型就是理念。
阿多诺1955年对《单行道》的评论也回应了世纪之初的那场争论,他认为格奥格尔正是在替代“理念”的意义上使用了“思想图像”,理念在柏拉图那里“是一个自在之物,能使自己被观照到,尽管这种观照只是精神性的”,而思想图像在本雅明和格奥尔格那里的相同之处就在于,将主观和偶然的经验把握为客观性事物的展现。也就是说,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相同的是,本雅明的理念也不是人的主观构造物,而是客观实在;它尽管是自在之物,却不是康德的不可知的“物自体”。但在另一方面,本雅明的理念是能够自我呈现的,真理内容本身就是潜藏在事物内部的客观实在,被日常观察视为“主观和偶然的经验”的便是它的种种呈现,因此,不同于具体事物不能与之平起平坐的柏拉图的理念,本雅明的理念不仅有经验的参与,而且还在“具体的经验整体”中得到表征。那些分有理念的经验现象,在本雅明看来能够对真理发声,并表征真理。思想图像因此是本雅明把思辨层面上阐发的理念建构落到实处的一次文本实验,以蒙太奇拼贴的方式,具体而琐碎的日常即景被临时地聚集起来,拉出惯常的语境,拆分和重新并置后揭示出一种非同一性的关系。时代的末微之物由此进入了观察者的认知之眼,在他新的表述和用境中褪去了虚假的表象,以被拯救的元素的形式参与真理的表达,从而从总体上,它们的相互折射可以启示一个时代的整体真理。

(康德,图片源自Yand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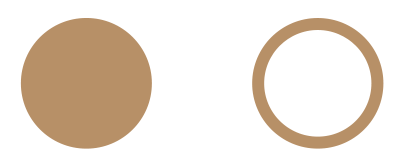
若从德语史中溯源,依据格林词典,“Denkbild”的确定使用可上溯至卡斯帕·施蒂勒、温克尔曼和赫尔德。施蒂勒编纂的《德语语言的谱系和发展》(1691)作为现代德语词典学的开端是对德语词汇进行全面记录的首次尝试,在“Bild”词条下,他为“denk-oder gedenkbild”注拉丁译文“mnemosynum”(纪念物),即承载纪念或回忆的物品。到了温克尔曼和赫尔德,“Denkbild”都在与寓意(Allegorie)和寓意画(Emblem)相关联的语境下出现。舒尔茨只在《古代艺术史》中发现温克尔曼对该词的一次使用,该词被用来指称洛可可艺术所缺失而希腊艺术所完美拥有的品质,那就是“庄严而有教义的思想图像”。这里的“思想图像”要从温克尔曼的艺术理想和寓意观来加以理解。在“诗画互通”的基础上,温克尔曼认为作为哑默诗艺的绘画也要和诗一样表达思想、呈现意义,而思想的生成必须通过寓意。因为寓意是“意味着普遍概念的图像”,它在图像与思想之间搭建了一座意义之桥,而寓意的生成又需要艺术家倚凭来自古代的智识性资源,它们源于神话、各民族智慧以及“含有感性形象和图像的纪念碑、硬币和器皿等,普遍概念正是藉此才诗意地形成”。在温克尔曼的艺术理想中,化身为普遍概念的图像典范乃希腊神话,思想图像因此就是能够直观呈现普遍概念的希腊神话图景。而温克尔曼坚持形象或符号与意义之间具有确定性的指称关系,“理想的寓意是一种无需铭文之提示的图像”,因此神话图像应是自明的寓意图像。寓意的产生是否需要借助语言系统,则构成了温克尔曼与赫尔德的意见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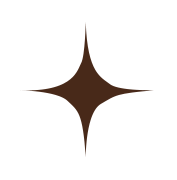


(赫尔德与温克尔曼,图片源自Yandex)
温克尔曼还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1756)中提到“艺术家将会明白,里帕的图像学、胡格对古代民族的思想图像的研究会带来多少愉快”。这里的图像学、思想图像研究都指向了寓意图像志体系,舒尔茨在其研究中遗漏了此处文献,而正是在“寓意画”的意义上,该词被赫尔德使用得更加频繁,它在赫尔德的著述中首先作为寓意画的替代说法出现。在《随笔》(第5部)(1793)中,赫尔德收录了安德里亚(J.V. Andreä)于17世纪初创作的譬喻故事,他指认这些譬喻故事接近于寓意与寓意画:“对于作者来说,这和伊索寓言是两码事。他的一少部分创作接近于寓言;而大部分都趋近于意义和思想图像(寓意画)、寓意、拟人故事等,它们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寓言。”赫尔德直接把“意义和思想图像”(Sinn-und Denkbilder)等同于寓意画(Embleme),这种等同用括号内的替代来表示。
思想图像在此并无柏拉图理念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意,而是从其构词法出发指称这种图像和文字结合的艺术:寓意画(Emblem)。寓意画是一种产生于近代早期的古老艺术形式,文艺复兴时期在欧洲广泛兴起,具有对大众的劝喻意义,意大利人文学者阿尔恰蒂于1531年出版的《铭图集》标志它成为一种文学类型确定下来。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图文整合的形式,既诉诸于视觉也诉诸于知性和想象:居于中间的画面承担描绘功能,上方的标题和下方的说明性文字即解题则承担对画面的阐释功能。寓意画中的寓意需要通过文字说明方可得到清晰明确的表达,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赫尔德表现出与古典艺术教育家温克尔曼不同的对寓意画的价值判断,赫尔德指出,“人们往往还想向眼睛展示过去无法向它们展示的东西,比如意味深长的思想和譬喻,甚至是惯用语和短语、谚语、政治格言;如果这些本身不够自明,就用充满智慧的语言来解释图像的智慧……在其他地方将择机更细致地区分纯粹的古希腊寓意精神和晚近时代的寓意画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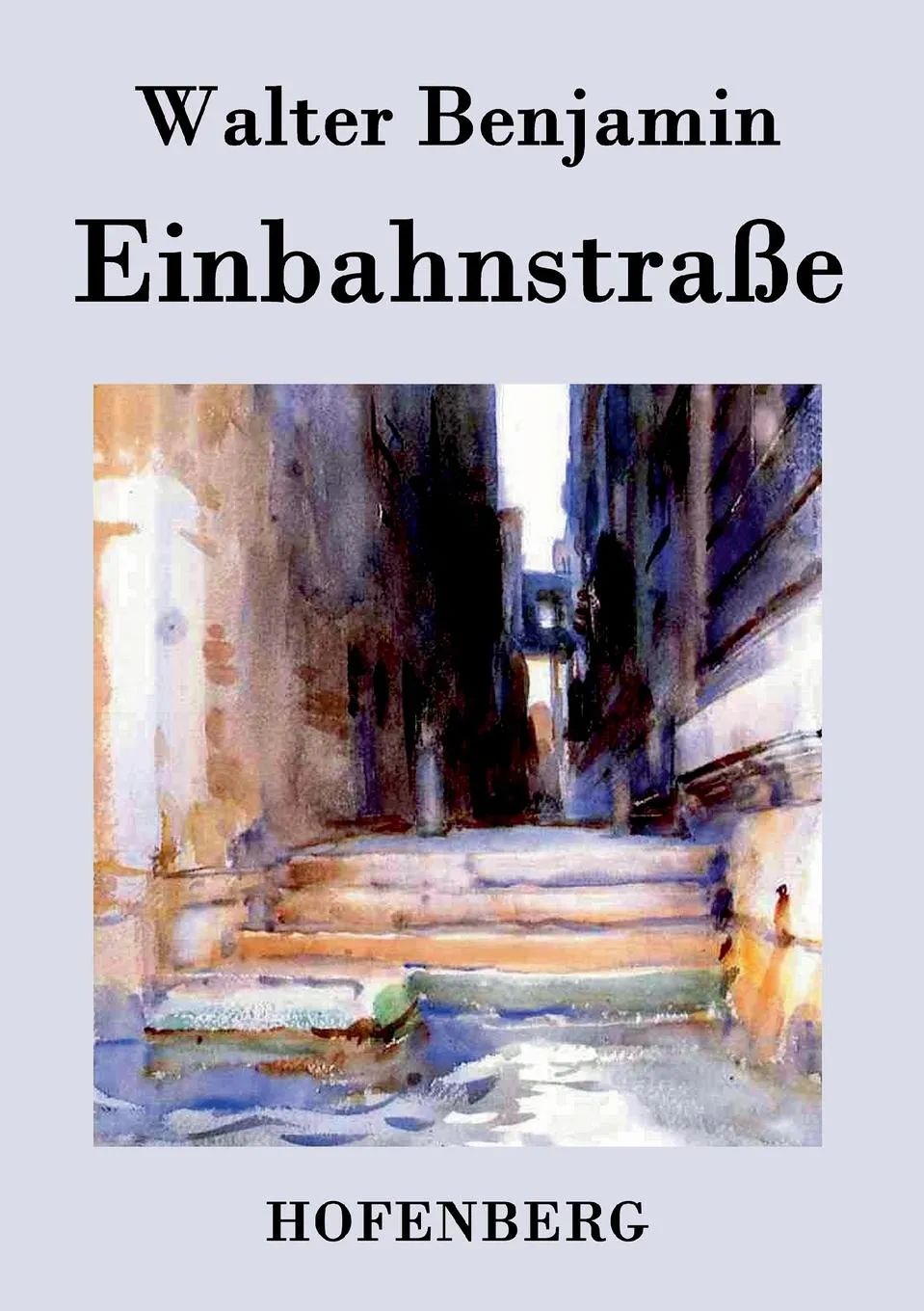
(《单行道》,图片源自Yandex)
施拉费尔(Heinz Schlaffer)在其1973年关于思想图像作为文学类型的开创性研究中首次指出思想图像与寓意画之间的相似性,他推测本雅明正是在对巴洛克艺术的研究中发现了“思想图像”,该词简明扼要地标示出这种文学类型在思想与直观方面的双重特性。以《单行道》为例,寓意画和思想图像的标题都具有短悍有力的特征,“致男人们”“小心台阶!”“墙面出租”等都再现了寓意画标题的功能,所不同的是寓意画中简明扼要的警语(道德准则或行为指南)在本雅明这里以现代街道旁常见的标识或广告现身,与道德无关,它们呈现出城市生活和商品美学的特征。寓意画中的画面与文字说明在本雅明这里合二为一,全由文字组成,思想内含于由文字“描画”的图像中,而位于展示前位的是语词的图像性,图像启动之后,所言说的他物才随图展开,寓意同样参与到意义的生成中。如果说寓意画表现为感官和思想的交汇,即图像和语词的交汇,这种交汇表现为互动,即图像意义化和语词图像化,那么思想图像也表现为一种从可视化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可视化的双向运动,具象之物与抽象之思相互指涉,彼此蕴含。图像的展开看似是日常生活世界的自我呈现,实则是事物被拉出原有语境而被并置共现,连通两种不同事物的语词往往成为结构的铰链,而思想就在事物的陌生化构型中同时形成,产生了作为对世界认知的寓意。例如《单行道》中的《13号》一篇展现的是书和妓女的二元图像结构,其中第9条为“书和妓女在展示(ausstellen)自己的时候,都喜欢以脊背(Rücken)示人”。“Rücken”一词既指人的脊背,又指书脊;而“ausstellen”既标示了二者的共通之处,也给出了寓意的明确指向,该词意即“展览、陈列”,宾语一般是物,尤其是商品,本雅明就是用“Ausstellungswert”(展示价值)来指称复制艺术品的价值的,而人对自己的展现即在人前亮相并介绍自己,通常不使用“ausstellen”而是“vorstellen”。妓女和书籍的关联由此得以建立,同时披露的还有它们被异化的性质。在两者的相似和悖谬关系中所呈示的,是书籍的商业化和社会边缘人的物化及异化。
如果继续从《单行道》的文本出发,我们可以看出思想图像与寓意画在题材和意图上存在本质区别。首先,寓意画取材于自然、神话、中世纪文学及《圣经》内容,而思想图像则取自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直接观察。其次,寓意画承载的是意义,思想图像承载的则是反思。施拉费尔指出,寓意画的材料与寓意之间是正相关的类比关系,最终产生的是感觉现象与道德观念的和谐,而思想图像的主导意旨是批判,现实碎片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不是和谐而是对立的。对具体之物的反思意味着损毁表象而重新把握其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达到任何一个‘更高的’理念而去扬弃或克服事实存在”,思想图像要做的恰恰是在对现象实施手术的过程中使现象得到拯救,令其处于一种全新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的构型即是真理的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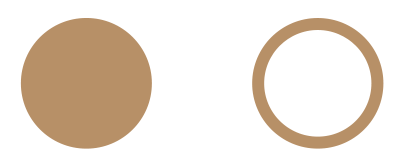
思想图像也被赫尔德用来指称一种实现完美认知的思维方式。在《促进人道主义的通信》第七十封信中,“人类之纯粹形式的思想图像”意谓人道主义的图像,而人道主义理念无论何时都完好无损地存贮于希腊神话的诸神形象中,神话赋予了思想图像以直观可感的材料。“每个给出完整图像的纯粹理念”在赫尔德这里“不是通过逻辑推演或抽象的哲学方式被把握,而是通过形成感性的、心灵直观的诗意行为开启的”。思想图像在此涉及的实质是认识论问题,赫尔德从思维源于感性的立场出发,把类比作为认知的方法和原则,反对康德的还原论,并宣称自己“追随图像,追随相似性……因为这是我思维能力唯一的游戏方式”。因此图像在赫尔德处即认知之途,而思想图像就代表与概念思维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比起概念,图像语言才更有能力进入事物的本质。
而在本雅明这里,思想图像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与其认识论理想相契合的思维方式。与赫尔德相同,本雅明的认识论也是在对康德哲学的接受和批判中形成的,在他对康德体系的改造中,经验概念首当其冲。概而言之,本雅明不仅要扩展经验的范围,还要把经验从工具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优先权。二元论体系下的康德哲学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划界而使经验材料不可僭妄,但在本雅明这里,经验现象不仅可以和理念沟通,还可在得到拯救的情况下一跃而入理念王国。比之像康德的还原主义者将经验现象还原为可计量的基质和无感性成分的定理形式,使之沦为提供给知识的素材,用过之后一弃了之,本雅明则将它们从附属地位拯救出来,在保留其繁多与特殊性的前提下,令其以事物本质的成分进入理念而承担表征真理的功能。思维的运动过程从而在蕴于化身为意象的经验现象中展开。因此思想图像于本雅明就是一种形象化的运思方式,它一方面使得思想具有独特的形象性,另一方面又使经验碎片在被抽离出固有语境的状态下与哲学思辨融为一体。这就对语言文字提出了要求,深入研究本雅明独特写作方式的当代学者魏格尔认为,语言就是他施展其“停顿状态下的辩证法”的图像之地,“凭思想图像这种文学类型,本雅明就生产和写作出这样的图像,用以解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正如魏格尔所说,思想图像“可被视作本雅明图像思考(Bilddenken)的工作核心。他的思想图像好似被书写出的辨证意象,逐字逐句成为文字的星丛排布,在其中展开图像与思考的辩证法,清晰可见”。“倚凭模仿能力,图像这一‘停顿状态下的辩证法’变身为文字,并以如下方式运转起来,即相关观念的起源和生产都变得可见……人们可以把这种写作方式理解为是文字模仿了图像的意义构造。”“可见”道出了这种思维运行的视觉特性,本不具有可视性的抽象观念也有了直观的生动意味。文字具有一维线性和时间特性,而星丛排布则是对各元素之空间关系的表达;当观念的产生和生产都变得可见,就需要一种“图像文字”(Bilder-Schrift)的写作。魏格尔将本雅明的图像思考称作“语言上的星丛排布,本雅明的语言表达习惯凭此而处在一种超越了概念和隐喻之对立的状态”,思想图像也因此超越了文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成为第三种形式。
正是在这种表达形式中,蕴含了本雅明从始至终的思想关切——真理也即客观理念的表征问题。本雅明曾表示,将哲学家与艺术家联系在一起的即是表征的任务,作为哲学家的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尝试以文学乃至艺术的表现形式践行其真理观。以寓意画的技法,思想图像即意欲以这样的图式展示本雅明在图像思考下的哲学星丛:于时间中流动的文字呈示一幅幅可直观的空间性构图,画面与意义(本质)就在被书写和阅读的图像中统一和共在,正如本雅明在对巴洛克寓意画研究中所作的判断,“寓意画家并不是在‘图像背后’给出本质”,而是把本质作为题解的文字拉到图像前。
无论理念还是化为文字的寓意画,它们的展现都表现为一个视觉化的显像过程,而真理乃语言所意指的真理,自然藉由语言得到表达,因此叙述尤其是语词的图像性便是思想图像的关键,语词在具象和抽象之间的连通为寓意画的画面与解题能够交互指涉提供了保证。《单行道》中的《技术紧急救援》呈现了一幅关于真理的图像,它通过几处图像化的叙述和连通器一样的词语实现了图像与意义的相互指涉,或者说,完成了图像直观和思想观念的双重建构。该篇首先把真理视为一个具体的观察对象(小孩、女子),一幅摄影师面对真理的拍摄画面便现于眼前。该篇的文眼“Objektiv”指称“物镜”,而它的词根“Objekt”意即“客体”“对象”,因此在这幅拍摄真理的图像中,物镜就是面对客体去捕获客体的镜头,它作为关键词既保证了寓意的明确指向,也完成了具象与抽象的相互转化。“Objektiv”在此既非概念,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作隐喻,而是沟通观念使其获得外形的图像本身。因此,画面还未及描绘完毕,寓意反思已徐徐展开:将对象摄录下来的摄影技术对应的就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认知方式,它背后的认知主体带着探寻的意图,欲将真理像外来物一样捕获,而在这种认知方式下真理只可能永不现身。而对本雅明而言,真理乃意图之死,它潜藏在事物内部,每每以不同的形态在刹那间显现。该篇最后借奥斯曼宫廷里的宫女呈现了真理的真正形态,真理所身披之物正是她就近抓起的一件恰好落到手里的绸缎,也即从认知主体那里借来的某件外衣如某个词语或范畴。在具体和抽象之间的交互中,画面与题解同时发生,真理及对真理的认知过程得以显像其间,在此过程中,图像的直观一直在沟通着抽象的反思,而寓意的显现也并不会倾轧并优先于图像,这便是作为思维方式的思想图像的运思法则和言说方式。
“思想图像”的语义光谱从“纪念物”增加到“寓意画”“理念”和与概念思维相对的“思维方式”,到本雅明这里成为一种包含了具体情况和与之相关的反思的文学类型。从本质上来说,思想图像不单是一种文学类型,它不仅仅是《本雅明全集》第四卷中被归置在“思想图像”分类下的那些短篇,更是本雅明在解构传统思维方式的不断尝试中形成的独特写作方式,也是本雅明对客观理念进行形象化建构的写作实践。作为与寓意画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思想图像,其文本目的也不仅仅在于产生寓意,因为思想并没有把图像仅仅作为一个例子留在身后,而是与图像相互交融相互成就,抽象的运思仍能回到具象的层面,图像并没有被扬弃,换句话说,本雅明运思和写作的图像性本身就内在于其思想的形成与表达当中,其内容与形式有如本雅明童年回忆里的长筒袜,被包卷起来的毛线兜和毛线袜本就是一体的。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6期,“重读”栏目,责任编辑王涛,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文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回 顾
点击图片,进入微店订阅
投稿邮箱
wgwxdt@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