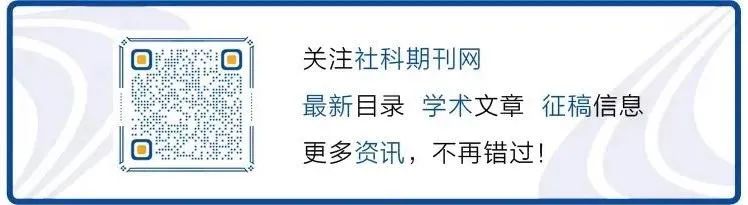新作评论 | 以父之名的精神寻根——评2020年度俄罗斯大书奖获奖作品《牛顿手稿》

李春雨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理教授。主持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出版专著1部,译著6部,发表论文19篇。译著《记忆记忆》获《新京报》2020年度好书及第三届力冈俄语文学翻译奖入围奖,专著《老舍作品在俄罗斯》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内容提要 《牛顿手稿》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伊利切夫斯基的最新长篇力作,荣膺2020年度大书奖头奖。小说反映了当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失根危机,以一场以父之名(生理之父、精神之父、信仰之父)的精神寻根之旅,生动诠释了科学与神学理性融合、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精神寻觅永不止步等贯穿作家文学创作始终的核心价值观,堪称作家的集大成之作。作家以此呼吁人类摒弃自我膨胀与狂妄,克服对异质存在的恐惧与拒斥,重返相信神话、崇拜父亲的童年时代,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探索世界奥秘。
关键词 伊利切夫斯基 《牛顿手稿》 父亲崇拜 精神寻根
2020年12月10日,当代俄罗斯文坛最高奖项——大书奖揭晓,著名作家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личевский,1970—)凭借最新长篇力作《牛顿手稿》(Чертёж Ньютона)摘得头奖。中国读者对伊利切夫斯基并不陌生,其长篇小说代表作、2007年度俄语布克奖获奖作品《马蒂斯》(Матисс)于2009年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学界引起不少关注。《马蒂斯》一举成名之后,其2010年长篇小说《波斯人》(Перс)又荣膺大书奖二等奖,而《牛顿手稿》则是作家暌违十年之后斩获的又一重磅奖项。伊利切夫斯基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寻求自我突破,以免造成读者审美疲劳。在回应何为真正的“大书”时,他指出:“能否激发重读的欲望是唯一标准。”伊利切夫斯基致力于体裁创新,俄罗斯评论者称其“有意识地打破(新)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种最主流的当代文学范式……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对写作死亡的救赎,甚至可以说,是对俄罗斯文学死亡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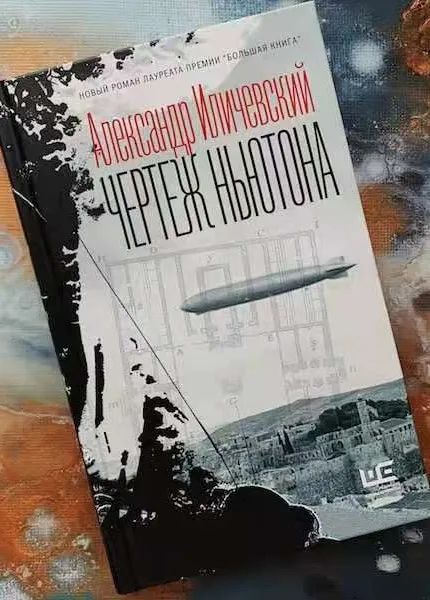

(《牛顿手稿》与伊利切夫斯基,图片源自Yandex)
伊利切夫斯基自称广义上的旅行者、世界公民,游记是其文学创作的核心体裁,旅行写作也构成了评论界对其创作的审美期待与考察视野。他笔下的主人公无不热衷于地理空间位移,视线与地貌构成其小说的两个独立行动主体。俄罗斯评论者指出:“‘审视地貌’是对其小说的精确概括。视线与地貌的相互关系作为红线贯穿,构筑起外部事件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旅行“以一种生活方式渗透进了俄国人的文化当中,并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承下来,最终升华至民族性格中的‘旅行情结’”。而对于伊利切夫斯基的主人公而言,旅行既是一种逃离,即逃离庸常生活的拘囿以及对未知的恐惧;又是一种寻觅,即以视线寻觅不可见之物,从而发现或者抵达。《波斯人》中的主人公便是如此。他是一位地质学家、石油勘探者,同时又酷爱旅行,热衷摄影。他不仅仅是在旅行,也像冲浪运动员追逐转瞬即逝的浪头一样捕捉灵光乍现的诗意,以此保持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完美平衡,故俄罗斯学者将《波斯人》赞誉为“一部教导人们如何在不完美的世界完美生活的并不说教的教科书”。《牛顿手稿》延续了作家一贯的旅行写作风格,以跨越内华达、帕米尔、耶路撒冷的三次旅行反映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失根危机,借由一场以父之名的精神寻根之旅,探讨了极具普世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主题:当今社会,人类的精神应向何处寻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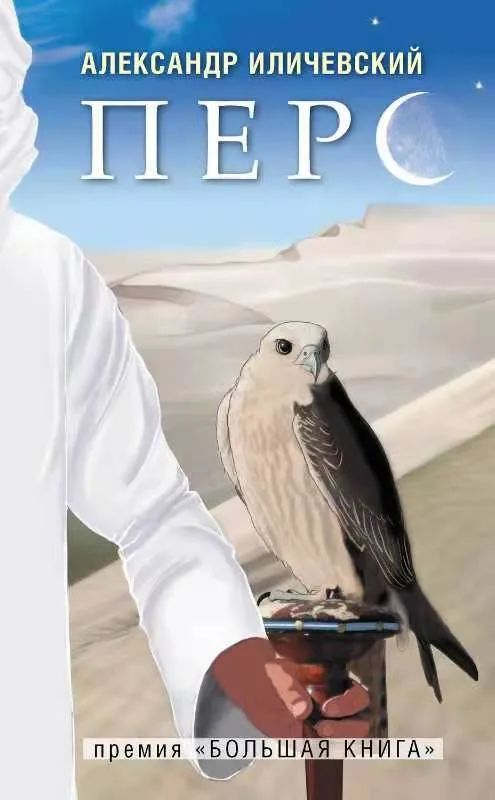
(《波斯人》,图片源自Yandex)
苏联解体之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失去了赖以栖居的、持续整个20世纪的乌托邦神话,一时间变成了存在主义的流浪汉。伊利切夫斯基曾在一次访谈中如是自述:“我们家之前在阿塞拜疆有一栋房子,我们失去了它,更准确地讲是被时代剥夺了,从那时起,我便再也无法找到安身之处。我时常梦见那栋房子,失去了主人,灌进了雨水,住进了鸟儿、陌生人,梦见死掉的花园。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思乡梦境。大概从那时起,我就不大相信命运了,不再寄希望于能够找到一栋房子,一栋实实在在的,在形而上学层面不会被摧毁的房子。”作家赖以成名的长篇小说《马蒂斯》便通过一位物理学者沦为流浪汉的故事反映了最后一代苏联人的集体流浪状态。对于这部小说,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主人公的流浪是“从无意识到潜意识再到有意识的筹划之后的出走”,他将流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在流浪中寻找自由和阳光。事实上,这里的“流浪”具有肉身与精神双重指涉,不仅指肉体上的居无定所,更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并且,假如肉身流浪是暂时的、可以解决的,那么精神流浪则是持久的、难以终结的。换言之,较之于肉身失所,精神失根才是伊利切夫斯基文学探索的核心关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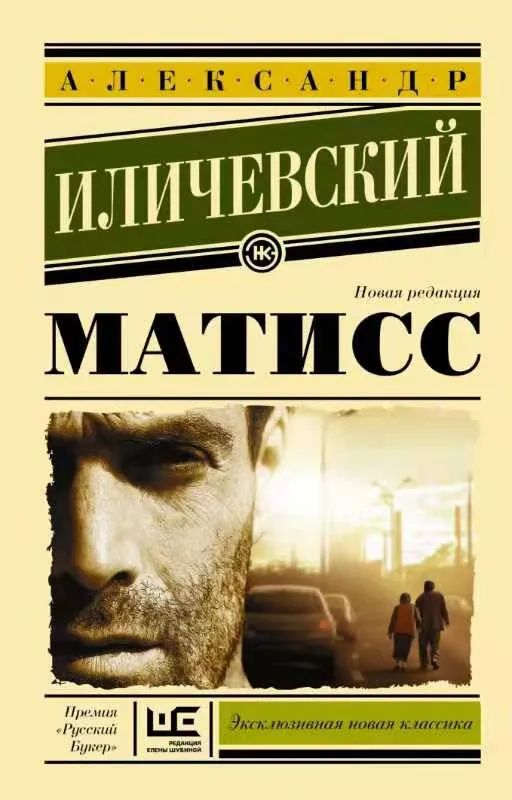
(《马蒂斯》,图片源自Yandex)
在《牛顿手稿》中,“精神失根”这一主题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小说通过讲述主人公的岳母及其本人的遭遇,反映了当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失根的真实现状。“我”的岳母被美国内华达一个网络邪教组织洗脑,变卖家产,迁居美国,成了一具被邪教团体随意操纵的行尸走肉。“我”受妻子之托,只身前往美国,驾车穿越内华达州沙漠,去拯救岳母。毫无疑问,岳母是无数由于信仰真空而精神失根的普通民众的代表,而“我”则代表了高级知识分子。“我”的职业身份是一位专门钻研暗物质的物理科研工作者,试图通过记录运动中的带电粒子在空气中遗留的痕迹,研究出一种算法来解码关于这些痕迹的海量数据,从而接近暗物质乃至整个宇宙构造之谜。从内华达返回之后,“我”前往帕米尔高原一家曾在大学时代实习过的苏联科学实验站考察,却发现这座实验站久已废弃,破败不堪,竟成了幽灵游荡之所。这暗示着主人公的科学信仰同样遭遇了危机。
在这两场旅行途中,主人公与各种超现实存在不期而遇,为这部科学哲理小说增添了些许魔幻色彩。比如内华达沙漠中体型庞大、足如车轮的兔子怪物,小镇旅馆中一袭红裙的少女幽灵,帕米尔山地原本只存在于当地传说中的“上界”居民等等。当主人公深夜漫游在阒寂无人的沙漠星空之下,漫天星辰突然开始舞蹈,荒漠之灵从天穹降临,它们形态各异,有些缺少臂膀,有些半人半兽,翅膀大小不一,大如鹤翼,小如手帕。“其中一个飞得如此之低,我分明嗅到了它所散发出的麝香,但那气味随即变成了令人惊奇的河水气息,准确地讲,是刚从河水中跃出的鱼……偶尔,那些在我头顶往来穿梭的异质存在的零碎思想言语片段会传到我的耳边,似悄语,似合唱,似牛哞,似嗤笑,似呜咽。”对于这些异质存在,主人公起初出于职业本能,试图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比如将其归结为酷暑、脱水、疲惫等因素所导致的视听幻觉或光影错觉,但最后又不得不将其一一推翻,承认科学自有其边界,并不能解释世间一切。
如果说以上种种遭遇动摇了“我”的科学信仰,那么父亲的失踪则造成了“我”彻底的精神失根。“我”的父亲是一位神秘主义诗人、梦想家、流浪者。在外人眼中,他不过是一个性格乖戾的嬉皮士拥趸和旧物收藏者,而在主人公心目中,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哲人和真理探索者。主人公对父亲无限崇拜,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努力继承其生活方式、音乐品味及思想理念。全书中,主人公对父亲的回忆占到三分之一篇幅,他旅行途中关于各种主题的抒情插笔也大多来自父亲的谈话和日记。父亲对圣城耶路撒冷的古老历史无限神往,曾多次前往朝圣,后来在一次考察中神秘失踪。由此,“我”前往耶路撒冷,开始了漫长的寻父之旅。如果说主人公现实旅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那么其精神朝圣的目的则是为了追随父亲的足迹,完成其未竟的精神探索。“失踪的父亲”可以被视作对当今社会精神失根状态的隐喻,而多重内涵的“父亲”形象则为主人公的精神寻根提供了初始驱动力与精神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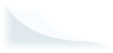
“父亲”是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但父亲与儿子,特别是与成年的儿子之间往往会爆发激烈冲突,比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比如俄狄浦斯。但伊利切夫斯基的作品却一贯宣扬父亲崇拜。作家坦言:“在我的理解中,父亲是圣经人物,是上帝的隐喻,是家的隐喻,是流浪者最终能够觅得的近乎天堂的世界。”在《马蒂斯》中,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就充当了这样的父亲角色。马蒂斯是主人公最终选择流浪的驱动力,也是其流浪途中的力量源泉,画家凭借其忧郁不羁的自我形象及其绚丽夺目的艺术创作成为主人公一路追寻的精神之父。《牛顿手稿》中也同样充斥着浓郁的父亲崇拜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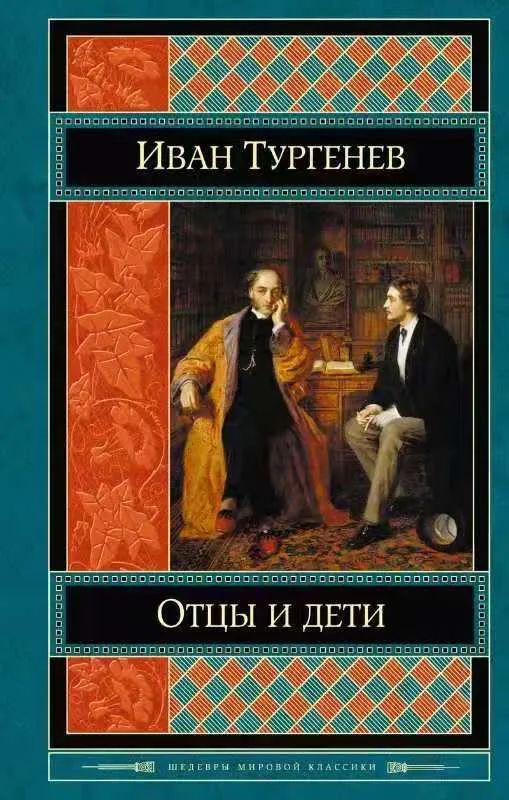
(《父与子》,图片源自Yandex)
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成年儿子对父亲的崇拜呢?我们可以在《牛顿手稿》中找到一些提示线索。小说主人公在与魂灵进行接触与交流时,有过这样一段心理活动:“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孩子。对于神话情节的深信不疑又回到了我的内心,这魂灵是那么的活泼,温暖,像只小狗崽。”这段话对于揭示作家的创作思想尤为关键,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理念,即“重返童年时代”,这实际上是作家为人类精神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即摒弃成年时代的自我膨胀与狂妄,克服对异质存在的恐惧与拒斥,以开放的态度探索世界奥秘。而与之一起回归的,还有童年时代所固有的父亲崇拜。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的“父亲”并非单纯的实在形象,除了生理上的父亲之外,至少包含以下两重寓意:精神之父和信仰之父。
如前所述,小说中父亲的权威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而父子二人共同的精神之父是在晚年由科学转入神学,试图以神学弥补科学之局限的伟大科学家牛顿。主人公有一次跟随父亲坐火车穿越锡兰,在慢吞吞的列车的车厢顶上,“我们谈起了牛顿,认为无论是科学还是神学,都是时候尝试相互学习某些东西了。牛顿对于神学问题的科学态度被我们一致视作处理二者关系的典范”。牛顿晚年笃信神学,至死都在致力于对不复存在的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做精确计算,因为他坚信,自然法则和上帝真理的密码都隐藏在圣殿的构造和比例之中,可以通过计算圣殿尺寸加以破解。于牛顿而言,所罗门圣殿是世界的图纸,是开启宇宙奥秘的钥匙。世人大多对此疑惑不解,将之视为走火入魔,为伟大科学家“晚节不保”扼腕叹息,而伊利切夫斯基却认为:“伟大科学家牛顿最主要的直觉不是要得出某些数据,而是要融合科学与神学。”(“Бомжи”)早在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数学家》(Математик)中,伊利切夫斯基便塑造了一位牛顿式的主人公——一位数学天才,三十五岁便荣膺具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茨奖,后来却一度痴迷于亡灵复活,为此遍访墓地。

(牛顿,图片源自Yandex)
伊利切夫斯基的这种观念与其深厚的理科背景有直接关系。作家从小便极具理科天赋,中学就读于莫斯科大学附属物理数学特长班,本科毕业于全球知名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МФТИ)应用物理学系理论物理学专业。1991至1998年,伊利切夫斯基在以色列和加利福尼亚从事物理学的科研工作。然而,多年的前沿科研工作却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拥有怎样的实力和潜能,科学终归有其边界。在《牛顿手稿》中,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说:“世界内容之深奥是无法预测的。它高于逻辑,要求科学家随时准备发现其中某些与理性思维相悖的新联系。”作家本人也曾表示:“人类是时候习惯于以下事实了,即一个深奥真理会违背另一个深奥真理。”(“Бомжи”)另一方面,神学可以给予科学灵感与驱力。《牛顿手稿》中提到了牛顿最为尊崇的圣经人物——以诺。以诺是《旧约·圣经》中的第一位学者型先知,在公元前三至前二世纪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诺书》曾一度被奉为正典。据《圣经》记载:“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以诺拥有对于旧约时代而言过于神秘的破解世界构造的热情,他曾将星星描述为“燃烧的群山”,这令牛顿震惊不已,因为将星星视为绵延的实体,而非天幕上的点的想法在旧约时代太过超前。作家在访谈中也曾提到:“尼古拉·费德罗夫认为,将所有死者复活是人类应当致力完成的首要任务,并委托齐奥尔科夫斯基为安置将来被复活的亡灵寻求出路。航天学实际上便由此发轫。”(“Бомжи”)
小说主人公继承牛顿遗志,融合科学与神学的探索,最终将“精神之父”引向“信仰之父”。这里的“信仰之父”不单指上帝或者其他神明,而泛指终极信仰的膜拜对象,在小说中,它化身为主人公毕生钻研的暗物质:“我必须找到一个不可折弯的、完全归属于现实的轴,能让我将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全部串到上面。最后我发现,这个轴就是暗物质。我开始潜心阅读大量的最新科研成果,后来逐渐意识到,魂灵便是隐藏的宇宙质量。我一直寻寻觅觅的暗物质,原来也在寻找我,所以我才能够看到魂灵……我所需要的那根轴,原来就是科学认知与神学顿悟之间的分水岭与结合点。”主人公终于领悟到:科学与神学是人类精神文明相对矗立的两座圣殿,黑洞、暗物质、N维空间也好,上帝、幽灵、天堂地狱也好,无不是超越日常体验与寻常思维的世界观感,都是为破解世界的超验性而建造的。二者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甚至理应相互融合的。
科学与神学相融合的理念,还通过小说精心设计的叙事结构表现出来。三场旅行的目的地绝非偶然,而是极具象征意义:内华达邪教组织可以视为宗教的极端发展,帕米尔废弃的科研站可以视为科学的局限性。作家选取这样两个标志性意象,无疑意在表明:科学与神学在相互排斥的道路上行不通,于是便导向了合理的结论,即科学与神学应理性融合,而精神寻根之旅的终点站——圣城耶路撒冷,便是该理念的象征与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耶路撒冷即是主人公为自己寻到的精神之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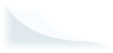
自古以来,描写耶路撒冷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伊利切夫斯基此前的游记小说《日落之城》(Город заката)同样是对这座古老圣城的命运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演变的艺术思考。在《牛顿手稿》中,作家纤毫毕现地再现了耶路撒冷市区及郊区的风貌与气息,使其以独立星球的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鲜活,宜居,生机勃勃:“耶路撒冷是唯一一座能够让人自由自在地活在自我想象中的城市。”耶路撒冷是圣城,是世界首都,是永恒之城,是世界的精髓、本质、极值。它既存在于地上,也存在于地下,还存在于形而上学空间,人类、福音书、旧约伪经书、牛顿的精神探索,都能在其中找到位置。“这里的任何一样物事都蕴藏着某些东西,它们对于整个人类(不多不少)的维持和使命都很重要……耶路撒冷是羊皮卷。”在作家看来,耶路撒冷是这样一座城市,其中不仅蕴藏着,而且每天都在展示着有关世界构造的上帝奇迹。正是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众多的《圣经》事件,单纯置身其间便能感觉到自己是其参与者。耶路撒冷的魔力在于,它抹除了过去、圣经时间与现在三者之间的界限,在新生活的肌理之下能够看到数千年历史。“整个城市本身就是神话,由众多神话建构而成……假如现实是狂风,耶路撒冷的神话便是正确扬起的风帆,其安置艺术能够确保桅杆完好无损,以便整个文明史顺利行进。”在科学理性至上的时代,圣城耶路撒冷对于神学信仰的坚守是难能可贵的,是主人公精神寻根的第一处落脚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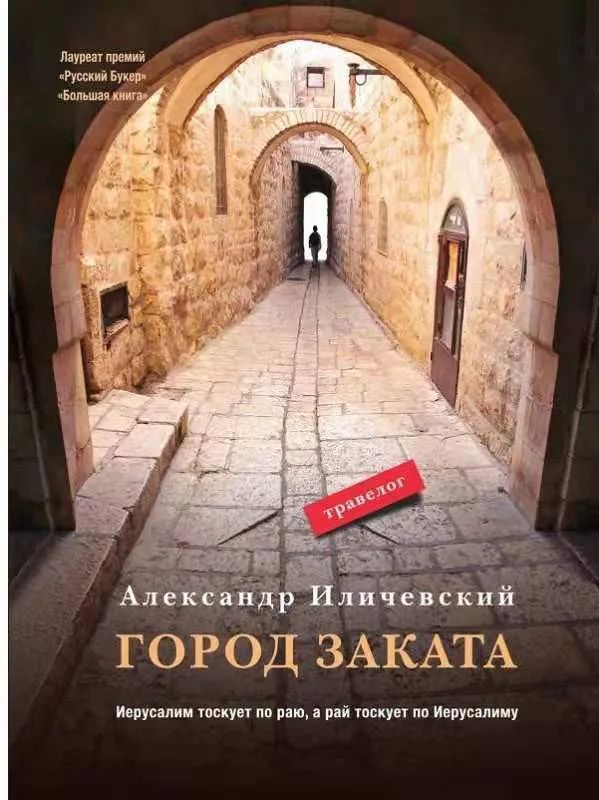
(《日落之城》,图片源自Yandex)
作家借助耶路撒冷想要传达的又一重要理念,在于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和平共处。耶路撒冷是处在时间之外的超验之地,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视为圣城,里面和平共处着那么多信仰相左之人。这在圣城堡垒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堡垒中不得不容忍很多东西,因为只有向战友让步才能够活下去。人们在这里往往能够成为一辈子的朋友,而换作其他地方,他们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撕破对方的喉咙:基布兹成员与资本主义者、左翼与右翼、城里人与乡下人、警察与违法者。在堡垒中你能见到左翼分子请右翼分子喝咖啡、吃点心,宗教蒙昧主义者对无神论者温柔以待。要知道,在战斗中保护彼此的后背是一回事,日复一日为邻人的利益而自我约束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凭借后者才能容忍别人的臭袜子和唱了八百六十遍的也门失恋情歌,而这将人至少变成了天使。”如果说在《波斯人》中作家将目光聚焦于里海这片多民族、多宗教聚集的区域,以此展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话,那么在《牛顿手稿》中,作家则将圣城耶路撒冷视作人类文明的圣地,以此寄托不同民族和谐共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想。
如果说圣城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所罗门圣殿则是世界中心的中心。小说主人公秉承牛顿遗志,追随父亲足迹,与一个科研团队一道,尝试借助三千年来自然力量在古洞穴墙壁上留下的纹路来推测圣殿轮廓,并借助先进的光学设备,以特殊方式操纵光线,终于成功地再现了圣殿影像。这个幻影在城市上空漂浮,仿佛传说中的隐城基捷日——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刺破晨雾时,人们便会看到这座幻影之城。圣殿幻影的细节和比例的真实性得到了众多犹太教拉比的证实,却在民众之间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同人群对此反应迥异:“游客们断言,这是以再现消逝的历史画面作为噱头的灯光秀;居民中的阿拉伯人愤怒不已,要求当局立即停止这种渎神行径;犹太居民则分成两派,一派恐惧而兴奋,另一派则陷入恐慌。”对于这场争论,作家并未做出评判,而只是表达了自我立场:“时间每分每秒都在充实圣殿幻影的细节,这令我惶惶不安,逼着我思考,世界是否需要圣殿,一如世界是否需要上帝。世界为何需要圣殿,我回答不出。但我确切地知道,我自己为何需要圣殿。”
最终,所罗门圣殿的复现并未揭开任何惊世秘密,而失踪的父亲依旧下落不明。由此,贯穿小说的两大悬念——父亲的失踪与牛顿手稿的奥秘——以不了了之的方式被搁置,主人公以父之名的精神寻根之旅似乎也并未终结。在笔者看来,这种开放式结局是作家有意为之。显然,对于精神寻根这一极具普世性又极具私人性的宏大命题,作家并不想给出统一结论。作家借由主人公的求索向读者提供了精神寻根的某种范式,却并不觊觎唯一的终极真理,因为在他看来,精神寻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场永不止步的朝圣之旅,每个人都应该亲力亲为。《牛顿手稿》生动地诠释了科学与神学理性融合、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精神寻觅永不止步等贯彻作家文学创作始终的核心价值观,堪称其集大成之作。借由这样的价值观,作家呼吁人类摒弃成年时代的自我膨胀与狂妄,克服对异质存在的恐惧与拒斥,重返相信神话、崇拜父亲的童年时代,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探索世界奥秘。正如俄罗斯学者罗季奥诺夫所说:“伊利切夫斯基以《牛顿手稿》对读者发出呼吁——去寻找。但不一定要去寻找所罗门圣殿。最重要的是不断追寻,而且永不止步于求得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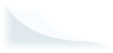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1期,“新作评论”专栏,责任编辑苏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