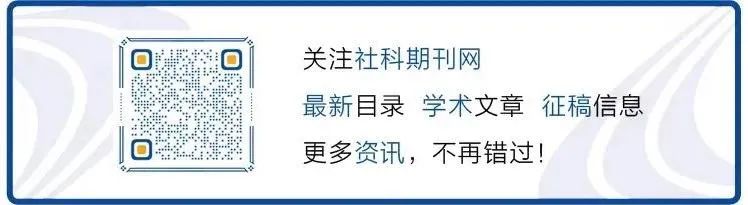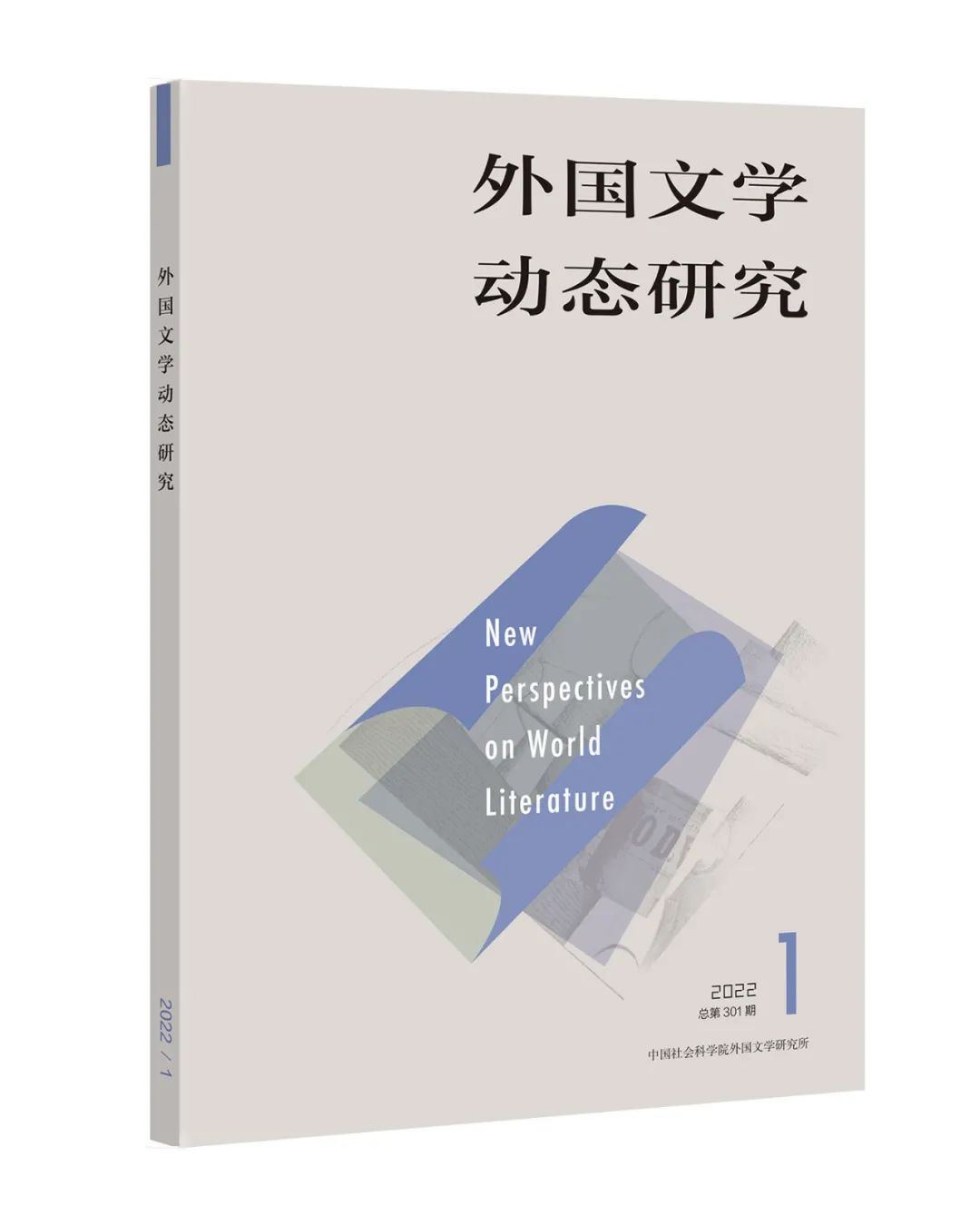作家研究| 私人文本发掘与阅读中的道德悖论——拜厄特小说《占有》中的维多利亚书信与日记

林 芸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现当代文学。出版译著《罗伯特·彭斯:动荡时代的诗歌全才》(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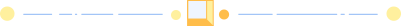
内容提要 1990年布克奖获奖作品《占有》是当代英国作家A.S.拜厄特的一部新维多利亚小说,她在书中通过“腹语术”呈现给读者风格各异、品类众多的维多利亚文本,其中的书信与日记不仅是小说叙事的媒介,更反映出作家对私人文本的发掘与阅读过程中所蕴含的道德悖论的深入思考。拜厄特提出看似透明的书信与日记可能暗含防御与诱惑的双重意志,同时探讨了读者在阅读私人文本时应如何应对自身可疑的“偷窥者”身份,并在道德疑虑和追寻真相之间做出选择。
关键词 A.S.拜厄特 《占有》 私人文本 道德悖论
1990年,英国作家拜厄特(A. S. Byatt,1936—)凭借新维多利亚小说《占有》(Possession: A Romance,1990)荣膺布克奖。在传统爱情故事和探案情节的框架内,小说叙事围绕几位当代学者通过发掘失落的文本追寻两位维多利亚诗人之间的隐秘情事展开,不同寻常的是,作家投入大量篇幅仿写了品类众多、风格各异的维多利亚文本,试图将读者带回19世纪的英国,也将关注点引向了历史书写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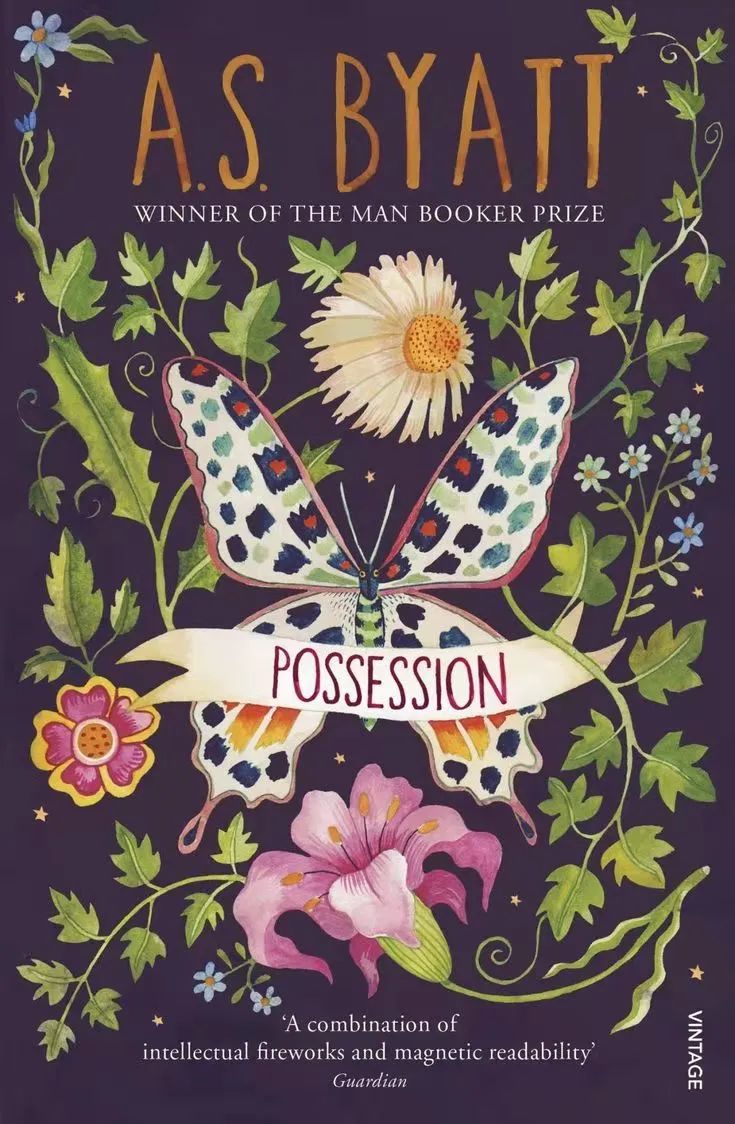

(拜厄特和《占有》,图片源自Yandex)
学者多将这部作品称为“历史编纂体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因为《占有》“对历史的叙述始终被一种自我指涉和自我反诘的后现代意识所统摄”,书中的维多利亚历史是“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中被建构的”,揭示出“那些将叙事再现简单化的概念存在问题”,小说家在构筑历史的过程中既让读者沉迷其中,也通过展露历史书写的过程揭露了这一体验的虚幻性。不可否认,拜厄特在小说中复现的各类维多利亚文本凸显了历史叙事的过程以及她对这一过程的高度自觉,但将《占有》称为“历史编纂体元小说”的问题在于,这一概念强调了历史文本的互文性中“彻底的不确定和不可靠性”,而揭示历史的文本性与虚构性似乎已被定性为后现代小说的群体特征,但《占有》恰恰是对这一症候的回应,我们读到的并不全是“关于其他阅读的阅读,关于其他阐释的阐释”。作家并没有在不断衍生的文本中颠覆故事的可信度,她强调的不是历史真实的不可知,而是什么可知,以及如何获得这样的认知,更重要的问题是当读者和研究者在追寻历史真实的过程中需要以跨越道德边界为代价时该如何抉择。因此,《占有》虽在形式上具有后现代小说的外壳,但在内核上却继承了维多利亚小说的道德严肃性,而书中的众多维多利亚文本则成为引发这一问题的契机。
评论者注意到这本五百余页的鸿篇巨制中“各种文体纷乱杂陈,交错相间……大量的文中文形成错综复杂的文本碎片”。拜厄特将这种历史书写称为“腹语术”(ventriloquism),“想要体现一个人能够真正听见那些维多利亚时代逝者的声音,我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维多利亚语序在维多利亚语境中书写维多利亚文字,并让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和在维多利亚时代一样”。她也明确指出选择这一概念的原因:“我现在希望转向一种我称之为‘腹语术’的历史书写,从而回避‘戏仿’(parody)或‘拼贴’(pastiche)中沉甸甸的道德内涵。”徐蕾认为“她心目中的‘腹语术’没有与‘戏仿’概念相关的游戏、反讽因素,也并非当代作家无法形成个性化风格、不得不胡乱拼凑的无奈选择”,而是“从古代人物的文化身份与艺术气质出发,模拟人物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独特声音,作家借由语言穿梭时空的魔力让逝去的灵魂附体于人物身上”。更确切地说,拜厄特以反讽口吻用“沉甸甸的道德内涵”嘲讽“戏仿”或“拼贴”等后现代文学批评概念使严肃认真的历史书写失去了重量,在语言游戏中消解了道德内涵而使文本变得轻飘飘,相反,“腹语术”则是抛弃了游戏与反讽态度的严肃模仿,是全情投入的角色扮演,是通过文字进入历史,唤起过去,恢复历史书写的厚重与其中真正“沉甸甸的道德内涵”。因此,她的立场绝非拆解历史文本,把这些“错综复杂的文本碎片”仅仅看作具有后现代或元小说特征的写作手法忽视了她在每一种文体仿写中所展现的问题意识及独到思考。
在这些嵌入小说的文本中,评论者的兴趣更多集中于文学性鲜明的神话、诗歌与童话,探究其中的原型、隐喻、改写以及它们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而书中大量的书信与日记则较少受到重视。一个重要却少有人提出的问题是,当拜厄特将“腹语术”作为重构历史的叙事手段时,她为何在小说中花费大量篇幅编织这些对叙事并无太大推动作用同时缺乏文学性的文本?德布拉切认为作家在重写维多利亚书信时“将这种书写女性化”,艾什与拉摩特在书信中逐渐建立的亲密关系既激发了女诗人的创造力也威胁着她独立而脆弱的“艺术家身份”。史夫曼也将书中艾什妻子的日记看作一种女性书写形式,认为在日记中表达自我是女性以一种隐秘方式颠覆了社会为其预设的刻板形象。但本文认为拜厄特对这两类文本的仿写所涉及的关键问题不是女性身份和女性写作,或者说不是谁在写,而是这类文本自身所蕴含的矛盾,因为它们不只是个人表达的途径,也在时光流转中成为一类特殊的史料,通过在小说语境中虚构书信与日记,拜厄特不仅呈现了它们从私人文本转变为公开文本的过程中为书中的读者和研究者设下的陷阱、诱惑与道德困境,也将小说读者置于类似境地,在两个层面上探讨了私人文本发掘与阅读中的道德悖论。


作家的日记与书信比他们的文学创作更透明吗?拜厄特通过将此类私人文本嵌入小说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占有》中,艾伦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艾什的妻子,去世后留下一部冗长的日记,乏味到让那些想在日记中发掘微言大义的后世学者感叹“艾伦·艾什非常无趣”。在第十二章,拜厄特用约十页篇幅呈现出日记的冰山一角,它们写于艾什和女诗人拉摩特陷入婚外情后去约克郡私会之时,而艾伦在日记中只像流水账一般记录了家务琐事,似乎对婚姻危机一无所知。这种平静似乎符合人们对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天使”的想象,但艾伦过度模式化的自我呈现也让小说中的当代学者产生了怀疑,莫德读过日记之后就困惑地说:“她是怎样一个人,我无法形成清晰的概念,也说不出自己是否喜欢她。她谈到一些事,有趣的事,但这些无法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负责艾伦日记编撰的比阿特丽斯则在漫长的苦读岁月之后猜测道:“我想她知道会有人读她的日记”,“她写日记是为了迷惑”,这种迷惑性源于她“有计划地遗漏”了一些内容。
日记虽以自我倾诉为动因,但难以排除“日记文本内部‘隐身听者’的存在。尽管这一‘隐身听者’是沉默的、无言的,没有独立的话语权,但其存在本身必然影响甚至左右日记的写作。‘文饰’就是日记隐身听者存在的产物,从而在根本上导致了日记真实性和自由度是相对的、有限的”。当日记作者意识到可能会有旁人翻开日记,这种私人书写就不再是映照内心的镜子,而成了一道不透明的帐幕,甚至可能成为作者在和想象中读者的互动中编织的语言陷阱。那么艾伦日记中的“隐身听者”是谁?作为著名诗人的妻子,她意识到自己留下的文字有可能会成为后世研究者或猎奇者争抢的对象,为了保护丈夫的私生活免遭窥探,她对日记进行了“文饰”,放大可说的,隐去不可说的,从而迷惑预料中的“隐身听者”。
然而艾伦又为何留下一部日记?如果书写是为了隐藏,不写岂非更彻底的隐藏?在第二十五章,艾伦日记再次出现,在丈夫去世当天写下的这篇日记中,她透露出有些重要的信件未曾焚毁,而是随诗人葬入了坟墓和“文饰”日记的谨慎相比,这是一种鲁莽而危险的泄密,原因何在?在临近尾声的这一章中,拜厄特用全知叙事手法将隐藏在日记之后的艾伦推到幕前,直接描述了她写下日记后的内心活动:“她坐下继续制造日记中那些谨慎编辑、小心过滤(strained,这一隐喻来自果冻制作)的真相。之后她会决定拿它怎么办。对于那些正在聚集的尸鬼和秃鹫,这既是防御,也是诱饵。”“尸鬼”和“秃鹫”均以死尸为食,暗指那些在诗人身后逐利之徒,“制造”含有设计、编造之意,“过滤”则利用制作食物的隐喻强调去除与筛选,艾伦“文饰”日记的目的透露无疑。“防御”是为了保护逝者,同时,艾伦也解释了为何要留下日记作为“诱饵”:
如果尸鬼又将它们掘出该如何?
那么她或许可以得到公正的评价,当我不在此世作为见证的时候。

(艾米莉·狄金森,图片源自Yandex)
通过展现艾伦日记中防御与诱惑的双重意图,拜厄特探讨了这一私人文本所蕴含的复杂与矛盾,同时影射了现实中作家书信与日记的真实状态。她曾提到女诗人拉摩特的原型是艾米莉·狄金森,而狄金森本人的书信就“充满了机巧、奇思和谜团”,她会针对不同收信人采用不同风格,并在信中虚构“面具人物的自我”,这使得她的书信和诗歌一样“变成了虚构作品”。书信和日记虽然并不透明,但其私密的属性必然引发读者对作者自我表白的期待,尽管这种表白所揭示的所谓内心真实往往只是另一重面具。拜厄特在《占有》中对私人文本复杂性的探讨不仅展现了日记与书信作者的多重心理,也引出了私人文本阅读者可能遇到的问题。


回看文学史,现实中的伟大作家最彻底的自我保护是直接或间接毁去那些他们不想公之于众的私人文本,简·奥斯丁的姐姐在其死后烧掉了她的信,奥登要求朋友销毁他们手中的信,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占有》中,艾什临终前对妻子说:“烧掉一切他们不应该看的东西”,“和我们的记忆一起烧掉对于我们来说有意义的一切,让任何人都无法将它们变成闲置的古玩或谎言”。通过这一取材于现实的作家遗愿,拜厄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读者对作家私人资料的发掘有无道德底线?对真相的追求是否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在遵循作家遗愿和追寻真相之间应如何取舍?

(简·奥斯丁,图片源自Yandex)
奥登写道,“今日大量被当成是学术研究的活动,其实无异于趁他人外出而偷阅其信件。从道德上而言,他人外出,还是进了坟墓,偷阅他人的信件都是一样的不好”,“我们应该牢记,大多数的天才艺术家都宁愿不要人为他们写传记”。《占有》中当代学者揭秘维多利亚诗人恋情的故事恰恰起于偷窃,终于掘墓。小说开篇,罗兰在伦敦图书馆的一本书中发现了艾什写给拉摩特的第一封信的草稿,并将其偷走,这一具有“原罪”性质的行为成为揭开真相的起点。小说临近结束,克罗普教授掘开艾什的坟墓,找到了拉摩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划上了故事的句号。从学术道德角度看,两位学者均有污点,但作家对他们的刻画却截然不同,罗兰最终成为一位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而克罗普则成了全书最大的反派。面对同样的学术不端,拜厄特一褒一贬的写法中是否存在双重道德标准?本文认为,她的判断标准似乎不在罪行的轻重,而在行事的动机。

(奥登,图片源自Yandex)
罗兰在读到艾什书信草稿的一瞬间就出于“学术本能而异常兴奋”,不仅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伟大学术发现的隐秘入口,更使他着迷的是信中所展现出的一个和固有形象完全不同的艾什,因此他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一种类似于求知欲的“冲动”,而非“偷窃”。之后,他不断对自己也对他人解释窃信的动机,并将个人的好奇心与独占发现成果的学术贪婪划清界限:
“好吧,我希望成为完成这项工作的人,”罗兰开口时没有多想,但他立刻看到自己遭受的侮辱,“等一下——事实不是那样,完全不是。这是切身相关的一件事,你不明白。我是个老派的文本批评家,不是传记作者——我做这件事并非为了这一类的——不是为了利益……”
“我只是想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

相比之下,作家对克罗普教授盗墓行为的刻画则迥然不同,他成为反派并非因为盗墓在道德上更加不可原谅,而是因为动机不纯。艾什研究专家、财大气粗的美国学者克罗普教授四处重金搜罗和诗人有关的物品,对物的占有是为了彰显出身份与地位:“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挥舞着权力”,“支票簿带来的权力”。作为一个典型的发死人财的传记作者,他像占有财物一样占有与艾什生活相关的一切。在掘墓前,他谈到可能装有书信的铁盒:“它的价值多少取决于我对它的估价”,“即使里面空空如也依然价值高昂”。随后,作家在描写他于夜黑风高的雷雨之夜掘墓被捉的戏码时,运用了一系列哥特元素,刻意营造出一种荒诞的闹剧氛围,通过戏仿狄更斯小说中恶棍遭惩的经典场景将他塑造成典型的反派,以这种高度风格化的手法对他进行了嘲讽。
此外,书中当代学者的道德疑虑还来源于是否应该将本不该进入公众视野的私人文本公之于众。克罗普掘墓被抓后,学者们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处理艾什墓中挖出的铁盒:
她环顾四周,发现无人响应。莫蒂默·克罗普说:“如果你们真的这样认为,你们在我发现它之前就可以行使公民权自行逮捕我了。”
布拉凯德说:“这话确实没错。”
利奥诺拉说:“如果她不想让人发现,为何又任由人们找到它?为什么没有将它放在她的怀中,或者他的怀中?”
莫德说:“我们需要故事的结尾。”
“无法保证那就是我们将要发现的东西,”布拉凯德说。
“但我们必须看一眼,”莫德说。


尽管学者们对真相的追求冲淡了道德上的疑虑,但不可否认阅读私人文本依然类似于偷窥。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偷窥有违作家意愿,罗兰窃信之后才有意私藏,避免将诗人的秘密公之于众。在发现两诗人书简后,罗兰明确说,“我们并非寻找丑闻”,相反,他与莫德担心书信的命运,因为“它们是私人的”,因此不希望书信最终出现在展示柜中。他在阅读艾什写给拉摩特的书信时感到不安,因为和艾什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不同,“这些信,这些专注而充满激情的信从来也不是写给他看的”;但罗兰与莫德依然通读了艾什与拉摩特之间的情书,更为复杂的是,拜厄特在第十章用近五十页篇幅将这些情书直接呈现给读者,使小说读者和书中学者一起变身为他们本不该成为的“隐身听者”,成为偷窥私人信件的同谋。
从推动叙事的角度而言,题为“书简”的第十章似乎并不必要。罗兰和莫德早在第五章就已发现这些情书,在第八章开始分头阅读两位诗人的书信,到第十章悬念已经铺设充分,但这五十页书简并未揭开悬念,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的几次见面和最后的分开,但发生过什么依然成谜。拜厄特曾借罗兰之口探讨过书信的特质:“书信是一种无法预设尾声的叙事方式,没有闭合的结尾……书信不讲故事,因为他们不知道一行行读下去自己会走向何处……最终,书信不仅不把读者看作共同作者、预言家或猜谜者,也不把读者看作读者;如果是真实的书信,它们只写给一位读者。”因为书信是只写给收信人的,因此所有第三方读者都会成为偷窥者。这不仅是一种道德困境,也给阅读带来困难,因为写信的双方会因为排除了其他读者而写下心照不宣的文字,同时在信中留下断裂与空白。
但这漫长而考验耐心的第十章又必不可少。在这部有着侦探小说结构的作品中,读者也许期待在开篇三分之一处的这一章中发现更多线索,但他们却迷失在旁枝错节的文字中,同时也在一封封书简内处处分叉的小径中渐渐遗忘寻找线索的企图,而被文字本身吸引。与18世纪书信体小说不同,拜厄特淡化了书信的叙事功能,但也充分利用了其作为“写信人内心生活最为直接的物证”的优势,展示了艾什与拉摩特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和读者所期待的充满甜言蜜语的情书不同,两位诗人的书简包罗万象,他们以理性的笔调谈到阅读与写作,谈到一个时代的信仰危机,谈到科学与道德,谈到对爱情的理解和各自的生活状态,同时在文字上展现出一种难以概括的丰富与充盈,拜厄特在仿写过程中常常用长句和破折号再现两位诗人语言的精致与曲折,以及自然迸发的诗意。作为“腹语术”的直接例证,拜厄特在第十章中通过“按照维多利亚语序在维多利亚语境中书写维多利亚文字”,使小说的读者“真正听见那些维多利亚时代逝者的声音”并进入那个时代。通过这五十页的文字旅程,小说读者从道德上可疑的私人信件偷窥者变成了诗意心灵的倾听者。
相比于书中的当代学者,拜厄特对小说读者更为慷慨,她将书中学者发掘的书信与日记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使读者在阅读中分享了胜利果实,却不必背负书中偷信掘墓者所面对的道德谴责,而是带着清白的良心与超脱的姿态坦然潜入这些私人文本深处,分享两位维多利亚诗人心灵的激情与思想的温度。因此,小说第十章也具有某种治愈读者的功效。德布拉切发现,与小说中大量的维多利亚书信相比,罗兰与莫德之间仅有的八封书信并未成为表达爱情的途径,相反,这样一种原本亲密的书写形式“展现出两个人物之间的忧虑感”,作为一种时代和文化的症候,对爱情缺乏信任使他们“无法通过文字交流表达自我”。因此,对于罗兰与莫德,追寻这段维多利亚罗曼史的旅程也是自我探寻的救赎之旅,而当代小说读者多少拥有和他们同样的后现代症候,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我们所知甚多,但知识的重负所造成的信仰缺失与普遍怀疑也带来了感受力的磨损与情感的疏离,如拜厄特所言,“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们……严肃地对待‘爱’,而现代人则用现代或后现代的批评术语去思考这个问题”,而通过私人文本进入具有情感温度的历史时刻是拜厄特治疗这一症候的方式。沙特尔沃思在评价《占有》时写道:


拜厄特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导师海伦·加德纳认为作家之所以反对成为传记书写的对象,是因为他们知道“传记作家的焦点将几乎完全集中在他个人的私生活……寻找那个‘真人’会阻碍甚至扭曲作家‘第二自我’的反应——正是作家的‘第二自我’,才写下了那些诗歌或小说,并通过它们‘生活和言说’”。但她也同时指出尽管作品“独立于作家汲取来创作它的那些经验和情绪”,但那些关于“作家的经验和情绪”的传记信息“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和享受。这其实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评方法”。拜厄特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与其老师不谋而合,一方面,她虽然通过“腹语术”呈现了与艾什和拉摩特相关的私人文本中隐藏的“真人”,让书中的当代学者们带着道德污点不择手段地潜入两位诗人的私生活,但也传达出学者们对自身行为的疑虑以及作家对私生活被窃取的不安。另一方面,她同样以“腹语术”和更多的篇幅仿写了两位维多利亚诗人以“第二自我”创作的诗歌,暗示只有艺术作品才是传记研究的最终目的并具有永恒的价值,同时通过罗兰和莫德的经历展现作家私人文本中透露出的“经验与情绪”能够带来悸动人心、重塑读者的阅读体验。在这两类文本的交织中,拜厄特和加德纳一样相信了解作家的内在人生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和享受,并最终加深我们对于自身与当下的领悟,即使对于私人经验与情绪的获取可能使读者进入道德的幽暗地带,她对这一矛盾的探讨传达出对人文主义阅读与批评传统的信念与反思。

(《占有》的电影海报,图片源自豆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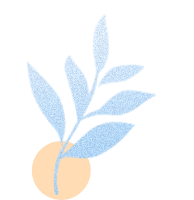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