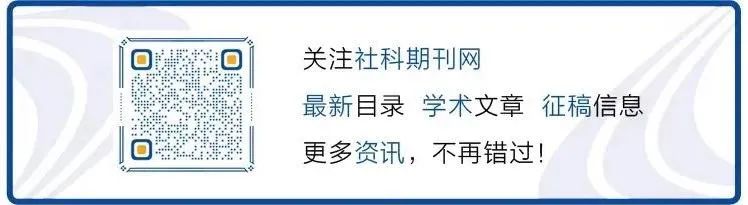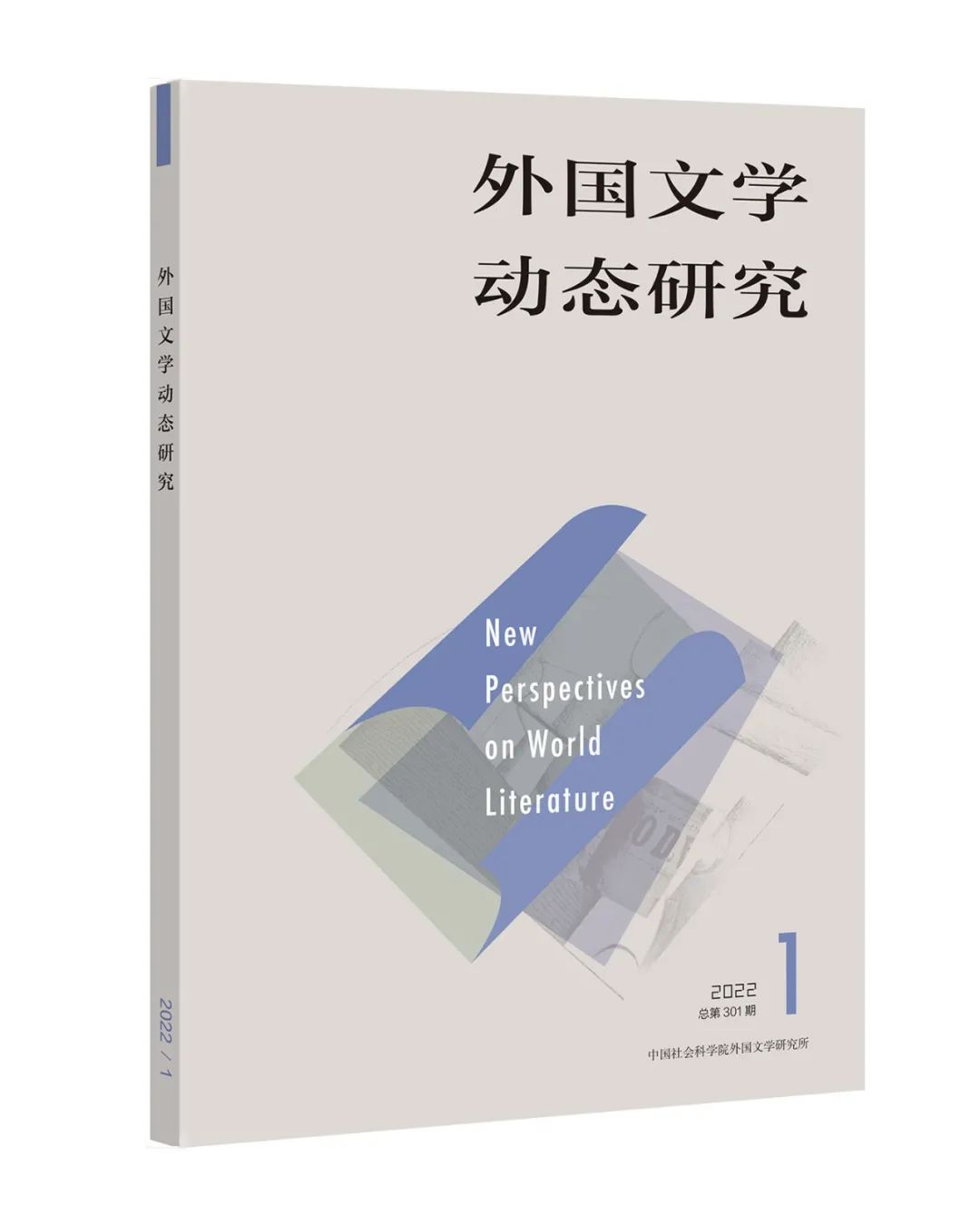动态研究 | 论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民族性

何宁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出版有专著《哈代研究史》和编著《20世纪英国文学史》等。

内容提要 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英国文学主流的视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索利·麦克林、安格斯·麦克尼凯尔和克里斯托弗·怀特等诗人的创作承继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古老传统,以具有民族色彩的独特视角来书写当代苏格兰的各种社会问题,并在艺术风格和形式上对苏格兰盖尔语诗歌加以拓展,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推动了苏格兰盖尔语文化进入当代英国社会文化生活。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发展中呈现的民族性,让人们得以反思当代苏格兰主流民族文化的形塑,进一步丰富了当代苏格兰民族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 苏格兰 盖尔语 当代诗歌 民族性

在当代苏格兰诗歌的发展中,英语诗歌是其中绝对的主流,但另外两种语言的诗歌作品,即苏格兰语(Scots)诗歌和苏格兰盖尔语(Scottish Gaelic)诗歌,也构成了当代苏格兰诗歌不可或缺的部分。早在20世纪初,苏格兰语诗歌经由休·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1892—1978)的创作进入了英国诗歌主流。在麦克迪尔米德之后,几乎所有的当代苏格兰主流诗人都用苏格兰语创作过诗歌,从而赋予了苏格兰语新的文学生命,并通过诗歌进一步传播了苏格兰语。与苏格兰语的广泛使用不同,苏格兰盖尔语目前的使用者不及使用苏格兰语的十分之一,而且使用地区仅限于苏格兰北部。正因如此,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为英国主流文学界所了解和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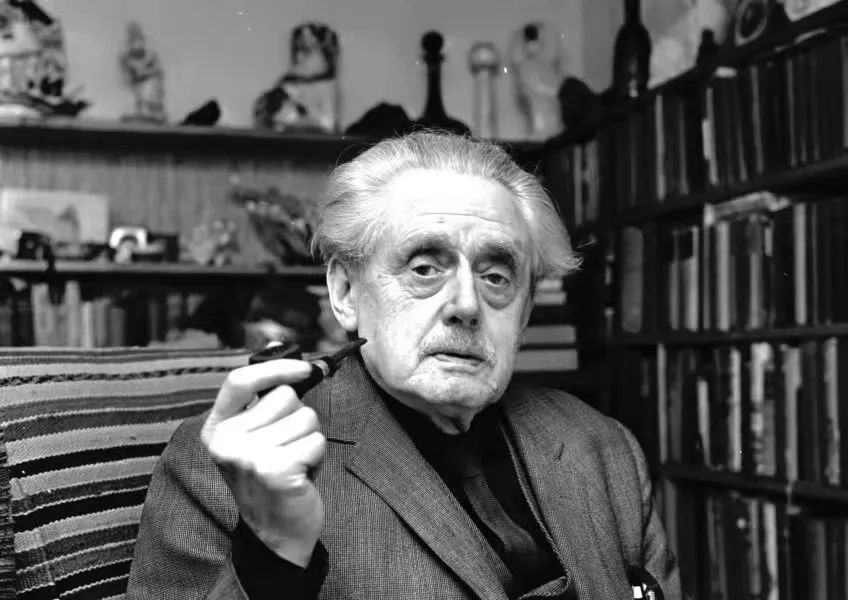
(休·麦克迪尔米德,图片源自Yandex)
虽然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创作贯穿了整个20世纪,但直到1971年伊恩·克莱顿·史密斯(Ian Crichton Smith,1928—1998)将诗人索利·麦克林(Sorely Maclean,1911—1996)的《致艾米尔的诗》(Poems to Eimhir)翻译成英语以后,这部以爱情的甜蜜与失落的痛苦为书写主题的诗集才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意识到了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存在。1976年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出版了英语和苏格兰盖尔语对照的双语诗歌选集《现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Modern Scottish Gaelic Poems),收录了麦克林、乔治·坎贝尔·黑(George Campbell Hay,1915—1984)、伊恩·克莱顿·史密斯、德里克·汤姆森(Derick Thomason,1921—2012)和诗集的编者唐纳德·麦考利(Donald MacAulay,1930—2017)的诗歌作品。这部诗集让苏格兰盖尔语诗歌得到了当代英国诗坛的关注,也奠定了之后苏格兰盖尔语诗集双语出版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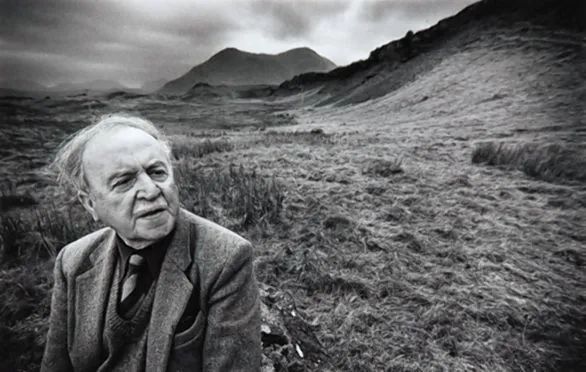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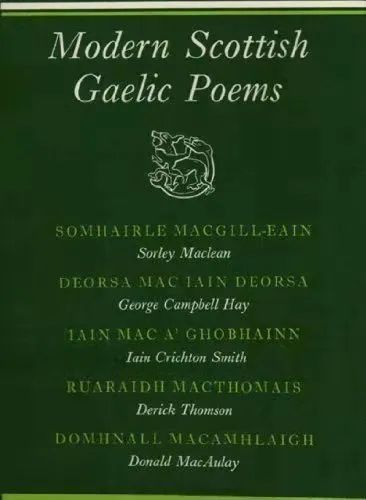
(索利·麦克林和《现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图片源自Yandex)
在近五十年的发展中,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创作对苏格兰盖尔语文化民族传统予以弘扬,对当代苏格兰的社会问题加以呈现和思考,丰富并发展了当代苏格兰民族文化,得到了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代英国诗歌中具有独特影响的声音。

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人在创作中,首先关注的是对苏格兰盖尔语诗歌民族传统的承继与发展。传统的苏格兰盖尔语诗歌擅长情感书写,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人承继了这一特色,创作出不少动人的爱情诗歌。诗人安格斯·麦克尼凯尔(Aonghas MacNeacail,1942—)的作品《牧神节》(“lupercal”)将动人的意象融入流畅的韵律,赋予传统的爱情主题以新的活力。

在爱情萌芽日
让心发出
最温暖的思绪
爱情的泉水
让心去寻找
欢乐的海洋
在爱情萌芽日
让亲吻比
小时更长
比风更甜蜜
如果微风
忽然变得凛冽
我们将安然在
彼此的拥抱中
犹如两支完整的蜡烛
相互照亮

诗歌用简洁的语言刻画出爱情的意象:爱情的泉水、欢乐的海洋。恋人在风中甜蜜地接吻,紧紧依偎在一起。尽管用词和韵律毫不繁复,也并没有刻意创造新的意象,但麦克尼凯尔的成功之处在于将诗歌的所有元素都融合得恰到好处,“爱情萌芽日”(latha pór gaoil/love seed day)与诗歌的标题“牧神节”(lupercal)的音韵相同,情感层层递进,直到最后以彼此燃烧的蜡烛将爱意的表达推向高潮。成功的情感书写让这首诗歌得到评论界的好评,入选了2008年苏格兰最佳诗歌。
受到叶芝和麦克迪尔米德等20世纪英国民族诗人的影响,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为苏格兰盖尔语地区塑造了民族文化的代表意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是麦克林在诗歌《翰雷格》(“Hallaig”)中所书写的苏格兰盖尔语地区乡村翰雷格。翰雷格是麦克林家乡拉塞岛(Raasay)上的乡村地名,经过诗人的艺术创作,融合对这一地区的古老文化和历史上的文化清洗的回忆和反思,成为当代苏格兰盖尔语文化的标志意象之一。作为苏格兰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一个多世纪的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彻底改变了苏格兰高地和北部岛屿的生活方式。贵族出于经济利益,将土地上的农民赶走,改为牧场养羊。这不仅让无数苏格兰高地人流离失所,不得不南下就业,并且在之后由于饥荒而迁徙北美和澳大利亚,造成了苏格兰民族世界性的流散。虽然清洗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但毫无疑问,它是“对一种活态文化的攻击”。在高地清洗之前,苏格兰高地和北部岛屿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家族生活,这正是诗人在作品呈现的苏格兰盖尔语民族文化。

他们还在翰雷格,
麦克林和麦克劳德家族,
所有麦克·吉尔·查卢姆时代在那里生活的人:
逝去的人都还活着。

与叶芝在《因尼斯弗利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中所表达的情绪不同,面对已经完全被毁弃的翰雷格村,麦克林明确表达出对传统文化被破坏的哀伤和痛心。对一心建构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叶芝而言,因尼斯弗利岛的自然风貌是民族过往历史积淀的象征,而对麦克林而言,毁弃的翰雷格则是民族文化被野蛮破坏的见证。诗歌首尾呼应,以鹿的意象贯穿诗歌的始终,与诗歌所描述的地方十分贴合,因为拉塞岛(Raasay,盖尔语为Ratharsair)在盖尔语中的意思就是狍之岛(Isle of the Roe Deer)。从篇首语的“时间,这只鹿,在翰雷格的树林中”,到诗歌结尾书写子弹将会击中时间这只鹿,让翰雷格的一切都就此冻住,“只要我活着,他的血就不会被找到”,诗人表现出守护和发展苏格兰盖尔语文化的坚定决心。麦克林在这首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代表作中,以树木和鹿这对苏格兰盖尔语地区的典型意象来书写苏格兰盖尔语民族文化传统,思考当代苏格兰盖尔语文化的未来,让翰雷格作为苏格兰盖尔语民族文化的象征得到英国主流文化的认同,也让自己“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盖尔语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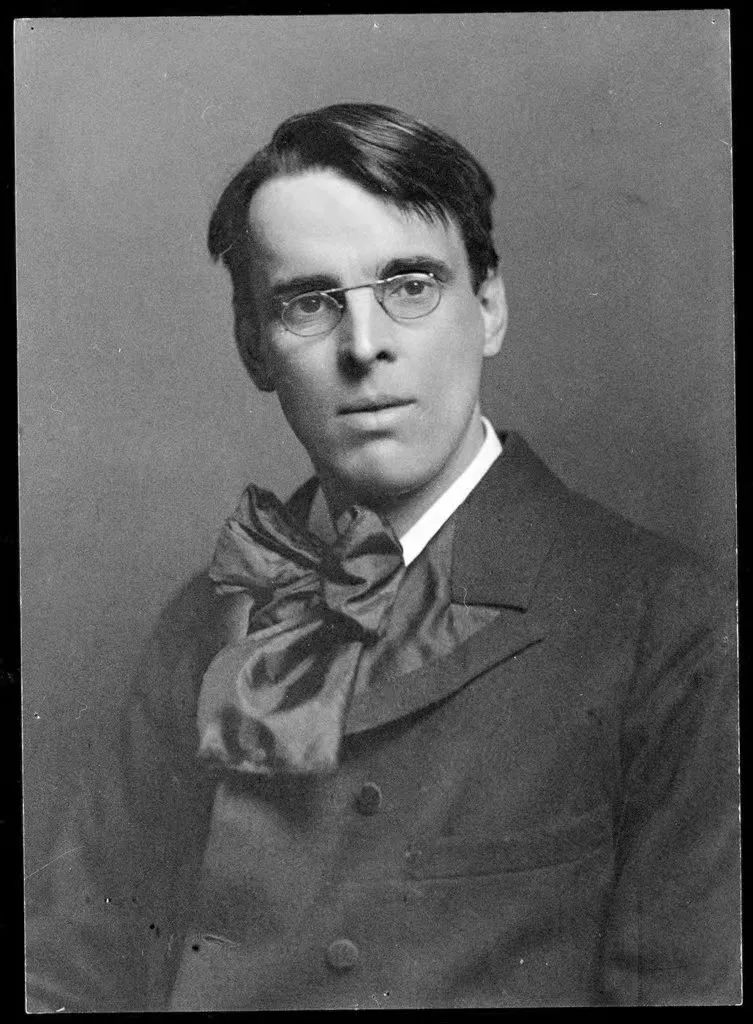
(叶芝,图片源自Yandex)

在承继传统、让世界认识苏格兰盖尔语民族文化之外,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能得到读者的广泛接受,原因还在于诗人们对民族性的书写并没有沉湎于对过往传统文化的追怀,而是在创作中运用苏格兰盖尔语这一古老的语言来关切当下的苏格兰社会生活,真正让苏格兰盖尔语民族文化融入当代世界的多元文化发展之中。在诗歌《真正的宣言》(“the real manifesto”)中,麦克尼凯尔用简洁的诗句,对当代英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阐释了自己的看法,议题涵盖经济、贸易、工业、国防、外交、教育、住房、卫生、艺术、法律和媒体等。对当代社会中对人们生活影响广泛的媒体,诗人这样写道:

媒体
如果他们说出真相
我们会说是谎言
如果他们说的是谎言那它们
肯定不会是我们的谎言

麦克尼凯尔将人们与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简练的诗句形象地呈现出来。一方面,人们对媒体具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即使媒体报道是真实的,也会被认为是谎言,阴谋论的想法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人们也习惯于将一切问题的产生都推卸给媒体,而逃避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正如诗歌的第二段所描写的:人们沉浸在媒体的谎言中,逃避真相,却认为这一切与自己毫无关系。与对媒体的普遍看法不同,麦克尼凯尔以辩证的形式对当代媒体的乱象予以反思,指出媒体的报道之所以会不真实,是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共识:人们不希望得到真相,同时又将这一问题推给媒体。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心理,造就了当代大众与媒体之间不断相互指责、实则相互依存的关系。诗人对当代媒体的乱象予以辩证地分析,认为正是大众的心理需求造就了媒体各种不负责任的虚假报道。麦克尼凯尔以简短的诗行批判了当代社会的重要议题:对教育费用高昂的批评、对住房困难的嘲讽、对法律管制的反思等等,简洁深刻又发人深思。对当代英国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既拓展了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题材,又让盖尔语诗歌获得了广泛的读者关注,从而让苏格兰盖尔语诗歌成为当代英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从20世纪后期开始,生态和环境议题一直是当代英国诗歌关注的重点,当代盖尔语诗人积极参与对生态议题的思考,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麦克尼凯尔在诗歌《三样东西》(“three things”)中采用苏格兰盖尔语诗歌传统的歌谣形式,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掠夺。

鲑鱼来自水池
鹿来自沼原
树来自森林
三样东西
从自然里拿走
不是犯罪
松鸡、鲑鱼和鹿
……还有土地、土地、土地
他们是谁的
谁偷走了他们
他们是谁的
谁偷走了他们
他们是谁的
谁偷走了他们

诗歌中的三样东西都来源于自然,把他们拿走究竟是不是犯罪呢?虽然诗歌开头的黑体部分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最后三个诗段却反复追问,这些自然中的东西究竟属于谁,并明确地用“偷”来指称拿走他们的行为,与黑体部分形成强烈的反差。诗歌开头的论断代表着人类的传统认识,表现出对自然予取予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之后重复的追问则表达出诗人对生态的关切,是当代苏格兰民族对自然和人类关系的反思,体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省,意在强调对自然生态的保护。麦克尼凯尔在承继传统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歌谣风格的同时,融入了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诗歌艺术手法,通过诗歌中不同字体的对比来彰显诗歌的主题。诗歌的风格既有苏格兰盖尔语诗歌传统歌谣的特色,也有语言诗歌流派的影子,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得清晰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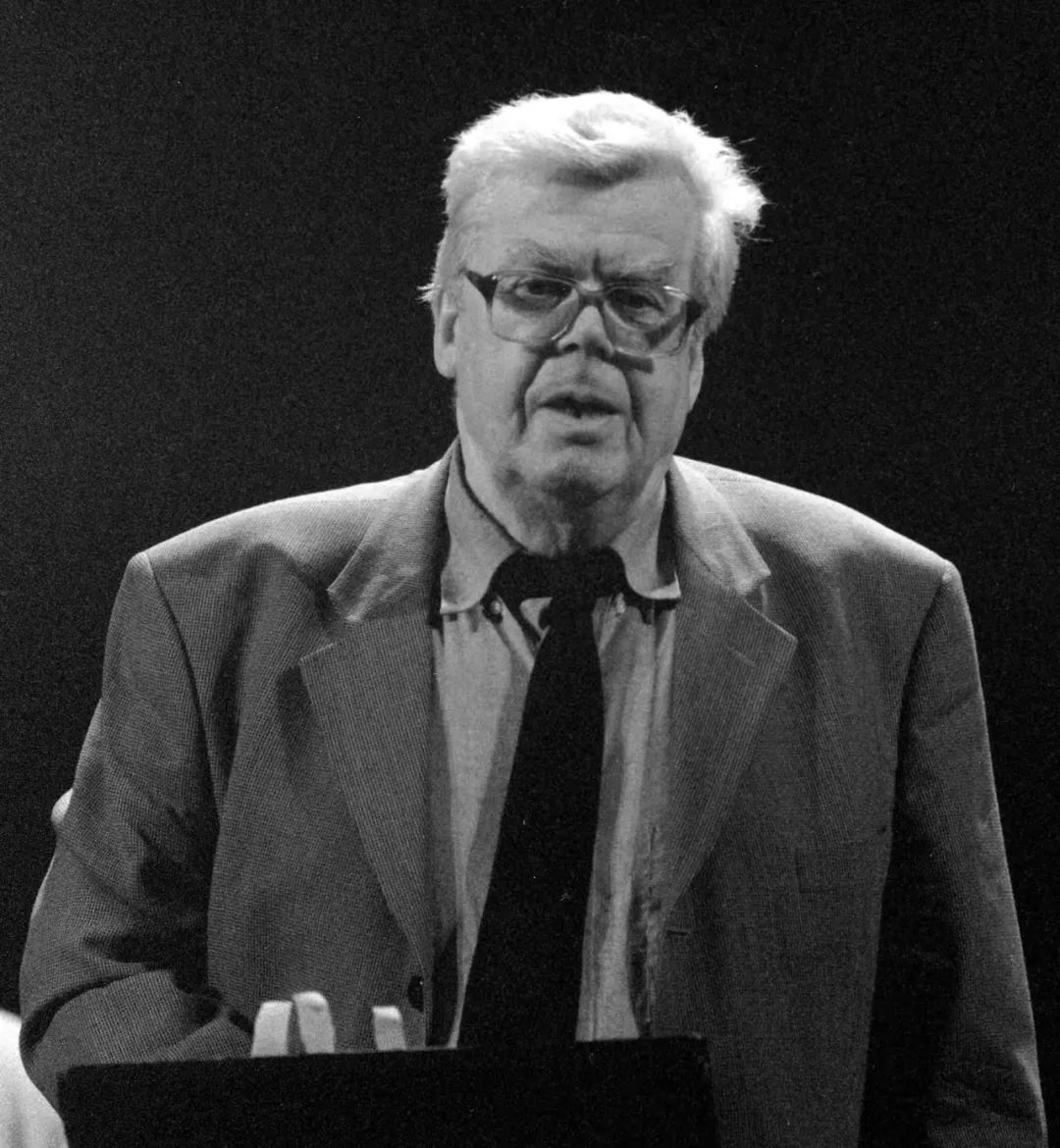
(德里克·汤姆森,图片源自Yandex)
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不仅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书写,同时还注重对民族诗歌创作的丰富和创新,以融入以英语文学为主导的当代英国文化。诗人德里克·汤姆森首先用自由体(free verse)来创作苏格兰盖尔语诗歌,打破了传统苏格兰盖尔语诗歌在韵律和节奏方面的限制,为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也成为之后苏格兰盖尔语诗人主要采用的诗歌形式。汤姆森的革新不仅得到了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人的追随,更得到了英国主流文学界的认可。他在1982年出版的诗歌合集《劫掠竖琴》(Creachadh na Clàrsaich/Plundering the Harp)成为首部获得苏格兰十字年度书籍奖(Saltire Book of the Year Award)的盖尔语作品,标志着苏格兰盖尔语诗歌正式为当代英国主流文化所接受。麦克尼凯尔则引入美国语言诗歌和垮掉派诗歌,尤其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艺术风格,赋予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现代气息。与卡明斯(E. E. Cummings)相似,在几乎所有的诗歌创作中,他都采用小写字母,只在少数诗歌标题中采用大写,同时还运用诗行中的断句、留白的长度等形式主义的技巧来传达诗歌的内容,深化想要表达的主题,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麦克尼凯尔诗行中使用的“这些空间,与诗行间的断行一起”构成了他诗歌中基本的节奏元素,铸就了诗人的个人风格,为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增加了新的活力。

(卡明斯,图片源自Yandex)
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人通过对诗歌传统的反思,来进一步推进盖尔语诗歌的现代化,从而得以更好地与当代英国文学主流融合。在书写母亲的诗歌《我看见苹果丛中的你》(“i saw you among the apples”)中,麦克尼凯尔将对逝去母亲的回忆与苹果、夏娃和自己的童年记忆融合起来,把情感与哲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同时加以书写,情感动人,哲思深邃,体现出他在创作中对主题和风格的出色融合。诗歌中既有真挚的母子情感展现,也有对女性生活的描写,还穿插了对记忆、话语和权力结构的反思。诗歌开篇描写的母亲形象温馨感人:

啊,记忆中的母亲
我看见苹果丛中的你
在修剪树木
你在想着甜蜜的事

诗人在之后的诗歌段落都用“虽然”(though)来开头,以反复的转折将对女性生活的反思,推演到对社会话语建构的批判。第二段借母亲的去世指出《圣经》是关于“夏娃和苹果和/男人的诱惑”,而第三段则将母亲的生活总结为“一次爱情和寡居”。在诗歌的最后一段,诗人以对母亲的记忆来呈现社会对女性和话语的建构。

虽然我会说是你在说话
但当我的希望是
听到你的声音之时
说话的是我记忆中的你
而在我的记忆中每到
说话的时候你很少会多说
如同离开伊甸园的夏娃

诗人在这里将自己对母亲的记忆、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和女性角色的社会建构融合在一起。在诗人自己的记忆中,母亲总是会说话的,但事实上,生活中的母亲一向沉默寡言。由此,记忆中的母亲呈现出一种矛盾性:诗人所期待的母亲和诗人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母亲并不相同。母亲之所以在有机会说话时保持沉默,原因来自于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在作品的结尾,诗人指出母亲之所以接受传统中压制女性的社会文化,源于她所受的学校教育。通过书写母亲的寡居生活、苹果树丛中的辛勤劳作和沉默少言的现象,麦克尼凯尔将受到苏格兰盖尔语文化传统束缚的女性生活予以呈现,并对造成这一现象的教育和社会文化体系予以批评。诗人通过苹果这一意象将记忆中的母亲和《圣经》中的夏娃联系起来,对苏格兰盖尔语的民族文化传统予以整体性反思,让诗人获得了“吟游诗人的声音所需要的深度和庄严”。
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的创作不仅对苏格兰盖尔语的民族传统文化予以思考,更为整个苏格兰民族文化的自我审视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视角。苏格兰诗歌的传统是对民族文化的吟唱。20世纪的苏格兰诗人承继这一传统,以自己的诗歌创作推动当代民族文化的形塑。但是,如同克里斯托弗·怀特(Christopher Whyte,1952—)所质疑的,苏格兰文学这种理想化的民族传统通过文学经典和社会建构将苏格兰民族传统与父权体系捆绑在一起,从而压制了其他群体在苏格兰民族文学中的声音。因此当代苏格兰的文学批评传统需要修正,仅仅关注文学中的“苏格兰性问题”是不够的,文学批评家们迫切需要从各种多样的视角来考察苏格兰文学。对用苏格兰盖尔语来进行诗歌创作的怀特而言,考察苏格兰文学“不同的视角”之一无疑就是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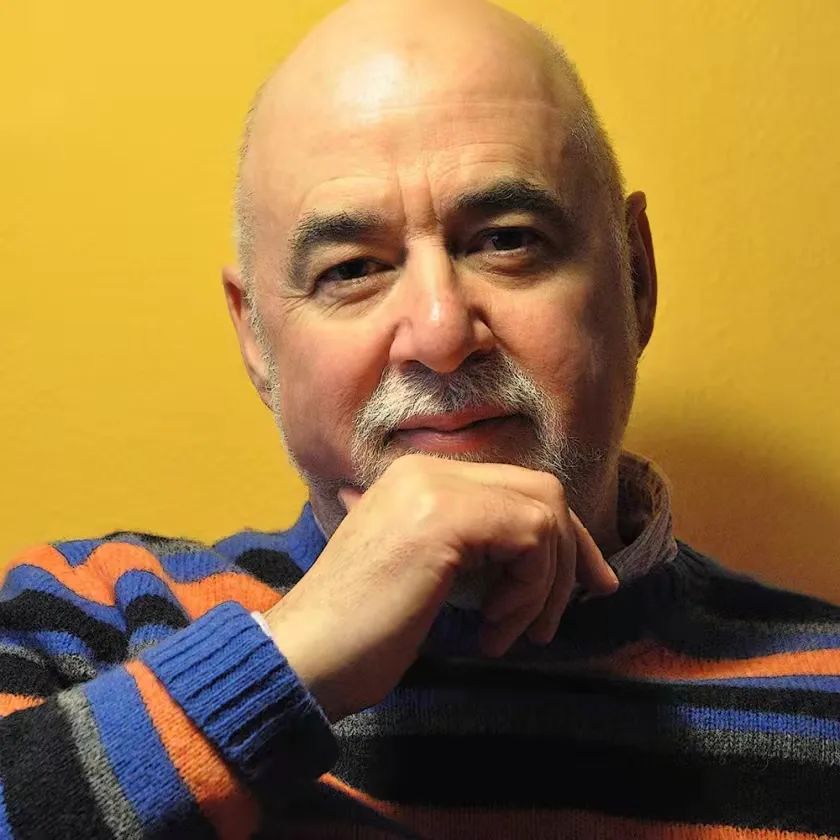
(克里斯托弗·怀特,图片源自Yandex)
作为当代最具争议性的苏格兰诗人之一,怀特对苏格兰诗歌的主流传统不以为然,并试图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和评论予以打破。在诗歌创作方面,他破除了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人约定俗成的规矩,不为自己的盖尔语诗歌同时提供英语版本。尽管他本人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但他坚持认为应该由他人来翻译自己的诗歌作品,并为此撰文《反对自我翻译》(“Against Self-translation”)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从批判的角度来审视当代苏格兰诗歌对传统毫无保留的推崇,将这种民族传统对内部不同声音的压制作为问题提出,从而真正将苏格兰文学传统予以现代化。在怀特的作品中,他对作为苏格兰少数群体语言的盖尔语重新加以形塑,打破了人们对苏格兰盖尔语的刻板印象,将它作为一种新的、让诗人发声的语言:“他们告诉我你很古老,/但你的青春活力让我着迷。”在怀特看来,盖尔语和其他语言具有同样的生命力,不足之处在于当代词汇的匮乏。
作为苏格兰的原生语言,苏格兰盖尔语是苏格兰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根据人们普遍接受的盖尔语历史,苏格兰盖尔语来源于公元1至5世纪爱尔兰人对不列颠岛的入侵。传统上认为,苏格兰的名称也来自这一历史。不过,随着苏格兰地区的发展,尤其是进入近代之后,联合王国的发展让英语成为苏格兰地区的主流语言,而苏格兰盖尔语人口则在不断下降。在分析麦克尼凯尔作品书写的自然意象时,怀特认为,使用自然意象可以回避盖尔语缺乏当代词汇这一问题,但同时也强化了盖尔语诗歌的“生态性”,拉大了盖尔语和当代生活的距离。对于一种要挣扎生存的语言而言,这并不是好事。怀特对盖尔语诗歌中过度运用自然生态意象的批评,让人反思当代苏格兰诗歌的整体发展。从对苏格兰民族性的追求伊始,当代苏格兰诗人就将自然书写作为民族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让当代苏格兰诗歌呈现出与主流英语诗歌的不同风格,有助于突出苏格兰诗歌的独立民族传统。可是,如果对这一传统过于强调,甚至将自然生态书写作为当代苏格兰诗歌未来发展的主要选择,则不仅会让苏格兰诗歌的发展过于单一,也会在强调与自然生态接近的同时,和当下社会的其他重要议题疏离,失去读者的认同。作为当代苏格兰诗歌的研究者和创作者,怀特的批判让我们得以从更加多元的视角来审视当代苏格兰诗歌中的民族性,发掘出当代苏格兰诗歌的丰富蕴涵。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当代苏格兰诗歌中,英语诗歌独占鳌头,苏格兰语诗歌不时出现在几乎所有主流诗人的作品中,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用苏格兰盖尔语创作的诗歌逐渐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索利·麦克林的情诗是当代英语世界对苏格兰盖尔语诗歌最初的认知,而安格斯·麦克尼凯尔的创作则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突出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使得这一古老的语言得以扬长避短,以有限的词汇来书写和思考复杂的当代社会。苏格兰盖尔语诗集在出版时提供英语对照,这种双语发表的策略保证了作为主流的英语读者可以阅读和了解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成为苏格兰盖尔语诗歌在英语主导的文学世界中的生存之道。
从麦克林,到麦克尼凯尔和怀特,当代苏格兰盖尔语的诗歌创作继承和发扬盖尔语诗歌民族传统,关注社会现实议题,与主流文化融合,丰富了当代苏格兰诗歌中的民族性书写,业已成为当代苏格兰英语诗歌之外的重要文学成就,是众彩纷呈的当代苏格兰诗歌蓬勃发展的活力源泉之一。当代苏格兰盖尔语诗歌以独特的语言魅力,对传统的承继、批判和反思,对社会问题和自然生态的书写,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人类所面对的复杂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当代苏格兰诗歌的民族传统,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一部分。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2期,“动态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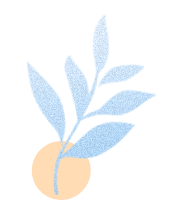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或阅读原文,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