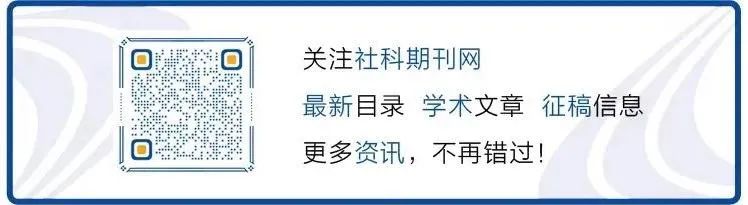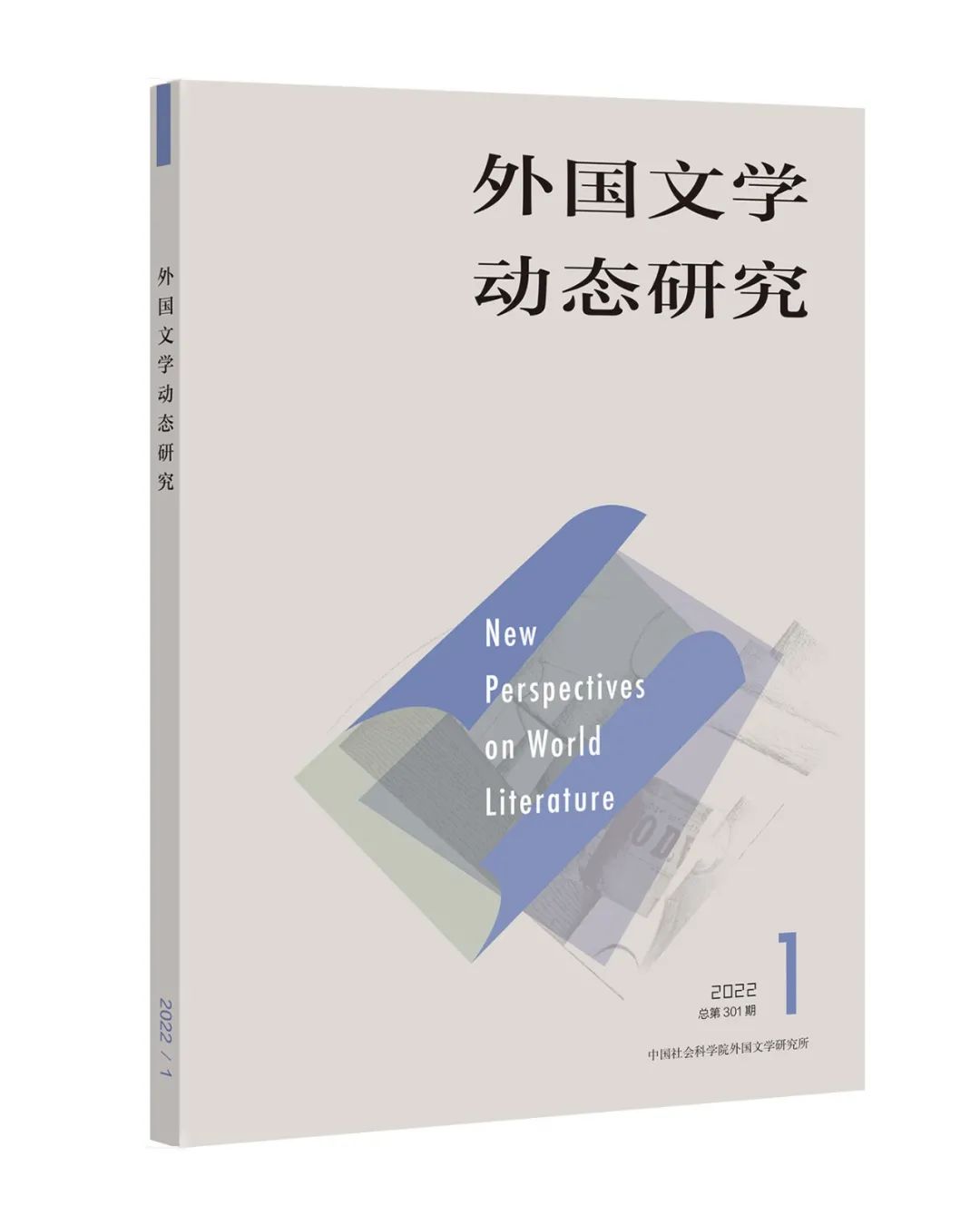新作评论 | 历史是怎么制成的:沃达拉兹金《岛的辩护》中的历史叙事结构

颜 宽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莫斯科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域外文学,出版译著《克莱尔家的夜晚》(四川人民出版社,金色俄罗斯丛书第四辑,2022年)。


内容提要 本文借用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理念剖析《岛的辩护》中的历史观。小说中交替出现的两种体裁,即岛屿的编年史与个人历史解读,形成了公共/私人话语对照的文本结构。它们的矛盾冲突揭露了传统历史观的片面性,其本质是受视角限制、受动机影响的叙事加工。但作者并未因此偏向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相对主义,而是将道德确立为人类共有的历史阐释标准,构建了以道德为发展动力的历史观。本文认为,小说具备新现代主义的创作特征。与此同时,小说也富有深刻的东正教精神内涵。
关键词 沃达拉兹金 《岛的辩护》 元史学 新现代主义 东正教



叶甫盖尼·戈尔曼诺维奇·沃达拉兹金(Водолазкин Е.Г. 1964—)是当代俄罗斯文坛以历史反思见长的作家,他的书写具备从中世纪到现当代的广阔视域。然而,作家的历史探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后见之明,即对“终结某个历史时期”的内在矛盾的挖掘,他更为关注的是“历史反思”这一社会行为本身的涵义。换言之,沃达拉兹金关注的不是“历史中发生了什么或者为什么发生”,而是“历史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产品,其本身是怎么制成的,制作目的是什么”。这无疑赋予了其作品以元历史的特征,代表作《拉夫尔》(Лавр)与《飞行员》(Авиатор)即借助“时空穿越”的艺术手法,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碎片拼贴在同一文本中,主人公由此获得“旁观者清”的外位性视角,并反思历史意识本身的生成与存在意义。本文认为,关于历史本质的思考在沃达拉兹金2020年的新作《岛的辩护》(Оправдание Острова)中进一步展开,并较之以往有了更为鲜明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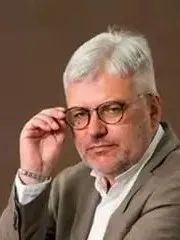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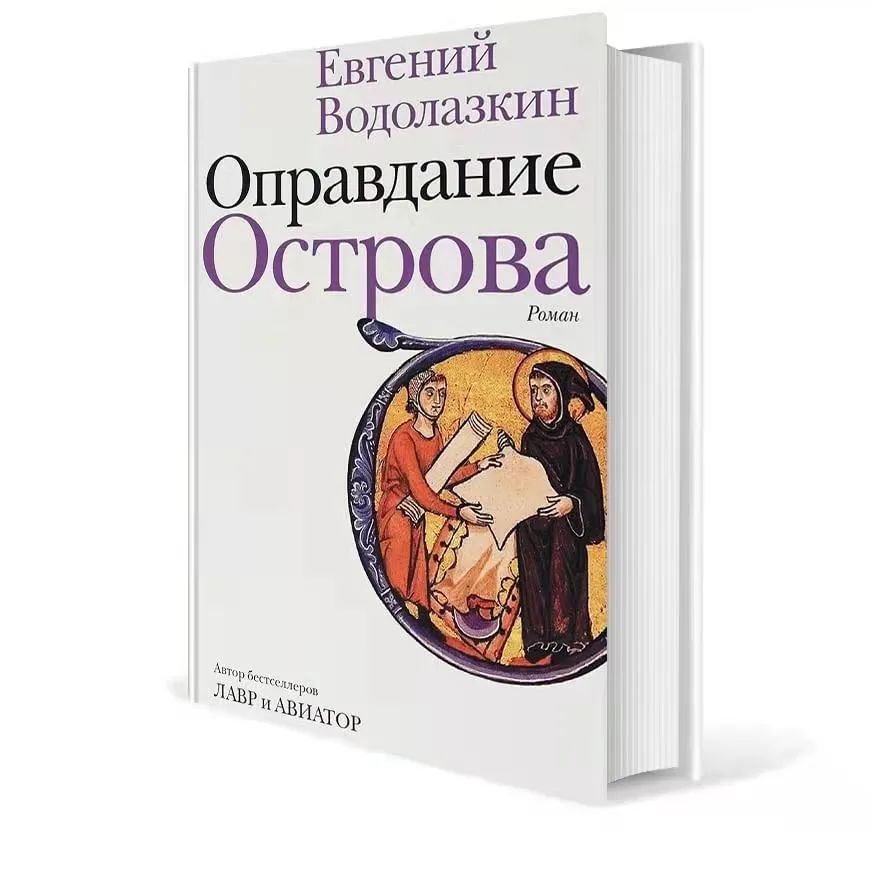
(叶甫盖尼·戈尔曼诺维奇·沃达拉兹金与《岛的辩护》,图片源自Yandex)
这种鲜明性反映在小说的乌托邦性质上。在去除了现实条件的拘束后,沃达拉兹金将“历史”的制作过程完整地暴露在一个由艺术支配的试验场中。该小说以编年史的形式展开,主要内容是某个不知名岛屿从中世纪到现当代的历史记载。编年史的作者是岛屿上的数代东正教僧侣,他们以每个统治者为一节,书写了共二十五个章节,记载了自民族诞生以来的过往。除此,编年史的每个章节后附有个人回忆录性质的评论。评论的作者是岛屿上的一对王室夫妇,也是小说的主人公。在三百四十七年的漫长人生中,他们几乎亲历了岛上所有的历史变迁。与此同时,作者还展开了另一条情节线索: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勒克莱尔以岛屿历史为背景,拍摄了一部关于王室夫妇的人物传记电影。岛屿的编年史由不同时代、不同政治体制的社会历史片段构成,俨然是一段西欧与俄罗斯近千年历史的缩影。
本文旨在分析小说所表现出的三种历史叙事策略:第一种是“据事直书”的传统历史观,它以物质世界的因果关系为历史的发展动力,宣称以中性、客观的角度还原历史真相,并借由公共话语对私人话语的掩盖,来形成表面上统一的历史;第二种是泛文本式的历史观。后现代的语境放大了历史的叙事性与个体的独立性,将“过去”视作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因此并不存在统一的历史,而只存在取决于个人叙事视角的相对性历史;第三种则是形而上的历史观,将道德伦理视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致力于追寻普遍性的原则。在小说中,作者揭露了第一种历史观的片面性和第二种历史观的虚无主义,并将第三种历史观视作历史反思的合适形态,因为道德将作为后现代世界中每个孤立个体的纽带,引导世界进入一个单独的、统一的、真正普遍的“历史”的应许之地。
通常来说,人们对待历史的“常识性”态度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由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还原,正如近代历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那句名言所述,历史不是“判断过去,也不是指导同时代的人着眼于未来,而是说明它本来是什么”。这类“以事实为基础”的纯粹历史考察,似乎有理由宣称自己是一门摈除了主观性的、中性透明的学科。但正是这样的历史观在小说中受到作者的质疑。
小说主体是岛屿的编年史。与此同时,交替出现的非官方话语,如对历史片段的评价、个人回忆录、秘史片段,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另一面,与编年史的历史叙事相互映照。借助这一手段,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历史观不可避免的片面性。这首先归咎于叙事者的视角局限。
比如,主人公帕尔菲尼亚与柯西尼娅(以下简称帕与柯)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向读者转述事件的经过,提供了另一版本的历史。以小说第六章所记载的二人的婚礼为例,在编年史作者笔下,婚礼被描绘为一场盛大的国家庆典。他利用多个细节营造这一历史事件的神圣性,比如奇迹般出现的三只白鸽,柯西尼娅在婚誓前的娇羞与染着处女之血的床单。但紧接其后的评论却立马证实前文所述不过是受视角限制而造成的误解。根据帕与柯的自述,钟楼上的三只白鸽是人为的安排,柯西尼娅异常的脸色也并非是娇羞,而是逃婚前的迟疑,染红的床单则是用山羊血伪造而成。
编年史的作者无法以每个人的内在视角完整地审视事件,这就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记载并非真实的还原,而是个人视角的片面转述。但这样的历史叙事借由公共话语对私人话语的压制,造成了一种统一历史的假象:当公共话语主导的历史版本宣称自己的绝对真实时,其他的私人话语往往淹没在喧嚣中。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的作用不仅仅是记录,更多的时候是覆盖那些不应存在的声音。
传统历史叙事的片面性不仅可以归结于视角限制,还受到历史记述者的动机影响。作家向读者展示叙事者是如何通过拣选与重组材料,将“过去”处理为一段具有开端、高潮与结局的完整情节的。这一结构是为传达事先放置于“历史”中的意义。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在“过往的历史”中发现意义,而是为了符合某个意义而去建构一段“过往的历史”。
比如,在小说第四章“摄政王尤斯京”中,僧侣普罗格比出于恐惧在正史中将尤斯京塑造为一代贤王,但每到夜晚,他又会写下这个暴虐残忍之人的真相。两个历史版本选取了同样的事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叙事的手段。尤斯京通过逼宫大主教获得了权力,但在正史中却被美化为临危受命。为了延长自己的摄政期限,尤斯京修改了王储的年龄,但普罗格比却将此举解释为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教育王储,为他们将来的执政做好充足的准备”。似乎为了说服读者,普罗格比在正史中写道:“众所周知,每当谈论起时间、年龄以及相似的现象时,就会引发何等的混乱。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各不相同,因此人们很难找到共同语言。”最后尤斯京的意外死亡也被披上一层圣人的光芒,“他们就像两把虔诚的火炬,床榻成为他们的陵墓”。但真相却是:这是一场蓄意纵火,人们对尤斯京的愤怒已无法遏制。如此一来,普罗格比在正史中塑造了一个贤王的形象,倘若不是秘史的发现,这一历史叙事将成为“真正”客观的过往。
沃达拉兹金借用此类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的对比,暴露了历史叙事本身(至少在正史中)的不透明性与片面性。它要么来自于视野的限制,要么受叙事者的动机影响。因而,任何历史都不具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真实”的权力,它们仅仅是对整个事件的一种阐释。正如作者本人在关于小说的访谈中所说,历史叙事中的“客观性的确是一个应该追求的目标,但它却像地平线一样遥不可及”。任何宣称唯一真实的历史,在沃达拉兹金看来都是一种话语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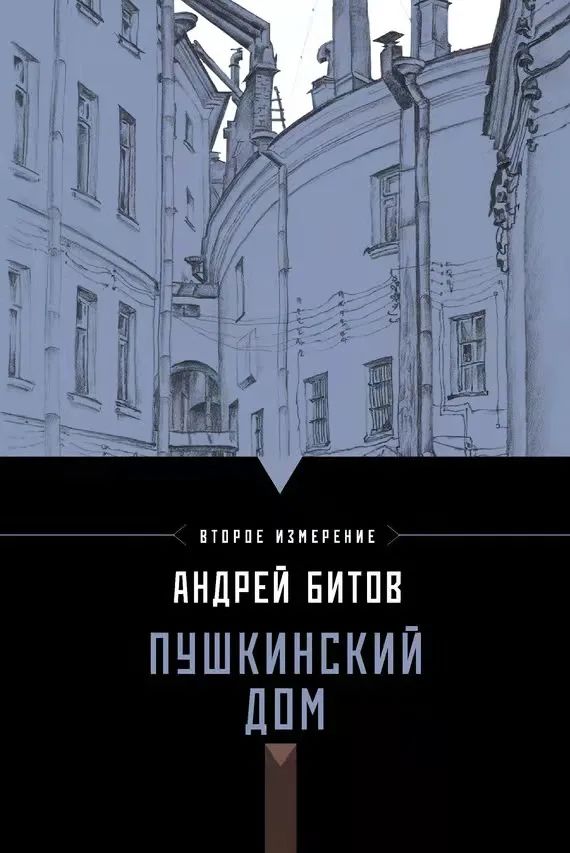
(比托夫与《普希金之家》,图片源自Yandex)
可见,沃达拉兹金之所以提供多个历史版本,其用意是允许读者自行组合与构建一个岛屿历史的“真相”。换言之,在这里没有绝对的真相与谬误,因为任何的历史叙事都是为理解事件而进行的情节化。作家所持有的这种历史态度,令人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末以比托夫、西尼亚夫斯基和叶罗菲耶夫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对俄罗斯历史的解构。以比托夫的小说《普希金之家》(Пушкинский дом)为例,斯大林的葬礼仪式令小说主人公意识到,历史本身也许就是一场伪装的游戏。作者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讽刺了社会的伪装性:“当然,不可能假设大家都未经密谋而能装出同一个样子。那样的话,社会就变成了什么?认为社会就是集体性的不真诚……”而在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Прогулки с Пушкиным)中,作者更是大胆地重构了普希金的形象。他笔下的普希金一反官方的正统版本,被塑造为一个唐璜式的轻浮好色之徒。作为普希金的资深崇拜者,西尼亚夫斯基以这样的方式挑战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物模板,赋予普希金更鲜明的人性特征。在这些后现代作品中,私人话语以戏谑荒诞的口吻推倒了前历史时期建立的公共话语权威,在对历史的个人阐释中获得了自由。

后现代式的历史叙事是私人话语的胜利,它提供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推翻了话语霸权。比如在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的小说《碲钉国》(Теллурия)中,作者将数十种历史政治体制并置在同一个时空内,构成了各自的乌托邦理想。众多的私人话语拒绝意识形态的霸权,但这并不能掩盖过度自由阐释带来的危险。同样是在《碲钉国》中,作者利用五十个历史片段向读者证实,“个体幸福的基础在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从不替他人命运做决定”,但一个完整、统一、真实的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这就是后现代主义长期为人所诟病的相对主义。多个版本的历史叙事并不会令真相越加清晰,反而在各自为战的争论中消磨了人们对真相的探求。海登·怀特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后现代的“泛文本主义”。他如此写道:“对泛文本论而言,任何对历史的表述都被视为一个语言、思想和想象的建构,而不是假定存在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结构的记录。”换言之,历史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不再是关于某个确实发生的事件的记载,而是一个等待被阐释的符号网络,至于事实真相也被认为是一种假定的理想,并非客观的存在。沃达拉兹金在小说中就表现了此类因私人话语膨胀而导致的泛文本式历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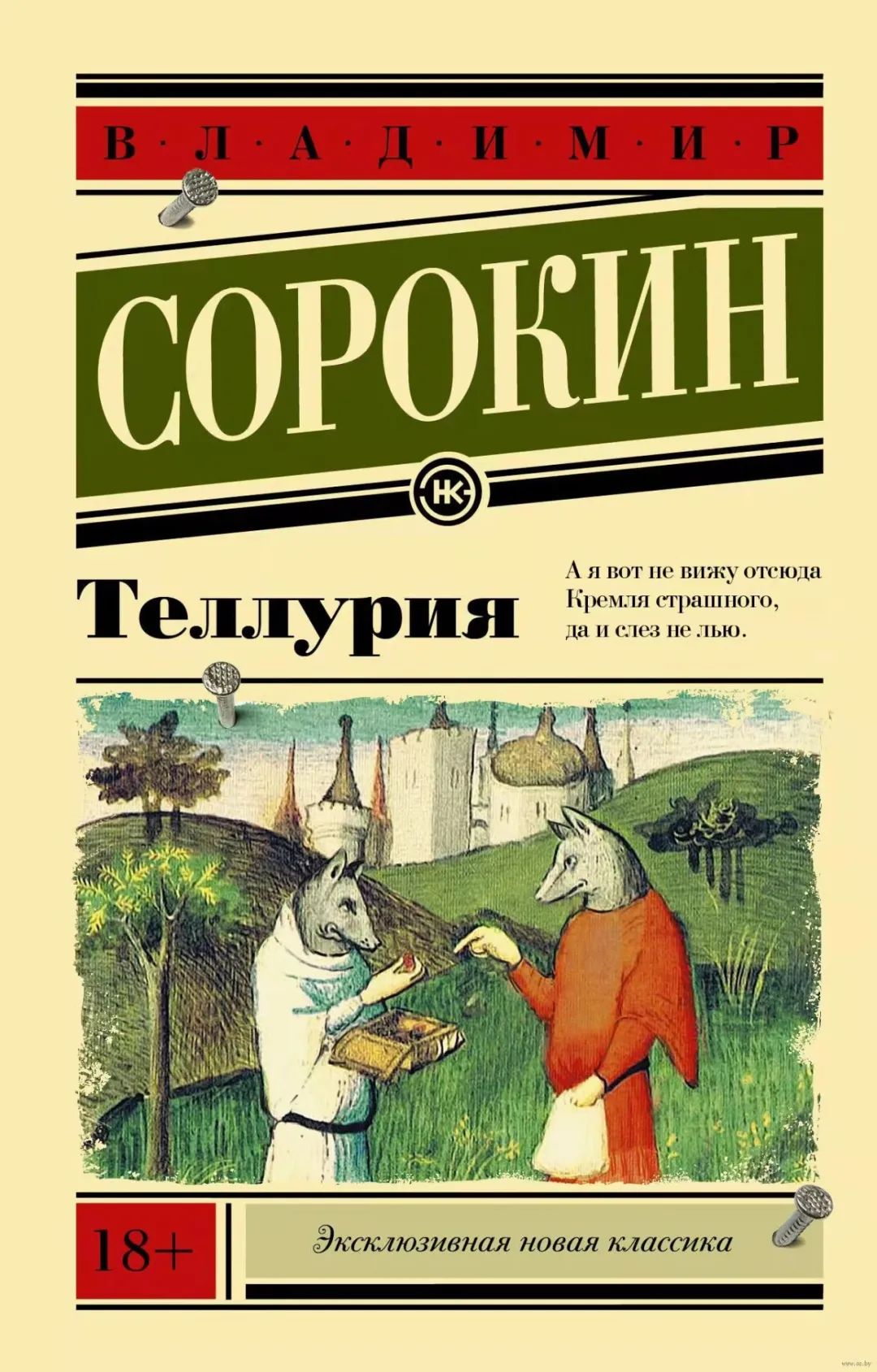
(弗拉基米尔·索罗金与《碲钉国》,图片源自Yandex)
沃达拉兹金有意在主人公的历史评论中穿插了二人受邀作为历史顾问参与电影拍摄的情节。作者借主人公的视角,展示了导演如何利用镜头语言现场制作历史想象物。电影并不符合帕与柯的真实经历,甚至有意歪曲二人的生活。导演的镜头美学都围绕着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原则,但它追求的并非还原事件本貌,而是依据某种标准答案进行事件的再建构。作者借导演之口道出这种现实主义的本质:“现实,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从可能性的角度而言,它有可能是什么。”从最小的衣饰细节到场景布置,主人公的经历与电影阐释的矛盾在拍摄中逐步升级,最后在拍摄爱情戏一刻爆发。导演试图将人物间柏拉图式的爱情处理为“特里斯丹和伊索尔德”的翻版,只因后者是现代观众眼中中世纪爱情的典范。换言之,电影中的历史是一个提前对所有问题都备好标准答案的技术团队所创造的想象物。它关注的不是事件如何表现得真实,而是如何令观众相信事件的真实。如果说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可以宣称“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那么沃达拉兹金借这一情节就是在暗讽,泛文本主义视域下,观众的诞生也应以事实的死亡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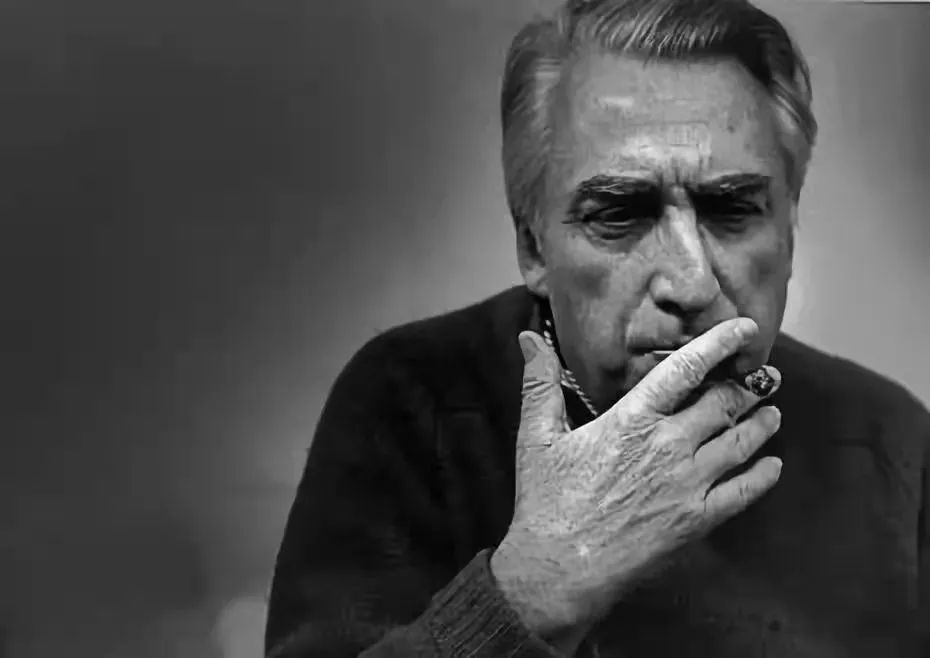
(罗兰·巴特,图片源自Yandex)
私人话语的任意性甚至造成对历史本身的攻击。在小说中,新时代的历史研究者阿塔纳斯执意要销毁岛屿的被殖民史,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历史是不光荣的,那么它就不应被称之为历史”。他命令编年史的作者剪下九十四页文献手稿并付之一炬。沃达拉兹金展示了解构历史的极端性,即将意义的来源从事实转移到阐释。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的人们自由地对待历史:无论何人,无论何处都可以书写历史,这难道不是诸多假象产生的原因吗?”
过度发挥叙事性令历史陷入相对主义的漩涡,想象甚至以此为借口取代真实发生的事件。这造就了一场毫无限制的私人话语狂欢,个体在对历史的肆意裁剪中拼贴出自己想要的答案,个人眼中的历史结果将取决于他看待历史的方式,取决于他希望历史证实什么样的观点。
如此,对历史的理解似乎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公共话语主导的客观历史叙事掩藏了自身的虚构性,往往形成渗透着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私人话语主导的泛文本式叙事却否定了统一历史的可能性,取消了人的历史责任感,历史反思沦为“没有真相,只有观点”的文本阐释游戏。而沃达拉兹金在作品中借用帕与柯的历史评论侧面反映了第三种历史观,平衡了公共与私人话语的历史叙事,提出了一种既具统一性又避免霸权的历史叙事结构——以道德为发展动力的历史观。

上文所述的两种历史叙事都暴露了自己的片面性,“每一个人总会按他自己的倾向与要求建立因果的链条”。沃达拉兹金将这种历史称为“从侧面观察的历史”:“当代的历史思维受到局势影响,并非单纯地描述事件。历史取决于政治目的性,这令历史记述变成了斗争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的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的视角总是侧边的。”为了克服这一点,作家在小说中提出一种俯视的历史观,它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层面,选取了某个涉及全人类本质的永恒角度来考察历史,从而将孤独个体的历史连接成一个统一的人类历史。这个永恒的角度正是道德伦理。
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历史观将社会变迁的真正原因归结于某些非物质的因素,如人群的思想与感受。在小说中,主人公称其为“历史的节奏”:“某些事物的消逝不是因为它们的过错,而是因为它们的时间到头了。另一些事物的出现不是因为它们的正确,而是因为它们的时间到来了。”这种“节奏”构成了岛屿的隐性历史,表面上看似可归结于政治、经济、利益纷争的历史变迁,在深层次上都可归结于道德伦理问题。
比如,小说第十四章中岛屿上爆发了第一次暴动。此时帕尔菲尼亚已为岛屿带来了繁荣,没有了愚昧、饥饿、犯罪与瘟疫,也没有了外来强敌的入侵与殖民,人人理应陶醉于幸福中。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岛民们开始组织游行,呼喊着?“民主”与“自由”,要求揭露政府的恶行。这些人甚至自己也无法解释,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就像刺杀帕尔菲尼亚的列昂纳德所说:“他并没有感到对帕尔菲尼亚的憎恨,只是责任感促使他丢出炸弹。在他眼中,一切权力都是公开的罪恶,它们应当被消除。至于王室夫妇广受爱戴的事实,在他们眼中只会妨碍行动。”这一切似乎违背了常识。但从人群的思想与情绪角度来看,暴动的真正原因是对“平凡”的疲倦和对“改变”的迷信。它像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传播,激发了人内心深处的恶意,一无所知的岛民在这场狂欢中释放压抑良久的激情。他们将暴力与无耻视作历史变革发展的必要手段,以未来之名杀害无辜的神父与卫兵,而杀人犯却被铸成了雕像竖立在广场中央。
不难看出作者在这段描写中映射了人类历史上的数次悲剧,但这一切并不能归结于某个人的邪恶意志,而是一个时代“恶的共鸣”,是集体的道德堕落与以“人”为中心的利己主义的膨胀。它反复出现在人类历史中,是诸多历史灾难的真正缘由。在小说中,它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岛屿的漫长历史中,比如岛屿上数次的南北战争。它们看起来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起因,从王位继承权的争夺、政治理念的分歧到爱情的报复、饥荒等等;但以道德的角度来审视这出历史剧目的反复上演,其原因只在于数百年间岛屿居民们并未学会相亲相爱,而贪婪与唯利是图倒是只增不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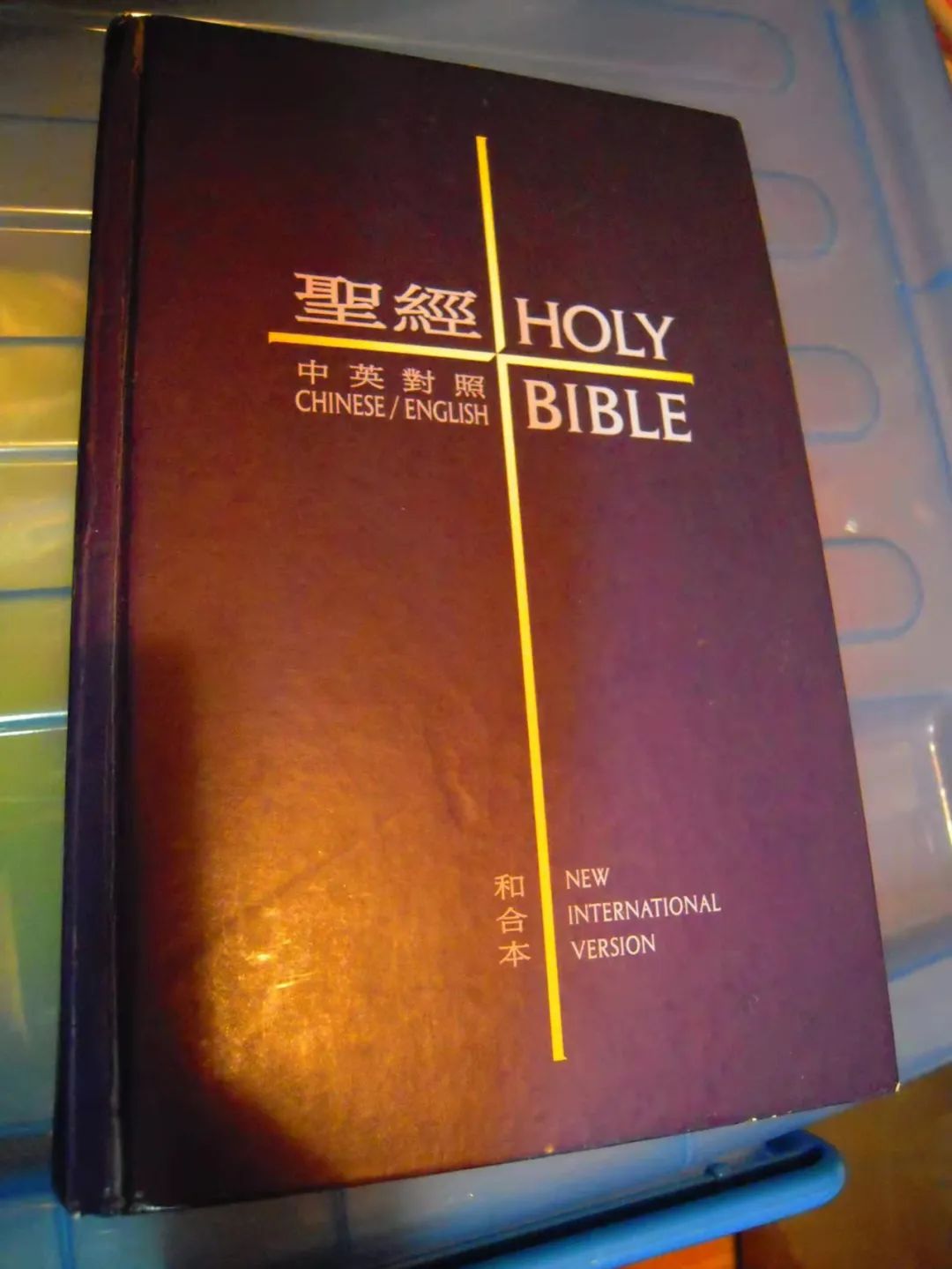
(《圣经》,图片源自Yandex)
这种历史观恰恰解决了后现代历史叙事造成的相对主义。道德理论成为连接个体的纽带,令不同的私人话语朝向共同的叙事模式,塑造出一种无叙事主体的公共历史话语,以类似上帝的旁观视角展开历史叙事。值得一提的是,沃达拉兹金的道德历史观显然以基督教的人道精神为核心,认为俄罗斯与整个西欧文明都应以人道为历史出发点,重新将上帝而不是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小说的名称《岛的辩护》最能体现这一宗教思想内涵。“岛的辩护”是指面对谁的辩护?辩护的原因是什么?读者在小说相呼应的开头与结尾中就能找到答案。小说开头提及了《圣经·创世纪》中索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向神祈求,神答应他只要在城中找到十个义人,就不毁灭城市。但在罪恶的索多玛与蛾摩拉甚至找不到一个义人,于是神降下了天火。而在小说的结尾处,岛屿面临着火山喷发的危险,似乎要重演索多玛的悲剧。根据古老的预言,只有在岛屿上找到三个义人与上天对话,岛屿的危机才会被化解,因此岛的辩护,正是岛民们面对上帝做出的道德辩护:在犯下诸多罪恶后,人类需要向上帝证明自己仍具有存在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正是义人的存在,他们证明了人类尚且具有被拯救的价值。沃达拉兹金在访谈中也证实了作品的这一内涵,他将帕与柯比作历史花坛中的鲜花,“而美艳的花朵是为了其他花坛中的植物而存在的,因为看见义人,就有了想要成为义人的愿望”。这恰好说明沃达拉兹金的元史学性。所谓的“元史学”,按照海登·怀特的定义,乃是“提出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沃达拉兹金关注的不是“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而是“历史如何进行反思,反思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作者面向的不是已经发生的过去,而是尚未显现的“将来”,历史事件的真与假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它的阐释会为人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未来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作者希望以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策略来改变当代人类的实践方式。于是作者提出,道德将为所有的历史阐释提供一个永恒不变的锚点。无论个体采取什么样的叙事角度,它的历史话语必须以道德为出发点,这是因为道德本身就是历史的目的。因此在《岛的辩护》中,一个好的历史叙事并非客观的叙事,而是可以引导人们走向道德完善的叙事。

《岛的辩护》反映了俄罗斯文坛近年来兴起的新现代主义意识。“新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在俄罗斯最早见于1999年柳·维亚兹米基诺娃(Вязмитинова Л.)评论德米特里·沃杰尼科夫诗集《假日》(Holiday)的论述。作者十分恰当地指出,沃杰尼科夫的创作反映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向一种崭新的现代主义范式的过渡。一批年轻作家力图在破碎的后现代世界图景中重新建立一种永恒的、普遍的价值体系。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岛的辩护》中。作家以后现代的方式解构了客观的历史叙事策略。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后现代叙事造成的泛文本化。因此,作家确立了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视历史为道德完善的过程。这无疑符合新现代主义所追求的普遍性价值,即“不仅仅局限于对遥远时代与岁月的具体历史问题挖掘,而是更应该发现它那些超越时间的、本体论性质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沃达拉兹金笔下的道德也并非绝对中性客观,它本质上是基督教思想的艺术化体现。东正教思想中的“同心同德”(соборность)贯穿小说始末,成为作者提出的道德历史观的基础。我国学者刘文飞认为,现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已自觉地转向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一新意识形态便是东正教信仰。一个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真空迟早是需要填充的,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信仰作为一种新的民族思想体系似乎已成为俄罗斯人的集体无意识。”沃达拉兹金的这部作品正是这一趋势的极好例证。
综上所述,小说《岛的辩护》以历史为考察对象,深刻分析了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主导的两种历史叙事结构,探讨了历史反思的本质,提出一种以道德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元史观。小说既体现了俄罗斯文坛近年来兴起的新现代主义思潮,也反映了东正教意识形态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渗透。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2期,“新作评论”栏目,责任编辑苏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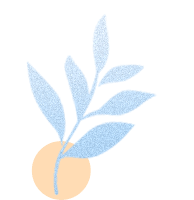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或阅读原文,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