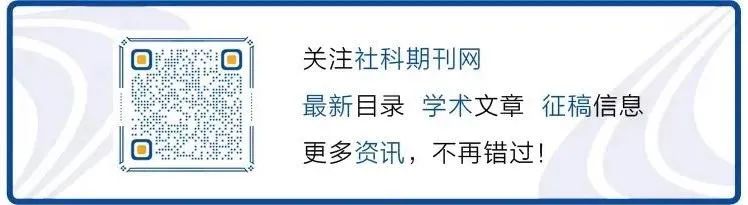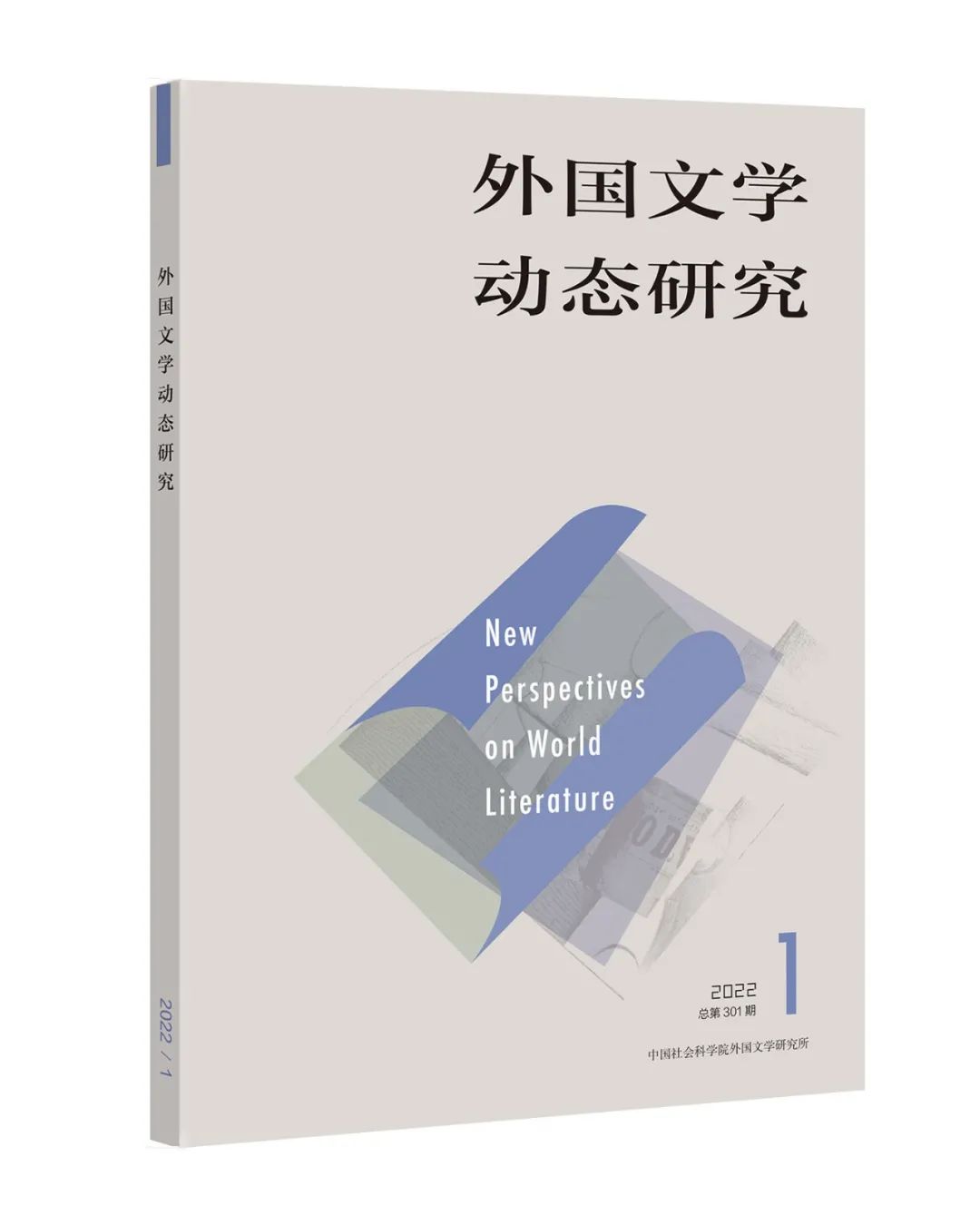戴夫·艾格斯小说《国王的全息图》中的当代旅行叙事

聂祝琳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文学。
内容提要 戴夫·艾格斯的《国王的全息图》以美国主人公在沙特阿拉伯的后“9·11”跨国商务旅行为主要情节,对全球化时代美国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展开思考。主人公的沙特阿拉伯旅行既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衰落的美国中产阶级追逐美国梦的幻灭之旅,也是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参照下美国例外论的消解之旅。同时,主人公作为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受害者身份及其对传统制造业的怀旧情结亦保障了小说中“帝国之眼”的隐蔽运作。
关键词 戴夫·艾格斯 《国王的全息图》 美国梦 美国例外论 “帝国之眼”

(戴夫·艾格斯,图片源自Yandex)
在《剑桥旅行写作指南》(2002)的导论部分,英国学者彼得·休姆和蒂姆·扬斯曾溯源欧洲文学史,论证了写作和旅行之间源远流长的联结关系。对于由漂洋过海的欧洲移民建立,并在西进运动和交通革命中不断繁荣壮大的美国而言,旅行、迁徙、运动不但早已镌刻于美国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更是作为一大母题贯穿于美国文学史。尽管学界已从旅行叙事的模式、主人公旅行的空间分布、旅行交通方式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归纳了美国文学的旅行叙事特征,但由于相关研究对象主要为美国经典文学作品,旅行叙事在全球化时代的最新发展尚未受到应有的注目。事实上,旅行叙事正是致力于“参与由消费和全球化生成的语境和概念辩论”的“全球化小说”(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的一大惯用叙事策略。面对全球化时代新状况,当代旅行叙事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其一,旅行叙事的人物主体范围不断扩大,既包括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者,也包括身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边缘的弱势群体;其二,旅行叙事不再执着于本地与外地、旅行者与土著民等二元对立的身份划分模式,而是更加强调文化身份的流动与杂糅。与此同时,当代旅行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和传统旅行叙事一样,难以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幽灵对旅行写作的困扰,经常或明或暗地加入与资本的合谋。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1970—)是当代美国全球化小说领域的代表人物,早在《你会知道我们的速度!》(You Shall Know Our Velocity!,2002)中,艾格斯便通过天真的美国主人公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行探讨了“旅行、消费和西方人充满罪恶的富足”之间的关系。在《国王的全息图》(A Hologram for the King,2012)中,艾格斯借美国主人公的跨国商务旅行继续追踪美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最新进展。小说将故事背景设定于2010年的沙特阿拉伯,讲述了生活困窘、婚姻失意的美国推销员艾伦·克莱(Alan Clay)为赢得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以下简称KAEC)的全息图竞标在沙特阿拉伯的一系列际遇。该书出版后收获好评如潮。评论界称赞小说是对全球经济展开的“美丽而残酷的探索”。鉴于《国王的全息图》鲜明的旅行叙事特色,本文将从小说的旅行元素出发,考察其旅行叙事特征及深意。旅行不但为《国王的全息图》提供了广阔的地域空间,亦为小说的情节搭建了天然的框架。传统的美国旅行叙事常常将旅行与美国梦、身份认同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本小说基于新世纪的具体时代背景进一步探讨了相关问题。艾伦的跨国之旅既是当代经济结构转型中衰落的中产阶级追寻美国梦的幻灭之旅,也是后“9·11”时代美国例外论的消解之旅。同时,主人公的受害者身份及其对传统制造业的怀旧情结也保障着小说中“帝国之眼”的隐蔽运作,体现了艾格斯难以彻底摆脱的意识形态局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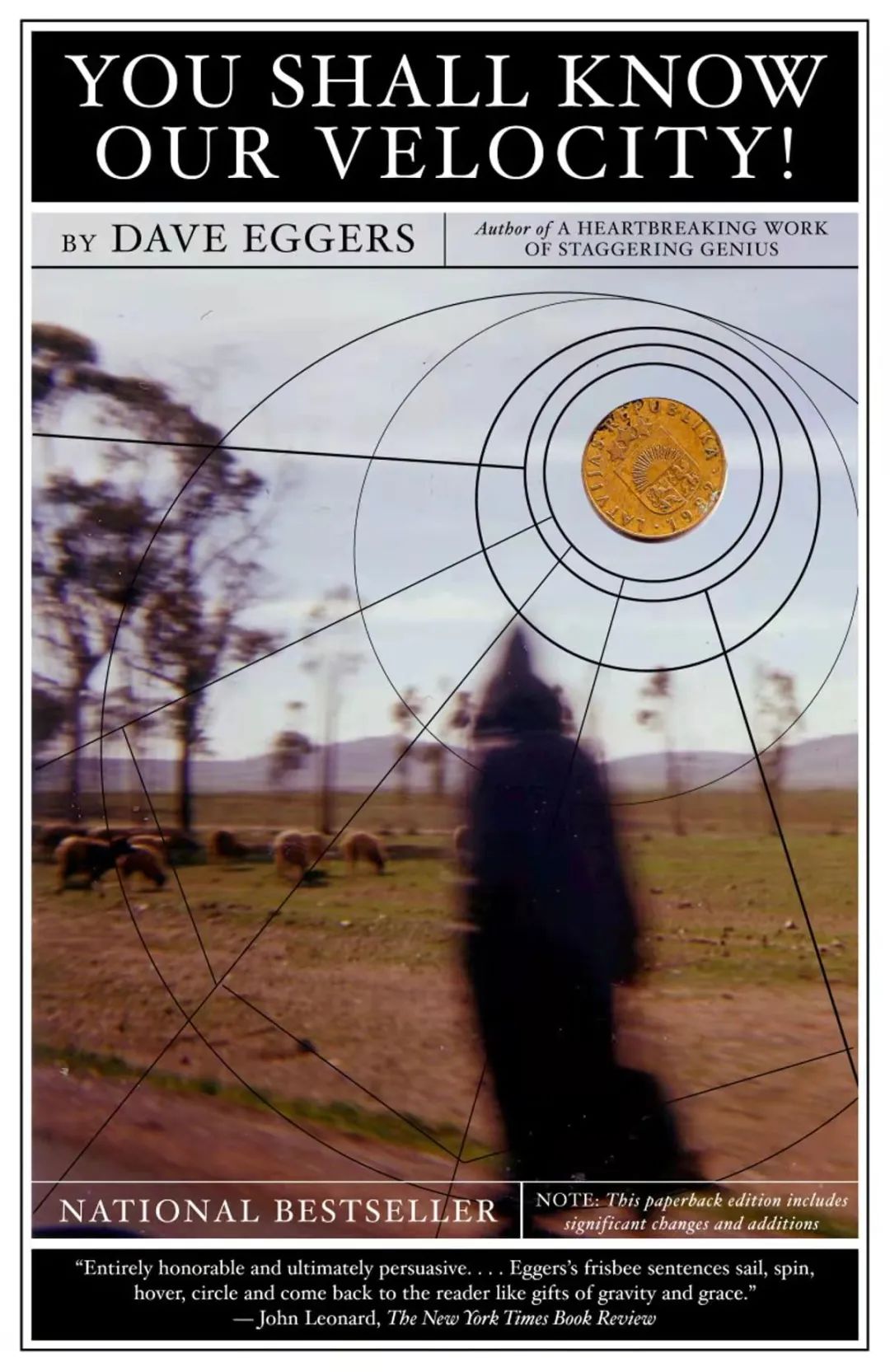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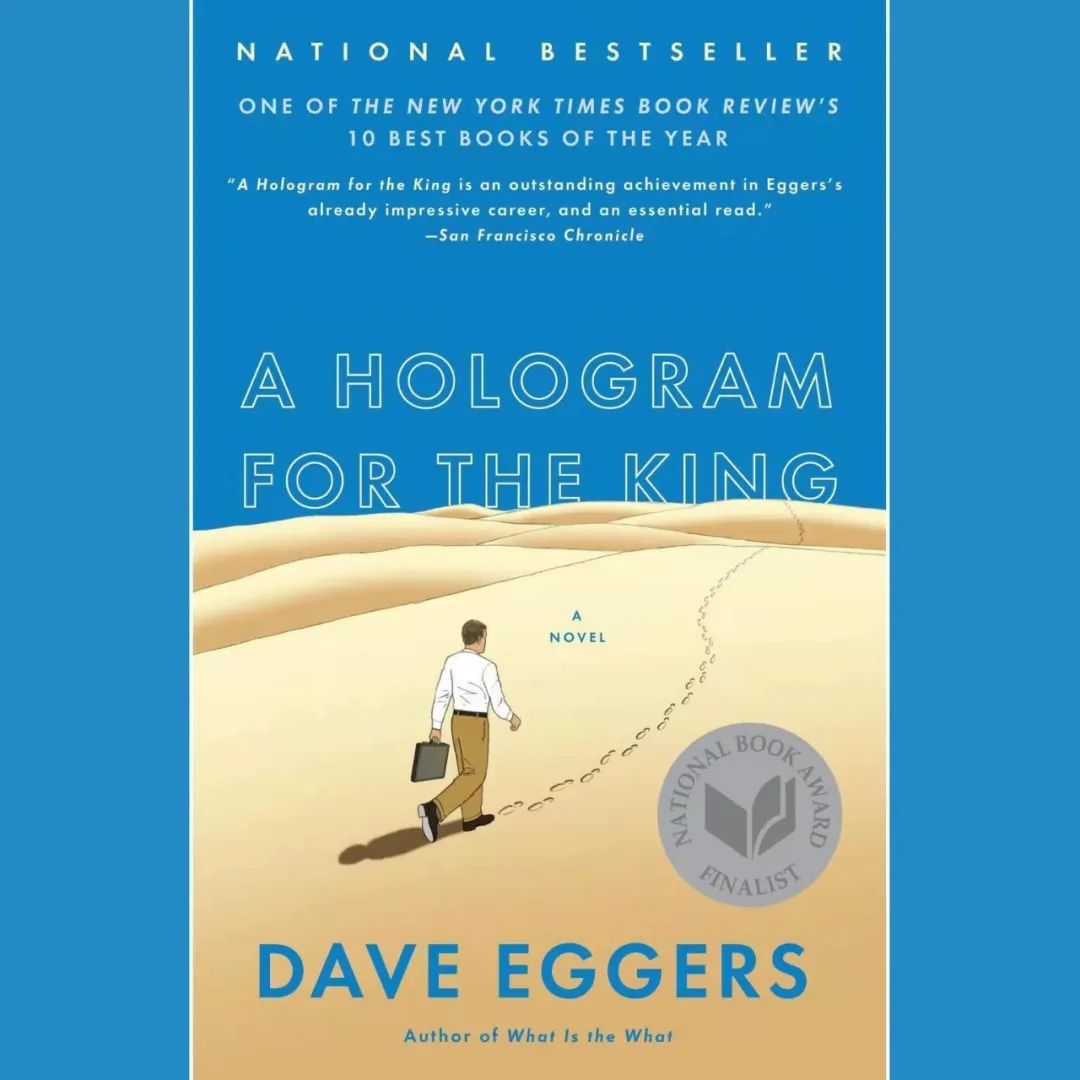
(《你会知道我们的速度!》和《国王的全息图》,图片源自Yandex)
一、美国梦的幻灭之旅
美国梦脱胎于早期清教思想中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的蓬勃发展,美国梦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所有关于美国梦的描述中,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大萧条时期发表的美国梦定义流传最广。在他看来,美国梦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依据自身能力或成就过上更好、更富足、更充实的生活”的国家梦想,“任何人,无论男女,无论其身世背景与社会地位,都能充分发挥其禀赋与才能,并因此得到他人的承认”。换言之,个体凭借后天努力力争上游的社会流动性正是美国梦的核心。作为“实现美国梦的象征性的、也是最简单的途径”,旅行因此成为美国文学中主人公追寻美国梦的一大重要意象。
《国王的全息图》中,艾伦在一次次的上路旅行中向梦想出发。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笔下的威利·洛曼一样,青年时期的艾伦一度是命运垂青的对象。艾伦从大学辍学,凭借前辈乔·特里沃尔传授的四大推销秘诀,即金钱、浪漫、自保、认同,他在一系列美国大型制造业公司摸爬滚打,轻而易举地过上了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此期间,“在路上”是艾伦的生活缩影:“清晨,他会在西区的工厂,看着数以百计闪闪发光的乳白色自行车在晨光中装车。接着,他会驱车一路向南,在下午抵达马顿、兰图尔或者奥尔顿考察经销商销售情况。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艾伦以传统制造业为支柱的美国梦逐渐溃散,他甚至沦落到不得不抛售房产支付女儿学费的境地。也就是说,不同于米勒将威利美国梦的幻灭归结为该人物对美国梦的扭曲理解,艾格斯更加强调导致艾伦美国梦幻灭的外部因素,即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对传统制造业从业者的打击。中产阶级崩解的现状意味着艾伦的美国梦在美国已然失去立足之地,异域商务旅行也就成为他展开的最后一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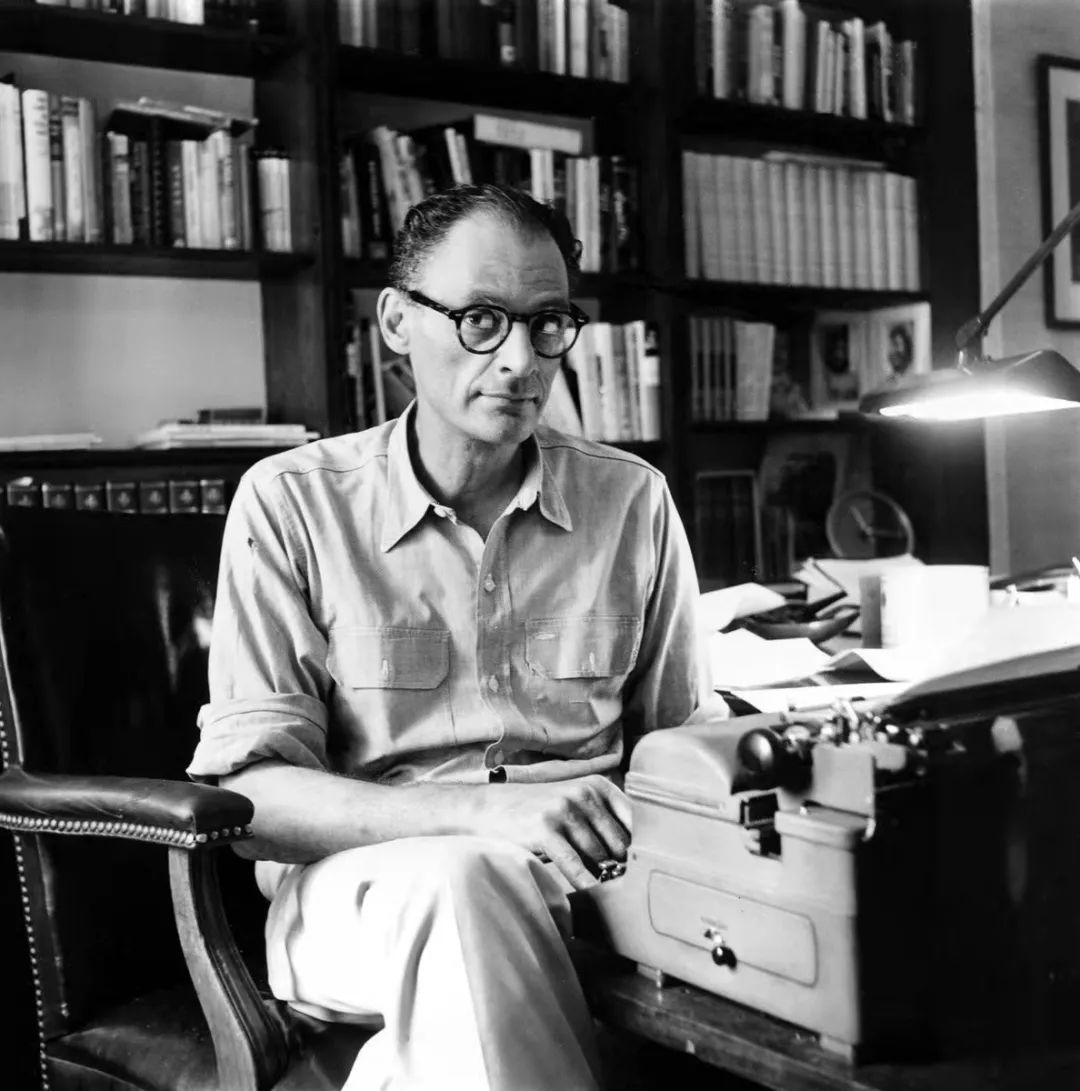
(阿瑟·米勒,图片源自Yandex)
艾伦曾说自己“不知身在何处”。事实上,这恰好反映出他在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中的边缘化境地。如果说熟练掌握推销诀窍的艾伦曾是同行尊敬与学习的榜样,在KAEC的美国团队中,他却是唯一不懂全息图技术的人,“少了他,团队照样能运作”。正因如此,艾伦频繁沉迷于对往昔时光的追忆。当他驾驶游艇行驶在KAEC的人工运河时,浮现在他脑海的是自己担任施文自行车行政主管时和同事们的假期垂钓。“在密歇根湖等地,施文人发展出一套专属于施文的垂钓文化。他们会在日内瓦湖与副总裁和几位经过遴选的顶级零售商共度周末。艾伦想念这一切的一切。”施文甚至使艾伦邂逅爱情:他与前妻露比相识于施文自行车商业版图扩张时期在巴西的商务旅行。尽管二人多年的婚姻生活并不融洽,甚至最终决定以电子邮件代替电话交流,但初遇露比时的艾伦却被前者执着于零和博弈的旺盛精力深深吸引。从某种程度上说,视野开阔、天马行空,沉迷于拯救世界的凌云壮志的露比正是美国梦的象征。而如果说艾伦与露比的相爱表明传统制造业一度是美国梦的宠儿,那么随着婚后的艾伦越来越使露比感到“难堪”,制造业沦为美国国家梦想的弃子的事实也就无可改变了。
在从波士顿到伦敦的航班上,借酒消愁的邻座男子一度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归咎于新兴制造业大国的竞争,认为相较于后者的强劲势头,美国变成了“家猫”。艾伦同样难逃懊丧情绪的侵扰,将中、韩、越等亚洲国家视作美国传统制造业衰落的罪魁祸首:“你想降低单位成本,所以选择在亚洲生产,但很快供应商就不需要你了,不是吗?老话说,授人以渔。中国人学会了‘捕鱼’,于是世界上99%的自行车都成了中国制造,甚至是中国某省制造。”然而怨言背后的事实却更加复杂。正如艾伦的父亲罗恩所说,艾伦对促成施文的破产有着“并非无关紧要”的作用。无论是开拓国际市场还是解散美国本土工会,艾伦在施文参与的种种商业计划均为美国经济顺应资本逐利本性主动调整的一部分,因为“制造业会永远乘着驳船周游世界,寻觅最廉价的生产条件”,而个体除了在过去与当下的罅隙中适应变化的时代以外别无他法。从这个角度看,代表全美最大的IT供应商热莱恩特(Reliant)参与KAEC的全息图竞标无异于艾伦为延续美国梦与传统制造业的“联姻”实施的权宜之计,因为作为美国经济“新宠”的数字产业正是帮助他回归人生巅峰时刻的救命稻草:“任务结束后,艾伦会用薪酬还清波士顿的债务,整装再出发。他会开一家小小的自行车工厂,从年产一千辆起步,逐年壮大规模。他会用零钱支付凯特的学费。他会赶走房产经纪人,结清尾款。他会像巨人一样昂首阔步……”
而艾伦在KAEC的见闻却不断暗示,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寻梦或许只是另一场梦魇。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小说的中心意象——全息图。除了作为《国王的全息图》中美国数字产业的缩影外,全息图缺席在场的幻象特质正是对名实分离的KAEC的隐喻。在其对外宣传中,号称“伟人的远见,民族的希望”的KAEC竭力为参观者勾勒美好的蓝图。在首次前往KAEC的途中,无论是悬挂在高速公路边的巨型广告牌中其乐融融的沙特阿拉伯家庭还是海报横幅上干练的商业精英都给艾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欢迎中心的实体微缩模型和电脑合成的城市宣传片更使艾伦欢呼雀跃,“它看起来会是继巴黎之后最伟大的城市”。然而,现实中的KAEC却一派荒凉。除了屈指可数的三幢建筑物和在风沙中不断将沙子扫回沙漠的菲律宾民工之外,“整个地方就像月球上一处刚刚被中途弃置的开发项目”。用出租车司机优素福的话说:“KAEC已经完蛋了。”如果说引入科技感十足的全息图是沙特阿拉伯国王以超现实拟像引领KAEC乃至沙特阿拉伯加入全球数字经济的应时之举,那么现实中KAEC了无生气的沙漠景观则不由使人联想到艾伦六年前为成立自行车公司向银行贷款,却发现自己因未及时注销在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购物时办理的信用卡导致永久失去商业贷款办理资格时对美国银行业的控诉,“香蕉共和国扼杀了像他这样的创业者推动国家前进的能力。它毁了他的信用,也毁了美国”。
在评价美国经典文学中欧洲旅行的文化内涵时,田俊武指出:“美国人的欧洲行旅既是一种文化朝圣,又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更是在异国环境中对美国民族身份的重新建构。”尽管在相关访谈中,艾格斯称《国王的全息图》“并非一本关于沙特阿拉伯的小说”,但如若考虑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在后“9·11”美国经济、政治战略中的敏感位置,我们便会发现,《国王的全息图》中主人公旅行的时空背景正蕴含着小说对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反思。
如前所述,全息图般的KAEC和数字产业主导下的美国经济呈现较为显著的映射关系,而初来乍到的艾伦却无法辨别KAEC的“真面目”。事实上,这是因为艾伦本人就是一个全息图式的人物——受强烈自尊心的驱使,潦倒的艾伦不但习惯于在人际交往中佩戴成功人士的假面,更不时落入盲目乐观和家长制作风的陷阱。如果说艾伦的姓氏(Clay,即上帝造人时所用的原材料)使其成为全球化时代普通美国人的缩影,那么小说对艾伦的去英雄化则进一步将其与例外论神话主导下的新世纪美国相联。
美国例外论,即“坚信美国实现了其他所有国家所渴望的国家理想”的假定向来在美国文化中占据核心位置。“9·11”后,这一不断强化的“国家幻象”(state fantasy)却遮蔽着美国每况愈下的经济地位与国际关系。艾伦在KAEC的种种尴尬经历便是新世纪美国美好的自我认知(名)和残酷的现实处境(实)之间巨大落差的具象表征。尽管美国人的身份一度赋予艾伦强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事实却是“美国商人”的头衔并不能成为他的沙特阿拉伯通行证。
在KAEC,美国团队无法进驻凉爽且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黑匣子”,只能蜗居于简陋的临时帐篷搜寻时隐时现的网络信号,甚至连寻找对接人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一波三折。当艾伦在海边的粉色别墅中试图以裁决者的身份介入民工纠纷时,他险些摔倒的滑稽姿态和调解失败后反被民工追赶的狼狈遭遇更是对自以为是的美国经济现状的反讽。超级大国成为乙方,中东小国成为甲方,二者逆转的追逐关系表明,美国至高无上的例外地位不再理所当然。相比之下,前来竞标的中国公司不但了解国王来访的详情,更是拥有在“黑匣子”内完成全息图展示的权利。如果说曾经的亚洲国家只能凭借较低的生产力成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美国一较高下,那么中国公司在KAEC的出现则意味着即使是美国拥有显著优势的数字经济领域如今也难逃发展中国家的强势竞争。
孤立无援的帐篷同样讽喻了自诩为自由与正义灯塔的美国与其后“9·11”时代堪忧的国际关系之间的名不符实。通过将“忧郁”(melancholia)概念引入社会政治领域,巴特勒(Judith Butler)抨击了后“9·11”美国以绝对受害者自居,对内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强化审查制度,对外诉诸报复性军事打击的举国忧郁症(national melancholia)。艾伦脖子上的脂肪瘤便是该忧郁症的生理表征:“长在他脊椎上的肿块一定具备致命的侵略性。最近他一直思路不清、行动笨拙,这使他感觉非常糟糕。他感到体内有东西在生长,侵蚀他、破坏他的元气,榨干他所有的敏锐与意志。”虽然该肿块最终被证明对他的身体健康毫无影响,但艾伦的疑虑却与“9·11”后的美国将中东伊斯兰世界视为其政治假想敌的偏执如出一辙。艾伦的山间旅行更是对美国政治忧郁症及其恶果的隐喻:拒绝与艾伦握手的优素福父亲、冷淡的管家,以及将艾伦误认为CIA特工的村民无不影射着沙特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戒备;而夜间猎狼行动中沉迷于救世主幻想的艾伦误伤羊倌的举动,则与美国号称“无限正义”的反恐战争不无相似之处。当子弹与羊倌擦肩而过时,艾伦不再是羊群的守护者,而成为狼群的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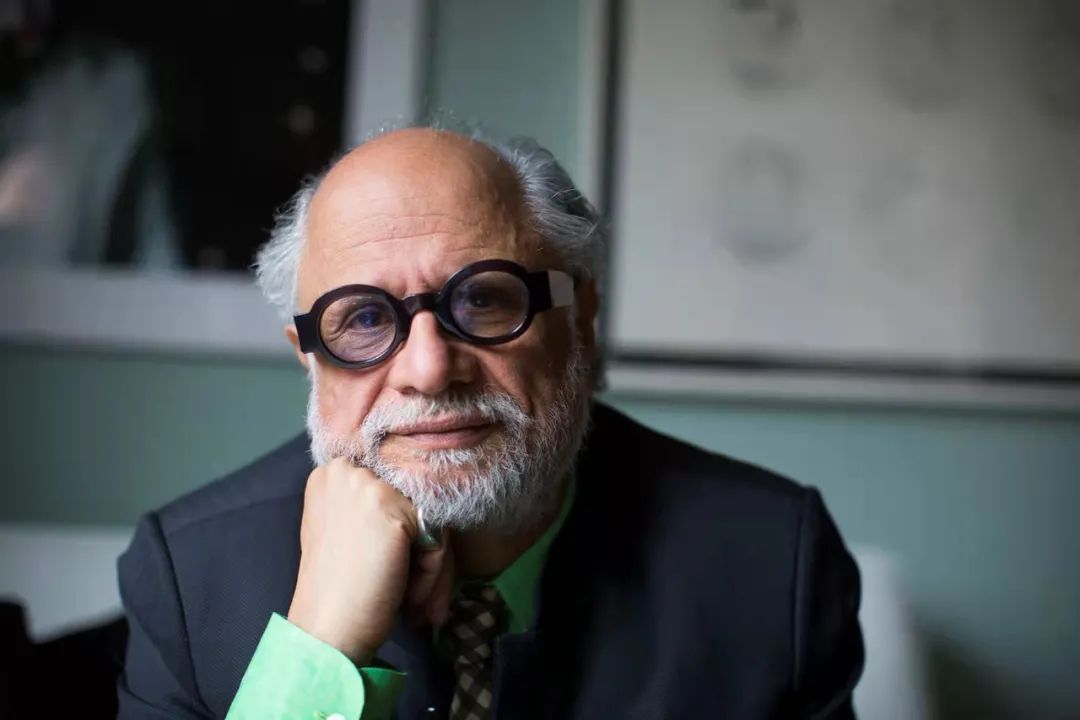
(霍米·巴巴,图片源自Yandex)
随着艾伦对沙特阿拉伯的了解不断加深,他对该国的刻板印象亦不断消退。尽管初到沙特阿拉伯的艾伦一度将这个国度与恐怖主义和爆炸袭击挂钩,甚至在目睹身着黑色布卡陪伴孩子玩耍的女人时“打了个寒战”,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事实上“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换言之,沙特阿拉伯同样具备名(国际刻板形象)实(真实国情)分离的特征。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将介于两种文化之间、兼具包容性与超越性的居间状态称作第三空间(third space),认为其以异质性与混杂性挑战了强调同质性与统一性的文化本质主义观。书中的沙特阿拉伯正是这样一个涌动着混杂与开放潜质的地方,既有希尔顿酒店、KAEC等极具后现代气息的场所,亦有忙碌而热闹的“老城区”;既有对平板电脑、全息图、流行音乐等世俗产品的热情,亦有对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虔信。优素福是艾伦了解沙特阿拉伯的最佳向导:是他带艾伦走进当地餐馆,品尝沙特阿拉伯美食,也是他将艾伦带至父亲的山中城堡,使其得以领略与海景全然不同的沙特阿拉伯山间风光。在艾伦和村民的对话中,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和英语的优素福亦肩负起文化翻译的桥梁作用,使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与优素福的交往甚至治愈了艾伦在沙特阿拉伯持续多日的失眠。当他在车上伴着优素福和另一位沙特阿拉伯青年热烈的阿拉伯语对话进入梦乡时,沙特阿拉伯于艾伦而言已从亟需提防的恐怖分子蜕变为淳朴善良的异国老友。同样对艾伦认识他者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他的爱恋对象——拥有多国血统的沙特阿拉伯女医生扎赫拉。通过将美沙文化差异化简为“细丝”(filament),扎赫拉戏谑了文明冲突论的危言耸听。由扎赫拉领衔的国际医疗团队为艾伦切除肿块的手术因此无异于一台治疗政治忧郁症的手术。当手术台的灯光开启,美国病人与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的医生超越了文化隔阂,在双向信任中齐心协力,将刚愎自用的美式忧郁连根拔除。
在《东方学》(Orientalism,1978)中,萨义德从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出发,开启了当代旅行文学的后殖民研究范式。在他看来,“事实性陈述和虚构性描写的结合意味着殖民主义旅行写作最适合‘充实’东/西方二元划分的基本骨架”。西方旅行文学描绘的东方风景绝非单纯的怡情悦性之作,往往蕴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正是藉由旅行者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野蛮、愚昧的东方不断强化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吸引西方读者加入对遥远国度的探索与入侵。随着去殖民化运动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将帝国构建意义的权利置于监视之下”的努力,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家对旅行文学中的东方主义思维传统予以关注和反思。艾格斯即为一例。如前所述,《国王的全息图》通过主人公艾伦在沙特阿拉伯结下的友情和爱情表达了对东西二元对立向对话转变的美好愿景。艾格斯甚至邀请沙特阿拉伯友人审阅小说初稿,确保小说没有文化和语言表达错误。但许是由于旅行文学本身就“极易产生自我—他者的身份意识和历史的比照玄想”的缘故,美国白人作家的身份注定了艾格斯无法彻底超越“帝国之眼”的魔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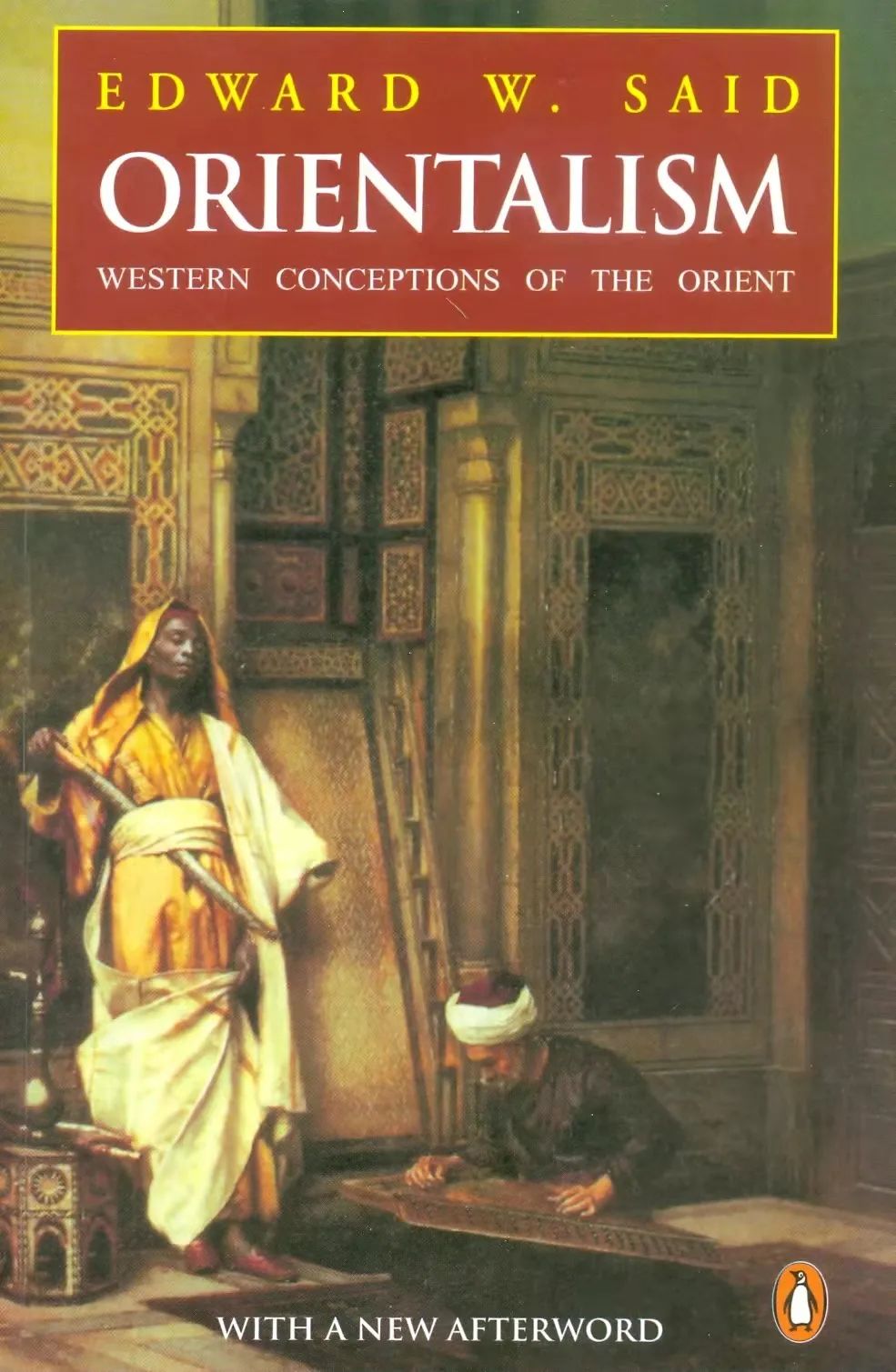
(《东方学》,图片源自Yandex)
在粉色别墅中,尽管艾伦险些摔倒的小插曲可以看作是对宗主国和殖民地关系的戏仿,但与散发着汗酸味和烟味、呆若木鸡的第三世界民工相比,西装革履、自带英国腔的艾伦一出场就掌握着话语权和裁决权。民工纠纷的源头——艾伦的美国同事随手扔掉的旧手机则使人联想到传统旅行叙事中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海岸游荡者(beach combers)。虽然在《国王的全息图》中,美国人并未因为这部手机成为民工的座上宾,但手机被奉若神明的地位却无疑呼应了传统海岸游荡者写作中东西方之间前现代与现代的二元区分。愤怒的民工更是落入了东方刻板印象的陷阱。“房间里的气氛很快阴沉下来。其余的工人将艾伦团团包围,朝他大喊大叫。有人拉他的袖子,有人从背后推他……他后退几步,连声道歉,不知是否应该转头就跑。”在群情激愤的民工和满心愧疚的艾伦的对比中,古老的东方学话语借助类似于普拉特笔下“反征服”(anti-conquest)的旅行书写策略重获生机:通过赋予艾伦“天真无辜”的特质,《国王的全息图》以非暴力的形式取代了帝国主义的征服修辞。艾伦作为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受害者的人物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高人一等的帝国殖民者身份更加隐蔽的运作。
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1972)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作为资本主义运转机制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疆域化概念做出阐释,认为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的诱惑下“既对欲望之流与社会生产之流进行最大限度的去疆域化,又对去疆域化了的各种‘流’进行再疆域化”,个体则在资本主义机器对欲望无限循环的释放与禁锢中沦为金钱的奴隶,而冲破该困境的唯一出路便在于使去疆域化的离心力超越再疆域化的向心力。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中,他们进一步将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与大地(terre)、平滑空间(smooth space)、纹理化空间(striated space)等地理概念相关联。由此,去疆域化成为对边界的超越和融贯大地上各种地层(statum)的动态过程,再疆域化则意味着全新疆域的生成,是“从可以任意驰骋的疆野进入界限分明的院墙之内,以静止、久坐、定居为目的”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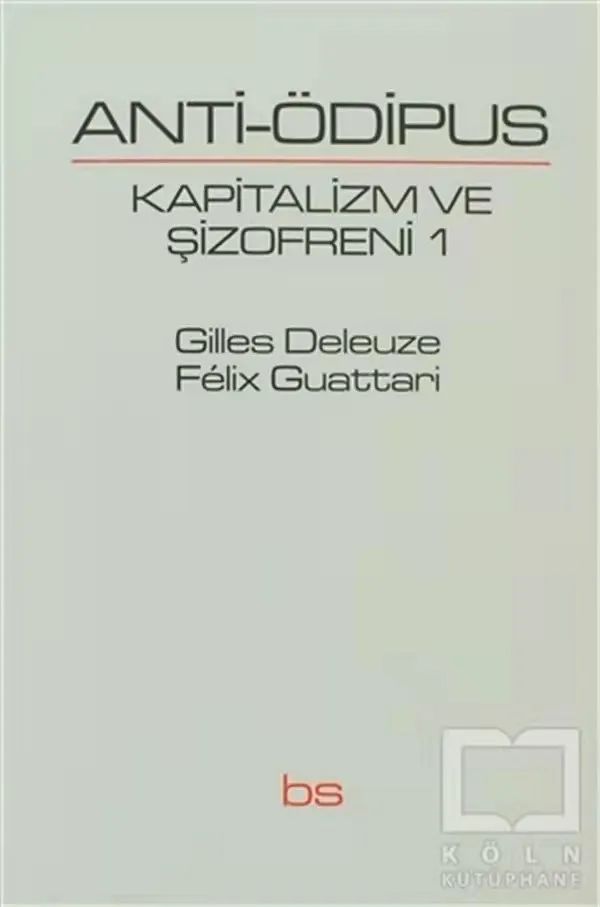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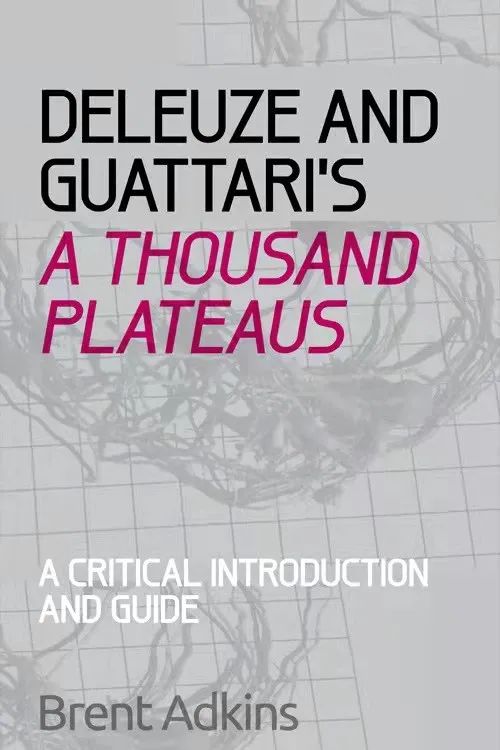
(《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图片源自Yandex)
《国王的全息图》中,曾效力于一家名牌童鞋公司,在新罕布什尔安享晚年的罗恩便是这一对矛盾运动的生动解说。回归乡野的罗恩不但在农场饲养各种动物,更是常年在自己开掘的湖中游泳,被艾伦戏称为“泥人”。从表面看,罗恩似乎实现了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解辖域化逃逸。但事实上,他从未停止对全球经济的关注。在电话中,他向艾伦抱怨道:“每天……亚洲各地都有成百上千艘集装箱货船满载各种各样的商品驶离港口……而我们的同胞却成天坐在中国制造的椅子上,用中国制造的电脑,驶过中国制造的大桥制作网站和全息图。”罗恩向自然的回归因此无异于对已逝的传统制造业时代的守护。尽管艾伦和父亲龃龉不断,但两人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沙特阿拉伯之旅本就是艾伦为使传统制造业与美国梦再续前缘的无奈之举。如果说艾伦一度对罗恩归隐自然的选择不以为然,他同样会在大自然的召唤下挽起裤腿漫步沙滩,感受红海轻柔的海浪和清凉的海水。小说结尾处,得知美国公司竞标失败的艾伦透过帐篷的塑料窗望向落日下的碧海,决定留在沙特阿拉伯。从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的视角看,这一“介于悲剧和惩罚之间”的结局实则蕴藏着某种含混性。一方面,艾伦从窗内远眺的举动意味着留在沙特阿拉伯的决定是一次革命性位移,作为典型平滑空间的大海隐喻了艾伦向“最为卓越的被解域者”的蜕变。但正如小说末段所说:“他还不能回家,不能像这样空手而归。所以他会留下来,他不得不留下来。否则当国王再次到来时,谁会在这里呢?”以传统经济模式对现有资本主义体制进行再疆域化改革或许才是艾伦选择留下的终极目标。
看似矛盾的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最终指向的,是小说对基于例外论的美国孤立主义的青睐。这具体体现于艾伦对“墙”的执念:在酒店独酌时,他一度将房间的墙壁视为自己的“朋友”;与扎赫拉的聊天同样唤起他与罗恩在野外搭建临时雪屋的美好回忆。正如艾伦所说:“当时,那(雪屋)是我们最好的御寒物……当一切安顿好后,那里非常暖和。”人工堆砌的坚实雪墙不但是艾伦对传统制造业怀旧情结的物质寄托,更因其构造的独一无二的御寒空间流露出小说对美国一家独大的例外地位的怀念和以孤立主义为指导重振霸权的渴望。因此,小说对美国后来居上的竞争对手——中国的负面描写便不足为奇。除了扎赫拉团队中使艾伦不胜其扰的癫狂的中国麻醉师外,中国公司甚至通过“恶心的”价格战夺走了纽约“归零地”(Ground Zero)建造工程的防爆玻璃生产资格,使美国“颜面尽失”。中国公司在全息图竞标中的胜出,更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呼应。正如扎赫拉所说:“我不知道阿卜杜拉和他的团队是否会突然改变效忠对象。也许你们不再是他的最爱。”“效忠”一词所蕴含的联盟意味,高度契合了亨廷顿对儒家文明或将联手伊斯兰文明对抗西方文明的预言,投射出小说对后“9·11”时代非西方文明冲击下美国非例外处境的抗拒。
进入新世纪以来,深陷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泥沼的美国不得不直面超级大国国内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双向衰退的危机,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最少介入”原则还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口号,都指向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复萌。《国王的全息图》将小说背景设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东,借助美国主人公的跨国旅行巧妙地将当代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并置展现,表达了对美国梦和美国例外论兼具反思与惋惜的复杂情感。小说展现了新孤立主义思潮的涌动下,艾格斯作为文学家的自省和作为超级大国一份子的自负之间的纠结与摇摆。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3期,“新作评论”栏目,责任编辑王涛,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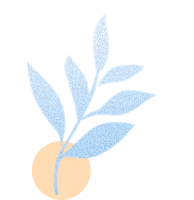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或阅读原文,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