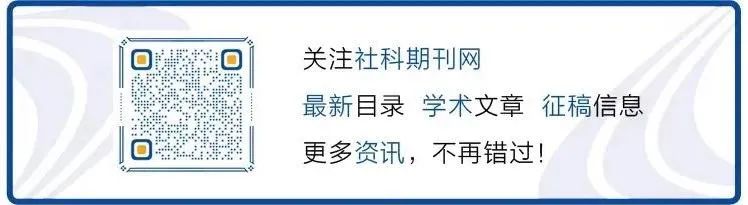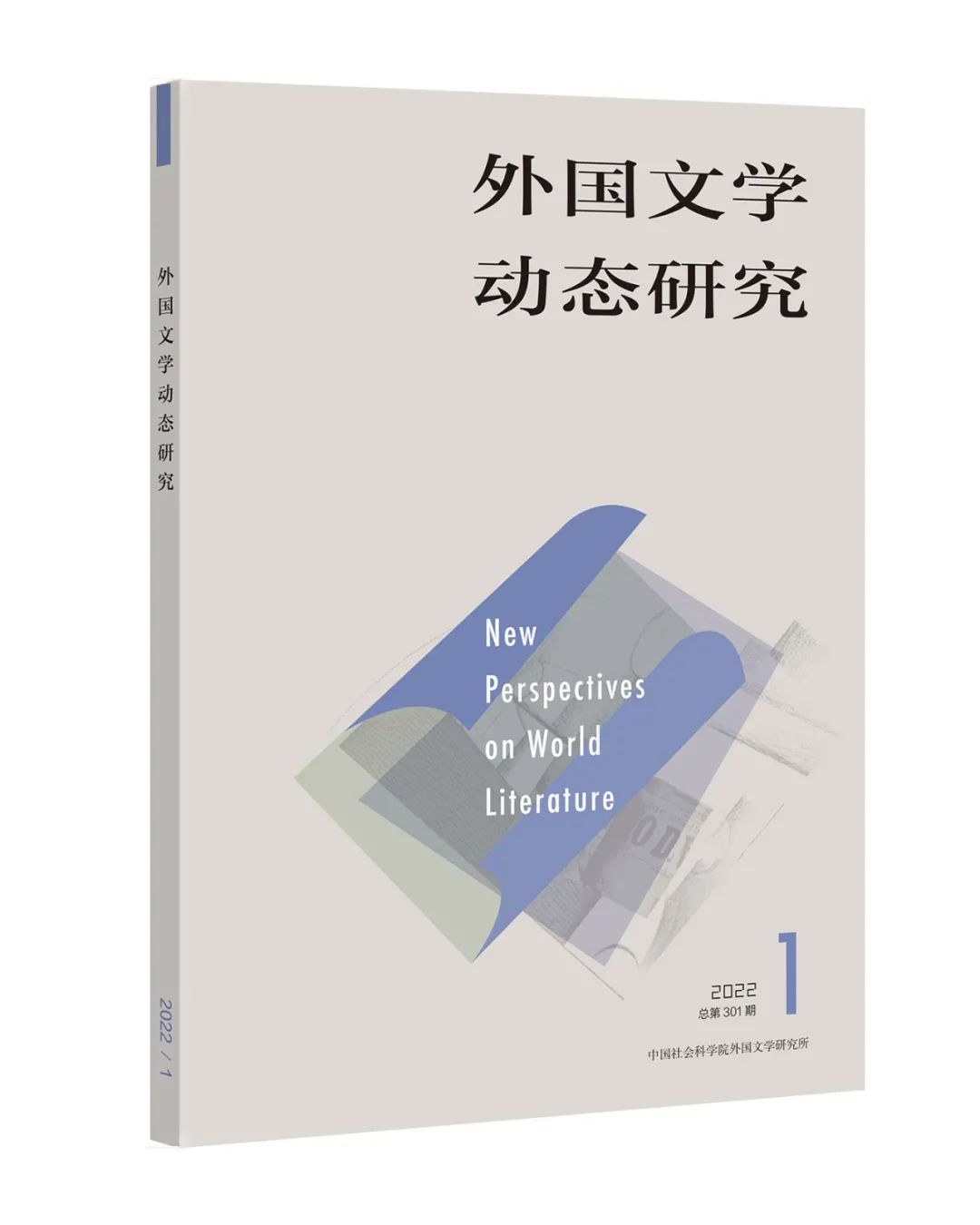作家研究 | 后现代视域下的模糊地带——萨拉·鲁尔戏剧研究

李言实 博士,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当代戏剧、中西戏剧比较。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博士生院马丁·西格戏剧中心访问学者(2017.02—2018.02),2019年度山西省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近年来主持省级课题7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2项,在《戏剧》《戏剧艺术》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20多篇。
内容提要 萨拉·鲁尔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她的剧作对当代美国社会和生活投入了极大关注。在后现代社会中,诸多传统上认为的不同甚至对立开始共存于同一空间,构成一种多元杂糅、生死共存、亦真亦幻的后现代景观。萨拉·鲁尔表达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她的剧作表现了对男性与女性、生命与死亡、现实与虚构等方面矛盾的悖论统一。在性别身份建构上,她解构了男性和女性的传统二元对立,塑造了性别身份模糊的角色;在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上,她打破了生命与死亡的对立状态,建构了生与死的模糊地带;在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上,她打破社会真实与戏剧虚构的边界,构建了二者相互交融的模糊空间。通过解构传统的二元对立,鲁尔在其剧作中构建了一个多元杂糅的模糊地带,展现了21世纪美国社会的后现代景观。
关键词 萨拉·鲁尔 美国戏剧 后现代 模糊地带
萨拉·鲁尔(Sarah Ruhl,1974—)是21世纪以来美国最重要和最受西方戏剧界关注的剧作家之一。她的剧作在美国各地的地区剧院、外百老汇和百老汇演出并受到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曾获普利策奖最佳剧作和托尼奖最佳剧作提名奖。她的剧作也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德、澳、加、中等国家上演。

(萨拉·鲁尔,图片源自Yandex)
进入21世纪,美国社会在各方面发生了变化。随着边缘人群站起来发声和维权,人们对性别身份的认识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性别身份不再局限于男性和女性,而是出现了跨性别群体,与之一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爱情也不再局限于男女两性之间,异性恋、同性恋等模式已不能解释随之出现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对生活甚至生命的介入越来越多,人们对生命与死亡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生与死的概念、界限等不断得以改进和修正;随着越来越多的真实元素进入戏剧,戏剧也开始反噬真实,传统意义上戏剧的虚构与生活的真实之间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映照、融合共存的复杂局面。在这一背景下,诸多传统上认为的不同甚至对立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开始共存于同一空间,构成一种多元杂糅、人机共生、亦真亦幻的后现代景观。萨拉·鲁尔关注到美国当代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在其戏剧作品中表达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性别身份认同是自我认同很重要的一部分。传统上,自我识别或社会建构的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性别身份认同不再局限于男性和女性,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了跨性别群体,他们并不想要在主流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是向传统主流性别制度提出挑战,以表达对传统的男女二分法的抗拒。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性别身份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是表演性的、可变的,而不是一个静态固定不变的本质性的身份。与之一致的是,酷儿理论也反对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二分结构,认为异性恋或同性恋是一种强迫性的性表达,会扼杀掉一切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在男性与女性、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存在着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动态的模糊地带。
萨拉·鲁尔的《晚归:牛仔之歌》(Late: A Cowboy Song, 2006)讲述了一个家庭主妇和一个女牛仔之间暧昧的感情故事。女主角玛丽和她的丈夫克里克从小就喜欢对方,结婚后,克里克仍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没有工作,喜欢待在家里看电影《完美生活》。玛丽怀孕之后越来越喜欢和儿时的玩伴雷德相处,雷德是匹兹堡郊外农场的一名(女)牛仔。雷德教玛丽骑马,她们一起跳舞,一起度过许多美好时光,而这正是玛丽经常回家迟到的原因。

(朱迪斯·巴特勒,图片源自Yandex)
此剧中,鲁尔塑造了两个性别身份模糊的角色——女牛仔雷德和性别身份不明确的婴儿。首先是兼具男性特质和女性气质的角色——独立于家庭和城市生活之外的(女)牛仔——雷德。角色列表中作家刻意指出:“雷德:她不是女牛仔,她是牛仔。”在玛丽眼中,雷德独立而有魅力,玛丽非常享受和雷德相处的时光。第一幕,雷德骑马送玛丽回家,克里克表达了不满:“一个尊重丈夫的女人不会跟另一个男人骑着马到她丈夫的前门……”玛丽告诉他:“她是个女人。”克里克质疑:“她以为她是谁?是万宝路男人吗?”玛丽回答说:“算是吧。她是个牛仔。”在《牛仔英雄: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牛仔形象》中,威廉·赛威格总结了美国牛仔的特点,即:有淳朴的智慧,了解大自然,对女士彬彬有礼。此外,牛仔马术娴熟。鲁尔将这些特质都赋予了“她”——雷德。她既知道怎么“做简单的决定,做简单的事情”,同时与自然相处融洽,她不仅知道怎么赞美女性,而且认为玛丽是知道如何接受赞美的“淑女”。相较于玛丽的淑女气质,雷德表现出绅士般的牛仔品质。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的困扰》中认为,性别是可操演(performative)而不是天生的(ontological),她区分了性别的三种状态,即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以及操演(performance)的性别。雷德一个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女性——虽然也不能排除其性别模糊的可能性;她在社交中表现出了传统牛仔的男性气概;她和玛丽的交往可以说是一种性别操演,其中既有同性之间的友谊,又有异性之间的爱恋,也许还有其他可以尽情想象的可能性。雷德和玛丽的相处模式挑战了玛丽和克里克之间的异性恋关系,同时也挑战了电影《完美生活》中所表现的理想化的传统美国家庭模式。
雷德之外,鲁尔还塑造了另一个性别身份模糊的角色——玛丽和克里克的孩子,进一步挑战了传统的性别二分法观念。孩子出生时就兼具男性和女性特征,即通常所说的阴阳人。在给孩子起名时,玛丽和克里克有了分歧,于是多年来他们都以各自给孩子起的名字来称呼他/她。克里克希望孩子叫吉尔(Jill),玛丽给孩子起名“布鲁”(Blue),他们决定给孩子冠以两人的姓氏,即吉尔/布鲁·史密斯·索恩迪格。玛丽之所以给孩子取名布鲁,也出于雷德的原因,她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真正拥有独立的人格。就像雷德一样……”这样一个中性的名字,就像玛丽在中餐厅打开的空白幸运符一样,给予孩子身份识别和发展以无限的可能性。对于孩子未来的性别身份,玛丽持宽容态度:她可以选择成为她想成为的性别,包括中性。但克里克更希望孩子有一个明确的性别——男或女。玛丽对此质疑道:“为什么她就必须非此即彼?”值得一提的是,在剧作的扉页鲁尔特意表达了对导师保拉·沃格尔以及安妮·福斯托-斯特灵的感激之情。斯特灵教授是布朗大学生物和性别研究专家,也是沃格尔的同性伴侣,在其《身体性别的划分:性别政治与性别的建构》中,她反对目前通行的用医学手段来改变出生时性别模糊的新生儿的性别,呼吁对跨性别者更大的接受和包容。在这一点上,玛丽与其主张相一致。在全剧最后,玛丽和雷德共骑在马上,一起唱起了牛仔之歌:“给我一个孩子,她出落成女子,骑马似男人,还戴着面具。”
21世纪以来,从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到酷儿政治,都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于既定性别规范与体制的抗争。《晚归:牛仔之歌》通过塑造两个边缘人——女牛仔雷德和双性婴儿,表现了酷儿理论所主张的打破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更具开放性、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与后现代主义性别身份的建构模式相契合。通过雷德和布鲁/吉尔这两个角色,鲁尔不仅表达了对性别身份模糊这个问题的关切,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后现代语境下对于传统男女二分的反对,以及对既有模式和秩序的挑战和质疑。21世纪以来,从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到酷儿政治,都体现了美国社会内部掀起的对于既定性别规范与体制的抗争。
生命与死亡是文学/戏剧作品的永恒主题。传统上,人们认为生命和死亡是相互对立的两种状态。进入21世纪,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这种观念。随着对技术的依赖越来越高,手机成为人们须臾不离的重要工具,甚至成为人的身体/思想的一部分,成为一个体外器官。每一部手机就是一个“我”,是处于一个由全球几十亿人构成的巨大网格中的一个节点。如果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手机仍然保持待机状态,仍然在这个网格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他是活着还是死了呢?萨拉·鲁尔2007年的剧作《亡者的手机》(Dead Man’s Cell Phone)就是讨论传统与技术、生命与死亡的一部后现代作品。

(《亡者的手机》剧照,图片源自Yandex)
《亡者的手机》中简在一家咖啡厅接听了亡者戈登的电话,生出一种“他还活着”的假象,由此进入戈登的生活。她几乎爱上了她幻想中的戈登。但是随着电话信息和记忆的构建,真正的戈登与她一厢情愿的想象大相径庭:他非法贩卖人体器官,是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在与其家人交往的过程中,简爱上了戈登的弟弟德怀特,他和简一样,喜欢用传统纸张书写的信息。当简继续以戈登的身份去处理生意的时候,在机场被一个寻找肾源的女人开枪打死。简疯狂地给德怀特打电话,但是手机已经和它的主人一样死去了。绝望的简砸烂了手机,获得了救赎的机会,她被时空隧道送回纽约,与德怀特相拥享受了全世界“最浓烈的爱情”。
首先,现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剧名《亡者的手机》包含了两个悖论性的概念,亡者——一个有机体和他用来与世界沟通的工具——手机。这个有机体死了,但是这个工具却是构成有机体的基本要素。而这个拿起亡者手机的女子英文名为“Jean”,与“gene”(基因)是同音异形字,也是构成有机体的基本要素。亡者已逝,他的手机仍然活着。也就是说,通过手机建立的他与家人、朋友、生意伙伴的联系仍然存在。死者的名字叫“Gorden”,与“Gordian”读音相近,在古希腊神话中,“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意为“难解的结”,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它砍断。所以当简决定接听戈登的手机的时候,她就维持了死者的关系网络,进入了戈登/戈尔迪之结,戈登就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存活于这个网格之中。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凯瑟琳·海尔斯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控制论、文学和信息学中的虚拟身体》中提出了一个启发性观点:生命的本质不在于身体,而在于信息;人工智能机器或技术装置与生物有机体没有本质区别,由它们传送的信息已然成了人类在场的证明。具体而言,戈登的在场已不由其肉身所代表,而是由技术装置即手机及其所承载的信息,或曰数据流来证明。换言之,在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由技术媒介,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来构建。对于戈登的联系人来说,他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活着,而是取决于手机所传递的信息。这种信息交流方式给传统生存模式带来冲击,也进一步挑战,甚至改变了生命与死亡的二元对立,构建了一个介于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模糊地带。
其次,生命和死亡都是由记忆构建的,人们传统上使用纸质的记录方式来承载记忆,但是在网络时代,记忆成为看不到摸不着的信息。那么如何记录一个生命的诞生或死亡?如何通过信息来判断生命的存在或逝去?简在大屠杀纪念馆工作,她的工作与记忆和死亡相关,她负责照看亡者的物品,她想要记住所有的事情,“甚至别人的记忆”。她离开这个保存有死者物品的纪念馆,通过另一个死者的“活着的”手机进入了生者的生命轮回。简用自己的想象构建出一个近乎完美的戈登,虽然这个戈登与大家记忆中的戈登大相径庭,但是大家都很乐意接受,仿佛死亡能够抹去一切令人不快的记忆。第二幕一开始,戈登复活了。但是随着戈登的回忆,我们发现他和简想象的戈登完全不同——他从事的是黑市人体器官买卖,将赚来的钱变成了妻子手上昂贵的戒指。他为了实现目的不择手段,还为自己找到貌似合理的理由:“我所做的就是确保这些可怜的坏家伙死得其所——我确保他们的器官能够给需要的人。”当简去约翰内斯堡机场继续戈登的一桩肾脏生意,被黑衣女子打晕过去的时候,她和戈登经过“灵魂通道”来到地狱——一个专为在黑市上买卖人体器官的人和爱他们的人的专属之地。简发现这个地方有点荒僻,虽然看不到其他人,但她仍然能听到手机里传出的说话声,“空气会记住这个地方的所有音乐”。手机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一部手机就是一个记忆的存储库,一种让它的主人——死者戈登在某种意义上得以复活的方式。通过模糊传统生与死的界限,鲁尔意在使我们思考:我们以为我们了解的事物,我们以为已经死去的事物,可以被发现,可以被重新发现并且重新具有生命力。
一直以来,戏剧与现实的关系都是戏剧理论的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是对现实的模仿,这一思想贯穿了西方戏剧发展的历史,现实与模仿的二元对立也一直伴随其中。为了区分戏剧的虚构世界与真实的现实世界,戏剧用化妆、服饰等手段将剧中的虚构角色和现实中的演员本人区别开来,但是,当演员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其身份和行动具有戏剧与现实的双重性。在戏剧创作和排演的过程中,萨拉·鲁尔也注意到了演员和舞台角色及其行动的双重性。她尤其关注舞台上涉及人物亲密关系的种种问题,如接吻,如何在舞台行动中融入真实,如何将这个舞台行动带入现实,角色和演员如何跨越现实和虚构界限,生活/表演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和虚构的模糊地带。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都体现在她的《舞台之吻》(Stage Kiss, 2014)一剧中。在接受“节目单”网站(Playbill.com)的采访时,鲁尔说:“这部戏是关于在舞台上接吻这种现象的。我在剧院里工作了十五年。有人以接吻为工作,他们来上班,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吻,我总觉得这很奇怪,我想深入探索这件事情……这是关于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不真实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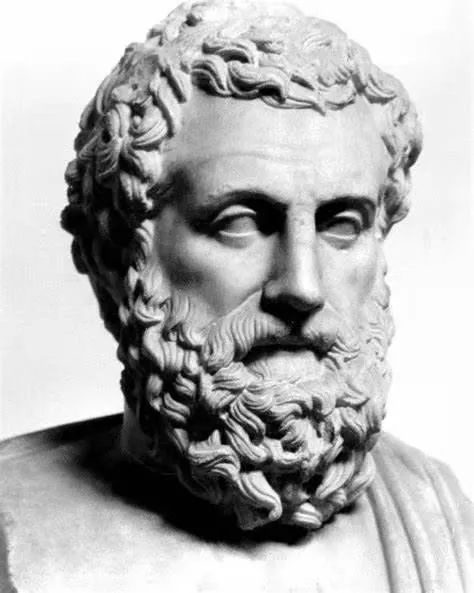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图片源自Yandex)
《舞台之吻》中两个旧情人?“她”和“他”是二十多年前的初恋,如今已人到中年。在复排一部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剧《最后的吻》中,他们需要相互亲吻。排练过程中,他们旧情复燃,舞台上的吻延续到舞台下,又从舞台下到舞台上。鲁尔用戏中戏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故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她”和“他”在舞台上接吻的时候,一开始是出于剧情的需要,那么从哪一刻起,两个角色之吻成了两个演员之吻呢?演出结束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吻是不是也有角色情感的成分鲁尔在这部戏中通过寻找“真吻和假吻之间难以界定的分界点”,进一步探讨真实生活和虚构艺术之间的关系,即是戏剧模仿生活,还是生活模仿戏剧。
首先,鲁尔以元戏剧的手法创造出双重故事空间,以戏剧和生活两个层面的相互映照,模糊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虚拟的戏剧空间,“她”和“他”重排一部音乐剧,“她”在其中扮演艾达,“他”演约翰尼。艾达的生命只有一个月了,临终前她想见一见她的初恋情人。接到电话后,约翰尼从瑞典赶回纽约,在她位于曼哈顿的豪宅里陪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在艾达富有而体贴的丈夫的包容下,他们重拾当年旧情,艾达的病情也因此得以好转。不过,在共同生活中约翰尼却爱上艾达的女儿,并带她私奔去了瑞典,最后留下艾达自己收拾残局。在现实生活空间,“她”和“他”是二十年前的初恋情人,现在的“她”已有丈夫和女儿,而“他”也有女朋友。排练中,他们旧情复燃了。两个故事同时展开,环境和人物如此相似,以至于他们自己也常常分不清虚构与现实,在戏剧与生活、角色与真实自我之间来回摇摆。他们自己可能都很难界定,他们的吻和情在哪一刻是角色的,哪一刻是演员自我的。
与双重故事空间相一致的是,剧中人物也具有戏剧角色和现实自我的双重身份,他们总是分不清戏剧和现实,经常混淆角色和自身的话语及行动。最初,排练休息的时候,“她”和“他”还能够走出剧中角色,回到现实中。随着情节的发展,他们在剧中角色和真实自我之间频繁出入,不知是因戏生情还是因情入戏,逐渐模糊了剧中角色和现实自我的身份。幕间休息时,“她”以剧中角色名“约翰尼”称呼“他”,而“他”以剧中人名“艾达”加上生活中“她”的夫姓来称呼“她”,而“她”先以艾达的身份说话,接着仿佛意识到什么,又再次以自己真实的身份说“我不知道”。剧情接近尾声,“她”越来越深陷其中,希望继续这种戏剧中的生活:“我不想是我,我想成为艾达。”但是,“他”想要的并不是艾达,而是真实的“她”。他们开始接吻——如舞台指示所示“一个真正的吻”。这个吻如何区别于舞台上的吻?可能他们自己也分不清。“她”问:“我刚刚吻你的时候是不是像一个演员吻另一个演员或者一个人吻另一个人,因为在前几周我吻了你这么多次,我现在都分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了。”他回答:“像两个人之间的吻。”但是戏演完了,没有人告诉他们(吻)“该如何结束”,或者“什么时候结束”,又或者“也许没有结束”。
“她”和“他”入戏越来越深,甚至将戏剧带入生活,开始以剧中的角色在现实中生活。第二场第一幕,在曼哈顿的一个公寓中,“她”和“他”穿着剧中的衣服,仍以剧中角色艾达和约翰尼的口吻说话,这使得观众误以为他们仍在演出中。但是,地上散乱的对此剧的差评和窗外的噪音告诉观众,这是现实生活中。将他们从戏中生活唤醒和提醒他们回到现实中的人,是“她”的丈夫哈里森。哈里森了解他的妻子,知道“她”不能分清戏剧和现实,他认为他们之间仅仅是演戏,并不是真正的爱情:“你们互相亲吻,一晚上亲九次,一周演八场,一共演四周,你们一共要亲二百八十八次。这不是爱。这是催产素。”哈里森让“他”“不要以那种30年代戏中的腔调说话”,让“她”“脱下戏服,咱们回家吧”。他希望“她”教自己演戏:“我想让你带我去剧场,每周吻我一次,假装我是别人。每周一次,你想让我是谁我就是谁;我想让你是谁你就是谁。”最后,“他”离开了,“她”和丈夫哈里森在舞台上拥吻,舞台指示的说明是“这个吻简单得就像真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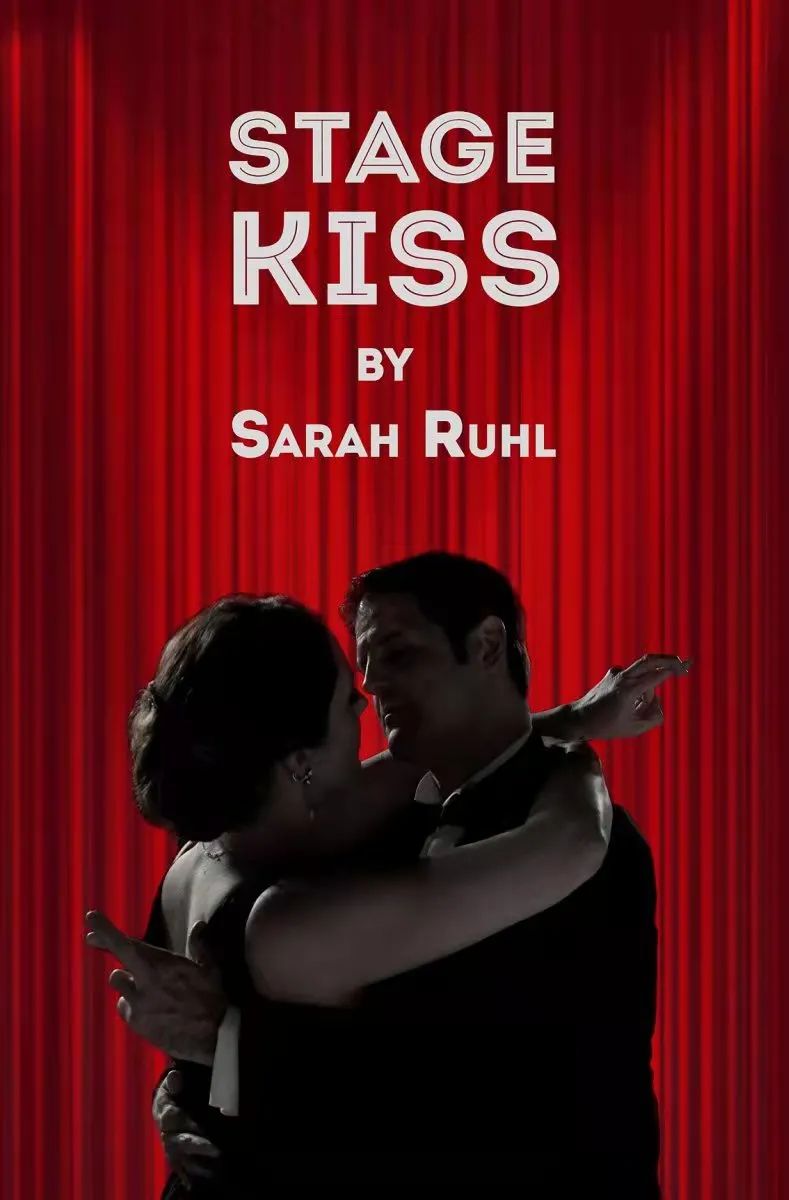
(《舞台之吻》,图片源自Yandex)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想将“她”从戏中拉回现实生活的哈里森,自己却只能以进入戏剧的方式来亲吻妻子,挽回与妻子的爱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舞台之吻》是温情的,因为它打破了舞台上浪漫爱情的幻象,挽救了现实生活中的婚姻;但同时它又是无情的,因为现实婚姻得以拯救是以其进入舞台上的幻象为代价,所以剧终之前哈里森和“她”之间所谓“真实”的吻就被嵌入了戏剧的框架。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使得生活与戏剧、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更为复杂。鲁尔用《舞台之吻》解构了它们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构建了一个相互交叠和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划出界限的模糊地带。
温蒂·B·法里斯认为,现代主义与认识论,或者说与知识的问题相关,而后现代主义更关心的是本体论,或者说关于存在(being)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拉·鲁尔的剧作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后现代主义,而不是现代主义的特点,她没有去寻求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真理”,而是更愿意探寻和挑战传统观念本身,并且更关注本体论而非认识论。她质疑传统的男女二分法,表现了21世纪以来社会性别观念的转变;她模糊了传统生与死之间的界限,表现了技术的进步给传统观念带来的冲击;她甚至打破了戏剧与生活、艺术与现实的界限,表现了二者相互介入、相互映照的复杂的关系。通过解构传统的二元对立,鲁尔在其剧作中构建了一个多元杂糅、生死共存、亦真亦幻的模糊地带,展现了21世纪美国社会的后现代景观。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3期,“作家研究”专栏,责任编辑苏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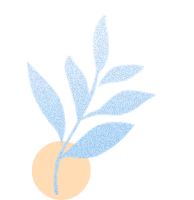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或阅读原文,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