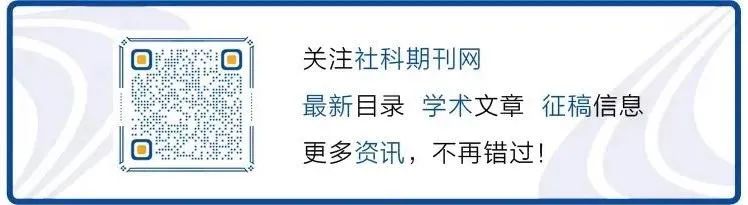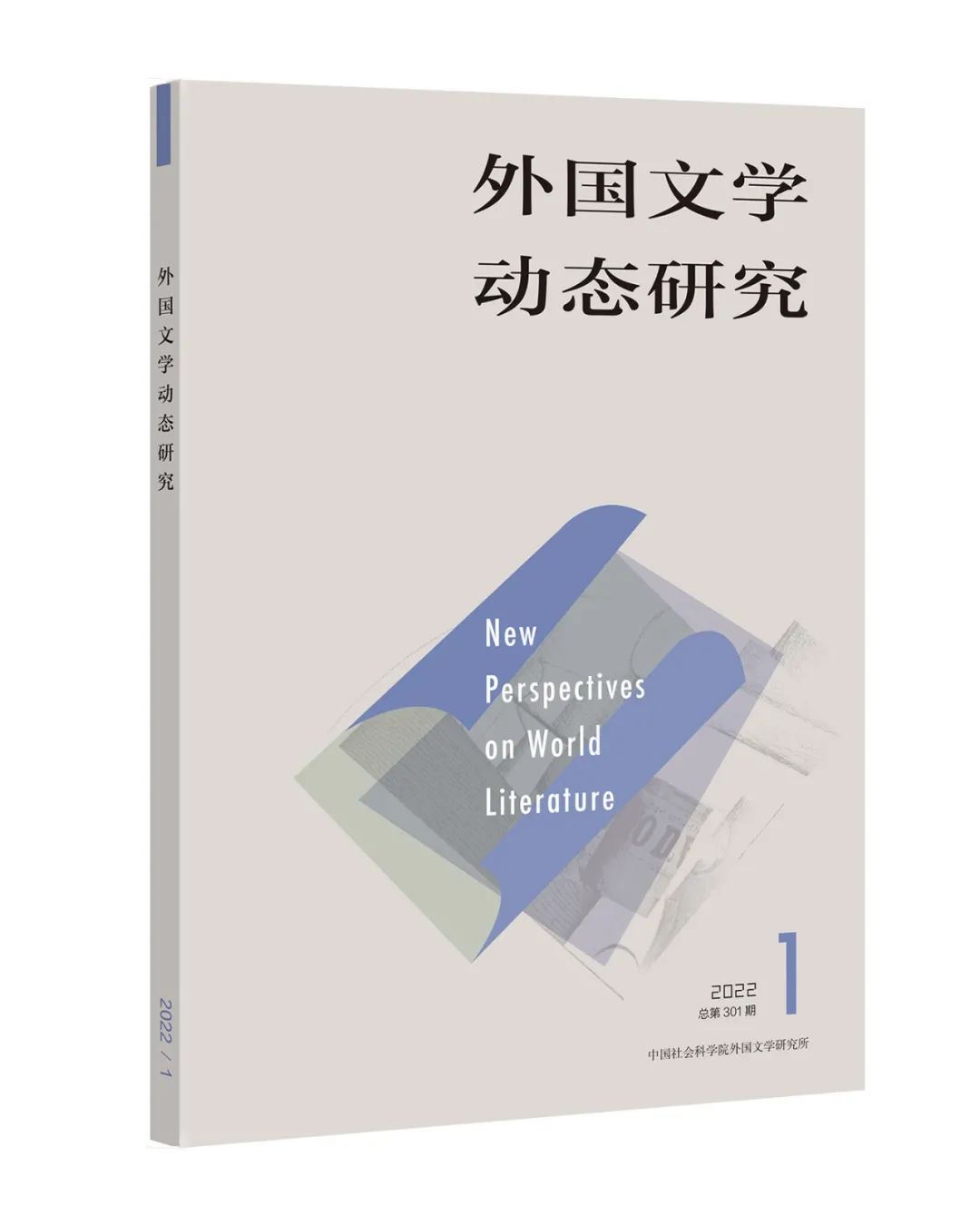动态研究 | 美国“9·11”小说中的时空记忆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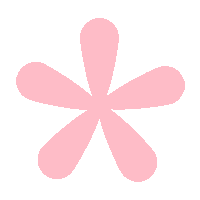


王薇 博士,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美国小说及文化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2项,在《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内容提要 2001年以降,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为叙事要点的美国“9·11”小说,从多角度、多层次塑造时空记忆场的方式,唤醒、再生后“9·11”时代文化记忆。本文运用诺拉的“记忆场”概念,分别从时间记忆场和空间记忆场两方面入手,着重探讨美国“9·11”小说如何呈现“此刻”(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和“此地”(世贸双塔和“归零地”)等相对固定的时空记忆场,又是如何从“记忆场”踱进“纪念地”书写,进而揭示美国“9·11”小说时空记忆场的动态演变特征。本文认为,“记忆场”到“纪念地”的书写使美国“9·11”小说摆脱了常见的创伤书写带来的负面观感,产生了时间进程延续与空间秩序重建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 美国“9·11”小说 记忆场 纪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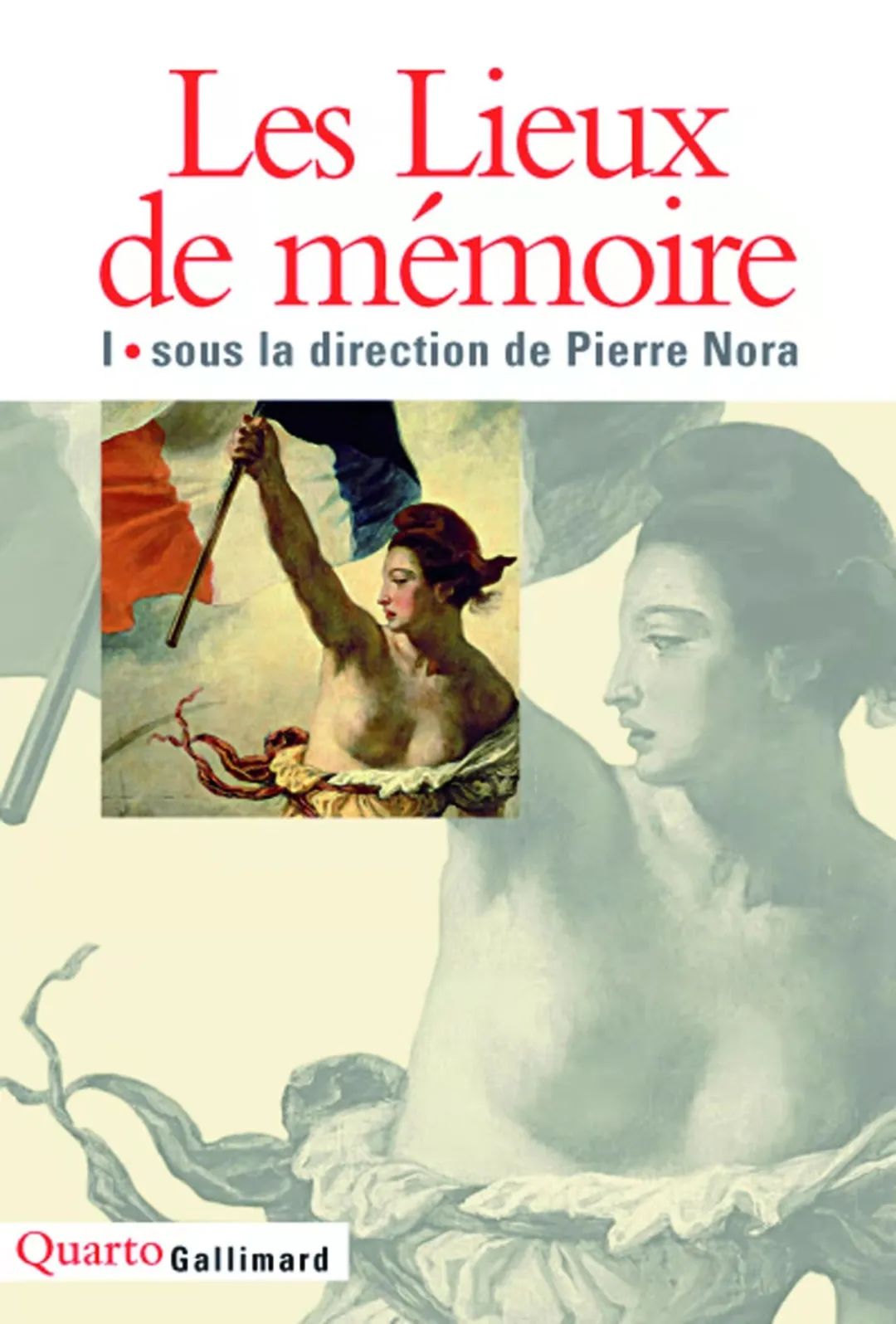
(《记忆场》,图片源自Yandex)
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在七卷本巨著《记忆场》中提出“记忆场”这一概念,以此指“任何能在集体层面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文化现象(无论物质的、社会的或精神的)”。《记忆场》收入了一百三十个“法国民族的记忆以特别的程度得以浓缩、体现和结晶的记忆场”。按照诺拉的观点,“记忆场”具有“物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意义”。也就是说,“记忆场”不仅是肉眼可见、亲身经历的记忆场所,而且可以是占据时间单元、具有抽象意义、形成仪式对象等文化现象的普遍集合。颇具动态和张力的“记忆场”概念,为研究文学作品中的时空意象具有理论借鉴意义。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为叙事主题的美国“9·11”小说,以多角度、多层次塑造时空记忆场的方式,唤醒、再生后“9·11”时代文化记忆。本文运用诺拉的“记忆场”概念,分别从时间记忆场和空间记忆场两个部分入手,探讨美国“9·11”小说如何呈现“此刻”(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和“此地”(世贸双塔和“归零地”)这个相对固定的时空记忆场,以及如何从“记忆场”踱进“纪念地”书写,进而揭示美国“9·11”小说时空记忆场的动态演变特征。

美国著名作家唐·德里罗曾说:“正是失去了的历史才成为小说精巧细致的编织物,小说就是重温曾经发生的一切,也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就叙事与历史的关系而言,德里罗认为,当历史成为失去了的记忆之时,小说能使我们得以再次理解过去、理解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9·11”小说成为作家们对“9·11”恐怖袭击事件进行的“第二次诉说”。“9·11”事件发生之后,针对蜂拥而至的媒体呈现和文学表达,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曾犀利质问道:“我们能够马上听到这些事件有无先例吗?我们能够马上认识它们,并从中汲取教训吗?”正如巴特勒所言,对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突发性灾难事件,文学创作试图在“第二次诉说”中快速认识、理解与反思或许着实不易。面对令人震惊、恐惧、悲伤、愤怒的事件现场,文学的第一要务是在大众可以理解的感知/认知的范畴中,找到符合文学逻辑的表述方式。从弗尔、德里罗、沃德等作家创作的美国“9·11”小说来看,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如德里罗所言通过“第二诉说”将“过往的形象”保留下来,以再现“此刻”的书写方式——尤其着重书写瞬间停滞——构造同质于“此刻”的时间记忆场。
整体来看,无论是故事时间的选择还是话语时间的设定,“9·11”小说都详实记录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的个体体验,以再现“此刻”的书写,摆脱追述往事的叙述眼光,直接指涉在场的“此刻”。其中,对时间瞬间凝滞的集中呈现,成为“9·11”小说的“此刻在场”描写的主要方式,使“9·11”小说存储并保留了相对同质特征的“此刻”的时间意义。具体来看,在美国“9·11”小说中,“那一天的晴朗天空”成为瞬间凝滞性时间“记忆场”的描述对象。时间标尺——2001年9月11日,成为“此刻在场”的时间表现形式。小说中,物理时间停滞在“那一天”,似乎“天空”成为“那一天”悲剧性停滞时刻的权威见证。比如,在小说《恐怖分子》中,“那一天天空特别明亮,那个虚幻的蓝天已成为传说,一个天国般的讽刺,成为美国传奇的一部分,如同火焰的红色尾焰”;在《坠落的人》中,“那一天的天空迥然不同,一片晴朗”。在《回声制造者》中,主人公马克的混乱记忆停留在“纽约是漂浮在远处地平线上的一片黑色羽毛”。可以说,大众在仰望天空的时刻,“晴朗的天空”与“漫天的灰尘”产生了戏剧性的撞击,同时刺激观者产生更加强烈的直观感知。正如罗伯·格里耶指出的,“在现代小说叙述中,人们会说时间在其时序中被切断了,它再也不流动,描述在原地踏步,在自相矛盾,在兜圈子,瞬间否定了连续性”。之所以在“9·11”小说中大量存在此类瞬间凝滞描写,无疑是因为瞬间记忆的“否定连续性”。随着物理时间的停滞,小说的叙事时间产生中顿,人物的心理时间感知却由于“此刻”的静止而产生了延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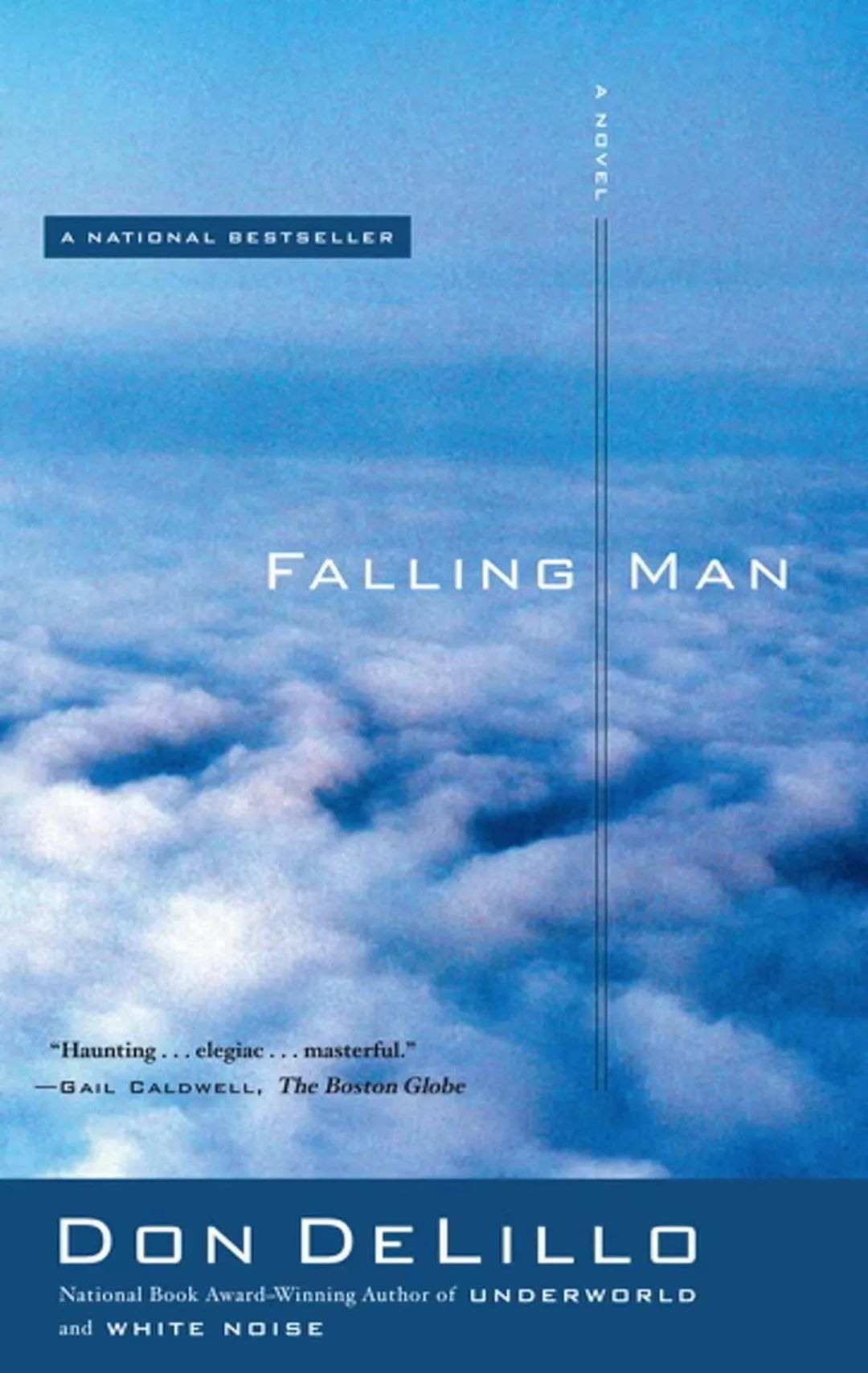
(《坠落的人》,图片源自Yandex)
如果说凭借瞬间凝滞书写加强的是“此刻”再现的叙事效果,那么,“此刻”再现的叙事目的便是催生后“9·11”文化记忆。也就是说,美国小说凭借“此刻”再现的时间记忆场叙事方式,进一步推进了文化记忆的深层重构与再生。例如,德里罗小说《坠落的人》中,街头艺人反复进行的“坠落的人”表演,即是凭借“此刻”再现而重构后“9·11”文化记忆的典型一例。小说的第三部分标题便是这位街头行为艺术表演者的名字“戴维·雅尼阿克”。街头艺人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使主要人物丽昂产生精神顿悟,他反复表演的内容正是在“9·11”事件当天从世贸双塔上纵身跃下的“坠落的人”的景象。街头艺人的表演,唤起观者对“9·11”事件瞬间闪光灯记忆,同时不断地提醒文本内的旁观者和文本外的读者:“那一天”——2001年9月11日——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已经“缺席”。可以说,德里罗通过对街头艺人反复表演的叙述,将“9·11”事件融入了集合过去和现在的时间观之中:“此刻”不再是纯粹的凝滞的“现在”,而是吸纳了过去的要素,演变成为更加具有生产性的文化记忆瞬间。本质上看,德里罗对街头艺人“坠落的人”的叙述内容,关注的焦点不再是“9·11”事件所存留的瞬间记忆本身,而是在或反复操演,或切割重组,或调遣变形的过程中生成的一种“被记忆所解释的习惯”。也就是说,由于“过去”的嵌入,记忆在关注持续、反复、动态呈现的叙事过程中重构了异质化的事件意义。
由此,在“9·11”事件发生十余年后,对经受了恐惧、焦虑、失去感知意义的后“9·11”时代观者而言,“9·11”事件的文化记忆既存在于那个难忘瞬间的停滞感觉之中,又存在于“此刻”和“过去”之间的交叉重叠。对“9·11”小说中时间“记忆场”的构建而言,“此刻”在场书写形成瞬间凝滞的事件记忆,这意味着相对同质的文化记忆得以留存;“此刻”再现书写则通过反复的操演,将“过去”嵌入“当下”,从而形成“立足当下、回望过去”的相对异质的文化记忆。由此,美国“9·11”小说的时间“记忆场”将“9·11”事件的认知过程动态化,并对后“9·11”文化记忆进行了异质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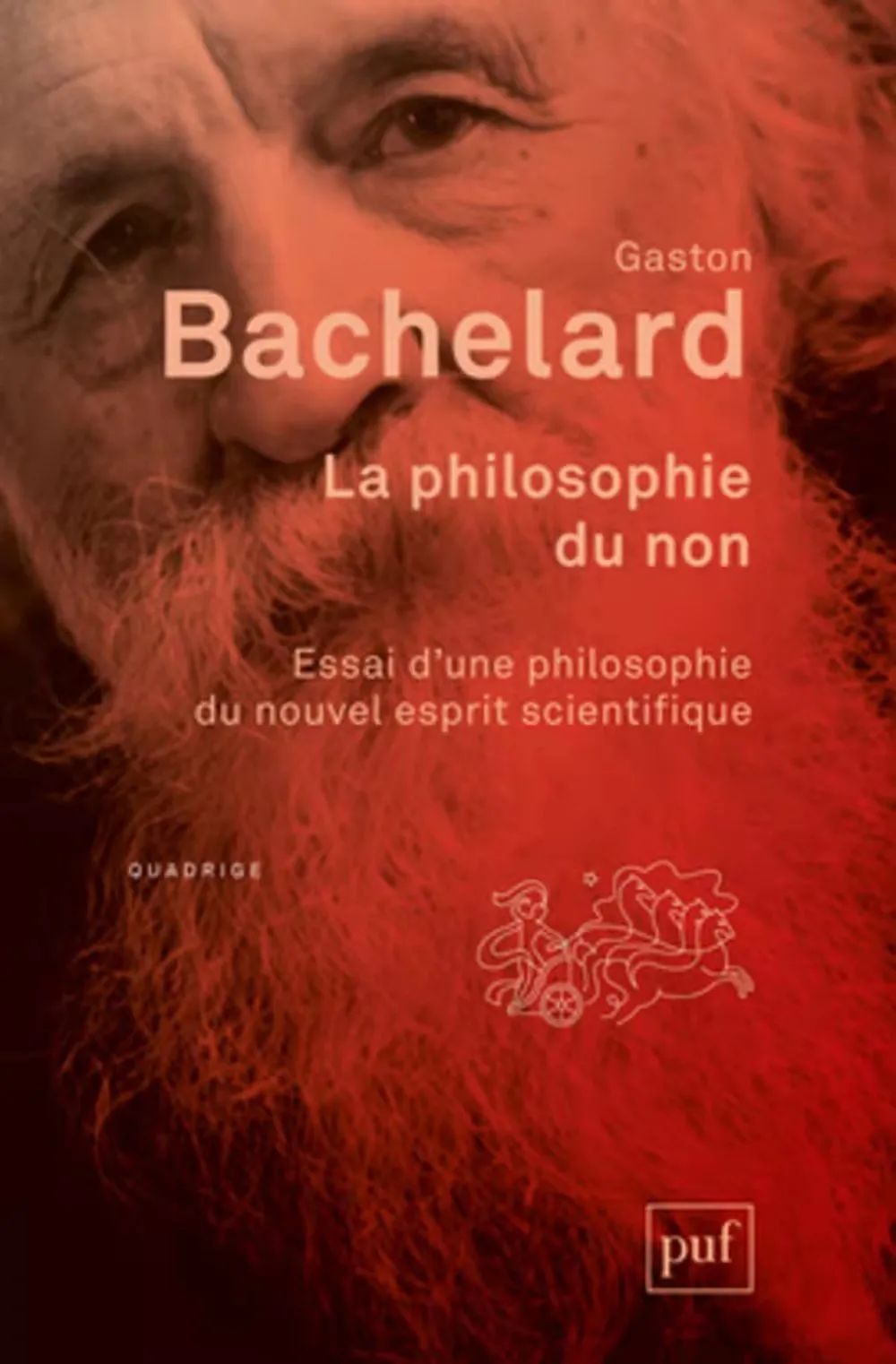
(《空间的诗学》,图片源自Yandex)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曾说:“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关于后“9·11”文化记忆的讨论,不仅需要考察时间记忆场中凝结在“此刻”所生成的文化记忆,而且需要具体探讨各种空间记忆场的构成要素。正如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的“化石”隐喻,美国“9·11”小说中纷繁的空间想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往记忆在具体空间中的再现。从多部美国“9·11”小说的空间书写范畴来看,核心空间记忆场主要涉及对倒塌的世贸双塔以及随后形成的废墟“归零地”等物理空间的再现。下文以美国“9·11”小说中核心空间记忆场从世贸双塔到“归零地”的演变为切入点,分析美国“9·11”小说的空间记忆场如何实现对文化记忆的唤醒与重构。
“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袭地点之一——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华尔街的世贸中心,成为多部“9·11”小说空间“记忆场”书写的核心物理空间。首先,世贸双塔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这在多部“9·11”小说中得到鲜明的呈现。作为纽约曼哈顿的标志性建筑,世贸双塔自20世纪70年代落成以来便代表着“一座想象美国的碉堡”。世贸双塔之所以成为了恐怖袭击的首要目标,是因为摧毁世贸双塔所产生的符号象征意义远远超越建筑物被摧毁的客观事实——“这象征着资本主义特权能力的丧失”。
如果说“9·11”事件中被摧毁的世贸双塔象征着“资本主义特权能力的丧失”,那么在小说《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作家科伦·麦凯恩别出心裁地展现了另外一次对世贸双塔“善意的、诗意的”突袭。20世纪70年代,在刚刚落成的世贸双塔之间,法国艺人进行了一场走钢丝表演。作家麦凯恩创造性地将两场相隔二十七年、发生在世贸双塔间的历史事件进行并置,使世贸双塔产生了某种历史对称性符号意义:“走钢丝的人”对双塔进行“善意的、诗意的”突袭,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征服”了世贸双塔,使自己成为傲居高处、俯瞰众生的“王者”,使世贸双塔从一个“想象美国的碉堡”转变为一个被降服的“臣子”。反观“9·11”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毁大楼,并不是以行为艺术,而是以自杀式爆炸这种更加暴力的“表演”,摧毁了世贸双塔。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在两场事件中世贸双塔都从目空一切的帝国主义象征的位置上被拉下、被征服,但从结果来看,在走钢丝事件中世贸双塔以“存在”为基本前提,而在“9·11”事件中,世贸双塔的“消失”成为恐怖袭击的直接结果。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在小说中形成了故事的张力:读者在为“走钢丝的人”的征服壮举呐喊欢呼的同时,深刻体悟着世贸双塔在当下的悲剧性结局。
其次,“9·11”事件中,世贸南北双塔相隔十七分钟相继遇袭,这种重复袭击产生的叠加恐怖效果也成为美国“9·11”小说空间记忆场的描述重点。例如,在小说《坠落的人》中有如下场景:从“9·11”灾难现场死里逃生的主人公基思,在“9·11”事件之后,与妻子丽昂一起观看了“那些飞机”的录像。在当事人的事后记忆中,“两架飞机”相继出现在“那一天”的天空中:
如现场见证人所述,当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北塔,带给人们的观感除了惊讶之外,仅仅认为这发生了一场意外事故:“它看上去仍然像是发生了意外,第一架飞机。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我站在这里,距离这么遥远,完全置身事外,依然觉得它是一次意外事故。”然而,随着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南塔,“出人意料的效果”被完全打破,“人的意图的力量”即邪恶之人的邪恶意图的破坏力量呈现在世人面前。正如小说中人物所言,“第二架,到了第二架飞机出现时,我们更成熟一些,心里更清楚一些”。受害者所说的“心里更清楚”,实际上是由于两架飞机的撞击,让人们确认了这是一场蓄意实施的恐怖袭击,“更成熟”则是人们打消了幼稚而单纯的意外事故之感,开始思考事件的严重性与严肃性。正如小说中的描述:“第二架飞机从湛蓝剔透的天空中钻出来,这就是那一段叫人刻骨铭心的连续镜头。那一转瞬即逝的冲刺携带着生命和历史,冲向遥远的地方,远远超越了双子塔楼。”如果说,第一架飞机的撞击标志着悲剧的开端,那么第二架飞机则超越了世贸双塔的悲剧本身,使这场袭击事件的恐怖影响辐射至更广阔的空间记忆场——“冲向遥远的地方”。因此,世贸双塔的一再“归零”,不仅意味着恐怖的降临、传统的丧失、现实的创伤,更能体现空间秩序的彻底失衡。
此外,美国“9·11”小说对世贸双塔遇袭后成为废墟“归零地”的描写,也成为“9·11”小说进行重塑的空间“记忆场”。本质来看,“归零地”的文化意义与文学史中惯常表达的废墟意义存在显著差异。众多古代遗址形成的“废墟”,一如瓦尔特·本雅明的精彩论述,体现了“历史是如何踱进它的发生地的”。也就是说,废墟本应承载的,正是自古流传、能继续传承的历史,理应成为文化记忆生成的支撑物与基石。然而,“9·11”事件后的这片废墟——“归零地”,并没有古代遗址废墟所必然关联的那些久远历史。在恐怖分子挟持第一架飞机撞上北塔的瞬间,到世贸双塔完全倒塌的时刻,中间仅仅相隔一百零三分钟。可以说,这个空间在瞬间便成为了一片废墟。古代遗址废墟在浪漫派诗人的笔下化为了“永恒踱进的场地”,文学为这些久远的建筑残存镀上了一层美和永恒的光晕,而在美国“9·11”小说中,这片“归零地”废墟在瞬间毁灭后残存于世,在文化记忆的生成中并没有历史的沧桑和美感,而仅存阴暗的光线、颓废的氛围和令人沮丧的无助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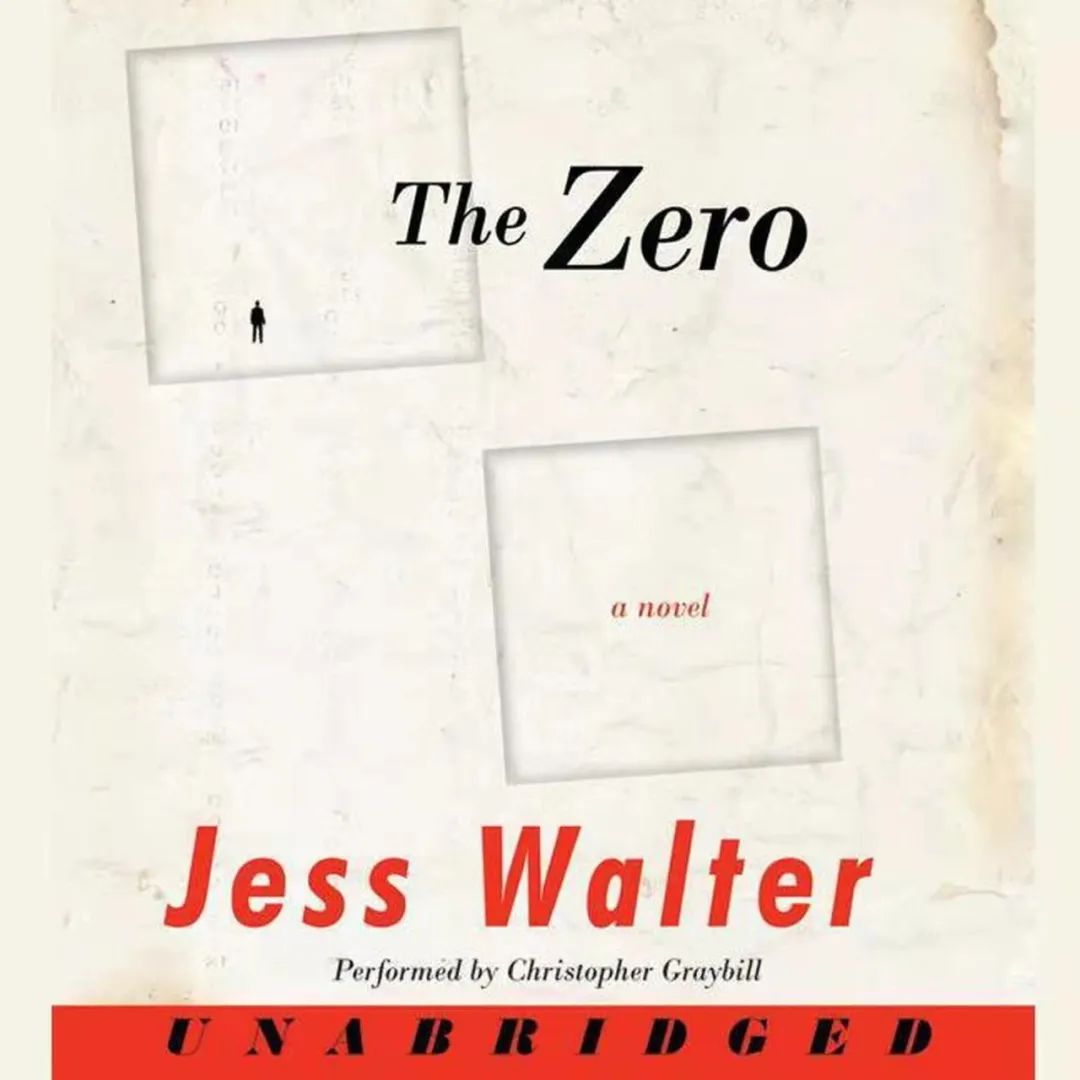

(《零》和杰斯·沃尔特,图片源自Yandex)
杰斯·沃尔特(Jess Walter)的《零》(The Zero)是一部典型的“归零地”题材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布莱恩是一名纽约警察,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被秘密政府部门征召,前去世贸双塔废墟“归零地”,调查废墟附近发现的可疑“纸片”。在小说《零》的开头,沃尔特将“纸片”比喻成“飞翔的鸟儿”,并以充满诗意的描写方式向读者展现这个废墟空间:
随着小说中的“纸片”漫天飘落,《零》中的空间记忆场以世贸双塔及“归零地”为起点,辐射到范围更广的物理空间。除《零》之外,《坠落的人》《恐怖分子》《回声制造者》等众多美国“9·11”小说的空间书写,均凭借覆盖更广的文化记忆提取情境,“最大程度地审视最糟糕的世界”。正如《坠落的人》开篇,德里罗写道:“这不是一条曼哈顿街道,这是整个世界。”如果说此处文本标志着作家将主人公无处可逃的危机情境刻意扩大,使之形成“整个世界”的灾难场所,那么,以此为代表的美国“9·11”小说的空间记忆场,则以世贸双塔和“归零地”为书写起点,以“整个世界”为书写氛围,随之生成的是超越“此地”、辐射面甚广的后“9·11”文化记忆提取情境。

美国“9·11”小说时空记忆场,无论是对“此刻”的再现,还是对“此地”的重塑,凭借时间的瞬间凝滞和空间的拓展演变,愈发呈现出超越“此刻此地”的异质特征。从叙述旨归来看,前文所述美国“9·11”小说时空记忆场,不仅实现了见证过往的再现式书写,而且凭借跨越“此刻”,超越“此地”,产生从“记忆场”转向“纪念地”的书写趋向。如果说,“记忆场”书写重在见证过往、体现在历史和创伤中产生的断裂感,那么美国“9·11”小说中的“纪念地”书写,则更为注重营造面向未来的疗愈和延续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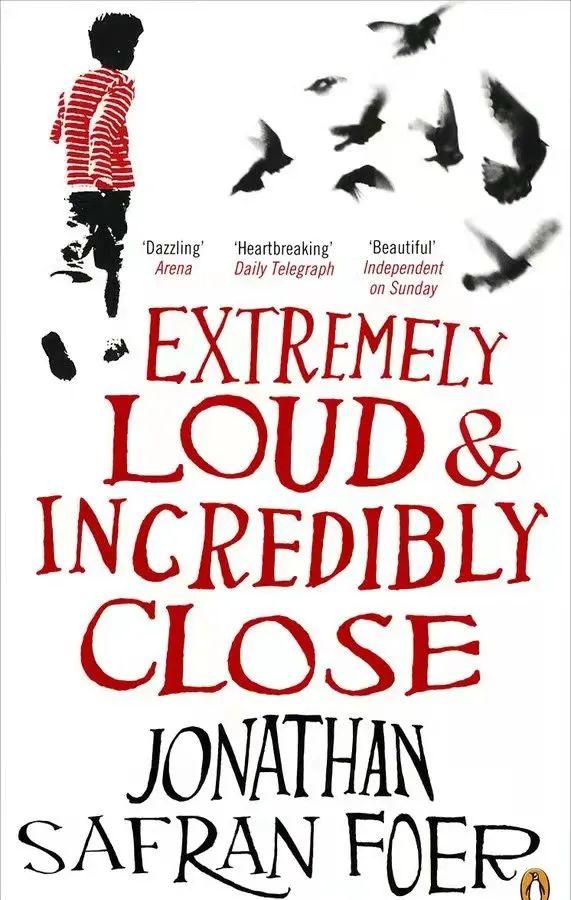
(《特别响,非常近》,图片源自Yandex)
不同于“归零地”在后“9·11”文化记忆中存留的阴暗光线、颓废氛围和令人沮丧的无助感,“纪念地”是一个体现着现实与过去非连续性的记忆场,它需要经历再设计与再建设的过程,从而标明现实与过去的显著差别。例如,在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中,在“9·11”事件中痛失父亲的九岁男孩奥斯卡,代表了游走在后“9·11”危机城市中的“漫游者”形象。小说家弗尔透过男孩奥斯卡天真心灵体会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辨别各种记忆与遗忘的谎言,并大量运用具有乌托邦特征的科学幻想以及“寻找第六区”等儿童游戏,试图在这个失去了秩序的“异托邦”中找寻心灵救赎之路。如皮埃尔·诺拉所言,“记忆场”到“纪念地”的转变,实则为从“回忆氛围”到“回忆之地”的过渡。也就是说,作为“回忆之地”的“纪念地”,为了让那些不再存在、不再有效的东西继续有效地存在,必须编织一个“故事”,用以填补那已经成为过去的“氛围”。可以说,《特别响,非常近》透过奥斯卡的纽约都市漫游,恰是通过建构“故事”的方式,补偿性地重寻纽约都市中失落了的温情与秩序,实现了“记忆场”到“纪念地”的过渡。
虽然“纪念地”将“此刻此地”划归到遥远的过去,以显著特征标明了过去与现实之间的非连续性,但是“纪念地”可以利用其特殊的设计重新激活回忆,甚至重塑文化记忆。也就是说,在编织“纪念地故事”的过程中,过去的残存物成为故事的元素,也成为了再生文化记忆的关联点、生长点。2011年,在“9·11”事件发生十周年之际出版的小说《屈服》(The Submission),便是直接形塑“9·11”“纪念地”的作品。小说中,建筑设计师穆罕默德·可汗凭借作品“花园”(“The Garden”)在匿名的“9·11”纪念地设计比赛中获胜。然而,比赛结果揭晓后,却由于其穆斯林身份,“花园”作品遭遇到媒体和大众的质疑。整部小说围绕着建筑师、评审团、遇难者家属等对纪念地——“花园”进行多元阐释。由此,有别于其他“9·11”小说时空记忆场的见证视角,《屈服》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大众对穆斯林群体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为焦点,切入“纪念地”的书写,成为打破创伤叙述模式的“9·11”小说创新之作。小说中,“此刻”不再凝固于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而是以面向未来的方式书写了“纪念地”的建造以及人物二十年后的何去何从;“此地”也不再局限在世贸双塔和“归零地”,而是跨越美国与印度孟买等多空间,多次转换,使得被记忆或是被遗忘的“记忆场”转变为曾经冲突对抗的双方得以彼此再交流、再认识的“纪念地”。
综上所述,凭借“记忆场”到“纪念地”书写,《屈服》《特别响,非常近》等美国“9·11”小说摆脱了常见的创伤书写带来的负面观感,产生了时间进程延续与空间秩序重建的双重意义。对美国“9·11”小说家们而言,重要的不是“记忆场”争夺之战的孰胜孰败,而是强烈身份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意识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正如小说《屈服》的结尾所述,二十年后,当“9·11”遇难者的儿子把纪念父亲的石堆安放于建筑师建造在遥远印度孟买的“纪念地”——“花园”中时,曾经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在“想象”中达成了共识。又如在《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结尾,“人类秩序的碎片”在一只钟表响起时寻回了秩序——“世界在旋转。我们跌跌撞撞继续前进,在他人身上找到我们自己的延续”。由此,在遥远的空间维度中,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中,“记忆场”踱进了具有和谐共存效应的“纪念地”。沃德曼把《屈服》的结尾设置在遥远之地,麦凯恩把小说结尾设置在“离现在不算太远,离过去也不算远”的未来,可见,作家们在“纪念地”书写中感兴趣的,是为后“9·11”文化记忆营造一个跨越时空、彼此关联的“记忆场”。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3期,“动态研究”专栏,责任编辑苏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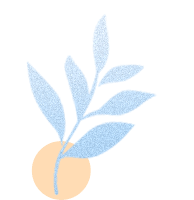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或阅读原文,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