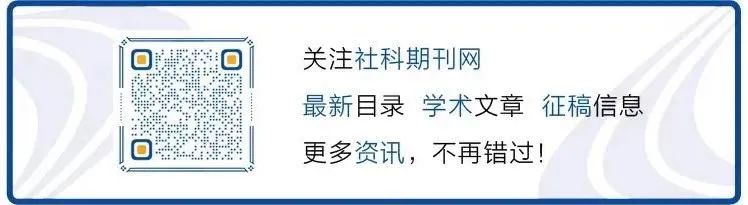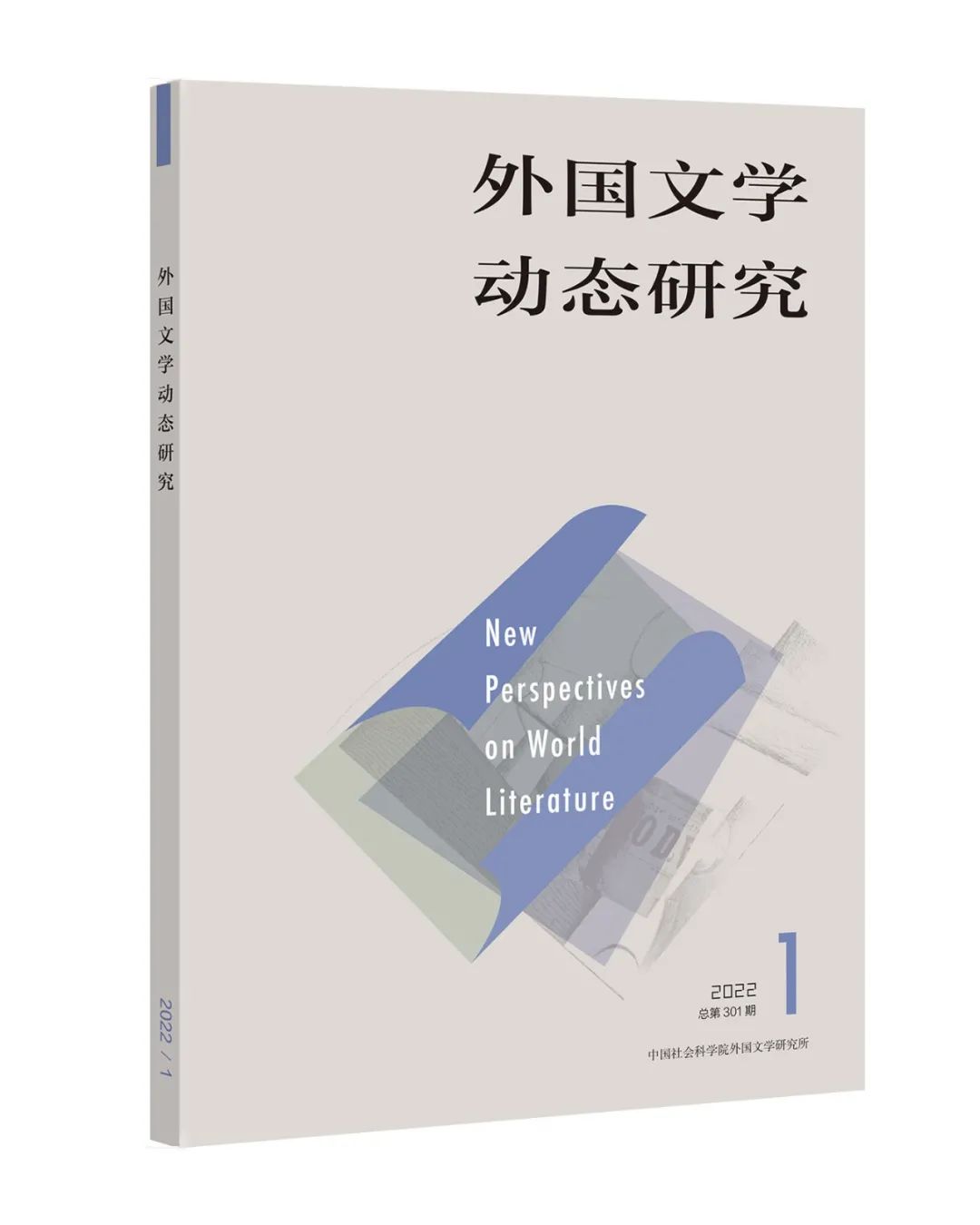作家研究|非洲女性主义写作的困境与出路——从《一封如此长的信》谈起

王天宇 博士,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学与比 较文学。近期出版的专著有À la recherche du style original de Lao She: étude sur les versions françaises de ses œuvres romanesques(Paris: éditions l’Harmattan, 2022)。本文为江苏省 “双创博士”项目(JSSCBS202101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 玛利亚玛·芭的书信体小说《一封如此长的信》以一名塞内加尔中上阶层黑人穆斯林妇女的视角,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社会中的非洲女性经验。因主人公拉玛杜莱面对传统与现代、反殖民与反男权问题的态度复杂暧昧,该小说自出版以来就争议不断。这种争议是非洲女性主义写作不得不面对的困难之一。本文通过解读小说的本土女性意识表达及其遭遇的各种批评,认为非洲女性写作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产物,唯有通过对父权和帝国双重话语霸权的解构,才能发出真正的非洲女性主义之声。
关键词 非洲女性主义 反殖民 反男权 玛利亚玛·芭 《一封如此长的信》
非洲女性主义写作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二次西方女性主义浪潮的双重背景下,许多非洲女性作家有意识地聚焦非洲女性的生存状况,抗议社会不公,以重塑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非洲女性文化。其中,《一封如此长的信》(Une si longue lettre,以下简称《一封信》)是一部无法绕过的作品,其作者是塞内加尔女作家玛利亚玛·芭(Mariama Bâ,1929—1981)。小说以书信体形式展开叙事,全书是主人公拉玛杜莱在丈夫意外去世后写给女性友人阿伊萨杜的一封长信。1979年,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非洲文学场域中,小说因塑造拉玛杜莱和阿伊萨杜这两个能独立言说和行动、“愿意为改善自己生活做出选择”的女性形象获得关注,并于次年在法兰克福书展荣获首届“非洲诺玛文学奖”。但主人公拉玛杜莱面对传统与现代、反殖民与反男权问题的复杂暧昧态度也引起了争议。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小说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而非洲主流评论却又将书中显露的女性主义意识视为殖民者对非洲人的文明教化,认为它过于激进,挑战了非洲传统的社会秩序。芭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具有多层含义:反男权或反殖民,二者是否无法共存?这种困境是芭个人还是她所属阶级面临的难题,抑或是非洲女性作家的共同命运?2021年,《世界报(非洲版)》将《一封信》作为非洲文学经典再次推介,并强调其女性主义表达“始终具有现实观照意义”。这种现实观照的意义来源于何处?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当初的争议与困境如今已不复存在?重读这部小说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以上问题,并为审视非洲女性主义写作及其相关理论话语构建所面对的困境与出路提供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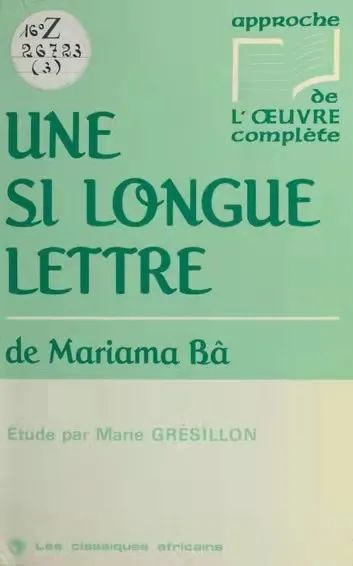
(玛利亚玛·芭与《一封如此长的信》,图片源自Yandex)
《世界报》将《一封信》称为“关于塞内加尔女性境况的故事/宣言书”,诺玛奖的颁奖词则赞美其反映了“社会变迁中的非洲女性生存状态”。若说聚焦非洲女性较为普遍的生存经验与困境是小说一大特点,这一特点正是以婚姻与家庭为切入点描写呈现的。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即拉玛杜莱出身塞内加尔中上阶层,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稳定工作,自称“非洲为数不多的现代女性的先行者”。她与丈夫莫多·法勒自学生时代恋爱结婚,生育了十二个孩子。莫多曾留学法国,后进入工会担任要职,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之后求娶了自己女儿的同学比娜图,抛弃了拉玛杜莱和原本的家庭。
主人公的角色设定带有作者玛利亚玛·芭自己的影子。与拉玛杜莱的成长经历相似,在成为一名活跃于多个妇女协会和组织的社会活动家、作家前,芭曾经历过三次失败的婚姻。她在《一封信》中展现了穆斯林传统习俗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影响:一夫四妻,丈夫无需告知妻子就可以再娶,并可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供养第二个家庭;丈夫死后,妻子需为其守制隐居四个月零十天,还可能像财物一样被他的兄弟“继承”。女性在其中沦为服从和沉默的主体,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独立的女性往往也难以避免婚姻生活的悲剧,莫多的两任妻子拉玛杜莱和比娜图,阿伊萨杜与其丈夫马沃多的第二任妻子小娜布都是这种穆斯林婚姻传统的受害者。马沃多的母亲娜布婶婶和比娜图的母亲则是旧道德的代表,她们维护陈旧的父权制,默认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曾经的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一夫多妻制的卫道者,站在了现代女性权利诉求的对立面。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女性之间相互伤害,并将这种伤害一代代地传递。
尼日利亚女性主义学者、诗人奥昆迪普-莱斯利将这种女性间的互相伤害更多归因于女性自我的消极认知,“女性被自我的消极形象所束缚,这种形象是历经几个世纪父权制和等级制度内化形成的;她们对客观问题的反应常常表现为自我挫败和自我折磨”。比娜图的母亲贪图钱财,强迫女儿嫁给她同学的父亲莫多,对此,比娜图只能像只“被献祭的绵羊”嫁给她口中那个“老男人!大肚子!老头!”,却丝毫不敢违抗母亲的命令。娜布婶婶自豪于自己的贵族出身,认为“女性的首要品格就是顺从”。而她为儿子挑选的第二个老婆,即小娜布,则甘于接受自己姑姑的摆布,似乎她人生的最终目标便只是成为马沃多的妻子。
同样是面对丈夫中年后再娶,阿伊萨杜和拉玛杜莱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阿伊萨杜勇敢地选择独自承担,带着孩子移居美国;拉玛杜莱虽然羡慕阿伊萨杜是“新生活的勇敢先行者”,却顾念与丈夫多年的温情留了下来,“别无选择”地遵从伊斯兰的教义,进入一夫多妻的婚姻。这两种选择反映了后殖民时代塞内加尔妇女面对生活变故时的不同态度。正如拉玛杜莱所意识到的,“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连接了两段不同的历史,一段是被殖民,一段是独立”。社会环境仍在殖民与独立之间拉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在传统和现代中无所适从。可幸的是拉玛杜莱并没有一直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亲身丈量了社会赋予女性的那点微薄的自由度”后,她果断拒绝了莫多的哥哥唐希尔的求婚:“你忘了我有心,有理智,我不是任人把玩的物品。”小说在拒婚的情节后不久便提到了1972年塞内加尔颁布的《家庭法》,该法案明确规定禁止休妻,结婚需要双方签字同意,且丈夫需在签字前确定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像莫多和马沃多那样瞒着妻子另娶的行为自此便是违法的。这是塞内加尔妇女运动的重要成果,象征着当地女性冲破伊斯兰教传统婚姻、家庭模式桎梏的开始,“总算赋予最卑微的女性曾经多少次被忽略的尊严了”。
芭对非洲妇女生存处境的描写由家庭开始,却并不止于家庭。她将家庭与国家直接关联起来,指出私人家庭生活是公共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的家庭汇聚在一起,才构成了国家。而一个国家能否获得成功,也最终取决于每个家庭。”非洲女性的次等地位不仅体现在家庭里,更显现于社会中。“独立将近二十年了!……什么时候文明社会能够不以性别,而是以价值为标准评判呢?”拉玛杜莱对国会议员达乌达的这番质问振聋发聩。20世纪60年代,随着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非洲许多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和民族解放。新的政治机构应运而生,而殖民统治的余威犹在。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国家政党和社会形态在西方与非洲、传统与现代之间来回摇摆,社会内部矛盾愈加凸显。塞内加尔于1960年宣布独立,此后二十年间,由曾任“黑人性”运动领袖的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担任国家总统。为发展经济,他主张与法国保持密切联系,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因此被斥“有违历史”、仍未摆脱“殖民统治的逻辑”,这导致他所提出的以非洲民族独立、黑人文化复兴为主要诉求的“黑人性”(négritude)概念也连带遭到质疑。芭尤其批判这一概念对非洲女性片面化的处理模式,“我们[女性]已不再需要被当作‘非洲母亲’(African Mother)来怀旧、赞颂,这是男性出于焦虑将它与‘母亲非洲’(Mother Africa)相混淆的结果”。换言之,殖民前的非洲被理想化为“母亲非洲”,是黑色人种共同的故乡与精神家园,而非洲女性则被当作“母亲非洲”的具像化,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她们美丽、纯洁,却依旧是无法言语的他者形象。就像是恋爱时,莫多给拉玛杜莱写的那封信所言:“我随身带着你的照片,你就是我的守护女神。”非洲女性鲜活多样的生命,她们为自身以及国家独立与发展所作的一切都被掩盖在这浪漫却扁平化的母亲形象之下。妇女的受教育权、同工同酬仍无法得到保障,国会“一百多议员只有四个女议员”这些都加剧了她们社会“边缘人”的身份。

(桑格尔,图片源自Yandex)
加拿大非裔学者乌艾德拉苟在《非洲女性写作》中指出:“分析非洲妇女写作现状问题,不能不考虑其产生的背景。这一背景包含着一个要素,那就是沉默。它划定了一个空间,那就是边缘性。经过长期沉默后形成的妇女话语带有被排斥的痕迹,与男性话语霸权相对。”写作在非洲长期被认为是男性专属的活动领域,女性写作在读者、评论、研究中被遗忘是“司空见惯的”。芭也曾因女性写作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而感到沮丧:“在所有文化中,提出主张和抗议的女性会遭到贬低。如果说轻易消散的言语使得女性边缘化,那人们将怎样评价将自己思想永久记录的女性?这解释了女性作家的迟疑。她们在非洲文学中的存在感几乎为零。但她们不得不表达和写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塞内加尔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芭主张以写作介入社会,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为非洲女性发声,帮助她们找回主体地位和言说权力。其目的并不在于制造男女性别对立,而是探寻未来非洲发展的正确道路。她这种立场选择是自身性别(女性)、种族(黑人)、阶级(非洲中上阶层)、宗教(伊斯兰教)及所处社会历史语境(后殖民)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正如印度裔女性主义学者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所强调的,“在姐妹情谊之外的仍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非洲女性所遭遇的压迫不仅来自性别歧视,还须考虑种族压迫、阶级斗争、帝国殖民等各种要素的作用。《一封信》中,芭对后殖民时代塞内加尔社会状况的思考正是她描绘非洲女性生存境况的画布和底色。

(莫汉蒂,图片源自Yandex)
一方面,殖民统治造成的种族歧视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同化”政策让黑人及其文化遭到贬斥,芭为此痛心不已,渴望寻求解放之路。拉玛杜莱的儿子马沃多·法勒在文科方面拥有非凡的天才,却因老师无法忍受哲学课第一名是黑人,作业总是被莫名扣分。拉玛杜莱一面劝说儿子妥协,一面又渴望在年轻一代中看到“清亮的眼神、准备还击的拳头”。另一个儿子在街上踢球被撞流血,她“一边擦洗地板,一边思考人的身份问题”:既然黑人和白人均拥有同样的鲜血、器官与病痛,“所有人彼此联系”,“为什么因为虚无的理由……要发动肮脏的战争来自相残杀呢?”基于人类共通点对种族平等展开思考,是当时非洲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思维倾向。桑戈尔、塞泽尔等人也曾试图从《人权宣言》出发,通过强调黑人与普世人性的联系来消除人们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抨击殖民制度。芭还反思了“同化”政策对黑人思想、风俗的影响。“同化”政策是法国巩固和发展殖民地统治的一项重要手段,拿破仑三世宣称这是为了让被殖民者“顺从于我们的法律,习惯于我们的统治,臣服于我们的优越性”。但显然,这只是殖民者一厢情愿的美梦。比如,被打上“进步”标签的西方的裤子、帽子和烟斗就真的能让非洲人臣服于宗主国的优越性么?芭借拉玛杜莱之口,从裤子这一实物出发,对“同化”政策的不合理进行了批判。西方的裤装本身并不适合曲线突出的非洲女性,“给躯体带来的并非解放,而是包裹与束缚”,却因殖民文化影响而在西非女性眼中成了“时髦”的象征。芭在小说中给出了她的预测,年轻一代最终只会觉得“自己的穿着是多么可笑”。
另一方面,芭又肯定“同化”政策的确具有一定的文化教养作用。小说中,作者专设章节回顾了女主角在法属西非学校求学的时光。那段时光见证了拉玛杜莱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是真正的姐妹,注定投身于解放事业”;更见证了她摆脱传统、迷信和风俗的桎梏,拥抱平等思想的开始——“学会欣赏异域文化之美,同时也不会否定自己的文化”。拉玛杜莱眼中“彩虹般的”学校为她开启了认识现代西方的通道,将她培育为横跨西方与黑非洲、传统与现代的“新一代非洲女性”。
学校拓宽了拉玛杜莱的视野,也造就了她复杂暧昧的价值取向。小说中作者对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直接评判并不常见,更多是借拉玛杜莱之口记录前殖民地人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踌躇不定,以表达自己的态度。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非洲传统手工业的凋敝,拉玛杜莱反问:“难道我们对此可以毫无担忧,反而额手称庆么?”她的“三剑客”女儿追求时尚,偷偷学会了抽烟,也令其疑惑:“现代化是否就一定伴随着道德的败坏?”个人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拉玛杜莱的彷徨也是后殖民时代众多非洲国家现状的写照。新非洲究竟该呈现怎样的面貌?个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该如何选择?拉玛杜莱的观念和做法无疑是出于现实考虑:非此即彼的选择被暂时搁置,她强调“在混乱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更具建设性”。因此,即便莫多背弃了他们的婚姻与家庭,拉玛杜莱还是能看到他的优点,肯定了他作为工会领导立足眼下、为工人谋求实际好处的务实品格。“何必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实现可能实现的就已经可以视为胜利”是莫多的口号,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拉玛杜莱为何没有像阿伊萨杜一样从旧环境出走,又为何在实现个人经济与思想独立后还会无奈地说“生存的欲望扼杀了生存的尊严”。
不得不承认,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长久失语、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打破沉默、发出声音往往被视为一种越界。这造成她们在写作时带有“自我审查”的倾向,她们比男性作家顾虑更多,表现出一种折衷主义。《一封信》中,不仅是拉玛杜莱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常常模棱两可,小说书信体的选用也是穆斯林传统与法语学校双重影响的结果。作为芭的代言人,拉玛杜莱在小说开始就告诉读者,私密的交流是非洲女性的传统:“我们的祖母是邻居,她们的家之间只隔着一块‘塔帕德’,她们每天都要聊天、交流信息。”而法语学校女生之间信件交流的习惯不仅让她们建立了维系终身的友谊,更培养了她们言说与书写的习惯。小说以女性间的书信展开叙述,语言也偏向口语化,作者借这种貌似私密的女性交流习惯作为掩护,才得以“合法地”讨论塞内加尔诸多亟待治愈的社会弊病。
这种女性主义表达在日后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尼日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家内梅卡认为,对边缘化的恐惧影响了《一封信》中的人物设置,小说中的激进女性角色被弱化处理令人惋惜。她对此发出疑问:“为什么《一封信》中的核心人物是拉玛杜莱而不是阿伊萨杜?”随即她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些激进的女性角色被弱化是女作家不得不协商妥协的结果。她们既想要表现文化上的团结,又必须符合女性神话。其次,存于在女作家意识边缘的读者或批评家(在这个词的明显指向男性)限制和制约了她们的创作。”然而,即便是这种被弱化的女性话语,也在出版后甚至在2011年还被批判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比如费米·奥乔-艾德就对作家本人及其在《一封信》中塑造的两个主要女性形象持非常负面的评价,认为芭所主张的女性主义不符合非洲现实,是一种波伏娃式的女性主义,对于非洲社会与文化、婚姻与家庭来说都是一种危险。
类似批评凸显了芭那一代非洲女性作家“共同的无奈”,也即非洲女性主义创作在早期不得不面对的双重困境。首先,女性发声本身就是对非洲男性话语霸权的挑战,而它对非洲传统社会的基础,即父权制的批判,更被视作一种颠覆行为。其次,西方女性主义被引入非洲,在女性思想解放上固然有其先进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西方价值观念的横向移植,它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削弱、分化了非洲的反殖民力量。再者,“女性主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西方外来概念,受它启蒙的非洲女性主义写作能否真正反映非洲女性的生存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又该如何处理反父权和反殖民、本土文化与西方影响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决定了非洲女性主义话语构建的路径及其面貌。
事实上,无论是显是隐,“反殖民”都是非洲女性主义写作无法回避的主题,而当地宗教文化传统则是非洲女性存在和表达的基础。1947年,尚在学校的芭就直言:“我的理性变白,我的脑袋还是黑的。我的血液一如既往的纯洁……血管虽已受教化,我的血液还保有自己的特质,随黑色的达姆鼓声反抗跳动。”西方思想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作为芭的代言人,拉玛杜莱在想象新欧洲的面孔时更直接否定了“固守西方意识形态”的做法。芭的女性主义之声不排斥自身植根于塞内加尔的宗教文化身份。小说开头,拉玛杜莱就直言自己“从小受严苛的宗教教育”,对晨昏礼、为逝者做遗产清算的米拉斯以及守制等伊斯兰教习俗均严格遵守。尽管深受一夫多妻制所苦,她却坦诚:“虽然我理解你[阿伊萨杜]的选择,也尊重所有选择自由的女性,但我从未想过在婚姻之外寻找幸福。”因而,拉玛杜莱的独立之路与阿伊萨杜不同,她没有离婚或抛弃故土,她所追求的是一种与自身及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女性权益保障。
《一封信》中,反父权被置于反殖民的大背景下,主人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移是对后殖民时代非洲及非洲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在路上不断摸索与展开实践。小说尾声,拉玛杜莱在年轻一代身上看到了希望。对于儿子在哲学课上受到的出于种族歧视的不公对待,校长选择支持学生而非老师。大女儿达芭否认婚姻是一条锁链,认为它应该是“双方彼此融入的生命规划”,她的想法也得到了丈夫阿布杜的尊重。在现代家庭关系中,妻子不再是丈夫的附属品或仆人,而是作为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被肯定。在社会生活中,以达芭为代表的新时代女性面对“决策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将由男性把持”的现状也并不气馁,她们选择绕过无谓的政党争执,借助协会举办社会活动,尽力在各方面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年轻一代在传统与现代的割裂中更显理智,也更具有主动选择的魄力,极具战斗精神。在现代与传统的辩证思考中,拉玛杜莱的角色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女儿小阿伊萨杜违背《古兰经》教义未婚先孕,拉玛杜莱选择放下自己中上层出身的骄傲,抛却对“社会禁忌的顾虑”,以女儿的生命与幸福为先,平静地接受了一个新家庭的诞生。她也由此认识到性教育的重要。如果说拉玛杜莱对“三剑客”女儿进行性教育这一行为本身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传统穆斯林社会具有开创性意义,她对性的理解仍是循着《古兰经》的教义:性是崇高的,“一个放荡的女人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这也印证了芭的女性主义之声并不完全背弃当地宗教文化,而是一种经过本土化的女性主义表达。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女性主义在非洲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不仅是非洲男性,大多数女性作家也都在创作中刻意回避这一主题。塞内加尔女作家阿米娜塔·索·法勒(Aminata Sow Fall)曾多次反对将她的作品纳入女性主义写作的范畴,她表示:“我[的创作]不属于女性主义题材。我不是作为女性在写作,而是作为人类。”

(阿米娜塔·索·法勒,图片源自Yandex)
南非作家贝西·黑德在其遗作《孤独的女人》中也提出,在她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里,女性主义没有必要。这首先是因为,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均面临诸多严峻问题,民族独立、种族和阶级斗争等都被置于改善女性生存状况之前。其次,出身精英阶层,接受过西方教育,这是早期非洲女性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也是评论界对于非洲女性主义诟病最多的一点。批评者认为这是非洲一小撮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女性主义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和贫民窟的穷困女性所无法参与的奢侈品。但反过来,没有女性主义者的发声,我们难道就可以认为在田园牧歌般性别平衡的传统非洲,女性未曾遭受过任何不公与压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一些历史资料显示早在古代非洲就已出现类似当代女性主义的声音(在某些民族,女性还曾作为统治者、战士)。如果说殖民时代的产物是文化混杂,诞生于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女性主义写作本身即是一种文化融合产物。这不仅是由于其书写对象的文化构成很复杂,也源于表达者自带跨文化视角。
作为非洲最早的女性法语作家之一,相比同时代无法受教育的大部分非洲女性,芭无疑是幸运的。西方教育赋予她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和独立分析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她以欧洲语言书写与表达的能力,这成为她之于原生社会环境的独特性。芭对用殖民者语言写作可能造成的问题早有预判。她指出:“作者使用的[欧洲]语言仅被一小部分人理解和言说。他的政治任务极有可能失败,因为他的信息覆盖面有限,且会被并非他所面向的群体听到。”限于欧洲语言在当地的普及度,只有极少部分殖民地人民能阅读和理解小说,但域外读者群体却因此扩大了,作者的声音被传达到更远的地方。芭对小说不确定的读者群体不仅有所感知,并且在写作中做出了回应。这主要体现在主人公不确定的对话者上。虽然小说伊始就言明,这是写给阿伊萨杜的一封长信,但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拉玛杜莱有时像是喃喃自语,有时又像是对着丈夫莫多在说话,有时甚至像是在与信外的某个人倾诉。而开头作者不厌其烦地向一位与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女性解释穆斯林殡葬习俗,也从侧面印证了芭对这部小说潜在的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读者群有一定的构想。
诚然,由于作者社会文化身份的限制,《一封信》所展现的实为一种特殊的非洲女性之声。主人公拉玛杜莱出身塞内加尔中上阶层,经济独立,享有许多普通非洲女性无法企及的特权。但小说描绘的非洲妇女生存经验及其困境不可否认有其普遍性,芭的表达困境也并非个例,而是非洲女性主义创作及批评话语构建从早期直到今日必须面对的难题。它对应着斯皮瓦克笔下作为“属下的属下”的困境:“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非洲女性受到的压迫具有两重性。一是非洲女性相对非洲男性多了一层父权制的压迫。受男权至上的传统习俗压迫,非洲女性很少有机会为自我发声。《一封信》中,拉玛杜莱也曾长期失声,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沉默,三十年的侮辱”后,这一次她拒绝被亡夫兄弟“继承”,抵抗了旧婚姻制度的无理裹挟。二是非洲女性相对西方白人女性多了殖民主义的压迫。莫汉蒂认为西方白人女性主义以自我为中心,通过话语“生产/再现出一个复合的、特殊的‘第三世界女性’”。“第三世界女性”由此被当作一个同质的群体、一块铁板,被无差别地打上落后、守旧的标签,与文明、进步的“第一世界女性”形成二元对立。这实质上是西方女性主义相对第三世界女性的殖民话语霸权。为解构上述双重话语霸权的压迫,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指出要关注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考察被压迫女性的生活经验,并强调言说的重要性。这与以芭为代表的非洲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异曲同工。《一封信》中,芭从未将反殖民和反父权视作无法并存的选项,而是在反殖民的大背景下展开反父权的思考。通过大女儿达芭这一理想女性形象的塑造,她点明非洲女性作家唯有同时反抗这一双重压迫,才有可能走出困境,构建真正的非洲女性主义之声。

(斯皮瓦克,图片源自必应)
芭呈现经过弱化的女性主义,既是无奈之举,亦是有意识的选择。非洲女性作家争取自我表达的权利,反对歧视和霸权,其目的并非贬损男性话语。恰恰相反,一如拉玛杜莱的声明:“我仍然坚信男女间的互补不仅必要,而且不可避免。”男女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是非洲女性主义的最终诉求,也是穆斯林最理想的婚姻、家庭模式。芭的女性主义之声受西方启蒙,却始终立足本土语境,是一种跨文化的产物,其最终和唯一的落脚点都在“生命”这一宏大的议题上。小说最后一章“归来”写道:“所有人的命运在宗教与法制的滥用下都如出一辙”,“我的思考集中在生命问题上……通过了解全球时事扩大视野”。在此,非洲女性主义写作被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重塑社会变革中的非洲女性经验,反抗社会不公,修正被话语霸权所扭曲的非洲女性形象,帮助非洲女性重新定义自我;另一方面倡导多元与差异,谋求人类文化共存与共生。
非洲女性写作具有显著的跨文化性,它同时指向“非洲”“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三个重要议题。西方女性主义作为非洲一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女性的启蒙思想,给她们带来女性意识觉醒的同时,也造成了她们的反抗困境——在后殖民时代非洲文化复兴的诉求下,她们的反男权话语被视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谋。玛丽亚玛·芭的本土化女性主义表达是后殖民时代、女性主义与非洲文化传统直接对话的结果。因其社会文化身份和所处时代、地理的局限,芭的创作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但就其世界影响来看,它代表一度集体失语的非洲女性发声,拓展了非洲文学的创作外延,丰富了世界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涵。同时,借由不确定的读者群体构建,非洲女性的生存状况、情感体验及其对社会机制的批判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研究非洲女性主义文学,了解非洲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话语构建的困境与出路,或可成为探究当下全球文化杂糅现象乃至人类命运发展颇有意义的切入点。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5期,“作家研究”专栏,责任编辑王涛,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
订阅2023年刊物限时九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