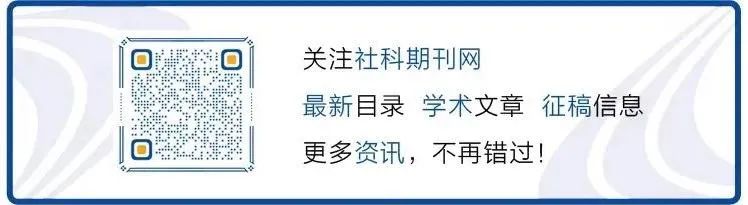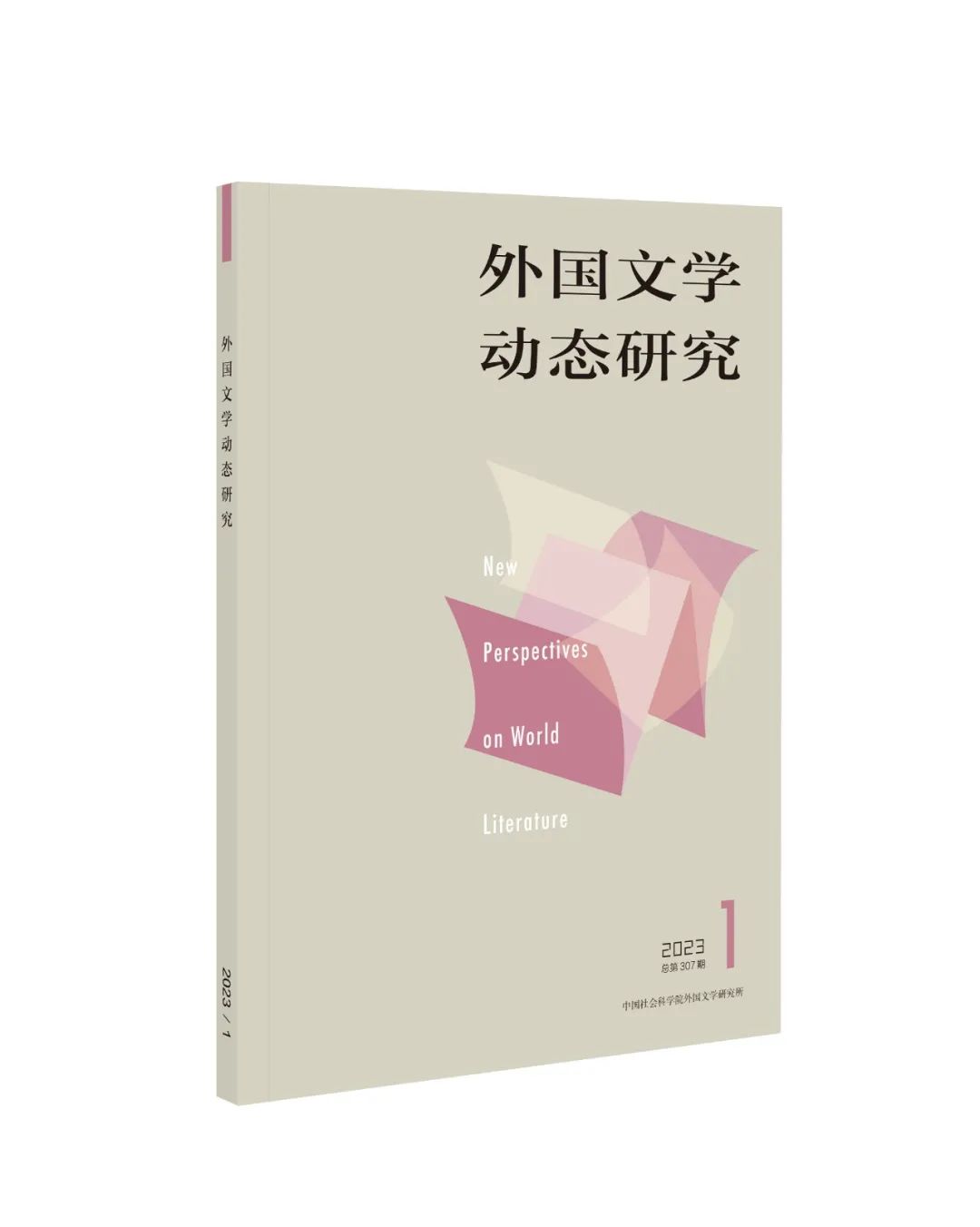专题 | 如何讲述爱尔兰故事?——析芬坦·奥图尔《我们不了解自己:1958年以来的爱尔兰个人历史》的叙事性非虚构写作

李 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爱尔兰当代文学和文化翻译。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让我们看见这棵树”:爱尔兰抹大拉洗衣房的文化再现与假性记忆的可能性》(载《外国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内容提要 爱尔兰著名学者、《爱尔兰时报》专栏作家芬坦·奥图尔的非虚构历史述作《我们不了解自己:1958年以来的爱尔兰个人历史》以史实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将个人经验和历史意识相融合,描绘了现代爱尔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迁,以生动有趣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故事,达到小说的美学高度。在这一主题突出、情感丰沛的民族故事中,奥图尔着重对爱尔兰的民族问题做了深刻剖析,不论是分析民众对待宗教权威的逃避策略——“不知道的知道”,还是分析北爱冲突背后的天主教殉道情结和男性气质,奥图尔都能切中要害,他的文字发人深省又不乏对民族和人民的爱与理解。诚如詹姆斯·伍德所言,继乔伊斯的小说之后,奥图尔的这部非虚构作品再次试图锻造民族的良心。
关键词 芬坦·奥图尔 叙事性非虚构写作 爱尔兰悖论 不知道的知道 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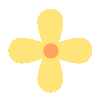
在谈到文学作品如何书写历史时,人们经常引用德国18世纪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的名言:“小说因历史的缺点而崛起。”小说被视作对历史的补充和纠正,因为历史书写无法捕捉私人经验和想法,而小说则能弥补这一缺憾。然而,著有《小说机杼》的美国学者詹姆斯·伍德却为一部历史叙事作品——《我们不了解自己:1958年以来的爱尔兰个人历史》(We Don’t Know Ourselves: A Personal History of Ireland Since 1958,2021)——撰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书评。伍德认为此作虽是非虚构写作,读起来却像“一部伟大的悲喜剧式的爱尔兰小说(a great tragicomic Irish novel)”。书评人安娜·芒道也认为此书有小说的资质,爱尔兰作家科伦姆·麦坎恩则称赞其叙事架构“与小说一样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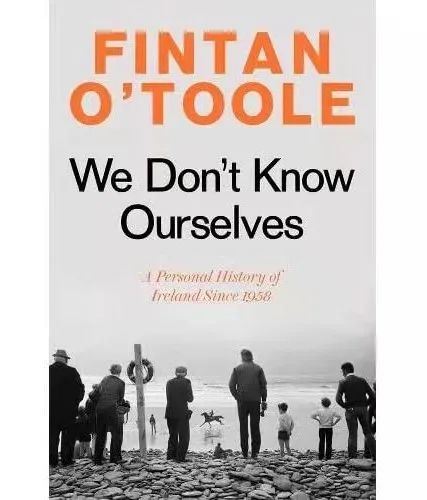

(《我们不了解自己:1958年以来的爱尔兰个人历史》和芬坦·奥图尔,图片源自Yandex)
此书的作者是爱尔兰著名学者、文评家芬坦·奥图尔(Fintan O’Toole,1958—),奥图尔是新闻记者出身,但著述颇丰,包括文学评论(尤其是剧评)、时事分析、历史述评等,长期为《爱尔兰时报》《纽约书评》等报刊杂志撰稿,已出版二十多部著作,获新闻与欧洲媒体奖、奥威尔新闻奖等多个奖项,2020年入选爱尔兰皇家学院院士。2021年出版的《我们不了解自己》当属他三十多年写作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六百二十四页,分为四十三章,按时间顺序排列,展示从作者出生的1958年至2018年这六十年间爱尔兰社会的巨大变迁,其叙事形式十分驳杂,混合了新闻报道、历史叙述、社论、回忆录、文学评论、影视评论,甚至还夹杂了名人八卦与丑闻。此书出版后热评如潮,获2021年爱尔兰图书奖非虚构写作奖,各大主流报刊如《纽约时报》《卫报》《泰晤士文学增刊》也都邀请作家、学者撰文推荐。爱尔兰作家讲故事的传统早已为人所知,但该作是在史实和统计数据基础上,将个人经验与民族历史融合,讲述了一个关于民族国家的动人故事,堪称叙事性非虚构写作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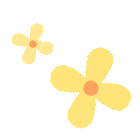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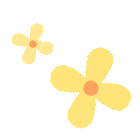
一、 奥图尔笔下的叙事性非虚构写作:讲述爱尔兰故事
非虚构写作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很快风靡世界,成为长盛不衰的写作类别,但其作为一种文类也一直不断被重新定义和再阐释,衍生出各种次类别和名目,如创意非虚构写作、事实文学、非虚构小说、文学新闻主义、叙事性非虚构写作等,其中的叙事性非虚构写作(narrative nonfiction writing)得到了更多关注。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罗伯特·瓦尔在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the Nei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资助下讲授叙事性非虚构写作多年,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混杂的形式,在真实人物、地点和事件基础上,运用小说、戏剧的技法建构中心叙事、搭建场景、描绘多面向的人物,“以动人的声音讲述读者愿意听的故事”。为突出叙事的特点,瓦尔引用了纳博科夫区分叙事和情节的著名评论,即情节是讲述国王死了,接着王后也死了,而叙事则是讲述国王死了,接着王后伤心而死,瓦尔总结道:“叙事性非虚构将已经发生的事件连接起来,并赋予其意义和情感。”杰克·哈特在《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中突出了此类写作所借助的文学表现手法,如故事结构、视角、人物、场景、动作、对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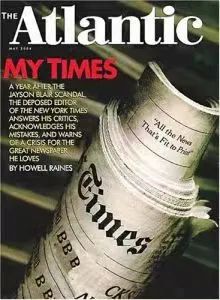
(《大西洋月刊》,图片源自Yandex)
《我们不了解自己》虽包罗万象、枝繁叶茂,但主线与副线相辅相成,主题突出,将现代爱尔兰历史整合成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故事,划出一条哈特在《指南》中强调的叙事弧线(narrative arc),同时也标记和探讨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意义,如爱尔兰加入欧盟的努力、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访问、长达三十多年(60年代至90年代)的北爱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等。此外,奥图尔还将个人经验融入这一关于民族历史的非虚构写作中。这位父亲是公交车售票员、母亲是清洁工的男孩在经受住教会学校的考验后考上大学,成为记者、作家,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跃升。他在该书结尾的致谢词中写道:“我的人生太枯燥乏味,不值得写回忆录,而现代爱尔兰的历史却从不枯燥乏味。但我的人生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跨越并映照了这段时期的变化。”的确,全书就像一部爱尔兰版本的《阿甘正传》,其中男主角和家人总是奇异地出现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或与重要人物有交集。就谋篇布局来说,四十三个章节以时间顺序排列,每章都突出一个话题,通常从奥图尔自己、他的家人和他人的故事经历讲起,再延伸至更大的历史叙事和社会图景。这种个人经验与宏观历史图景的融合,反映出作者强烈的见证与反思意识,正如洪治纲所言:“非虚构写作的最大特点,无疑就是创作主体带着明确的主观意图和表达策略展开叙事行动。”
在《我们不了解自己》中,现代爱尔兰的故事从奥图尔出生的1958年那年开始,源于一个悖论:50年代的爱尔兰政治、宗教保守,经济落后,孤立无援,年轻人不断移民离开。为挽留流失的人口,必须提振经济,而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拥抱全球化,吸引外资,创造工作机会,促进城市化进程等。当时以德·瓦勒拉(De Valera)为首的革命精英组成的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捍卫新兴民族国家以天主教立国的保守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此,奥图尔评价道:“这是1958年的大赌博:在经济上一切都将改变,而文化上一切将保持不变。”然而在六十年的巨变中,爱尔兰势不可挡地走入现代化,在经济上创造了凯尔特之虎的奇迹,在文化上变得更加多元、自由,在此过程中,原本至高无上的天主教会也轰然倒塌。当然,奥图尔在书中绝不是要讲述一个简单的成功故事,而是更多着墨于其中的痛苦、悲伤和纠结。正如他所言:
“爱尔兰”,作为一种观念,几乎是令人窒息般地连贯和固定:天主教的、民族主义的、乡村的。这是这个地方的柏拉图理式。但是作为人们生活经验的爱尔兰却是不连贯、不固定的。第一个爱尔兰被限制、被保护,以隔绝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第二个爱尔兰则无拘无束,不断变化,大步走向外部世界。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主教与民族主义融合的霸权并没有被削弱,教会控制教育、娱乐、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经济发展与社会保守成为平行宇宙,互不影响。直到90年代,教会各式丑闻曝光,以爱尔兰共和党(Fianna Fáil)党魁查尔斯·豪伊(Charles Haughey)为代表的政客贪腐行为败露,伤害到本土经济,爱尔兰人民才开始直面曾经不敢面对的现实,鼓起勇气摈弃第一个柏拉图理式的爱尔兰,承认多元、复杂和变化。

(爱尔兰总理瓦勒拉向大主教下跪,图片源自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s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一个故事总有恶棍和主角,这个关于爱尔兰的故事也不例外。爱尔兰著名作家约翰·班维尔在书评中提到,书中最大的恶棍乃是代表天主教会权力的都柏林大主教约翰·查尔斯·麦奎德(John Charles McQuaid)。麦奎德自1940年起统治爱尔兰长达三十多年,权力通天,连总理瓦勒拉也臣服于他。奥图尔对这位主教的讲述既有史料支撑,更有文学性的生动描绘。例如,这位大主教在其宅邸装有一个望远镜,用以俯瞰全城,似乎象征他如上帝般无所不知。最能体现主教精神统治的标志性事件也发生在奥图尔出生的1958年。爱尔兰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国际都柏林戏剧节被主办方取消,仅仅因为麦奎德大主教在私下场合对上演乔伊斯、奥凯西的作品表示不悦。此事还殃及另一位重量级的剧作家贝克特,贝克特当时正筹备其作品《终局》在都柏林派克剧院的首演,还计划携这部剧和另一部哑剧《无言的行动》参加戏剧节。得知戏剧节被取消后,贝克特为表示抗议,宣布禁止自己所有的作品在爱尔兰上演,并义愤填膺地给派克剧院的总监艾伦·辛普森写信:“只要爱尔兰还盛行这种情况,我就不愿意我的作品在这里上演,不管是不是戏剧节。如果没有人抗议,那么他们会永远得逞下去。这是我能做的最大的抗议。”
至于故事的主要角色,除了爱尔兰本身,还有美国。奥图尔在书中清晰地展示了爱尔兰在各方面的变化如何借力甚至依赖美国。首先是经济发展仰赖美国投资,他引用了爱尔兰美国商会的数据:自1990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间,美国公司在爱尔兰的投资是对中国投资的五倍。这样规模的投资当然令这一弹丸小国经济腾飞,造就了90年代凯尔特之虎的奇迹。其二,伴随美国投资而来的美国大众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漫画、电视节目、西部片,在爱尔兰盛行数十年,甚至连美国文化夹带的自由开放(主要是关于性的再现)似乎都可以被适度包容。其三,自60年代开始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激励了爱尔兰社会各方的民权运动。1990年当选为爱尔兰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的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也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更戏剧性的是,就连天主教会于90年代爆发的丑闻也与美国有关。1992年,《爱尔兰时报》报道一条新闻,当时“德高望重”的戈尔韦市主教埃蒙·凯西(Eamon Casey)竟然长期与一名美国女人(爱尔兰移民)有染,还育有十七岁的私生子,并多次挪用教区公款为这段关系买单。凯西丑闻成为爱尔兰天主教会衰落的转折点,教会的虚伪也终于得到暴露。

(玛丽·罗宾逊,图片源自Yandex)
美国的影响无处不在,奥图尔充满讽刺地总结了爱尔兰作为后殖民国家的尴尬艰难处境:
将爱尔兰经济向英国开放,让英国老板可以雇佣爱尔兰工人,这等于是承认失败。而在爱尔兰小城镇引入美国公司则意味着拥抱令人激动的现代性,而且还同时与伟大的美国爱尔兰离散人群重新连接,这其中充满希望——从旅游收入到为结束南北爱分裂民族事业的捐款。在这一希望之中,也有对世界另一种想象地域的憧憬。爱尔兰不想与土耳其、希腊和冰岛这些穷国为伍,也不想成为附庸于英镑地带的伊拉克和缅甸。它想跻身西欧国家,但人家对它根本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它的位置在哪里?考虑了所有的地域后,答案就是波多黎各。
此处奥图尔是承继爱尔兰作家弗兰恩·奥布莱恩(Flann O’Brien)于1958年在《爱尔兰时报》专栏文章中给出的饱含反讽意味的建议:“(爱尔兰)的目标应该是获得美国第四十九个联邦州的资格。(艾森豪威尔总统会发现我们的高尔夫球场是一流的。)初级阶段是跟阿拉斯加、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一样,成为美国的属地。”由此可见,从斯威夫特到奥布莱恩、再到奥图尔,爱尔兰幽默讽刺的文脉从来没有断过。

(鲍比桑兹在贝尔法斯特城市涂鸦之一,图片由本文作者拍摄)
当然,讽刺挖苦的背后是作者清醒的认知。在书中,奥图尔几乎花了同样篇幅谈论爱尔兰美国梦(American Dream)的另一面——美国噩梦(American Nightmare)。例如,在经济上,爱尔兰的发展过度依赖美国高新技术跨国公司投资,这些公司利用爱尔兰低工资、低税收和地理位置优势,顺利打入西欧市场,同时也使得爱尔兰的经济缺乏韧性,面对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此外,80年代都柏林的“海洛因流行病”也是美国噩梦的复制,吸毒成瘾成为爱尔兰年轻一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再如,自60年代开始的北爱问题受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和平解决派系冲突问题,反而走向暴力和动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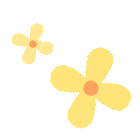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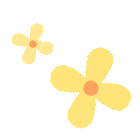
二、奥图尔笔下的爱尔兰问题:“不知道的知道”与民族执念
西奥多·切尼在《写作创意非虚构作品》中指出,创意非虚构作品运用事实讲述一个故事,但也使用许多小说的技巧来使故事生动丰满,使读者产生情感共鸣,这需要“讲故事的技巧和一个有良心的报道者的研究能力”,因此,创意非虚构作家不但引述权威机构来理解和报道事实,还必须超越事实,发现其中的意义,并以有趣、唤发情感和富有教益的方式呈现意义。哈特也认为,“正是意义、情感和启迪,构成了主题”,“在完整充实的故事中,动作线的延伸——在小说中我们称作‘情节’——是为主题服务的。主题会让读者感觉到,花时间来阅读很值得”。
现代爱尔兰的故事是从一个悖论开始的,这个故事的主题也充满矛盾和悖论,奥图尔在书中将其总结为“不知道的知道”(unknown known),并以诸多案例进行说明。“不知道的知道”是爱尔兰民众面对教会和政府的问题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明哲保身,或对教会严苛的道德规范阳奉阴违。正如班维尔在书评中总结的:“爱尔兰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知道怎么去不知道。”毫无疑问,在此过程中必然出现虚伪、含混、自相矛盾和悖论。事实上,这些都是奥图尔书中的高频词汇。奥图尔将这种“不知道的知道”称为高度复杂的文化,并援引爱尔兰戏剧大师布莱恩·弗里尔(Brian Friel)的名作《翻译》(Translations,1979)中的场景:19世纪30年代,一个讲爱尔兰语的村庄面临英国的政治、文化、军事入侵,六十多岁的乡村教书先生休(Hugh)同意教女孩麦尔拉(Máire)英语,他说:“我会教给你已有的词汇和语法,但是,这些会帮助你解释其中的隐秘之处(privacies)吗?”

(布莱恩·弗里尔,图片源自Yandex)
这里面的“隐秘之处”引得好,毕竟大部分“不知道的知道”是围绕性这一主题的。众所周知,天主教关于性的清规戒律很多,除了对神父禁欲的规定,也对教徒的性活动严加规范,如禁止使用避孕手段、禁止堕胎等。1963年,爱尔兰国内出现一种神秘的进口药丸,被称为“调经药”,看似用于调节女性不正常的经期,实际是避孕药。该药在60年代的爱尔兰女性群体中的使用率为5%,对其真正的用途,医生患者都心知肚明,只是不说破而已。奥图尔将这种阳奉阴违的做法称为“躲避康尼”(Connie dodging),康尼的全名为科尔内利乌斯·鲁西(Cornelius Lucey),是科克市的主教,也是麦奎德大主教的朋友。他在其控制的教区推行严格的四旬期斋戒,即在复活节之前的四十天内每天只能吃一顿正餐、两次斋点,斋点类似喝茶时搭配的饼干。科克城中有位咖啡店的老板将这种小饼干放大数倍,做成巨型大饼,随即所有烘焙店都开始效仿,以帮助市民在斋戒时蒙混过关。于是,这种巨饼被称为“康尼躲避饼”(Connie Dodgers),在这样的策略中,人们似乎并没有违抗上帝的律法,只是躲闪了。
1968年英国堕胎合法化后,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女性前往英国终止妊娠。奥图尔给出的统计数字是,自1970年至2019年爱尔兰全民公投堕胎合法之间,至少有二十五万名爱尔兰女性越过海峡寻求帮助。然而,在这个国家的公共领域,这一数字是不存在的。奥图尔评论道:
这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做了天主教爱尔兰一直想做的事——建构两个平行宇宙、两种真相。人们可以有理有据地说,爱尔兰没有堕胎行为,当然不像不敬上帝的英格兰。但爱尔兰妇女们,只要她们能有钱去英国堕胎,就会非常感谢英格兰对上帝的不敬。不问,不说,不要使两个世界互相碰触,那么这个体系就可以长期维持下去。
令人深思的是,这种遍布生活各个方面的“不知道的知道”也有其阴暗面,例如,虽然民众听说或目睹天主教机构对女性、儿童的囚禁、虐待或某一政客、主教的腐败、不轨行为,却假装无知,听之任之。对此虚伪行径揭露得很透彻的是彼得·马伦于2002年导演的电影《抹大拉姐妹》(The Magdalene Sisters),影片中一位被神父性侵的抹大拉女孩在宗教节日集会上大声叫喊,试图揭露神父的不轨行为,但现场所有的民众都充耳不闻、无动于衷。
相较之下,奥图尔更能理解和共情民众的虚伪,他认为,这“关乎生存,是人们为了活下去而做的事情”:
这是一种活着的方式——通过沉默、逃避、富有创意的含混——如果社会在变化,而权威结构因为太根深蒂固而似乎无法改变,绝大多数的人民不会直接挑战权威,他们会绕行,会见风使舵,暗暗嘲讽,以避免公众敌意和羞辱。这个时代的爱尔兰人民——甚至也许是在此之前,在漫长的殖民时期——是机敏巧妙的虚伪大师。
这种对权威无力抵抗、但又心有不甘的心理也印证了霍米·巴巴提出的含混(ambivalence)概念。这一概念很好地描述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复杂关系,被殖民者从来不是要么“顺从”,要么“反抗”,而是在中间地带不断摇摆,其行为也徘徊在模拟(mimicry)和嘲笑(mockery)之间。很显然,奥图尔看出,经历过殖民统治的爱尔兰人民对虚以委蛇、闪挪腾移早已驾轻就熟,从英国殖民者到国内的天主教会,他们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应对的权威而已。
除去呈现“不知道的知道”这一主题,奥图尔还精准地扣住了历史叙事的另一个主题:爱尔兰人对民族的执念和浪漫幻想。在奥图尔看来,北爱冲突造成的痛苦来自对虚构民族身份的执念。1969年,原本致力于爱尔兰统一大业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内部产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以军官为主)开始协助其政党——新芬党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伦敦议会取得更多席位,以和平实现其政治诉求,不希望北爱街头沦为派系冲突的血腥之地;而另一部分的临时派(The Provisionals,简称为the Provos)则没有上述顾虑,反而诉诸更暴力的行为。
奥图尔借助文学批评和心理分析对临时派的暴力行径做了非常精到的解读。他认为,临时派承袭了1916年复活节起义所包含的天主教献祭和殉道情结,这一情结来自天主教基督死亡与复活的意象,但又与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诉求融合在一起。除去惯常的暗杀、偷袭和汽车炸弹,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问题时期最受关注的行为之一就是被关押在英国监狱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采取的绝食抗议行为。绝食抗议开始于1972年,诉求是要英国政府承认他们的政治地位,不把他们与一般罪犯同等对待。英国政府一开始犹豫不决,囚犯们的绝食抗议也没有进行到底。然而,在1979年撒切尔当选首相后,英国政府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81年,一个名叫博比·桑兹(Bobby Sands)的关键人物走上历史舞台。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临时派领导人是诗人,具有浪漫革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熟谙弗兰兹·法侬(Frantz Fanon)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革命理论,他的诗歌承继19世纪爱尔兰民族斗士简·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之母)和复活节起义领袖之一的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Pearse)作品的主题。桑兹认为,只有绝对的牺牲、死亡才能有效用。1981年5月5日,他在绝食六十六天后死亡,是北爱问题时期因绝食而死的十名爱尔兰共和军囚犯中的第一位。贝尔法斯特的一个重要景点就是天主教街区墙上的巨型政治壁画,其中一幅再现桑兹的壁画清晰地将其与基督联系在一起,长发的桑兹面带仁慈的笑容,壁画介绍词为:博比·桑兹,诗人、爱尔兰人、革命者、爱尔兰共和军志愿者。关于桑兹绝食的意义,奥图尔评论道:
这有艺术的结构。正如一部戏剧作品,过滤了宏大的世界,将其精简为一小撮角色,绝食示威所达到的效果正是之前的1916年复活节起义领导人被执行死刑的效果。关于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复杂事件和许多死亡被升华为七名签署了爱尔兰共和国宣言的领导者的英雄悲剧……现在北爱问题的复杂性和成千上万的死者也被简化为绝食示威面对死亡的十个人。而且不止这一简化——没过多久,这十个人也从记忆中消褪,整出戏被浓缩为博比·桑兹的身体。
然而,现实绝不可能像戏剧表演那样简单,高潮过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个人的身体并没有终结暴力,反而赋予暴力新的理由。
除了爱尔兰公共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殉道情结,奥图尔还探讨了私人层面的男性气质,认为北爱问题中的暴力现象与有毒的男性气质有关,即对暴力的浪漫化和英雄幻想,而且这一现象存在于派系冲突两方以青年男性为主的群体中。他们因北爱问题获得一种虚妄的崇高感,觉得自己是英雄史诗中的人物。北爱记者约翰·莱特的父亲为新教徒准军事组织成员,他如此评论道:
我们生活在电视新闻的报道里,这有着一种奇怪的、几乎是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将你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中间隔开来:比如,暴乱。结果就是一种类似纪录片的虚构,还有,一种邪恶的荣耀感不断地降低人们的道德准则,宽容以前无法想象的行为。以前是读惊悚小说、间谍小说、战争书籍和007的男人们——像我父亲——看电影通常也直奔黑帮片和西部片,现在他们有机会主演自己版本的爱国主义英雄幻想片了。
萧伯纳曾借其作品《英国佬的另一个岛》(John Bull’s Other Island,1904)反驳叶芝提出的“古老的理想主义”,对那些浪漫情怀嗤之以鼻,批评爱尔兰人的心灵中除了想象别无所有。奥图尔则更进一步指出,某些浪漫情怀不仅没用,甚至有害,一旦溢出文学艺术想象的界域,流入社会现实,极易导致暴力的悲剧。在他看来,北爱问题最终解决的起点是从献祭牺牲的浪漫神话中走出来,不再执拗,采取更灵活、务实的态度面对现实。北爱和平进程始于1993年,以杰瑞·亚当斯(Gerry Adams)为首的新芬党做出让步,承认北爱一百万名新教徒认同英国的民族身份,显然,他意识到,实现南北爱统一不会如想象中那样一蹴而就。在新芬党的干预下,爱尔兰共和军逐渐停止军事行动,最终于1998年签订北爱和平条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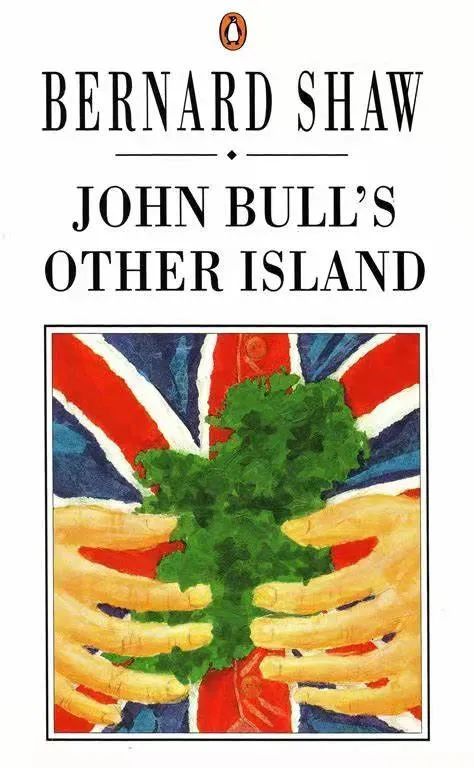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图片源自Yandex)
毋庸质疑,90年代是现代爱尔兰民族命运的转折期。困扰爱尔兰三十多年的北爱问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与此同时,教会的衰落势不可挡,爱尔兰官方开始调查各类教会机构(母婴之家、工业学校、抹大拉洗衣房)所犯下的罪行。很多艺术家也开始创作各类文艺作品(纪实文学、回忆录、小说、诗歌、戏剧、纪录片)再现和讨论种种不堪往事。整个社会风向改变,“不知道的知道”成为知道的知道,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出来讲述曾经被遮蔽、被否认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得到了民众体认。
“不知道的知道”与殉道情结反映了两个爱尔兰(理念中的爱尔兰和现实生活中的爱尔兰)的角力:一方渴望稳定,期待完全通过想象和执念建构过去与未来;另一方了解真实生活的复杂经验,但无力公开反抗,只能通过躲避、沉默和含混来应对。在故事的结尾,这个民族国家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现实,大胆地拥抱未知、多元、变化和不确定。回看1958年开启的这场“赌博”,奥图尔充满信心地总结道:“我出生的时候,爱尔兰没有未来,现在也没有未来。在过去,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想法,需要敲响变化的警钟。而现在,这是一个更积极的观念:我们不需要单一、已知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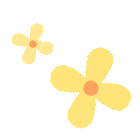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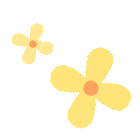
结 语
1961年,贝克特在接受神学家汤姆·德莱弗(Tom Driver)的采访中说:“找到可以容放混乱的形式,是当今艺术家的任务。”贝克特所谓的混乱延续至今,而奥图尔的《我们不了解自己》以叙事性非虚构的形式容放并归置爱尔兰六十年变迁的混乱,将其呈现为一个主题突出、情感丰沛的民族故事。他对爱尔兰问题的分析鞭辟入里,批判有力,伍德因此将其与乔伊斯相提并论:
他最大的长处是极其智慧又毫不留情的批判性审视,对自己民族的过去和现在都做出细致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斯蒂芬·代达勒斯允诺要从自己灵魂中锻造其民族未曾有过的良心;尽管不如代达勒斯那样富有诗意,但奥图尔的确有乔伊斯一样的愤怒,讲述他的民族如何最终打破宗教和迷信的束缚,创造自己的良心。
当然,正如此书杂糅的各种体裁所示,奥图尔的情感其实是复杂的,既有怀疑和愤怒,也有热爱和自豪。另一位书评人的点评也许更为确切:“芬坦·奥图尔的爱尔兰现代历史之旅是一名作家写给他祖国的一封带刺的情书。”因此,我们可以说,爱尔兰人可能不了解自己,但作家奥图尔是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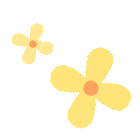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1期,“爱尔兰分治百年”专题,责任编辑龚璇,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培 育 终审:文 安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