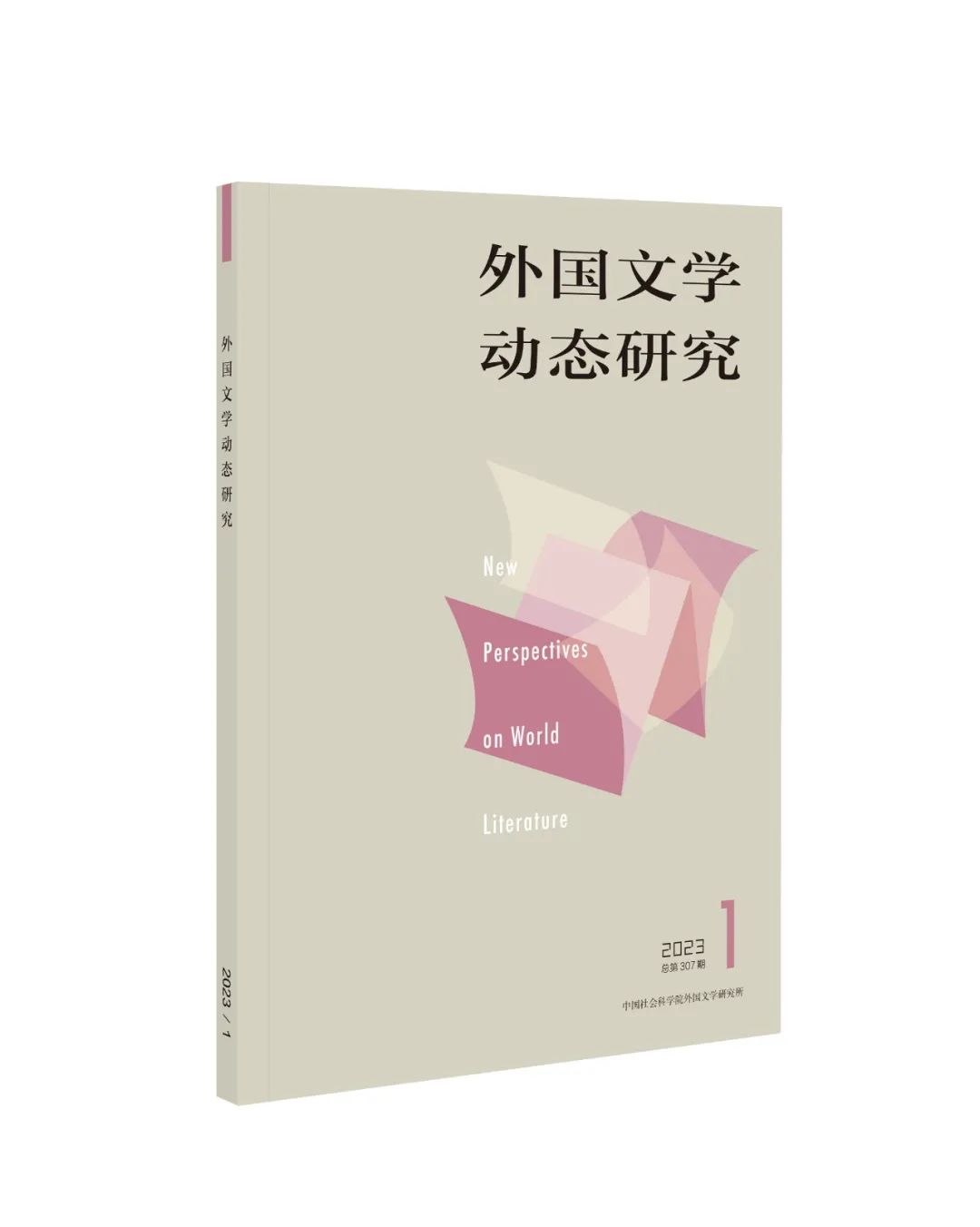转载 | 苏联当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

严永兴 祖籍浙江余姚,1940 年9 月16日出生于上海,1952到1958年就读于上海市市东中学,1958 年9月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1962 年7月毕业后长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部工作,1979 年5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历任《世界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外国文学动态》副主编,任副编审、编审。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译有长篇小说《悬崖》《撒旦起舞》《黑夜即将来临》《虎皮武士》《萨逊的大卫》《生存与命运》(合译)、《兽笼》《命运线》等,总计二百万字,著有《辉煌与失落——俄罗斯文学百年》等研究性成果,选编《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苏联卷》《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俄罗斯卷》《白银时代丛书》(六卷),参与编撰《新编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辞典》《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词典》《外国争议作家、作品大观》等。
自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被确立之后,浪漫主义在苏联文学中的地位,可以说,一直是很微妙的。
三十年代初,虽然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法捷耶夫等人也曾提出过“积极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的概念,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指的创作方法,而只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浪漫主义精神,或曰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是否应该在苏联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始终就没有明确过。

(卢那察尔斯基,图片源自Yandex )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文艺批评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苏联理论界开始迫切需要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包括浪漫主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于是,1966年,苏联作家协会和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组织召开了一个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的理论讨论会。讨论会上,莫斯科大学教授奥夫恰连科率先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基本创作方法之外,在苏联文学中还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创作方法,即社会主义浪漫主义。这种“新型的浪漫主义”并不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对立”,而是有机的“融合”、“联合”、“结合”和“综合”。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见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三十余年来头一次遇到了认真的挑战。奥夫恰连科的观点,不仅给浪漫主义在苏联文学中以一席之地,而且简直要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了。更有甚者,奥夫恰连科关于创作方法多样化的主张,在讨论会上及会后还得到了另一些文艺理论家的赞同和支持。他们有的甚至还提出,除浪漫主义之外,批判现实主义、“新型的自然主义”等都是可以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共存的”。
一些理论家还举出文学创作中的大量例子,来说明实际上浪漫主义始终没有离开过苏联文学,始终是许多作家采用的创作方法之一。不仅早期的高尔基的《海燕之歌》、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等作品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佳作,而且从俄罗斯作家列昂诺夫、卡达耶夫、卡维林、格林的文学创作中,从乌克兰著名作家扬诺夫斯基、杜甫仁科、冈察尔、斯捷利马赫的作品中,从哈萨克作家努尔佩伊索夫、亚美尼亚作家马捷沃相、吉尔吉斯作家艾特马托夫、楚克奇作家雷特海乌的小说中,以及从梅热莱斯基、武尔贡、马雷什科、巴让等诗人的诗歌中,都可以读到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出色描绘,以及强烈的对比,瑰丽的想象,大胆的幻想、巨大的概括与象征,典型的夸张与虚拟,现实与神话的结合,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等等。所有这些,他们认为,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才固有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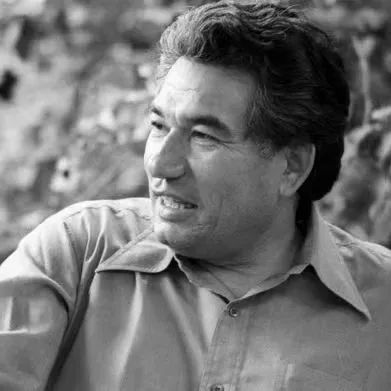

(艾特马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图片源自Yandex)
但是,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彼得罗夫博士为首的一批文艺理论家们却认为奥夫恰连科的观点简直大谬不然。他们指出,在苏联文学中只能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统一的创作方法,它容纳得下象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一些丰富多来的风格现象。有的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一些“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的拥护者看来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并不能找到本质上区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些特点。所谓的高尚的精神世界、内在的激情、诗情画意等实际上并不是浪漫主义所独有的,恰恰正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因此,他们的主张是,浪漫主义属于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基础上的风格的多样化。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和风格的多样化,虽然只有几字之差,但是,却事关重大。两种意见针尖对麦芒、未能、也不可能取得一致。
此后,奥夫恰连科不改原衷,继续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文学过程》(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68)一书和《争论在继续》(《新世界》杂志1971年第5期)一文中,坚持自已的观点,向理论界提出挑战。1972年,科学院通讯院士德·马尔科夫在《文学问题》杂志上发表文章,开始同奥夫恰连科展开论战。第二年,德·马尔科夫以及另两位通讯院士苏奇科夫和洛米泽在《文学评论》杂志上撰文,尖锐批评奥夫恰连科的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是“苏联文学中创作方法的多元论”,将使“我们的文学失去方向”。

(奥夫恰连科,图片源自Yandex)
但是,看来德·马尔科夫也并不赞同风格的多样化的理论。因为院士同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他的“开放体系”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上是个新的美学体系,这一美学体系应当是开放性的,也就是“真实描写生活的历史的开放的体系”。这一体系,对作家来说,“在题材的选择以及采用足以表达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法方面”,“都是历史的开放的”。它也不局限于“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而是可以“把过去和现代其他各种艺术流派在表现手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结为一个整体”。当然,它对各种艺术流派和手段的接受并不是“无边的”,它们必须“适合社会主义思想和美学标准。”
新的“开放体系”理论的提出,给本来就因浪漫主义等问题的讨论搞得不平静的水面,又投下了一块巨石,引起新的波澜。1975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出面组织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新现象”的科学讨论会,来讨论召开放体系”问题。本来“开放体系”理论的提出,对于浪漫主义问题似乎是较为妥善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既反对了创作方法的多元论,维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唯一的”或“统一的”创作方法的地位,又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它同其他流派或创作方法,尤其是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只把它们当作统一的创作方法基础上风格的多样化。但是,这一理论又涉及到许多其他重大的理论问题,其中包括对现代主义的看法和态度问题,所以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争论也显得越发激烈,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浪漫主义问题的讨论与我们也不无关系。记得1980年我国文艺界就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展开讨论时,苏联方面就很注意。苏联一位文艺理论家托罗普季夫还在1982年第1期的《文学问题》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关于现实主义的探索(中国的创作方法问题)》,对我国文艺界的这次争论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只能创作出“无冲突的、足资垂训的和粉饰现实的作品”。而“革命现实主义”这一术语,也是个“明显的错误”。这样“就产生了术语上的混乱”,“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似是而非的混合”。
在创作实践上,这些年来,苏联作家创作的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其实,也不单是现实主义的,倒是浪漫主义的特征要明显得多。比如,在艾特马托夫的中篇《白轮船》(1970,获1977年苏联国家奖金)中,童话与现实、梦幻与隐喻交相辉映,浑然一体,使浪漫主义得到了炽烈的升腾。作品要揭露和鞭挞的是山林巡视员奥罗兹库尔无恶不作的罪行。但作家把有关大角母鹿的美丽的民间传说贯穿其中,并且通过心地善良的男孩那种种充满神奇色彩的幻想,以及奥罗兹库尔使童心毁灭,男孩投海,化作人鱼而去的浪漫主义手法,来揭露现实世界的丑恶。
获1975年国家奖金的《白比姆黑耳朵》,乃是通过一条通人性、懂人话的白比姆狗,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悲惨遭遇和感受来揭露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的。这种浪漫主义的虚拟性,表面上似乎破坏了生活的真实,但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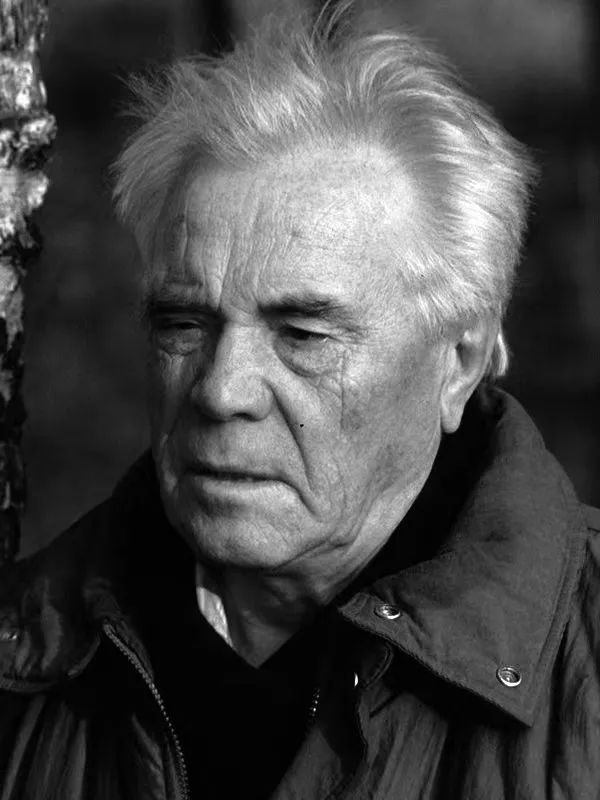

(阿斯塔菲耶夫和《鱼王》,图片源自Yandex)
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6,获1978年苏联国家奖金),其主题是保护大自然,揭露偷猎者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但作者把自然界的力量拟人化,通过“鱼王”对偷猎者的严厉惩罚来展开主题,告诫人们要保护大自然,否则必将受到养育万物的大自然的报复。
如果说,上面所举的几部作品都属暴露文学,作者在揭露现实时,故意采取虚虚实实的手法的话,那么,最近获国家奖的叶夫图申科的长诗《妈妈与中子弹》(1982),虽是政论作品,却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妈妈参加过卫国战争,现在她老了,但还在报亭卖报。她卖的是后天的报纸。可是谁都不愿看后天的报纸。诗人从后天的报纸上看到了未来的寡妇,怀抱着已经死去的未来的婴儿。突然中子弹爆炸,地球上甚至连一个寡妇也没有剩下,剩下的只是一座座儿童乐园。诗人没有丧失记忆,他记得自己的过去,记得当过红军将领被肃反的外祖父还有一个妹妹在白俄罗斯农村。德国法西斯把烧红的烙铁烫在她的胸脯上,她并没有屈服。如今她正领着托尔斯泰、甘地、爱因斯坦和耶稣走在和平进军的行列中。作者用妈妈、记忆、后夭的报纸和中子弹象征和平、历史、未来和战争,把现实、未来、科学幻想融为一体,注入了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优。长诗采用自由诗体,没有严格的韵律,联想跌宕跳跃,充满浪满主义的概括和象征,受到了评论界高度的赞扬。这说明,浪漫主义是可以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相融合”的。
我们再谈谈现代主义。提起现代主义,不但苏联文艺界,恐怕我们也会“谈虎色变”。确实,现代主义在苏联很长时间都是被视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反动的意识形态表现而遭到坚决否定的。
其实,现代主义并不光是西方所有。早期苏联文学的一些作家和诗人也曾归附过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流派。像阿赫玛托娃的高峰主义,叶赛宁的意象主义,勃洛克的象征主义,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等等。只是后来他们有的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归依新的文学潮流,有的不愿合作,移居国外。
苏联文艺界对现代主义的态度也并不都是铁板一块。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一度曾在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如潘诺娃的长篇《感伤的罗曼史》(1958)、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带星星的火车票》(1961)、沃兹涅先斯基的组诗《长诗<三角梨>里的三十首抒情离题诗》(1962)和叶夫图申科的《苏维埃政权下一个时代儿的自白》(1963)等。此外,出版社也曾于1961年出版过被视为颓废派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集》。
就是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也开始有所介绍。卡夫卡的《在苦役营》和《变形记》被翻译过来,登载在《外国文学》杂志1964年的第1期上。文艺评论家叶夫根尼娅·克尼波维奇在译文后发表评介文章,称卡夫卡“并不是个现实主义者,但他确实是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寻求真理的艺术家。”1965年第9期的《外国文学》杂志又刊登了法国荒诞派戏剧家尤内斯库的剧本《犀牛》。杂志在《后记》中介绍这部作品的时候说,剧本有着“客观的、真正的意义”,有着“人道主义的激情”。并且认为尤内斯库得以“找到资本主义世界中鲜明、准确的艺术形象”。
也许,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至少可以看作是某种松动。而且,苏联理论界确实也开始对现代主义及其代表性作家进行比较认真和深入的研究。如1965年就有符·德聂伯罗夫的《二十世纪长篇小说的特征》和德·扎东斯基的《弗兰茨·卡夫卡和现代主义问题》两部研究现代主义的专著问世。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西方现代派的态度应该说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前面提过,1966年苏联召开过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的理论讨论会。在会上,评论家凯德琳娜就曾提出过,苏联文学必须“不断扩充自己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考察的手段的宝库,使那些从其本质上看来似乎与我们的艺术迥然有别的心理分析和概括的原则,如‘意识流’之类,也能在社会主义土壤上被同化”。1967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科全书》里,在“现代主义”的条目中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无意断然把现代主义归结为世界文学和世界社会精神发展中的‘渣滓’”。现实主义文学也“可以吸收现代主义者所推行的个别手法”,如“意识流、蒙太奇、叙事时间的反常”等等。“它们可以摆脱现代主义的哲学内容而丰富现实主义。”并且认为,“在一系列大作家(如福克纳,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海明威)的创作中,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点往往同时并存和互相交织在一起。”甚至说,象阿波利奈尔、普鲁斯特、卡夫卡、穆齐尔、乔伊斯、加缪、艾略特等这些现代派作家,对“他们的遗产应当作为认真研究的对象”。从一些西方文学专家的研究专著来看,他们的分析则更为具体,观点更为明确。比如扎东斯基在1979年出版的《在我们的时代》一书中写道,“在现代主义潮流里流动着尚未毁坏的旧的现实主义的余渣。其中也就产生了新的现实主义的凝块。”因此,他以为,决不能把现代主义潮流“看作某种颓废的现象而加以蔑视”。他指出,现代主义“并非是自觉反动的美学体系”,但是“可以为反动势力所利用”。
苏联理论界这些年来对“开放体系”的争论,涉及到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便是现代主义问题。反对者认为,“开放体系”是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行门户开放,同现代主义同流合污。同意者表示,所谓“开放”,是向“生活的真实”以及“社会的和艺术的进步”开放。争论仍在继续,官方至今还未表态,情况如何,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但是,我以为,探索和争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开放体系”的提出,必将促使理论界对现代主义的进一步研究,来决定对它的取舍。笼统地把现代主义说成反动的艺术流派已经是无力的表现了。

(《一日长于百年》,图片源自Yandex)
在文艺创作上,著名作家艾特马托夫在借鉴现代主义手法方面可以说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长篇《一日长于百年》1980年发表后,一方面赢得了高度的赞扬,认为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普通铁路工人叶季盖这一正面形象,深刻揭示了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一个劳动者对人类命运所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在所谓“宇宙线索”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艾特马托夫在作品中是用两条平行的线索来展现主题的。一条线索是通过主人公为朋友送葬的一日内的活动,回忆了他那坎坷的一生,塑造了一个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老工人的形象。另一条线索描写就在主人公为老友下葬的那天夜晚,一艘巨大的苏联宇宙飞船从他的头顶飞过,与美国发射的飞船一起飞向美苏联合空间站。原空间站的两名宇航员已经私自接受位于银河系的外星人邀请,去访问那个文明世界,外星人愿意与地球接触,用自己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文明帮助地球。但美苏两个特命全权委员会紧急磋商的结果,竟然拒绝同外星人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丧失了加速地球文明建设的机会。作家把几世纪前的神奇的民间传说、想象丰富的科学幻想和当代的现实生活交相辉映;让过去、现在、将来,天上、人间、地下相互交织,这种手法在苏联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在1980年第12期的《文学问题》杂志上谈《一日长于百年》的创作时,曾承认,这部作品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和启发。这就使我们想起哥伦比亚著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9)。这部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不也是采用把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科学幻想同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手法来揭示主题的吗?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通过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来反映严酷的现实生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绝望和传统价值的破灭。
当然,这种手法不单是魔幻现实主义才有,在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中也并不少见。比如,美国著名战后实验小说家冯尼戈特的长篇《第五号屠宰场》(1969),也是通过科学幻想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生活同感情间的混乱。对西方作家来说,要摆脱无法解决的矛盾、痛苦、灾祸和不幸,最好的办法似乎便是飞向宇宙。
艾特马托夫借鉴这种手法,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正是为了使人们正视当今地球上那种令人担忧的现实。借鉴而有所创新,这是作家努力探索的结果。
(原文载《文艺评论》1985年第5期,感谢《文艺评论》授权转载。)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