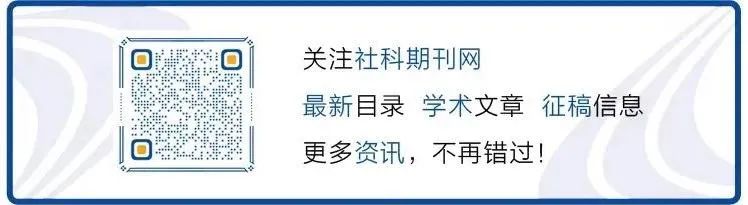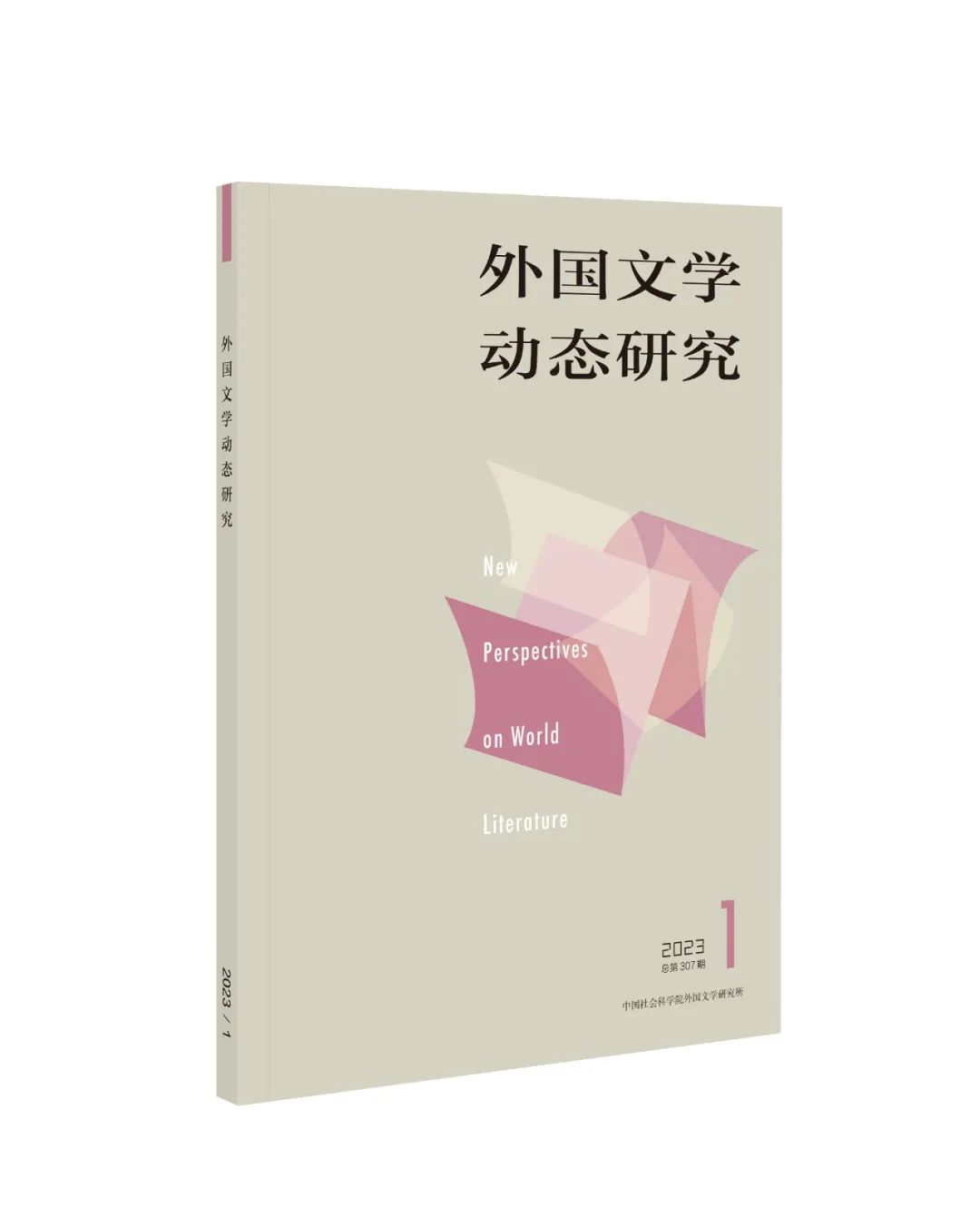动态研究 | “后戏剧”式重构:康·博戈莫洛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戏剧书写

内容提要 康斯坦丁·博戈莫洛夫是当代俄罗斯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为大胆的戏剧导演,他的舞台不是用来搬演,而是用于讨论、拆解和重构文学作品,作家文本不再是文学作品剧场化的绝对中心,而是通过“后戏剧”式书写获得一系列衍生意义。博戈莫洛夫以“文本清零”的手法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文本打散,重构成一部部与原作大相径庭的戏剧作品,并将一百多年前的人物置于现代语境下,呈现他们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博戈莫洛夫继承了俄罗斯戏剧学派源远流长的心理现实主义传统,在“后戏剧”语境下借助现代技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指向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揭示出当代人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
关键词 康·博戈莫洛夫 “后戏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 重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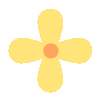
今天提及舞台艺术领域的“俄罗斯戏剧学派”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俄罗斯戏剧导演对本国文学经典的多样化阐释。这些形态各异的解读延续了文学经典的艺术生命,同时也造就了大放异彩的俄罗斯当代舞台艺术。在诸多俄罗斯文学经典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受当代导演的青睐,而对其解读最具新意的当属莫斯科小布隆纳亚话剧院艺术总监兼总导演康斯坦丁·博戈莫洛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Богомолов,1975—)。他的舞台以独特的方式重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作品。


(康斯坦丁·博戈莫洛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图片源自Yandex)
在博戈莫洛夫的舞台上,经典文本不再是文学作品剧场化的绝对中心,也并不作为舞台创作的脚本。它可以为实现剧场性功能被重释和重构,并在戏剧书写过程中获得一系列衍生意义。这种书写方式的基础是协调文学性与剧场性的美学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文学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博戈莫洛夫的试验割裂了舞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联系,相反,在某些方面,文学性因素反而获得了更大自由,而且剧场性因素也相应地被赋予了更多文学性功能。虽然博戈莫洛夫打造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后戏剧剧场,但在“后戏剧”语境下,这种舞台美学建构方式呈现出了显明的“后戏剧”倾向。
一、“文本清零”的剧本重构
在传统戏剧舞台上,文学剧本是艺术再创作的基础和中心,而在博戈莫洛夫的舞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作失去了“一剧之本”的地位。博戈莫洛夫这种处理文学原作的方式,被人们称作“文本清零”(обнуление текста)。
博戈莫洛夫的“文本清零”并非彻底抛弃原作,而是对其进行一定的重组和调整,重新分配传统解读版本中所谓重点场面和一般性场面的权重,以往被视为重点的情节和场面在博戈莫洛夫这里一笔带过,甚至完全消失。《罪与罚》略去了原作开头和结尾的重要情节。原作故事始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犹豫是否要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来验证自己关于“平凡人”和“不平凡人”的理论,随后母亲的来信以及与索尼娅的父亲马尔梅拉多夫的相遇让他下定了采取行动的决心,接下来谋杀老太婆的场面是整部作品的第一个高潮,也是能够鲜明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叙事风格和技巧的部分。但博戈莫洛夫将拉斯柯尔尼科夫母亲来信作为幕启,开场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长达七分钟的大段独白,略带删减地读了信的内容,随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与马尔梅拉多夫的会面。整部剧的主体部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妹妹的雇主斯维德里盖洛夫以及侦查员波尔菲里之间的大段对白。原作中杀害阿廖娜和利扎韦塔的情节被直接删掉了。原作结尾,主人公被判服苦役、在西伯利亚与索尼娅相遇的情节也没有出现在舞台上,而是一段静场后拉斯柯尔尼科夫面向观众宣告是自己杀死了阿廖娜和利扎韦塔,并深鞠一躬下场。
文本的重构还体现在导演对出场人物和情节“无中生有”的重组上。戏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设置了一个原作中并不存在的人物——布宁,由博戈莫洛夫本人扮演。他如同剧中人的导师一样与角色谈心,又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质问“群魔”。 此外,该剧的情节也是《群魔》《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三部作品的拼贴。比如,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和埃尔克利的一场戏,剧情用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和伊凡在酒馆会面的场景。台词沿用了小说原文,埃尔克利甚至穿的是小说中阿廖沙的修士服,还改信了基督。在这次交谈中,伊凡历数了无辜的孩子遭受的苦难,比如有人把婴儿向上抛,然后用刺刀接住,借此来说明“人残忍得技艺精湛”以及阿廖沙的上帝“好不到哪儿去”,进而表达他不会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在剧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里,“群魔”领袖彼得以伊凡之口向自己的狂热崇拜者埃尔克利表达相同看法来坚定对方信念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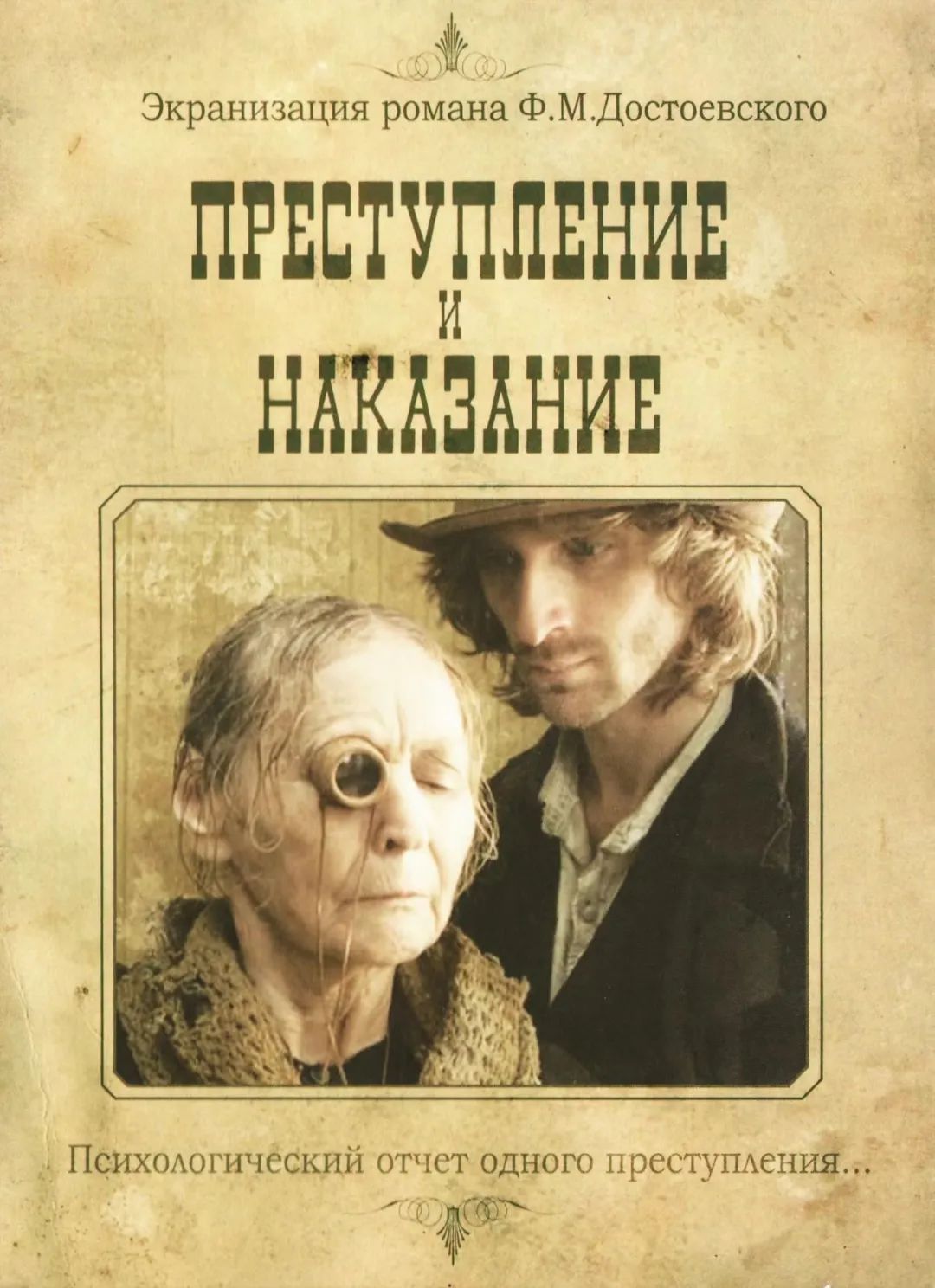
(《群魔》和《罪与罚》,图片源自Yandex)
博戈莫洛夫对原作文本的重构可以做多重解读。基里洛夫这个灵魂被操控者并未像原著中那样写下认罪声明并替彼得代过而采取他始终宣扬的“封神”手段——自杀;舞台上,他手里紧握的不是左轮手枪而是香槟,开香槟的声音代替了枪声,接着字幕显示基里洛夫趁彼得在走廊扒着剧院窗户跳到街上逃走了。这个结尾可以说是基里洛夫背信弃义,也可以解读为基里洛夫终于摆脱了“群魔”的控制,义无反顾地去热爱生命,回归自由意志。
二、“舞台静默”中的人物重构
基于文学剧本的冲突、性格、形体动作等一系列传统的舞台表现手段,在博戈莫洛夫这里都被淡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瘸腿女人”扮演者玛丽亚·舒马科娃称这种舞台表现风格为“最小化外部表现”。舞台氛围整体呈现为一种“舞台静默”,“舞台静默”并非演员不说话、采取哑剧的表演方式,而恰恰相反,它呈现出来的是“纯净的”剧本,演员只有念白,鲜有甚至没有明显的形体动作,人物在整场演出中可以待在几个特定位置表述台词,没有任何外部行动。
舞台剧《罪与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形体动作在舞台上消隐了。《罪与罚》略去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老太婆的正面冲突场面,只留下拉斯柯尔尼科夫与马尔梅拉多夫、波尔菲里、索尼娅以及斯维德里盖洛夫几个人物之间的大段对话(长则半个小时,短则十几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人物则待在各自相对固定的舞台区域进行对话,演员很少挪动位置,也鲜有手势和肢体动作,而是如同蜡像一般“空谈”,仅有的一次正面冲突场面——沙托夫被枪杀,也安排在主场景幕后区域。
“舞台静默”除了淡化人物外部行动,对人物的情绪表达也进行了相应处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歇斯底里式的极端情绪,博戈莫洛夫在舞台上关注的却是歇斯底里背后人物的极度理性。《罪与罚》的人物一反常态地没有任何狂热、昏厥、神经质的抽搐等激动表现,相反,所有人物都处于冷静分析的正常状态。卢仁甚至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台词。然而,我们绝不能据此判断演出中的人物是冷淡的、缺乏热情的,甚至认为他们的表演是没有感情的,“人物的热情只不过不再作为一种标记,(在博戈莫洛夫的戏中)将感受细腻的人与无动于衷的人区分开来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要把‘平凡人’和‘不平凡人’区分开来一样困难”。这实际上呼应了《罪与罚》原作中与索尼娅探讨“罪”的问题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所表达的对“罪”的看法:“你同样出了格……你是自杀,你害了一个生命……自己的生命(这反正都一样)……所以我们应该一起走,走同一条路!让我们走吧!”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来,索尼娅“自杀”和他自己杀死老太婆并无差异,都是“罪”。
在博戈莫洛夫的舞台上,所有人物都处于冷静状态,没有区别,出场人物都是“平凡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在博戈莫洛夫舞台上通常被置于日常生活状态,念白的声音接近人们日常说话的音量和语气,没有任何“舞台腔”的痕迹,也没有歇斯底里的行为,自始至终都是平淡如水的叙述,甚至人物的性别、年龄、服饰等外部特征均被弱化,但我们依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状态。“在博戈莫洛夫的戏里,心理能量以最小化外部表现的方式强烈地流露出来。”
就性别而言,斯塔夫罗金的扮演者是博戈莫洛夫的“御用”女演员亚历山德拉·列别诺克。原作中的人物年龄设定在舞台上也失效了,学生身份的沙托夫的扮演者是演员阵容中年龄最大的赫拉布罗夫,而年长的基里洛夫则启用了最年轻的演员多尔任科夫。导演这样处理除了营造新奇效果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刻意模糊观众对角色外在因素的关注,而将注意力转向角色的内心状态,也就是“角色由谁来扮演不重要,不管你扮演的是男女老少,重要的是出场时你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状态,即便女演员身着男士制服出场,观众很快就会相信你所传达的状态”。扮演索尼娅的马林娜·伊格纳托娃比索尼娅母亲的扮演者还要年长。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索尼娅未来的样子,也可以认为导演向我们呈现了承受苦难的索尼娅(靠卖身为家人贴补家用)历经蹂躏之后内心的状态。这一手法在卢仁身上用得更妙。小说中,卢仁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娅的未婚夫。杜尼娅迫于生计委身于他,而这个人是一个宣称“爱人先爱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小人。博戈莫洛夫出人意料地将这个角色交给了特型演员阿列克谢·因格列维奇。阿列克谢在舞台上与杜尼娅出双入对,始终陪伴在她身边,没有一句台词,但他本人的侏儒身材在舞台上昭示了这个人物与身材高挑的杜尼娅极不般配,而且暗指角色内心的猥琐(这里没有任何诋毁和侮辱阿列克谢本人身体缺陷意思)。这种处理让身体超越了语义符号的范畴。“在戏剧剧场中,舞台决斗中的身体杀害只是对精神决斗的一种比喻,而在后戏剧剧场中,身体的运动或残障、有形或者无形性、整体或部分性则凸现出来。”身体上的消减和错位并未导致舞台语义的混乱,戏剧的意义反而得到了强化,这就是雷曼所谓的“戏剧过程是在身体之间发生的,而后戏剧过程则是在身体之上发生的”。
三、极简舞台的时空重构
如果说本文前两部分探讨的是文学作品向剧场艺术转化过程中文学性因素的剧场化重构,那么后两部分将探讨剧场性因素的文学化重构。博戈莫洛夫通常采用一个布景到底的舞台设计,鲜有转换,而唯一的布景往往使用鲜明的极简风格。在这里,空间和时间的划分是不明确的,却表现出更鲜明的叙事性,与原作相得益彰。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故事发生地的建筑在舞台上被设计成现代框架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将这一形式运用得极为巧妙。舞台的主体由左右上三面屏幕(偶尔使用后方的屏幕)组成,中间是三面网格墙围出来的空间。这个设计灵感一方面让观众联想到监狱,另一方面暗指《圣经》的典故。在彼得向“五人小组”成员发表演说以及随后与其狂热崇拜者埃尔克利交谈的场景中,舞台上方屏幕显示的是牢房铁窗栅栏的图形(图形四角配的是俄文“网”的四个字母)和《路加福音》中的一句话“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路加福音》里西门彼得(圣彼得)是一个渔夫,一整夜没打到鱼,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显然,这是违背渔夫经验的建议。彼得并不情愿,但还是听从了耶稣的话,令他惊奇的是,他打到了很多鱼。于是,彼得放弃家产,跟随耶稣,成为十二门徒之一。巧合的是,“群魔”首领也叫彼得,只不过在这里,彼得不是追随别人,而是被追随者,被其崇拜者埃尔克利视为“耶稣”。因此,这个典故用在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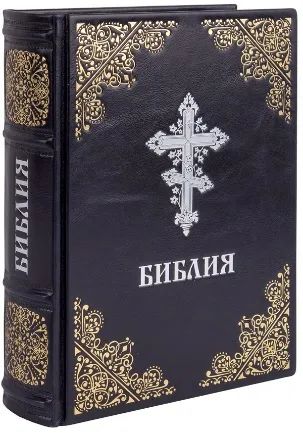
(《圣经》,图片源自Yandex)
《罪与罚》则更为简洁。舞台两侧各放置了一张长吧台,正后方是一个方台。这些区域在不同场景发挥着酒吧吧台、警局办公桌和索尼娅的床等功能。舞台以黑、白、灰的冷色调为主,没有明显的场幕区分。不同场景切换通过舞台建筑框架上的LED灯光调整来实现。当灰色的空房间亮起黄色灯光时,代表场景转换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与马尔梅拉多夫初次相遇的酒馆。蓝色灯光代表警局,而粉色灯光代表索尼娅的房间。空间是博戈莫洛夫“后戏剧”式舞台设计最直观的体现,而舞台上还有一个被导演动了手脚却往往为我们所忽视的东西——时间。
仍然以《罪与罚》为例。舞台上的剧情时间已经不是小说的叙事时间,而是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时间。剧情是主人公内心斗争的心路历程。演出始于第一次引起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波动的母亲来信,其后与马尔梅拉多夫、波尔菲里、斯维德里盖洛夫以及索尼娅的相遇一次次引发主人公的内心斗争。当他内心的一切斗争结束,即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认罪的时刻,全剧幕落。主人公面向观众席宣布杀人凶手是自己,然后鞠躬下场。所以,舞台时间截取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斗争的时间,对外部行动发生的时间(包括谋杀老太婆)做了减法。除了时间的减法,博戈莫洛夫的舞台还给人一种极强的时间错位感。不管是演戏的演员,还是看戏的观众,都感觉尽管舞台上演的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好像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这种时间的错位感及其意义的生成基于观众的群体感知,或者说基于对某个集体度过的时间的记忆,“时间经验变成了一种身体、感官真实,一种精神真实”。
博戈莫洛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剧情和人物拉到当下状态。人物穿的是现代服装,舞台上的家具,如《罪与罚》的吧台和《公爵》中象征棺材的日光浴机,也都是现代风格,与观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家居用品别无二致。个别台词也相应做了现代化处理。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最后基里洛夫犹豫要不要自杀的时候,他听到楼下的两个朋友喊他下来喝酒,他回答说,“我不能下楼,因为我感染了新冠”。导演将剧情移植到2020年上半年莫斯科居家隔离的语境下。
此外,博戈莫洛夫还善于使用歌曲来重构舞台时间。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手机铃声是《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我的心儿不能平静》,与人物的内心斗争相呼应;沙托夫被彼得枪杀时,舞台背景音乐是维克多·崔的《一颗叫做太阳的星星》,歌词“红色,红色的血,一个钟头之后已成尘埃,再过一个钟头会生花长草,三个钟头之后,它继续流动”不仅与剧情的氛围相得益彰,更能让观众感觉仿佛置身于苏联时期的生活剧中。

(《办公室的故事》,图片源自Yandex)
小布隆纳亚剧院官网上导演本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评价是“(展现了)几个世纪并未改变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现实”。在博戈莫洛夫看来,一百多年前的经典文学作品所描述的现实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导演将经典呈现在舞台上不仅仅为了让观众沉浸在故事本身之中,更是引导他们去思考当下的问题,用时代经典回应当下热点。作为剧场性因素的舞台时空,由破碎的文学时空重构为极具导演个性化风格的文学性因素,并发挥着更鲜明的叙事功能,同时被赋予了跨越时代的新意义。
四、实时影像的视角重构
博戈莫洛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呈现方式打破了以往的舞台表现原则。“静默”舞台有着极大的台词密度,所有外部行动都被尽量缩减,因此,观众需要时刻关注演员本身的表演细节,而导演的非传统舞台处理又导致观众无法细致观察。在这种情况下,导演借助摄像技术在舞台上实现多个视角的并置,解决了艺术手法上的这个矛盾。
博戈莫洛夫通常会安排两个手持摄像机的技术人员在舞台上,分别对准一位演员,或者从不同角度拍摄同一位演员,然后将实时画面同步呈现在舞台上方(偶尔在后方)以及两侧的屏幕上。这种多视角近距离的观看方式让剧场里任何位置的观众都可以清晰看到演员的细微表情和细小动作,产生“演员就在身边”的错觉。
将摄像技术运用于舞台对戏剧艺术来说并不算新鲜。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博戈莫洛夫将实时影像与舞台氛围有机结合,契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重构的视角实现了原作深刻揭示人物心灵深处全部奥秘的艺术目的。特写镜头拉近了观看距离,而外部动作的简化使得人物内心的空间被让渡出来,观众得以直接洞察“舞台静默”表象之下的人物内心世界。这也是博戈莫洛夫在戏剧舞台上挖掘的影像新功能。
我们可以借鉴巫鸿先生研究中国屏风时提出的“重屏”这一概念来定义这个功能。如果将整个镜框式舞台的台口视作观众面前的屏幕,那么博戈莫洛夫挂在舞台上的幕布就是屏中屏。它不仅是展示影像的媒介,具有舞台艺术性,其本身也是舞台上的一个道具,具有物质性。这个身兼艺术性和物质性的道具,为观众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划分了舞台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在舞台上同样接受着演员的观看,作为映照人物内心的一面镜子而存在,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以审视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重屏为人物表达和观众观看打造了一个二维心理空间。戏剧理论家雷曼指出了近半个世纪欧美戏剧的两个转向:一是从以文学为中心转向以剧场为中心;二是从演出者的叙述与阐释转向观众的接受与解释。作为“后戏剧”语境产物的“重屏”,将剧场里的观看拆解为演员看演员、演员看自己和观众看演员的多重视角。观众的观看从旁观转向参与,其视角成为舞台创作的一部分。这样,剧场性因素的观看参与到文学文本的阐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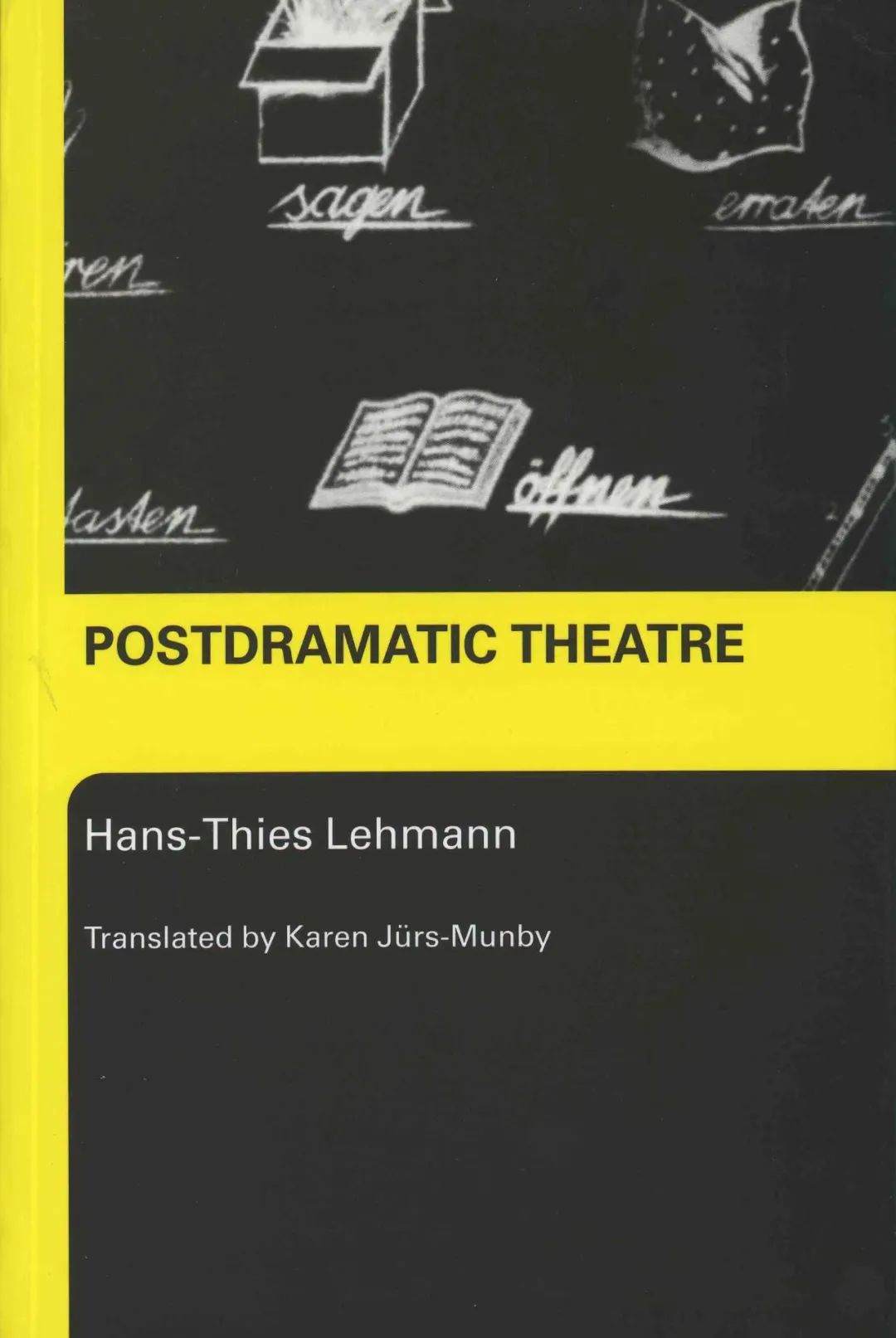

(《后戏剧剧场》和雷曼,图片源自Yandex)
博戈莫洛夫通常会设置三至四块屏幕(有时舞台前方和后方也会放置),不过舞台中央区域的屏幕一般是可升降的投影幕布,升起时,它悬在舞台上方,落下之后,就成了演员身后的隔板,将前台再次区隔出“前台”和“后台”。并非所有剧情都发生在“前台”,比如彼得枪杀沙托夫的场景就设置在“后台”,实时影像同步呈现在屏幕上,这就进一步压缩了外部行动在舞台上的比重。《罪与罚》甚至直接略去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害老太婆的戏,将更多的舞台空间让给了内心世界。屏幕就是我们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入口,或者说,就是人物内心世界本身。演出中,当演员直视摄像机的时候,往往就是人物凭借独白坦露内心世界的时候。人物仿佛在与另一个自己对话,构建另一个舞台叙事声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里沙托夫因意见不合与斯塔夫罗金产生了冲突,影像与字幕的功能在这场戏里相得益彰。沙托夫先是给了斯塔夫罗金一记耳光(这也是这场正面冲突唯一的外部肢体表达),斯塔夫罗金愤怒地抬起手,准备回一巴掌,但手停在了半空中。此时舞台正后方屏幕显示的是《马太福音》的文字“斯塔夫罗金想到‘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将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而左右两侧以及上方屏幕是斯塔夫罗金背在身后紧握拳头的特写镜头,人物内心与人物动作之间的巨大张力由此跃然于重屏空间之上。可见,屏幕作为一种物质性和艺术性的综合体以及“后戏剧”式视角的媒介,在博戈莫洛夫的舞台上发挥了直抵人物内心深处的文学叙事功能。
博戈莫洛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戏剧书写并非单纯的文学作品搬演,也并非借助各种现代技术手段的介入。在他的重构框架下,原作在舞台上失去了原有形态,但作品的意义却并未因此而折损,反而以另类的方式得到强化。这种策略得以奏效,究其根本,在于博戈莫洛夫的戏剧书写不是将作品的文学性向剧场性转化,或以剧场性转移文学性,而是在文学性与剧场性相互渗透中重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诸元素。放眼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欧美戏剧发展史,这种理念属于“后戏剧”趋势的产物。“传统戏剧的总体观念,是致力于在舞台上创造一个艺术的小世界。文学剧本是创造的基础和中心——围绕剧本所提供的情节、人物、对话、动作等,由舞台各部门(表演、舞美等)在导演指挥下进行有机综合,最终呈现于舞台。这类戏剧的文学性很强,而且起着主导作用;同时也重视舞台性,即用各种风格和手段把剧本‘树立’在舞台上。”博戈莫洛夫并没有执行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树立”在舞台上的任务,而是将其拆解,重构出一个剧场艺术的新文本。这个新文本在制作上突破“剧本中心”,在观念上充分释放“剧场性”。这种反对以文学为中心的戏剧观念与解构主义以及后现代反对以“语言”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无关系。博戈莫洛夫同样否认一个中心的在场,文学性因素和剧场性因素平等地参与文学作品的戏剧书写,两者均非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对权威。博戈莫洛夫的重构即制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文学性和剧场性两个维度中的差异,而“演出文本”的意义恰恰生成于文学性和剧场性的相互作用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博戈莫洛夫的舞台也是一种“不断产生差异的游戏”。
博戈莫洛夫执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偏离原作的尝试,因为不论剧本本身,还是舞台呈现手段,都突破了原作的规定情境,但它同时又是最贴近原作的尝试。当剥离一切现代技术外壳之后,它显露出来的依然是在俄罗斯戏剧学派心理现实主义框架下极具现代生活指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精神内核。也有观点认为博戈莫洛夫的手法影响了观剧体验,但这种大胆尝试作为当代新锐导演对文学经典的另类解读,本身就彰显了俄罗斯戏剧和俄罗斯文学在当下时代的鲜活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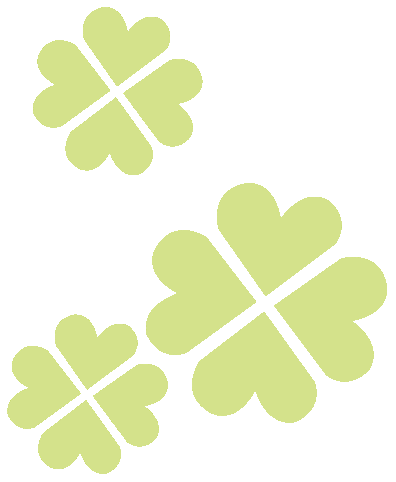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1期,“动态研究”专栏,责任编辑苏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排版:培 育 终审:文 安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