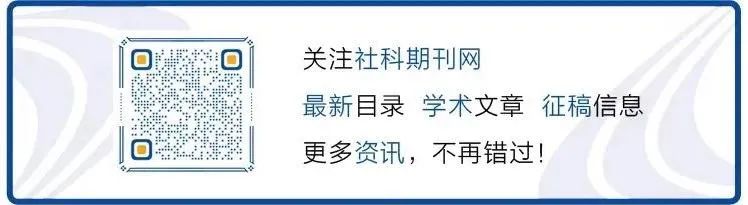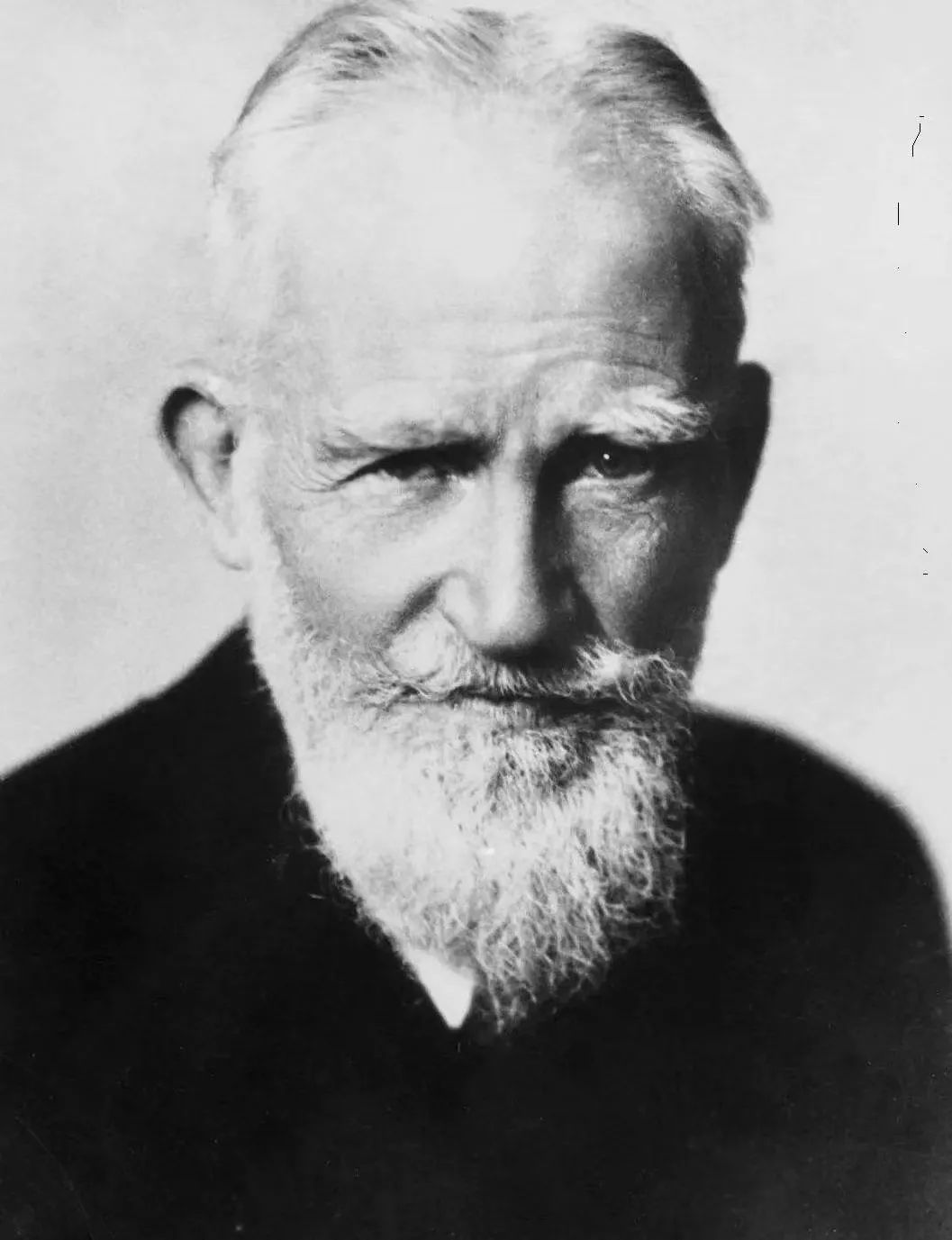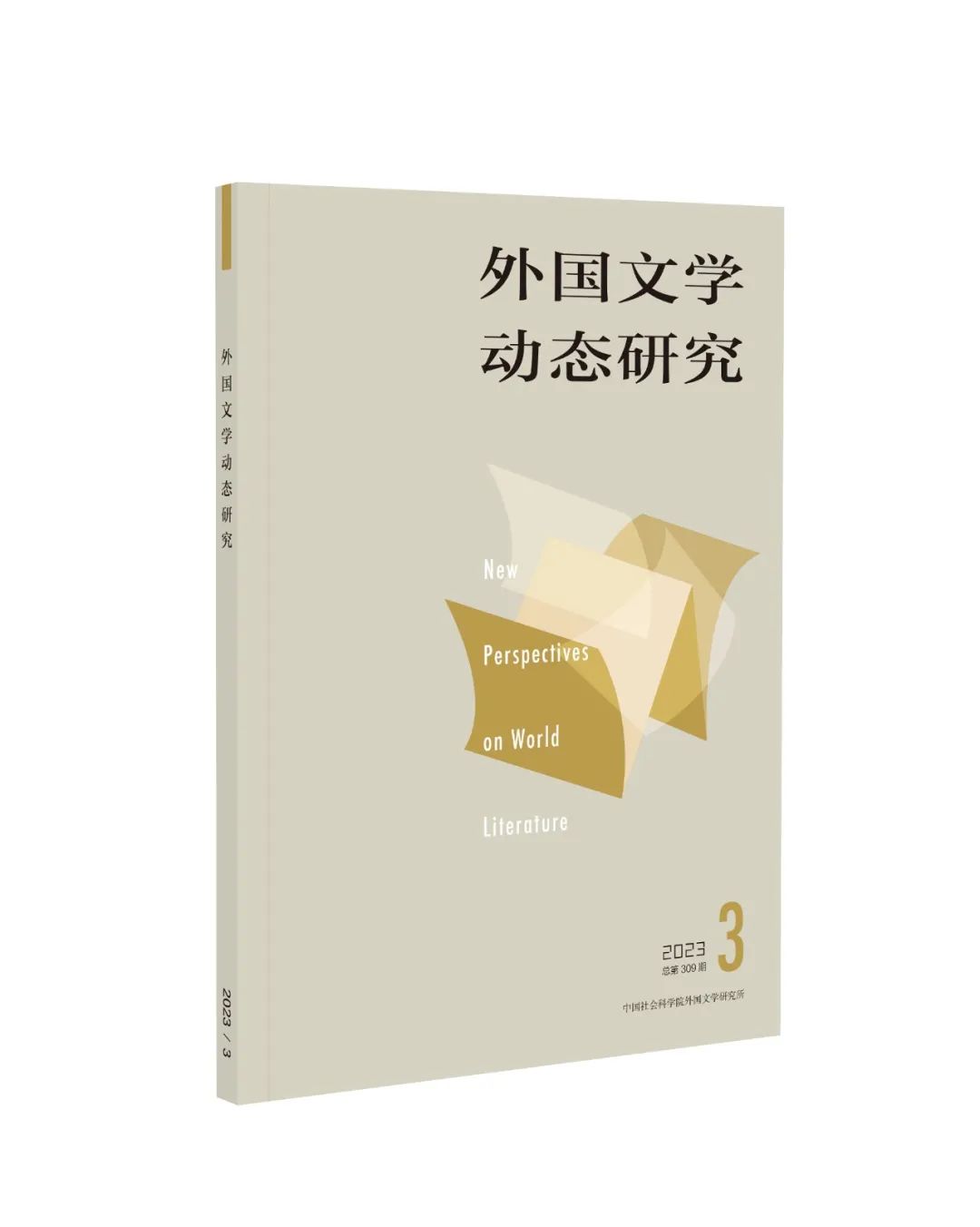作家研究丨个体的自我塑造与流动的民族性——从塞巴斯蒂安·巴里《无尽岁月》看爱尔兰性的发展变化
郭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爱尔兰文学。
内容提要
塞巴斯蒂安·巴里的小说《无尽岁月》以19世纪40年代大批爱尔兰人在大饥荒后移民美国为起点,结合家族秘史、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讲述一个在美国经历了印第安人战争和内战的爱尔兰人托马斯·麦克纳尔蒂的成长和挣扎。托马斯身上既有与爱尔兰人的刻板印象相契合的行为和品质,又有不见容于其所处时代男性身份成规的特征,寄寓了巴里对爱尔兰民族特性的理解。本文通过对托马斯人格中种种矛盾对立之处的分析,探讨巴里如何立足当下的意识形态话语为其对爱尔兰性的想象寻找历史根源。通过叙述主人公的成长与变化,巴里将流动的、建构中的民族性投射到这一象征性人物的自我重构中,试图在变动的爱尔兰性中寻找连续性。
关键词
《无尽岁月》 个体成长 自我塑造 爱尔兰性

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1955—)是当代最为学界和读者关注的爱尔兰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之一。他的《无尽岁月》(Days Without End,2016)是“麦克纳尔蒂家族”系列故事中的新作,让巴里第二次获得司各特历史小说奖。这部小说继续从家族秘史和祖辈经历出发,叙述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的个人命运,揭示记忆在个人身份建构中的作用,以跨文化的视角塑造了一个在美国挣扎求存的爱尔兰人。小说以自传的形式展开,人到中年的托马斯·麦克纳尔蒂回忆了十三岁以来的人生经历:目睹家人死于大饥荒后,幸存下来的托马斯乘船来到加拿大,随后到了美国,与有印第安血统的约翰·科尔相遇,两人四处游历,在密苏里州的达格斯维尔(Daggsville)矿区酒吧从事过男扮女装的舞者工作,参加了印第安人战争以及美国内战,告别战场后,他们来到战友林吉·梅根在田纳西州的农场生活。托马斯的遭遇既特殊又一般,特殊在于他拥有多重身份,他是同性恋,有“异装癖”,还做了逃兵;一般在于他从爱情与战场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战争的残酷,这一个体经历在移民与士兵中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小说以真实历史为背景,但在人物设定和情节安排上却有许多与时代不符之处,值得深思。首先,托马斯和约翰之间的同性感情自然且坚定,周围的人包括他们的战友和上级也默许了他们的感情,没有对两人的关系表现出敌意或排斥。在“同性恋”还没有被科学地认识并被合法化的年代,在崇尚个人主义和男性气概的西进运动和残酷的战争中,托马斯的性向与主流性别标准格格不入,但却能安然无恙甚至能与爱人结婚,这使他的经历显得格外美好。其次,托马斯和约翰结伴而行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扮作女性在酒吧与矿工跳舞。托马斯比约翰更享受性别身份的转换,他穿上女孩的衣服后感到“自己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人,一个全新的女孩。脱胎换骨自由无羁,就像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被解放的那些奴隶”。离开军队时,他们收养了印第安苏族女孩,为其取名薇诺娜,最后,一对同性爱人和一个少数族裔女孩组建的家庭回到农场,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些情节安排有何深意?托马斯的“异装癖”,或者说他从舞者工作中获得的对自己性向的认知,与其士兵身份是否有矛盾和断裂之处?从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变成印第安人的加害者,这一身份转换是否造成了托马斯内心的不安?收养行为和田园生活是否是他安抚良心的尝试?在可信的历史背景下,巴里塑造这样理想化的人物经历意欲何为?

塞巴斯蒂安·巴里与《无尽岁月》,图片源自Yand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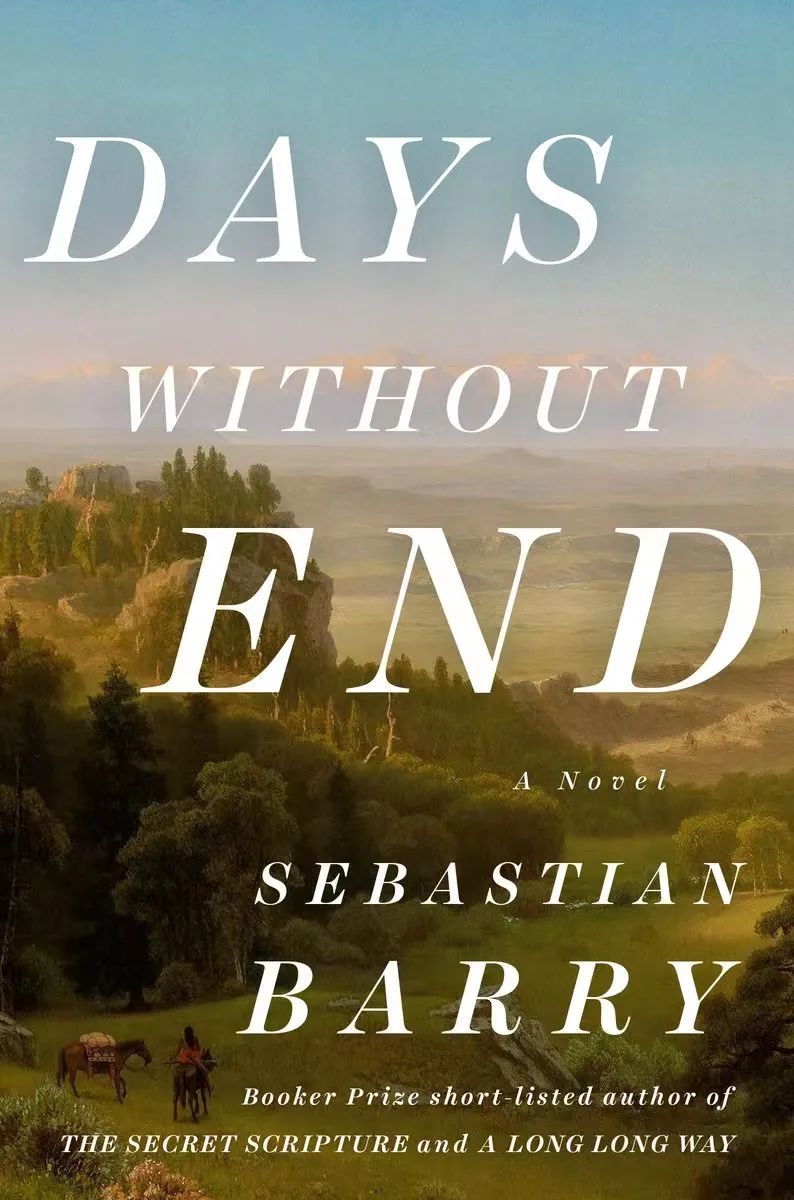
一
性少数者的个体重塑与作家的创作意图
小说序言引用了美国音乐家、作曲家约翰·马蒂亚斯(John Mathias)的歌词“我见行人,衣衫褴褛,疲惫不已”。托马斯的人生恰如其词,永远步履蹒跚,总是在路上。他经历过多次危及生命的打击,但每次都能战胜困难幸存下来。对于极端情况对人格的破坏,托马斯在加拿大流浪时就有清楚的认识。他说,“饥荒会夺走人的所有。我们曾拥有的都化为乌有。曾经的言谈、音乐、斯莱戈、故事、未来和过去,统统变成非常类似动物排泄物的东西”。于是,托马斯对爱尔兰的一切从来不愿谈论太多,他成了一个只向明天看的人,一个乐观主义者。刻意藏起的过往恰恰证明太过沉重的创伤是不可言说的,过去遥不可及,他必须在异国他乡寻找新的认同,约翰的出现恰到好处地提供了机会。两人相遇相知的过程非常自然,带着命定的意味,托马斯回忆道,这是一次“奇异但又命中注定的相遇。是一种幸运”。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不怀敌意又和他一样一无所有的人,自我与他人重新建立起有意义的、积极的关系,是托马斯在个人价值被饥荒和流浪剥夺后重新获得人的尊严的开始。
当原本形塑个体身份的体制、文化无法发挥作用时,个体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建构,托马斯在爱情和男扮女装的工作中发现了全新的自我。巴里没有详述托马斯和约翰是如何坠入爱河的,只是不断描述两人的亲密:他们夜间相拥入眠;他们规划战争结束后的游历计划;他们暂别战场后收养了薇诺娜并像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在光线昏暗的教堂里,在视力不济的神父注视下,穿着连衣裙的托马斯临时更名“托马西娜”,与约翰完成了结婚仪式。从托马斯的视角来看,他与约翰的感情是自然生长、真挚坚定的,两人之间有无需言语就能理解彼此心思和意图的默契,他对约翰有与生俱来的信任感,“从不觉得约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他根本发现不了”。虽说巴里对二人性向的交代因铺垫不足而稍显突兀,但二人的感情毋庸置疑是真挚的,是在并肩厮杀中积累下来的,是在共同经历营地洪水、补给未到饥荒蔓延和悲惨的战俘生活等种种磨难后日渐稳固的。托马斯的异装倾向也体现了性别意识的觉醒,在农场安家后,穿女装对于托马斯和他周围的人而言已经成了一种习以为常,以至于农场的自由黑人丁尼生见到穿着女装的托马斯会像绅士一样脱帽致意,礼貌地称呼他为女士。作为异性恋者,巴里对同性恋的刻画灵感很大部分来自对儿子与其同性恋人日常相处的观察,或许因为儿子曾和他谈起处境艰难的男同性恋会将异装作为一种赋权方式,所以才有了托马斯这样一个虚构人物。
从性向与性别的角度看,托马斯通过主动的选择完全重构了自己的身份。爱尔兰的一切似乎都与他再无瓜葛,作为男性的认知也随棺材船的起航留在了斯莱戈,他发自内心地接受了自己生而为男性,逐渐成长为女性的身份转变,他不再是儿子、弟弟,而是母亲和妻子。然而,他又是矛盾的。他同情印第安人,惊叹于他们的高贵,赞美他们在饥荒中帮助美国骑兵渡过难关的慷慨,但在毁灭他们的时候却又毫不犹豫。他像母亲一样呵护关爱薇诺娜,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薇诺娜之所以无家可归,来到美国营地生活,接受尼尔上校妻子的美国式教育,并逐渐失去与印第安文化的联系,罪魁祸首就是他们这些骑兵。托马斯甚至想,薇诺娜如果要为家人报仇并在半夜割断他和约翰的喉咙也是有正当理由的。在内心的斗争中,托马斯的主体意识逐渐成形,他找回了在饥荒、流浪、战争中迷失的人性,作为一个重生的新人融入了美国社会。
诚然,不同时代都有同性恋者与异装爱好者,然而,并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宽容不服从既定性别角色的人。历史学家彼得·博格以1850至1920年间美国边疆和西部人们的异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发现异装现象不仅普遍,甚至是西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人异装是出于对生理性别的叛逆心理,有的则是为了职业发展,异装者通常都有同性性行为。这一事实被刻意掩盖,原因在于随着现代性别观念的发展,人们在怀旧情绪中为西部塑造了阳刚硬汉的刻板形象,与同性恋相关的异装历史便被驱逐到阴影中了。博格告诉我们,一旦异装者对性别常规的挑战暴露在日光之下,就会在职场受挫,被社会排挤,被媒体妖魔化,因行为不端被逮捕、审判。从当时的地方小报来看,人们对异装现象和同性恋人群的关注主要出于猎奇,也混杂着鄙视与恐惧。
巴里通过托马斯这个人物所表达的,是对同性恋和异装现象背后个体生存的关切。托马斯在人生的重要节点面对的都是单选题:不离开爱尔兰就会饿死;扮女孩在酒吧与矿工跳舞是为了生存;屠杀印第安人以及参与美国内战还是为了生计,并非出于种族歧视或是为了解放黑人的崇高理想。可以说,整部小说的主旋律就是个体如何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之和解。小说表现出的积极、乐观与爱尔兰的发展有关。21世纪见证了爱尔兰的飞速变化,2015年爱尔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全民公投的形式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的国家,法案的通过无疑表现出当代爱尔兰追求文化多元、开放的姿态。巴里十分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他在《爱尔兰时报》上发表公开信号召人们尊重不同群体拥有合法婚姻的平等权利,《无尽岁月》这部“致爱子托比”的小说显然也是为了表达对儿子的支持与父爱。由此可以推断,巴里在小说中寄托了对一个宽容友好的社会的理想,托马斯的经历与其所处时代主流并不相符,却提供了一次修正误解、消解压迫、暴力的机会。可以说,托马斯的好运是作家有意安排的结果,透露着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善良期许。
伊格尔顿,图片源自Yandex
伊格尔顿指出:“文学作品不是神秘的灵感的产物,也不是简单地按照作者的心理状态就能说明的。它们是知觉的形式,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它们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或意识形态有关。而那种意识形态又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意识形态是“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文学可以反映意识形态,也可以突破甚至改造意识形态。21世纪的爱尔兰是剧变之地,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女性堕胎权公投相继通过意味着当下以政治正确为表征的性别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无尽岁月》对托马斯人生的理想化虚构或许有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嫌疑,但以文学方式宣传这一意识形态也是希望更多人能乘上变局的东风,为当下的潮流助力。
二
怪异主体与隐含的民族性话语
“爱尔兰性”几乎是每位爱尔兰作家在创作中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即使是像王尔德、乔伊斯、贝克特这样身份归属存疑的作家,也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爱尔兰民族特性的思考,巴里同样不会对这个话题无动于衷。流浪他乡的人会倾向于建构全新的身份,闭口不谈过去,不想触及祖国文化、历史、传统等可以定义自己身份归属的问题,托马斯也不例外,他在与美国社会的互动中思考自己所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他身上的爱尔兰属性,有些被保留下来,有些则被有意搁置,正是在挑选和重建的过程中,他的自我意识得以彰显。
随着叙事不断推进,读者不难发现,虽然这个在美国成长起来的自我看似与爱尔兰关系不大,但无论托马斯如何回避,他在斯莱戈亲历的灾难以及亲人亡魂都是隐形的在场,作为幸存者的内疚感和故乡文化的影响在今后的岁月里成了幽灵和保护神,不时出现。托马斯和约翰曾带薇诺娜投奔努尼先生,以表演默剧谋生,托马斯依然扮作女性,要在台上和约翰上演一段亲密的接触。首次上演前,在灯光的照射下,极度紧张的托马斯想起了在爱尔兰横尸路边的父亲。在“先捕他的马”要求用自己的侄女——也就是薇诺娜——来交换尼尔上校幸存的女儿时,托马斯悲从中来,心情复杂:失去旧时战友的悲痛惋惜、对战争中的死者和被害的尼尔夫人的哀悼,还有意识深处对斯莱戈去世多年的家人的怀念。对托马斯来说,斯莱戈是个不能被轻易提起的词,与故乡有关的一切不是死亡就是衰败:“漂浮在眼前的是母亲肮脏的衣物。被死神毁掉的姐姐的围裙。她们冰冷瘦削的脸庞。在纵深的记忆里,父亲像是一抹黄油,一个污点。他的黑色高礼帽像个压坏了的手风琴。”托马斯拉回思绪,他知道“先捕他的马”是杀死尼尔太太的凶手,但酋长是在报复,因为美国骑兵杀死了他的妻儿,摧毁了他的家园,薇诺娜愿意交换是因为尼尔太太曾善待她。托马斯收养了薇诺娜,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但他心里明白,薇诺娜并不是他真正的女儿。那么她如今是美国人还是印第安人?薇诺娜看似在两个世界里游刃有余,实则夹在两种文化之间,在两个阵营中都没有归属感,就和如今的自己一样。带薇诺娜离开营地后,托马斯在南下的火车上继续对两个世界的思考,他想,他之所以会相信自己穿上女装后就是女人,是因为在目睹姐姐死后,他夺走了姐姐的运气,姐姐则悄悄溜进自己的身体,在里面筑了巢。火车途经圣路易斯时,托马斯看着战火中的断壁残垣,想到了自己的身份归属:一边是解放了的黑人奴隶,一边是荒凉的村庄,自己现在是美国人了吗?他也不能确定。
在北美生活了二十多年,托马斯仍然没有完全融入这片土地。他是大饥荒后来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中的一员,他在战争中遇到的同胞,无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还是作为敌人的对手,都有对过去三缄其口的倾向。托马斯注意到,他见到的爱尔兰人都和他一样是矛盾的:“他可以是装扮成恶魔的天使,也可以是装扮成天使的恶魔。但不管是哪种情形,在和爱尔兰人交流的时候你不是在跟一个人说话。他可以尽己所能帮助你,也可以把你气到七窍生烟。一位爱尔兰骑兵可以是战场上最英勇的战士,也可以是胆怯的懦夫。”在托马斯看来,每个爱尔兰人都有两副面孔。他们在美国军队中,被制服和集体生活赋予了某种新的身份,这一身份与他们原本的爱尔兰身份相去甚远,然而在某些时刻,爱尔兰的根还是会露出来。内战中两个阵营里的爱尔兰士兵会在冲锋时用盖尔语喊叫,托马斯与他的爱尔兰裔战友们喝酒时和“舞台上的爱尔兰人”一模一样——粗鲁、醉酒,还喋喋不休。通过对刻板印象的操控,巴里似乎在强调爱尔兰人表现出的民族特性。
诚然,“爱尔兰性”向来是一个想象大于现实、偶然多于自然的概念,是殖民话语的一部分,也是爱尔兰人自我建构的结果。在民族主义运动时期,爱尔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将英国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前的凯尔特文化或者是盖尔文化作为爱尔兰民族性的根基,试图从古老传统中汲取营养,以此构建现代爱尔兰的自我认同。1937年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并颁布自己的宪法,宪法肯定了从传统中寻找立国之本的合法性,为爱尔兰民族特性设计了三大支柱——与工业化的英国相对立的重农主义、与新教对立的天主教、将女性权利限制在家庭内部的父权制。然而,从爱尔兰制定第一个经济发展计划、申请加入欧共体开始,爱尔兰性赖以建构的保守主义政治话语土壤就开始松动,一种立足当下、努力让爱尔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话语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自由、开放、多元成为爱尔兰社会的主旋律。爱尔兰文学评论家谢默斯·迪恩主编的《爱尔兰文学费尔顿选集》就是试图聚焦微观叙事,通过文学与社会对话,展现爱尔兰身份的包容性。随着天主教教会势力的式微、工业化的扩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爱尔兰民族主义不断被“祛魅”,爱尔兰性早已不是铁板一块,描述爱尔兰人的形容词也越来越丰富鲜活。
谢默斯·迪恩,图片源自Yandex
托马斯与爱尔兰民族性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相互背离的方面:一方面是他对过往的沉默、对爱尔兰特性的掩盖,他的同性恋倾向及异装癖更与天主教对性向及性别行为设置的规范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是他的多思、细腻和女性化特质,斯莱戈在他内心深处留下的印记、他对家人的愧疚永远都在影响他,他身体里住着的是凯尔特人的灵魂。他和约翰、薇诺娜组成的家庭因为他主动的女性化具备了传统核心家庭的特征,而他之所以能对印第安人产生共情也是由于爱尔兰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相似经历。美国在托马斯眼里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他离开爱尔兰是出于无奈,而不是把美洲大陆视为应许之地。对饥荒的恐惧深入托马斯的骨髓,在战争期间,这恐惧的每一次重演都提醒着他的来处。托马斯离开战场后回归田园的选择也耐人寻味。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最后又过上了爱尔兰西部的农村生活。托马斯一家的主仆关系是建立在团体互助基础上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这也是爱尔兰农村生活模式的延续。小说结尾处,托马斯为解救薇诺娜,不得已杀掉战友史达林·卡尔顿并当了逃兵,被军事法庭判处一百天的劳役,每天的工作是将大石块碎成小石块。这与爱尔兰大饥荒期间英国政府为纾解农村地区食物短缺、绝大多数家庭没有收入无法生存的悲惨状况而推行的救济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
巴里将托马斯放置在万般无奈的环境之中,在他的成长轨迹和爱尔兰的经历的沧海桑田之间建构了一种象征性的等同,最终指向的是爱尔兰性的发展变化。托马斯的经历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成长,他在饥荒和杀戮等创伤性事件后的自我疗愈与人格重建映射出从废墟中重生的爱尔兰,他的特殊性向以及周围人的反应也不仅仅是为了呈现一个怪异的主人公,更象征着爱尔兰民族吐故纳新、自我成长的能力,是巴里在当代背景下,对民族国家在经历殖民、内战、后现代异质文化挑战后应如何重塑自我的思考和想象。巴里生活的爱尔兰仍处在变动之中,许多原本坚固的上层建筑,比如天主教教会,不断受到冲击,伴随“报复性”解放到来的是对民族何去何从的思考,这种思考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也影响着文学创作。巴里眼中变化发展着的爱尔兰,对边缘化和少数群体持包容态度的爱尔兰,都被投射到托马斯身上,通过放大托马斯的好运,巴里表达了对变化中的爱尔兰性的省思,或许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披着美国外衣的爱尔兰故事。
萧伯纳,图片源自Yandex
结 语
巴里之所以在美国地图上绘制托马斯十三岁以后的人生轨迹,或许与萧伯纳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中对彼得·基根神父的考虑相似。基根神父为了寻找在爱尔兰不曾见过的奇迹而到罗马、索邦、牛津、耶路撒冷游历,他出走半生,归来后才发现,这些奇迹在爱尔兰也有,只是他一直视而不见。通过对托马斯这个特殊主体的刻画,《无尽岁月》表达了巴里对变动中的爱尔兰社会、爱尔兰性的关切。对于他来说,美国是一片让改变发生的沃土,是用以重新定义爱尔兰性的实验室,为他提供了“站在外面好好观察自家房子面貌的绝佳视角”。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3期“作家研究”专栏,责任编辑龚璇,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艾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雨璇 终审:文安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