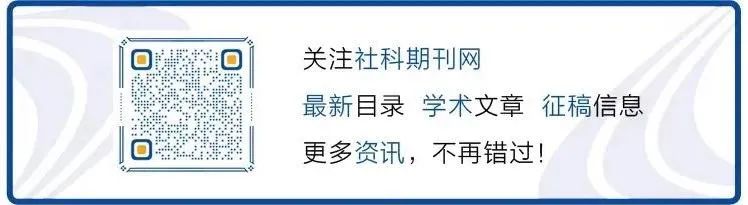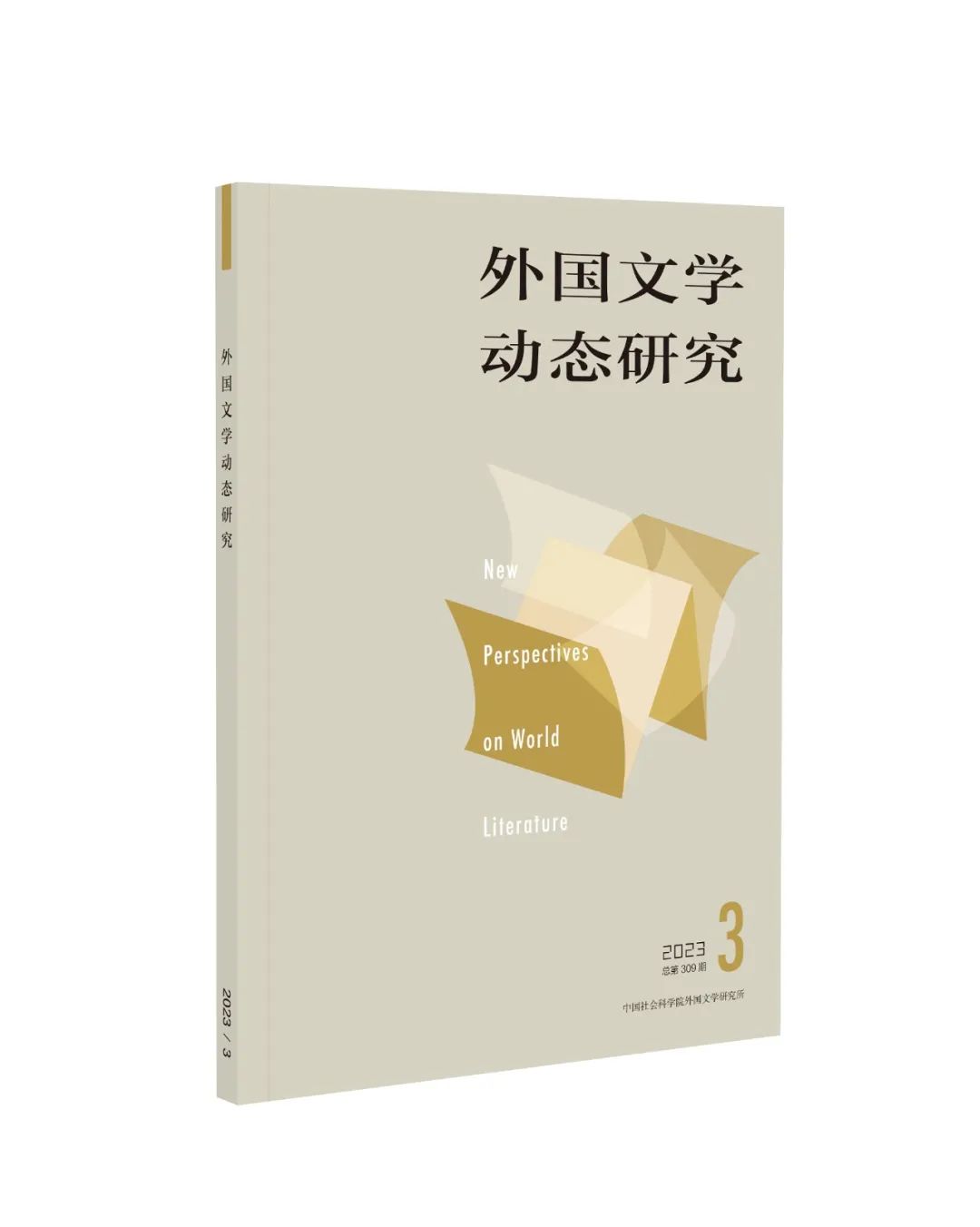新作评论丨文学作为一种试验场:克鲁萨诺夫小说《天使咬伤》中的欧亚帝国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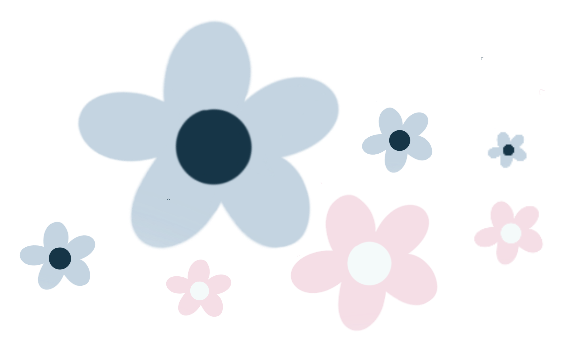
孔俐颖,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俄罗斯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边界地带的求索:佩列文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危机》(载《当代外国文学》2023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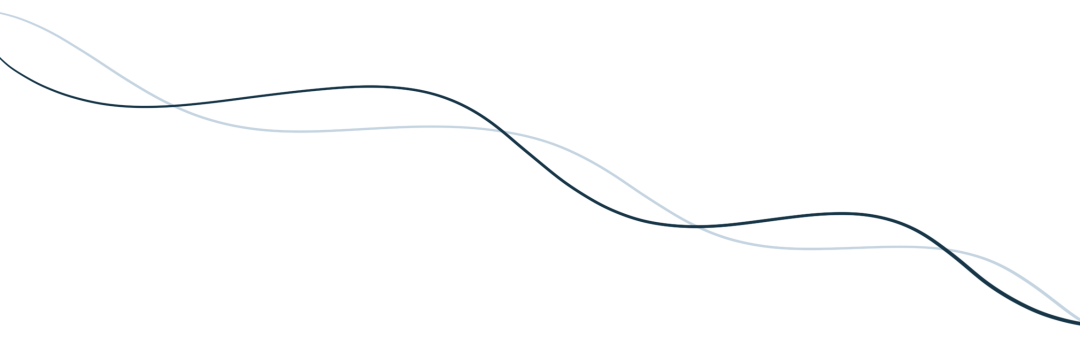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和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取向的大讨论再度兴起,有不少人开始怀念昔日超级大国逝去的地理范围和政治权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此背景下,号召在东西方之间折中,奉行强国复兴思想的“新欧亚主义”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末最受瞩目的社会思潮之一,在文学界表现为帝国怀旧浪潮的兴起。作为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帕维尔·克鲁萨诺夫以创作回应现实生活和千百年来困扰俄罗斯的东西方归属问题。在小说《天使咬伤》中,克鲁萨诺夫以后现代视角展开瑰丽的想象,以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大地为底色,借助历史、神话、传说等神秘元素,融合俄罗斯精神传统中的弥赛亚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因子,擘画出一幅激荡人心的欧亚帝国画卷。
关键词 克鲁萨诺夫 东西方问题 新欧亚主义 中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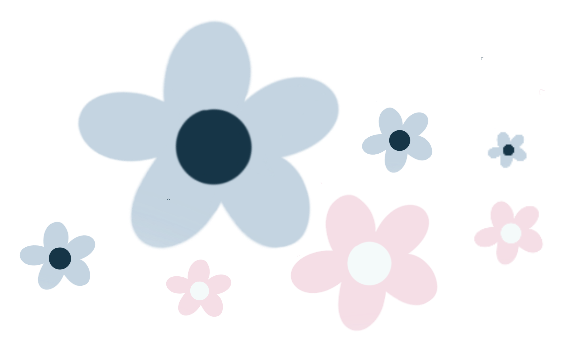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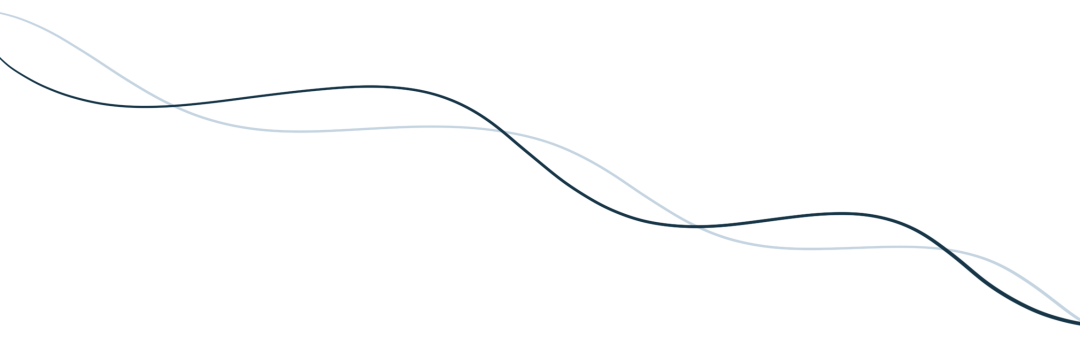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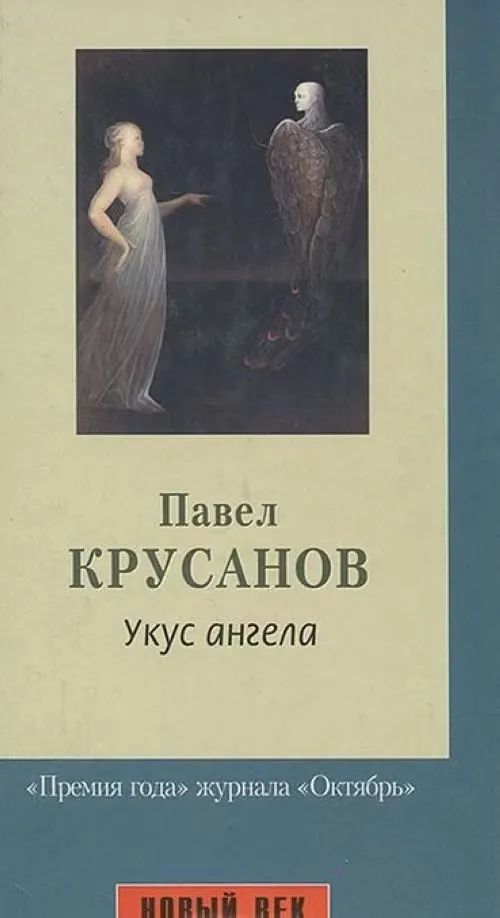

《天使咬伤》和帕维尔·克鲁萨诺夫
图片源自Yandex
帕维尔·克鲁萨诺夫(Павел Крусанов, 1961—)是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记者、政论家、出版社总编辑,主要活跃于圣彼得堡。他自1989年开始从事编辑工作,1992年加入圣彼得堡作家协会,2001年参与创立了与新欧亚主义思想较为相近的“彼得堡原教旨主义”(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ундаменитализм)文学团体。著名文学评论家В.托波罗夫称克鲁萨诺夫、С.诺索夫、В.纳扎罗夫,А.谢卡茨基等“彼得堡原教旨主义者”为“新谢拉皮翁兄弟”。克鲁萨诺夫文学功底深厚,先后出版作品数十部,两次获《十月》杂志奖,并入围全国畅销书奖、大书奖等,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作家最富盛名的代表作《天使咬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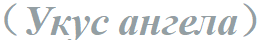 初刊于1999年(《十月》杂志第12期),次年出版单行本。该小说于2003年获《十月》杂志奖,并入选《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系列,2016年推出中译本。如今距小说首次出版已逾二十年,期间多次再版,在俄罗斯和西方学界依然持续受到关注、研究和阐释,俄罗斯学界曾在小说出版二十周年之际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可见其不同凡响的魅力。
初刊于1999年(《十月》杂志第12期),次年出版单行本。该小说于2003年获《十月》杂志奖,并入选《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系列,2016年推出中译本。如今距小说首次出版已逾二十年,期间多次再版,在俄罗斯和西方学界依然持续受到关注、研究和阐释,俄罗斯学界曾在小说出版二十周年之际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可见其不同凡响的魅力。
本文将从对小说《天使咬伤》中“欧亚帝国想象”的研究出发,揭示这一想象的深厚历史渊源,并紧扣当下文化政治语境,审视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思潮在作家创作中的具体展现。
一、 新欧亚主义思潮与克鲁萨诺夫的创作
克鲁萨诺夫的早期创作深受威廉·福克纳的影响,同时他也酷爱法国的葛农、埃佛拉以及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昂季耶夫、丹尼列夫斯基等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对古典欧亚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列夫·古米廖夫等人的学说如数家珍,以此奠定了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倾向。随着创作进入成熟期,克鲁萨诺夫开始明显受到新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
新欧亚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俄罗斯广为流行,这是对20世纪初欧亚主义思潮的复兴。由此看来,两者均兴起于内忧外患的时代。欧亚主义的出现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内外矛盾交织以及蓬勃发展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的综合影响,而新欧亚主义的诞生则与苏联解体后西化浪潮席卷俄罗斯、俄罗斯政府推行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和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社会矛盾激化、国际地位下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等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面临剧烈的社会变革,两代欧亚主义者均延续了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方问题的思考,采用了与“斯拉夫派”较为接近的主张,都强调立足本国土壤、走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以东正教为基础构建思想体系,反对欧洲中心论,也反对将民族主义视为构建俄国的唯一因素,主张确保欧亚双向平衡,构建欧亚-俄罗斯式的民族融汇的发展空间。欧亚主义学说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侨民知识分子阶层,由流亡海外的俄国思想家特鲁别茨科伊、阿列克谢耶夫、萨维茨基等人提出,几经分化后逐步发展为后来的古典欧亚主义思想,涵盖了历史、地理、文化、哲学、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在维·伊万诺夫、勃洛克、别雷以及阿·托尔斯泰、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等作家创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新欧亚主义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典欧亚主义的意识形态信条,尤其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民族起源“元气说”以及民族互动理论,较为侧重民族学、历史学、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关系等方面,突出国家主义和强国论思想,提倡在东正教俄罗斯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克鲁萨诺夫本人与“强国思想”的代表人物杜金私交甚笃,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密切参与政治生活的“彼得堡原教旨主义”文学团体并与普罗汉诺夫、贝科夫等作家一道在“帝国主义文学”中感性言说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关注现实生活的创作传统。
《天使咬伤》是克鲁萨诺夫在1999至2005年创作的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外两部为《钟声》和《美国小洞》),欧亚主义元素在三部曲中得到了不同的演绎。其中,《钟声》讲述了诺鲁什金家族几代人的生活,他们是象征纯洁力量的塔楼的捍卫者,与邪恶力量抗争,防止其进入塔楼内,并肩负着在关键时刻敲响钟声,唤醒俄罗斯人民,拯救俄罗斯命运的责任,小说还表达了欧亚主义者对古老贵族庄园生活的眷恋,创造了一个关于俄罗斯帝国历史的神话。《美国小洞》通过主人公谢尔盖·库列欣团体设法挑唆北美人在美国挖掘一个类似科拉深井的超深洞,从而实现不费一兵一卒,成功摧毁美国并复兴俄罗斯的计划,践行了杜金的反大西洋主义言论和“强国论”思想。欧亚主义元素在《天使咬伤》中则得到了最为突出的体现,克鲁萨诺夫以文学作为试验场,将欧亚主义神话作为编织民族叙事的材料,将血缘作为构建身份认同的纽带,并通过西方的负面“他者”形象映射民族意识,从而塑造了一位雄韬伟略的中俄混血沙皇形象,在想象中构建了一个充满弥赛亚意识的欧亚帝国,重塑了当代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最终达到缓和社会危机的目的。
二、《天使咬伤》中的欧亚帝国想象
《天使咬伤》被称为后现代魔幻主义长篇小说,呈现的是一个想象中的欧亚帝国。小说以沙皇伊万登基为基础虚构时间线,无法与沙俄帝国和事实上以军事帝国形态呈现的苏联对应。小说中沙皇带领远征军作战,南并土耳其,西控东中欧,直捣奥地利边境,其铁骑踏遍北非,同时觊觎北美,参战国家均采用真实国名,但那些栩栩如生的战争场景却均为虚构,与卫国战争、世界大战等真实历史事件无关,我们甚至无从得知小说讲述的是过去还是未来。与此同时,文中还充斥着一系列梦境、幻想、象征、直觉、魔鬼、黑暗、混沌、占星术、末世论等非理性元素,令人不知何处是真实,何处是虚幻。事实上,克鲁萨诺夫以后现代手段对时空进行解构,将时间打乱,对空间做模糊处理,旨在突破外部客观世界的框架,描绘想象中的世界。
(一)神话:编织民族叙事的材料
别尔嘉耶夫在《历史的意义》中指出:“历史不是一套客观的经验事实;历史是一个神话。神话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的;但是一种有别于经验事实的现实。”克鲁萨诺夫深谙历史与神话之间的辩证关系,以神话的方式建构历史,抒发对俄罗斯空间和历史一致性的幻想,在神话中言说和反思民族历史命运,从而为编织民族叙事、构建身份认同提供了绝佳的材料。
小说中的帝国植根于欧亚主义神话空间。关于帝国,奉行欧亚主义历史观的维尔纳茨基如是表述:“伟大的帝国是欧亚大陆稳定的国家和政权形式。斯堪的纳维亚人、匈奴人和蒙古人建立的帝国正是如此,莫斯科帝国和全俄帝国也一样。然而,只有当统治精英没有脱离人民,内部的地下水滋养了政权时,欧亚大陆的帝国才是强大而有活力的。”克鲁萨诺夫笔下的主人公伊万是一位来自民间的沙皇,他和姐姐塔尼娅的父亲尼基塔是俄罗斯近卫军军官,母亲是出自“礼仪之邦”的中国女人张三妹,欧亚两种文化因子在姐弟俩身上交汇,这也象征着俄罗斯与亚洲之间的联系古已有之,源远流长,且俄罗斯自身的亚洲属性根深蒂固,符合欧亚主义者的观点。伊万出生后,父亲因在战争中负伤、流血过多而去世,母亲则在生下他后便刎颈自尽,从此伊万成为一名遗孤。这种身份设定富有悲剧英雄色彩,为其自立自强、坚毅果敢的性格形成和成就一番霸业奠定了基础,其魄力堪比成吉思汗与伊凡雷帝。母亲死后化作一只欧洲鳇,象征了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交融,同时也富有东方禅宗思想中“灵魂转世”的意味。父母去世后,伊万和姐姐塔尼娅被委托给本县首席贵族抚养,这位首席贵族温厚善良、通情达理,且有些怀旧情结。姐弟俩和首席贵族之子彼得在充满原生家庭幸福气息的涅基塔耶夫庄园长大。这座位于外省的神话般的庄园是俄罗斯的象征,与让塔尼娅沾染上浪荡风气的欧化之都彼得堡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坐落于高加索山地的阿乌尔,则与外省庄园又构成了俄罗斯与东方的二元对立。三者共同构成了俄罗斯作为中间性的西方-俄罗斯-东方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俄罗斯作家都具有高加索情结,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等。在俄罗斯文学中,高加索早已凝聚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想象,是富有异域风情的东方形象,象征着原始和野性。正是在阿乌尔反抗叛军的战斗中,伊万被叛乱者和山民冠以具有魔鬼色彩的“伊万-撒旦”称号,颇有莱蒙托夫笔下“恶魔”形象(非贬义)的影子。伊万与彼得之间的关系十分耐人寻味,伊万被送入武备学校学习后,很快凭借天赋异禀和刻苦训练入选精英连。彼得则热爱哲学和文学,思辨能力强。两人一文一武,在性格和能力上互补,后来成为帝国事业的同路人,他们之间的关系隐喻古希腊神话中的双生意象,构成了一组镜像凝视的“同貌人”体系,同时象征着文明与自然以及重理性思辨的欧洲人和重直觉感官的亚洲人两种身份属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也是俄罗斯内部自身东西方二重性的表征。后来,伊万在武备连遇到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一名旧教派信徒,他可以看透伊万的想法,俨然上帝的化身。老人正在寻找行过登基涂油仪式的君主,要把火炬人嘱咐的最后一位君主的挂件交给他。他说道:“君主一定是带有标记的。只是普通人的眼睛看不见……就像天使吻了他一样。但这个吻不是悲伤的,而是充满激情的,带着咬伤的。何况我手里还有挂件:它会准确指出秘密君主是谁,君主越近,挂件就越热。”这段话点明了小说标题“天使咬伤”的来由,并以神话形式说明了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的弥赛亚意识。老人发现,伊万的靠近使太阳形状的金色挂件变得十分烫手,而太阳在神话传说中象征荣耀和权力,这为伊万成为下一任沙皇,即推动历史进程、影响俄罗斯国家命运的神选之人奠定了基础,也与新欧亚主义秉承东正教神圣使命、赋予俄罗斯率欧亚各民族拯救世界的使命主张相符。
与伊万的宿命论身世相对应,欧亚主义神话空间始终笼罩着浓厚的末世论色彩,这与欧亚主义学说诞生和复兴的时代所带给人们的末世感受一致。小说中充满了黑暗、阴影、雾气和水等常见意象。第七章标题《大洪水前夕——登基前半年》与圣彼得堡文化符号体系中的末世论神话“倒在水中的混沌”构成互文。在本章的开篇首次出现赫卡忒犬:“一股不可思议的罪孽之气在城市的各个街道上空游荡,渴望着化身现实。赫卡忒的梦,她面目狰狞的犬不易觉察地挤在现实世界的门槛边。”在希腊神话中,赫卡忒是掌管幽灵和魔法的女神,与月光、夜晚、灵魂、地狱、精灵、魔法和妖术等元素联系在一起。赫卡忒犬在小说尾声中重现,为了结束折磨人间的世界大战,伊万决定动用上帝赋予的权力放赫卡忒犬进入我们的世界,这一举动看似为后现代主义式的解构,旨在将一切化为虚空,其实不然。提及“虚空”,国内外学界通常认为是与克鲁萨诺夫同时期的俄罗斯作家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笔下重要主题。佩列文与克鲁萨诺夫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亲身经历苏联解体,均在作品中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的东西方母题,尝试为国家未来发展道路提供自己的思考。佩列文在《夏伯阳与虚空》《变者圣书》等多部小说中构建了独特的神话空间,以东方禅宗的精神性“虚空”抵抗西方物质文明的“虚空”,将历史、现实和人的存在均指向虚空,放下在东西方之间进行民族定位的执念,号召俄罗斯人以精神自由的姿态踏上新的历史道路。换言之,将“虚空”本身作为东西方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比之下,克鲁萨诺夫构造的欧亚主义神话空间并不止步于“虚空”,而是尝试有所突破。小说中提到,当代世界的危机不可逆转,混乱将是当代世界的最后一个词。“下决心理解混乱,有力量、毅力和勇气在那些在洪水面前惊惶不安的理智以及念着‘我们之后再来洪水’咒语的疯狂抗争的人们面前,果敢、高兴地向世界宣称:‘大洪水之后就是我们!’”由此可见,克鲁萨诺夫呼吁的是一种虚空之上的建构性力量,在这个层面上,作者“不会停留在任何历史经验上,而是直接向往永恒,克服‘尘世的重力’,因为它忠于终极知识——对尘世历史的有限性的认识。在这条路上,甚至连帝国都不能成为目标”。

佩列文,图片源自Yandex
(二)血缘:构建身份认同的纽带
《天使咬伤》的故事情节主要发生在圣彼得堡。正如学者莫里古诺夫所说,从性别意义上,彼得堡具有男性城市的特征。他认为:“彼得堡自称为堡,并不完全偶然。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城市是男性的。”在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中,彼得堡呈现了如彼得大帝君临天下的威严、服从统一意志的“兵营”氛围,以及其欧洲风范等,这些都使其具有拯救者、父亲、新郎的象征意味,符合小说人物的身份设定。如前所述,伊万是俄罗斯军官尼基塔和中国女子张三妹所生。尼基塔是俄罗斯贵族之后,他的“一字胡很考究,向上拧着,他穿着浅绿色的制服,上面还有金线缝缀的肩章,显示出制服的主人是勇猛的布列斯克近卫军的一员”。张三妹的祖先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子,她“父亲是一个平民,在哈巴罗夫斯克城边有一个鱼铺,因为有一手绝活儿名声远扬——他能把鲤鱼抛向空中,并且在空中就给鲤鱼开肠破肚,还不弄碎鱼子”。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的荣光,《庄子》中“庖丁解牛”的传统典故,对这些元素的运用都凸显了张三妹出身中国名门的身份属性。由此可见,伊万身上流淌着两大帝国的血脉,身份十分尊贵,验证了预言家所言:“一个可以引领人们穿越恐怖新世界的带路人会在俄罗斯的锤和中国的砧之间诞生。”这为他日后登基为沙皇埋下伏笔。小说中,伊万与亲姐姐塔尼娅自小互相爱慕,塔尼娅先是嫁给了童年玩伴、监护人之子彼得,后来成为伊万的情妇,并育有一子涅斯托尔。事实上,乱伦现象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神话,比如地母盖亚和天神乌兰诺斯(母子)、天神宙斯与女神赫拉(姐弟)之间的婚姻及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等等,象征着神性、超人力量以及强烈的自我意识,而在凡尘俗世中只有君主最接近神明,因而此处亦是对伊万高贵身份的暗示。塔尼娅的传奇身世也充满中国元素。其名字的谐音与中国历史朝代“唐”(Тан)十分相似,因而让母亲想到满地黄土的故乡和祖先的风云岁月,另外相较于只有俄文名的伊万,塔尼娅还拥有一个中文名——月面女神王梓嬁。书中写道:“伊万刚从车上下来,出现在房子的凉台上时,月面塔尼娅正坐在茶炊旁,纤纤玉指捏着菱形块的饼干喝着薄荷茶……”一位有着花容月貌的中国古典美人形象跃然纸上,与道教神话中的“月宫仙子”嫦娥形象相对应。但在性格上,塔尼娅却具有俄罗斯人热爱自由的习性,她年少在彼得堡习画,沾染了首都迷恋禁忌的浪荡习气。姐弟俩的结合,使塔尼娅如愿获得如赞颂汉武帝宠妃“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赞美。沙皇伊万的中俄混血身份和情感经历,预示着他所缔造的帝国是一个欧亚融汇的发展空间,与欧亚主义者所说“如果把我们周围的文化和生活元素相结合,我们不羞于承认自己是欧亚主义者”的观点相呼应。
《天使咬伤》里的中俄“混血”自然延伸至中俄两国关系上,小说总体上对待中国持较为正面的态度。彼得肯定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讽刺西方国家混淆文明和技术进步,对俄罗斯和中国片面理解:“现在热烈拥护自由的人十分胆怯,就如同敬畏他们片面理解的文化一样,这种胆怯来自于他们理性空间升起的一团团奇怪的雾气。否则他们凭什么顽固地把文明和技术进步混为一谈,还极其兴奋地称某个囚犯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文明国家,却说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有一千年历史的俄罗斯除了野蛮,什么都没有。”
克鲁萨诺夫还在小说中描述了许多虚构的世界大战场景。在小说开篇,俄罗斯帝国的主要对手是奥斯曼帝国、波兰和美国,伊万的父亲尼基塔正是俄罗斯远征军的一员。伊万登基后继续推行帝国扩张战略,在曼德海峡全歼英国-意大利混合分舰队,发动“白蚁”战役试图牵制美国,并向埃及、近东、波斯和锡斯坦等地多线作战。在小说中,中国始终以强大的帝国和俄罗斯盟友的形象出现。例如,彼得的白蚁战役计划里包含两个步骤:“一是把有色军武装起来,二是由非洲俄罗斯人组建教练军。中国盟友允诺在这一阶段由唐人街的第五纵队提供积极支持。”事实上,小说《天使咬伤》创作于20至21世纪之交,结合时代语境不难发现,文中的中俄关系极富隐喻色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失败,转而实行“全方位”外交政策,这与新欧亚主义在反思亲西派的大西洋主义造成被动局面后提出的政策东移并实现东西兼顾、全面发展“大东方战略”的战略主张异曲同工。在俄罗斯政府推行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中,中国始终是亚太政策的重点。2001年中俄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的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和国际地位下降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加。因此,这一时期俄罗斯小说中出现较多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并不奇怪,这些创作被誉为“智慧转型的东方转向”,以佩列文的《夏伯阳与虚空》( ,1996)、索罗金的《蓝油脂》(Голубое сало,1999)、霍利姆·王·扎伊奇克(彼得堡汉学家维亚·雷巴科夫和伊·阿利耶夫的笔名)的《欧亚交响曲》(
,1996)、索罗金的《蓝油脂》(Голубое сало,1999)、霍利姆·王·扎伊奇克(彼得堡汉学家维亚·雷巴科夫和伊·阿利耶夫的笔名)的《欧亚交响曲》( ,2000—2005)系列小说等为代表。我国学者刘亚丁认为,这种“被美化的乌托邦”形象是集体想象的产物,“源于对于1990年代之后俄罗斯社会失范行为的反思,是一种补偿心理”。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克鲁萨诺夫笔下富有中国元素的欧亚帝国亦可理解为一种借用异国情调、强大帝国根基的隐喻。
,2000—2005)系列小说等为代表。我国学者刘亚丁认为,这种“被美化的乌托邦”形象是集体想象的产物,“源于对于1990年代之后俄罗斯社会失范行为的反思,是一种补偿心理”。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克鲁萨诺夫笔下富有中国元素的欧亚帝国亦可理解为一种借用异国情调、强大帝国根基的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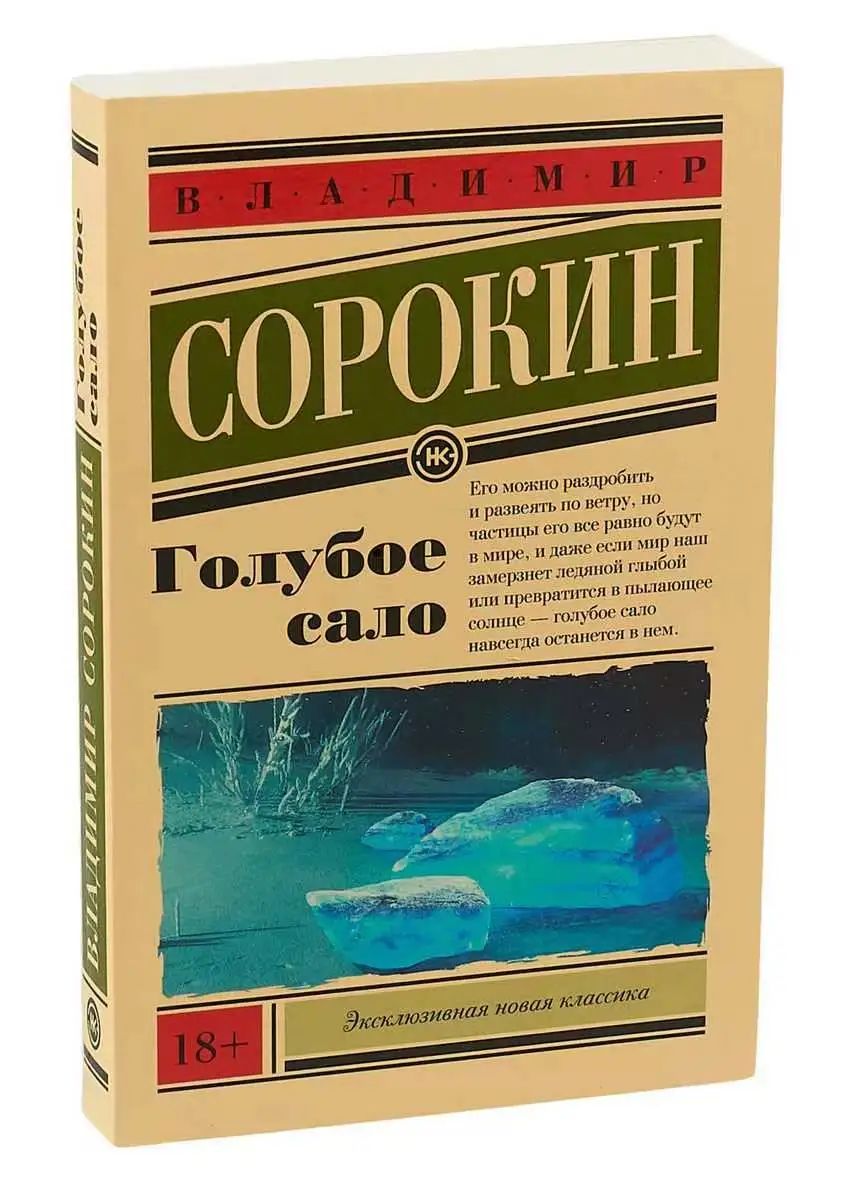

《蓝油脂》和索罗金,图片源自Yandex
(三)他者:映射民族意识的镜子
“他者”形象对自我认知是极为重要的参照,发现、假造他者并对其形象进行贬低和妖魔化,依据对立的他者来界定自我是文学作品民族主义表达的一个重要侧面。在小说《天使咬伤》中,作者以“他者”为镜,通过丑化“他者”形象,实现对帝国的自我美化,从而映射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小说中,首当其冲的“他者”,是“西方派”和“西方形象”。作者延续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论争这一传统母题。其中“西方派”以布雷林为首。布雷林有白化病,长相丑陋,颇具漫画色彩:“没有颜色的睫毛和眉毛连同大面积秃顶让他的一张脸看上去极其裸露,甚至让人想把这张脸盖上。”作为一位亲欧美派,布雷林极力鼓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热忱捍卫所谓的人类理智的合理性和胜利,因为处事圆滑、擅长趋炎附势而被称作“老滑头”。与之针锋相对的“斯拉夫派”主要由伊万、彼得、政客戈瓦洛夫等人组成。伊万和彼得自小在外省的涅基塔耶夫庄园长大,均由彼得的父亲列格科斯图波夫抚养成人。列格科斯图波夫有怀旧情结,常对家人说“我们从我不感兴趣的谈话对象美国人说起吧,他们不能引发我任何联想……”或“伟大的不列颠艺术家是由不列颠批评家想象出来的,他们认为应该如此”。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伊万和彼得自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伊万体格高大匀称,从武备士开始,一路升迁至将军、帝国总督、执政官、沙皇,“不仅没有打过一场败仗,也从未让自己的部队遭受过任何无谓的损失。他是个英雄,他的一句话可以拯救千万条生命,也可以让他们从此消失。从西伯利亚到马达加斯加,再到美洲——他的名字威震四方”。不难发现,沙皇伊万体现着尼采的“超人”哲学,即反抗平庸,并能够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改变世界。彼得是伊万的童年伙伴及其登基之路的得力助手,一直奉行帝国主义理念,在他看来,帝王是神通的大自然的化身,矗立在自己统治下的被圣化的宇宙和宇宙的反光镜中。彼得博览群书,擅长引经据典,总是能为沙皇伊万的种种举动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彼时布雷林和伊万同为执政官,为铲除伊万登基之路的阻碍,彼得编造了布雷林纠缠塔尼娅的谣言,成功激怒了伊万。布雷林像自由农民一样穿着肥大的裤子,有生之年第一次坐二等车厢仓皇出逃,他经由华沙逃往英国,接连给同胞写呼吁书,给欧洲各国元首写信请求庇护,但无人回应。最终,布雷林和他的残余势力均被歼灭。在小说中,美国一直以负面的西方形象存在,是俄罗斯的宿敌。为了对付美国,彼得曾献一计:用炼金术提取的黄金在第三帝国兑换美元,再用美元购买美国的土地、企业和各种媒体,引发通货膨胀,摧毁美国金融,之后买通媒体进行反战宣传,刺激种族、地区和宗教冲突,使“原本已经失去理智的美国人变得头脑更不正常”。事实上,小说中负面的西方“他者”形象在现实中也有迹可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及价值理念上实行“全盘西化”。然而,西方鼓吹的休克疗法无视俄罗斯自身的地缘条件、资源优势和历史文化传统,使俄罗斯社会陷入混乱。西方承诺向俄罗斯提供缓解危机的巨额贷款从未兑现,却设下贸易壁垒,阻挠俄罗斯参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同时,西方还用大众传媒抹黑俄罗斯,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新欧亚主义思潮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面对西方国家的打压,俄罗斯人民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君主带领他们走出困境。普京总统于2000年上台,给人民带来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当时恰逢小说《天使咬伤》出版,俄罗斯学者达尼尔金直言救世主般的沙皇形象正是普京的化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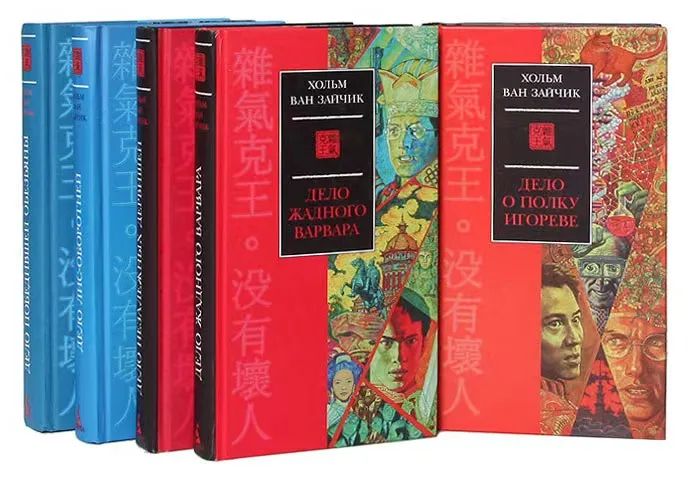
《欧亚交响曲》系列小说
图片源自Yandex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对待中国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肯定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中国文化典故信手拈来,体现出对中国美学的自觉接受,且将中国塑造为可以牵制美国的俄罗斯盟友,展现出中国强大、正面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却在中俄关系上视中国为可以美化民族自我的“他者”,文化误读现象在书中时有出现。以伊万的中俄混血出身为例,他的母亲张三妹跟随他的父亲尼基塔离家出走,夫妻二人按照东正教仪式举办婚礼,张三妹根据东正教历得名乌里扬娜,并生下塔尼娅和伊万。伊万出生后,张三妹自尽,化作一条欧洲鳇。在当代俄罗斯小说中,俄罗斯民族与异族之间带有诱惑、征服或交融意味的爱恋关系常被用来隐喻民族间的势位关系。中国女子嫁给俄罗斯男子,接受俄罗斯文化,皈依东正教,暗喻俄罗斯在中俄关系上的强势。其次,小说主人公在提及中国时言辞常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伊万曾讽刺中国皇帝愚昧无知:“那个中国傻皇帝预定了加利福尼亚蚯蚓冬天钓鱼用。他还以为鱼儿不吃摇蚊幼虫鱼饵呢!万一因为这个外国霍乱传了过来,鱼儿都大肚子朝上飘起来怎么办?”事实上,沙皇伊万姓氏“涅基塔耶夫”的谐音意为“非中国人”,这也是对根深蒂固的俄罗斯属性的强调。此外,文中还杜撰了一道骇人听闻的中国菜肴“猪眼”:“串在烧红的铁钎上烧制出来的,赤热的铁钎让猪皮包裹的猪眼中的液体不断沸腾着,里面是浑浊的眼球。”由此可见,俄罗斯主人公对中国文化还抱有一定偏见,从侧面体现出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优越感令它实在难以彻底“向东看”,这从伊万的言论“上帝在宇宙中像鹭鸶一样用一条腿站着,俄罗斯的上帝的脚”中也可见一斑。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细节反映出俄罗斯的所谓“中国同盟军”意识,是俄罗斯帝国迫于国际形势和基于自身利益而与中国形成的一种共边关系,作者有利用中俄混血的噱头蹭当时中俄合作热度的嫌疑。因此,我们也需对文中出现的中国元素保持清醒的认识。

普京,图片源自Yandex
结 语
克鲁萨诺夫在小说《天使咬伤》中通过神话编织民族叙事,用血缘建构身份认同,以他者形象映射民族意识,打造出具有多维度意义的欧亚帝国。首先,作者在小说中继承了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方发展道路的思考,提供了一份具有新欧亚主义特色的答卷。作为一名彼得堡原教旨主义者,克鲁萨诺夫以文学为阵地感性言说了立足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确保欧亚双向平衡以实现强国复兴的政治主张。其次,作家顺应了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试图以弱化的帝国意识抵制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填补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后陷入的精神虚空。此外,有别于俄罗斯经典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传统,克鲁萨诺夫反其道而行之,采用“大人物”叙事刻画出一位叱咤风云的伟人形象,并在其身上寄托民族复兴的希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再次,有评论者质疑克鲁萨诺夫乞灵于民族主义话语表述是看重其中的商业价值,具有功利色彩,并认为这种从大众文化思潮中汲取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想以重新确立民族文化话语的权威性的做法是后现代主义的媚俗变体。对此,克鲁萨诺夫在采访中澄清自己笔下的“帝国”所强调的是一种和谐与秩序的美学理念,而非所谓的帝国复辟。此外,他多次阐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在于回归历史维度,找回尊严和独立的根基,将一种伟大的精神注入俄罗斯,而非呈现西方读者想读到的“摇摇欲坠,像约伯一样坐在灰烬上的俄罗斯”。由此可见,克鲁萨诺夫在创作中也探讨了一种使文学反向作用于地缘政治的可能,赋予其创作以鲜明的时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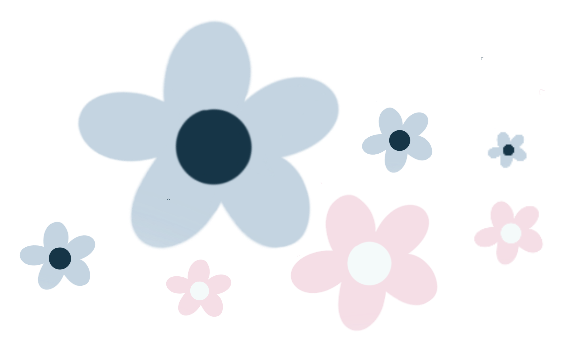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3期“新作评论”专栏,责任编辑苏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萌
排版:王雨璇 终审:文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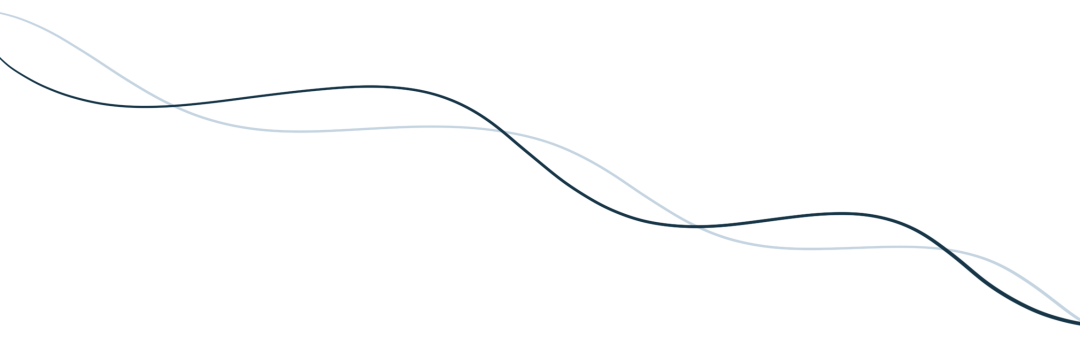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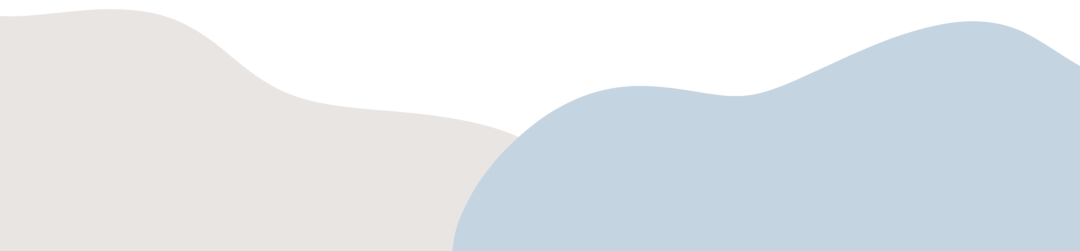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