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文学评论
-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 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 古典学研究
- 德语文学研究
- 冯至讲坛
- 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品及作家研究丨三色堇与《仲夏夜梦》中的情感复兴


姚琳,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和莎士比亚研究。近期发表的论文有《亨利五世的魅影——莎剧〈亨利四世〉的创作意图》(载《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世纪英国文学研究”(22&ZD2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 莎士比亚在喜剧《仲夏夜梦》中赋予三色堇等植物汁液神奇作用,这一手法与盛行于16世纪的体液理论密切相关,体现了英国社会当时流行的以生理学为基础的心理、情感认知方式。剧中暗含的对人的自然情感和个体理性的肯定,既展现了16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大众的普遍精神需求,也预示了17世纪将要出现的情感观念转变:人们的情感表达逐渐摆脱斯多葛学派长期以来的影响,人的自然情感被高举,情感的控制和失控及其政治后果随之也成为文学写作的热点,这一变化昭示着一场情感的复兴。
关键词 《仲夏夜梦》三色堇 体液理论 情感复兴

《仲夏夜梦》是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喜剧,因其充满浪漫梦幻的情调,备受历代观众喜爱。梁实秋先生认为:“《仲夏夜梦》是莎士比亚青春时代最后的也是最成熟的一部喜剧,里面充满了幻想和丰富的生活力……,是想象的一场狂欢。” 当然,莎士比亚的幻想及其浪漫喜剧效果,仍然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剧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情节,三色堇(一作“爱懒花”)花汁的魔法便是一例:“它落在西方一朵小花上,原是乳一般的白,现在爱的创伤使它变成紫红,女郎唤它做‘三色堇’……从那花里提出汁浆,若是点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无论是男是女,睁开眼就会疯狂地爱上他所看见的第一个人。”三色堇,见于英国植物学家约翰·杰拉德于1597年出版的《植物志》。书中说这种几乎没有任何气味的“红心草”(heart-ease)非常悦目,能够使人的内心平静安宁。《植物志》同时记载了另一种名为“沉睡的龙葵”(sleepy nightshade)的植物,称小小数枚便可导致昏睡,食用过量就会当场死亡。杰拉德认为可以使人内心平静(heart-ease)的小花,其花汁经过莎士比亚的文学想象具有了爱的魔力(love charm)。这种植物的汁液在剧中一再发挥作用,是剧情发展不可或缺的道具,正如沉睡的龙葵和乌头草对于推动《罗密欧与朱丽叶》 悲剧情节的发展必不可少一样。16世纪中叶英国本土植物学家的出现,意味着莎士比亚在他的创作生涯早期就已经有较为专业的植物志可参考了。本文以《仲夏夜梦》对三色堇花汁的创造性运用为例,尝试探讨莎士比亚的文学想象与16世纪的植物学、生理学和情感理论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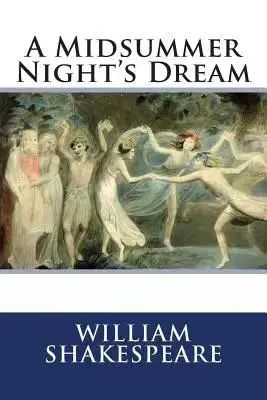

《仲夏夜之梦》和莎士比亚,图片源自Yandex
一、 三色堇汁液与体液平衡:《仲夏夜梦》中的
药理与情感
三色堇以及其他植物的汁液在《仲夏夜梦》中出现了五次。第一次在第二幕,仙王奥伯龙觊觎仙后铁达尼亚从印度带回的侍童,而铁达尼亚却严词拒绝了他的要求。仙王奥伯龙对铁达尼亚的违逆非常生气,决定要叫她吃点苦头,便命令夜游神扑克取来三色堇的汁浆,“等她睡了把汁浆滴在她的眼上:她醒来看见的第一个东西,无论是狮、熊、狼、牛或是顽皮的猴子,她都要忠心爱恋地去追求”,并说,“我另有一种药草可以解除她的魔祟,但是我要让她先把小童给我”。正如本文前文所述,三色堇本因丘比特的爱箭带来的创伤而得名,因爱而不得而生,然而其汁液的功效却是使仙后铁达尼亚失去了本心,叫她爱得盲目,变成了爱的惩罚。
仙王奥伯龙在等待扑克采花归来的时候,偶然间目睹了雅典青年地美特利阿斯对海伦娜的厌弃和薄情,而海伦娜却为爱失去自我,孤勇直前。奥伯龙便在为仙后滴上汁液之后,命扑克带着剩余的三色堇花汁遍访整个森林,找到那位把“雅典的服装穿在身”的薄幸的青年,用花汁“涂抹他的眼睛”。然而,扑克却错把与荷米亚相爱的赖桑德当作地美特利阿斯,在赖桑德的眼皮上滴上了三色堇的汁液。赖桑德醒来第一眼看到了海伦娜,也像仙后一样失去自我意识,把荷米亚抛在脑后,转而爱上了海伦娜。他甚至贬斥荷米亚,称她为乌鸦,是甜腻得应该丢弃的食物,是众人弃绝的异教邪说。
第三次使用三色堇的汁液是在第三幕第二场。地美特利阿斯在森林中遇到荷米亚,荷米亚因找不到赖桑德而坚信是地美特利阿斯杀掉了赖桑德,地美特利阿斯对她的绝情感到心灰意冷,身心疲惫,便在森林中倒下睡去。仙王奥伯龙和扑克发觉前面认错了人,扑克便急忙去寻找海伦娜,仙王奥伯龙则留下来为熟睡的地美特利阿斯滴上三色堇的汁浆。“这花颜色紫红,曾被鸠彼得射中,你浸入他的眼瞳。当他看见他的爱人,让她的光艳照临,有如天边的金星。”

三色堇,图片源自Yandex
地美特利阿斯被滴上三色堇汁液之后,一改往日对海伦娜的无情和冷淡,转而对她大加赞美:“我拿什么来比拟你的眼睛?水晶嫌太浑浊。”然而此时赖桑德也因三色堇的魔汁倾心于海伦娜。海伦娜面对赖桑德一直以来莫名其妙的追求和地美特利阿斯突然的爱意,懊恼至极,加上密友荷米亚也因为赖桑德变心对她恶语相向,于是打算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赖桑德和地美特利阿斯决定要展开决斗。扑克根据仙王奥伯龙的谋划扰乱了他们的行踪,几个回合下来,二人困乏至极,倒卧睡去。扑克趁机再次挤草汁于赖桑德的眼皮之上:“在你眼上我要滴上,温柔的情人,一点药浆。”若不细读,读者可能错以为扑克用的还是三色堇的汁液,但是莎士比亚在这里强调该药浆具有“virtuous property”(令人贞洁的性质)。因此,究竟是哪种植物,尚待揭晓。
为仙后铁达尼亚解去魔法是在第四幕。仙王奥伯龙不忍看到仙后痴爱一个长着驴耳朵的凡人,在得到自己心仪的侍童之后,决定为仙后解去魔法。奥伯龙的台词,“Dian’s bud o’er Cupid’s flower,hath such force and blessed power”,梁实秋将其译为“戴安的花苞力量大,胜过丘比特的花”。戴安(Dian)即狄安娜,罗马神话中主管月亮、狩猎、林地、野生动物和童贞的女神,是贞洁的象征。在《仲夏夜梦》第一幕,提西阿斯曾警告荷米亚,她若违抗了父亲的意志,就得在狄安娜的神坛前严守戒律,终生不嫁。英语中至今还用“to be a Diana”表示终身不嫁。根据梁实秋译本的注释,此处“戴安的花苞”,即“牡荆”或称“贞节树”之花苞,有令男女贞洁之力。由此来看,解去赖桑德三色堇汁液的魔力时所用的草汁,很可能就是戴安花的汁液。
植物汁液共出场五次,前三次是三色堇的汁液,分别作用在铁达尼亚、赖桑德和地美特利阿斯的眼皮上;后两次是戴安花的汁液,分别作用在赖桑德和铁达尼亚身上,用来解去三色堇花汁的魔法,使三对恋人终成眷属。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植物草药只对生物体的生物机能发生作用,由此改变生命状态,这是符合人们的一般现实经验的。到了《仲夏夜梦》,植物汁液不仅作用于生理层面,还能对心理和情感产生改造作用,显然体现了更多的幻想成分。莎士比亚幻想的依据,很可能来自历史悠久的体液学说。
从古希腊直至19世纪细菌理论建立之前,体液论(humoralism)一直是西方医学的主导理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普遍认为身体和精神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因此,人们倾向于用身体原因来解释精神状况,反之亦然。据约翰·威廉·德雷珀的不完全统计,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上半叶,至少有四十部论文或手册从四种体液(humours)的角度探讨了人体生理和心理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便是提摩太·布莱特(Timothy Bright)的《忧郁论》(1586)和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解剖》(1621)。
“健康和疾病是某种形式的平衡和不平衡。而这种平衡主要指液体——chymoi的平衡,该词通常被翻译成‘体液’(humour),它同样表示植物的汁液或水果的汁液。”体液平衡会带来机体的有序运转,而不平衡则引起机体的失序。疾病一般是由于体液异常造成的:体液在全身过多或缺乏、在一个器官中不适当集中都会引起疾病。而治疗的基本原则便是通过调整饮食使体液恢复均衡。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各种食物都是按热、冷、湿和干的程度来描述,以便人们可以选择那些与其病恙性质相反的食物,因为他们所处时代的医学知识告诉他们,血液温热而湿润,黄胆汁温热又干燥,黑胆汁冰冷而干燥,黏液冰冷又湿润。而在《仲夏夜梦》中,植物的汁液被赋予了快速改变人体体液比例的功能:使人产生病恙,改变人的性情或情感,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又能疗治身心,使人恢复健康和正常。
仙后铁达尼亚被施用三色堇花汁之后,她的眼睛似乎是得了某种疾病,直接影响了她对周遭事物的判断。她爱上了一个“温柔的人”,并愿意把最好的生活给他,俨然陷入了一种仙俗不分、尊卑不论的迷狂。赖桑德,这个饱读诗书的恋人,见识过因血统、年龄或他人的谗言而破灭的山盟海誓,也听说过被战争、死亡或疾病断送的两情相悦。为了捍卫真爱,他不惜和荷米亚逃离雅典,在外流亡。然而,一滴三色堇汁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立场:“我爱的不是荷米亚,是海伦娜;谁不愿换一只鸽子舍一只乌鸦?”地美特利阿斯在剧中同样被施用了三色堇,但并没有像铁达尼亚和赖桑德那样得到戴安花汁液的解救。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经历过一次情感变化。在第一幕第一场,海伦娜曾苦恼感叹:“地美特利阿斯没见荷米亚的眼睛,下雹一般的发誓说他只是我的人;等到这阵雹被荷米亚的热力一烤,他化了,那一阵的誓言也都融解了。”荷米亚身上的“热力”喻指她的性情和脾气,当然也是其体内的主导体液产生的结果。所以,地美特利阿斯其实是受到了荷米亚的主导体液的间接影响,是最先被改变的那个人。他的情感状态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失序的轨道上,而三色堇的汁液恰好把他拉了回来:“一定有一种力量,——我对荷米亚的爱竟像雪似的融消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剧终时刻只有地美特利阿斯仍然受控于三色堇的魔力,而无需解药。
二、 情感与理性共生下的情感复兴
在《仲夏夜梦》中,三色堇和戴安花汁液既是引起混乱的诱因,又是恢复平衡的决定性力量。在这两种植物液体的作用下,剧中角色的心理、情感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于铁达尼亚来讲,三色堇花汁在发挥惩戒作用的同时也把她和仙王的失和推向了高潮;赖桑德的情感则是走向自我背叛;而说到地美特利阿斯,三色堇的花汁又把他带回到了昔日恋人的身边。而戴安花汁虽然并不能保证赖桑德和铁达尼亚从今往后忠贞不贰,但至少可以使他们恢复正常的判断力,帮助他们回归有序的生活。
莎士比亚认为,正是人的失序带来了自然的失序,人应该对自然的失调和混乱负责——“这恶果是来自我们的争执,来自我们的反目;我们是这场祸患的根源。”人被提升到超越自然、影响自然的高度,是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的人文精神表达。另一方面,在莎士比亚的这出戏剧中,植物汁液的药理作用与体液理论相互贯通,在破坏人际情感秩序之后又最终使每个人各得其所,达到和谐与平衡,这也昭示着一场以人的世俗情感为中心的情感复兴。
从古典时代到17世纪,表达情感或激情的词汇passion一直带有被动含义。从语源上来讲,passion来自古法语和拉丁语,专指the Passion,即Christ’s Passion(基督受难),意即耶稣为救赎人类忍受被钉十字架的苦难,后来其“遭受”“忍受、忍耐”之义得到保留。到了14世纪后期,passion具有了情感(feeling)和情绪(emotion)的意义。一般来讲,emotion常被看作是passion的现代表达,而passion的派生词passive和passivity至今还保留着“被动”的意义,暗含着人的内部世界不得不经验、承受、忍耐外部世界的迫害、折磨和压力的意味。抛开情感一词在词源上的宗教内涵,人的情感具有一定被动性,这在西方文化传统里也是有标记的。比如,人们认为,人的情感取决于人体生理结构,如受到四种体液的比例所制约。这一点从西方自然哲学对情感的探究重点上也可见一斑。
自古典时代以来,人类对情感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自然哲学领域内,即探究情感的“潮起和潮落,生发和衰退,它们怎样造成各种影响,它们导致哪些肉体效应”。柏拉图甚至认为不同的情感在人体内有其生发的相应位置:颈部以下充满朽坏的情感,肝脏则充满欲望等较为低劣的情感;心脏部分充满了刚毅和愤怒的好战情绪,因此有可能成为理性的潜在盟友,而灵魂不朽的部分则在头部。正因为这样的区分,情感是非常麻烦的:快乐是“邪恶最强烈的诱惑”,而痛苦则会“将美好的事物吓跑”;欲望是野兽,而理性会用它的鞭子“愤怒”来驯服和抑制其他情绪。显然,柏拉图把理性看作医治情感的一剂良药,自此奠定了理性与情感的二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情感并不是与理性相对立而存在的,情感是判断,是修辞的技艺,情感应该由理性来控制,一个人的性格应该用理性来教育。他强调情感的社会建构作用,而受到社会习得的情感的熏陶是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多葛学派则走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反面,他们承认情感是判断,但是是错误的判断,始于自我保护的动物性冲动,因此应该由理性来消除掉。在用理性压制情感这一点上,斯多葛学派和柏拉图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一致。论及情感,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引入了“自由意志”的概念,认为情感若得到正确的引导将有益于灵魂,否则就对灵魂有害,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作为一位基督教神父,奥古斯丁把情感放到信仰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依据他的看法,自由意志本质上属于神学理性:低级的、世俗的情感与原罪有关,经由神学理性拣选的高级的、神圣的情感才是信徒们应该追求的。阿奎纳和奥古斯丁一样,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中的灵魂三分中受益良多,认为情感是一种不羁的力量,是堕落灵魂的疾病,因此需要理性的约束。这种对情感的总体贬抑态度在中世纪时期为很多人接受,甚至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如彼特拉克也还在沿袭前辈们的观点。在其1360年写就的《论命运的补救》(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中,彼特拉克声称要消除作者和读者的激情。在这一点上,彼特拉克因循了斯多葛学派对待情感的理想状态。到了15至16世纪,大量探究情感的作品开始出现。从广义上来讲,贯穿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张力实际上是斯多葛主义与奥古斯丁主义之间的张力。斯多葛学派最终因“徒劳地试图把由自然塑造的人类变成石头”,毫无人道地严苛压制情感而逐渐遭到抛弃。越来越多的人文主义者更倾向于较为温和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立场,因为相较于压制所有情感的斯多葛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把情感看作人们对周遭事物的自然反应,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取这一立场的话,更有可能实现美德,或至少改善个人道德状况。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有德性的人,不仅能在理性的指导下做对的事情,还能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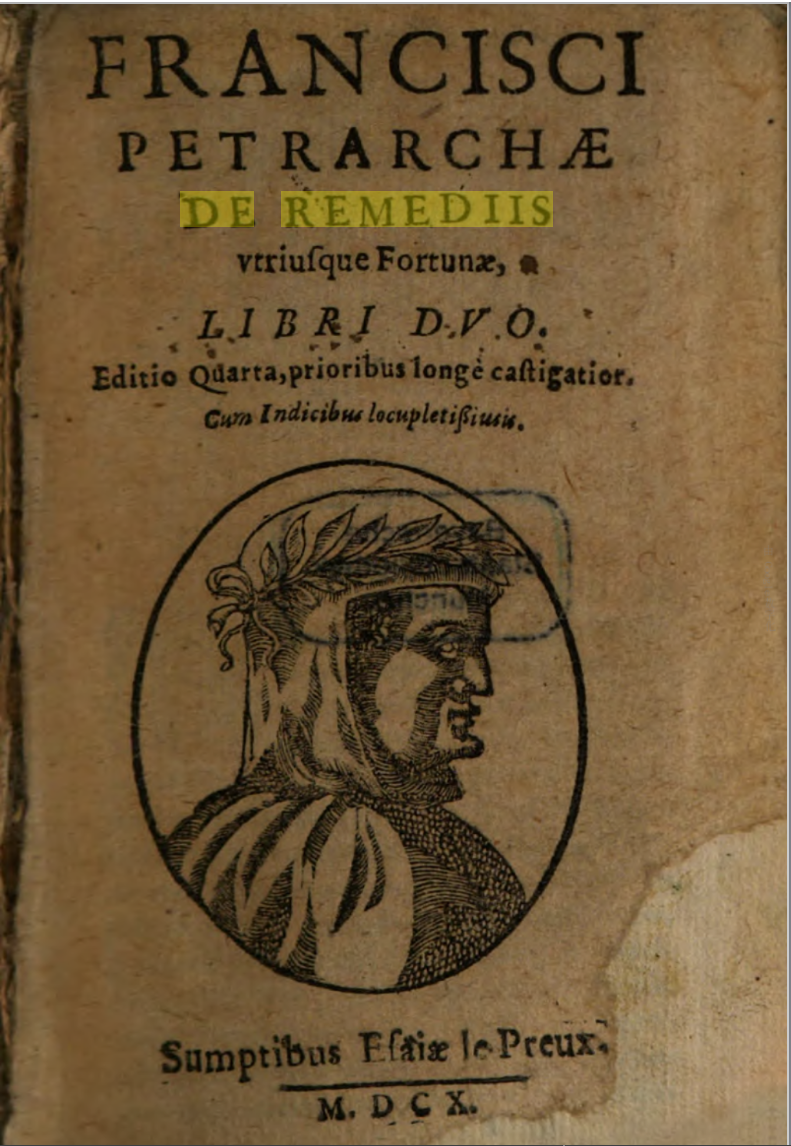

《论命运的补救》,图片源自谷歌图书
彼得拉克,图片源自Yandex
除此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也从普鲁塔克、昆体良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有别于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比如普鲁塔克摈弃斯多葛学派对情感的理想化驱除,赞成较为持中的态度;而昆体良则区分强情感和弱情感:前者激烈暴力,意在对他人施加控制或恶意扰乱;后者压抑克制,意在说服他人或善意诱导。由此,人文主义者们开始把目光落至人的身上,直面作为自然人的情感状态。
不难发现,从自然理性到神学理性,情感作为非理性因素一直处于被压制甚至被鞭笞的状态。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尽管认为上帝是理性的源泉,却无不拘泥于理性和信仰孰高孰低的争辩,在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中泥潭深陷。到了早期现代,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萌发了“一股追求个体自主的理性主义潜流”,人类理性接替自然理性和神学理性成为关注焦点;而非理性主义作为隐性的支流,一直寄托在理性主义身上,人类的世俗情感从未消失。莎士比亚觉察到了这股暗流,将植物的汁液与四体液对人体的决定作用联系起来。在《仲夏夜梦》中,人的情感虽然依然具有被动性,仿佛受植物药理宰制,但剧作在更大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世俗情感,展现了文艺复兴这个崭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此外,莎士比亚在擢升人及人的情感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理性。在《仲夏夜梦》中,赖桑德被误施了魔法之后,转而对海伦娜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并认为“现在我的理性发展到智慧的顶点了,所以理性成为我的意志的向导”。一个因魔法失智之人把失序的情感状态称为“智慧的顶点”,这里对理性是有些许的讽刺,但此处并非否定理性,而是说明盲目的情感全面控制了赖桑德,而他浑然不觉。同样地,当线团看到受魔法控制的仙后深情迷恋一个凡人,不禁感叹:“在这年头理性与爱情难得合在一起。”此处,仙后和赖桑德一样被情感充满,理性处于暂时缺失的状态。除了这种把情感与理性并置从而提升情感的做法,莎士比亚更是借提西阿斯之口直接肯定情感:
我初来的时候,许多大学者们用预先准备好的颂词来欢迎我;我看见他们发抖,脸也白了,在句子当中常常停顿,在惊慌中把熟练的词句都哽咽得说不出口,结果呢,哑口无言的戛然而止,根本没有对我表示欢迎。可是,相信我,爱,我在这缄默当中领略到了祝颂,在这敬畏的羞怯当中我所领略到的意义,正不下于鼓舌如簧的大胆的雄辩。所以,据我看,衷心的爱敬与质朴的口讷,虽然话说得最少,意思表示得最多。
谨慎的、矫饰的,经过理性加工的,不过是“鼓舌如簧的大胆的雄辩”,都不及“衷心的爱敬与质朴的口讷”那么丰富。无言是发乎本心的,是和人的本性相符的,而这种本性恰恰是由每一个个体那作为物质的身体构成决定的。当然,莎士比亚在肯定情感的同时也较为隐微地肯定理性:
我的梦究竞是怎样的一个梦,没有人的眼曾听见过,没有人的耳曾看见过,人的手不能尝,他的口不能懂,他的心不能讲。
这是织工线团从夜游神扑克施加给他的梦境中醒来后的一段话。莎士比亚借线团之口,分别以眼睛、耳朵、手指代五感中的听觉、视觉、味觉;以耳代眼,以口代脑,以心代口。这段话打乱了感觉的常规表达方式,加剧了整部剧所表达的感官混乱。线团是一个凡人,在遭遇夜游神扑克之后被变为人身驴首的怪物。然而,身体外观的变形并没有给其理智带来任何影响:顶着驴头的他并没有如扑克所愿,变得和驴一样愚蠢。他在仙后面前不仅能口吐格言,还会谈笑怡情;在面对仙后的夸赞时,他自嘲自己不够聪明,跑不出仙后的林子;他还能根据服侍仙后的四小仙的名字来判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功用。这一切都证明线团并没有变得像眼睛上被滴了三色堇花汁的赖桑德等人一样盲目,失去了对周遭事物的理性判断,而是依旧保持着理性。没有人的眼曾听见过,因为他的眼睛所看见的别人不曾听到过;没有人的耳曾看见过,因为他的耳朵所听到的别人都不曾见到过;人的手不能尝,因为他的手所触摸到的,没有人能品出其中的韵味;他的口不能懂,因为即使他说出来也不能使他人信服;他的心不能讲,因为他心里所感受到的愉悦情感不能语与他人。线团这段暗语式的台词充分表达了他在走出幻境之后内心的一种撕扯,即基于理性的情感与基于虚荣本能的情感之间的撕扯:究竟是告诉同伴,引来羡慕、嫉妒或嘲讽来无限放大内心的愉悦,还是为了维护仙王仙后的尊严或者为了避免别人不相信他而三缄其口?最终,有理性加持的情感险胜:“诸位,我要报告一些奇事:但是别问我是什么事;因为如果我会告诉你们,我便算不得一个真正的雅典人。”线团以做“一个真正的雅典人”的理性决策压制了猎奇炫耀的虚荣心,维护了人、神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莎士比亚选择线团这样一个喜剧角色说出这一席颠三倒四又不无智慧的话,既是营造轻松诙谐的气氛,又是表达个人从情感到理性再到情感的思想闭环,体现了在“一个真正的雅典人”,也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的内心,情感与理性共生、平衡的状态。
三、 情感之用
莎士比亚的《仲夏夜梦》创作于16世纪末期。17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已经弥漫着对情感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与欧洲早期现代对知识与控制力——无论是控制自我还是控制他人——的关注息息相关。在此以前,尽管长期以来基督教对人是否可以塑造自我是存疑的,正如奥古斯丁曾说,“放下自我。你若试图建构自我,你建造的不过是一片废墟”,但到了16世纪,人们似乎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人类的自我塑造是一个可操纵的、巧妙的过程。而情感是自我塑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在1532年出版的《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已经谈到情感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对一位君主的重要性。《激情之用》(The Use of the Passions,1649)的译者蒙默思伯爵在该书的引言部分认为此书对怀有掌控自己、指挥和统治他人之权力雄图的帝王和君主,将会是一把“密钥”。情感论题也时常出现在17世纪时人写给国君的谏言书中:要想施行成功的统治,一位国君必须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以免盛怒之下行不公之事从而丧失民心;一位国君也必须能读懂和操纵周围人的情感,明察和驾驭朝臣以及民众的野心、嫉妒、恐惧和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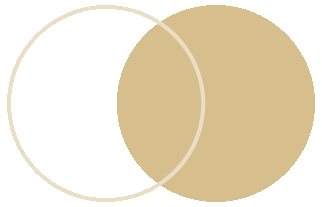


《君主论》和马基雅维里,图片源自Yandex
控制自我的前提,是认识自我和掌控自身情感;控制他人,则要读懂他人的情感状态,进而加以操纵以实现利己的目的。在《仲夏夜梦》中,仙后铁达尼亚、赖桑德和地美特利阿斯被施用了三色堇药汁,失去了对自身情感的认知和掌控,而这一切背后的操控者正是仙王奥伯龙。他因求而不得而愤怒,因愤怒而惩戒铁达尼亚,又因怜悯而解救铁达尼亚,并最终得到侍童,实现自己的意愿。其间,他虽因同情海伦娜而误伤赖桑德,但最终却能适时化解危机,使两对恋人各得其所。
仙王奥伯龙向仙后铁达尼亚提出索要印度侍童的主张,从本质上来讲是在宣示对铁达尼亚情感的控制权。铁达尼亚对侍童的过分宠爱激起了奥伯龙的嫉妒,而她拒绝交出侍童的违拗行为更加挑战了仙王的权威。他俩一出场便互称对方为“骄傲的铁达尼亚”和“嫉妒的奥伯龙”。奥伯龙更是严词诘问铁达尼亚:“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可见铁达尼亚的骄傲已经对奥伯龙作为王者和丈夫的尊严产生了威胁。仙王奥伯龙使用植物药液达到挽回权力和尊严的目的,成为剧中最成功的情感操控者。一方面,他通过操纵他人的情感满足了自己的情感需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力;另一方面,这个控制他人情感的过程,也伴随着仙王对自我情感状态的调整和控制。在他看到仙后把花环戴在驴耳上时,于心不忍地说道:“我开始怜悯她的痴爱。”在讨要到了印度侍童之后,他为仙后的眼睛解去了“可恼的翳障”。仙王奥伯龙对自身的情感状态和情感需求有清晰的认识,并根据自身的需求创造条件去实施对他人的控制。仙王奥伯朗和织工线团仿佛是一对互为参照的人物,呈现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情感图景。
结 论
《仲夏夜梦》赋予三色堇等植物汁液以魔力,以植物汁液的药理作用影响人体体液,通过生理影响剧中人物的心理和情感走向,既是以植物元素回应当时的自然哲学所侧重的情感属性,又是对16世纪流行的体液论的创造性运用。莎士比亚在其他剧目中直接提到了体液(humour)以及不同角色由不同体液主导的情感状态。例如,在《泰特斯·安庄尼克斯》中,他四次提及“humour”,讨论泰特斯的本性。此外,他还借亚伦之口直言:“虽然维诺斯使得你(塔摩拉:作者注)春心荡漾,支配我的心情的却是阴森的土星。”约翰王两次将谋杀约瑟王子归咎于他的“humour”,并在第一次和休伯特密谋此事时已经言明这种“humour”是“乖戾的忧郁症”,“已经烘烤过你的血液,把你的血液变成为混稠的东西”。刻画克利兰纳奥斯、奥赛罗这样的军人角色的时候,莎士比亚使用胆汁质(choleric)一词达到四十余次之多。但是莎士比亚笔下并非只有由某一种体液主导的角色类型,像亨利五世和哈姆雷特那样性情多层次多维度的角色在其剧作中更多。这些人物对自身情感状态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和反思,并能够主动控制和运用情感。莎士比亚剧作在人物刻画上既呈现了情感的自然属性,又观照了情感的社会属性和政治维度,映照出在16至17世纪之交的文艺复兴时代,情感正在复兴。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4期“作品及作家研究”专栏,责任编辑萧莎,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萌
排版:王雨璇 终审:文安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室 邮编:100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