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文学评论
-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 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 古典学研究
- 德语文学研究
- 冯至讲坛
- 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
域外近著评论丨世界体系视野下的世界文学观念重构——评《叠合发展与不平衡:迈向世界文学的新理论》

李孟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西方文论与英语后殖民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论世界文学观念起源的后殖民因素》(载《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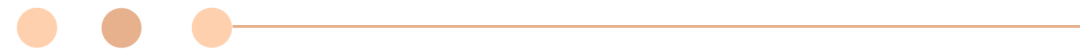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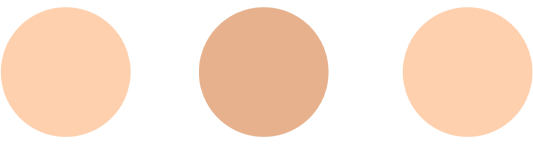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本文将英国华威大学研究集体的理论著作《叠合发展与不平衡:迈向世界文学的新理论》置于世界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之中,认为该书以世界体系为核心,透过资本主义的叠合发展与不平衡重构了世界文学的观念,将之定位为对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进行书写的文学作品;并且在如何运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来建构世界文学观念方面,重点关注了边缘文学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书写,为边缘文学的经典性建立了理论依据。不过,这种重构的实践中也存在窄化世界文学范围,从而与世界文学背后的包容性格格不入的理论缺陷。
关键词 世界文学 华威大学研究集体 世界体系 《叠合发展与不平衡》 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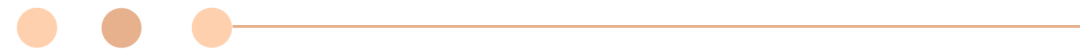
21世纪以来,在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等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文学学科呈现出鲜明的世界文学转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术团队,华威大学研究集体(以下简称“华威”)的著作《叠合发展与不平衡:迈向世界文学的新理论》(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World-Literature,2015,以下简称“《叠合》”)将世界文学中的“世界”定位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重点关注不同地域的文学文本如何对现代世界体系在结构上的叠合发展与不平衡进行书写。《叠合》一书在概念界定、研究方法、跨学科协作等多个层面尝试构建新的世界文学理论,由此成为继《文学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1999)、《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2000)、《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3)等专论之后又一部在世界文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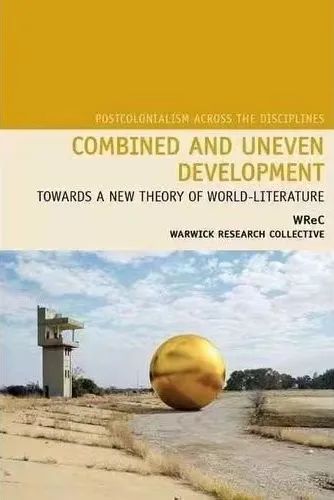
《叠合发展与不平衡:迈向世界文学的新理论》,图片源自Yandex

一、 世界文学的重新定义

通过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叠合发展与不平衡来重新定位世界文学,是《叠合》一书的写作主旨。华威将世界文学定义为“世界体系的文学,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文学”,认为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书写的文学作品均可以被视作世界文学。同时,华威将“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改为“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以突出自身的理论建构乃是对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体系”(world-system)理论的继承。
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模型中,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单一且不平等的组织结构,由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三个层级构成,位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处于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沃勒斯坦指出:“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一个我们可以称其为欧洲世界体系的格局宣告形成。”这一时期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得到发展与扩散。以葡萄牙为代表的贸易帝国虽然早在15世纪末便与亚洲建立了广泛联系,但是贸易层面的互通有无并未从本质上触动亚洲固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运作模式,所以15至16世纪的亚洲仅仅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外部竞争场”,而非南北美洲那样的“边缘地区”。及至19世纪,现代世界体系在殖民扩张与世界市场的开拓中将以亚洲为代表的广阔地域纳入其中,最终使资本主义彻底实现了对于整个世界的征服,所有的“外部竞争场”均转变为“边缘地区”。所以,有鉴于19世纪之后资本化的世界才在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主义扩张中正式建立,华威界定的世界文学主要指代过去200年的文学创作。
在华威之前,莫莱蒂与卡萨诺瓦均曾以现代世界体系为视角来阐释世界文学,并对华威产生了一定影响。莫莱蒂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用新的批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没有人能仅通过阅读更多作品就能找到一种方法。”所以,莫莱蒂并不致力于通过文本阅读来建构世界文学观念,而是借助世界体系理论来呈现世界文学的不平等结构:
国际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同时既是一,又是不平等的:有一个核心和一个边缘(以及一个亚边缘),它们被捆束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关系之中。一,并且不平等:一种文学(歌德和马克思所说的单数的世界文学);抑或更好的说法是一种世界文学体系(相关文学的体系),但却不同于歌德和马克思所希望的一个体系,因为它相当不平等。
依据莫莱蒂的理论,世界文学与国际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具有相似的不平等结构,位于体系核心的民族国家在国际文学资本的竞争中占据支配地位,这造成“某种文化的命运……与另一种‘完全忽视它’的(位于中心)的文化相交叉并受其影响发生变化”。为验证这一设想,莫莱蒂以“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为方法,将现代小说的发展模式理解为“西方的形式影响(一般指法国与英国形式)与地方原料折中的结果”。在这一理论构想下,以英法为代表的文学中心成为文学技法与形式创新的源泉,而边缘地区则只能通过继承中心的文学资本来带动本国文学的发展。
同样,卡萨诺瓦将世界文学空间划分为中心与边缘组成的等级结构,边缘文学要获得国际声望就要经过文学中心的祝圣。巴黎曾是众望所归的文学世界之都,所以巴黎的“翻译、述评、颂词及评论就是识别和判决,它使那些存在于文学空间之外的或尚未显露的空间获得文学价值”。卡萨诺瓦认为,尽管国际政治与经济权力会对文学空间的运作产生一定影响,但文学空间并不仅仅是全球政治空间的衍生品,相反,文学空间具有自身的审美与评价体系,所以,法国虽然在世界体系中算不上核心,法国文学却能够在文学世界中居于主导地位。
综上可见,莫莱蒂与卡萨诺瓦主要将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应用于文学体系的发展与演变逻辑,据此分析文学中心对边缘的影响及边缘对中心文学资本的依赖。然而,两人却并未根据世界体系理论构建自己的世界文学的概念,而且将两者的关系辨析限定在文本的外部研究中。
但是,莫莱蒂没有将世界文学理解为经典作品的集合,也没有将之视作一种阅读模式,而是将世界文学看作一个与世界体系相似的单一且不平等的等级结构,这对华威产生了启发。华威认为,莫莱蒂在这一过程中激活了叠合发展与不平衡理论,而后者则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特征。
叠合发展与不平衡理论最重要的奠基人为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认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吸纳先进文明的过程中往往会造成各个发展阶段的混合,他将这一发展规律称之为“叠合规律”,其特征体现在“发展道路上各个时期的相似,某些阶段的相互结合,古老的形式与最现代的形式的混合”。以19世纪沙皇俄国为例,在西欧的影响与干预下,俄罗斯在缺少工商业基础的情况下被迫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资产阶级的软弱又促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依赖于旧地主阶级,即“一个阶级的任务经由另一个阶级之手去加以解决,这就是落后国家特有的叠合方式之一”。由于缺少与西欧先进国家相似的社会结构与发展轨迹,这一叠合特点在俄罗斯的工业化道路上得到了更为明显的体现。19世纪下半叶及至20世纪初,俄罗斯的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形成共存,而资本主义大工厂“周围是小村落,是逐年衰败的草屋和木屋村落”。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叠合状况在世界各地均普遍存在。可见,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取缔旧的生产关系,它还可能与后者并行不悖,所以叠合发展与不平衡主要被用来指代“资本主义形式和关系与‘古老的经济生活形式’及早先存在的社会和阶级关系同时存在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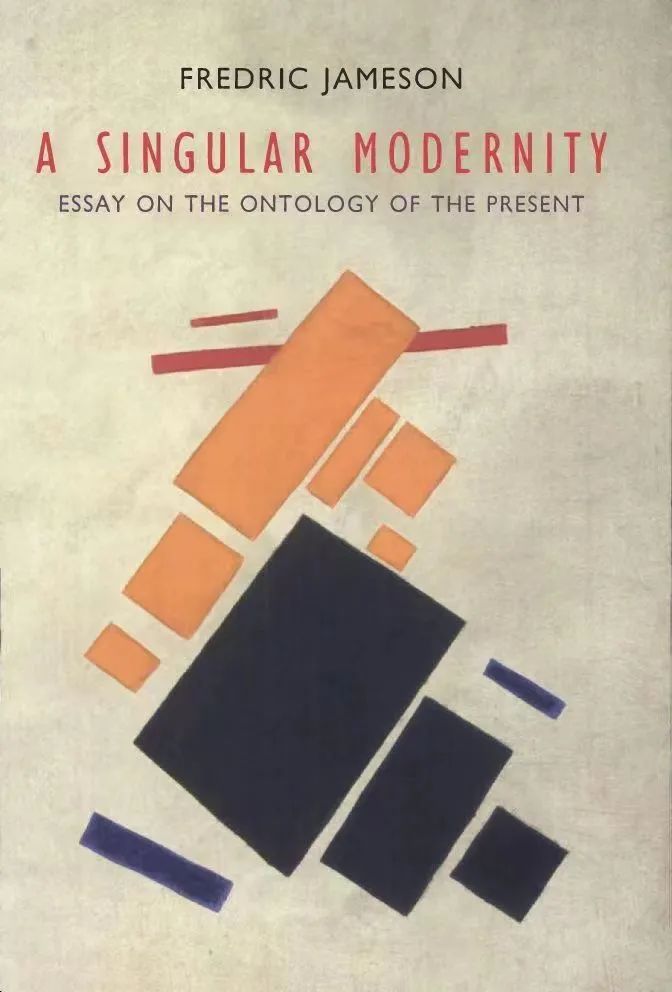
《单一的现代性》,图片源自Yandex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也译作詹明信)同样关注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叠合发展问题。在《单一的现代性》(A Singular Modernity,2002)中,詹姆逊认为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理解不能忽视全球资本主义这一总体框架,所以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对应的单一结构,中心与边缘国家均处于单一的现代性中。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中,詹姆逊则指出现代性的“非同时发生的事物的同时性”(simultaneity of the nonsimultaneous)特征,这主要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现代与前现代的不同生产方式可以与社会结构在同一时期并存,具体表现在“手工艺和卡特尔(cartels)联合,农田和克虏伯(Krupp)工厂或远方的福特汽车工厂并存”。在詹姆逊的启发下,华威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单一且全球散播的普遍现象,其特征并非现代与非现代的二元对立,而在于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两种社会形态的叠合共存。这种不平衡发展也并不仅仅是落后国家的独有特质,而是涵盖发达与不发达国家,这表明不平衡本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现代性既非时间范畴,也非地理范畴,所以它并不遵循从西方到非西方的时序过程,也不恪守从城市到农村的发展路径或从男性到女性的性别分工,相反资本主义现代化依赖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与畸形发展。
华威以世界体系为核心,将现代性、现代世界体系、叠合发展与不平衡加以理论整合,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滋生了叠合发展与不平衡中的现代性。所以,华威重在考察不同文化与地域背景下生产的文本所包含的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体验,探索世界文学如何书写资本主义的叠合发展与不平衡问题。

二、 比较文学的方法论:
批判唯心主义

叠合发展与不平衡的理论优势在于可以更为直观地把握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性既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也见诸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差异。例如,巴西里约热内卢、印度孟买、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城市中繁华街区与贫民窟之间的对立便是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不平衡的典型缩影。华威不认为全球化可以消除体系内部的不平等,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追求文学领域的平等交流仅仅是一种奢望,而欧洲、西方等概念背后的同质化倾向则使内部的不平衡被掩盖;故而,华威对文学研究中将比较文学视作“公平竞技场”(level playing field)的唯心主义倾向做法表示质疑,这一学科倾向在建构比较文学理论时往往脱离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结构,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论重构实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在学科机制上避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之死》中认为比较文学定义的相对宽松使之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容纳所有的文学研究,本可以成为一个公平竞技场。不过,比较文学受制于语言霸权,即便文化研究与多元文化主义打破了固有的学科界限,人们在语言学习层面也无力进行有效拓展,因此比较文学的学科空间不可能摆脱政治霸权的操控,这样,全球南方就成为学科空间中的“本土提供信息者”(native informant),而非平等的参与者。为改变这一现状,斯皮瓦克“不提倡该学科的政治化”,而是提倡通过语言学习来实现“敌对政治的去政治化,迈向将要到来的友谊政治”。在实践中,斯皮瓦克鼓励比较文学学者不再以欧洲语言为核心,而是加强全球南方语言的学习,以推动南北方之间在文学交流上的平等。与斯皮瓦克的观点不同,华威认为尽管比较文学学科经历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洗礼与针对欧洲中心主义及东方主义的批判,但是欧洲中心主义在欧美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与其对比较文学抱有乐观主义的幻想,倒不如将之视作一门政治化的学科。
在对斯皮瓦克提出批评的同时,华威指出,“一些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希望将‘公平竞技场’的理念追溯到过去,认为比较文学最深层的内在倾向一直是这种‘全球性’或‘普遍性’”。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便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尽管阿普特与斯皮瓦克的比较文学观念有所不同,但两人却有着相似的唯心主义倾向,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部权力机制对于比较文学的影响。在《翻译地带:一种新的比较文学》中,阿普特认为:“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在原则上是全球性的,即使它在战后时期的制度建立使欧洲获得了最大份额的批评关注,并忽视了非西方文学。”为此,阿普特以奥地利语文学家列奥·施皮策(Leo Spitzer)的流亡经历与学术实践来论证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性倾向。施皮策于1933至1936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执教期间积极学习土耳其语,并创建语文学学院,在教学与学术实践中极力践行多语言原则。阿普特认为,“作为把全球带入文本的批评性阅读实践的证据”,施皮策的比较文学实践在当今时代得到继承,所以“从许多方面来说,近年来文学经典全球化的热潮可以被视为民族文学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合并’”。在施皮策的影响下,阿普特通过翻译、语文学、多语主义等策略来建构新的比较文学观念,以实现对于民族文学的超越,推行文学领域的平等交流。

列奥·施皮策,图片源自Yandex
华威认为,阿普特虽然正视了全球化对于比较文学的影响,但却忽略了世界体系对于学科空间的干预。在方法论层面,阿普特以比较文学反对民族文学的做法忽略了英语的世界地位早已不是一门民族语言。在语言与文学实践中,英语与现实的权力体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所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等批评实践才得以在英语系建立学术空间,也使少数族裔在英语系得以立足。然而,上述批评实践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空间中却缺少可持续性。在翻译、语文学、多语主义等问题上,尽管比较文学一直提倡多种语言的学习,但这并不代表语言的平等。比如,殖民时代大量的殖民地官员与东方学家往往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祖鲁语、乌尔都语等语言,这种出于统治需要的多语主义丝毫不会动摇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所以,“一种根本的不平等——不是内在的,而是完全社会的……这种不平等是由翻译、出版、阅读、教育等多种社会逻辑因素决定的”。为印证这一观点,华威援引了文化批评家周蕾(Rey Chow)的论述:“由于一般认为语言是中立的,比较文学的讨论不仅很少注意到世界上各个语言、文化之间进行跨国交流时,实际上立足点并不平等,也很少注意到‘语言背后隐藏着支配关系’,更遑论去厘清(当前)比较研究中预设的语言对等概念,或许只是一种不切实际而无法实现的空想。”所以,华威认为“比较文学对多语言性的坚持往往是一种明确的语言拜物教(因此也是专业经验的权威)的支配作用,而不是对文化对话或社会相互关系的任何承诺”。
从华威对斯皮瓦克与阿普特的批判来看,问题的焦点在于比较文学能否通过重建方法论摆脱权力关系的干预,实现文学上的平等交流。比较文学从诞生之初便是一个带有欧洲中心倾向的学科。例如,梅茨尔(Hugo Meltzl de Lotmnitz)虽然在《比较文学当前任务》(“Present Task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1877)中将比较文学追溯至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强调比较文学的多语言原则,但他却将字母文字之外的文学创作排除出比较文学研究的殿堂,这一做法无疑暴露了他的东方主义倾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比较文学的学科生态得到了较大的改观,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The Bernheimer Report”)便将“西方文化传统(包括高层的和大众的)和非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比较”视作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梅茨尔,图片源自Yandex
21世纪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文学转向使非西方文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但这并不代表比较文学脱离了现实政治对学科内部的干预。事实上,世界文学理论的复兴本就与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息息相关,而这一潜藏的权力逻辑在于“只有那些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所形成的特权空间里居住的公民,才倾向于自信地谈论他们超越国家的能力和愿望”。在世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浪潮中,尽管非西方文本得到了空前关注,但是评定世界文学的标准与尺度却仍由西方话语来掌管:首先,世界文学理论建构很少借鉴非西方文论资源,这种理论上的不平等实质上反映了中心与边缘在文学研究上的话语权差异;其次,世界文学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便是全球范围内的英语文学,重要的文学奖项与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也仍由西方学界所掌管,西方依然是文学祝圣的中心。可见,尽管比较文学确实将研究范围从早期的西欧文学扩展为世界文学,但它仍无法仅凭研究方法的变革突破世界体系的干预,建立民族文学间的平等交流。面对这一现实,华威的理论优势就在于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结构与学科空间紧密关联起来,力图纠正学科发展过程中对于权力关系的漠视与僵化处理,这为如何在外部研究中定位世界文学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如何在文本内部研究中分析世界文学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书写均具有重要意义。

三、 超越现实主义与
现代主义的边缘美学

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使全球处于一种单一的现代性之中,那么在这一总体性空间内的文学创作便无法独立于世界体系的叠合发展与不平衡特征之外。在这一理论视野下,华威更关注文学文本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史实性描述,文学形式的创新则可以理解为资本化进程的产物,这也使华威“所理解的‘世界文学’是一个分析范畴,而不是一个以审美判断为中心的范畴”。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同时性结构中,传统的文学形式划分的弊病在于以僵化的时间界限限定了文学的演变逻辑,忽略了边缘文学如何以形式创新对世界体系进行回应,所以华威认为:“我们更愿意谈论的不是文学形式在空洞的时间中的蔓延或展开(因此,文学史被划分为连续的‘时期’——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而是通过世界资本化的长期浪潮带来的形式(而且往往与其他预先存在的形式发生碰撞)。”
正因为考虑到世界体系的同时性特征,华威认为,落后国家在政治与经济层面的边缘境遇并不代表这些国家无法孕育伟大作品与形式创新,相反,它们与世界体系的中心处于同一时代,对于叠合发展与不平衡问题也有体会且体会更为深刻,这无疑为杰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例如,沙皇俄国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的不平衡状况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将落后和不协调的感觉转化为文学创新和优势的源泉,将古老的和新兴的共同存在处理成一种现代形式,这在19世纪的文学空间中几乎没有匹敌者”。19世纪以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为代表的巴西作家则在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本国的大庄园奴隶制“相矛盾的当地条件下肯定欧洲思想和理想:其结果是一种独特的美学,其特点是各种不平衡、文体不匹配和不可能的连续性”。

马查多·德·阿西斯,图片源自Yandex
华威由此认识到19世纪的边缘文学创作已经涵盖了现代主义的美学特质,所以有必要超越既往对于现代主义的僵化理解,也就是“将‘现代主义’的嬗变理解为对现实主义的取消——如果不是完全否定的话”。在这一问题上,华威的看法与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的见解相一致,即“现代性是一个性质范畴,而不是一个时间范畴”。阿多诺在与卢卡奇的论争中认为现代主义并非背离了现实,而是“通过自身的形式法则,以审美的方式间接地揭示了社会的本质,以反叛者的姿态对现实存在作了无情的否定,从而使人对这个世界获得更加清醒的认识”。在阿多诺的启发下,华威认为现代主义并非是对现实主义的接续与取代:“阿多诺对现代主义的辩护是对现代主义化的现实主义的拱卫。反之亦然:对现实主义的维护将采取认同其现代主义的方式。”当然,华威与阿多诺也存在不同之处,那就是华威通过边缘文学研究来打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时间界限,而阿多诺则主要基于中心文学创作来证明这一问题。华威认为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同样应该超越既往的地理界线划分,这就需要将文本置于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加以讨论,“从叠合发展与不平衡的角度来阅读现代主义文学,就是用一只眼睛来阅读它的现实主义。这样的解读与公认的文学史风格背道而驰,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一直试图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制造隔阂”。
不同于传统的文类学方法,华威一方面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时空界限进行有机调和,另一方面认为边缘文学作品在对世界体系的叠合发展与不平衡加以书写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对现实主义加以改进却又与现代主义不尽相同的形式特征,即“非现实主义”(irrealist)。非现实主义的产生与资本化的原始积累及其所形成的资本帝国息息相关,在这一进程中边缘国家遭受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种族主义等多重压迫,传统与现代的并置打乱了个体对于自我与世界的认知,这样的时代面貌使边缘作家往往要通过形式上的创新来展现扭曲的时空体验。于是,读者可以领略到苏丹作家塔伊卜·萨利赫(Tayeb Salih)运用时空交叉的叙述者来表现苏丹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震荡摇摆,感受到俄罗斯当代作家维克多·佩列文(Victor Pelevin)以超现实的梦幻体验来描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等层面的矛盾与失序状态,体会到南非作家伊凡·维拉迪斯拉维克(Ivan Vladislavic)以约翰内斯堡的城市建筑格局来隐喻种族隔离对于南非社会所造成的撕裂与精神创伤。虽然非现实主义写作在运用“反线性的情节线索、元叙事方法、不完整的人物特征、不可靠的叙述者、矛盾的观点”等叙述策略的过程中具备了欧美现代主义的形式特征,但这同样是边缘作家在审视资本主义对于生活经验与本土空间造成的破坏时所不得不采用的创作方法,因此边缘文学不能简单地套用欧美经验来评判,而应该放置于世界体系中的不平衡情境中加以观照。
边缘文学的上述形式特征也是作家在创作中对于本土文化的自觉调用。例如,萨利赫在《移居北方的时节》(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1966)中便将传统阿拉伯的口头说书形式与现代主义进行并置,以此来隐喻边缘社会空间在面对世界体系所带来的文化变局时所产生的多重矛盾及其对于现有秩序的反抗;冰岛作家赫尔多尔·拉斯克内斯(Halldór Laxness)在《原子站》(The Atom Station,1948)中则运用《萨迦》等古代民间传说展现现代化进程中全球与区域文化的融合,表达冰岛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时代焦虑。总之,在华威看来,对非现实主义美学加以界定的过程中既要避免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视作阶段性的范畴,也要对文学形式创新的历史特殊性进行讨论,不能简单地将边缘美学视作西方形式与本土材料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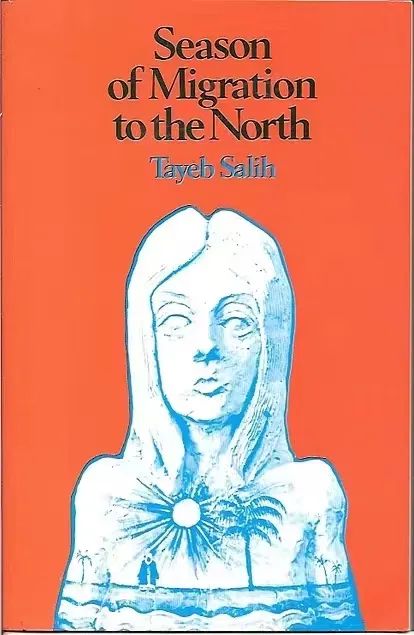
《移居北方的时节》,图片源自Yandex

四、《叠合》的理论意义与
局限性

自爱克曼于1835年出版《歌德谈话录》,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世界文学概念便登上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引起了广泛争议。在对中国传奇《好逑传》与法国歌谣诗人贝朗瑞的诗歌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歌德认为,“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同时,歌德指出世界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各个民族应该思想一致;而是说,各个民族应当相互了解,彼此理解,即使不能相互喜爱也至少能彼此容忍”。可见,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主要基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视角,致力于打破民族文学的封闭界限,使文学研究与交流能够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成果。马恩则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引发的生产关系变革出发,将世界文学概念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一维度之下,认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从地方的自给自足转向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必将引发文化领域的相似变革,所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歌德与马恩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了两种路径:一是如何依据世界文学背后的多元文化畅想实现民族文学间的广泛交流与文明互鉴;二是如何将世界文学置于资本主义这一框架体系之下来探讨资本主义进程对于文学生产与交流所产生的导向性影响。从世界文学理论在19至20世纪的发展变化来看,勃兰兑斯、奥尔巴赫、艾田伯等理论家大多遵循了歌德的理论路径,并从翻译、语文学、阅读等多个层面丰富了世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也大多将学科的谱系源头之一追溯至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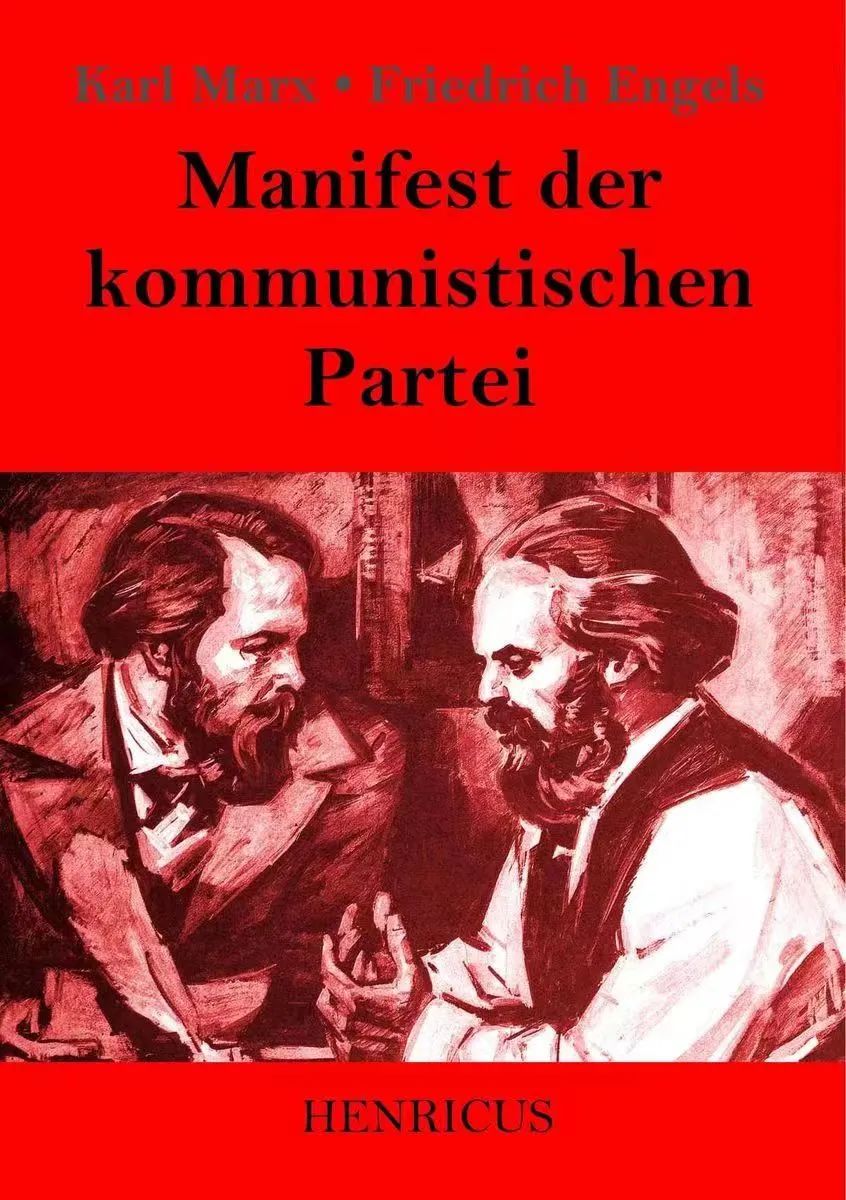
《共产党宣言》,图片源自Yandex
自21世纪以后,世界文学在方法论与理论层面得到更为深入的拓展,其中两种世界文学研讨取向尤为引人关注:一种是分析文本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过程中的流通、翻译、阅读等现象;另一种则关注文学作品对于流散、跨界、移民等现象的跨文化书写。第一种方法是达姆罗什(又译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提出的,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点:“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三、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第二种方法则主要源自强调文化身份观念重塑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作为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霍米·巴巴在建构混杂性身份观念的同时对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予以修正:“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可能是研究文化如何通过对‘他者’的投射来认识自己。曾经,民族传统的传承是世界文学的主要主题,而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提出,移民、被殖民者或政治难民的跨国历史——这些边境和边界的状况——可能是世界文学的领土。”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念正视了世界文学在流通过程的多元起源,使世界文学经典不再以欧洲为中心;霍米·巴巴则立足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文化冲突,着手挖掘流散族群跨文化创作的经典性。上述两种世界文学路径与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学界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息息相关。
尽管马恩对于世界文学的阐释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的理论源头之一,但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一框架下进行世界文学理论建构方面却一度缺少相应的学术进展。而华威充分调用托洛茨基、沃勒斯坦、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世界文学研究发挥了推动作用。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马恩将世界文学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关联起来,强调生产与流通方式的变革必然打破封闭的文化界限,使文学领域的生产与消费由民族走向世界。华威的创新之处则在于考察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叠合发展与不平衡对于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重点关注文学文本如何呈现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平衡,这也使华威得以从马恩的文本外部研究转向文本的内外研究兼顾。除对于马恩世界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外,《叠合》的理论贡献还可以从以下多个侧面予以把握。

霍米巴巴,图片源自必应
首先,《叠合》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状况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文学概念。世界文学自创生以来便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如果将世界文学定位为世界范围内全部文学作品的集合,那么它将成为一个难以把握的巨大实体。如果将世界文学定义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学经典,那么关于经典性的评价标准又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达姆罗什的奠基性意义在于从流通、翻译、阅读三个层面定义了世界文学。《叠合》一书将世界文学的“世界”定位为现代世界体系,使世界文学观念更明确地与现实世界格局、与历史建立关联,将理解世界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这一前提之下。在这一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下,华威敏锐地意识到比较文学学科建构中的唯心主义倾向,并对斯皮瓦克与阿普特的比较文学观念提出批判。
其次,在如何运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来建构世界文学观念这一问题上,《叠合》实现了对于莫莱蒂与卡萨诺瓦的修正。莫莱蒂与卡萨诺瓦在运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过程中都过于强调文学中心对边缘文学的导向性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双向影响模式及边缘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华威则重点关注边缘文学如何对现代世界体系进行书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非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由此产生了挖掘边缘文学的形式创新的潜能,为边缘文学的经典化建立了理论依据。
最后,作为利物浦大学出版社“跨学科的后殖民主义”系列丛书之一,《叠合》超越了既往后殖民研究在地域与族裔划分上所形成的学科界限。后殖民研究的兴起与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英语新文学(new literatures in English)等概念的提出息息相关。在这一学术谱系中,后殖民研究往往将自身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在反殖斗争中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殖民地。随着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的加剧,后殖民研究也将视角延伸至跨国空间中的族裔散居。然而,这一框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使其文学传统中的后殖民性被掩盖,这也使如何把握中心国家的少数族裔或土著文学的后殖民性问题成为富有争议的话题。此外,在欧洲或西方这一总体性空间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学传统也很少在后殖民语境中得到重视。后殖民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将前殖民地定位为边缘的同时却在结构的层面将其他处于类似境遇的文学生态排除在视野之外。纵观《叠合》一书,虽然后殖民文学因其创作主题上的优势而在全书的谋篇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叠合发展与不平衡的理论优势也使华威在建构世界文学理论时超越了后殖民研究所形成的学科界限,将冰岛、斯洛伐克、俄罗斯等国的文学创作与后殖民文学置于同一框架之下。华威既打破了后殖民、宗主国、中心、边缘、欧洲、西方等概念之间的僵化界限,丰富了后殖民研究的学术范式,又贯彻了达姆罗什对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倡议——“比较文学学者今后不需要的是更多的限制性立场,坚持认为只有一种文学、一种理论方法或一种政治标签在智力上或道德上值得我们去做……今天提倡一种或另一种方法来反对所有其他方法的努力,不太可能比其好辩的前辈有更长的保质期。”
当然,在认识到华威学术贡献的过程中也应该正视其不足。华威在时间跨度上缩小了世界文学的范围,这一做法无疑与世界文学畅想内在的包容性格格不入。如果说世界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体现在对现代世界体系中叠合发展与不平衡现象的书写,那么作家在描绘这一主题的过程中则往往会调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文学资源与文学形式来表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但传统的文学资源往往并非真正退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运作,而是可以借助新的时代背景予以多样化的解读,体现其现代性的价值。同时,从相关世界文学作品选的编纂来看,对边缘文学的重视本就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与变化具有一定关系,而中国、印度、韩国、越南等东方国家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正随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并不意味着要将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文学作品排除在外。在语言层面,华威在分析英语文学以外的作品时仅仅依赖英译本的做法也存在一定问题,对此,达姆罗什认为华威的理论缺陷在于忽略了“语言本身的物质性”,这造成华威没能将“萨利赫等作家完全置于其物质环境中”。总之,借助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世界文学的权力关系,并在此过程中挖掘边缘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正是华威为世界文学研究所带来的有益启示。然而,在这一观念实践中同样要协调好理论的局部视野与世界文学背后的包容取向,才能充分调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资源,建立普适性的世界文学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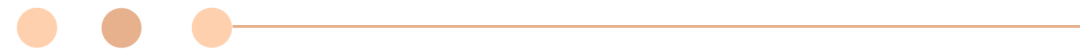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4期“域外近著评论”专栏,责任编辑王涛,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艾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雨璇 终审:文安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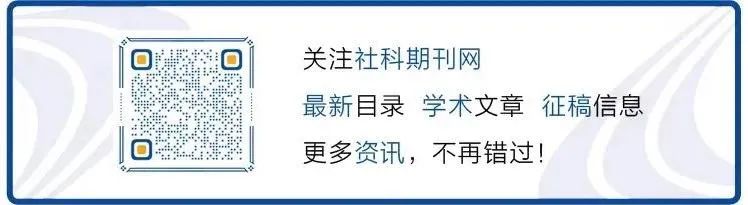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室 邮编:100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