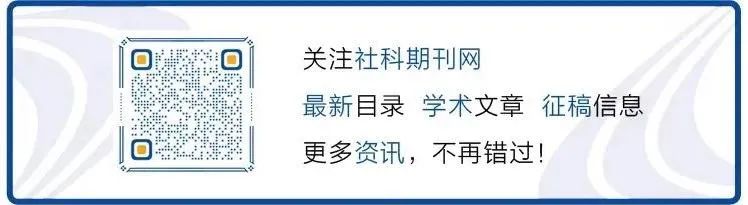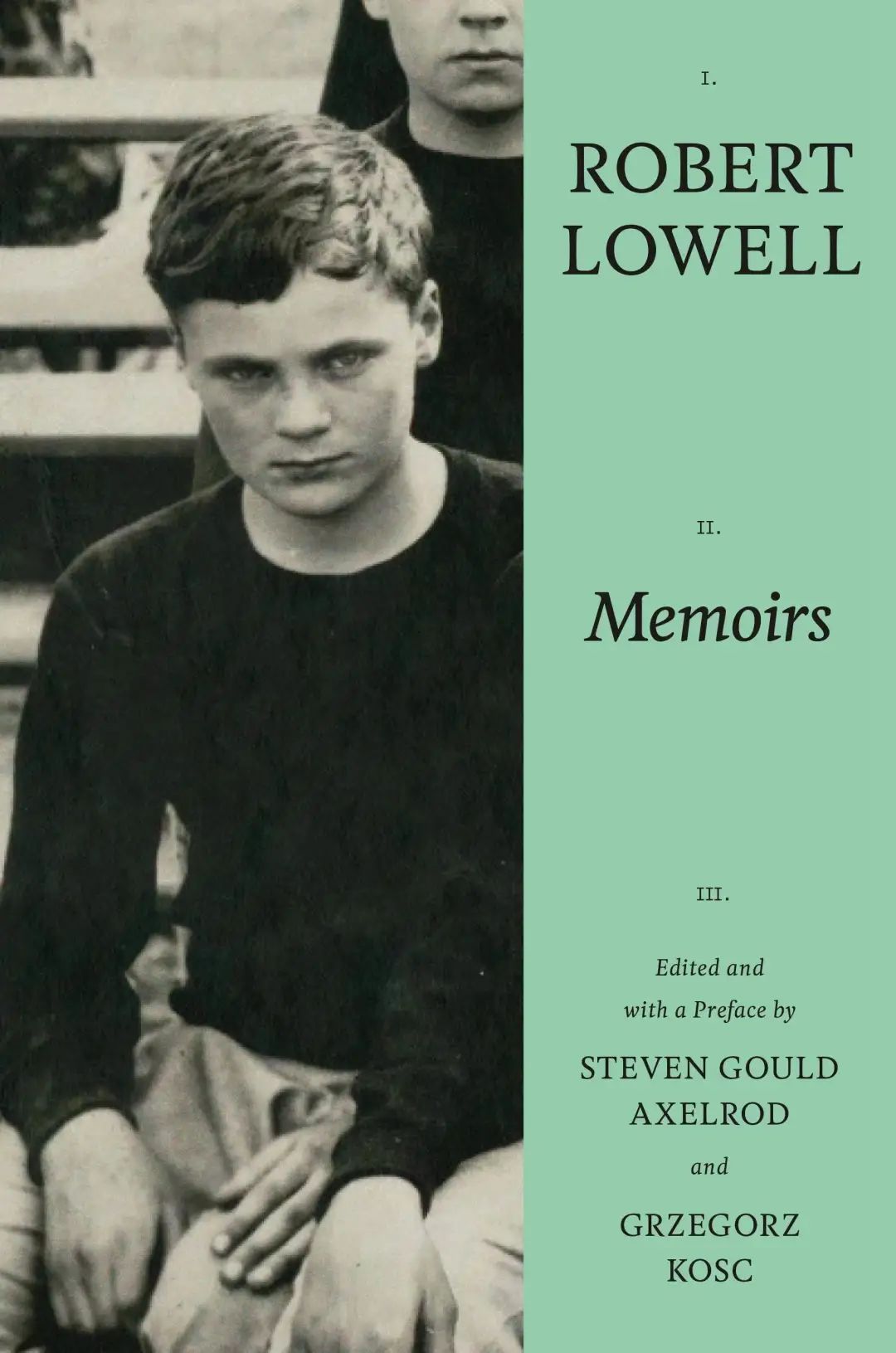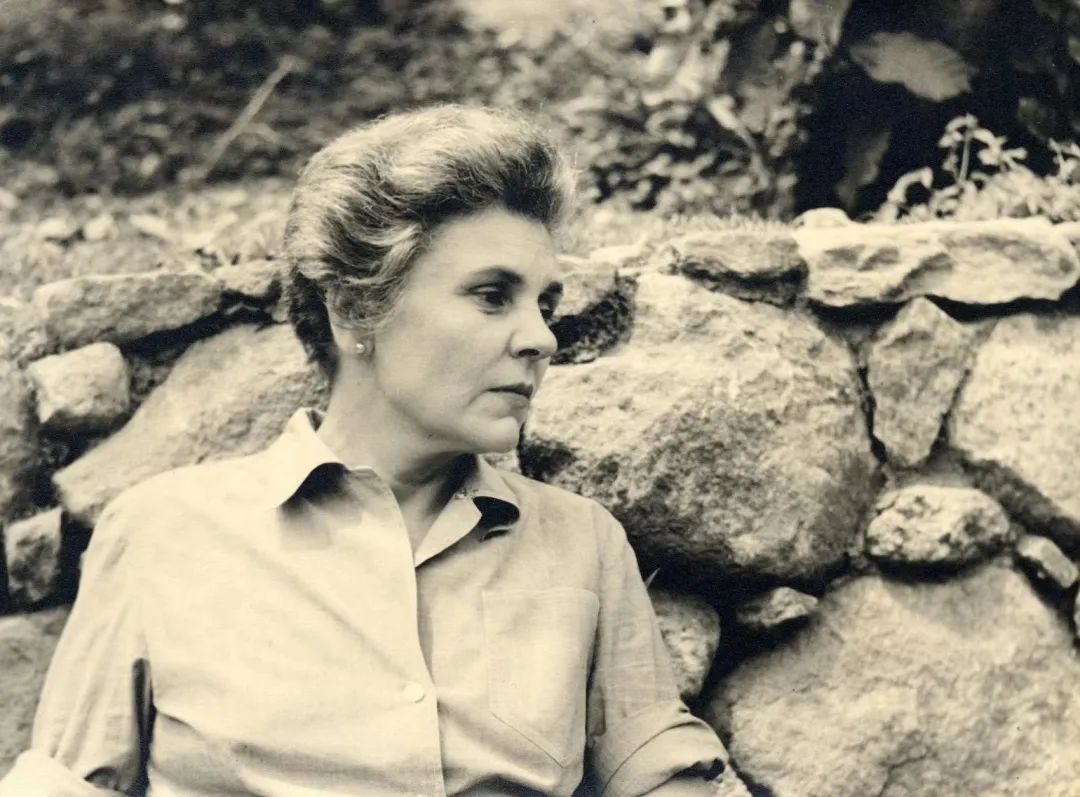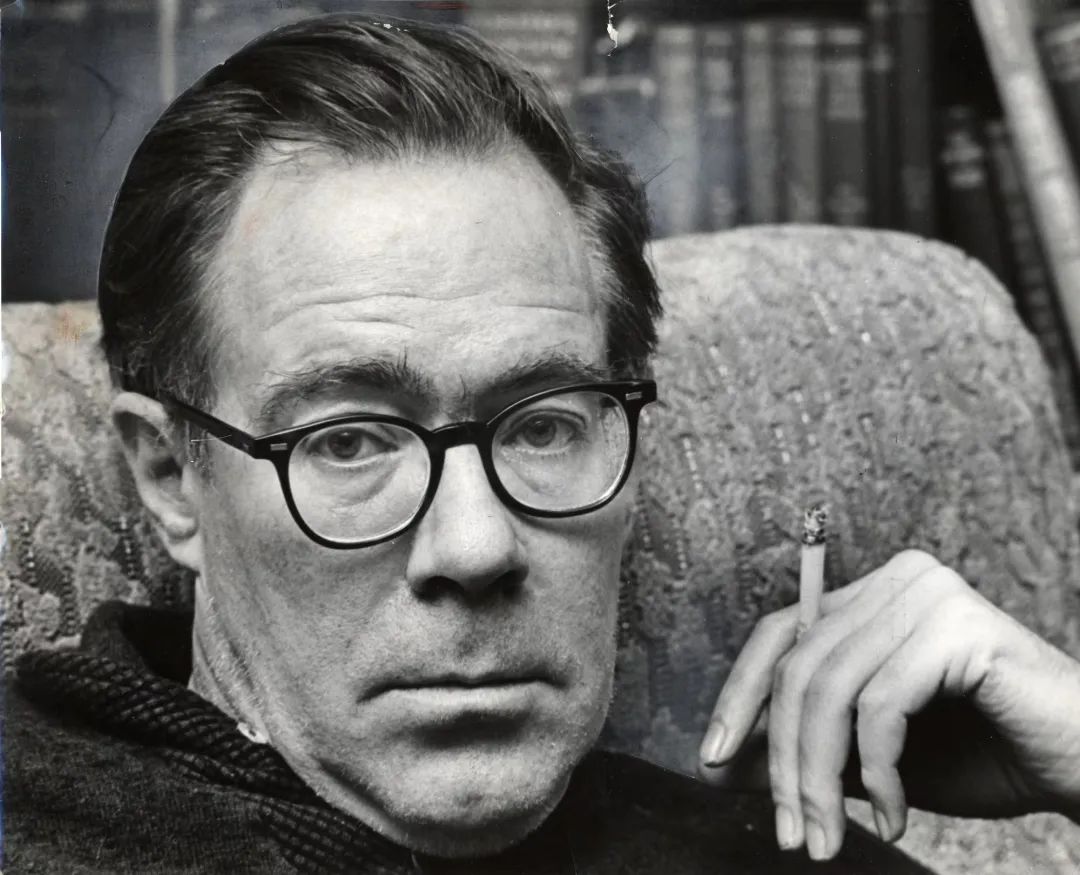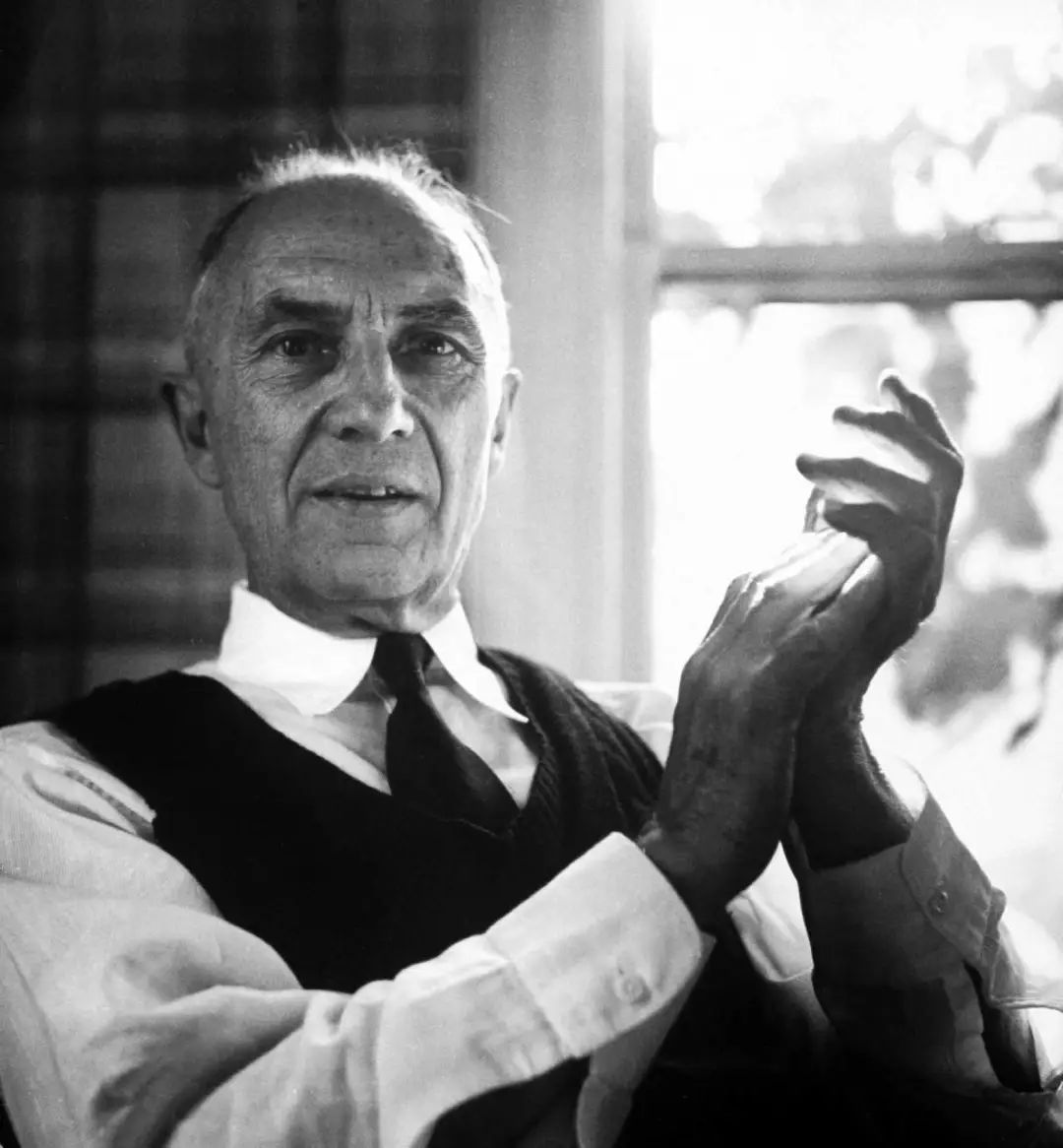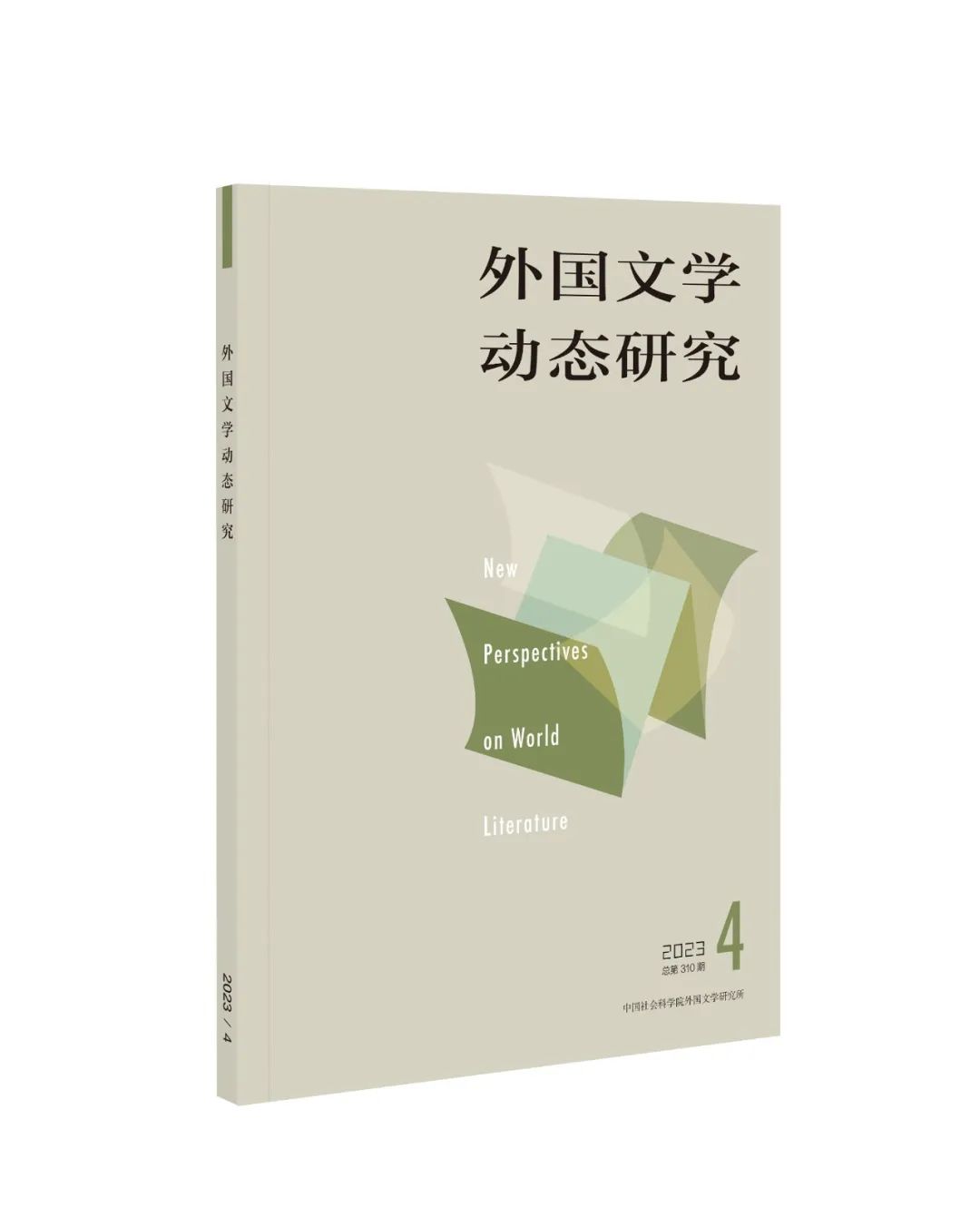域外近著评论 | 《罗伯特·洛厄尔回忆录》中的“文学发现”

殷书林,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诗歌与诗学批评。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公民〉中的种族形象定性与特雷沃恩·马丁案》(收入《上外法律评论》总第7卷,法律出版社,2021年)。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规划项目“罗伯特·洛厄尔诗歌中的历史与文化符号研究”(编号2018114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提要《罗伯特·洛厄尔回忆录》于2022年8月问世,首度全文发表了《我的自传》等洛厄尔的散文作品,被誉为“史无前例的文学发现”。本文结合洛厄尔的诗集《生活研究》和书信等文献,比较分析这部回忆录与吉鲁版《罗伯特·洛厄尔散文集》中的相关篇章,探讨《罗伯特·洛厄尔回忆录》的重要价值。本文认为,洛厄尔的自传写作对其诗风产生了直接影响,堪称《生活研究》的序曲;还原版《在平衡的水族馆附近》等篇章,客观反映了洛厄尔的创作初衷,对理解其人其诗具有关键乃至颠覆性意义;洛厄尔关于福特、泰特、兰塞姆、艾略特、庞德、威廉斯、贾雷尔、贝里曼、普拉斯和塞克斯顿等人的回忆与评价风趣幽默,是深入研究其文学关系和散文特色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 罗伯特·洛厄尔 《罗伯特·洛厄尔回忆录》 《罗伯特·洛厄尔散文集》
引 言



《生活研究》和罗伯特·洛厄尔,图片源自Yandex
著名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又译罗伯特·洛威尔,1917—1977)是20世纪美国诗歌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集《威利勋爵的城堡》(Lord Weary’s Castle,1946)、《生活研究》(Life Studies,1959)和《致联邦死难者》(For the Union Dead,1964)已成为美国诗歌史上的经典。他的散文作品亦颇丰,著名自传体散文《里维尔街91号》(“91 Revere Street”)先刊载于《党派评论》(The Partisan Review),后收入《生活研究》。1987年,在洛厄尔逝世十周年之际,罗伯特·吉鲁(Robert Giroux)主编出版了《罗伯特·洛厄尔散文集》(Robert Lowell: Collected Prose)。2003年,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弗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主编出版了大部头《罗伯特·洛厄尔诗集》(Robert Lowell: Collected Poems),再次掀起一股洛厄尔出版和研究热潮。此后,《罗伯特·洛厄尔书信集》(The Letters of Robert Lowell,2005)和《隔空絮语:毕肖普与洛厄尔书信全集》(Words in Air: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lizabeth Bishop and Robert Lowell,2008)相继问世,为研究洛厄尔其人其诗提供了重要文献。
2022年8月,诗歌评论家、洛厄尔研究专家、洛厄尔协会主席阿克塞尔罗德(Steven Gould Axelrod)与考斯克(Grzegorz Kosc)编辑出版了洛厄尔散文集的第一卷《罗伯特·洛厄尔回忆录》(Robert Lowell: Memoirs,下称《回忆录》)。这部散文集面世后广受好评,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学发现”。《回忆录》中的篇章与吉鲁版《罗伯特·洛厄尔散文集》有部分重叠,但是,阿克塞尔罗德明确指出,吉鲁在编辑过程中对一些篇章删减或改动过度,而《回忆录》则以原貌形式再现了洛厄尔的自传和评论等作品。
《罗伯特·洛厄尔回忆录》,图片源自Yandex
具体而言,这部回忆录呈现出三大亮点:一是它忠实再现了洛厄尔在1954至1957年间创作的《我的自传》(“My Autobiography”)的完整版;二是它指出了吉鲁在《罗伯特·洛厄尔散文集》中对一些重要篇章的过度编辑和删减,以原貌形式再现了《在平衡的水族馆附近》(“Near the Balanced Aquarium”)等核心篇章的本来面目;三是它完整收录了洛厄尔撰写的关于泰特、兰塞姆、福特、艾略特、庞德、威廉斯、弗罗斯特、沃伦、贾雷尔、贝里曼、普拉斯和塞克斯顿等作家的诗歌评论、回忆或悼文。这些资料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认识洛厄尔的童年创伤、家族衰落、精神病史以及他克服精神危机的心路历程,也有助于研究者认识散文创作对《生活研究》的直接影响,是研究现代主义、新批评、自白派诗学以及洛厄尔散文特色不可或缺的瑰宝。
一、 洛厄尔自传:《生活研究》的
奠基之作
《回忆录》收录了洛厄尔的两个自传作品,一是包括《战前波士顿》(Antebellum Boston)和《里维尔街91号》在内的《我的自传》,一是以《在平衡的水族馆附近》为核心篇目的《危机及后遗症》(“Crisis and Aftermath”)。前者记述了洛厄尔对童年创伤、家族历史、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回忆,后者则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他的躁郁症发作后在精神病院治疗和康复的经历。这两部自传均创作于他的代表作《生活研究》之前,无论从内容还是散文化风格来看,都称得上是《生活研究》的奠基之作。作家兼书评家查克拉博蒂夸赞它是“未发表过的宝石之作”。美国诗人兼评论家克莱因扎勒称“它值得拥有更多读者”,并且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许会成为最令人难忘的洛厄尔作品”。或许可以说,没有洛厄尔的自传写作,就不会有《生活研究》这部经典。
综合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洛厄尔创作自传的动因可概括为三点。其一,自传写作是精神分析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如阿克塞尔罗德所言,自传写作是“一种理解自我的方法”,一种“康复方式”。洛厄尔也认为,写作是“生命守护者”(a life preserver)。1954年2月,洛厄尔的母亲在意大利旅游时因中风不治而亡,他大受刺激,躁郁症发作,住进纽约医院的佩恩·惠特尼精神病诊所(Payne Whitney Clinic),接受“谈话疗法”(talk therapy,即精神分析治疗)和“职业疗法”(occupational therapy),并于1954年夏开始自传写作,一直坚持到1957年2月。六个月后,他开始创作《生活研究》第四部分“生活研究”中的诗歌。
其二,洛厄尔写自传也是为了克服创作瓶颈。他在发表《威利勋爵的城堡》后仅发表了《卡瓦诺家族的磨坊》(The Mills of the Kavanaughs,1951),且反响平平。1955年4月,他主动提出与吉鲁签订出版自传的合同,但最终并未履约。吉鲁在《罗伯特·洛厄尔散文集》一书的前言里推断说,洛厄尔“想让此法律文书作为创作的鞭策手段(a goad to writing)”。
伊丽莎白·毕肖普,图片源自Yandex
其三,洛厄尔创作自传很大程度上源自好友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激励和影响。1953年,毕肖普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了两篇著名的自传性散文《在那个村庄》(“In the Village”)和《格温多琳》(“Gwendolyn”),深受洛厄尔喜爱。在1954年1月1日写给毕肖普的信中,他盛赞这两部作品,认为它们“极具自传性”,是“一部新斯科舍成长小说的组成部分”。1954年11月14日,他对毕肖普说,他正在尝试写散文,但他觉得写散文并非易事,而是“地狱般的工作”。在1955年5月5日写给毕肖普的书信中,他透露了创作进度,还对其自传进行了一番自评:“整个冬季我都在尝试写自传,现在已经完成了大约一百页书稿。它相当蹩脚,不够严谨,而且很魔幻,但是,它也许能勉强过关。我喜欢不受格律阻碍的这种状态,我感觉无拘无束,可以随意深入散文的任何细节,毫无限制。”1955年5月20日,毕肖普再次写信鼓励他,“请你一定要写一部自传,或者,写一篇素描式简传。某种程度上讲,我创作的那两三篇这类作品是一种自我满足——满足了想坦白、想诉说真相的欲望”。
洛厄尔的自传写作不仅是心理分析疗法的组成部分,还为《生活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也对他的诗歌创作风格产生了直接且革命性的影响。《生活研究》被公认为洛厄尔诗歌风格变化的分水岭,是美国诗歌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研究《生活研究》的诗风转变问题时,国内外学者关注到了威廉斯、金斯堡、毕肖普等人对洛厄尔的影响,但大都忽视了洛厄尔的自传和散文创作与其诗风转变的密切联系。其实,洛厄尔生前多次提及他对散文和小说的浓厚兴趣。比如,在1961年《巴黎评论》的访谈中,他谈及想要开设小说课程,讲授“俄国短篇小说、波德莱尔、新批评乃至小说”。他认为“最理想的现代文学样式是小说”,因此,在创作实践中,他“想要[写]像散文一样流畅优美的东西”。1964年,在《论“臭鼬时辰”》(“On ‘Skunk Hour’”)一文里,他再度谈及小说和散文,称“诗歌的最佳风格,并非英语作品里众多风格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像契诃夫或者福楼拜的散文风格”。洛厄尔对散文风格的热衷由此可见一斑,而《回忆录》的问世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
洛厄尔诗风由现代主义向自白派模式的转变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渐进的。他的前期代表作《威利勋爵的城堡》和《生活研究》是这一演变过程的具体体现和重要见证。《威利勋爵的城堡》是深受现代主义和新批评理论影响的诗集,充满典故和象征,晦涩难懂。《生活研究》则体现出明显的过渡和变化:该诗集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运用大量圣经或历史典故、隐喻、象征和讽喻,语言晦涩,仍然体现出显著的现代主义诗歌特点,其中多首诗先后于1953年和1954年在不同期刊上发表过,比如《越过阿尔卑斯》(“Beyond the Alps”)发表在1953年夏的《肯庸评论》(Kenyon Review)上,《就职典礼日:1953年1月》(“Inauguration Day: January 1953”)发表在1953年11月的《党派评论》上,《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发表在1954年4月的《邂逅》(Encounter)上。
但是,第二部分即自传散文《里维尔街91号》和第四部分“生活研究”中的诗歌,或是其前期自传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基于自传内容而创作的诗歌。《生活研究》于1959年4月在英国首发时并未包括《里维尔街91号》,同年在美国发行时,才收为诗集的第二部分。这一变化标志着洛厄尔诗风的重大转变。评论家罗伯茨称,“它给《生活研究》提供了一个间奏曲,标志着洛厄尔诗歌主题与技巧的变化。它还介绍了诗人的家族和不和睦的家庭,因而更能与后续诗歌中的‘研究’形成呼应”。第四部分的诗歌创作主要在1957年8月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完成,其速度之所以如此迅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传书写奠定了基础。
比较《回忆录》中的自传部分与《生活研究》中的“生活研究”,可以发现,《指挥官洛厄尔》(“Commander Lowell”)、《贝弗利农场的临终日子》(“Terminal Days at Beverly Farms”)、《我与温斯洛舅舅的最后一个午后》(“My Last Afternoon with Uncle Devereux Winslow”),《从拉帕洛远航回家》(“Sailing Home from Rapallo”)和《从忧郁中醒来》(“Waking in the Blue”)这些诗歌中的人物、事件等元素均出自回忆录内容,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可以说,洛厄尔的自传为客观、深入诠释《生活研究》提供了可靠文献,而自传和诗歌两种文学样式所呈现出的特点也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 作为隐喻的“水族馆”:
“失衡”与“平衡”之辨
《回忆录》收录了未曾发表的洛厄尔自传,完整呈现原作,对客观、准确理解和诠释洛厄尔的自传和诗歌等作品具有重要价值。
吉鲁在编辑《罗伯特·洛厄尔散文集》的过程中对多篇文章的标题、语句乃至段落内容等进行过改动、删减或置换。比如,他把《费城》(“Philadelphia”)这篇内容迥异的散文添进了《战前波士顿》,把《福特·麦多克斯·福特的〈意外之获〉序》(“Foreword to Ford Madox Ford’s Buckshee”)的标题改为《福特·麦多克斯·福特》。事实上,洛厄尔在《生活研究》中还发表了《福特·麦多克斯·福特》一诗。《回忆录》中还原了该序言的标题,还新收录了关于福特的另一篇回忆录《福特·麦多克斯·福特琐忆》(“Memories of Ford Madox Ford”)。
吉鲁对洛厄尔自传最伤筋动骨的编辑当属收于《危机与后遗症》这部自传中的文章《在平衡的水族馆附近》。他把原稿标题中的“平衡”(Balanced)改为“失衡”(Unbalanced),文章题目由此变成了《在失衡的水族馆附近》(“Near the Unbalanced Aquarium”),而且他还删去了原稿中长达近七页的“倒叙”(flashbacks)内容。更成问题的是,手稿中原文长约三页的结尾被误放在了另一文件夹里,吉鲁当时不仅没有发现,而且自作主张从手稿《两年来我才渐渐平静下来》(“For Two Years I Have Been Cooling off ”)一文中截取、拼凑出了一个结尾。
阿克塞尔罗德在《回忆录》的引言和第二部分的简介中对吉鲁版《在失衡的水族馆附近》中“过度修剪”(heavily pruned)的不合理性做了充分说明。他还与考克斯合作撰写了《罗伯特·吉鲁与洛厄尔的〈在平衡的水族馆附近〉的编辑问题》(“Robert Giroux and the Editing of Lowell’s ‘The Balanced Aquarium’”)一文,详细论述了吉鲁的过度编辑对该文创作意图的淡化、对读者的误导以及对阅读体验的负面影响。他们指出,吉鲁把原标题中的“平衡”改为“失衡”,“具有误导性”(disorient),……抹杀了其原初隐喻”,使得这篇自传中建立的“康复之路这个框架从一开始便遭到破坏”。从《回忆录》收录的《两年来我才渐渐平静下来》一文,可窥见吉鲁编辑对水族馆一文的“破坏性”影响。该短文仅有四段,第一段开门见山,述说自己病情在逐渐好转:
两年来我才从三个月的病理性狂热中渐渐平静下来。现在我能轻易入睡,但有时候会惊醒。在梦中,我就像米开朗基罗制作的凹凸不平的雕塑,滚下山坡却完好无损。醒来时,我仿佛被毒打了一顿,每一根神经都仿佛被橡胶软管击打过似的。
接下来,洛厄尔谈到写自传的目的是“为了消磨时间”,又述及他写自传时联想起他人的一部自传,一部电影。主人公是一只㹴犬,名为“燃烧的房子”,其母被遗弃,其父是红遍天下的打斗冠军,而它决心成为冠军,杀掉其父。最后,它如愿以偿,得到了想要的“平静”(peace)。在最后一段,洛厄尔从该自传中的父子关系联想到自己与父亲的不和谐关系以及对“平静”的期许:“我父亲是一个温顺、忠诚、混沌之人。我不明白为何我曾如此反抗他。我希望能得到平静。”洛厄尔的父亲于1951年去世,《生活研究》中《在贝弗利农庄的临终日子》一诗的主人公就是他,而《两年来我才渐渐平静下来》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洛厄尔的疾病在渐渐好转,表达了他对“平静”生活的祈愿,与“平衡”论吻合。
然而,吉鲁删去了这篇短文中表达“平衡”意旨的第一段,仅选取后三段作为《在失衡的水族馆附近》的结尾,这一缺乏依据的嫁接不仅破坏了原作的完整性,也有故意回避“平衡”说之嫌。这一编辑手法与休斯当年对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阿里尔》(Ariel,又译《爱丽尔》)的操作如出一辙,经过休斯的删减和增添,普拉斯原作所表达的“重生”主题被改成了“自杀”意图。
在洛厄尔原稿中,“水族馆”这一隐喻出现在篇章结尾部分,因此,吉鲁版本里未曾出现这一隐喻。在原稿的结尾,洛厄尔叙述了自己康复后即将出院时的情景,他当时既“高兴”(pleased),又“伤心”(hurt)。其中有一段是关于水族馆的描述:
下方,在走廊尽头,日班导医员莫丝小姐对着平衡的水族馆大惊小怪:这是个庞然大物——里面有蜗牛、水生植物、长了七个尾巴的小鱼、袖珍太阳鱼和袖珍海鲢。她抱怨说,没有一个护士懂得“平衡”,还老是把面包屑和死苍蝇投进水里,结果鱼和蜗牛不知道是过来还是离开。我常开玩笑说,那水族馆是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院,“只有我不在展示之列”。
精神病院里的水族馆是为了“帮助精神病患者镇静下来”。水族馆里的水、植物和鱼等生物构成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原本处于平衡状态,而随意投放面包屑和死苍蝇必然破坏其生态环境,那位护士的抱怨是力图保护其生态系统的平衡。
洛厄尔称水族馆是“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院”,其实道出了水族馆这一隐喻的内涵,即精神病院是患者从疾病中重获平衡和康复之地。阿克塞尔罗德认为,“平衡的水族馆”这一隐喻恰巧是洛厄尔住院治疗想要表达的意图,即“在渴望秩序与接受紊乱之间寻求微妙平衡”。由此可见,《在平衡的水族馆附近》讲述的是一位精神病人的内心挣扎与为康复而付出的努力。如阿克塞尔罗德在序言中所概括的那样,它与其他自传篇章一起讲述了“一个痛苦灵魂的有力故事,一位作家怀着勇气与自律,探寻一条前进之路的故事”。
阿克塞尔罗德“平衡说”的合理性以及洛厄尔对治愈的渴望还可以从洛厄尔的自传、书信和诗歌中得到进一步佐证。洛厄尔所患的躁郁症,即“双相情感障碍”,当时医学界认为是可以治愈的,因此,洛厄尔对病愈始终充满期待。比如,在《我患了严重周期性躁郁症》(“I Suffer from Periodic Wild Maniac Explosions”)一文里,诗人明确表达了渴望治愈或减轻病情的强烈愿望:“我渴望心理疗法能根治这两种极端情绪,或者,至少让它们变得温和些,这样,在未来我就可以主动采取紧急预防措施,再也不会失控。”在文章结尾,洛厄尔再次表达了希望通过治疗回归正常生活的愿望:“我想继续原有的生活——婚姻、教学、创作。我认为,治疗能教我不放弃、不逃跑。我想我能学会眼脑并用。我希望能够发现自己的过错,并加以改正,做一个好丈夫、一个不断成长的作家和一名稳定而称职的老师。”在1959年3月30日写给毕肖普的信中,洛厄尔讲述了住院治疗情况,并表达了对治愈与活下去的信心。他写道:“我的治疗(一周三次)确实神奇,我期望,到明年这个时候我的心结就会解开。我的确想活下去,活到两鬓斑白,依然在成长。过去十年的苦难似乎得到了补偿。”在《生活研究》中的《三个月后回到家里》(“Home After Three Months Away”)一诗中,洛厄尔写到他的病“治愈了”(cured),表达了出院回到家后与女儿团聚时的欣喜。
约翰·贝里曼,图片源自Yandex
洛厄尔的精神疾病在20世纪50年代并非个例,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时代的产物。他在《西街和乐普克琐忆》(“Memories of West Street and Lepke”)一诗中,称50年代为“被镇静的50年代”(the tranquilized Fifties),其中包涵多重意蕴。从字面上讲,它明指洛厄尔患病服用镇静药的那个50年代,亦指镇静药“眠而通”(Miltown)广为流行的50年代。从政治和文化层面看,它又喻指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遵从文化和消费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与压抑所起到的“镇静”作用。自白派诗人贝里曼、斯诺德格拉斯、普拉斯和塞克斯顿等都经历过心理分析治疗,而且多以自杀而终。贝里曼在《梦歌·一五三》(“Dream Song 153”)里,对一代诗人的命运发出了与金斯堡一样的愤怒之声:“我憎恨上帝,他毁掉了这一代人。”贝里曼憎恨上帝先后夺取了泰特、理查德、兰德尔、德尔默和普拉斯的生命,憎恨他“让傻瓜们活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触及洛厄尔”。
其实,洛厄尔的作品显示他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只不过他具有“活下去”的勇气和意志。比如,在贝里曼自杀后,洛厄尔为他创作了挽歌《献给约翰·贝里曼》(“For John Berryman”)。在这首诗里,他不仅认同贝里曼在《梦歌·一五三》中表达的观点,认为他们那一代诗人“具有相同的命运”,同时,他还借用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对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称呼,说他们一代也是“被诅咒的一代”(“Les Maudits”)。在该挽歌中,洛厄尔坦言:“我曾一直想要活下去/以免你为我写挽歌。”在当时,“活下去”既是对命运、对世态的抗争,更是朋友间、诗人间相互强有力的鼓励与鞭策。这些诗行饱含洛厄尔对朋友的关心以及不屈于命运的意志和永不言弃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始终贯穿在他的生命与作品中。因此,“平衡”是洛厄尔在自传中表达出来的愿望,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与吉鲁版《在失衡的水族馆附近》相比,《在平衡的水族馆附近》不仅还原了洛厄尔原作的本来面目,而且更加凸显了洛厄尔散文的文学性。复原版不仅再现了标题中“平衡的水族馆”这一隐喻,也与结尾中的水族馆和患者得以治愈出院、获得“平衡”的主题相呼应,奠定了整篇散文的基调。从叙事策略看,洛厄尔以住院康复经历为叙事主线,又不时以倒叙形式讲述自我成长经历中的人与事,暗示这些人和事对他的影响以及与他所患疾病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此外,洛厄尔还借助照片和记忆,运用想象重新建构他不可能见到的场景,比如他父母的约会和婚礼场景等。这些基于他对父母的认知而创作的回忆场景虽属虚构,却亦幻亦真,幽默而风趣。
三、 作家群像中的自我画像
《回忆录》的第三部分《作家群中的人生》(“A Life among Writers”)创作于1959至1977年间,主要收录了洛厄尔对一些作家的回忆和评论,包括对他有重要影响的泰特、兰塞姆、福特、弗罗斯特、庞德、艾略特、威廉斯,包括其同辈诗人贾雷尔、贝里曼,也包括塞克斯顿和普拉斯等,最后一篇是他的著名自评随笔《读完六七篇关于我的评论之后》(“After Reading Six or Seven Essays on Me”)。这些评论或回忆绘就了一幅作家群像,也从侧面绘出了洛厄尔作为学徒、秘书、朋友和评论家的生动自画像。评论家赫尔曼·萨特曾给予这一部分高度评价,认为这一部分对研究美国现代主义而言是“一件值得珍视的藏品”。
作为美国诗歌史上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代表诗人,洛厄尔扮演着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角色。作为一个波士顿“婆罗门”(Brahmins)家族的后裔,他原本可以在哈佛完成学业,按照父母的期望规划人生,然而他却中途辍学,前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南方肯庸学院,师从兰塞姆和泰特,并结识了贾雷尔等同辈诗人和评论家,从而开启了他的从艺人生。
兰色姆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图片源自Yandex
对洛厄尔产生直接影响的有现代主义、新批评诗学理论以及毕肖普和贾雷尔等同辈诗人,他视兰塞姆为他的“知父”(intellectual father),称泰特为“田纳西版的艾略特”。在《读完六七篇关于我的评论之后》一文里,洛厄尔明确指出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诗人,即泰特、威廉斯和毕肖普。他首先模仿的是泰特,并认为自己“在模仿缪斯”,后来他又“被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伊丽莎白·毕肖普深深吸引”。初读威廉斯的自由体诗歌时,洛厄尔被“震撼得五体投地”(knocked over)。他感到自己“先前的创作宏大却无章法,缺乏时代性又陈腐守旧”,读了威廉斯以后,“先前的一切就都结束了”。因此,洛厄尔称威廉斯是诗歌创新革命的“榜样、解放者”,他的风格就是“美国风格”(the American style),他的“《帕特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草叶集》”。
谈及诗歌派别之间的论争时,洛厄尔详述了新批评派的创作宗旨以及威廉斯诗学的革命性意义,他说:“我所属的阵营,即泰特和兰塞姆阵营,倡导高度严谨,倡导用历史之铠甲全副武装。诗人需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创作,表达其全部智慧、激情和精微妙处。诗人有必要灵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希腊罗马经典、伊丽莎白时代的诗剧、17世纪玄学派诗歌传统,以及古今评论家、美学家和哲学家的东西。”
《作家群中的人生》没有收录洛厄尔关于毕肖普的散文,却收录了洛厄尔关于同代诗人贾雷尔和贝里曼等人的评论。他们与毕肖普一样,对洛厄尔有重要影响。以贾雷尔为例,洛厄尔在肯庸学院与其相识,并结下终生友情。在《兰德尔·贾雷尔简介》(“Introduction for Randall Jarrell”)一文里,洛厄尔谈及1937年首次把习作交给贾雷尔后得到的负面回应——“嗤之以鼻”(sniff of disgust)。洛厄尔认识到,贾雷尔的“诚实与权威”使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在漫长、无法预见的学徒道路上必须信赖的声音”。贾雷尔的确是一位独具慧眼的批评家,他在评论洛厄尔的《异样的国度》(Land of Unlikeness,1944)时断言,洛厄尔是“一位前途无量的诗人”,并大胆预言,“接下来几年里,一些最优秀诗歌将出自他的笔端”。洛厄尔称贾雷尔“绝对是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诗歌评论家”,或许正是因为贾雷尔在他“漫长的学徒道路上”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艾略特,图片源自Yandex
洛厄尔对福特、艾略特、庞德等诗人的评论或回忆同样体现出这些诗人对他的影响,同时,也对研究这些诗人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洛厄尔并不赞同评论界关于艾略特的《荒原》是“时代的反映”一说,而认为它是“内心发出的呐喊”(an inspired cri de coeur),是“个人的、发自内心的异质呐喊”。他对福特的回忆对福特研究也有重要价值。福特研究专家马克斯·桑德斯(Max Saunders)认为,福特的诗歌以“偏口语化”为特征,即“休弗式”风格(休弗是福特的另一个名字),读起来像“意识流”,至于这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则“难以追溯”。洛厄尔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琐忆》和《福特·麦多克斯·福特的〈意外之获〉序》中却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文中显示,福特集“健谈者”和“作家”于一身,其诗歌偏口语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创作方法是口述式的”。洛厄尔曾担任福特的记录员并称那是一份“苦差事”,因为他不懂速写,打字也不熟练,生怕会遗漏。洛厄尔的评论风格是“随意的”“直觉式的”,却不乏极具文学性的比喻和连珠妙语,他在评论或回忆中还记录了许多其他作家的逸闻趣事,表现出他们风趣与幽默的一面。
结 语
长期以来,学界对洛厄尔诗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伊恩·汉密尔顿的《洛厄尔传记》(Robert Lowell: A Biography,1982)和吉鲁的《罗伯特·洛厄尔散文集》等书中一些难以证实的信息或主观臆断内容的影响,导致对洛厄尔本人及其诗歌的某些误解或误读流传甚广。诺奖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移居美国初期曾经认为他患躁郁症是装病,但是,在深入认识和体验美国文化和政治后,他改变了对洛厄尔的态度,于2000年为洛厄尔创作了“一首迟到的诗”——《致罗伯特·洛厄尔》(“To Robert Lowell”),以示歉意、同情与哀思。
《回忆录》也全面反映出洛厄尔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体现了他在自传、诗歌评论和回忆录等方面的独特风格,使读者进一步领略其散文的风采。如克莱因扎勒所言,“罗伯特·洛厄尔因诗歌而闻名于世。但他的回忆录表明,在散文方面,他也绝非等闲之辈”。评论家马乔瑞·帕罗夫也表达过相同观点,她称《我的自传》和《在平衡的水族馆附近》本身就是“绝妙的充满诗意的文本”(superb poetic texts),甚至比基于这些自传素材、使用其中词汇和意象而创作出的抒情诗更为优美。由此可见,这部回忆录既有重要文献价值,也有其独特文学价值,亟待深入研究。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4期“域外近著评论”专栏,责任编辑龚璇,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萌
排版:王雨璇 终审:文安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