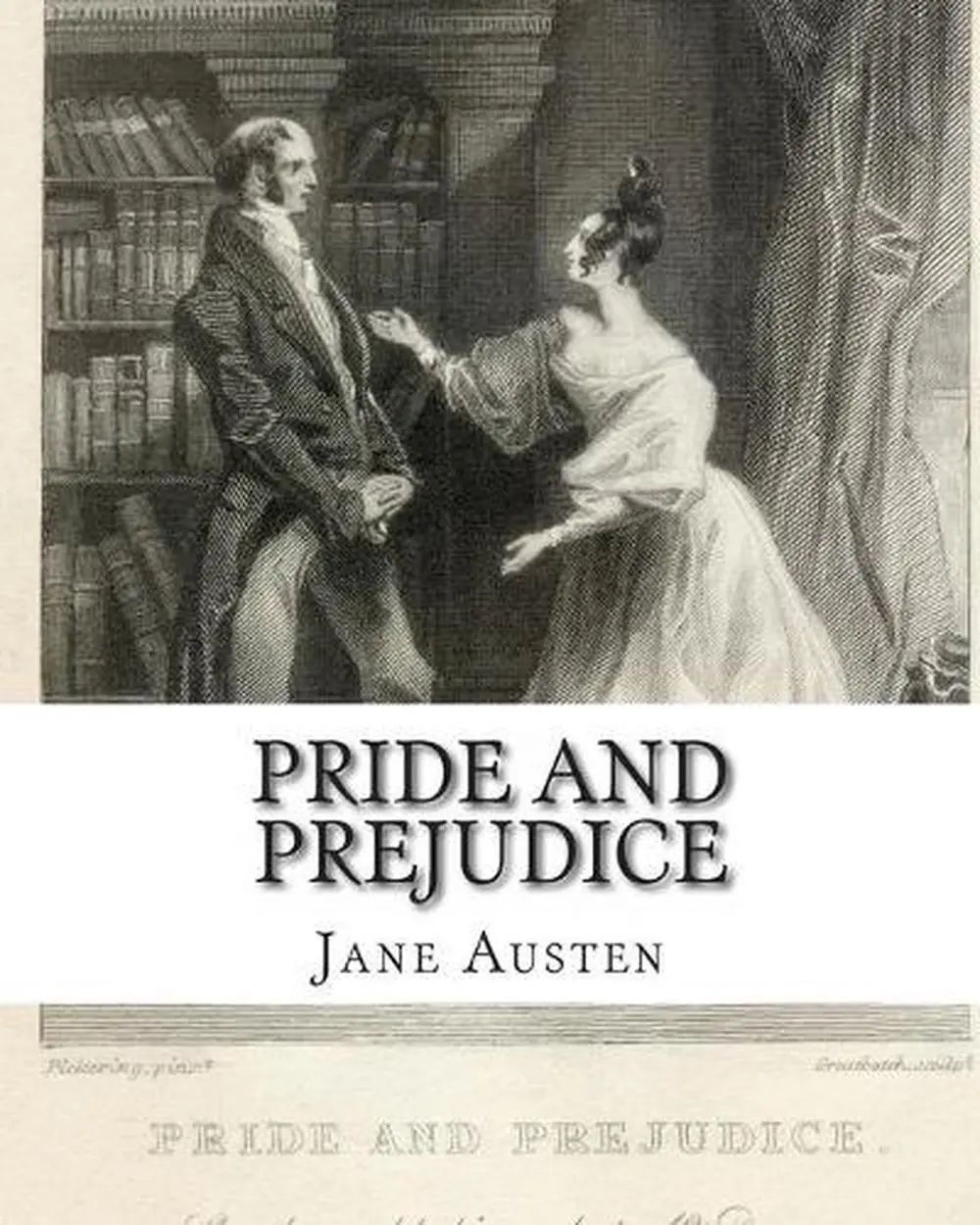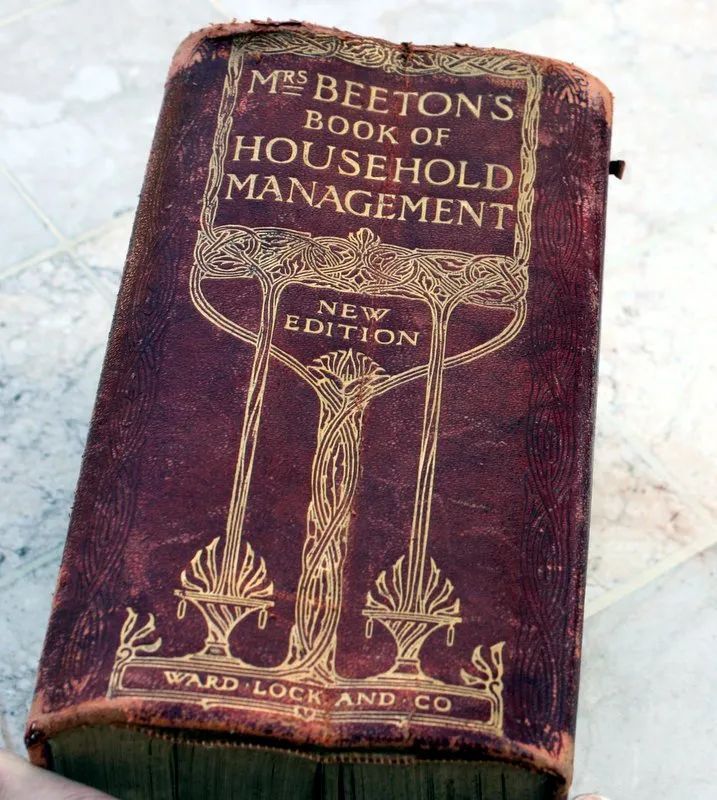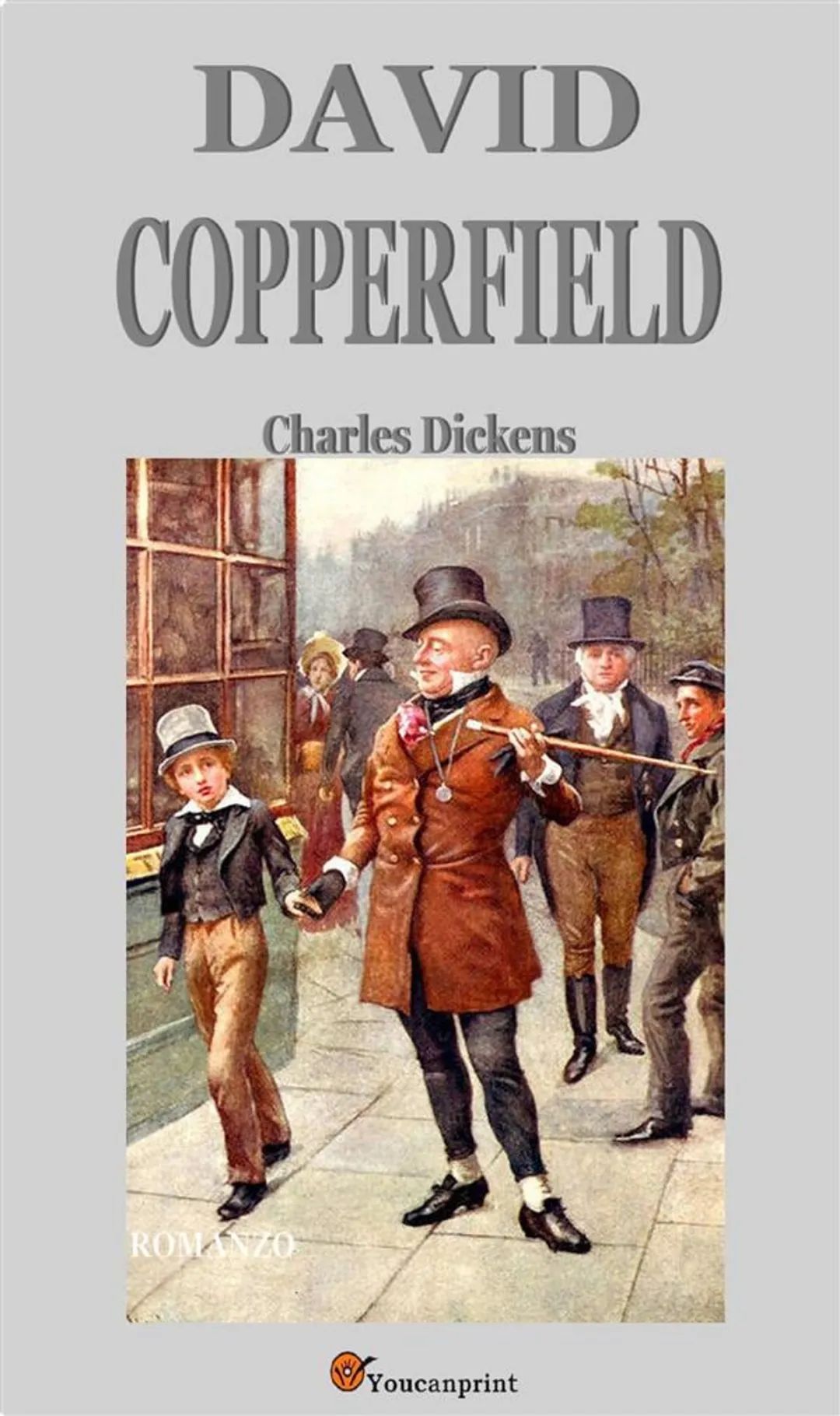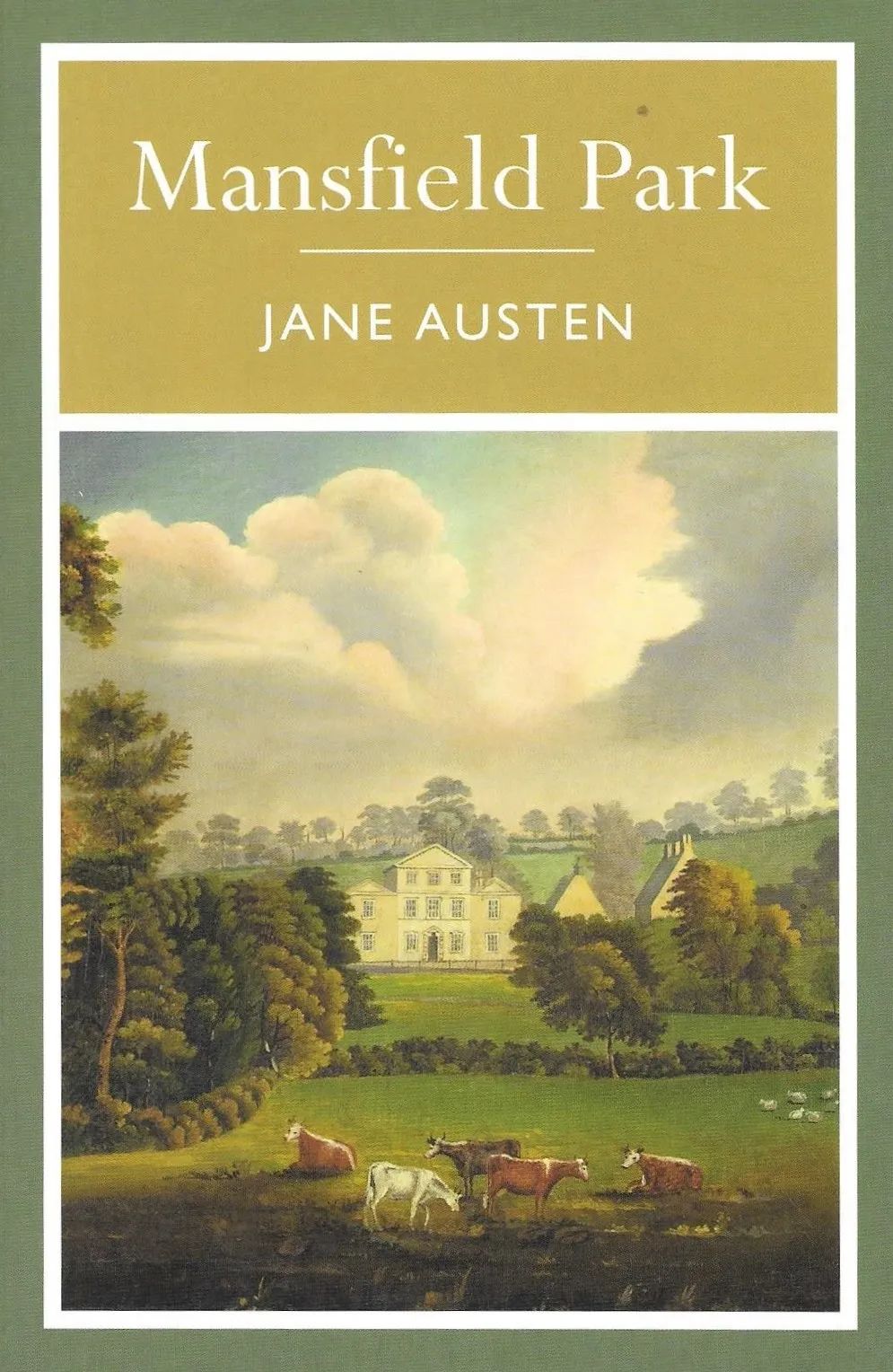文化研究丨维多利亚人对舒适的追求——以《英国妻子》与《大卫·科波菲尔》为例

傅燕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英国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老姑娘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雅文化——〈克兰福镇〉的淑女兼及〈爱玛〉》(载《外国文学》2022年第4期)。
内容提要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凭炫耀性消费彰显身份的风气盛行,中产阶层无视本阶层的经济实力,盲目仿效贵族的奢华生活方式。这种现象引起了维多利亚时代思想者的警觉。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行为指南的作者萨拉·艾利斯和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分别基于自身的性别与阶层,倡导一种与身份相匹配的、以提升生活舒适度为导向的生活方式。这种舒适而不奢华的生活方式以美德为根基,又可缓解焦虑、赢得体面、孕育美德、提升幸福,满足了维多利亚人的多重人生诉求。这种务实中庸的人生追求在中产阶层中表现最为明显,却又不局限于这个阶层。
关键词 舒适 维多利亚人 萨拉·艾利斯 《大卫·科波菲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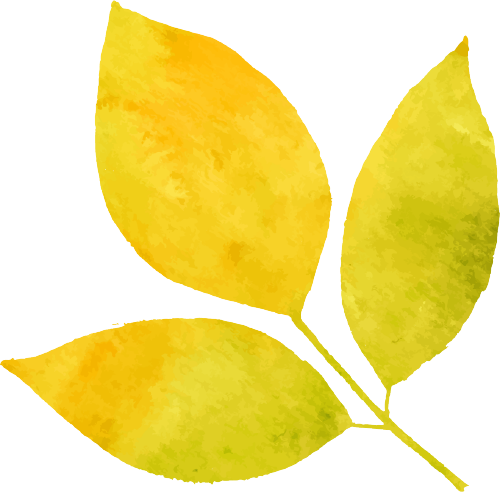
在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1813)中,伊丽莎白的堂亲柯林斯牧师向她求婚不成,转而向她的女友夏洛特·卢卡斯小姐求爱,竟然得到了回应。伊丽莎白满心疑惑,夏洛特的回答却简单得很:“我仅仅想要一个舒适的家。”夏洛特的婚姻不以浪漫爱情为基础,这容易让人以为她口中的“舒适”纯粹指柯林斯能够为她提供舒服安逸的物质生活。到18世纪90年代,更大一部分英国人已经能够获得让生活变得舒适的物品或设施。达西后来到访柯林斯家,在客厅里与伊丽莎白闲聊,也提到“这栋房子看着很舒适”。柯林斯的牧师住所、经济收入无疑为舒适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是,即便如此,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起初并不被伊丽莎白看好,直到去夏洛特家做客时,伊丽莎白才有了看问题的新视角。她看到夏洛特家里“一切都布置得整洁、有条理”,认为“这都应该归功于夏洛特”。夏洛特生性务实,深知女主人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凭着智慧在无爱的婚姻里创造出一种舒适的状态,获得了一种中间态的幸福,也得到了奥斯丁的认可。这种幸福既依赖于适度富足的物质条件,也有赖于女性创造舒适的能力。
简·奥斯丁和《傲慢与偏见》
图片源自Yandex
在19世纪的英国,更多人有财力也热衷于追求舒适。甚至女王夫妇也投身其中。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积极在白金汉宫官邸之外寻找舒适的私人家庭居所,于1845年购入怀特岛的奥斯本庄园(Osborne House),1852年又购入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Balmoral Castle)。从居所建筑的设计到花园树木的栽种,阿尔伯特亲王公务繁忙,却仍然亲力亲为,在重建这两处乡间别墅上投入了大量心血。在巴尔莫勒尔城堡,维多利亚女王感受到每一个地方都是“亲爱的阿尔伯特亲手创造,亲手劳作,亲手建造,亲手设计;……他高尚的品位与亲手的印记到处可见”。而奥斯本庄园给他们的感觉是“舒适惬意”。在那里,“这对夫妇可以尽情沉浸在幻想里,想象着他们就像英国任何一个中产阶层家庭一样”。女王夫妇厉行节约,努力与中产家庭保持一致步调,一心要享受普通人的幸福。虽然无法与王室相提并论,维多利亚女王的民众也有自己的舒适图景。典型的惬意地方是客厅壁炉前,矮桌、沙发、安乐椅随意围成的一个角落,有欢乐的家人陪伴左右。在这温馨的一幕里,看得见的是家具随意摆放(一改靠墙而立的规则)带来的悠闲安适,看不见的是女性所营造的舒适家庭生活,这才有了一家人脸上满足的表情。从中还可看出,维多利亚人向往的舒适以两性分工合作的家庭生活为主要载体。维多利亚人对舒适的追求,关乎家庭、幸福、美德、体面与品位,既是对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适度幸福的务实求取,又是对美德、精神升华的孜孜以求。
一、 舒适:一种生活方式
从词义的发展来看,“comfort”数世纪以来一直指的是身处困境中的个人或集体获得的一种道德、情感、精神或政治上的支持,直到18世纪才多了身体的舒适(physical comfort)这一层含义,反映在18世纪的消费革命中是人们的偏好在“文雅”之外多了“舒适”的选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雅(gentility)一直是英国中上层家庭物质文化的主导要素。直到18世纪,舒适才成为物质文化中一个关键性的价值标准。到了19世纪,在物品的批量生产与工业革命推动下,舒适从特属于中上层家庭的价值标准转化为一种“民主化”的生活状态:更多人能够享用舒适物品、设施与服务。从住房的取暖、照明与通风到服饰的布料与款式变化,从食物的多样与丰盛到火车等便利公共交通服务的启用,这一切都见证了大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世纪的英国,舒适被用以描绘越来越多人可获得的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与身心安宁的理想生活状态。更多英国人的生活中多了一项重要内容:追求舒适。其中,对舒适物质生活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求得身体的安适,最终获得心灵的自在满足。
维多利亚人热衷于追求的舒适具体指身体需要得到满足时身心体验到的放松愉悦、自在安适的知足状态,也包括了催生这种状态的物质条件。身体需要不仅包括生理上的基本需要,还包括维多利亚人眼里达到基本体面标准的文化建构的需要。维多利亚人为满足身体需要,不仅需要使人愉悦的舒适物品或设施,还需要以提高舒适度为导向的生活方式。本文关注的正是维多利亚人对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身心舒适状态的追求,这从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繁荣的中产阶层指南书出版市场中可见一斑。维多利亚时代出版了大量女性行为指南(conduct books)、家庭杂志、家政管理书,从中可以看出,舒适是广大中产阶层向往的理想生活状态。这些具有指南性质的书或杂志都涉及持家与家务管理问题,但各有专攻。比如,伊莎贝尔·毕顿(Isabella Beeton)闻名天下的《毕顿太太的家庭管理之书》(Mrs. Beeton’s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1861)简要论及持家原则,详细阐述烹饪技巧,为的是引导人们打造一个舒适的家。华伦太太(Mrs. Warren)的《低收入的舒适生活》(Comfort for Small Incomes,1866)意在指导人们避免开销浪费、凭微薄收入(年入200英镑)过上舒服的日子。就舒适话题而言,萨拉·艾利斯(Sarah Stickney Ellis,1799—1872)的指南书重新审视何谓真正的幸福,关注舒适生活方式的养成以及物质与精神财富之间的转化,并探讨这种生活方式的重要社会意义,因而兼具宏观与微观的指导意义。艾利斯力图改变的是中产阶层家庭不快乐的状态,因为“‘文雅’长久以来打了许多胜仗,打败了‘实用性’”。
伊莎贝尔·毕顿和《毕顿太太的家庭管理之书》
图片源自Yandex
作为19世纪知名的女性行为指南作者,艾利斯倡导一种以舒适为导向的生活方式,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英国妻子》(The Wives of England,1843)一书中。在艾利斯写作的19世纪30年代末,她发现中产阶层在追求文雅的道路上走偏了方向,过度推崇肤浅的物质文化,任由物质消费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他们仿效贵族奢华的生活方式,看重物质的身份象征意义,互相攀比、争相炫富,举全家之力来展示昂贵的家具、富丽的衣装、精美的食物、隆重的款待所代表的物质文化。对物质文化的迷恋中潜藏着维多利亚人对阶层下滑的深度恐惧。艾利斯指出,维多利亚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焦虑源头是人们渴望拥有比眼前更高的地位,渴望在社会等级上不断进阶,惧怕从现有的位置下滑。这也是该时代思想家约翰·穆勒观察到的现象:“每个人习惯性地不满足于自己身处的阶层。”在艾利斯看来,在这种“习惯”的驱使下,中产阶层若沉溺于追求功名利禄、奢华的生活,忽视了自省静思的精神修行,终将失去阶层特有的道德财富,而这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精神基调。
在一个阶层观念主导的社会里,追求文雅体面无疑是中产阶层显在的一大诉求。但在一个深受清教影响的商业社会里,人生的双重目标既有体面,也有救赎。这决定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层的处境,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多弗所强调的:他们身陷彰显世俗地位与从宗教、道德层面抵制物质世界之间的冲突。艾利斯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明白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从经济学角度鼓励个体消费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她担忧沉迷于物质对个人产生负面影响。她并不反对人们追求体面的身份,但主张中产阶层真正的尊严体面存在于个人的内在品格、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与身份相匹配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她认为中产阶层家庭应立足于本阶层的财富水平与幸福诉求,摒弃奢华,选择一种务实、节制有度的折中生活方式:致力于提升生活的舒适度。艾利斯虽然抵制奢华,却不主张通过禁欲苦行的隐士般生活来进行宗教修行,而是倡导在舒适的日常生活中践行美德、寻求精神的力量。
在艾利斯的观念中,英国的家庭特征是“家的舒适”。这也是维多利亚人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形成的基本共识:家是舒适的载体,舒适是家的核心要素。艾利斯十分强调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对财力有限的中产阶层家庭的重要性,主张优秀的家庭管理必须将节俭与舒适作为互为制衡的两大要素,以防过度节俭而牺牲了舒适与体面,或过分舒适而沦为奢华无度。她认为女性应当清楚舒适体面的家庭生活所需的开支,合理安排支出,做到物尽其用,减少开支浪费,使家庭保有财力,为养成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铺垫牢固的经济根基。她主张营造整洁有序的家庭环境,培养守时高效的家庭习惯,促进宁静和睦、放松安闲等要素的生成,通过舒适的生活展现出家庭的体面。她认为真正的舒适还应兼顾审美上的优雅,但优雅绝非通过展示贵重华丽的物品来体现,而是遵从好的品位的准则,追求简单、合适、和谐之美,不允许奢华来破坏完美的和谐感。这种优雅的美才可给人舒适感,起到抚慰人心的作用。
艾利斯尤其强调整洁的生活环境的打造,这不仅是出于社会地位与幸福的考虑。一方面,这样的家庭环境是身份的象征。在维多利亚时代,物品的批量生产使得原先只有少数人能获得的物品,如今也能走进许多人的生活,社会地位的标识从积聚私人物品这种相对不那么费钱的习惯,转为专注于保持洁净这种更费钱、费时的家庭习惯。另一方面,有如艾利斯指出,家庭生活的目标是“获取最大量的幸福”,家应该成为“最高级别的尘世幸福的现场”。这里所指的幸福部分正源自整洁舒适的居家环境,因为舒适已经被维多利亚人视为幸福的重要标准。艾利斯重视人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思想者的共识:干净清爽的居所不仅使身体舒适、心灵安宁,还将对人的品德产生潜移默化的良好影响。用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话说,“舒适使身体感到满足,而这是培育更好性情的必要条件”。
这种追求舒适的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道德属性,不仅因为它有助于孕育美德,还因为它以美德为根基。它遵循量入制出、勤俭自立的原则,符合新教伦理的基本精神。营造一时一刻的舒适并不难,难处在于使之成为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要求日复一日、恒久如常地践行美德、运用智慧。如艾利斯所言,“实现优秀的家庭管理,要求头脑与心灵兼具如此之多的优点”。它要求女性具有健全的体魄、勤劳节俭的美德、知足常乐的心态、通情达理的性情以及持家有方的才干,又要求夫妻齐心合力,男性坚守勤劳自律的工作伦理,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这种生活方式寻求节制适度的物质享受,但又从物质走向精神,通过物质生活的舒适使人们获得对生活的满足感。维多利亚人心中的家之所以能成为乐园,端赖于此。此外,知足的心灵状态可缓解不停地求取财富地位而引发的无尽焦虑,将人更好的本性激发出来,从而时不时从追名逐利的“低俗的焦虑、粗俗的烦恼”中走出并思索“那些与此生之外的更高存在具有同一性的事物”,促进精神世界的提升。
这种生活方式在作为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人群中盛行,又向阶层的两端延伸开来。与普通大众不同,对于贵族而言,奢华既是特权也是责任,他们肩负着用奢华彰显身份的阶层责任,但在奢华的生活中加入更多舒适要素,这样的生活亦具有无穷的吸引力:既舒适又不失优雅。舒适传递出体面的文化信号,迎合了商业精神引导下的维多利亚人热切追求财富、并将财富转化为身份地位的迫切需要。因此,下层民众也希望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同样能过上舒服的日子,赢得体面。艾利斯虽以中产阶层家庭为劝导的对象,同时却也希望借助中产阶层的社会角色与榜样的影响力将舒适生活的理念与水准扩展到其他阶层。和托马斯·卡莱尔等维多利亚时代思想者一样,艾利斯也认为相较于下层民众,中产阶层拥有更多财富,相应地应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她主张好客应该成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家不应沉浸在自身的舒适感中而产生排他性、变成一个封闭的空间,所以女主人应时常邀请他人来体验家的舒适,共享弥漫于家中的满足感,使他们获得良善的影响。女主人还应顾及社会上的穷人以及同一屋檐下仆人的生活。艾利斯建议女主人每年从家庭开支中预留一笔钱来接济穷人,在关心他们的灵魂之余不忘关心其身体,帮助他们饱食暖衣,不时上门传授勤俭持家的经验,而后再推进对穷人的宗教指引,这样比单纯的精神劝诫更有效。对于住家仆人,应保证他们有足够饭食与睡眠,传授缝补、制衣这样的生活技能,以身作则示范持家之道。这是中产阶层凭其社会责任感、借其社会影响力向各方人士推广舒适观念的重要渠道。舒适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幸福图景,吸引着维多利亚人基于自身的经济能力,营造属于自己的舒适生活。
二、 没有舒适,何以为家?
在《傲慢与偏见》中,夏洛特谈到人生理想时,说“仅仅想要一个舒适的家”,但这却不代表着“舒适的家”是易得之物。夏洛特用了“仅仅”(only)一词,是因为兼有爱情与“舒适”的家无疑是最高级别的幸福,而相较之下,没有爱情却舒适的家算是次一等的选择。夏洛特的渴望侧面揭示出19世纪英国人对舒适的重要性有了愈发深切的认识:舒适是家的核心要素、幸福的重要标准。在这一时期,婚姻家庭中愈发凸显的是建立在两性分工基础上友爱的盟友关系:丈夫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妻子则是家庭财富的共同管理人,负责在守护家庭经济根基的前提下,合理运用家庭财富,营造舒适生活。查尔斯·狄更斯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关注家庭生活议题的男作家,在半自传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49—1850)中对舒适议题与两性角色责任多有探讨,与艾利斯持有基本相同又略有微妙差异的观点。小说中的朵拉尽管赢得了大卫的爱情,却罕见地因无力持家而失去了女主角的位置。
查尔斯·狄更斯和《大卫·科波菲尔》
图片源自Yandex
小说中的大卫有两大显在的人生抱负:出人头地与追求幸福,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层的典型志向。在大卫心中,体面与幸福的诉求具化为对舒适的家的渴望。第一步便是为自己的小家庭租下一栋带有小花园的村舍,因为“到18世纪末,村舍成了英国舒适房子的典型”。他的舒适体验部分来自姑母给予的整洁有序的体面生活。十岁的大卫来到姑母家,对姑母的独栋村舍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整洁”。对姑母客厅的第一印象是“像珍妮特或姑母一样整洁”,家具虽古旧却洗擦得锃亮,客厅里还有“结实的椅子、桌子、粗毛地毯、一只猫咪、茶壶架、两只金丝雀、年代久远的瓷器、盛着玫瑰干花的大碗、各式各样的瓶罐”。这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客厅,桌椅、地毯、沙发、瓷器等物件显出了中产阶层文雅的物质文化,但大卫看到的体面还来自整洁有序的客厅环境。大卫眼里的姑母是“不一般地爱整洁和灵巧”。当时的姑母正处在破产的边缘,连多佛的房产也被迫卖掉,却把他在伦敦租住的房间小范围内重新布置了一下,还添置了些物件,让他的日子过得更舒服了。大卫心存感激,由衷地说姑母时时刻刻惦记着他,而“我可怜的母亲本人也不可能更好地爱我,或更用心研究怎样使我快乐”。大卫从姑母在他日常居家生活细节上的用心,感受到了深沉的爱。传记作者弗雷德·卡普兰认为,贝西·特伍德姑母代表的是大卫向往的社会阶层,也代表着中产阶层的安全感,这在大卫经历了贫困之后显得尤为值得向往。然而,这种安全感并不理所当然产生于一定量的财富中,它来自姑母将自己的财富与对大卫的爱转化为一心一意为他提供的一种舒适生活。
舒适生活的根基是开源节流、守护家庭财富。狄更斯从原生家庭的生活中尤为深切地体会到了理性节制的家庭消费习惯的重要性。父亲约翰·狄更斯只是一个小职员,年收入两百多镑,属于中产阶层的下层。但约翰·狄更斯与妻子伊丽莎白·狄更斯既无力开源,也没能养成节流的习惯。夫妻俩无视家庭财力现状,一心要仿效绅士家庭的生活方式,为求享乐提前消费,入不敷出便东凑西借,曾一度因无法及时偿还四十镑而负债入狱三个月,出狱后继续举债度日。家庭不时陷入财务危机,年少的狄更斯深受其害,过着不体面的生活不说,还曾在十二岁时被迫进入鞋油厂做苦工,一度学业中断,险些失去了接受教育、成为绅士的机会。约翰·狄更斯夫妇未能从习惯性欠债的混乱人生中吸取教训,却是查尔斯·狄更斯从中深刻认识到了节支开流、量入制出的必要性。因此,他也让少年大卫在当童工挣钱养活自己、每日安排三餐支出的过程中学会了重要的一课:财务上须自律节制,否则就得挨饿。
以浪漫爱情为基础又门第相当的婚姻注定承载着大卫人生的双重诉求。大卫以为朵拉是可以与他共创人生幸福的理想妻子。甜美娇嫩、天真烂漫的朵拉不仅赢得了大卫的爱情,还得到了创作者狄更斯的偏爱。但是,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创作备忘录里写过一条笔记:“引入真正的女主角”,这意味着会有一个虚幻的女主角,她很可能就是朵拉。在1850年5月7日的一封信中,狄更斯写出了对她何去何从的犹豫:“关于朵拉,还没想好,但今天必须做出决定了。”小说后来这样安排:朵拉身体羸弱,最终离开人世。朵拉注定无法成为真正的女主角,因为不符合大卫对她的角色期待。
事实上,大卫婚前送朵拉记账本和烹饪书,其实是在邀请她成为自己的人生友伴、一同创建舒适的家。狄更斯认同大卫对妻子的角色期待,也深知女主人对守卫家庭财富至关重要。但朵拉不懂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的道理,无视当时大卫的年收入估计仅有数百镑的现实。仅是两口之家,她却花了1.6英镑买了一条三文鱼,还准备一顿吃完。仆人也在利用女主人的无知,“蚕食”主人钱财,或偷窃或假借主人名义向商贩购物、借钱。正如毕顿所言,节俭是家庭美德,没有节俭,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兴旺发达。长此以往,摧毁的是大卫家庭的经济根基。不但如此,仆人干活也不得力。用餐时间无法保证,上了餐桌的食物没煮熟,大卫常常要饿着肚子出门上班。还有一个问题是无序。“秩序……是每一样物品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且又都在其位。”结果,在大卫家里,“每一样物件都没有自己的位置”,总有东西丢失不见,人又被困在狭小空间里。这一切问题出在朵拉对烹饪之类的家事一无所知。大卫曾问,他若想吃爱尔兰土豆洋葱炖肉,怎么办?朵拉说她会吩咐仆人去做。但女主人的工作显然不仅仅是张嘴吩咐仆人做事。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指南书给中产阶层女主人的一条基本建议是:在家庭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女主人不一定亲力亲为,但务必要熟悉家务、学会记账,从家务技能、劳作习惯、道德习性等方面指导、训练、监督仆人。原因是,训练有素的仆人基本上都涌向了贵族家庭,中产家庭在人力市场上能找到的大部分仆人都有待调教。朵拉的问题还在于她不肯付出努力。她没有学习持家之道的恒心,烹饪书令她头疼,记账本让她哭泣。华伦太太这样描述“朵拉·科波菲尔这一类人”:年轻太太“一想到自己的职责就颤抖”,希望能够找到可靠的中年女性来帮忙理家,“从自己手中接下家务管理的一切烦恼”。在维多利亚人眼里,朵拉是无心也无力担负家庭责任的女性典型。
但是,不懂持家理事的朵拉必须消失吗?有学者设想,不让朵拉死,艾格尼丝照样“可以当‘真正的女主角’,培养朵拉,管理家庭,照顾孩子,就像乔治娜·霍加斯……在狄更斯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学者继续指出,狄更斯不这么写,或许正因为在自传体小说中这样的安排会显得“太贴近生活,令人尴尬”。这样的猜测不无道理。乔治娜是凯瑟琳·狄更斯(即狄更斯妻子)的妹妹,从15岁起(1842年)进入狄更斯家,意在协助姐姐打理家庭。凯瑟琳长期处于怀孕生育状态,乔治娜实际上担当了管家的角色,甚至担负起照顾狄更斯家孩子的重任,也深得外甥、外甥女的爱戴。放弃了管家角色的凯瑟琳在家中的存在感变弱。1858年,狄更斯与凯瑟琳分居。这让我们有了后见之明:即便朵拉不死,她的管家角色由艾格尼丝分担,她与大卫的婚姻也未必能圆满长久。
婚姻的基础是日常家庭生活。恋爱可以是纯粹的心灵与精神的交流沟通,可以脱离日常例行轨道,婚姻却必须扎根于庸常的现实生活。用艾利斯的话说:“爱情也许会自发产生,但没有爱护和培育,便不会持久”,人们需要“情感的证据”。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在失去了新鲜感和诗意后,需要落实到琐碎的家庭日常中,才能累积深度与厚度,而它能否顺利转化为夫妻恩爱,所赖的绝不是单纯的言语示爱,而是夫妻共命运之下积极主动的责任分担。恋爱中的大卫可以生活在缥缈的云端,纯靠一片相思度日,如他所言:“我的主要食物是朵拉和咖啡。我害了相思病,食欲不振;我还挺开心的,我觉着有胃口正常吃饭都是对朵拉的不忠。”彼时身陷爱河的大卫表示自己并不明白结了婚的人怎么可能不幸福。婚姻中的大卫努力挣钱养家,却连三餐都没法得到保证,不禁发起牢骚来,抱怨道“这让人很不舒服”,“这种家务管理让人很不舒服”,还说“我们失掉了钱财与舒适,有时甚至是脾气”。这与大卫的恋爱语录形成了强烈反差,揭示的是恋爱与婚姻根基的不同。婚后的大卫不再能“把爱情当饭吃”,清醒地意识到舒适对于幸福家庭的重要性。
婚姻形态,不论是无爱却舒适,还是有爱却不舒适,凸显的是19世纪英国人的切身认知:没有舒适,何以为家?而舒适与否的关键在于持家的女性,因为维多利亚人认为“女性是舒适的家的守护者”。大卫说自己的婚姻里也有幸福,但不是他渴望的幸福,“总是缺了什么”。大卫所缺的,正是由女性营造的家庭生活的舒适感。朵拉不缺才艺,能歌善舞,娶到这样的妻子令大卫备感自豪。但用华伦太太接地气的话说,女人的“歌声、音乐、绘画、舞蹈喂不饱也照料不到她的丈夫和孩子,不过,饱食了一顿健康、可口的饭菜之后,这些无疑能使他们更快乐,常常还能让他们更幸福”。在务实的维多利亚人看来,才艺起到的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不是家庭生活必备,持家能力才是刚需。无力持家的朵拉要求大卫把她当作“孩童般的妻子”(child-wife),在某种意义上,她更像是18世纪的文学人物,因为到18世纪末,小说、铜版画、歌曲、诗歌中的理想妻子都是“年轻、依赖人、几乎像个孩子似的”,展现了一种“脆弱、无助”的形象。在狄更斯的笔下,朵拉的孩童般气质与娇小体形表现出了复杂又自洽的两面性,在讨人喜之外露出了潜藏着的另一面:朵拉无心也无力承担妻子的重负,沦为没有分量的轻飘的存在。女性的管家角色确实赋予了19世纪英国女性存在的分量。狄更斯或许从自己的婚姻生活中逐渐体会到了,所以才借朵拉之口说出她“会越来越当不了他的伴侣”。在女性个体发展十分受限的时代,担当管家角色是中产阶层女性鲜有的、成为与丈夫共命运的人生友伴的机会。
大卫与朵拉的故事不止于两人迈向婚姻殿堂的时刻,而延伸进了婚姻生活,这从侧面体现了维多利亚人对婚姻生活质量的关注与探索。大卫面对婚姻难题束手无策,曾向姑母求救,但即便为大卫感到焦虑,姑母也不肯出手相助,这似乎与她素日以大卫的幸福为念的作为相悖。姑母是怕自己的介入会伤害到朵拉,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藏在姑母的话里,大意是,这是大卫“自己选择”的,且“未来在你二人手中。没有人可以帮你;你必须自己解决问题。这就是婚姻……”。在情节安排上,狄更斯让大卫自由选择结婚对象,让反对女儿嫁给大卫的斯宾洛先生意外过世,让大卫在婚事上享受了充分的自主。伴随着个体自主的势必是自我负责。这也是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看到的一种趋势:在16至18世纪的英国,在个人主义兴起等因素影响下,原有加固核心家庭纽带的强有力的外援力量渐渐被排除在外,核心家庭“被迫依靠自己,除了自身内在的凝聚力,少有什么能将它凝聚起来”。大卫与朵拉的小家庭所能依赖的,就是“自身内在的凝聚力”,就是夫妻双方承担各自的角色责任。大卫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揭示了人类的普遍困境:浪漫爱情未必能带来幸福的婚姻,而弥合浪漫爱情与幸福婚姻之间裂缝的关键在于夫妻双方各尽其职,共同营造舒适的生活状态。
《曼斯菲尔德庄园》,图片源自Yandex
与大卫和朵拉的一见钟情不同,他与艾格尼丝的爱情属于日久生情,这是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累积下来的深厚情感,由此具备了坚实的根基。狄更斯采用的不是《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经历戏剧性冲突之后两相了解、进而相爱的形式,而是《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中爱德华与范妮的恋爱模式。它是从近似兄妹关系发展而成的互相吸引(生理与精神)、志同道合的亲密关系。大卫常称艾格尼丝为“我的向导与朋友”、“我最好的朋友”、“我少年时代的姐妹”,两人的爱情确是从友爱的朋友关系发展而来。大卫对艾格尼丝的第一印象是她的管家形象。十岁的大卫异地求学,寄居在艾格尼丝的家中。他初见艾格尼丝,地点便是在维克菲尔德先生的老房子里。大卫看到小小年纪的她身上挂着一小筐钥匙,“看起来像老房子里的管家那么沉稳谨慎”。维克菲尔德先生介绍女儿时的用词正是“我的小管家”。在艾格尼丝打理的这栋房子里,大卫感受到“每一样东西都散发着清幽和洁净的气息,和房子的外表一样显眼”。而老房子外观给大卫的印象是“一尘不染”,房前台阶“白得像铺上了纯净的亚麻布”,房子的角落、转角、雕刻、窗玻璃和小窗户“虽然像山丘一样古老,却又像落在山上的雪一样纯净”。这栋位于坎特伯雷市的老房子虽然年代久远,却保持着洁净的气息,与当时人们常见的肮脏的城市公共空间天壤有别。艾格尼丝年纪虽小,却已深谙当时中产阶层的一个持家习惯:使房前台阶每天保持洁白,屋内洁净有序。据朱蒂斯·弗兰德斯所言,房前台阶大概要经历如下清洗步骤:清扫、用水擦洗、漂白、覆盖上一层白黏土,待风干后还要用法兰绒布块擦拭,但台阶并不耐脏,一被踩踏就有印记,每天必须重复同样的步骤,因此,洁白的台阶足以表明“居住者的承诺是郑重的”,他们承诺自己不仅有责任而且有“道德责任”来打扫房子。艾格尼丝的家整洁、舒适,映现的是她的美德与才干。在日后长久的相处中,大卫看到的是,艾格尼丝与自己拥有同质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人生理想,体现于他们对体面、幸福、美德的追求中。
对大卫而言,艾格尼丝代表着放松、自在、安宁等舒适要素。大卫感觉到“艾格尼丝是他天然的家的一个要素”,遇上烦恼时,“来到艾格尼丝的身边”就是“找到了宁静和幸福”,像是“回到了家,像个疲惫的旅人,找到了一种幸福的安宁感”。这不是华丽的修辞、空洞的赞誉。大卫时常会想起“与艾格尼丝度过的那些心满意足的日子”,“在那栋亲切的老房子里”。艾格尼丝给了大卫一种家的感觉,正是基于她营造舒适家庭生活的能力。而且,大卫感受到了一种满足的心态,体验到了舒适有爱的生活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产生的良好影响。入住后不久,大卫便说老房子有一种“影响力”,带走了他在学校里的不安感(担心自己当童工的经历被同学发现),一敲响大门,便“感觉不安在慢慢消失”。大卫又说,艾格尼丝形同一股“宁静的影响力”,遍布她所居住的城市,在每一个角落里,他都能感受到同一种“更宁静的气氛”、同一种“平静、沉思、柔和的精神”,体会到一种“庄重的快乐”,使得他“精神冷静,心灵放松”。这种冷静、放松便是大卫用来对抗阶层下滑焦虑的力量。在大卫心中,艾格尼丝便是人格化了的家,在对艾格尼丝的这一形象的反复确认中,大卫确认了对艾格尼丝的爱情。而婚后,艾格尼丝的爱还将体现于尽心营造一个舒适的家。
大卫与艾格尼丝的故事揭示的是,维多利亚人享受的舒适生活状态是夫妻合力而生的产物,有赖于夫妻二人分别履行他们内化于心的家庭责任。狄更斯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显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男性的典型视角与期待。有别于狄更斯的是,艾利斯还力图在责任话语之内替女性谋求一种补偿机制,即女性在营造一个舒适的家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创造人生幸福。培养女性具备这种创造幸福的能力,正是指南书的主要目标之一。夏洛特、朵拉、艾格尼丝这样的女性正是艾利斯指南书的目标受众(尽管夏洛特的时代早于艾利斯指南书问世的时间)。夏洛特曾说过“不论多么不确定能否带来幸福”,婚姻都是使她们这种受过教育但财产不多的年轻女子免于贫困的“保护剂”。在艾利斯看来,婚姻确实是女性人生的关键转折点。夏洛特的选择,有降低对理想婚姻的期待而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更有接受现实、务实求取、追求次一等幸福的勇敢。夏洛特的选择揭示了财务不独立的女性的不自由,但从她对婚姻生活的积极建设中又可瞥见艾利斯极力培养的女性掌控生活自主权的能力。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层女性深受固化的两性观念的束缚,基本上不具备独立经济能力。没有经济能力又没有富足家底的女性在生活中是被动的,而唯一能化被动为主动的途径便是具备和发挥营造舒适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一定能带来理想状态下的夫妻恩爱,但至少有望创造一种中间态的幸福。在婚姻不一定能带来幸福的时候,女性的这种能力更是一种“保护剂”。当然,这种能力无法与现代女性对生活的把控能力相提并论,但依然值得称道。这种务实却非浪漫主义的生活态度是支撑19世纪英国女性为受缚的人生寻求意义的力量。
结 语
当维多利亚人在探讨、追求舒适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或许未曾料到,一二百年以后,这依然是现代人拥抱的理想生活方式。伴随着现代女性开始拥有独立经济能力,以及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体的出现,现代人的舒适生活未必都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以两性分工合作的家庭为主要载体,现代人也未必一定在这种生活中寄托培育美德、来世救赎的期待。但即便如此,舒适的价值观念能被现代社会广为接受,根本原因仍在于舒适本身具有的实用性:舒适的生活催生愉悦安宁的心灵状态,缓解现代人无处不在的焦虑,使人获得体面并收获温和中庸的幸福,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的基本需要。不过,这些实用性产生的必要条件却不可忽视。当维多利亚人在追求舒适的时候,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必须建立在量入为出、节制自律的基础上。在这种新教伦理基本精神的指引下,人们才有望在享受丰富物质带来的舒适幸福的同时却又避开伴随着消费社会兴起而日渐膨胀的物欲对人心产生的不良影响。因此,在物质极度丰富、人们普遍富裕、消费者信贷盛行的现代社会中,若一味追求享乐却不以节制有度的美德为根基,无法理性消费,恐怕更容易陷入因贷致贫的境地。对舒适的追求虽是维多利亚人在调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矛盾的过程中寻得的折中出路,却仍旧能满足现代人的多样人生诉求,并提醒现代人避开贫困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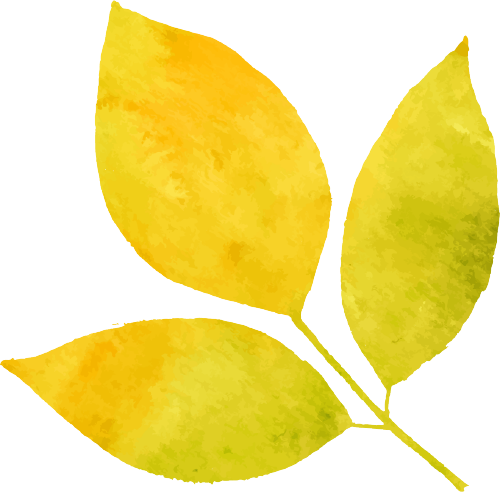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5期“文化研究”专栏,责任编辑龚璇,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艾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雨璇 终审:文安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