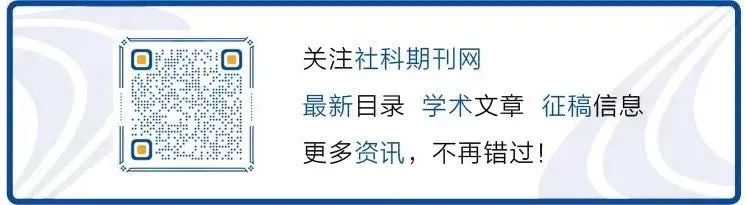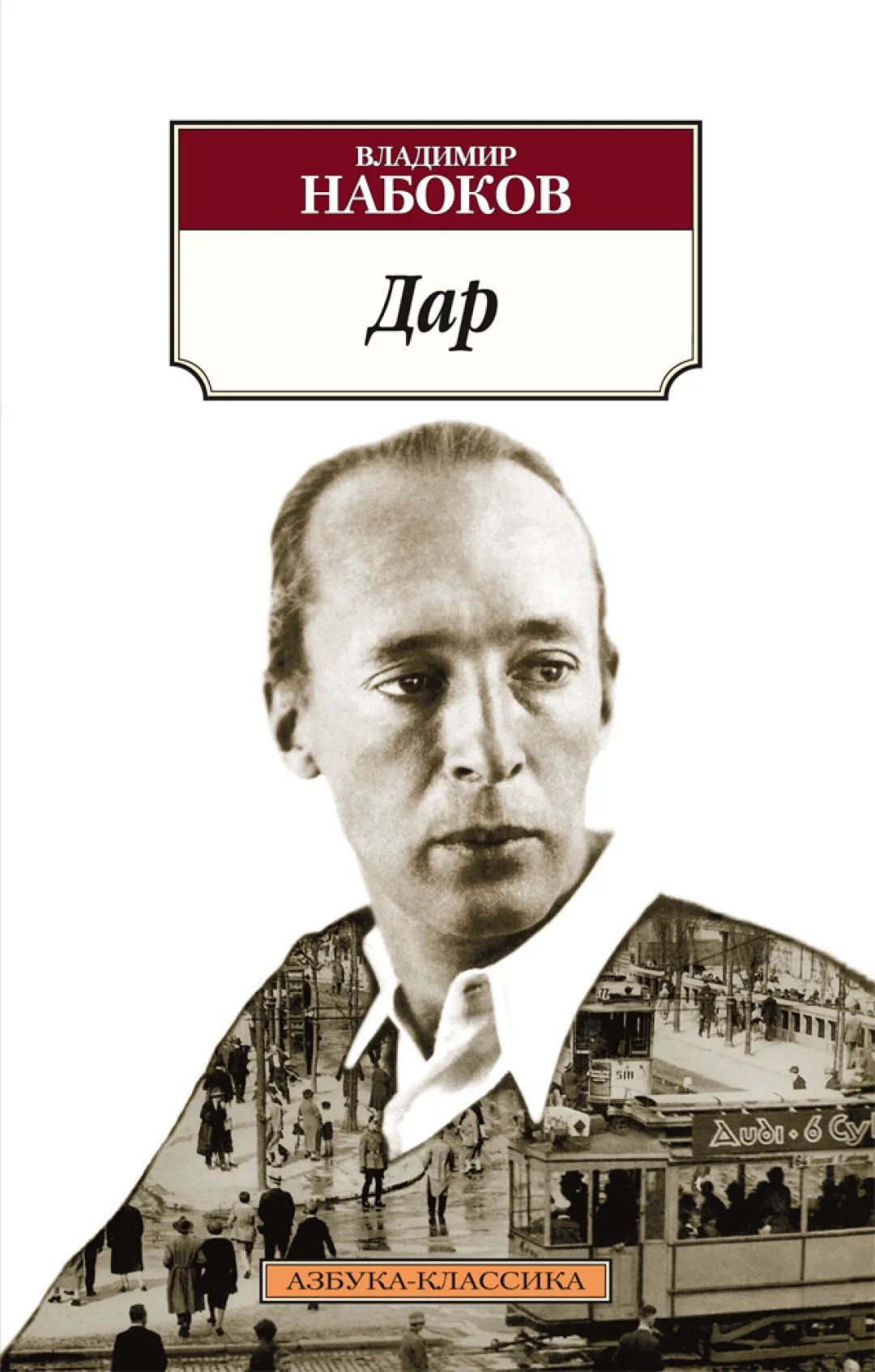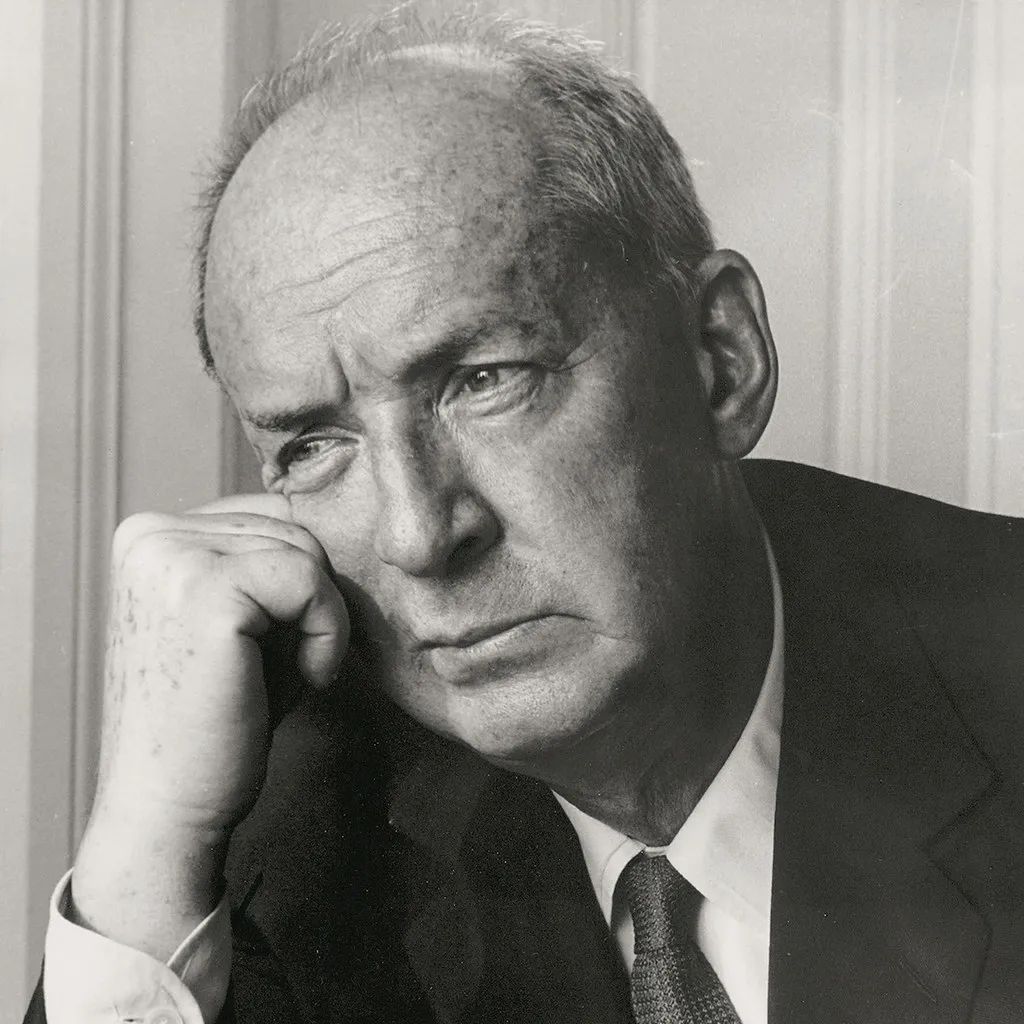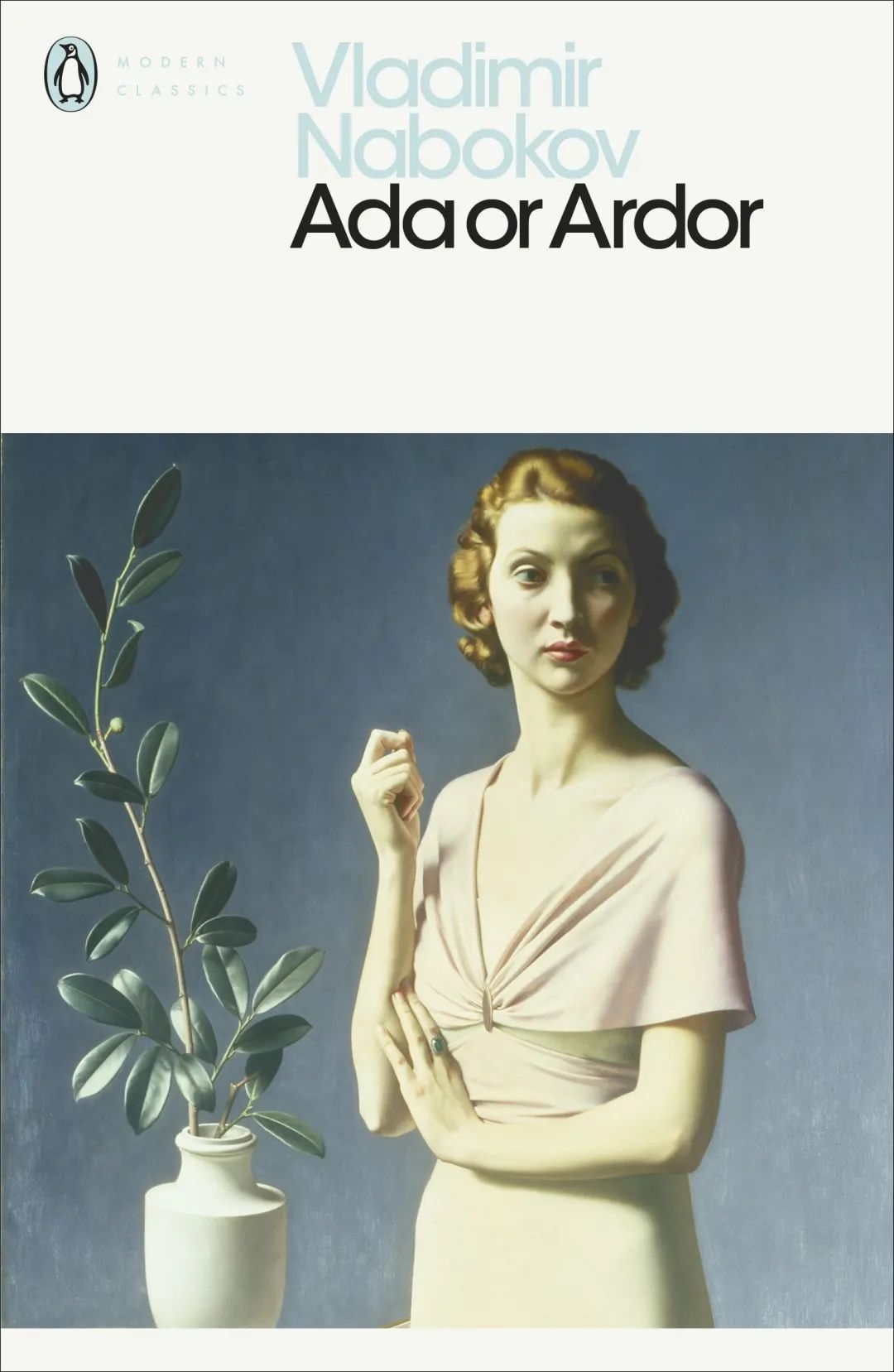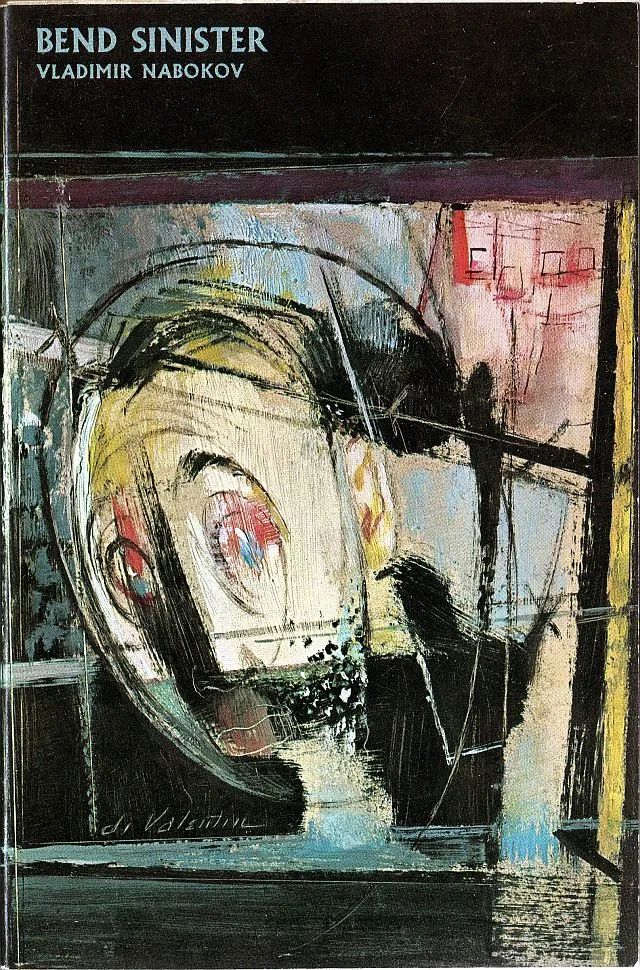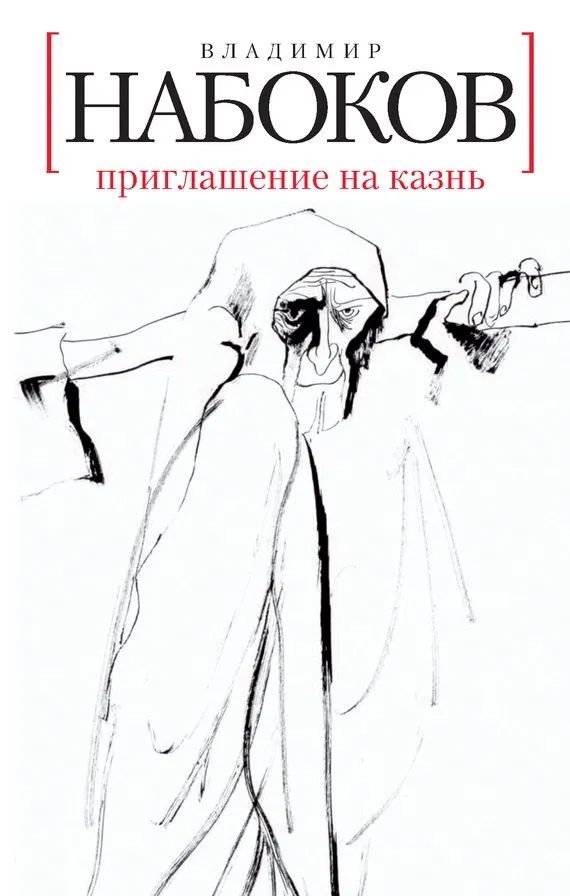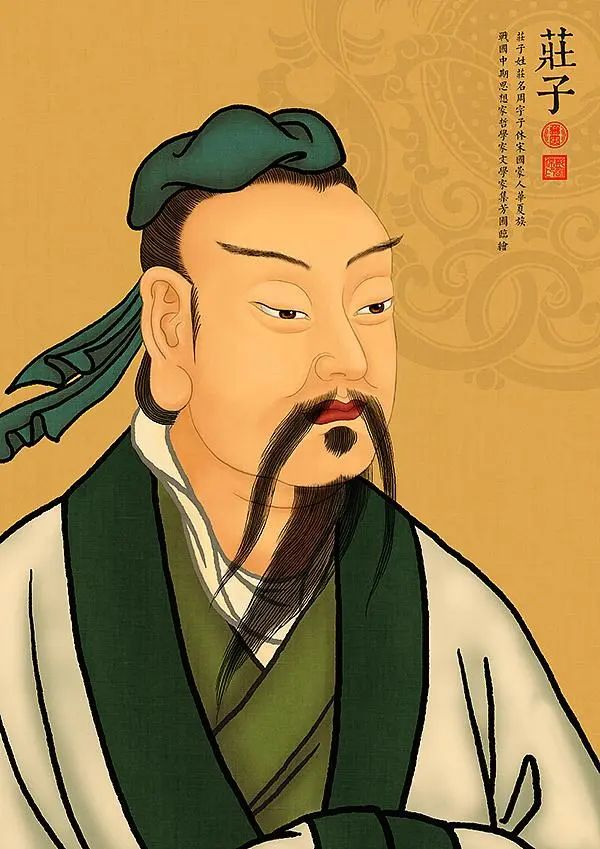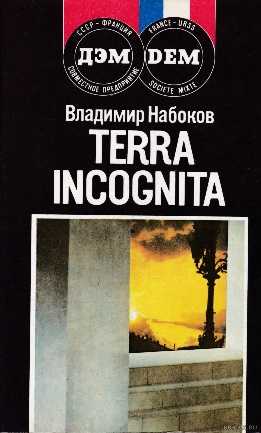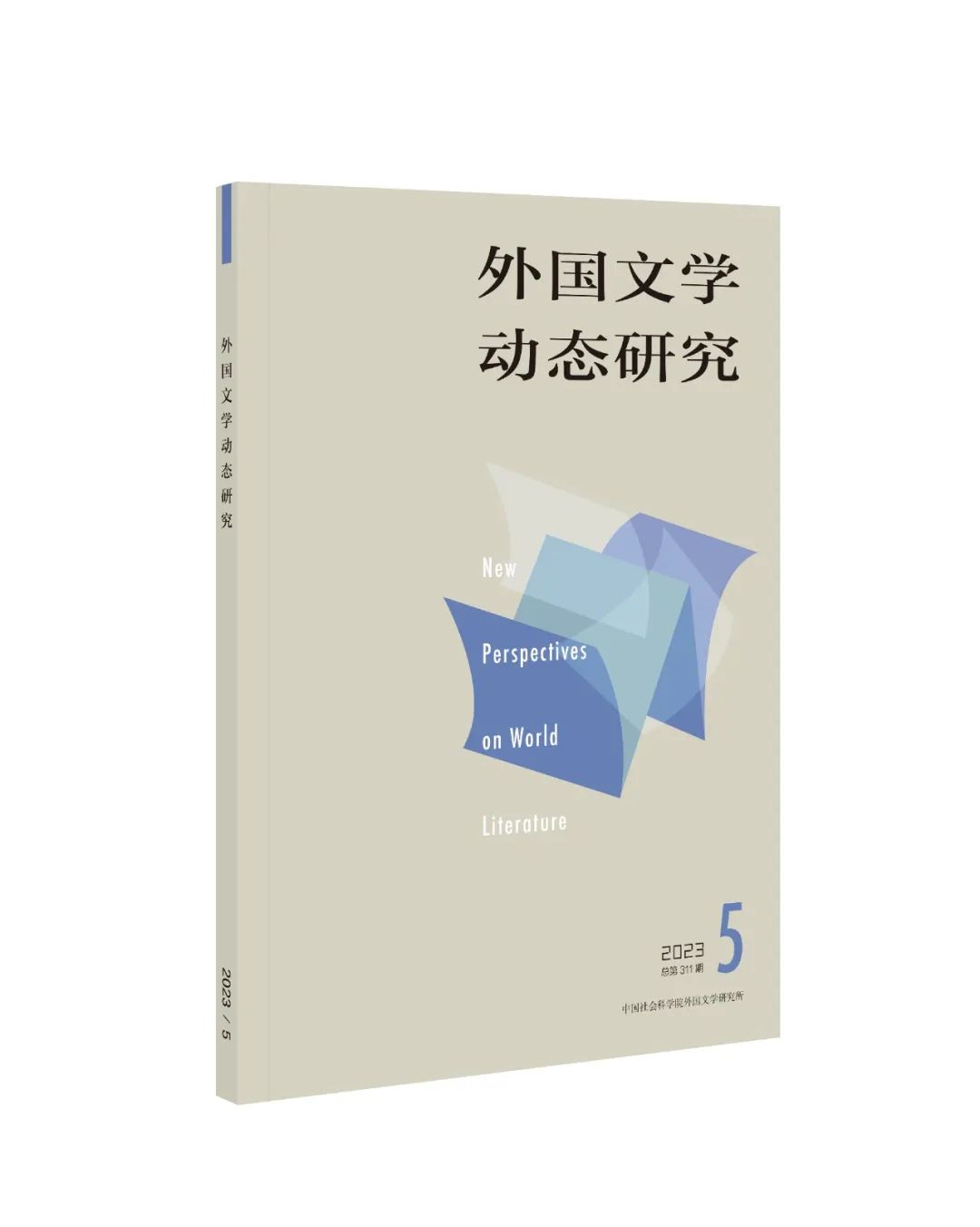文化研究丨纳博科夫与他笔下的中国

文导微,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侨民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走近俄语作家纳博科夫-西林——〈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长篇小说《天赋》注解〉评介》(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
内容提要 纳博科夫对“自然”的中国和“人”的中国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对前者心驰神往,对后者却少有褒扬。面对中国的物时,他对热门特产不屑一顾,却对非流行的跳棋加以青眼;他不仅引用过“庄周梦蝶”的故事,也在创作中提出过类似的疑问。本文从纳博科夫笔下的中国反观他对中国的态度,同时从他对中国的想象中探察他的个性与喜恶——对鳞翅目昆虫与棋类的兴趣、对残酷和死刑的憎恶、对流行的警惕、对梦觉主题和生死主题的关注等。
关键词 纳博科夫 中国 作家个性
引 言
纳博科夫(В. Набоков,1899—1977)从未到过中国。除了写到中国西部行的小说《天赋》(Дар,1937—1938;1952),他作品里的中国元素并不那么突出。他的传记作者博伊德也结合《天赋》言及此,认为他对中国“考虑不多”。
《天赋》和纳博科夫,图片源自Yandex
博伊德所言固然不错,但纳博科夫对中国虽然不多却持续不断的关注和他的某种中国情结也引人瞩目:圣彼得堡十卷本纳博科夫文集里,没有一卷不提中国;他与人合写过一个名为《中国屏风》(Китайские Ширмы,1924)的小品;他不止一次表达想来中国的愿望,也确曾打算“组织一场去中国西部山区的昆虫学考察”;他“梦见自己在中国奔跑”,还在手术台上的幻梦中看见母亲是位中国太太……
关于纳博科夫与中国的讨论,一方面能填补我国学界论及“俄罗斯文学里的中国”一类话题时对纳博科夫的文本观照的缺失,另一方面,对该话题的讨论也能丰富纳博科夫研究。国内有文章系统梳理了从古至今俄罗斯文学与历史文献中的东方观,可纳博科夫的文本却在这样相对全面的考察中被遗漏了。国内学者专论过普希金、托尔斯泰、佩列文等多位俄罗斯文人笔下的中国,但也不曾以纳博科夫笔下的中国作为专题。现有相关成果仅有两篇文章:一篇结合俄国、欧洲和中国的文化语境,考察纳博科夫柏林时期作品里与中国有关的细节、情节、意象等;另一篇结合俄罗斯文学的东方书写传统,考察纳博科夫的几首俄语诗作与《天赋》里的东方主题。本文别于二者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本文的研究对象相对全面,包括作家不同时期的俄语创作及其英译本和英语创作,以及评论作品和书信等。二、角度不同,前述两篇文章均视纳博科夫的相关文字为俄罗斯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本文则主要视其为纳博科夫个人观念世界的一部分,在展示纳博科夫笔下中国的同时,反观纳博科夫的个性与喜恶。
纳博科夫虽未到过中国,但他生长的环境里却不缺少中国的气息。1899年,纳博科夫生于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及其近郊,有不少来自18世纪欧洲热衷模仿中国艺术的“中国风”的产物,如中国宫、中国剧院和中式凉亭等。纳博科夫在俄国生长的十几年,正逢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当时的一些诗人如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古米廖夫等的诗歌里都有中国主题。20世纪初的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中国的军阀混战、科兹洛夫发掘西夏遗址等,也是离纳博科夫较近的有关中国的重大事件。相对较远的历史经纬至少也有:19世纪出现的几部描写俄罗斯人去中国和在中国旅行的著作、鸦片战争、更早时候开始的中俄商贸与文化往来、欧洲对中国的一度狂热、马可·波罗的游记等等。这些地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方面的远近事实,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和影响了纳博科夫对中国的书写。
从时间和空间来看,离纳博科夫较近的一件事情,是科兹洛夫考察队挖掘的西夏文物在圣彼得堡的展出。1908至1909年,科兹洛夫考察队在内蒙古西部发掘出西夏黑水城遗址,发现并掠走大量珍贵的文物,运往圣彼得堡,这让“全俄罗斯沉浸在探险的狂热当中”,很可能也影响到了少年纳博科夫。后来,青年纳博科夫有意资助由博物学家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率领的昆虫学考察队赴中国西部考察,这里面或许多少也带有科兹洛夫引发的探险狂热的余温,尽管纳博科夫的兴趣不在宝藏而在昆虫。资助愿望因俄国革命爆发而落空,但中国却让他念念不忘,而科兹洛夫和格鲁姆及其在中国的见闻,后来也进入了他的小说。
一、“遥远的国度”与纳博科夫
对鳞翅目昆虫的兴趣
纳博科夫在给爱人的信里说“我很想去非洲,还有亚洲”。这份念想同样体现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德莱尔在情感失落时觉得“要能去趟中国就好了”——就像普希金在求婚受挫后想过“去遥远的中国的长城脚下”,他还经常“描画满是冒险和旅行的生活……中国,埃及……”;皮里格拉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蝶蛾,其中一只就来自中国的打箭炉(即康定),他渴望亲自到那些遥远的国度(далеких стран)去捕捉最稀罕的蝴蝶;雪后,一只松鸡“就在我的屋后找到你的中国”;“没听过蓝喜鹊在中国的柳树上喳喳鸣叫”会是临终之人的遗憾之一。
在《天赋》里,念想转化为一次虚构的旅行。小说第二章有近十页集中讲述主人公的父亲在中国西部的科考探险。望着父亲书房里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的画,主人公在想象中与父亲的驮运队一起上路,走过天山、南山、黄河、西藏高原、罗布泊等地,看过峡谷流水、大漠落日、雪山杜鹃等景象,见过角百灵、柳树、蓝喜鹊、银莲花等各种动植物……一路上,追寻或发现知名或不知名的蝶蛾或其幼虫,连根部形似蝶蛾幼虫的虫草也得到了关注。据统计,在这不到十页的篇幅里,提到的蝶蛾就有十余种,动植物共有约五十种。——中国的动植物在纳博科夫后期的英语小说如《微暗的火:一部小说》(1962)和《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1969)(下简称《爱达》)里仍被提及,有时还进入了诗行或者文字游戏。纳博科夫没有到过中国,但不能因此臆测,《天赋》里一些细节描写如“丝绒般的空气中只听见骆驼沉重、加快的呼吸声和它们宽阔脚掌的沙沙响声”或看似奇异的事物如“挂满灰白果子的白色花楸或披着红皮的白桦”只是想象。恰好相反,纳博科夫对中国西部的描述有较高的写实性,因为他参考了亲自到过中国的人们的作品:多利宁发现,纳博科夫大量借用了他人的文本——《天赋》第二章的一半“就像由对大量文献资料的引用与换说构成的精巧的拼贴画”,而格鲁姆和科兹洛夫的作品则分别是其“主要来源”和“重要来源”。
《微暗的火》和《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
图片源自Yandex
这些描写展现出来的中国,主要是中国的大自然,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那是也曾让普希金向往的异域远方。这种向往,在纳博科夫这里,有时以直抒胸臆的形式表达出来;有时,则具体地表现为对中国的地理地貌和动植物群如临其境、津津有味的细致描绘,展露出纳博科夫在博物学方面尤其是对鳞翅目昆虫的兴趣。被问到“除了写小说之外您最喜欢或者最想做什么”时,纳博科夫回答“当然是捕蝴蝶啦,还有研究蝴蝶”,甚至说文学灵感给他的愉悦和回报不及在显微镜下发现一个新器官或在山里发现一个新品种给他带来的狂喜,如果俄国没有发生革命,他很有可能完全投身于鳞翅目昆虫学,根本不写小说。
二、“沉闷乏味、原始落后的地方”
与纳博科夫对残酷和死刑的憎恶
尽管纳博科夫对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表现出向往,但一言以蔽之地说“纳博科夫作品里流淌出的东方情调富有诗情画意”、他的东方是“浪漫神秘的想象之境”却是片面的,因为在他的笔下,中国是个“沉闷乏味、原始落后的地方(dreary,primitive spots)”,很多时候并无诗意、浪漫可言,那里的现代人似乎不讲卫生、不讲公德、缺少生气,古代统治者的专制更是远离文明。
《天赋》虽赞叹“只有在中国,晨雾才那样迷人”,但也写到中国的公共场所既脏乱又嘈杂,旅店里“只有吆唤声”、“这些旅舍的气味、中国人居住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特殊的气味:厨房的油烟、厩肥燃烧的烟、鸦片和马厩的腐臭相互混杂”。这虽是对格鲁姆游记的转述,但从纳博科夫对素材的取舍中也能看出他的态度,这其中有他个人喜好的影子,如对旅馆“绝对安静”的需求。另一方面,纳博科夫笔下又有一些“安静”的中国人:他们不笑;他们是一个徒劳泼水的老人、是河上干活的一个苦力、是一些洗衣工人、是一张低垂着的脸;他们没有言语,似乎也缺少生气。
对一些中国人,纳博科夫还用“狡猾的”、“自私的”、“傻瓜”、“邪恶的”等词语来描述,也偶尔用西方常见的个别有轻蔑意味的形容。偶尔他也称赞中国人的手艺,例如“它们瓷一般的鳞片仿佛是由一个细致的中国人涂的色”,也以中性笔调写过中国人,例如“便便大腹乐得直抖,中国的业余鸟类爱好者笑呵呵地说……”。但无论褒贬或是不置可否,大多都只一笔带过。
可有一类话题,纳博科夫却一再提起,有时还给了相对较多的笔墨。在小说、评论、传记、书信里,纳博科夫多次写到残酷与死刑:“中国的酷刑”、“中国风格的残酷行为”、中国的刽子手、用孩子进行残忍试验的研究所里的一个中国人、一组展示中国一次常规死刑行刑过程的连拍照片……《天赋》的主人公还因冻结在冰河上的野牦牛想到商纣王:
不知为何我想到那个出于好奇剖开孕妇肚子的暴君受辛,有一天,他看见挑夫在寒冷的早晨淌水走过小河,便命人切下他们的小腿,为了看一眼,骨髓是什么状态。
纳博科夫还把破坏性极大的翻译比作“中国的酷刑”:
但加尼特译成了“两人很胖”,从而损害了果戈理。我有时想,这些旧的英文“译文”很像中国一度流行的千刀万剐。那种凌迟的做法是,差不多每五分钟就从受刑者的身体上剜去止咳片大小的一块,直到一点一点地(一切都经过刻意挑选,以便让受刑者活到第九百九十九块)将他的整个身体仔细地剐掉。
他再三提到中国人的残酷和死刑,并不惜笔墨对古代东方暴君的专制与残酷做了较细的转述。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和许多欧洲人一样,认为中国的文化“原始、残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个人对残酷和死刑的憎恶和反对。
纳博科夫曾在访谈中多次表示自己憎恶残酷。在创作和批评里,他不仅写到加诸肉体的残酷(如上文提到的例子),也写到加诸精神的残酷(如《爱达》里凡与爱达对卢塞特内心世界的漠视),还指出旁观者面对残酷行为时的冷漠甚至兴奋也是一种残酷,比如《斩首之邀》(Приглашение на казнь,1935—1936;1938)、《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1947)等作品里写到看客对受压迫的个体的无动于衷与幸灾乐祸,以及他讲《堂吉诃德》时对该小说的谴责。有学者甚至认为,“纳博科夫的艺术其实就是关于‘残酷’的艺术”;而死刑也是纳博科夫和他那位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父亲符·德·纳博科夫以各自的方式反对的酷刑,在《斩首之邀》和《天赋》里,死刑主题都有集中表现。
《庶出的标志》和《斩首之邀》
图片源自Yandex
三、“无用之物”与纳博科夫
对流行的警惕和对棋类的兴趣
就“人”的中国而言,纳博科夫还写到中国人制造的物,大的有中式建筑如中式大门,小的有中国制造的掌中之物如纨扇。
其中,丝绸、瓷器、玉器等至今驰名世界的中国特产,是较显眼的一类。瓷器、丝绸、扇子等在俄国一度被认为“是品位高雅的代表,一些贵族收集了大量中国物品”。虽然纳博科夫圣彼得堡的家里也摆过一小尊中国的神像,但他的态度还是与大众不同,他在小说里否定了它们的意义:“……卖的净是中国产品,丝绸、花瓶、杯碗——在海边谁需要这一切呢”;“……一小尊袒腹的寿山石神像,……一只于田玉做的小杯子,……还有许多类似的无用之物(хлам)”。
在他笔下,中国物品的跟风者或使用者未必“品位高雅”:用一个中国花瓶装饰门厅、热爱收集“高雅”物品的霍尔太太“凸出的门牙上沾着口红”,会着迷地听人为纳粹辩解;因扇子“重新流行”卖起扇子(有的扇面上绘有中国蝴蝶)的弗洛拉是个风流成性的女人;身着中式家居服的波塔波夫“看起来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其外孙女“喜欢有关暴力和东方智慧的书”;熊猫皮床罩的使用者是个做作的姑娘……其实,不仅是中国物品,人造的“东方情调”同样也不被纳博科夫认可:喜欢东方物什、有间东方风格的地下室的加斯通是个头脑无趣的人,对小男孩格外关注,有类似癖好的奎尔蒂也有东方风格的起居室。
纳博科夫的态度或许只是个人趣味,或许也有几分知识分子对流行的警惕。在文学创作与教学中,他曾戏谑“那代年轻诗人热衷的修饰语”,拒不迎合“某种时髦的阐释或批评观点”。或许,他是受到了18世纪末开始兴起于欧洲的“东方(其中包括中国)文化无用、落后、僵化”论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博伊德便指出:“纳博科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没有展现出他最好的样子,……纳博科夫在多数时候都坚决反对种族主义,但他无疑对那些所知甚少的文化比如非洲文化和亚洲文化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这方面,他跟随了他那个时代和地方的偏见——但是在多数时候他又超越了这些。”
可以跟“无用之物”稍做对比的一个物类是纳博科夫作品里出现的文娱类物品,包含中国的麻将、跳棋等。可能由于它们并非流行、热门,而纳博科夫又是象棋爱好者,他对它们并无微词。跳棋还被提了至少三次,其中一次,跳棋棋盘线孔相连的图案被用作对星球表面的某种形容。另外,纳博科夫喜欢编制象棋棋题,他的作品中也时常出现象棋、象棋的着数、象棋痴迷者、与象棋有关的意象等,他还有棋题与诗的合集。也许是对象棋的兴趣让他在众多的异国细物里特别挑出了棋类并且数次提起,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写中国象棋,却不得而知。
四、“中国诗人”与纳博科夫
对梦觉主题和生死主题的关注
尽管纳博科夫对“东方智慧”似乎不以为然,并将其与“暴力”并提,可他对庄子却有些不同。在评论文章《莱蒙托夫幻景》(“The Lermontov Mirage”,1941)里,讲莱蒙托夫《梦》一诗时,他较完整地引用了“庄周梦蝶”:
于是我就想到那个中国诗人,他梦见他是一只蝴蝶,接着,他醒来以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做了蝶梦的中国诗人(Chinese poet),还是说,一只蝴蝶梦见它是一个中国诗人。
对比《庄子》原文: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可以看到,虽然在纳博科夫的引文里,人物的名字和身份有些模糊,也不见“栩栩然……不知周也”“蘧蘧然周也”等心理细节,但主要情节与中心句都得到了准确复述。这样的复述也体现出复述者关注的重点,至少有:蝴蝶意象,梦与现实的难辨。
纳博科夫从莱蒙托夫的诗联想到“庄周梦蝶”的原因之一,应该是诗里有梦与现实的难辨。在莱蒙托夫的诗中,主人公“我”梦见自己身受重伤倒在山谷的沙地上,血一点点滴出;这个“我”梦见的自己睡去了,梦见家乡一位姑娘;而姑娘则梦见,在那山谷里躺着一具熟悉的尸体,滴血成线。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在这首诗里,是“我”梦见的自己梦见了“她”,还是“她”疑似梦见了被“我”梦见的自己。
此外,之所以想到“庄周梦蝶”,还因为诗里有生与死的难辨。纳博科夫说此诗出了个错——“熟悉的尸体(знакомый труп)”。他认为,“熟悉的尸体”或其英译“well-known body”都不好,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糟糕的语法现象”,还因为“在《梦》这首诗本身死者和生者是那样无可救药地混在一起”,但他又说,“在某个意义上讲,要不是出了那愚蠢的错误,这首诗或许会少一些神奇”,接下来,他就提到“梦蝶”典故——“于是我就想到那个中国诗人……”。纳博科夫从“生死”想到“梦蝶”,据此可合理推测,纳博科夫也许了解“庄周梦蝶”的上下文(如此前的“丽姬悔泣”),而不是只知道一个“梦蝶”片段,因为单从这一片段似乎很难看出其寓生死于梦觉的意思。
纳博科夫想到“庄周梦蝶”,是因为他看到莱蒙托夫的诗里有同样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即梦觉难辨、生死难辨的主题,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能看到。
他的诗作《梦》(Сон,1925)里就有梦觉难辨的主题。一个雨夜,主人公梦见自己仰卧在堆满干草的马车上,车轮嘎吱作响,半梦半醒时,他听见雨打窗框响,一时间“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梦”,是他乡夜里窗框不安的呻吟,还是干草堆里就在唇边的一朵洋甘菊。
庄子,图片源自百度
《未知地带》(Terra incognita,1931)同“庄周梦蝶”更近一层。该小说似乎在写身陷丛林沼泽里的叙事者及其同伴在死前的最后时光,但这位患上热病的叙事者在描述周围环境时,又多次将丛林景象与室内景象混淆(天空-青墙、芦苇-壁纸的芦苇花样、两栖动物-扶手椅、岩石-床铺、鸟儿-长颈玻璃瓶等),对两种时空何为现实的判断也是一时此一时彼。这就重复了庄子的句式:不知是患了热病的探险者在丛林里幻梦出城市的房间、最后死了,还是房间里的发热病人梦见了一场探险、还活着?博伊德从另一角度指出《未知地带》与“庄周梦蝶”的相似:“就像那位中国圣贤庄子从梦中醒来(他是一个梦见自己是只蝴蝶的人,或者它是一只梦见自己是个人的蝴蝶?),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感到,我们只有往外跨步才能知道我们的现实所处的位置,但活着的时候我们却无法跨出那一步。”博伊德的着眼点不在“难辨”,而在“不知”或者说“欲知”。
的确,两个故事都能让人感到,有生之年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的现实所处的位置”。但还是有些微差别。往外跨步才能“知道”什么这一说法,好像更适用于纳博科夫的作品,却不太适用于庄子的作品。在纳博科夫这里,“不知”的后面还有对“知”的渴求。小说标题“未知地带”既指叙事者身处其中的原始丛林里的不知名处,又指事实上叙事者未知身处哪种现实,眼前景象的暧昧不断给他带来困扰,他一直在试着看清,而死则可能是得到答案的契机。就像纳博科夫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完美》(Совершенство,1932)的主人公在死时和死后终于清楚看见过去与当下、亲历的与非亲历的一切(如博伊德所说,“也许只是因为他死了,他现在能将所有的生活都呈现在眼前”),《未知地带》的叙事者在将“死”之时似乎突然摆脱了此前的游移不定,终于接近了真相,“我明白了,纠缠不休的房间是赝品,……我明白了,真的东西——它在这里:这片奇妙而可怕的热带天空,这些耀眼的芦苇马刀……”,这种“明白”让他“发现自己有了力量”。且不论真相究竟如何,可以看到的是,在这里,“知”的获得让一个人身心振奋,“知”是被肯定的。然而,在庄子的故事里,说“不知”并非为了求“知”,“知”不是追求的目标。在第一个“不知”(“不知周也”)这里,“知”不被需要,因为“不知”是个假定前提,庄子由此展开讨论。而且,正如周作蝶时“不知周”,身为此时不知彼,人在生时也不可能知道死后的情景、死后是苦是乐,因此,如成疏所言,不必“当生虑死,妄起忧悲”。在第二个“不知”亦即纳博科夫所引的“不知”(“不知周之梦……”)这里,“知”同样不可得,也非必要。梦觉难辨,“往外跨步”也无解,因为正如郭注云“自周而言,故称觉尔,未必非梦也”,就像死生难辨,生者以生为生而死者非之、以生为死,生者以死为死而死者非之、以死为生,两方都是自是而非彼,但其实如郭注云“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庄子不困于名相之别,不执一端,安时处顺,“成然寐,蘧然觉”,生或死,梦或醒,人或蝶,都无所往而不乐。尽管面临的谜题相似,俄裔作家和中国哲人对待的方式是不同的。
纳博科夫将哲人庄子误作“诗人”,也未顾及透露作者主观倾向的“蘧蘧然”等细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虽然他看到“庄周梦蝶”的生死主题,但与其深层的哲学思想仍有隔膜,他从中接收到的,主要是文学层面的东西,包括蝴蝶这一诗意而又让他感觉亲切的意象和他本人作品中也有的相似主题,简言之,主要是他熟悉和喜爱的东西。
另外,对比纳博科夫的俄语作品和它们的英译本时,我们还注意到,纳博科夫俄语小说里一些有关中国的内容,在后来的英译本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删改,如“中国的小神像”成了“黄铜玩偶”、“中国墨水”成了“印度墨水”,或是接连几行都被删除。改得较多的是《王,后,杰克》,变动至少五处,如“要能去趟中国就好了”改成“我想我明天要去跟伊西达约个会”,“这个路人明天要去中国或者他是个有名的密探或者杂技演员”改成“长凳上那个老人年轻的时候——哦,我不知道——也许,是个有名的杂技演员”。如果说改成“印度墨水(India ink)”可能是为押头韵,其他变动似乎不像是出于修辞的考虑。这些删改或许也从反面说明,科兹洛夫20世纪初对西夏遗址的发掘确曾在纳博科夫心里燃起探险热情,而到20世纪下半叶纳博科夫处理小说英译本时,热情有所冷却。
结 语
毛姆《在中国屏风上》的译者唐建清认为,“一种异国形象既是对‘他者’的注视和观看,同时也是形象构想者的自我呈现”。纳博科夫笔下的中国同样如此:在他书写中国的同时,他的一些个人特点也呈现出来。
纳博科夫对“自然”的中国和“人”的中国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对前者心驰神往,对后者却少有褒扬。面对中国的物时,他对热门特产不屑一顾,却对非流行的跳棋加以青眼;“庄周梦蝶”的故事被他引用,他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疑问。纳博科夫没有到过中国,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有赖于文献资料,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集体想象,但也与他个人好恶密切相关,有时体现出他的个人特点——对鳞翅目昆虫与棋类的兴趣、对残酷和死刑的憎恶、对流行的警惕、对梦觉主题与生死主题的关注等等。
综而观之,纳博科夫所见的中国更多是物质层面的,主要是他通过文献资料了解并为之着迷的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因商贸、战争和文献资料进入其视野的中国物产。虽也引用过庄子,但他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了解不多,也无意深入。尽管他不曾像前辈托尔斯泰那样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着迷,不可能像后辈佩列文那样将中国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研究他的中国观对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而言似乎意义不大,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梳理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它并不只是一位中国的纳博科夫研究者对该作家对本国态度的好奇。
它首先有增加资料、填补空缺的意义。国外的纳博科夫研究早已扩展到研究该作家与地理、绘画、电影、火车、汽车和飞机等的话题,那么,对该作家的文学文本自身的研究,也值得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对纳博科夫十卷本文集里每一卷都提及中国这一现实,不该无视——更何况这里涉及的还是一个世界无法忽视的大国和一位世界无法忽视的大作家——至少可以对大部分的相关素材做一次初步、粗略的梳理,让人了解纳博科夫笔下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其次,对这个问题的梳理让人具体看到纳博科夫笔下的中国与他的个人特点的关联,看到他的个人特点在中国主题上的体现,这是看他个人特点的一个新角度,就像通过对比素材与成文去了解纳博科夫的细节艺术是一个新角度,能更新人们对该作家的既有认知。日后谈及纳博科夫与“残酷”“蝴蝶”等时,必要时也可用其在中国主题上的相应体现作为例证。此外,本文曾提到纳博科夫小说对他人游记所写事实的借用、纳博科夫俄语作品里的中国主题到英译本后的变动,因此,对纳博科夫笔下中国这一问题的梳理,还有助于更全面地看待纳博科夫的作品、看到这位强调“虚构”的作家的虚构作品里非虚构性的部分,同时也为纳博科夫作品今后的异文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留意的地方。这对纳博科夫学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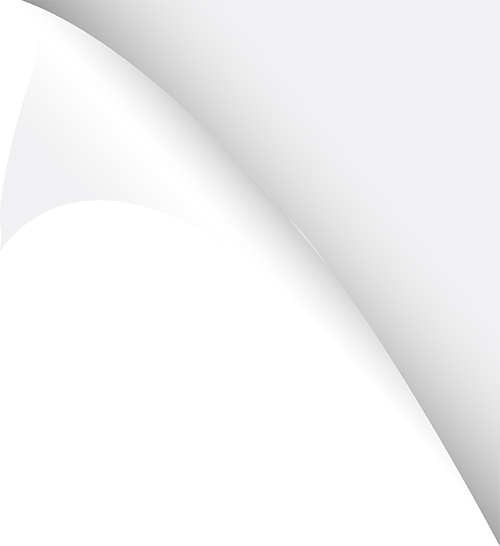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5期“文化研究”专栏,责任编辑龚璇,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萌
排版:王雨璇 终审:文安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点击封面or阅读原文
进入微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