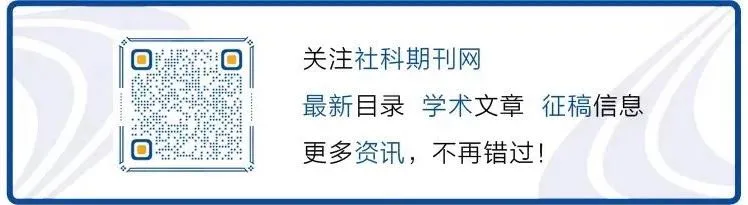作品及作家研究丨古斯塔夫·鲁作品中“家园”及“在家者”的存在论意义——以《天堂随笔》和《致收割者》为例

苑宁,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瑞士法语文学、现代法语诗歌。近期发表的论文有《雅各泰〈绿意册〉中的植物诗学》(载《外国文学》2023年第5期)。
内容提要 瑞士法语诗人古斯塔夫·鲁是促成20世纪瑞士法语诗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人物之一,存在之思贯穿其“农人文明”书写之始终。本文拟将其两部散文诗集《天堂随笔》和《致收割者》置于荷尔德林的“回家”诗思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烛照下,以探索鲁借助“在家者”形象构建起的独特的存在诗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读不仅呈现了荷尔德林的“家园”概念的本质,且能够作为有效工具用以揭示鲁作品中隐匿的存在维度,显化主人公的“在家者”身份以及“家园”的存在论意义,照亮鲁散文诗的诗性本质,驳斥将这两部作品视为同性爱欲书写的狭隘解读。
关键词 古斯塔夫·鲁 荷尔德林 海德格尔 家 存在
引 言
古斯塔夫·鲁(Gustave Roud,1897—1976)是瑞士著名法语诗人、翻译家、文学批评家,虽毕生蛰居乡间,其文学成就的光芒却照彻20世纪整个瑞士法语文坛,菲利普·雅各泰(Philippe Jaccottet)、雅克·谢塞(Jacques Chessex)、莫里斯·夏帕(Maurice Chappaz)、安娜·佩利耶(Anne Perrier)等多位享誉世界的瑞士作家和艺术家都尊鲁为典范。鲁与皮埃尔-路易·马泰(Pierre-Louis Matthey)、埃德蒙-亨利·克里兹奈尔(Edmond-Henri Crisinel)并立于 20世纪上半叶瑞士诗坛前沿,是促成瑞士法语诗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人物。鲁深刻认同荷尔德林以诗歌为本质命名的尝试,他以散文诗为主要文体,将“存在”之思化入对瑞士乡野生活和“农人文明”(civilisation paysanne)的书写中,在凝视自然万物尤其是作为“大地之子”的农人时,得以挣脱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所布设的庸常之网,洞察潜伏于生命表象之下的一种宇宙秩序。瑞士诗歌评论家玛丽昂·格拉芙认为,鲁的散文诗是具有“伦理介入”意识的“诗意经验”,是“形而上学及存在层面的重大拷问”。乔治·尼科尔称鲁的诗作是“诗学意义上最为纯洁和精准的表达”。
古斯塔夫·鲁和《天堂随笔》、《致收割者》
图片源自Yandex
“农人”这一形象贯穿鲁的多部散文诗作品,而出版于1932年的《天堂随笔》(Essai pour un paradis)和1941年的《致收割者》(Pour un moissonneur)这两部诗人壮年之作更是全篇聚焦一位名唤艾梅(Aimé)的农人。评论界对于这一人物的解读,多基于诗作对艾梅的赤裸身体以及叙事者与艾梅二人肢体接触的描写,并从诗人《日记》(Journal)中关于其与多位农人朋友往来的记述中搜集证据,判定诗人与艾梅是同性爱人关系,继而考据艾梅的真实身份,将其定位到鲁在《天堂随笔》的致辞中提及的奥利维耶·谢尔皮奥·德·萨朗旦(Olivier Cherpillod de Sarandin)身上。然而这一判定,不论属实与否,本质上都属于去诗意化操作,使得鲁的散文诗失去象征意义和寓言功能,从而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语言”(Sage)贬黜为日常语言。因此,本文不赞同在鲁的生平中寻找艾梅的原型人物的印记,而是选择将鲁的《天堂随笔》和《致收割者》置于荷尔德林的“回家”(Heimkunft)之诗思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清辉烛照下,探索鲁如何通过构建“在家者”形象来书写一种独特的存在诗学。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存在论解读,揭开了后者诗歌中隐现的家园本质,我们亦可将这一解读作为有效工具,来发掘鲁作品中隐匿的存在论深意,照亮其散文诗的诗性本质,因为“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诗歌的本质即是倾听、回应、建构存在。正是在存在维度上,瑞士尤其是汝拉地区的自然景观呈现出“人世天堂”(paradis humain)的象征意义,而人物艾梅则摆脱了普遍认为的“情人”身份,显露其“在家者”真身。鲁的创作初衷或在于以萨朗旦这一真实存在的农民友人为载体,将他所眷恋的所有农人——可能是瑞士最后一代诗意栖居者——的形象浓缩其中,将现代性浪潮侵袭下渐行渐远的传统生存方式所蕴藏的核心精神注入其中,从而借由这个亦虚亦实的人物,提取出人类与世界之间种种复杂而有序的可能关联,亦是借由“在家者”这个中间人让存在论意义上的“家园”从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浮现出来,这正是鲁以语言之诗书写存在之诗的前提,也是他继续德国浪漫主义尤其是荷尔德林留下的“回家”使命的关键行为。
一、 回家之路——海德格尔、荷尔德林
与古斯塔夫·鲁
“在家”这一隐喻作为“隐秘的浪漫存在论潜流”深刻影响了德国的思想史。17世纪上半叶,德国诗人弗雷德里希·冯·洛高(Friedrich von Logau)在《格言诗》(Sinngedichte)中首次将“在家”与存在意义上的主体性相关联。其后,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将“在家”概念“抽象化”和“心灵化”。18世纪末,深受赫尔德影响的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洞察到日常生活与社会秩序之下人类“在世而不在家”这一根本性存在危机,从此开启了漫长的“归家”之路。诺瓦利斯在《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中自问:“在异域的天空下”,“我还能否怀想家园”?荷尔德林则在悲歌《还乡》中诉说归家冲动:“故土的门户/诱人深入到那充满希望的远方”,“回故乡,回到我熟悉的鲜花盛开的道路上”。他有意给故乡以“苏维恩”(Suevien)这样一个古老的名称,借其承载“故乡最古老的、最本己的、依然隐而不显的、但原初地已经最有准备的本质”。
赫尔德,图片源自Yandex
荷尔德林正是连接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和古斯塔夫·鲁存在诗学的枢纽。鲁深受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影响。作为翻译家,他译介到法语世界的四位重量级德语作家——荷尔德林、诺瓦利斯、里尔克以及特拉克尔(Georg Trakl)恰巧都备受海德格尔推崇,其中荷尔德林更是促使海德格尔于20世纪30年代实现诗思合一转型的关键人物。正是在荷尔德林的《还乡》一诗的启悟下,海德格尔借助诗歌这一超理性的“本真语言”,突破形而上学关注存在者而忽视存在本身这一精神阱架,在深入探求存在本源后从理论走向生存本身,提出“诗意栖居”这一现代人类社会救赎方案,以《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人诗意地栖居》以及《筑·居·思》等论著完成诗歌、语言、存在这三个面向的哲学聚合,继而构建起“回家”——返回“本源的附近”(Nahe-wohnen)——这一存在论概念。
里尔克和特拉克尔,图片源自Yandex
如果说鲁和海德格尔都分别与荷尔德林发生了具体而直接的关联,那么鲁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是什么?将鲁的作品置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角下有无可行性和必要性?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解这个问题:一、贯穿两部散文诗集的核心关切是什么?二、为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尤其是他关于荷尔德林“回家”的运思能够揭示鲁的作品的根本维度?
要回答以上问题,需从本文关注的两部散文诗集的概貌说起。瑞士学界一直难以定性鲁的作品,仅模糊地将之命名为散文诗(poèmes en prose),以示其杂糅性和复杂性。两部作品的散文性显而易见,体现为叙述连贯、语法标准以及叙事对象明确——即对艾梅不同生活图景的描述,包括劳作场面如播种、收割、摘果、磨刀,农歇时的日常行为如吃饭、喝酒、洗澡、睡觉,以及他与诗人作伴的散步、骑马、相谈。然而,与叙事内容的简单相对,两部作品的叙事方式和行文机制相当复杂:一方面,两部作品显现出非格律层面的“诗的破格”(poetic license),无法被直接归为散文体;另一方面,两部作品蕴含着某种诗歌美学,即通过打破日常指涉体系,超越客观真实,切断逻辑链条,从而尝试回归诗歌的根本特征即抒情性,以实现对内在经验和存在本质的溯源。这种诗歌美学在两部作品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诸种生活场景如百衲衣般交错叠加,没有任何过渡或背景交代;二、时间线被模糊化处理,看似清晰的时间标志实则相互矛盾,例如第一部分中,夜间尚被追忆的逝者艾梅,“日出”时分却复生,前来敲门;三、变形的回忆与梦境、想象交织缀连,令人难以辨别现实与超现实的边界:“可怜的记忆被魔法所困”;四、抒情与思辨随处而起,构成川流不息的内心独白,这一语流极具私密性,对事件、语境、逻辑不做解释,导致某些突然而发的情感和直接的指称如“人世天堂”“世界之主”等形成解读困难;五、不同人称交替出现且无过渡,例如诗人用第一、二人称指称自己,用第二、三人称指称艾梅,于是旁观者、对话者、被凝视者等身份相互转换跳跃,造成意义的增生和解读的不确定性。
如上种种特征导致鲁的作品呈现出言说悖论和阐释困难,催生了有关同性情欲书写的解读。那么,如何触及被诗人有意“隐匿”的本真语言呢?我们需找到诗人的核心关切,即贯穿其生命的关键思考。事实上,在《天堂随笔》开篇处,鲁即以隐喻的方式道出了作品的真正关切和诗意内涵。他述说当自己伏于桌前、梦回往事时,一只夜蛾飞入视线。诗人在夜蛾和艾梅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似性:“黎明前的旅伴,我的精神与你言说,就像面对一位我所爱的兄弟,我恳求你再等等,就像恳求他一样,而唯一的答复:你振翅一跃,扑入火中,比他还要迷醉。”短短几句,不在场的“兄弟”被三次与夜蛾相提并论,于是在以后者为中心构建起的隐喻体系里,意义从夜蛾流向艾梅,昭示主人公的根本身份和存在性本质:
它[我的精神]是夜蛾的影子,笑着模仿这以茸毛和灰烬组成的可怜的小小身躯,和它一样逃离了意识缺失的夜,是已失世界的脆弱的守护者。长夜将尽,火焰在等你,即将被焚的小小存在者,先于艾梅的伟大存在的小小存在者。……现在你已死了,而我却想要你重生,让你再次穿上那镌有符码的绒毛外套。这些符码如由一根睫毛绘出,我试着认出它们所组成的神秘童话,现在我知道了:孤独,孤独,红黑相间的涡卷图案隐隐说出,这是没有重量的生命应受的惩罚,随后就是死亡。啊!世上再无夜蛾也无人!
“意识缺失的夜”呼应“已失世界”,明确指向一种“末世想象”,鲁意识到自己或者说现代人类都是“一种已然倾颓、即将突变的文明的弃儿”。在这样的背景下,夜蛾的身份是“守护者”——“已失世界的脆弱的守护者”,同时双翅“镌有符码”和“神秘童话”,是真理的传递者。这一身份和价值,同样体现在艾梅身上,他作为存在真理的传递者、诗意栖居的实践者,以肩膀上的“光”与“意识缺失的夜”相对抗,并在这种对抗关系中,开启世界重新“组织自身”的可能性。诗人曾试图在“死去的语言”里寻找生命本质,以挣脱现代世界派生的存在构型,却在与几位同道友人伏首于诗篇时,忽然瞥见窗外“收割黑麦的人”的身影:“他的头映着天空,赤裸坚实的肩膀上流动着油一般的光。在他的周围,世界已经随着他的呼吸律动组织自身;山峦弯曲,又隆起,正当他黝黑光滑的胸膛起起伏伏时。”艾梅所开启的新的世界,正是后文鲁所谓的“人间天堂”即存在意义上的家园,“收割黑麦的人”不仅展示了空间易变的可能性,还揭示了人类存在方式对于空间易变的关键作用,因为世界随着“他的呼吸”组织自身秩序,山峦模仿其身体律动变化自身形态。至此,我们已能回答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鲁的核心关切:这一段中鲁以“伟大存在”唯一一次直接称呼艾梅,明确指出人物的关键意义在于其存在性,同样,由艾梅组织和显化的家园的根本属性亦是存在性,因此鲁作品的根本维度即是存在维度。由此得以链接我们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尤其是关于荷尔德林“回家”的运思揭示了鲁的作品的根本维度?在此或许可以借用海德格尔关于思想者与作诗者关系的讨论作答:
因为现在必须首先有思想者存在,作诗者的话语方成为可听闻的。唯有忧心者的运思,由于它思及那被诗意地表达出来的隐匿着的切近之神秘,才是“对诗人的追忆”。在此追忆中,才开始了与返乡诗人最初的亲缘关系。
“思想者”海德格尔以哲学语言对“作诗者的话语”进行解码,使后者成为“可听闻的”,他发现荷尔德林揭示了“家园”的存在论本质,即地理位置不能决定家之为家,家的本质特征是“切近”,“切近”中包含着一种可及性悖论:“锁闭的故乡”“难以赢获”,“返乡者到达之后,却尚未抵达故乡”。家乡虽可“照面”,但“最美好”的“发现物”已经隐匿。无论是“在家乡土地上定居的人们”还是“返乡人”都不能被认为已经抵达真正的家,因为他们都未曾“返回到故乡之本己要素中”。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家?海德格尔在评述荷尔德林的《返乡——致亲人》时给出了“家园”的定义:“‘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
海德格尔对家园的定义呈现出三重特征,空间性、存在性、完整性,而其中存在性是决定性因素。他对存在性的强调将存在从存在者身上分离出来,将动词原本具有的能量物归原主——“在”。如何存在,决定家是否为家。而鲁整部作品对在、在家、在家者,对在家者所开启的家园的关注,正契合了海德格尔借荷尔德林诗歌所揭示的家园之存在性。正是沿着这条路,鲁将荷尔德林的“回家”事业向前推进:不同于荷尔德林用诗歌或语言道说存在,鲁借由在家者用存在言说存在。如果说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作为“家”的寻觅者的诗人既是叙事者也是中心人物,那么鲁则将诗歌与诗人置于次要地位,或者说使之退居后景,而将艾梅所代表的“在家者”即存在的实践者推入前景。由此,鲁把诗歌从语言范畴扩展至存在范畴,以栖居之诗代替语言之诗,让存在本身言说存在。由于存在是超语言或前语言的,所以用以揭示存在的语言必有其先天局限性,能够令存在真正显现的唯一方式就是存在本身。鲁并未对家进行理论的或先验的描述,而是通过在家者最具体的生活实践对存在问题予以回答。
海德格尔,图片源自Yandex
二、 家园的表征——
应和、秩序和爱
“在家者”艾梅是自谓“流浪者”的诗人与“家园”之间的中间人,正是通过对艾梅生命经验的细腻体察,鲁试图窥见诺瓦利斯所言的“散落人间的天堂”的真实样貌:“这个男人凝望着、呼吸着。什么样的世界会倒映在他的目光中?从终将腐朽的事物中将升出怎样一个永恒之国,投射在他野鸽般赤裸裸的瞳孔里那温柔的一抹蓝中?”顺着诗人这个问题,即“永恒之国”所隐喻的“家园”究竟是何等模样,我们可从其对艾梅“在家之感”的陈述中提取出“家园”的三个主要特征——应和、秩序、爱。鲁如此描摹在“休息的耕田人”周围展开的“人世天堂”:
这唯一停下来的身体,斜倚着犁铧,让世界和他一起停歇,甚至邀请地平线加入他的休息。……从被命名的事物所组成的秋天里,升腾而起另一个音色清澈的秋天。一切都化作歌。玫瑰和村庄齐唱,一簇一簇的雏菊和山上的雪,犁镜和钢板一样的池塘水面,至高的云拱下极尽委蛇的山路,深沉的大地的种种色彩,绿、灰、粉,所有这些齐声歌唱。古老的合唱在消失后又重生,围绕着这副躯体回荡不绝。
生命之间的应和揭示出世界的三种本然特征:一、亲密性——“每一事物都在一种无法言说的温柔中贴合其他事物”;二、同构性——“一种被柔化的存在,从一种表象流向另一种,好像是同一个身体的不同显现,相互交换着滋养自身的血液”;三、关联性——事物之间表面的断裂或空白都被一种“情意”所填补:“山峦接纳了天空,耕地向草地退让,草围绕着它,没有一丝颤抖。”海德格尔曾指出,“此在的世界是一个共同世界”,“所谓在世,就是与他者共在”。“在家”,即“存在于世界中”(Sein-in-der-Welt),居于一个复合的关系场之中,与世界发生复杂互动。同样,鲁笔下的“家园”不是地理概念,而是超越时空范畴的关联体系: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以海德格尔所谓的聚集(legein)的方式共在,通过相互呼应而建立起彼此护持又各得其所的敞开域。
由此,应和便可引出鲁笔下家园的第二个特征,即秩序。诗人喜用音乐修辞描述自然事物中的秩序感:“被构设的广阔风景”中,“和弦与合奏响起,宏大的交响乐铺展开来”。他将“完美的存在”与“简单的组合”相关联:“完美的存在隐约显现,其踪影可在声、色、语句和分钟最为简单的组合中被察觉。”雅各泰也在鲁的风景美学中发现了一种“温柔的连缀”和“幸福的合奏”。在这样的空间中,万物适得其所,获得归属,发现并满足于本己本质。“在家”意味着众生归其本位,在其所在、是其所是、有其所有,即是将“存在”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的三重基本含义——作为系动词的“是”、作为持有的“有”和作为实存的“存在”——归于统一,于是整个世界处于一种恰到好处、满而不溢的秩序之中。
促使万物应和、构建世界秩序的原动力,是一种终极的生命体验——爱。这一线索实际上已经伏笔于主人公艾梅的名字中。艾梅(Aimé)是法语动词aimer(爱)的过去分词,可构成被动态,表示“被爱”之意。艾梅被宇宙所爱,天真而蒙昧地生存在万物深深的善意之中:“这倦怠的身躯,在宇宙温柔的轻抚之下,等待着尚未知晓的讯息。”被爱的艾梅同时爱着世界,这种宇宙之爱的双向性揭示了艾梅之名的第二重深意:动词不定式aimer与过去分词aimé是同音异形词,艾梅之名就是爱与被爱的统一体,是爱的施动者与受纳者的合一。作品中有大量对于爱欲的书写,“欲望”“赤裸”“肉体”成为高频词,诗人多用慢镜头特写身体局部和细腻触感,用缓缓流动的语言模拟滞留于肉体上的目光。例如,《天堂随笔》中《浴》一篇专写在河水中洗澡的艾梅:
你的肉体,或是赤裸,或是被覆盖在与太阳永恒相连的衣物之下,我知道水迷恋着你,无法自拔!不论是空中倾倒的水罐——它冰凉的水流深入你的喉咙(因为它是为你的唇舌解渴),还是那风儿——它像影子般与你结合然后死去、它清凉的羽毛在快感的战栗中融化于你的胸膛,亦或是睡眠,所有这些都不能让你燃烧着的身体复归平静。
然而此类情欲书写容易导向一种解读,如法国女作家玛丽莲·德比奥尔便从书中三次出现的“像女人一样”这一表述出发,认为诗人通过自比女性以抒发同性之好;她称鲁是“深陷爱河的人”,如“稼禾般”“等待被他所热切渴望的农人们收割”,而艾梅则是其“所爱之人”,有着“令人着迷的身体”。我们在回应德比奥尔的解读之前,可从“像女人一样”这一线索出发,定位其语境从而探求其真义。在《天堂随笔》中一篇名为《眠》的作品中,鲁如此描摹睡梦中的艾梅:“它(天空)轻轻俯向你,什么也不能搅扰你的清梦,连那巨大的蓝色头颅也不能,它无声地靠在你的胸膛,像女人一样。”可以发现,与艾梅发生情动的对象不是诗人或任何人,而是天空,也可以是前文中提到的水和风,是万物。艾梅与万物建立爱人关系,使世界自然而然成为家,即庇护爱的场所。
因此,当鲁写下“像女人一样”时,是将人类性别作为隐喻,指向一种深远的生命总体性,指向一种弥散于众生之间、无处不在的亲密关系。在性别隐喻的框架下,艾梅的肉体是男性的,女性代表他者身体,不仅是与自我有着亲密关系的他者,更是自我缺失的互补,是性别意义上的镜像,是构成身体完整性的二元结构的制衡点。在这一意义上,万物皆“像女人一样”。性别隐喻中的人体,实则为单性别,只有在与万物的亲近中才能获得圆满的自我。如果说艾梅的身体“令人着迷”,它并非被“人”所渴望,而是作为实现生命完满的可能路径而被万物所渴望。而被评论者称为“窥视者”的诗人鲁,所窥视的不仅是洗澡或耕作时艾梅的赤裸肉体,更是后者与世界肉身交缠时形成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原初场景”:“草木因与你肌肤相亲而沉醉,一种类似尖叫的声音从你幸福的肉体中流淌而出。”
三、 两种家园和两种存在方式
从艾梅的“在家之感”出发,我们提取到“家园”的具体表征和一般概貌,然而还需叩问的是,如果说鲁在作品开篇即明确了艾梅的存在论价值——“伟大存在”,那么他赋予空间“家园”的存在论意义体现在哪里?他笔下的“家”在何种程度上区别于世俗意义上的家?在《天堂随笔》中标题为《年》的作品中,鲁分辨出两种“家”:
今天早上,我的欢喜在于蓦然见到艾梅,在他生命尚未受损的这一刻,他正驾驶着收割机归来,向着他的家,头上是树叶组成的拱廊。这样的生命洋溢着无尽的幸福。这晴朗清晨中的迫不及待。身体被劳动所召唤,自觉如此有力又如此轻盈。
这段看似在描写艾梅归家的平凡一刻,其间却颇多疑笔:“早上”是一天的农事活动将始之时,“驾驶着收割机”的艾梅理当出发,但鲁何以称其“归来”?既言“归来”,又为何说艾梅的身体“被劳动所召唤”?若被劳动“召唤”,艾梅即当前往田间,又何以“向着他的家”?对于这段看似自相矛盾的陈述,诗人已留下线索,以斜体强调两处关键词——“他的”和“召唤”。主有形容词的斜体在下文不远处再次出现——“我的小房子”。顺着主有形容词这一线索,可以找到后文中“他们的房子”,我们发现诗人对于不同所属的空间的差异性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刻的描述:
山上的男人们沉睡在自己的烦恼之中,他们各有一个名字、一个女人,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孩子,——刚才你还像他们。我看着你。现在你独自一人。……大地可悲的起伏、路上扬起的漫天灰尘,还有山上的村庄,都被忘怀。这里是最基本之物的天下,它们以最纯净的方式存在着:阳光和水落在沙地上,凹处一片蒸腾的水雾,石头、空气以及一个男人的身体与它们完美结合。
在这段文字中,鲁勾勒出几组对立双方:人物上,“山上的男人们”和“独自一人”的“你”即艾梅;存在方式上,前者“沉睡在”“烦恼”中,后者与“最基本之物”完美结合;空间上,“他们的房子”或“山上的村庄”与艾梅所处的“最基本之物的天下”。然而,“山上的男人们”与艾梅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立?二者分别代表怎样的“家”?为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定位“山上的男人们”这一模糊指称。鲁的作品中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农人群体,其一是以艾梅为代表的秉持本真存在方式的“在家者”;另一类则是被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所规训的新农人们,他们已沦落为真正意义上的“奴隶”:“收割者向你[艾梅]伸出幽暗的手臂,/从此钉于大地的十字架上//……这无主之羊群的堆累,//这奴隶式的接受,你否定他们。”“否定”一词显示两种人群的对立,与“在家者”相对,被现代性裹挟的新农人们或可被称为“离家者”。他们被诗人形容为“盲目的生者”,失去了对自身和世界的感知,失去了与家园的关联——这是“比死亡更苦涩的缺席”。
荷尔德林,图片源自Yandex
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是荷尔德林、海德格尔、鲁共有的关切。海德格尔用“集置”描述当今世界的“气相”和“现代性灾难”,托马斯·希恩将之解释为“盘剥世界”,在这一气相中,任何存在者首先被视为“为了商业用途而亟待盘剥的东西”,即“工具理性以及商品化的关联物”。在鲁所呈现的“在家者”—“离家者”二元对立结构之下,潜藏着存在危机这一现代诗歌母题。在诗人所处的时代,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恒久未变的瑞士田间风光及其相关联的存在方式正在发生彻底转变,因此鲁的散文诗中潜伏着深痛的末世情怀和“永别”(adieu)意识——后者正是他第一部散文诗集的题目。直至最后一部作品《消失的田野》(Campagne perdue),诗人仍在反复咏叹理想文明的式微:“同一片天空下,同样的四季轮回中,农人世界的心灵慢慢狂热起来,直至无可救药”,“它宁静美好的面庞渐失从容。”
这些心灵“狂热”至“无可救药”的“离家者”,“沉睡在自己的烦恼中”,即使身在家中也难获海德格尔所说的“在家之感”。因此“他们的房子”仅仅只是世俗意义上物质或建筑层面的家,其本质是内在性,在“家”即在“内”,处于一种被包裹、被保护的相对中心地带,而内—外二分结构实则意味着割裂。与此相对,鲁通过对“他的家”即艾梅的家的悖论式书写,实现对“家”这一概念的陌生化和重构,揭示出一种诗性的、存在意义上的“家”,即外在的家,或者说是以外为内、内外无界的家,是大写的宇宙之家。上文提出的矛盾由此迎刃而解:“他的家”即艾梅的家就是劳动“召唤”身体的地方,去往自然田间即是“归来”、回家、成为“在家者”。由此,上面引文中第二处斜体文字“召唤”,显现出两方面的关键作用:其一,“召唤”是方向性的动作,家园的召唤与田间劳动的召唤相重合,就意味着家与自然的重合,艾梅所在的家园就是与“他们的房子”相对立的“最基本之物的天下”;其二,“召唤”的施动者是“劳动”——“身体被劳动所召唤”,说明在艾梅进入“在家”状态的过程中,“劳动”这一动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劳动”,农人被“召唤”(appeler)而享有真正的存在,生命得以焕新,“自觉如此有力又如此轻盈”。与大地直接相关的“劳动”,将身体的行止规律嵌入宇宙秩序之中,从而让世界成为家园:“所有这些功利的照料,所有这些有利可图的劳动,最终却导向世界之园的奇迹。”在荷尔德林有关“诗意栖居”的著名诗句中,常被忽视的前半句实则是后半句的前提条件:“人辛勤劳作,却诗意地安居在这大地上。”由此可见,存在者并非天然“在家”,世界原本也非“家”,促成关键性转化的即是“存在”这一动词而非名词:“当人安然栖居时,大地便成为大地。”通过存在,存在者将自身掷入世界中,与后者缔生具有滋养之力的联结,无数联结将世界变为具有包裹性和互动性的关联场域,由是为“家”,而存在者由此成为在家者。
从“他们的房子”到“宇宙家园”,两种不同的“家”实则隐喻两种不同的家—人关系模型和两种存在方式。“他们的房子”对应的是离心式的家—人关系,指向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非本真状态”,即存在者的存在呈碎片状,他们持有一种“家”的假象,自以为在世界中享有个体的、独立的家,但这虚幻的安全感实质上已割裂了此在所具有的同一性。与此相对,艾梅代表的则是向心式的家—人关系。两种家—人关系对应着两种生命情态:在家者沉浸于喜乐与爱之中,而离家者则深陷孤独之渊。这种孤独是双重的,它首先来源于离家者与在家者的隔阂:“艾梅驾驶着收割机而来”,“如此沉浸于他的生活,沉浸于他的亲近者的生活,与他的劳动如此和谐一体,以至于某种断裂突然出现……”“深渊”( abîme)这一意象贯穿鲁的毕生作品,间离之感无关距离,而在于存在方式的对立。因此,即使与艾梅身处同时同地,诗人也会感到有如隔海的孤独:“只要这男人转过身去,再次投入劳动,那古老的孤独,曾经的孤独,就倏然涌上心头!我的幸福又变成失落的伊甸园,被与日俱增的焦灼所包围,就像那些每年都会被扩建的篱笆,它们将花草与我相隔日远。”诗人由此揭示出“孤独”的第二重面向,即离家者与“家”——“失落的伊甸园”之间的疏远。如果说这“孤独”既“古老”且“与日俱增”,只因人类对“花草”久已背离,“孤独”是一种扎根于现代性的群体性心理境遇,或可用本雅明意义上的“碎片”来形容。“碎片”所隐喻的是人与人关系的割裂,也是全社会专业分工和流水线生产生活导致的对事物的体验的破碎,更是人与世界母体之间的血脉纽带被斩断。
四、神化书写:“异教之神”与“人世天堂”
《天堂随笔》与《致收割者》收录的都是具有哲理性的散文诗和寓言性作品,其中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笔触交错出现,令人难辨虚实,由此,批评界生发出两条解读之路:求实者将作品视为诗人与农人同性之爱的自传式书写,而重虚者则视艾梅为神圣化、偶像化的产物,是“巨大、庄严”的“天地之子”。后者或许缘于鲁笔下多处描述似有“神化”之嫌疑:“在悬止的太阳之下闪耀吧,统治吧,世界之主”;“你将空间的宏大天使封存在你的身体之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鲁赋予人物身体及其所在空间的所谓“神性”?这是否意味着上帝已死,新神登基,传统神学披新衣回归,继续以一种超验的超级存在者解释存在之源?是否意味着鲁把荷尔德林、尼采所留下的信仰断裂以一种平庸而盲目的方式进行弥合,再次回避对存在本身的追问?
荷尔德林、海德格尔、鲁都曾对传统宗教意象与符号加以借用与变形,都曾以象征或隐喻的方式表述一种超语言的神性体验。因这经验先于语言而存在,所以无论是哲学表述、诗性语言(如寓言、梦呓、谵语)还是神学修辞,都只能是对于所指的模仿、暗示、接近,都是一定程度上以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在敞开的过程中对真相加以保留。对宗教意象、符号的借用以及再赋新义,意味着以既有语言体系为出发点,通向新的指涉对象,这种重构的语言造就了荷尔德林、海德格尔、鲁三人的晦涩之名,但诗作为本真语言的开悟力也在于此。细察之下,三人化用宗教话语的方式不尽相同。荷尔德林作为“遗失的诸神”之神学的发明者,以直呼的方式为神祇命名,如“极乐之神”“时间之神”等。荷尔德林未尝不知借用既有神学修辞所造成的局限性,他“缺乏本真的命名词语来命名”“居住在神圣者中的他”,因而其诗篇“现在依然是一首无字的歌”。语言局限性的根源不仅在于真理的不确定性,还在于人“存在于世界中”这一根本境遇所决定的认知局限。至于海德格尔,则是在锻造一个将世俗的神学和哲学化的诗学相结合的表述体系,但他同样面临语言有效性的问题:“他的神躲在异教和基督教的废墟中,不符合任何正统宗教的教义……他召唤新的神,却又没有命名:任何一个明显的、使用过的名字——不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别的——都不能把这个神带向我们。”鲁选择了另一种神性表述方式,他没有试图命名或召唤任何神祇,他的神化书写的两大主要对象是身体和空间,即在家者和家园,且这一操作通常发生在抒情过程中,鲁通过赋予具体的人物和空间以所谓“神性”,将现实生活陌生化,暗示另一种“真实”的可能存在,这一点正与他所钟爱的法国象征主义的主旨相合。鲁声称:“任何相似度的考量,都不能使我远离这样一种抒情真实——它与现实貌合神离。”不论是作为“异教的神”的艾梅,还是被喻为“人世天堂”的家园,都将看似对立的人性与神性统合为一体,这是否指向一种与现实迥异的“抒情真实”?这种“抒情真实”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真实性?我们需从鲁对艾梅和“人世天堂”的具体的神化书写入手,分而述之。在《天堂随笔》中的《眠》中,鲁如此描写八月间某个中午“收割完黑麦”在大地上安睡的艾梅:
在他的衣裳和肉体中,天地重归于好;这是它们实现深度交融的地方。这强大的身体溢出自己影子的范围,流向四野八荒,如同被呈于供桌之上,身处拜伏在地的群山之间……在他身上,天地深感圆满,因为他在天地身上也深感圆满。大地将他呈于天空,将他置于最纯净的山峦一端,那是朝阳第一缕霞光所经之地。
再如河水中沐浴的艾梅:
你是永恒。臣服于空气、石头、水——你是它们的主人,踩在深处的石头之上,在早已提前沉醉于你狂野的怀抱的水流之畔。你静定地呼吸着,立于存在之巅,默默受纳着树叶以及长流之水的赞歌。你是一切事物的分寸,你是精确而纯洁的肉身……
从上述描写中可提取出被神化的身体的两个具体表征,即巨形化和至高性。首先,鲁的神化书写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以夸张的比例和巴洛克式的视觉美学缔造一种奇异的和谐:艾梅“睡在青草之间”,“脸颊枕在巨大的古铜色手臂上”。鲁以“巨大”(énorme)一词修饰艾梅的手臂,又称天地在“他的衣裳和肉体中”“重归于好”,其意不在于简单的夸张,意象与修辞的自由度实际上反映了诗人对某种“抒情真实”的追求。如果确如鲁所称,在现实真实之外存在着“抒情真实”,那么艾梅身体的巨形化从何种意义上可称为真实?这种变形又是在哪种视角下发生的?我们注意到,鲁称艾梅“立于存在之巅”,其“精确而纯洁的肉身”“是一切事物的分寸”。身体发生巨形化的场所不是视觉领域而是存在维度,艾梅所据有的“存在之巅”的相对位置,暗示了凝视者即诗人的视角是仰视,正是在这一视角下被凝视者的身体发生变形。这一仰视关系恰说明二人的真正关系不是平等的恋人关系,而是一种高下有别的关系,即在家者和离家者的关系。鲁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流浪者”“游荡者”,对他来说,艾梅就是“人世天堂”的开启者、世界秩序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返乡人”的启悟者和领路人。这种关系恰可解释被神化的身体的第二个表征,即至高性。鲁笔下的艾梅是“空气、石头、水”的“主人”,“受纳着树叶以及长流之水的赞歌”,他的目光能够催生“古老的王国”。身体在被崇高化、被神化的过程中与生物学上的身体拉开距离,暗示视觉或触觉所及的身体下隐匿着更为深邃的意义——“伟大存在”。
除却在家者的身体,鲁的神化书写的另一主要对象是空间。他不仅以题目《天堂随笔》明示空间的重要性,还借用“天堂”“世界之园”“永恒之国”等宗教意象指称艾梅所展开的家园,尤其将宗教传统中两个完全对立的空间捏合,构成“人世天堂”这一新词。诗人是否暗示这两个空间具有某种潜在的统一性甚至可转化性?他借用宗教意象意在何为?鲁如此描述“天堂”的显现:
昨天,艾梅在收割。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由此生出一种安歇之感……(他打磨镰刀时手肘抬起,我看到那柔软的皮肤下隆起的肌肉在镰刀柄的阴影下略显苍白,这赤裸的手臂,这干净的手臂,一抚之下整个世界都会平息。)所有这些都告诉我,我不是在空想,这完美的、令人心碎的、因其永恒而至高无上的天真,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它在我面前,犹如某种不可及又不可拒的东西。它改变了世界,抹除了时间,催生了一种奇迹般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次要之美(la beauté seconde)不再是分裂性的产物,而是统一性的产物。哦,天堂,人世天堂,我其实到达了这样一种境地——只爱实存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其他事物的幻想都不过是由我们的不足所致。
由上述描写可以观察到,“人世天堂”的显现总是与在家者的作用有关。诗人以多个形容词强调的“天真”,正是“改变”“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天真”即是对本己本质和旧有秩序的持存,艾梅以其“完美”的“天真”展开“人世天堂”,以“完好无损”的人性召唤“完好无损的大地”。因此,复归的进程是双重的,人性和家园之本然当同时重现:“人变回成人。在撕裂的大地上,圣园(le Jardin)重现。”由此可以引出对于“人世”向“天堂”转变过程的一个关键认知,即这一过程不是从零开始的新建构,而是向着本源的回归。旧有的世界秩序并非不再存在,而是现代人类以其存在活动切断了与家园的关联,使后者失去可见性而看似不存在。因而鲁不仅是瑞士文学评论家阿尔贝·备甘(Albert Béguin)口中书写“在场的诗人”(poètes de la présence),更是揭示“缺失的在场的诗人”(poètes de la présence perdue)。“缺失的在场”并非“缺席”,而是一种既“在”又“不在”的存在悖论,一种悬浮或真空状态的存在。存在者处于空间中而不在关系场中,失去与“命运本己要素”的关联而导致家园隐匿。
诺瓦利斯,图片源自Yandex
作品多次强调“消失”或“失去”一词,暗示某种理想空间或秩序的原本存在:“古老的合唱在消失后又重生,围绕着这副躯体回荡不绝”普世的“合唱”本自存在,继而“消失”,后又复得,因此在家者艾梅的作用与其说是使世界焕新,不如说是将其还原:“你把一个个村庄、一条条路、一座座山归还于我。你把失去的世界归还于我。”由此可以发现人世向天堂转化的可能性根基:鲁的“天堂”潜伏于“人世”之中,天堂“弥散于我们的身与心之上”,通常处于隐而不发、混沌无形的状态,有待存在者以具体的生活实践与之重新建立联系。鲁的“人世天堂”观念有着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呼应他多次提及的诺瓦利斯的“散落人间的天堂”。因此,借用基督教修辞并非为了承其传统,而是意在剥离或悬置社会历史强加于语言的附加物,令“天堂”一词退归于其最本己的意义,以指涉某种未达性、隐匿性、神秘性。“人世天堂”的辩证统一体,弥合了基督教意象体系中处于分立状态的两个空间,暗示日常空间与超验空间的可重叠性、存在论意义上的家园的隐匿性以及人世向天堂的可转化性。
结 语
借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线索,我们得以用哲学工具对诗性语言进行解码,揭示鲁散文诗集的存在维度和诗性本质,听取荷尔德林在历史上游发出的“回家”呼唤和鲁在历史下游给出的“在家”回应。鲁不仅继承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回家”传统,认同荷尔德林所揭示的家园本质和诗人普遍具有的“流浪者”身份——“诗人是被抛出在外者”,“被抛入那个‘之间’”,同时也延续了荷尔德林的“回家”事业:鲁把诗歌从语言范畴扩展至存在范畴,让存在本身言说存在,借由“在家者”具体且总体的生命经验、实践智慧和内在生活,直指本真状态的存在。“在家者”艾梅作为“真正生活”的实践者,以其“充满劳绩”、归属大地的存在,还原初始生命秩序,关联万物本己,从而以“在家”这一存在方式促进家园的显化。这一书写更新了家与在家者的关系:存在者的“在家”成为家之所以为家的先决条件,在家者获得相对于家的先在性。因此,不同于荷尔德林笔下的存在者与家园间关系的断裂,鲁笔下的返乡人享有家园的间歇性在场,能够通过在家者的媒介作用与家园建立间接联系,暂时性地弥合断裂。与荷尔德林近乎绝望的等待不同,鲁以“在家”作为一种现代人类救赎方案,呼应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人的责任,即理解、保护存在,赋予存在以形式,促使此在从非本真状态向本真状态转化。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4年第3期“作品及作家研究”专栏,责任编辑杜新华。前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s://www.nssd.cn/)可免费下载全文。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萌 张文颐
排版:雨 璇 终审:文安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