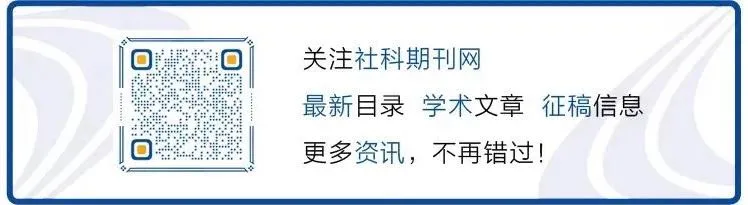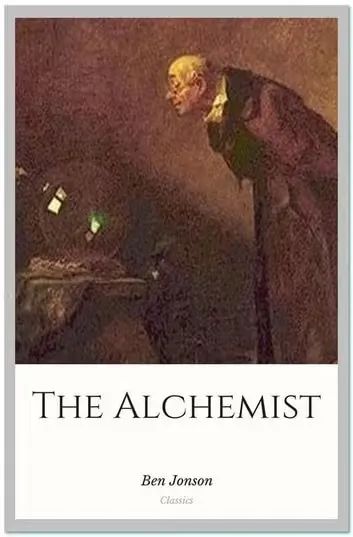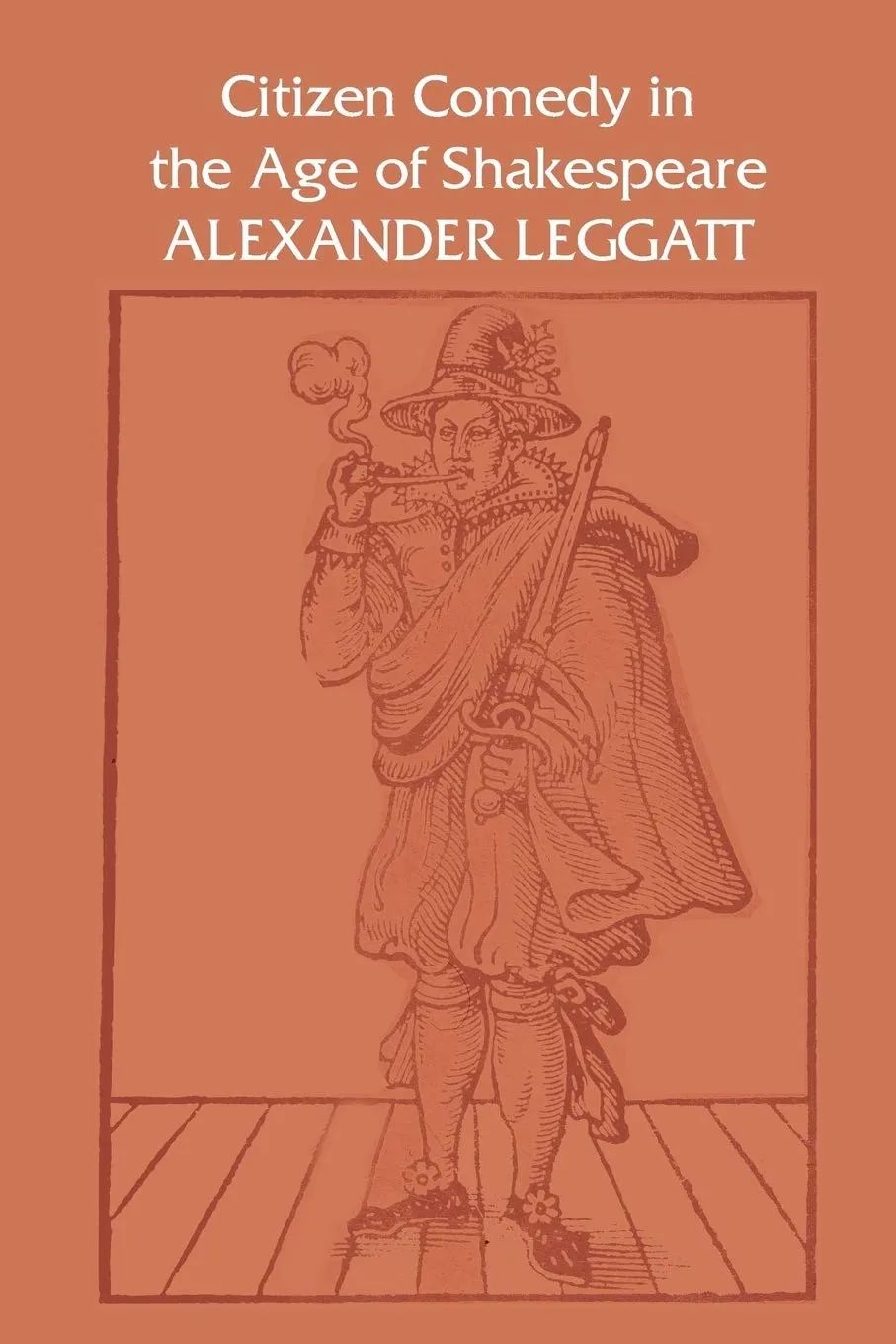文化研究丨金钱的流动与变形——《炼金术士》中的道德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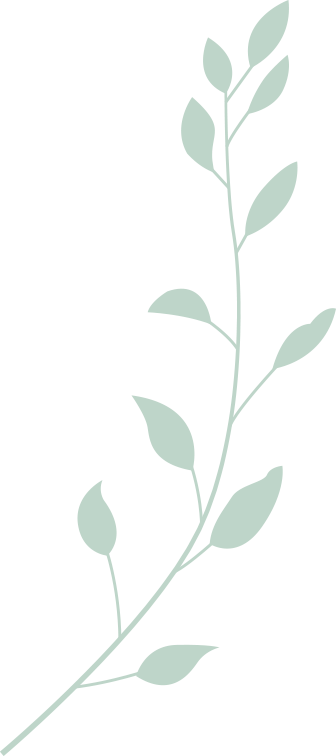
张文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现代英国戏剧。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莎士比亚的疯女人——论〈哈姆莱特〉中的奥菲丽雅与〈两贵亲〉中的狱吏女儿》(收入李伟民主编《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第四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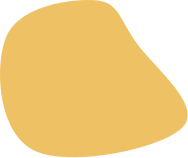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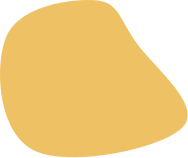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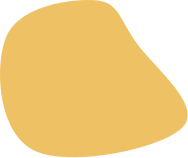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本·琼森的《炼金术士》是一部以17世纪初伦敦城市扩张和工商业发展为背景的城市喜剧,讲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二男一女凭借炼金术行骗的故事。金钱的流动与形变是贯穿全剧的重要线索,在伦敦这座“欲望都市”中,崇拜金钱、追逐名利的风气盛行,幻想不劳而获、点石成金的普通市民将炼金术作为获取金钱与权力的捷径,骗子则利用普通市民的焦虑与野心大肆敛财,然而他们的金钱梦最终都化为泡影。通过揭露炼金术骗局,《炼金术士》反映了伦敦人口聚集、城市扩张的新面貌,同时也揭示了新面貌之下更隐蔽、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与阶级矛盾。
关键词 本·琼森 《炼金术士》 城市喜剧 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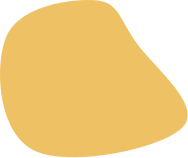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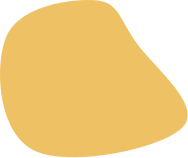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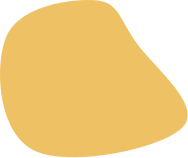
本·琼森(Ben Johnson,1572—1637)出生于英国伦敦,是一位与威廉·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在琼森生活的时代,英国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时期,中世纪封建社会体系正在瓦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要素逐渐成形。随着城市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伦敦吸引着各个阶层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寻求机遇,而人口的聚集又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在伦敦这座“欲望都市”中,崇拜金钱、追逐名利的风气盛行。早期现代的社会转型孕育了“城市喜剧”这类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现实讽刺作品,《炼金术士》便是其中颇为典型的一部。该剧的开场白体现了琼森对城市生活的兴趣:
我们的场景设在伦敦,
因为你会发现,
没有哪里能比伦敦更令人捧腹。
这里的风土孕育出最好的题材,
因为妓女,鸨母,乡绅,骗子,
以及许多其他人,
各有怪僻的性格;
这些如今被称为癖性的举止为舞台提供了样本。
本·琼森,图片源自Yandex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诱惑的扩张时代,伦敦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了获取金钱各显神通,《炼金术士》的故事便围绕一门号称“点石成金”的行当——炼金术——展开。在伦敦瘟疫爆发之际,黑修士街区的一位房屋主人拉夫维特(Lovewit)打算前往市郊躲避瘟疫,出发之前,他将房屋留给管家杰里米(Jeremy)看管。杰里米即剧中骗子法斯(Face)的原名,房屋主人离家后他改头换面,利用这间房屋收容炼金术士萨特尔(Subtle)和妓女桃儿(Dol),三人联手大肆吹嘘炼金术能将贱金属转化为贵金属,并结合占星术、算命、召唤精灵等其他骗术招徕社会各行各业的顾客,大肆敛财。在琼森笔下,无论是三人行骗团伙,还是律师助理达帕尔、烟草商德鲁格尔、清教牧师霍尔孙等登门拜访的“客户”,他们都展现了人性的贪婪与虚荣。《炼金术士》中最具代表性的角色是与《圣经》中贪财的财神(Mammon)同名的玛蒙爵士。他对所有人高喊:“发财吧!”这句话高度浓缩了早期现代伦敦社会对金钱的追逐和对世俗欲望的渴求,而这种时代精神在剧中具体表现为市民阶级迫切渴望点“石”成“金”,实现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在城市喜剧的作家们笔下,16与17世纪之交的伦敦可谓一座躁动不安的欲望都市。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研究者莱文认为,城市喜剧顺时而生,“迎合时代和日趋转向消费主义的大众”,“可能会警示商业活动的掠夺性危害,但同时也反映了城市不断增长的人口之下的经济新模式”。《炼金术士》的故事以瘟疫爆发为背景,反映了早期现代伦敦人口聚集、城市扩张的社会新面貌。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庄园制度的解体和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推动一大批佃农前往城市寻找工作,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与市场。自16世纪以来,英国城市化进展迅速,伦敦的聚集效应进一步加强,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的入迁。从1500年的约5万人至1600年的约20万人,伦敦人口翻了两番并且仍持续增长。伦敦城以“其适当的地理位置、强大的经济功能和优越的政治地位”成为英格兰无可替代的核心。
《炼金术士》,图片源自Yandex
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随着传统封建等级秩序的瓦解,此时的社会阶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城市工商业为早期现代英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市民阶层迅速崛起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力量,他们渴望将手中的金钱变形、置换为新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贵族的权威性。伴随城市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是社会观念的变迁,“在这个时代,财富的积累与经济实力的增强固然值得庆祝,然而大量人口在城市的聚集给传统道德价值与规范带来的危险同样显而易见”。在社会观念层面,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与转型不可避免地激发了阶级对立,带来道德失范、盘剥欺诈、失业贫困等乱象,导致诚信危机与商品拜物教的盛行。另一方面,城市扩张引发的城市病,如人口超负荷、环境污染、瘟疫大爆发等,又进一步激化了贫富差异、阶级对立等社会矛盾。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早期现代伦敦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自中世纪起,英国就时常遭受瘟疫的袭击,主要有鼠疫、霍乱、天花以及流感,最典型的当属鼠疫,由此引发的黑死病沉重打击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当时人们将瘟疫的流行视作上帝对人类的审判与惩罚,但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来看,密集的人口、横流的污水以及大批出没的老鼠为疾病的发生与传播创造了客观条件。伦敦“于1563年,1578至1579年,1582年,1592至1593年以及1603年数次爆发瘟疫,其中1563年与1603年的疫情最为严重,人口死亡率达四分之一”。瘟疫导致的人口死亡率呈现出明显的贫富差异,根据16世纪末一项以教区为单位统计的官方数据,伦敦最富有与最贫困的教区死亡率差异悬殊,瘟疫研究专家斯莱克认为原因在于“伦敦的富人们为了躲避感染,往往在疫情来临之际,或是爆发之前,逃离出城”。《炼金术士》中,在黑修士街区拥有房产的拉夫维特便是一位前往市郊躲避瘟疫的富人:
萨特尔
谁?有人打铃了。到窗口去看看,桃儿。老天啊,
别让主子这时来打扰咱们。
法 斯
哦,别怕他。只要一个礼拜死一个人,
他在伦敦外面就不敢回来。
琼森将戏剧场景设定在黑修士街区,是因为它在伦敦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自13世纪以来,黑修士街区便是英国国会、枢密院与中书法庭所在地,街区不受市政管辖,直接隶属于皇家。除此之外,“这片土地邻近河流,交通便利,还靠近圣保罗大教堂、律师学院等重要宗教、商业、政治场所”。在黑修士街区拥有房产意味着拉夫维特拥有非同寻常的权贵身份。伦敦瘟疫爆发后,政府为避免更多人感染出台了隔离政策,剧院等公共场所在此期间不得不关闭,富人如拉夫维特却具备前往市郊躲避瘟疫的财力,享有生命健康与人身自由的双重特权。相比之下,底层市民即便隔离家中,也存在较大的感染风险。瘟疫的爆发激化了贫富差异与阶级矛盾,对此,罗斯评论道,这部戏剧中的瘟疫在更大程度上象征着一种“抽象的感染”,剧中“人们绝对的自私自利是瘟疫所精准暴露出的一种道德疾病的症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瘟疫的威胁加剧了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对金钱与权力的焦虑,整个社会对金子的欲望催生了号称“点石成金”的炼金术的风靡。
全剧在萨特尔与法斯的争吵中开场。房屋主人拉夫维特离家后,法斯便将拉夫维特留下的房屋改头换面,与炼金术士萨特尔、妓女桃儿沆瀣一气、招摇撞骗。在这个行骗团体内部,萨特尔和法斯各怀鬼胎,互揭老底,萨特尔这样贬损法斯道:
那时你那么可怜,那么悲惨,
除了蜘蛛,或者更差劲的玩意儿,谁也不跟你打交道。
难道不是我把你从扫把、尘埃和浇水壶中提拔起来的吗?
难道不是我让你有了身份,
成了上等人?
难道不是我把你炼成了精华,
所花的力气可以炼两个点金石也不止?
《炼金术士》剧照
图片源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在《炼金术士》中,不光行骗团伙见钱眼开、唯利是图,向炼金术士寻求致富捷径的普通市民也个个财迷心窍、怀揣不劳而获的幻想。第一位“顾客”是律师助理达帕尔,他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且作为遗产继承人的他每年还有额外收入。然而达帕尔却不安于现状,在酒吧认识了法斯后,便来找炼金术士购买能帮他赌博赢钱的精灵。达帕尔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一个赢杯子和球与跑马赛的精灵”已不能满足他,他“想要一个在赌场赢大钱的精灵”,并且打算辞职专干赌博。他在法斯的引诱下求见桃儿扮演的富有而单身的“仙后殿下”,期待仙后恩赐金钱与美色。他面对仙后时以小搏大的心态与他在赌桌上的心态异曲同工。达帕尔家境优渥,已然位居社会的中上层,然而欲望膨胀的他却放弃安稳的前程,选择铤而走险,走上赌博、巫蛊与嫖娼的不归路,这对他熟谙法律、追求公正的职业身份构成了鲜明的讽刺。在义与利的分岔路口,达帕尔“顺应”时代洪流走上了盲目追逐金钱的不归路,是欲望都市中千千万万赌徒的一个缩影。
另一位渴望发财的年轻人德鲁格尔是一名烟草商人,他的需求体现了未加入同业公会的工商业个体户的焦虑与野心。在转型时期,城市同业公会“是行会发展的高级形式”,“通过国王颁发的皇家特许状,开始由从业人员自愿自觉的经济实体转变为合法的法人团体,确立了其有效的法律地位”,具有行业准入权、贸易搜查权、规范标准权、财务管理权等自治特权。德鲁格尔未成为杂货商同业公会的一员,因此他从事的烟草贸易并不受到法律法规与行业规定的认可。创业刚起步的他便试图从行业规则之外的邪术中探寻经营之道,委托炼金术士指点他门的朝向、货架的安放以及商标的设计。尽管德鲁格尔做生意资历尚浅,他的目标却不止于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同业公会会员。相反,他野心勃勃地企图“操纵自然”,请求炼金术士将他历书中“那些既不能做买卖也不能借钱的倒霉日子一笔勾掉”。德鲁格尔的焦虑与野心还体现在他对帕特里安夫人的觊觎上,尽管自知身份地位不入帕特里安夫人之眼,他仍然向萨特尔表明了意图占有隔壁这位年轻、富有寡妇的愿望。在转型期,市场秩序的不完善使投机倒把的工商业个体户有可乘之机,刺激了德鲁格尔之辈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野心。
向炼金术士求购点金石的不只是世俗的红男绿女,清教执事阿那尼阿斯和阿姆斯特丹的忧患牧师(Tribulation)也在“顾客”之列,他们虔诚的外表与贪婪的本质构成了鲜明的反讽。清教徒将《圣经》视作唯一权威,主张改革主教制度,这与安立甘教义中“君主是教会和世俗王国至尊首脑”的观点相对立,因而受到英国国王的反对。1604年初,在汉普顿宫会议上,清教徒宗教改革的请愿遭到继位不久的詹姆斯一世的拒绝,但这次失败并未能完全阻止17世纪的清教运动。此后,坚持理想的清教徒依然积极布道,面向社会大众开展净化心灵的道德改革运动,其中一部分激进分子遭到了较为严酷的宗教迫害与流放。奉行苦行僧生活的清教徒排斥包括戏剧在内的一切娱乐活动,他们的主张激起了御用剧作家琼森的不满。因此,在《炼金术士》中,琼森无情地揭露了清教徒的虚伪与贪婪。剧中的清教徒忧患牧师劝说阿那尼阿斯向“异教徒”萨特尔寻求“权宜之计”:“好兄弟,我们必须迁就所有可能成就神圣事业的手段。”这“不神圣”的手段即炼金术。
在欲望都市,即便是发展关乎精神信仰的宗教事业,也需要金钱作为支撑。忧患牧师的苏格兰长者教导他:“只有一种药——金子能让官员对我们的宗教较为仁慈”,而忧患牧师本人也十分认同这一观点,他告诉阿那尼阿斯,“我们需要赶紧去帮助被剥夺了执照的兄弟们,除非我们拥有点金石,否则办不成这事儿”。忧患牧师一方面将萨特尔视作道德败坏的渎神之人,另一方面又奉承拉拢萨特尔,希望用他的点金石点出金子以贿赂官员,清教牧师清高与世俗的反差滑稽可笑,颇具反讽意味。阿那尼阿斯的虚伪面目也同样具有喜剧效果,初登场时,他的道德标准比忧患牧师更苛刻,坚信“神圣的事业应该有神圣的路径”。然而,当萨特尔提出有办法将白镴伪造成荷兰银币时,阿那尼阿斯毫不犹豫地认可这种行为的合法性,并将其美化为仅仅是铸造外国货币。在欲望都市之中,即便是清教徒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见钱眼开、虚伪腐败之人,剧中这两位清教徒身份与性格的反差凸显了城市扩张时期社会贪婪拜金风气的盛行。




恶魔玛蒙,图片源自必应
玛蒙爵士剧照,图片源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这股追求世俗欲望的社会风气在玛蒙爵士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肥胖的玛蒙爵士与《圣经》中贪婪的财神同名,堪称恶魔玛蒙在人间的化身。玛蒙对金子和性的欲望最为强烈,他把一切愿望的实现都寄托在点金石的魔力之上:拥有点金石的人“能给予相信它的人荣誉、爱情、尊敬、寿数、安全、勇气——是的,还有胜利”。点金石还没到手,玛蒙便开始畅想日后奢侈淫荡的生活,他想要“买下德文郡和康沃尔所有矿藏”,“在三个月内将瘟疫从王国驱除”,如神仙帝王般“坐拥许多嫔妃佳丽”、“一晚可睡五十个女人”,用奇珍异宝制成的餐具享用奇异的美食,供养一群谄媚他的下人……在《炼金术士》的故事中,琼森将早期现代城市扩张的背景下欲望都市伦敦的兴盛与堕落、华美与丑恶一一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转型时期,社会的流动有力推动了金钱的流动,市民阶层崛起并且成为社会中争逐金钱的一股新势力。普通市民对金钱欲望的膨胀是炼金术得以盛行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在剧中,炼金术并没有如术士所宣称的那样帮助人们实现点石成金的变形,而是暗中促成了金钱在另一层面上的流动。
《炼金术士》揭露了以炼金术为中心的三人行骗团伙如何包装点金石的魔力、招徕顾客大肆行骗的过程。炼金术的概念与实验发源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古埃及,传说亚历山大的赫莫斯是炼金术的首创者,他所著的《炼金术文集》是这一学说最负盛名的文献。炼金术“具有特定的技术知识、神秘的语言、象征性的和谜一般的教义”,“点金石”是炼金术的产物,具有把贱金属转化成贵金属的性能。在中世纪,炼金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随着相关著作的出版,这门学说的研究于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鼎盛,得到皇室和权贵阶层的庇护与资助。然而,在人们对炼金术的追捧之下,冒充炼金术士牟利之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并未掌握神秘财富的钥匙,而是把炼金术当成非法敛财的工具。”琼森笔下的萨特尔便是这样一个自诩炼金术士的骗子,他凭借精妙的骗术引诱人们为所谓的“炼金术实验”不断投入资金,但这部分资金却始终没有如顾客们所期待的那般变形为贵金属,而是流入了萨特尔和他同伙的口袋中。
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图片源自必应
《炼金术士》中贯穿全剧的反讽是,炼金术屡屡失败、难以捉摸,真正点石成金、使萨特尔一伙凭空获利的,是故弄玄虚、玩弄人性的骗术。无论是许诺赌桌好运、创业成功还是占有美色,萨特尔一伙利用人性的贪婪,编织着“拥有点金石就拥有一切”的美梦,一步步将炼金术推向神坛。他们宣称点金石不仅能点铁成金,还是一种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万应灵药。在不断变换的面具之下,骗子们上演着为每位顾客量身定制的一出又一出好戏,时而欲擒故纵吊足对方的胃口,时而又蹦出一大串“专业术语”把人绕得云里雾里。尽管点金石的承诺从未兑现,他们精妙的骗术仍然引得登门拜访之人络绎不绝,纷纷为其投入资金。这个三人团伙屡屡得手的诀窍在于擅长制造美丽浮华的肥皂泡,将一切原本低贱卑微的东西变形为高贵华美之物。借由炼金术这一风行一时的骗局,琼森建构了早期现代伦敦的社会隐喻:在城市扩张的时代,人们相互欺诈、恶性竞争,急于点“石”成“金”,实现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变形”。
正如炼金术士萨特尔的名字Subtle(微妙的)所暗示的,萨特尔洞察世故、精通骗术,他和法斯都是狡猾老练的骗子。法斯在几位年轻的顾客面前自称将军,他也将一桩桩行骗的生意视为商战,运筹帷幄,随时准备与对手、甚至队友展开一番较量;而在社会资历更深厚的顾客面前,他又转变为炼金术士的助手,以抬高萨特尔的权威身份。他们与妓女桃儿相互配合,总能敏锐地把握顾客的脾性与需求,投人所好。桃儿在剧中始终象征着美色的诱惑,但针对不同的客人,她也相应地变化形象:为了使达帕尔臣服于小团体的权威,桃儿化装为富有的仙后,法斯又声称她是达帕尔的姑姑,要求达帕尔为她奉献出钱财;为了勾引玛蒙和瑟里,让他们为炼金术心甘情愿地投入更多,桃儿又成了被送来治疯病的贵族小姐。桃儿的姓氏卡门(Common)有普通、粗俗和共享之意,既透露了她作为底层平民的阶级身份,又暗含了她的职业属性,即身为妓女的她是一项可被共享的性资源。这一低贱的出身与她所扮演的高贵、神圣的角色构成了反讽。当玛蒙深信桃儿是贵族小姐,殷勤地与她攀谈时,法斯感慨道:“这就是现代社会,一个像桃儿·卡门的女人却成了一位伟大的贵妇人。”这里的“现代社会”确指英国新兴的工商业社会,更加开放、富有活力的市场带来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引入了不稳定因素,为骗子们的活动提供了温床。
三人团伙为每一位顾客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的虚幻世界,使受骗者沉醉于对金钱、美色、权力的欲望之中并为此付出代价。面对赌场赢钱的野心渐渐膨胀的律师助理达帕尔,萨特尔与法斯一唱一和,装作为难的样子,用欲擒故纵的计策引诱达帕尔增加佣金。面对年轻的烟草商德鲁格尔,萨特尔便信口开河,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德鲁格尔在他的指点下创业成功、加入行会、财富滚滚而来的景象,使德鲁格尔心服口服地献上金币。玛蒙是炼金术最忠诚的信徒,萨特尔抢先占领道德的制高点,以便日后失败时可以推卸责任:
如果你,我的孩子,偏离正道,
用它,如此伟大,如此普遍的事业,
仅为你一己的淫欲服务,
是的,诅咒肯定会随之降临,
摧毁你微妙而秘密的行径。
此外,面对故作清高的清教徒,萨特尔先和“助手”法斯以师徒问答的形式向阿那尼阿斯展示了炼金术的规章律令以增加他对炼金术的认同,但得知清教徒在看到点石成金之前不愿再多投入,萨特尔又变得急躁易怒,用假意毁灭炼金炉的极端方式来威胁阿那尼阿斯即刻付款、道歉。这间屋子的来客或虔诚,或轻慢,或单纯,或老到,但都在诡计多端的骗子们面前暴露了自身的弱点,贪婪使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炼金术的骗局中。即使是最初意欲揭穿炼金术骗局的“老顽固”瑟里,也在金钱与美色的诱惑下听从了法斯的安排,盲目相信法斯能帮助自己迎娶寡妇帕特里安夫人。
《炼金术士》中有两位女性角色,年轻富有的寡妇帕特里安夫人与身份低微的妓女桃儿·卡门,她们来自不同阶级,但都如同商品一般被男人们摆布、利用。相比于个性活泼、大胆索取的桃儿,帕特里安夫人的形象完全是被动、静态的,她任人摆布与占有,仿佛没有任何情欲与意志。法斯和萨特尔一边争夺她,一边将她作为诱饵勾起男顾客德鲁格尔和瑟里的欲望。她的哥哥也将她的改嫁视作一桩生意,希望通过她的婚姻实现自己的阶级跨越,因此发誓不允许妹妹与骑士阶层以下的人结婚。为了拉拢帕特里安夫人的哥哥——以跟人吵架取乐的咆哮男孩卡斯特勒,萨特尔又自诩决斗的专家,为卡斯特勒传授吵架的技巧,一步步接近帕特里安夫人。在取得卡斯特勒的信任后,萨特尔又透露出自己撮合年轻小姐和继承人的本事,法斯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将萨特尔包装成无所不知的博士,引诱卡斯特勒带妹妹共同掉入他们的圈套。在萨特尔和法斯的行骗连环计中,嫁妆丰厚的帕特里安夫人既是猎物,又是诱饵,成为骗子团伙与顾客们博弈的最大筹码。
萨特尔的炼金术实验终究是不可能成功的,骗子团伙所能做的只有不断拖延过程,诱骗顾客们投入更多定金。正当付了定金的顾客们急不可耐地向萨特尔索要炼金术的成果时,实验室爆炸的轰鸣终结了他们的幻想与期待。这场爆炸表面上看是一次意外,事实上更像是萨特尔为了掩盖自己炼不出点金石而故意安排的事故。为了应付顾客们的催促,萨特尔向正与玛蒙约会的桃儿递话让她发疯,顺势将实验室遇到的麻烦栽赃给出言不逊的玛蒙,将炼金失败归咎于神明对玛蒙的惩罚。对点金石的效力深信不疑的玛蒙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全然受骗,还额外追加了一百英镑作为补偿。对点金石的狂热与执着使玛蒙失去理智,深陷炼金术的圈套无法自拔。对于狂热崇拜金钱的人们来说,金钱已然发生了变形:它从稀有的货币上升为一种精神信仰。相比于精神支柱的坍塌,人们宁愿相信这只是一次偶然的实验失败,因而丝毫不动摇对炼金术的执念,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做发达的美梦。《炼金术士》中炼金的理论与实验不过是幌子和摆设,是小团体故弄玄虚的诈骗技巧,为炼金术赋予了点“石”成“金”的奇妙魔力。企图不劳而获的市民们将炼金术当作获取金钱与权力欲望的捷径,骗子们则利用人性的贪婪,借由点石成金的把戏实现自身的发财梦。通过这一颇具反讽意味的社会现象,琼森让我们认识到,尽管炼金的仪器、材料和人们的一切付出、期待都在爆炸中灰飞烟灭,人对金钱的欲望与野心却依然汹涌澎湃、生生不息。
在《炼金术士》的结尾,房屋主人的意外回归结束了萨特尔一伙用炼金术行骗的混乱场面。然而,看似“恶有恶报”的处置与秩序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公正的真正降临,金钱最终流向权贵阶层的结局反映了早期现代伦敦新的社会格局下更隐蔽、更深层次的阶级矛盾与社会冲突。
炼金的实验室爆炸后,三人行骗组继续周旋于一场场行骗生意之间。当瑟里上门追责时,法斯灵机一动,调动“愤怒的男孩”卡斯特勒出面,故意挑拨二人关系,将瑟里对自己的怒火引到这位热衷于吵架的卡斯特勒身上。他们将计就计应对愤怒的顾客,然而,外出躲避瘟疫的房屋主人拉夫维特突然回家打乱了小团体的计划。尽管法斯听闻房屋主人的归讯后急忙换回管家装扮,并且设法掩盖三人行骗的痕迹,但拉夫维特还是在邻居们的证实下揭穿了法斯在这间屋里干下的种种勾当。
在剧中,拉夫维特的邻居们始终对骗子们的猖獗行为起着一定的震慑与限制作用,暗中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在故事开头萨特尔与法斯发生激烈争执时,桃儿警告二人不要闹出动静惊扰到邻居们,以此促使他们和好。琼森将台上台下的时空巧妙地重叠,该剧1610年首演的地点黑修士剧场与剧中这间房屋皆坐落于黑修士街区。戏剧演出在当时被认为败坏道德,受到黑修士街区居民们的反对,认为“戏剧演出会吸引无业游民在此地胡作非为”。舞台上街坊们协助驱逐骗子们的剧情与剧场外居民们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相互呼应,戏内戏外颠覆与维护、冲突与制衡的重叠共同展现了早期现代伦敦社会各阶层不同声音的多元变奏。
真相败露后的法斯并未因此受到法律的制裁,处事老练的他即刻背弃了小团体的契约,霸占了三人共同牟取的赃款赃物,将其作为与房屋主人谈判的筹码。为了免除牢狱之灾,法斯不仅将小团体行骗所得全部上交房屋主人,还献上了寡妇帕特里安夫人和她的嫁妆。讽刺的是,拉夫维特一本正经地声称“我是一个认真的房屋主人,因此别掩盖任何东西”,话音未落,当法斯提出可以帮他找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寡妇作为补偿时,拉夫维特立刻欣然接受了这项交易:“得了,见见你的寡妇去吧。”在金钱与美色双重利益的诱惑下,道貌岸然的拉夫维特立刻放弃了正义与原则,与法斯结成一伙。他不再指责法斯将自己的房屋变成一座乌烟瘴气的淫窟,而是对他报以欣赏与感恩:
任何主人领受到仆人给他带来的幸福——
一个寡妇和一份巨额的财产,
而不由衷欣赏仆人的智慧,
给他以褒奖——
虽然他的名声有些瑕疵——
那他就是最忘恩负义的了。
收到贿赂后的拉夫维特改变了道德标准,站在与原先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发言。这一极富戏剧张力的前后反差不仅暴露了伪君子拉夫维特同样贪财好色、自欺欺人的本性,更有力地展现了金钱与美色的魔力能使人做出颠倒是非、完全利己的选择。
城市喜剧研究者莱格特认为,“拉夫维特的房屋如同一间布满镜子的大厅,并且反讽的是,他们[行骗团体]利用人性的贪婪对受骗者所施加的压力终究在这间屋的一面面镜子前反射回了自身”。法斯与萨特尔耗尽心机也未能在这场竞争中胜出,最终拉夫维特坐收渔利,独占了财富与美色,使得其他所有人的付出与期待都成为一场空。他们对点金石的渴求亦是如此,所有人的野心、美梦与算计都在实验室的爆炸中回归原点。不仅受骗者们的希望化为泡影,骗子们亦是如此。伴随炼金术的骗局一同破产的,还有小团体三人的协议。《炼金术士》开场萨特尔与法斯的斗嘴即暗示了他们因利而聚、各怀鬼胎。当房屋主人意外回归,他们无法对外行骗时,便都将欺骗的矛头指向了对方。察觉到法斯独占寡妇的意图,萨特尔与桃儿便决计转移所有不义之财而不与法斯分赃,而法斯则抢先一步将这笔钱财用于贿赂房屋主人。曾经流入骗子们口袋的金钱转而流向了拉夫维特:法斯回归管家杰米里的身份,一无所获,萨特尔和桃儿也在夜色中狼狈地离开了这间房屋。
莱格特著作《莎士比亚时代的城市喜剧》
图片源自必应
琼森将拉夫维特设定为唯一获利者的安排揭示了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权贵阶层盘剥欺占、巧取豪夺,在伦敦瘟疫肆行之时,他们具备在市郊躲避瘟疫的财力,相比隔离在家的底层市民更享有生命健康与人身自由的特权。当拉夫维特归家时,作为房屋主人的他重新宣告对房产的主权。管家法斯趁主人离家,利用这间房屋收容诈骗同伙,费尽心机编织环环相扣的骗局,然而他们从骗局中所得的一切都仿佛是利用房产所得的利息,在房屋主人回家后不得不悉数上交。对拉夫维特来说,私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使这些原本非法的所得合法化,他遣走了上门盘问的警察,顺理成章地占有财富与美色。小团体怀揣发财的愿景来到这间房屋,也借机收获了不少财富,然而机关算尽,到头来发现自己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拉夫维特免费的财产经理人,为富人进一步扩充财富提供便利,最终落入和受骗者们一样两手空空的境地。当台下观众为骗子们敛财未能得逞的结局感到愉悦、欢呼喝彩时,他们或许忽略了房屋主人作为权贵阶层如何盘剥压榨底层平民,利用社会分配规则操控金钱流向,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合法化的行径。琼森将这个看似“恶有恶报”的处置结局放置在社会转型期新市民阶层与旧权贵势力矛盾尖锐的背景之下,通过“公正”与“不公”的戏剧冲突呈现出更具现实批判力的反讽效果。
在《炼金术士》中,琼森一方面揭露了人们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中为了争夺经济利益与社会地位而不惜恶性竞争、相互欺诈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将剧中这群道德不完美的人物塑造成十恶不赦的角色,相反,在他们贪婪的人性中也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琼森没有交代骗子们行骗失败之后的生活,但在这个物欲横流、人人投机取巧的社会之中,潜在顾客并不会断绝,人们对金钱的渴望也不会被一次失败磨灭,因此这些骗子大有可能换个地方重操旧业。文艺复兴研究学者海恩斯认为,萨特尔、法斯和桃儿“代表新的社会可能性,他们来自伦敦社会新的空间、裂隙与能量,也为之奋斗”。他们依旧对金钱有强烈的欲望,保持着不受道德约束的激情与活力,这股能量让他们从失败中一次次的“重获新生”,在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欲望城市中卷土重来。
拉夫维特与行骗团体原本属于社会金字塔的两极,然而在伦敦爆发瘟疫的非常时期,二者机缘巧合地发生了位移与反转。拉夫维特前往市郊,即伦敦的边缘地带躲避瘟疫,临走前将他位于市中心黑修士街区的房屋交由管家代理,而管家趁此机会伙同炼金术士,二人在伪装的博士、将军身份之下借由炼金术的幌子从原本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成为顾客们眼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权威核心人物。以权贵阶层的这间房屋为落脚点,萨特尔一伙入侵旧世界等级制度的边界,短暂地将空间与权力的边缘与中心同时颠倒过来。尽管故事结尾这座房屋恢复了秩序,拉夫维特回归中心,骗子们也回归底层,但萨特尔一伙的越界行为依然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威胁。在剧中,琼森一方面书写了新阶层的颠覆能量及其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旧势力的回应与反制,在新旧两个世界的冲突与平衡中建构了早期现代伦敦复杂多样的社会风貌。正如吉本斯所言:“城市喜剧将城市生活的典型要素转化为重要模式,有意表达了讽刺批判,但同时也展现了更深层的冲突与改变。”
金钱的流动与形变是贯穿《炼金术士》的重要线索,它承载着剧中所有人追逐金钱的行动轨迹。金钱没有如炼金术士向他的顾客们所吹嘘的那样,在炼金术的魔法下无中生有——贱金属无法变形为贵金属,金钱仅仅是先流经行骗小团体之手,最后在社会分配的现行规则之下流向了权贵阶层。炼金术士和他的顾客们所代表的市民阶级之所以对金钱的流通环节投以格外炽热的目光,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期,不断扩张的城市规模创造了更开放的市场环境与前所未有的发财机遇,而占有金钱意味着跻身社会等级的新阶层。因此,金钱在这一时期不仅变形为社会新阶层的入场券,更是超越了物质属性,变形为拜物教的精神信仰。对于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英国而言,人们对金钱的渴望推动了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了土壤,金钱的意义也被拓宽,变形为社会变迁的符号。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4年第3期“文化研究”专栏,责任编辑龚璇。前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s://www.nssd.cn/)可免费下载全文。
责编:艾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雨璇 终审:文安
相关链接
往期回顾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 点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