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雪 “新诗人”、诗教与雅典观众的趣味:论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批评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与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图片来源:Yandex
然而,随着古典学界对欧里庇得斯悲剧的评价逐渐超越19世纪的框架,学者们也在重新认识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的关系。早在20世纪初,默里就注意到,“从阿里斯托芬的戏仿可知,他一定对欧里庇得斯的大量剧作谙熟于心,至少半心半意地着迷于他讽刺的对象”。而在这之后对阿里斯托芬的研究中,默里又详述了这种“半心半意”:欧里庇得斯的诗歌“萦绕在他的记忆与想象中,他带着一种魅惑与技巧戏仿它……但同时他又几乎确定无疑地反对它,就像他反对苏格拉底,反对一般而言的智者运动,反对那些关于女人的荒唐不经”。简言之,阿里斯托芬的“半心半意”也即在形式与内容上区别对待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迷恋欧里庇得斯的诗歌技艺,但是抵制其诗作所承载的伦理。不同于先前学者所认为的“双重攻击”,这种“文”与“道”的区隔成为接下来对两位诗人关系的一种常见的解释思路,20世纪中期以来,历代的研究者中都不乏类似角度的阐发。与此同时,又有学者着力于发掘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戏仿,并且发现这种戏仿并不是简单的化用,而是几乎系统性地定义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风格。故而晚近有学者试图进一步反转学术史的既成之论,尤为强调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着迷”,例如扎克伯格即认为,阿里斯托芬对这位悲剧诗人充满“尊重”甚至“偏爱”,因此在戏剧行文及主题上均“努力效仿”欧里庇得斯。只是如此一来,阿里斯托芬剧中对欧里庇得斯的负面呈现则显得愈加难于安置。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态度似乎注定是自相矛盾的悖论。
除了扎克伯格以外,当下还有不少研究聚焦于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的互文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针对互文风格的形式研究仍是“文”与“道”二分思路的延伸,强调二人行文风格的相似性实则回避了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矛盾态度之根本症结所在。重新审视阿里斯托芬剧中所表达的诗艺观,可以发现早期学者的观察其来有自,并且可以看出,对阿里斯托芬而言,诗歌的写作技艺与诗歌伦理载荷本是一体。换言之,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既然阿里斯托芬试图“以文载道”,又为何一定要仿效他眼中未能载道之“文”?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将阿里斯托芬所关切的伦理维度置于雅典的城邦生活与剧场语境的互动之中加以研讨,而这一点正是当下对两位诗人互文风格的研究所偏离的。本文通过解读阿里斯托夫笔下的“新诗人”,剖析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的诗学竞争,进而回观诗人生活时代雅典城邦的智识与文化议题,发现阿里斯托芬的写作方式仍然与他对欧里庇得斯的批评倾向息息相关: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态度具有内在的自洽性,其批评与效仿同出一辙,皆是出自戏剧与雅典剧场观众的互动,而这正是喜剧诗人与悲剧诗人共同参与并影响其时代文化实践的方式。阿里斯托芬因此得以将喜剧中寄寓的生活伦理传诸于世,然而,剧场中观众趣味构成的多元光谱指向了更具张力的戏剧意义的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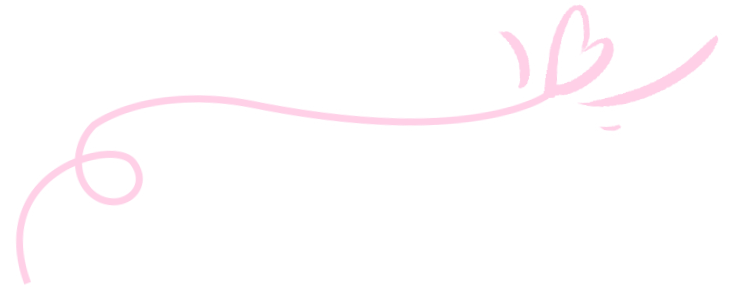

阿里斯托芬对于悲剧诗艺的关注始终处于某种“新”与“旧”的张力之中。在早年的喜剧《云》(Clouds)中,阿里斯托芬就使用了代际之争的情节来演绎欧里庇得斯悲剧与诗歌传统之间的差异,剧中斯瑞西阿德斯(Strepsiades)与其子斐狄庇得斯(Pheidippides)争执起来:
在这段话里,欧里庇得斯被称为“新诗人”,“新”既在字面意义上指欧里庇得斯属于年轻的一代,也在象征意义上指向现时、当下的思想状态与时代精神的更新。阿里斯托芬将欧里庇得斯与前辈诗人埃斯库罗斯之间的对立表现为“新”与“旧”之间的分裂,或者说,“当下”与“传统”之间的分裂。在剧中的父辈看来,欧里庇得斯的措辞精巧,不似前人古朴的行文,然而这种“精明的鬼东西”鼓励兄妹通奸、败坏人伦。
由此可见,对阿里斯托芬而言,诗歌的“文”与“道”原本密不可分。在后期的剧作《蛙》中,阿里斯托芬又令“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正面出场,再次演绎了二者所代表的“新”“旧”之争,并对诗教之义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该剧设计了两位诗人在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面前争夺冥府的诗人宝座的场景:
“技艺精湛”与“警世明德”概括了诗艺的意义:诗人通过精湛的写作技艺教育“城邦中的人”,使之在道德上成为“更好的人”。也就是说,诗人是人们的“教师”(Frogs:1055)。阿里斯托芬是最早明确提出诗歌创作应具有伦理教化意义的古希腊作家,但他并不是这一观念的发明者。毋宁说,他让这里的“欧里庇得斯”说出了诗人应有的一种“常识”。这种观念延续到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诗艺论中,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早期的文学批评家们。而剧中的“埃斯库罗斯”更将这一诗教的来源追溯到“古时”:“试看自古以来,那些高贵的诗人是多么有益啊!”(Frogs:1030-1031)“埃斯库罗斯”历数了古时的诗人们如何传授秘仪、禁忌、神示、医术、农事、战事等技艺,这些看起来是对诗歌的“粗暴的简单化解读或误读”,然而实则建构起了诗人从参与神圣事务到指导人的生活的“人类学”发展脉络。诗教的传承以对神圣的虔敬为根源,成为城邦中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伦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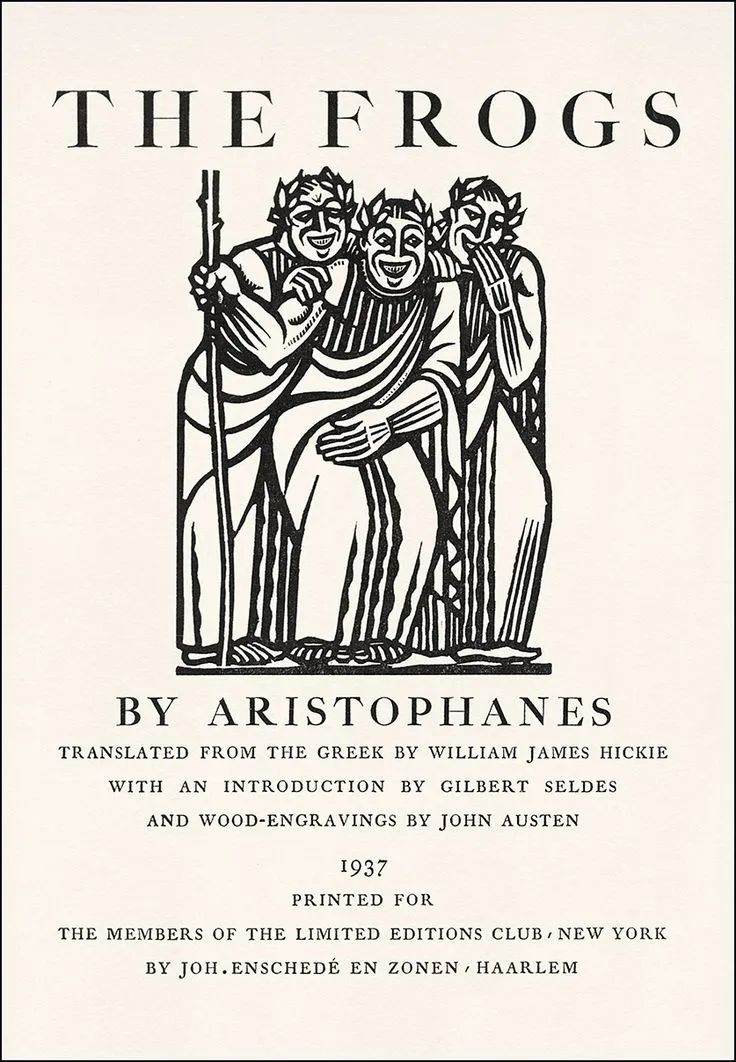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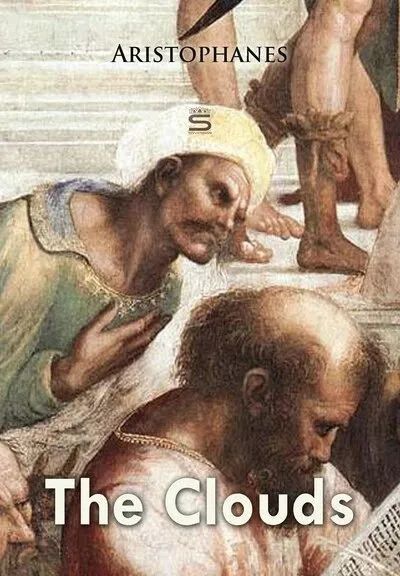
《蛙》(Frogs)与《云》(Clouds),图片来源:Yandex
“埃斯库罗斯”颂扬古时诗教,意谓自己的悲剧诗歌与之相承相继,而对面的“欧里庇得斯”与之背道而驰。与《云》中的父辈斯瑞西阿德斯类似,“埃斯库罗斯”也列举了“欧里庇得斯”所写的不伦情事,并且指控他让女人说出“活着等于不活着”这种诡辩之语;与之相对,自己则是用“伟大的词句”描写荷马式的半神的“英雄事迹”,传达“宏伟的观念”(Frogs:1043-1054,1059-1061,1079-1082)。这里“新”“旧”诗教的并置不仅意在说明前者使女人不再安分守己,而且折射出整个城邦生活的状态:“所以我们的城邦充满了弄文者和煽惑人心的猴子。”(Frogs:1083-1085)雅典新兴的智辩之术本来应用于城邦政治,不属于不能参与公共事务的女性,雅典政客用言辞煽惑人心的目标受众也不包括女性。然而智辩之风的影响却不限于公共政治,而是涉及城邦生活中的所有人。“埃斯库罗斯”这里的说法将悲剧中的女性诡辩与现实政治的乱象混为一谈,甚至有些倒果为因,实际上是暗指欧里庇得斯将智辩之术引入悲剧的“新诗教”加剧了整个城邦生活从上到下、从政治到日常各方面的价值危机。“活着等于不活着”大约出自欧里庇得斯的《波吕伊多斯》(Polyidus),现在仅余残篇,难以重建其戏剧语境,不过这些辞句在原剧中的意指显然要比喜剧中出离于语境的简单引用复杂。但是对阿里斯托芬而言,穷究原义并不是其批评的目的。在残篇之外,《蛙》中所列举的描写出轨女性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Frogs:1043)一剧完整存世,结合阿里斯托芬对剧中辩辞的指涉,我们可以更细致地观察其批评策略。
《希波吕托斯》中的辩辞“我的口发了誓,但我的心没有发誓” 正是阿里斯托芬最喜欢戏仿的欧里庇得斯诗句之一。该剧写的是淮德拉(Phaedra)恋上继子希波吕托斯的故事,这句隽语出自希波吕托斯和淮德拉乳母的对话:乳母向希波吕托斯透露了继母的爱慕,后者愤然之下欲说出实情,乳母提醒他曾立誓保持缄默。对此希波吕托斯答道:“我的口发了誓,但我的心没有发誓。”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誓言通常是由神来见证的,伪誓则有悖其虔敬信念。而剧中这句话表面上是以诡辩渎誓,实则写出了人物所处的两难困境。如果他要遵守神圣的誓约,就要违背人伦的要求,隐瞒继母的不轨。他不得不诉诸智者式的言辞之辩,以求解脱于道德之困。但是一时的辩才并未改变其持守,在后文中他两次重申不会违誓,并强调这是因为对神的“虔敬”。只是神圣的信条于人事无益,希波吕托斯因此见弃于父亲,受诅身亡。最后的降神(deus ex machina)揭示了事情的原委,而这一冷漠的降临以及迟到的“和解”无法挽回已然毁弃的人伦关系。希波吕托斯之外,剧中的女性角色淮德拉与乳母同样精于智辩,并且有意识地为不伦之事辩护,虽则淮德拉也因此而死。欧里庇得斯将智者式的言辞置于复杂的戏剧语境中,从而使属于人的道德判断不断面临严峻的挑战。
但无论戏剧语境如何复杂,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希波吕托斯的辞辩成了心口不一的自白。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斯托芬在《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与《蛙》中对“我的口发了誓,但我的心没有发誓”这句话的两次指涉都伴随着对欧里庇得斯剧中的另一句“我凭宙斯的住所——空气发誓”的戏谑(Frogs:100)。显然,对阿里斯托芬而言,这两句的效果是一致的。“空气”是智者运动中时兴的自然哲学概念,当时的自然哲人以物理现象取代了传统的诸神。欧里庇得斯剧中的讲辞常见对这类时兴概念的援引。在某种意义上,欧里庇得斯的写作确与传统的“虔敬”构成了距离。阿里斯托芬作为富有洞见的观察者,抓住了智辩之术进入悲剧之后对于传统诗教造成的某种根本性的改变。或者更准确地说,阿里斯托芬刻意忽略了欧里庇得斯戏剧构造的言与行的多重困境,而刻意突出了其新潮面向可能带来的问题。如《蛙》中的“埃斯库罗斯”对“古来”诗教的叙述所体现的,信神不仅意味着对神的虔敬,还意味着遵循这份虔敬所保证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智者式的“不虔敬”则动摇了以神圣为根基的整个伦理体系。除却修辞的指涉外,阿里斯托芬还在《云》中设想了一个苏格拉底的“思想所”来描摹新思潮之下雅典的智识生态:自然哲学以“科学”解释天象令诸神隐退,而智术就此登场以辞辩混淆了“有理”与“无理”,消解了人们习传的是非观(Clouds:94-99)。而同时阿里斯托芬又多次将欧里庇得斯描绘为苏格拉底的同道中人。欧里庇得斯与苏格拉底的形象重合揭示了前者的“新”诗教及其问题的根源所在——不同于传统诗教以虔敬为根基,“新诗”以人的智识和思辨取代了神圣的虔敬与依凭。
从阿里斯托芬的视角来看,这样一种对于人的伦理根基的变动是非常危险的:以虔敬为根基的传统诗教着眼于城邦生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新智识的“启蒙”打破了这一点,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就此而言,正是人的智识的不可靠造成了城邦生活的危机。《云》中的斐狄庇得斯从“思想所”学成归来,就运用他的思想开始宣扬儿子可以打父亲。欧里庇得斯悲剧与“思想所”的智识与智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斐狄庇得斯念完了欧里庇得斯有违人伦的诗句,与父亲争执不下,打起架来,还声称:“我懂得了这些新的(καινοῖς)技巧和说辞,能藐视既定的律法,真是太好了!”(Clouds:1399-1400)喜剧化的“精神弑父”意象直指“新”智识的破坏力。《蛙》则进一步具象化了欧里庇得斯的“新诗”之于传统伦理的作用,剧中的“欧里庇得斯”自述道:
正如《波吕伊多斯》等剧所体现的那样,在欧里庇得斯的笔下,精于智者式的修辞辩术、“有很多话说”的往往是“女人”“奴隶”这类在城邦公共生活中失语的、边缘的人物,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言说动摇着固有的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阿里斯托芬用“民主”一词概括了欧里庇得斯悲剧所隐含的这一激进倾向。欧里庇得斯剧场中的“民主”不是当时雅典人所理解的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反倒更像现代的某种“预言”。针对欧里庇得斯自称的“民主的方式”,剧中的狄俄尼索斯回应道,“你这方面的记录可不大好”(Frogs:953)。这句话大约是暗讽欧里庇得斯与雅典民主派的敌人有所往来。这个揶揄说明,在时人的眼中,将民主扩大到女性和奴隶是近乎僭主统治那般恶劣的事。剧中的“埃斯库罗斯”则将欧里庇得斯让“女人、主人、奴隶”都一样“说话”的做法称为“胡闹”:“你这样胡闹,不应该被判处死刑吗?”(Frogs:951)阿里斯托芬的用词之所以是“预言性”的,是因为他敏锐地抓住了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智识创新对传统生活秩序的挑战。不仅处于边缘的女人、奴隶,处于公共生活中心的公民群体一样会出现混乱。《云》中的斐狄庇得斯正是来自能够让后代接受较好的教育、有一定经济能力但并不富有的家庭,他本人可谓雅典年轻公民的典型代表。《蛙》中对此亦有所指,“你教人空谈、辩论,连体育馆都变得空荡荡。你教坏了我们的年轻人,还教船员们和他们的长官争辩”(Frogs:1069-1072)。习得了智辩之术的人们都不再安于原本的位置、履行应尽的义务,欧里庇得斯的“新诗”非但没有教导城邦中的人“成为更好的人”,反而使整个城邦生活都陷入动荡与不安之中。“精神弑父”的意象即是这种不安的终极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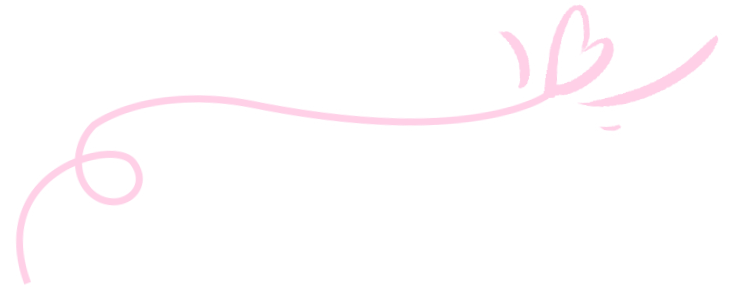

从上述线索来看,不难理解何以阿里斯托芬一度被视为欧里庇得斯的攻击者。但是回到雅典的剧场语境,即使所谓“攻击”也不应仅从字面上来理解:人们不会真的像“埃斯库罗斯”所说,认为欧里庇得斯因其诗艺就应该“被判处死刑”,除非是《地母节妇女》中那样诙谐的“审判”。该剧中“欧里庇得斯”因对女性的出格描写毁其清誉而被妇女们决议审判,只得变装出逃。如希斯所指出的,喜剧演出就像一场聚会,对于每位出席者而言氛围都应是宽松的。这提示我们,或许理解阿里斯托芬批评的关键正在于其剧场语境,而不能仅停留于对文本的索解:唯有透过剧场公众的视角,方可更近距离地看待喜剧的笑及其包裹的严肃内核。阿里斯托芬的写作首先面向与城邦生活攸关的公众关切,喜剧的讽刺只有作用于公众的一般印象,才能让人们抓住其中的笑点。阿里斯托芬选择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作为新思潮的代表来嘲讽,这本身就说明雅典社会对他们已形成某种认识。无论两人各自主张如何,对时人来说,他们都裹挟着智者运动带来的思辨。雅典公共生活的辞辩程序依赖于智者传授的修辞之术,然而人们又不能不感受到,新智识的“启蒙”对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了根本的冲击。这样的社会焦虑自然会投射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其悲剧批评也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诗”的教导会将城邦和它的年轻人引向何方?喜剧的戏谑回应的是观众的疑虑与不安。
阿里斯托芬给出的答案似乎不容乐观。而在进一步分析阿里斯托芬的立场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他在时人眼中的形象。据拜占庭学者阿里萨斯(Arethas)的辑录,老一辈的喜剧诗人克拉提努斯(Cratinus)表达过相关看法:
克拉提努斯这段话的具体戏剧语境已不可考。可以确定的是,剧中有一个对象被戏称为“欧里庇得里斯托芬”。显而易见,这是将两位诗人的名字合在了一起。喜剧的讽刺对象应该是观众熟悉的,这个名字的出现就说明,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给了时人亲近的观感和共同的辨识度。“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共同之处有两个方面,首先,他们都好弄言辞。ὑπολεπτολόγος由前缀ὑπο和λεπτολόγος合成,指的是一个人多少有几分(somewhat)能言善辩、言辞精妙(speaking subtly)。再者,他们都自诩睿智。γνωμιδιώκτης(γνωμοδιώκτης)由γνωμίδια(γνῶμαι)和διώκτης合成,διώκτης即“追逐者”,γνῶμαι本义“智慧、判断、观点”,又可引申为“格言、睿语、箴言”等。两个词都意味言辞与智识的精巧。因此也有学者将这句话的三个词翻译为“小小智识者(micro-intellectualist)、妙思搜寻者(hunter of subtle ideas)、欧里庇得里斯托芬”。
记载这一残篇的学者还提到,克拉提努斯写这一段是为了嘲笑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模仿。显然,现代学者在阿里斯托芬那里感受到的矛盾态度早已为古人所洞察。且不论阿里斯托芬本人意图如何,在其同时代人看来,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得斯的诗艺以言辞之术为载体,蕴含着新巧的智识和思辨。相较于“父辈诗人”克拉提努斯,阿里斯托芬也是“年轻一代的、新一代的诗人”。透过其同时代人的视角,阿里斯托芬表现出来的激进并不亚于欧里庇得斯。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女人、奴隶”同样“有很多话说”,这样的喜剧与欧里庇得斯的“民主式”悲剧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正是阿里斯托芬将女性及其问题性作为主要角色引入了喜剧,或者至少是他率先在剧中赋予女主角某种政治智慧,这本身就是一项不同寻常的诗艺创新。这其中欧里庇得斯的影响显而易见,也可以说,阿里斯托芬确然以某种方式追随着欧里庇得斯的道路。例如,同为涉及“性别战争”的剧作,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Medea)和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特》(Lysistrata)在言辞与论理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中,美狄亚为了向丈夫复仇决意杀子,她反复强调对于自身智识的省察,并以智者式的修辞论证了性别伦理加诸女性的“不幸”,包括德性的不对等,“我们不能对丈夫说不”,以及男女职责之别,“男人说我们在家过着没有危险的生活,他们却要提矛上阵”,而美狄亚表示自己宁愿上战场也不愿意生孩子。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中,吕西斯特拉特企图夺取雅典卫城,促成停战协议,她同样以面向公民演说的姿态控诉了性别角色的分界,女性被要求保持谦卑和沉默,“呆在家中操持家务”,以及男人说“战争是男人的事”,但结果是女人生的孩子被送上战场。由此可见,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中,城邦生活中的边缘人物也具备了智性的能力与言说的技巧,并且指向了对既有秩序的某种挑战。而在《鸟》(Birds)中,阿里斯托芬进一步“用言辞装上翅膀”,构想了一个传统伦理已全面瓦解的“云中鹁鸪国”(Νεφελοκοκκυγία)。剧中如此描述该国:
在这个高悬空中的乌托邦中,“奴隶”和“主人”不复有区别,也不再有对“野蛮人”的偏见,各种固有的分类和界限都不复存在。“长了翅膀”,人们就都不必拘泥于礼法,编藤条的小人物也可以成为国之柱石(see Birds:785-800)。鸟们“向天神宣战”(Birds:634),传统的虔敬信仰和习传律法所构建的差异与城邦秩序都消失了。如果说欧里庇得斯写作的是“新诗”,那么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同样有着“新诗”及其“败坏诗教”的特性。在这里,古代学者所记录的阿里斯托芬的“回应”就显得格外重要。据信,“阿里斯托芬在《控场的女人》(Women Seizing the Stage)中承认:我是使用了他的精致言辞,但我创作的思想(νοῦς)没他那么低俗”(Euripidea:T79)。

《鸟》(Birds),图片来源:Yandex
《控场的女人》现已佚失,这段话不一定就是针对克拉提努斯的评论做出的回应。不过至少在古代评注者眼中,阿里斯托芬剧中的这段话可以解释他与欧里庇得斯之间的相近与相异。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有着趋同的文风,但是阿里斯托芬自认比欧里庇得斯做得更好。“没他那么低俗”是一句喜剧化的戏语,隐含着两位诗人之间的较量。二人之间竞争的焦点是νοῦς,这个词比γνῶμαι更近于当时新智识运动的“智识”之所指。毕竟,自然哲人阿那克萨戈拉即以νοῦς(或译“理智”)取代诸神而著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阿里斯托芬”并未使用具有伦理意义的“美德”(ἀρετή)或“善”(ἀγαθός)等词语。在古代学者对残篇的引注之外,我们可以在阿里斯托芬的存世剧作中看到近似的竞争意向。在《云》中,阿里斯托芬拒绝将“最智慧的诗人”的名号给予欧里庇得斯:
“智慧的诗人”在《云》的戏剧语境中是一个引发冲突与纷争的“赞美”。阿里斯托芬通过斯瑞西阿德斯否认了欧里庇得斯应该拥有这项荣誉。而在这部剧的第一插曲(parabasis)中,阿里斯托芬已经将“智慧”的名号赋予了自己:“我应当得胜,被评为智慧的(σοφός)诗人。我认为你们都是聪明的观众,这是我最智慧的喜剧。”(Clouds:520-522)由此可见,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竞争的关键在于“智慧”。在智者(σοφιστής)运动的时代背景下,σοφός.亦不免如νοῦς一般指向新的言辞之术与智识潮流。阿里斯托芬意识到,观众亦已有此“智慧”,诗人的诗歌要交由观众运用这样的智识去选择、评判。阿里斯托芬显然对观众的接受有着高度的自觉。在《云》中,不仅斐狄庇得斯这样的年轻人,甚至斯瑞西阿德斯这样的父辈,都陷入了言辞辩驳的旋涡(see Clouds:1331-1344,1379-1439)。喜剧人物争论的伦理议题或许荒诞,但是双方“争论”一旦展开即表示人可以重新检视“既定的律法”。在一个智识“启蒙”的时代,神圣的根基首当其冲失去了其不言自明的超越性。属于人的思辨之智一旦觉醒,开始借助言辞进行分辨和批判,人的生活状态就再难如旧。无论雅典人对“不虔敬”有着怎样的警惕,在辞辩之风盛行的民主城邦中,新智识兴起之前的纯真状态已然失落。
当此之际,“新”与“旧”都被拖入同一场智识与智术的较量。如智者普罗塔戈拉所言,“每一件事上都有两种相反的论证”。“新”与“旧”成为同一场辩论中的正反方,而非两种相互隔绝、非此即彼的状态。《蛙》中的父辈诗人“埃斯库罗斯”与新诗人“欧里庇得斯”的同场辩驳本身就是时代语境的象喻,在“埃斯库罗斯”论证自己的方式更好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另一个精于言辞的“欧里庇得斯”,真正的埃斯库罗斯已经故去,只得由阿里斯托芬为之代言。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的插曲中声称自己是“最好的诗人”,会给观众“最好的教导”——也即“技艺精湛”与“警世明德”,但是对于在新的时代精神中写作的诗人而言,诗艺教诲不会再像古时那样被人们单纯地接受。古时的诗人依凭神赐灵感创作,古时的伦理因人对神圣的虔敬而传承,后者正是“埃斯库罗斯”追溯的诗歌教化作用于人的生活的“神圣历史”中隐伏的暗线。伴随着“启蒙”的到来,这条脉络被永久地改变了,接下来不同的生活方式都需要借助类似的言辞之智证明自身。因此我们看到,阿里斯托芬反复强调自己在“智识”上胜过欧里庇得斯。事实上,欧里庇得斯的剧中对于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有着与阿里斯托芬剧中类似的象喻。在《安提俄珀》(Antiope)描绘的兄弟之争中,主张按照传统的方式“去过战士的生活”“去作劳作之歌”的泽托斯(Zethus)与《蛙》中的“埃斯库罗斯”有相似之处,而泽托斯指责精于“智艺”的安菲昂(Amphion)“没有为正义之辩贡献一词”。欧里庇得斯同样意识到,当下关于城邦生活的伦理正义的“新”“旧”之争预设了以辞辩诉诸人的智识判断的路径。这是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共同参与的“当代”文化话语实践。也就是说,阿里斯托芬并非——至少并非只是——出于对欧里庇得斯之写作技艺的“迷恋”或“偏爱”而“努力效仿”欧里庇得斯,而是深刻地意识到了使用与之类似的表达方式的必要性:他们都要使用“新”的时代的语言,面对“新”的生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欧里庇得里斯托芬”一词表征了两位诗人的同质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表征着二者的竞争关系——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剧种,却在“启蒙”时代的文化实践舞台上同场竞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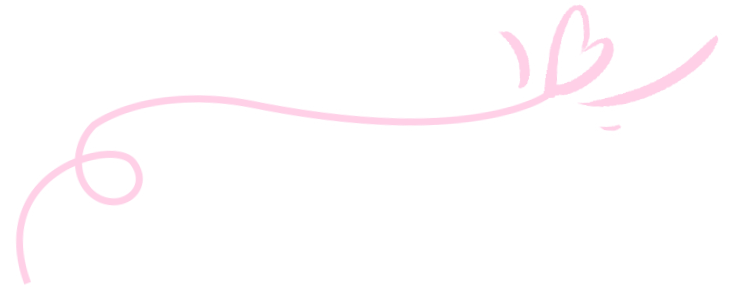

阿里斯托芬似乎试图表明,他在时代的舞台上比欧里庇得斯更加高明。至此我们可以再度评估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批评的意义。如前文所言,阿里斯托芬刻意忽略了欧里庇得斯戏剧设计中的一些复杂面向。不妨参看《阿卡奈人》中一段描写:剧中人执意向“欧里庇得斯”借取演出行头,后者拗不过只好说:“你把悲剧从我这里夺走了!”“你杀了我了!给你,我的剧作都消失了!”这可能是对现代文论中的“作者之死”最初的寓意表达。正如约瑟夫·普奇分析的,这一段形象地表现了作者权威与观众力量之间的紧张,“欧里庇得斯”看到了其剧作会遭遇的“减损”。或者说,“欧里庇得斯”意识到,他的剧作一旦上演,就要交于他人之手去生成意义。如阿里斯托芬所言,他的写作要赢得“智慧的观众”的赞赏:智识之诗竞争的核心就在于对观众的判断的争夺,以此方能表明自己更能为观众提供有益的指引。

狄奥尼索斯剧场(Theatre of Dionysus),图片来源:ancienttheatrearchive.com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里庇得斯”也促成了阿里斯托芬的写作之于观众的意义。阿里斯托芬的指涉是基于观众对欧里庇得斯及新智识的熟悉印象,反过来又会以其对“新诗”的潜在意向的批评阐释改造这种印象,进而引导观众的判断。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批评与其对新智识的演绎互为表里。虽然欧里庇得斯并未在《鸟》中出场,但是该剧中仍可见对他的喻指。《鸟》既在建造“言辞的城邦”,又以一种极端化的方式推演了“言辞的城邦”可能滑向的深渊。鸟国中人言道:“照你们的法律,打父亲是不行的。在我们这儿,一只鸟冲向他的父亲啄一下,叫一声,‘来呀,打我呀’,是可取的。”(Birds:757-759)父子相啄的意象与《云》对“新诗”造成的“精神弑父”的预见如出一辙。尽管阿里斯托芬在其指涉中简化了“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构造,但是在其喜剧写作中,阿里斯托芬又充分利用戏剧构造的复杂性,探索着“新”智识造成伦理失序的可能趋向。这或许是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更深层的相近,也是更深层的相异。他的《鸟》与《云》对儿子打父亲的极端化演绎是如此,其他剧作的设计也表现出这种探索。在《吕西斯特拉特》中,拥有智性的雅典妇女一边占领卫城,一边又无法拒绝男人的吸引,回归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而在另一部以反叛女性为主角的喜剧《公民大会妇女》(Ecclesiazusae)中,城邦陷入了反向的性剥削与纵欲的乱斗。要么回归传统,要么陷入动乱。恰如哈伯特注意到的,阿里斯托芬在剧中总是看似要实现某些愿望,但是“很快转入对智者式的乌托邦的讽刺攻击”。相较而言,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探索显得更为含混,《希波吕托斯》的降神中断了戏剧的议程,但并未解决人的智识与道德判断的困境,《美狄亚》的机械运用与之类似,美狄亚最后升空而去,效果近于“降神”,却留下了人间生活的伦理问题。这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向,一切有待于观众的思考。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欧里庇得斯的戏剧结构总是更具开放性。在某种意义上,阿里斯托芬的演绎也是对这种开放性的一种回应:在整个写作生涯对欧里庇得斯的不断指涉中,阿里斯托芬邀请观众体察,如果诗人的写作不虔敬,让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言说、非圣无法,继而随心所欲,会发生什么。在“言辞的翅膀”扇动下,诸社会群体不受控的激情汇聚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欲求”,一不留神就会从理智的觉醒走向暴力的释放。通过将欧里庇得斯转化为新智识的负面象征,阿里斯托芬演示了对智识城邦的二度建构与解构,进而引导观众在当下这场智识实验中的思考方向。
对观众而言,识别喜剧中的“欧里庇得斯”同时意味着辨识“新”智识的偏失倾向。通过将欧里庇得斯悲剧引入喜剧,阿里斯托芬写成了自己的“新诗”,并且反转了“新诗”之“败坏诗教”的特性;只是这种“反转”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在“启蒙”之后的语境中,面对观众的“智慧”,阿里斯托芬只能期待,雅典作为现实中的智识之邦,通过观看智识之诗滑向的深渊洞见自身的命运。根据中世纪抄本附注材料记载,阿里斯托芬因在《蛙》中给城邦的建议,被雅典人赠与由橄榄枝编成的、象征荣誉的桂冠。记载这一事件的学者认为所言建议指该剧插曲中提到的对因政治斗争失去公民权的雅典人的宽恕(see Frogs:686-705),但阿里斯托芬的建议并未限于此。最为瞩目的莫过于该剧在“诗人竞赛”的最后呼吁冥府的“埃斯库罗斯”“重返人世”:冥王送回“埃斯库罗斯”时说:“前去用善德之慧(γνώμαις ἀγαθαῖς)拯救我们的城邦,教育那些没有头脑的人们(ἀνοήτους)。”(Frogs:1501-1503)阿里斯托芬在这里一改“智慧的观众”的说法,表示在一个充满了新生之智的城邦中其实满是愚人。ἀνοήτους一词暗合着斐狄庇得斯式的盲目。前文提到,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城邦危机始终隐含着作为“新”诗教之根基的人的智识的不可靠,而斐狄庇得斯的形象作为雅典年轻公民的典型代表,暗示着追随欧里庇得斯的观众缺乏基本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的缺乏正是人的智识的不可靠性的集中反映。《蛙》这里的用词则将此一次点明。只是对于阿里斯托芬而言,其中根本的悖谬在于,其喜剧的接受也要依靠这种判断力。事实上,无论阿里斯托芬如何定位观众的“智慧”,他的创作至少预设了观众有能力识别并理解他对欧里庇得斯的戏仿与指涉及其批评要义。“观众都很聪明!”(Frogs:1118)对照“没有头脑的人们”,这些对观众“智慧”的表述或不无反讽之意。然而,阿里斯托芬作为高超的戏剧家,正是在对智识之诗的演绎中寻找到了他认为最为必要也最有利的与观众交流的方式,或者说向观众传达其道德“教化”的方式。面对前路的深渊,喜剧诗人引领城邦中人,或许尤其是斐狄庇得斯这样的年轻人,回望“埃斯库罗斯”所指向的“旧的道路”。
因此可以看到,用以指称“埃斯库罗斯”的“善德之慧”(γνώμαις ἀγαθαῖς)一词将伦理意义上的“善好”修饰词还于“睿智”(γνώμαις,γνῶμαι),从新知的睿语回归古老的智慧。父辈诗人的教诲系连着传统的城邦生活。在另一部为阿里斯托芬赢得头奖的剧作《骑士》(Knights)中,诗人同样呼唤“古时”的回归并赞美古时城邦中人们的美好名声和高尚品性。戏剧之神的冥府之旅实际上是一场怀旧之旅。相对于在“新”的迷途上的求索,“旧的道路”牵动绵延的乡愁——何处是归?在《和平》(Peace)中,人们回归了朴素的乡土生活:让我们把农具带回地里去,……让我们祈求诸神,给予希腊人财富,使我们收获丰足的大麦,贮满丰裕的美酒,还有无花果吃;女人给我们生孩子……阿里斯托芬在简单朴素的乡土生活中寄寓了他的现世依托。食物、美酒、(不那么出格的)性与生育——这些值得安享的要素不仅出现在《和平》中,而且出现在阿里斯托芬的大部分喜剧中。在反转云中建国的意象之后,喜剧的向往终究源自人间既有的生活。土地与女人的丰产总是成为现世生活的寄望——只要他们回到家中,没有发现妻子们如《吕西斯特拉特》与《公民大会妇女》中的女人们一样离开家宅。连绵延续的积极价值构成了根植于一方土地的美好旧时光的乡愁底色,而细观承载着乡愁的土地与女人,阿里斯托芬为“活着的雅典人”勾画的,或许只能是不再至高无上的传统,或如康斯坦所言,是相对于所谓“民主的方式”的“仁善的等级秩序”。无论如何,这幅“由宽广笔触勾勒的积极图景”势必对连年生活于战争、失落与不确定性中的雅典观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就此而言,故去诗人的“善德之慧”亦构成喜剧的智识之诗与观众互动的策略。“旧诗人”显然失去了神圣的超越性,因而也会遭到辩驳,例如被贬斥诗艺的粗糙(Clouds:1367),抑或被联想成“人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在战船上呼号划桨”的蒙昧过往(Frogs:1072-1073)。毕竟,阿里斯托芬知晓在一个智识“启蒙”的时代,所谓美好的古代也仍会受到新的判断力的不断审视。呼唤父辈诗人曾经的教诲,目的并非复刻其中的英雄事迹,而是随着对往昔的追念回归喜剧诗人勾勒的明确而仁善的城邦传统。阿里斯托芬试图向观众传达,真正有智之人会甄辨花样翻新的智识表演,拒绝像斐狄庇得斯们那样盲目追随欧里庇得斯,而是选择不同的方向。他所获得的荣誉或许表明,雅典观众领会了这一层教谕之意。也可以说,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指涉策略助其赢得了“智慧的观众”,使得相当一部分观众认同了他的演绎。雅典的戏剧竞赛结果虽非由观众直接投票产生,但评审的选择历来受到剧场中观众呼声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观众的主流意见。
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口传文化主导的社会,欧里庇得斯在喜剧剧场中的再现是悲剧首演及重演之外观众识记其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时代焦虑的背景下,阿里斯托芬的批评导向不可避免地会对人心之向背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欧里庇得斯在戏剧竞赛中负多胜少或也与此有关。在二十二次竞赛演出中,欧里庇得斯获得了五次头奖,远低于另一位前辈诗人索福克勒斯。虽然在现实中欧里庇得斯并未有机会与埃斯库罗斯对垒,但其竞赛生涯有近半个世纪与索福克勒斯相重合。而索福克勒斯年长欧里庇得斯许多,在精神气质上更接近于埃斯库罗斯:这位前辈正是以“虔敬”著称;在《蛙》的最后,也正是低调的索福克勒斯从埃斯库罗斯手中接过了冥府的宝座(Frogs:1515)。欧里庇得斯似乎确然在诗人的竞赛中落于下风。作为一位高度自觉的写作者,欧里庇得斯不可能不在意观众对自己的评价。根据中世纪抄本附注材料的记载,他曾经对《希波吕托斯》一剧进行修改,据说他改掉了剧中“不得体与受指责之处”(Euripidea:T29),才在第二次参赛时获得头奖。即便如此,这部剧仍然使他身陷争讼。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欧里庇得斯在一场交换财产案(antidosis)中与一个叫许癸埃农(Hygiaenon)的人对质,许癸埃农正是以该剧中的“我的口发了誓,但我的心没有发誓”为由,指责欧里庇得斯不虔敬。无论此案有多少真实性,我们可以看到它与阿里斯托芬剧中的指涉相重合。或许正是阿里斯托芬的戏谑与重塑强化了人们对欧里庇得斯诗句的负面解读,因此面对民众法庭会有人以此为借口攻击他的名誉和人品。又或许已经有一些观众将欧里庇得斯的写作视为真正的冒犯,许癸埃农作为其中之一利用了这种情况,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则为之推波助澜。总之,根据现有的史料,剧场与观众的交互作用是有可能形成某些公共意见的。
在阿里斯托芬看来,诗艺的目的终究在于指引城邦中的人遵循一方土地的习传伦理。而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中,习传的秩序失其所依,相形之下,索福克勒斯是更“安全”的竞赛头奖选项。《美狄亚》就输给了索福克勒斯与另一位籍籍无名的作者(Euripidea:T28)。观众对这部以女性的智识与复仇为主题的剧作做何反响?虽然我们无从确知,不过末等的奖项还是可以透露出观剧过程的挑战性。正因为美狄亚是女性,且属于“野蛮人”,其智性能力与智者式的言说以及杀子复仇的举动才更具破坏性,该剧所引发的反响与雅典观众的自我定位更加息息相关。就欧里庇得斯获奖情况而言,或许确如阿里斯托芬所望,大部分观众不至于如此“没有头脑”以致误入“新诗”导向的歧途。
但是阿里斯托芬写作的指向与观众的“智慧”之间仍然有着明显的张力。在评奖环节之外,戏剧竞赛的另一个程序也值得注意,即诗人向执政官提出演出资格的申请。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在创作生涯中获得演出资格的频率基本相同,平均约两年一次,并且可能从未有申请被拒。执政官不可能不考虑剧场中的民意,持续近半个世纪的选择只能是出于观众的意愿。显然,为喜剧诗人赋予桂冠的雅典观众并未抗拒欧里庇得斯悲剧的吸引力。而且,在《蛙》上演两个月之后,并非埃斯库罗斯,而是欧里庇得斯“重返人间”——后者的遗作在大酒神节上演,并获得头奖。

酒神节,图片来源:Yandex
此可见,观众的意见倾向本身就处于波动之中。这提示我们应注意到剧场中观众的构成及其趣味的多样。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尤其是晚期,雅典观众的组成很可能是非常丰富的。在狄俄尼索斯剧场以及山坡上没有座位的地方,除了坐着有一定地位的成年男性公民外,还聚集着大量的穷人、客籍民、外邦人,甚至奴隶和女性。他们在城邦人口中属于“边缘”人群,但在数量和比例上相当可观,各种人群共同构成了剧场中的“大众”。考虑到多样的观众构成,雅典剧场中的“民主”很可能异于公民大会,并非成年男性公民说了算,而更接近“女人、奴隶都说话”的“民主的方式”。而在《蛙》的冥府之旅中,阿里斯托芬更借助漫画式的手法直接表现了欧里庇得斯的剧场观众,“弑父者”赫然列于其中:“欧里庇得斯来到这里,把他的艺术表演给强盗,窃贼,弑父者(πατραλοίαισι),乞丐——哈得斯这些人可多了去了。他们一听到他的辩论和对驳,那些聪明话和巧计策,简直都发疯了,立刻把他当最智慧的人。”(Frogs:771-7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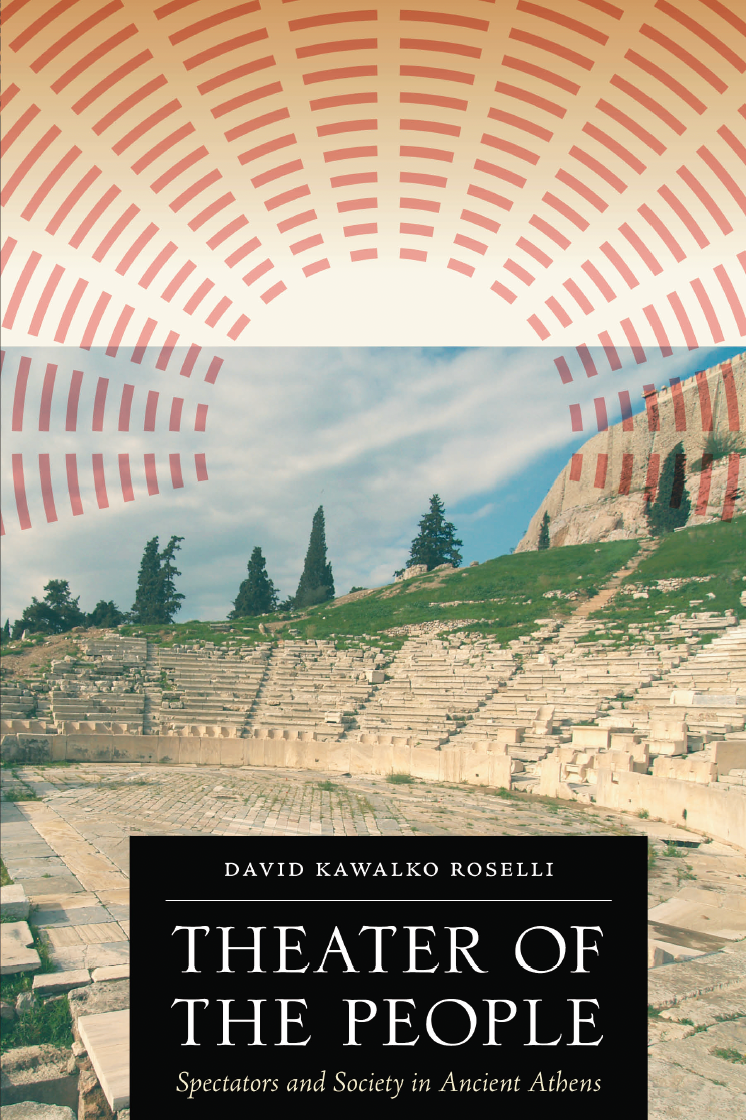
David K. Rosell, Theater of the People: Spectators and Society in Ancient Athens,图片来源:Jstor
这段描述有一定的攻击性,但它又反映了这样一个现象:欧里庇得斯悲剧所吸引的观众是多样化的。“强盗、窃贼、乞丐”皆指向对既有律法与城邦生活产生威胁的一些人,欧里庇得斯悲剧中的言辞巧智尤为他们所喜。如罗森所言,这显然是根据欧里庇得斯的某些剧情开的玩笑,但是它也暗示了诗人作品的接受最初依赖一些基于共同的价值而对其投入热情的“粉丝”。阿里斯托芬的笔触直指欧里庇得斯的智性修辞造成的效果:剧中的“聪明话”引得一些不法之徒“简直都发疯了”(Frogs:776)。然而,阿里斯托芬笔下的“欧里庇得斯”的另一段话对于其“粉丝”的形构及剧场反应的描绘透露出与以上不太一样的线索:“我展现日常生活,人们所看所知的事情。这样我就可以被审视。因为他们知道。所以,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也可以批判我。我从不虚张声势,不取走他们的判断力。”(Frogs:959-962)
这段文字更新了戏剧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表述。阿里斯托芬这段话讽刺的中心仍是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民主的方式”,并且他注意到了欧里庇得斯在面向普通人的生活的层面上改造了悲剧。只是“欧里庇得斯”的这段“自述”的视角却从诗人“教诲”观众转为观众“审视”诗人。这一视角的转变透露出欧里庇得斯悲剧对观众的“赋权”(empowerment)。阿里斯托芬确然洞察了欧里庇得斯的剧场策略,并且意识到自身与后者对观众“智慧”之定位的微妙连结与差异。欧里庇得斯同样知晓观众的“智慧”,不同于阿里斯托芬所暗指的“没有头脑的人们”,欧里庇得斯的剧场预设了观众更为积极的能动性——观众以自己的认知、理解来“判断”它。这样来看,欧里庇得斯对许癸埃农的回应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据信诗人答道,不应把酒神节竞赛的裁判带到法庭上来,他已经在那里对他的作品做出了辩护。这似乎是在说,对脱离了戏剧语境的单句的指摘是不对的。但是也可以理解为,相较于单一的民众法庭,欧里庇得斯更加寄希望于剧场观众的判断。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之所以有开放性的设计,是因为多样化的观众群体本身便具有开放性。无论是像阿里斯托芬这样有名的人物,还是无名的观众,都会对剧作的意义和价值做出自己的理解。就欧里庇得斯的剧场而言,所谓观众的“判断力”,意指观众能动地参与到戏剧意义的生成过程之中。或许可以设想在不同的演出场次,不同观众群体发出的声音有何等的不同,以及场面会是何等的激烈。发出不同声音的不(仅)是“人群”,而是“人”——每一个人对每场演出都有自己的评判。不妨再次回到前面的问题,《美狄亚》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会对此剧有何反响?她们或许会像阿里斯托芬笔下的雅典妇女一样认为欧里庇得斯诋毁了她们的“清誉”,指责她们“不虔敬”,又或许,更多的声音已经遗失在是年春季的卫城山下,我们只能通过隐约而曲折的印迹来寻觅。
雅典观众是如何表达各自声音的?女性观众是否更倾向于沉默?我们无法确知。但可以说,戏剧节的评奖是多重的观众反应角力与协商的结果。观众对戏剧中伦理问题的参与当构成多元的光谱,而非单一化或两极化。对于当时的雅典观众而言,对戏剧演出的不同评判和反馈本身也是城邦伦理的协商过程,而欧里庇得斯富于实验性的悲剧写作尤有助于这一过程的推进。开放的戏剧结构不仅预设了观众的判断力,也在观众对戏剧意义持续的能动参与中进一步培养他们的判断力。欧里庇得斯频繁获选的事实表明,雅典的观众整体上乐于在剧场中看到他的剧上演,欣赏欧里庇得斯的人未必像阿里斯托芬所描绘的那么“边缘”。或许,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存在着更隐秘的愿景。欧里庇得斯剧中的辩论和讲辞,“聪明话和巧计策”对应着剧场中的众声喧哗。在与“主流”“传统”的紧张关系中,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在“大众”中间流行。
并且这种“流行”在剧场中历久而弥新:在接下来的许多个世纪里,埃斯库罗斯淡出了观众的视野,欧里庇得斯占据了雅典以及全希腊的戏剧舞台。欧里庇得斯剧中的新意所向如何,也有待于每一个时代的观众索解。通过对“欧里庇得斯”的批评,阿里斯托芬为观众演绎了新的智识方向可能导向的歧途,在正与反或新与旧的两种论证的紧张关系中,阿里斯托芬通过演绎牵引着对故国的怀想以及对根植于一方土地的传统生活的乡愁。在历史的维度上,诗人们都有各自的“胜利”。欧里庇得斯剧场中的伦理意向仍然在对多样的观众开放——不仅包括当时的观众,也包括今天的我们、未来的观众。阿里斯托芬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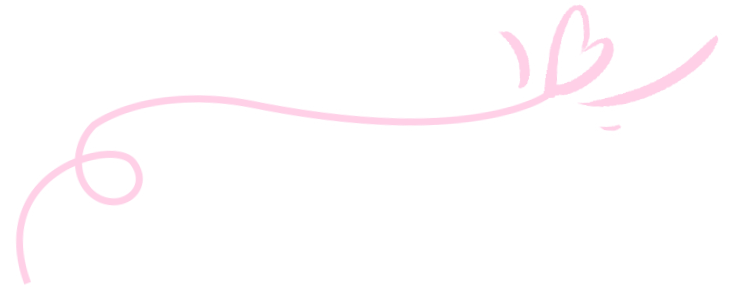

对阿里斯托芬的批评的重估并非20世纪以来才出现的。12世纪,拜占庭学者泽策斯(John Tzetzes)在对《蛙》所做的评注中就提到:“古注者实在愚昧无知,你会让自己相信(阿里斯托芬)这种人的胡言乱语吗?……此人(欧里庇得斯)不仅不应受责难,而且值得赞美,因为他的晓畅,因为每一部剧中非常精湛的叙事……”这段话所说的“古注”提示了一个古代批评的传统:如同19世纪的现代学者一样,将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攻击”援引为对这位悲剧诗人进行消极评价的佐证,共同造成了以谴责说为主的学术话语。而至少早在近千年以前,泽策斯已经感觉到了驳斥这一做法的必要。
克拉提努斯对“欧里庇得里斯托芬”的戏谑也可以被视为对阿里斯托芬悲剧批评的一种评估。透过其同时代人的眼光,二者原本如此相似,阿里斯托芬指责欧里庇得斯以新智识改造诗艺、背离传统诗教,但这一特性同样见于他自己的喜剧写作。克拉提努斯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剧场语境中做出相关的观察。在经过了许多个世纪的剧场再现之后,欧里庇得斯的演出记录消失于中世纪,然而拜占庭的古典教育中仍有着戏剧演诵的传统。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泽策斯会说,“如果在你面前展示欧里庇得斯的悲歌,我一定能让你潸然泪下”。重新评估欧里庇得斯以及阿里斯托芬的批评,似乎总是伴随着对于文本之外的表演维度的理解。
无论如何,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学者丢失了这一维度。早期学者或许过于依赖于文本的单一线索。一个巧合(更可能并非巧合)是,施莱格尔式的学术话语正是在欧里庇得斯的影响重现于现代舞台之后开始瓦解。至少默里参与了《美狄亚》的重演,并见证了该剧如何成为当时妇女参政权运动中的常演剧目。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默里对于欧里庇得斯与阿里斯托芬的重新认识引领了新的学术话语的形成。阿里斯托芬批评欧里庇得斯时的自相矛盾被重新提起,并被划分为亲其“文”而远其“道”这两个方面。但是,这样的解释思路并没有充分面对早期学者从阿里斯托芬那里阐发出的“以文载道”的诗艺观,反而留下了新的问题,即何以阿里斯托芬一定要亲近在他看来败坏城邦伦理的新诗艺。
晚近以来,对于古希腊戏剧的剧场研究已然成为显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出于对表演维度的关注,学者们聚焦于阿里斯托芬如何痴迷于欧里庇得斯并努力效法他以形成自己的风格或“品牌”,导致相关研究越来越趋向文风互涉的语言游戏,更加偏离了剧作所承载的城邦生活及其伦理问题的严峻性。欧里庇得斯研究用了百余年才走出19世纪,也没有人想再回到19世纪,或用上文“古注”的视角看待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面对曾经遗留的问题。此外,借助剧场性研究的视野,我们可以获得更有利的分析工具来重审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写作。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指涉正是其剧场策略的一部分,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分析戏剧的意义如何在与观众的互动中生成。具体而言,戏剧作为剧场中面向公众的演出如何回归其应有之义——在表演与观看中实现其意义,从而深度参与其时代的社会文化实践。阿里斯托芬与欧里庇得斯的剧场生涯都处于雅典新智识的风潮之中,观众同样如此。二人都对这一现状有着高度的自觉。在阿里斯托芬看来,以新的智识之诗来争夺观众的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实现诗歌教化的必要方式:通过对“新诗”的再演绎,将欧里庇得斯转化为新智识偏失意向的象征,从而引导观众回望城邦生活确定的传统。相较而言,欧里庇得斯的智识演绎则以更具开放性的戏剧设计唤起观众更为积极的能动性,牵动广泛的人群中更为复杂而隐秘的愿景。这或许也是欧里庇得斯在剧场持续流行的因原,并且也促成了阿里斯托芬剧场生命的某些延续。从雅典到希腊,从古至今,在面向观众的文化意义上,每一次演出的结束都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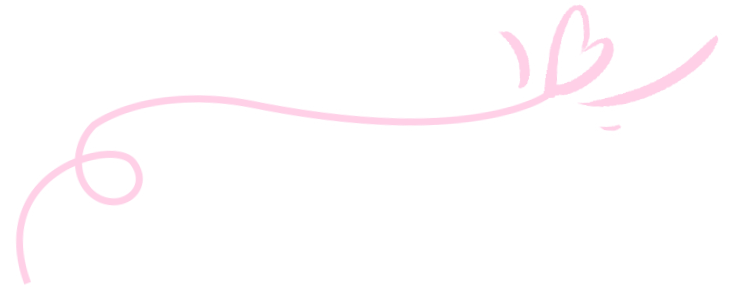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5年第1期“作品与作家研究”专栏,责任编辑杜新华。前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s://www.nssd.cn/)可免费下载全文。
责编:王纪睿 校对:郭鸿
排版:慧敏 终审: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