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凯|共时历史主义与历时历史主义:格林布拉特和菲尔斯基的对话

陈怀凯,博士,山东大学翻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近期发表的论文有《从〈瓦尔特·罗利爵士〉到〈文艺复兴自我塑形〉: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形观》(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2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忧郁书写”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菲尔斯基的后批判均关注艺术作品对读者的吸引力来源。格林布拉特将文学作品和其所属的历史时期捆绑在一起,通过解读文学作品来重构历史;菲尔斯基则将文学作品与所属历史时期“脱钩”,考察作品如何与当下环境发生碰撞并生成新的价值和新的意义。本文借助美国学者宋惠慈对共时历史主义与历时历史主义的区分,尝试揭示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与菲尔斯基后批判之间的理路分野,进而发现二者隐含的方法论层面的交集,探索让二者展开对话的可能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 后批判 共时历史主义 历时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 菲尔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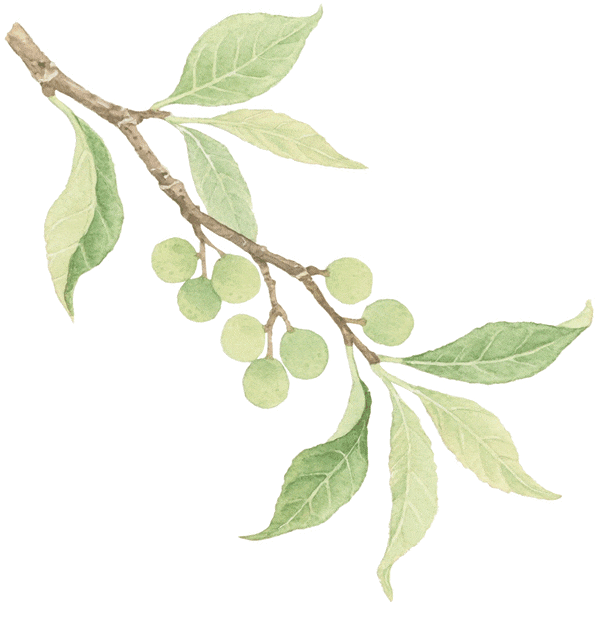
自2008年以来,美国学者芮塔·菲尔斯基(1956—)在《文学之用》(2008)、《批判的限度》(2015)和《入迷——艺术与依附》(2020)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过去几十年来英美文学研究领域中根深蒂固的“批判”模式进行梳理和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后批判”这一概念。“后批判”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文学批评的思路和空间,但也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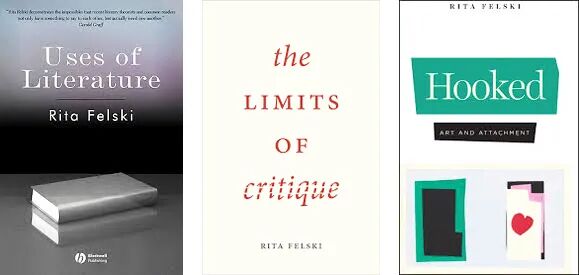
《文学之用》、《批评的限度》与《入迷——艺术与依附》封面图,图片来源:Bing
正如艾略特是在全面否定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非个人化”理论一样,菲尔斯基在探索后批判的过程中也是把相当一部分笔墨放在了对批判模式的质疑上,而她质疑的对象之一就是史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的新历史主义。在《批判的限度》一书中,菲尔斯基指责那些习惯了批判模式的批评者不但“以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梳理历史,试图发现不被人注意的联系和隐藏的原因”,而且往往认为“单个文本就像是庞大的社会整体的缩影,如果阅读得当,它们将揭示出这个整体的隐蔽真相”。菲尔斯基虽然没有点明批判对象是谁,但明眼人看得出此处暗指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所谓“以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梳理历史”,就是指一味搜捡并解读那些冷僻的历史材料,从而在文本解读中得出出人意料的结论,而格林布拉特最擅长的就是抓住历史的幽深和冷僻之处大做文章。所谓“将单个文本视作庞大的社会整体的缩影”,是指批评家通过对不起眼的文本进行“厚描”,借助“以部分代整体”的手法“触摸”整个社会的文化状况,而格林布拉特惯于关注诸如犯罪记录、医疗病例和趣闻轶事之类平常而琐碎的细节,以一种“一沙一世界”的方式来以小见大,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解读。可见,菲尔斯基是在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标志性操作手法——“从微不足道的碎片中召唤出复杂的生活世界”进行影射。
那么,菲尔斯基为何选取新历史主义作为靶子?应如何看待二者的这种对立?美国学者宋惠慈对“共时历史主义/历时历史主义”的区分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解析思路。按照宋惠慈的定义,所谓“共时历史主义”,是指“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放置到这一时期的诸多历史事件之中,以此解读该文本的意义”;所谓历时历史主义,则是指“将文本视为时空旅行中的客体”,考察文本意义随着时间推移或保持不变或发生转化的动态机制。以此划分标准来看,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的特定横截面上的文艺作品和其他类型的“文本”并置在一起进行考察,是一种典型的共时历史主义;菲尔斯基的后批判则将过去的文艺作品(相对于读者/听者而言,作品在时间上一律属于过去)置于由“行动者网络”构成的新环境之中,考察过去的作品和当下的新环境之间产生“依附”的形式和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历时历史主义。本文尝试结合后批判和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案例,对二者学理的分野加以论证和阐述。但需要指明的是,共时历史主义和历时历史主义并没有高下之分,后者的兴起也不意味着进步取代落后;文艺研究既需要共时地考察同一历史时期文艺作品和各种非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考察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发生历时变化的原因、路径和机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对比新历史主义和后批判的基础上,本文发现两种批评模式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从而力图探讨二者对话的基础和可能性。

菲尔斯基与宋惠慈,图片来源: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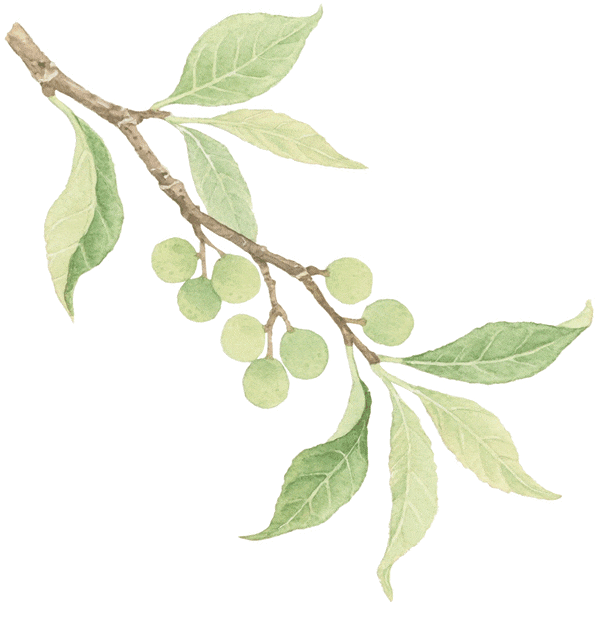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往往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文学经典(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与同时期的史料等非文学素材并置在一起,一方面借助对后者的分析使前者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前者的解读使后者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这其实就是将待阐释的一切对象(不论是文学还是非文学、艺术还是非艺术)放在同一台显微镜下,深度解析不同成分之间的相似性、差异和联系。正因如此,宋惠慈说道:
的确,如今人们所实践的“历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语义共时性:人们认定文本的意义即其所属的历史时期的属性;它属于这一历史时期,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扰。因此,这种历史主义批评的阐释框架是时间之轴的横截面。这样的阐释框架所凸显的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共时关系,而非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延伸关系。
这段话尽管没有挑明“人们所实践的‘历史主义’”中的“人们”具体指谁,但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们当在此列。宋惠慈这段话可以被视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版。众所周知,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某一特定时间点的“语言”而非其历史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索绪尔通过分析语言的共时性揭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维持语言连贯性和意义的规则和惯例,这与研究语言在不同时期演变的语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格林布拉特是知名的莎士比亚学者和专研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批评家,他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注的几乎都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特定“时间之轴的横截面”上的文学作品、王权政治、戏剧舞台、海外扩张和宗教信仰之间错综复杂的互文关系和永不停歇的深度互动。在格林布拉特的视野中,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社会状况相当于一个受规则支配的共时符号系统,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都是这一符号系统中的具体符号。新历史主义不是要孤立地考察这些单个的符号,也不是要追溯这些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而是将文艺复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暂时冻结,通过共时研究来发现这些具体符号之间的差异和联系,从而使背后庞大的语言逐渐浮出水面。

格林布拉特,图片来源:Bing
沿着这条思路,我们不难发现: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始于一种摆脱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的冲动,最终却又走向了另一种结构主义。在回忆20世纪60年代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求学经历时,格林布拉特说:“我顺应了文学批评的总体趋势,从将文本视为‘语象’,转向将文本视为文化制品。”威廉·K.维姆萨特的“语象”早已和艾伦·退特的“张力”一样,成为英美新批评的代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林布拉特这句话流露出了对广义上的“结构主义”批评模式的厌倦和寻求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强烈愿望。然而,他倡导并实践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并没有走出结构主义思维模式。英国学者尼玛·帕维尼在总结格林布拉特和另一位美国文学批评家乔纳森·戈尔德堡的批评实践时,曾对这一点做出过精彩的评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戈尔德堡和格林布拉特[在批评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都认为文化在共时层面上发挥着作为一个庞大整体文本的功能。这一假设是他们将看似不同的文化方面联系起来的基础,因为从根本上讲,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整体统一的印记。
帕维尼的这番话道出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本质:它其实是另一种结构主义。格林布拉特的求学生涯恰逢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如日中天的时代,他不想再像自己的老师们一样满足于对文本本身展开细读,在细读中将文本的意义构建成一个“精致的瓮”,而是希望打破文本的封闭空间,让一些新鲜空气流通进来。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对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进行了升级改造。这种升级改造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由专门细读文学文本转向细读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包括文学、宗教和世俗权力等在内的一切文本;二是在这种无差别地细读同一历史时期各类型文本的基础上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
格林布拉特在试图摆脱传统结构主义的努力中所摸索出的这种新型结构主义毕竟还是结构主义: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共时研究,只不过这种共时研究跟传统的结构主义相比在视野上要广阔得多。但不论其视野有多广阔,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所并置在一起的两个或多个文本通常来自同一个历史时期,这正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共时性所在。在《在惊异中占领——新世界的惊异》一书中,格林布拉特并置分析了哥伦布的航海日志和约翰·多恩的《神圣十四行诗14:三一神啊,请击碎我的心》,将这种共时历史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先是在读哥伦布的航海日志时分析出了诸如“邪恶的土著人(食人族)必须要先被奴役才能获得自由”之类的矛盾命题,而后又在多恩的神圣十四行诗中发现了“只有当你玷污我,我才能获得贞洁”之类的矛盾修辞。格林布拉特的结论是:哥伦布将基督教教义中的悖论性修辞挪用过来,剔除了其中的宗教和神学色彩,使之成为自己展开殖民征服的合法依据。哥伦布(1451—1506)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早期,多恩(1572—1631)则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二人一位是意大利人,另一位是英国人;一位是航海家,另一位是诗人;一位留下的文本是航海日志,另一位留下的是神圣十四行诗。但在格林布拉特那里,既然这二人同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新历史主义就可以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这两个人笔下两个不同的文本放置到一个共时的操作平台上,将他们的作品视为“时间之轴的横截面”上的两份材料进行研究。从这个案例不难看出,新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共时历史主义。

哥伦布与多恩,图片来源:B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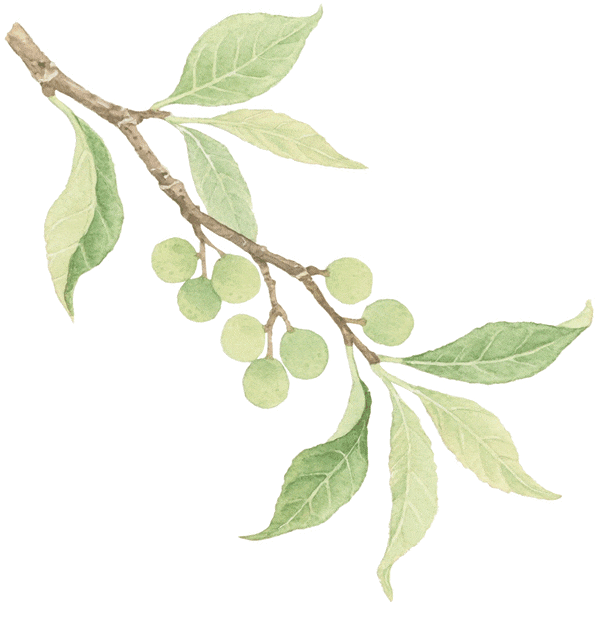
在一篇题为《共鸣理论》(1997)的论文中,宋惠慈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过去的文学文本“明明已经脱离诞生时的语境,为何仍能在当下产生意义,仍具备指意功能并持续引发其他的解读”?这个问题,以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代表的共时历史主义研究很难给出回答。格林布拉特的共时性研究路径决定了新历史主义很难追踪文学文本的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转化和流变,而菲尔斯基的后批判正是回答宋惠慈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后批判之所以在英美文学批评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精准地切中了过去几十年来盛行于英美文学研究界的所谓“怀疑式阅读”的命脉。菲尔斯基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提出的“怀疑阐释学”出发,对怀疑式阅读的缘起、谱系、具体表现乃至实践风格和气质类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指出了其局限。在菲尔斯基看来,精神分析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怀疑式阅读本质上都将文学解读视为一场“发掘”活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将文本解读视为一种“发掘”过程。这两种理论都在表面现象与隐藏的现实之间做出区分;二者都坚持认为,看似平静无波的表面掩盖着至关重要却又令人深感不安的真相。心理压抑与政治压迫可以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某种东西被一种控制力量强行压制、约束和掩盖。在这一框架下,越是看不到的东西越被认为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闪烁着启示性的力量。
这番话指出了精神分析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共同理论假设:发掘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为在表层和深层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批评家的存在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不为表象所迷惑,能够用他们最习惯的批判手法把被文本的表层所掩盖和压制的真相解读出来,从而达到“祛魅”的效果。菲尔斯基这段话中的“[心理]压抑”和“[政治]压迫”在原文中的名词分别是“repression”和“oppression”,只有两个字母之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在童年时的无意识欲望会受到自我的持续监管和压抑(repression),这种以监管和压抑为特点的防御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破坏性后果的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旨在迷惑并压迫(oppress)无产阶级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所以,在菲尔斯基看来,精神分析批评试图发掘出文本背后隐藏的无意识欲望,马克思主义批评则试图发掘出文本断裂处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两种批评方法都在展开具体的文本解读之前就已经假定了文本的普遍内涵:它要么是无意识的欲望流露出的痕迹,要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蔽体现。换言之,怀疑式阅读遵循的探索步骤是“罪犯-线索-罪行”,而且未经调查,就已定罪。
耐人寻味的是,菲尔斯基一方面把弗洛伊德当作怀疑式阅读的先驱之一,另一方面却又从弗洛伊德那里发现了摆脱和超越怀疑式阅读的灵感。这从菲尔斯基对弗洛伊德提出的“滞后性”的极为细致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来:
这个德语词最贴切的英文翻译是“afterwardness”,它集中体现了这样一个观点:意义并非一劳永逸地内嵌于某一特定时刻,而是弥散在时间的连续体之中。从治疗意义上来讲,该术语指的是其影响事后才被个体意识到的那种创伤性事件,其经典案例为弗洛伊德对“狼人”的研究。由于事件的发生与其产生的影响之间存在时间差,意义被推迟,被推向未来,而不是牢牢锚定于某一决定性时刻。
正是“滞后性”概念使菲尔斯基在共时历史主义和历时历史主义之间坚决地选择了后者。在《文学之用》一书中菲尔斯基提出了文学的四种功能:“认知”、“着迷”、“知识”和“震惊”。乍一看,她的文学动能论只不过是汉斯·罗伯特·尧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的另一种表述而已,但实则不然:接受美学否认作者是文本意义的垄断者,强调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积极建构,凸显读者特定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等因素在文本解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意义产生于文本自身的“视域”和读者的“期待视域”之间的融合;菲尔斯基则强调文本意义的滞后性和延展性,认为文本意义并不是被牢牢锁定在它诞生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新的情境不断发生碰撞和共鸣,从而不断产生新的意义。菲尔斯基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滞后性”概念被严重忽视和低估。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说她在2020年出版的《入迷——艺术与依附》中展开的一系列后批判阅读是一朵朵绽放的鲜花,那么那些花的种子早在她对弗洛伊德“滞后性”这一概念的阐发中就已种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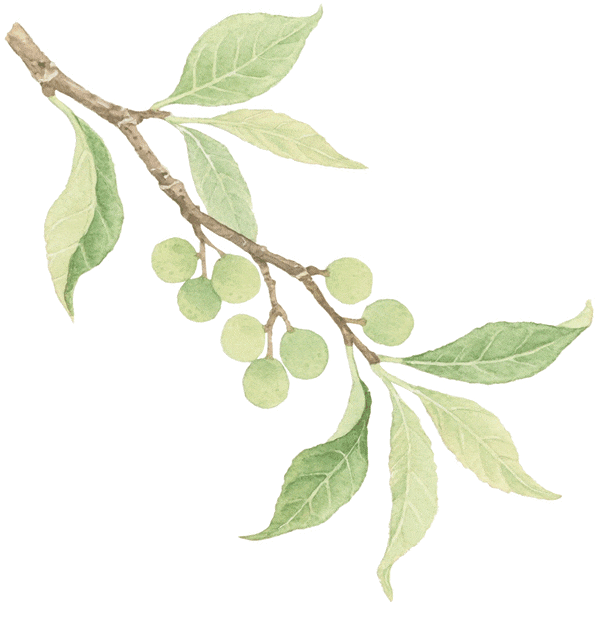
格林布拉特在谈到自己写《炼狱中的哈姆雷特》的初衷时称,他的这部著作要探讨“莎士比亚是借鉴了哪些资源才使得这部作品令人如此耳目一新而又欲罢不能”。菲尔斯基则在其《入迷——艺术与依附》一书中开宗明义:该书“强调‘依附’的重要性,既包括读者是怎样对艺术产生依附的,也包括艺术是怎样将读者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格林布拉特和菲尔斯基用词不同,但前者所谓的“让人欲罢不能”指文艺作品能凭借扣人心弦的情节或栩栩如生的描写牢牢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将作品和读者紧紧“黏合”在一起,这其实和后者所说的“依附”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问题是:既然格林布拉特和菲尔斯基展开文学研究的原始驱动力都是探索特定的文艺作品为何能吸引特定读者的注意力,那从这同一个问题出发之后,为什么一个走向了共时历史主义,另一个却走向了历时历史主义?
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共时历史主义以“疏离”为前提,持一种“平和坦然而又审慎中立的态度”;历时历史主义则关注文本和读者以及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依附关系,认可甚至鼓励文学引发的情感反应和审美效果,这样就不可能做到“平和坦然而又审慎中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就是批评者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出发去靠近文艺作品,以冷静镇定而置身事外的姿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状况(可以是从文学作品入手,也可以是从其他类型的文本和社会实践入手)进行全面考察。在解答前文提到的莎士比亚借鉴哪些资源创作了《哈姆雷特》这一问题时,格林布拉特将仅有寥寥几次出场机会的老哈姆雷特的鬼魂和文艺复兴时期残存的罗马天主教中的“炼狱”并置在一起进行分析。他认为,老哈姆雷特台词中的一些细节在不经意间暴露出一种可能:它是一个来自“炼狱”的鬼魂。考虑到当时新教成为国教而天主教已被宣布非法这一具体语境,格林布拉特进一步推断:塑造这个炼狱之鬼的莎士比亚本人也极有可能是一位秘密的天主教徒。这样一来,在格林布拉特的解读下,《哈姆雷特》就成了莎士比亚的秘密信仰与当时英国社会的官方信仰进行激烈交锋的隐蔽战场。
格林布拉特的共时历史主义让批评者从当下出发去靠近文艺作品,对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类型文本进行并置阅读,破译文本的意义,重构历史的面貌。菲尔斯基的历时历史主义则让文艺作品从过去出发来到当下,看看它经过这一番跨越时间的旅行之后在当下语境中有怎样的新意义,对当下的读者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和影响。在解答前文提及的艺术如何令读者对其产生依附等问题时,菲尔斯基不像格林布拉特那样回溯文艺作品诞生时的具体语境,而是着重对过去的作品影响当下读者的方式、原因和具体机制进行条分缕析:这部作品明明写于几百年前,为何仍会吸引我、打动我?它在穿越这几百年尘封的过程中与周遭环境发生了怎样的接触?在这接触的过程中它的意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读它时的审美反应?与格林布拉特的共时历史主义研究采取的第三人称视角刚好相反,菲尔斯基的历时历史主义批评强调不必刻意追求第三人称视角的冷静超然,也不必与“第一人称的声音”划清界限。她认为,过去的文学作品如何作用于当下的“我”,这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
菲尔斯基在《入迷——艺术与依附》一书中对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的音乐品味变化过程的分析,即是这种历时历史主义思维的典型例证。史密斯和她的诗人丈夫一起驾车去威尔士参加一场婚礼,途径丁登寺遗址时下车休息。不知不觉间,一向对加拿大白人女歌手琼尼·米歇尔的音乐反应冷淡的史密斯竟然哼唱起了其专辑《蓝色》中某首歌的歌词:她彻底爱上了米歇尔的音乐。菲尔斯基在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史密斯人生的前30年极度排斥米歇尔的歌曲,却在一瞬间爱上了后者的专辑《蓝色》(史密斯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大惑不解)?换言之,米歇尔那张专辑的内容本身从未发生任何变化,为何忽然在史密斯的耳朵里从噪音变成了天籁?这种意义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菲尔斯基解答这个问题的思路非常特别:这是因为史密斯停留在丁登寺遗址时,《蓝色》被突然“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环境之中,并与这种新环境发生了碰撞、激荡甚至某种化学反应,正是这种化学反应导致米歇尔的歌曲对史密斯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史密斯童年时父母从来没有在家中摆放过像米歇尔这样的白人女性的音乐制品;上大学时身边的朋友反复向她推荐米歇尔的音乐,她却依然无动于衷。停留在丁登寺遗址的时候,阳光洒向丁登寺,四下一片萧索,丈夫也吟诵起了起华兹华斯的诗歌。正是“这些行动者要素[丁登寺的废墟、山间景色和丈夫吟诵的华兹华斯诗句]的独特组合,促成了[史密斯]感知的转变”。菲尔斯基认为,作品诞生之后就会不断从旧的环境进入新的环境,而新环境中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因素与过去的作品发生碰撞,使作品的生命在新环境中得以拓展和延续。在菲尔斯基看来,当下语境的一切因素都可纳入“行动者”之列,它们构成一张庞大的行动者网络发挥作用。这张网络不但成分复杂,而且极不稳定,其排列组合方式永远处在变动之中。在史密斯的案例中,丁登寺遗址、周围景色和丈夫吟诵的华兹华斯的诗歌这三种行动者的组合恰好激活了米歇尔的音乐,由此拨动了史密斯的心弦。综上所述,如果说共时历史主义是回到作品的语境,是语境化,历时历史主义就是将作品抛入新的语境,是“再语境化”和“再再语境化”。
格林布拉特和菲尔斯基都追问文艺作品的魅力来源问题,二者的提问方式看似相同,实则有本质的区别。前者追问《哈姆雷特》这部作品为何“令人如此耳目一新而又欲罢不能”,但他并没有明确是谁“欲罢不能”;后者则明确指向扎迪·史密斯这一个体。更重要的是,格林布拉特将“人们”热爱《哈姆雷特》当作一个永恒的事实,探讨这种热爱背后的原因;菲尔斯基则追踪史密斯对米歇尔的个人反应从排斥到热爱的整个过程,试图找出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诸多因素。单从提问方式看,格林布拉特遵循的是共时模式,菲尔斯基走的则是历时路径。
二者不但在提问方式上有所差别,在解答思路上也存在巨大的分歧。如果让格林布拉特来解答史密斯的困惑,他可能会还原《蓝色》这张专辑创作时的历史语境,看看当时的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塑造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又如何成了当时各种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菲尔斯基则不然,她没有把这张专辑同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的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菲尔斯基没有做任何共时历史主义分析。她认为,文学作品要想随着时间推移一直具有价值和意义,就必须“吸引支持者、盟友和狂热的爱好者”。菲尔斯基这里所说的“支持者、盟友和狂热的爱好者”除了指具体的人,还可以是有助于文艺作品在新环境中生发出新价值和新意义的一切“非人类行动者”。在史密斯这个案例中,丁登寺的遗址、周围景色和丈夫吟诵的华兹华斯的诗歌都是“非人类行动者”。它们具有能动性,并组成了一个暂时的“联盟”。在这里,菲尔斯基显然借鉴了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文学艺术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单枪匹马作战,而是会不断进入新的网络,结成新的联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作品的意义得以拓展,生命得以延续。
时间不同,外在环境不同,听者(读者)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审美反应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被菲尔斯基称为“调谐”。她为何钟爱这个词?因为它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能“精准地描述现象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通过共鸣和调整来发生变化的”。这个词如果是不及物动词,就是“合拍”;如果是及物动词,那就是“使……合拍”。随着过去的作品闯入由新的行动者网络组成的新环境,不合拍变成了合拍,这就是调谐。不难看出,菲尔斯基的分析关心的不是共时的结构而是历时的变化,她的后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历时历史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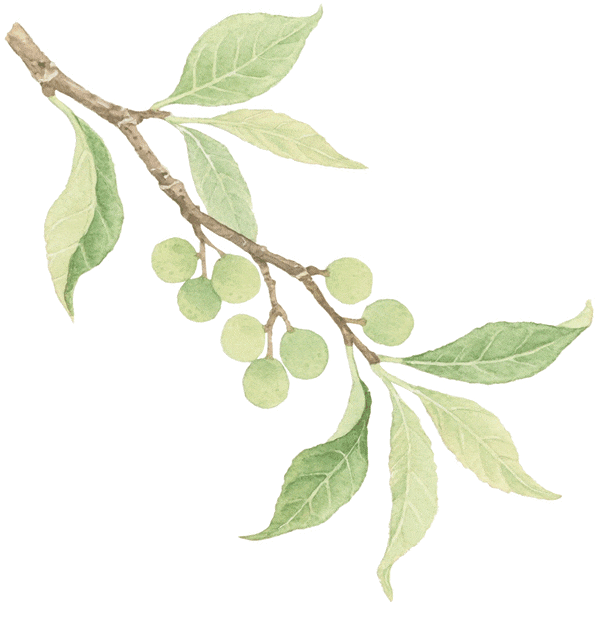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卡斯蒂格里亚称“‘后批判’这一术语日益流行,意味着文学研究可能出现了自40年前新历史主义诞生以来最重大的倾向性转变”。这番话很耐人寻味:一方面,他把后批判和新历史主义相提并论,说明他认为二者在文学批评史和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大致相当;另一方面,他认为就像新批评转向新历史主义一样,从新历史主义到后批判也标志着文学研究的一次根本性转变。然而,说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共时历史主义而后批判是一种历时历史主义,既不意味着二者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也并非像卡斯蒂格里亚那样,认为后批判将取代新历史主义成为文学研究的新一代正统。细加比较可以发现,新历史主义和后批判存在方法上的交集,隐含展开深度对话而非取而代之的可能。
格林布拉特不只一次提到莎士比亚那“如梦如幻的语言”让他痴迷,这是他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依附。他惯于以讲述轶闻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批评实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莎士比亚的商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社会能量的周转》一书,“每一章的开头都会讲述一则轶闻,这些轶闻出自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著作、布道辞或殖民者的见闻录”,这是他对自己批评方法的依附。他之所以写《炼狱中的哈姆雷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渴望“与自己的父亲展开对话”,这是他对亲情的依附。格林布拉特曾提到,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当下]流通,就是因为它们[随着时间流逝]在不断发生转变”,这种论断其实已经算是历时历史主义的“风起青萍之末”。然而,这些苗头在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那里只是一闪而过,没有被深入挖掘,更没有得到理论化。菲尔斯基并不专攻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炼狱中的哈姆雷特》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大胆想象:如果从后批判的视角来解读《炼狱中的哈姆雷特》,菲尔斯基一定大有文章可做。她很可能会将格林布拉特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和对自己父亲的依附联系起来,细致探究这些不同类型的依附通过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甚至左右着格林布拉特的学术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说菲尔斯基完全站在了格林布拉特的对立面,只能说她抓住了格林布拉特文学批评中的裂隙和空白,在后者一笔带过的地方驻足停留,对这些被忽视的地方进行放大和进一步的渲染,从而开辟了文学批评的新路径和新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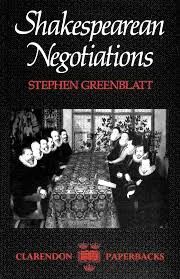
《莎士比亚的商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社会能量的周转》,图片来源:Bing
换个思路来看,菲尔斯基的后批判之中又何尝没有新历史主义的那种批判和怀疑呢?在《批判的限度》书评中,美国学者苏珊·韩德尔曼提到,她的一位同事曾自嘲“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是个文学爱好者,博士毕业的时候却成了一名文学斗士”,意思是批判模式已经让文学研究者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一开始因为热爱文学而投身文学研究,到头来却忘了什么是热爱,只剩下揭露、战斗和意识形态批判;换言之,文学研究已经由一种情感行为变成政治行为。这也是菲尔斯基对文学研究现状所做出的判断——批判将文学爱好者变成文学斗士的做法对文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然而,菲尔斯基本人不也是斗士吗?在《批判的限度》的第四章,她“专门生造了一个新词‘crrritique’(‘批——判’),以三个辅音‘r’延长‘批判’的发音,用如同机关枪连射般的声音效果来具象化批判的高频率发生现象”。对批判如此批判,其力度不可谓不大。菲尔斯基指出,批判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对文本进行‘去自然化’处理,揭示出它被社会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所谓批判,就是试图证明那些看似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不过是社会力量建构的产物。然而,菲尔斯基在其著述中不断强调:文学批评并非一定要采用批判模式不可,这种将文本放到历史发展的横截面上进行考察的做法早已根深蒂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文本解读方式,应当加以质疑。这就是说,共时历史主义的批判模式主张对文本进行去自然化处理,历时历史主义的后批判模式则提倡对共时历史主义的文本解读方式进行去自然化处理。虽然前者的处理对象是文本,后者的处理对象是批评方法,但在“视自然而然的东西为文化建构的结果”这一层意义上,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换言之,后批判在对批判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变成了批判。
其实,在后批判的萌芽时期,菲尔斯基的立场还是相对中正平和的。在2008年出版的《文学之用》中,菲尔斯基试图维持一种多元性和平衡性:“两位读者读《简·爱》,一位爱不释手,另一位则嗅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症候。”菲尔斯基没有评价这两种解读方式孰是孰非,也没有对它们做高下的判断,只是想说明对待文学作品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路径和方式。此外,这两种路径也并非完全对立或泾渭分明,我们完全可以“把分析和依附结合起来,把批评和热爱结合起来”。“分析”“批评”和“嗅到维多利亚时期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症候”显然是共时历史主义,是将文学作品放回原初语境进行冷静的批判;“依附”“热爱”和“爱不释手”则是历时历史主义,是将过去的文本拉到当下,考察它对当下读者造成的情感影响和审美效果。2008年的菲尔斯基尚认为共时历史主义和历时历史主义不但可以并存,而且可以有机结合;但到了2015年《批判的限度》出版之时,菲尔斯基或许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考虑,才在对批判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了另一种批判。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让以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共时历史主义和以菲尔斯基的后批判为代表的历时历史主义展开对话。从当下语境来看,这种对话不但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迫切甚至刻不容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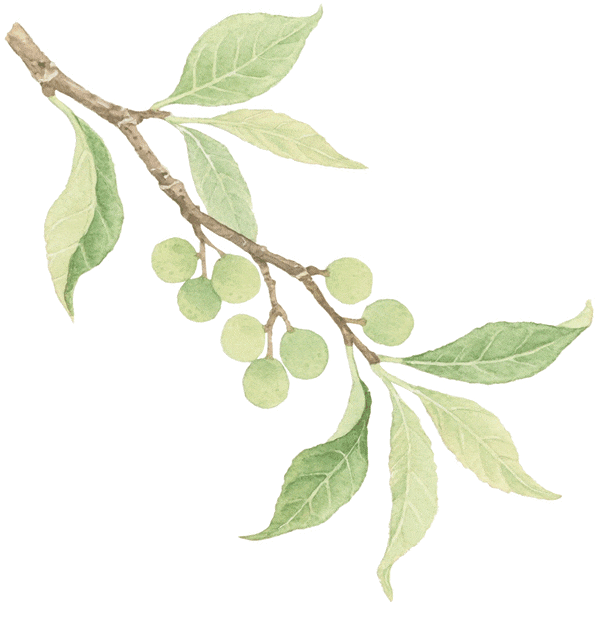
如果说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是将过去的文学文本和同时代其他类型的文本摆放在一起相互参照,菲尔斯基的后批判就是让过去的文本穿行到现在,探究它在当下的语境中生发出的新意义。二者在批评路径上的差异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新老问题:读者/批评者的人称和视角问题、文学的功能问题、文学批评的气质和风格问题等等。本文借助共时历史主义/历时历史主义这一组二元对立来揭示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批判思维与菲尔斯基后批判之间的理路分野,目的并非简单地贴标签,也不是要用线性发展和进步主义的眼光将后批判视为比新历史主义更新颖更先进的文学批评思潮,而是将二者并置在一起,让它们照亮内在的交集,并探索让二者展开深度对话的可能。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善于让不同类型的文本产生共鸣——或用历史文本照亮文学文本的意义,或用文学文本透视历史文本的“真实”。菲尔斯基的后批判拒绝将文本视为孤立的个体,主张对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依附关系进行考察,描述这种关系形成的过程和机制。共时历史主义的共鸣也好,历时历史主义的依附也罢,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意味着摆脱孤立状态并生成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让这两种历史主义进行对话或许并没有违背格林布拉特和菲尔斯基的本意。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5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专栏,责任编辑:王涛。注释从略,前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s://www.ncpssd.cn/)可免费下载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