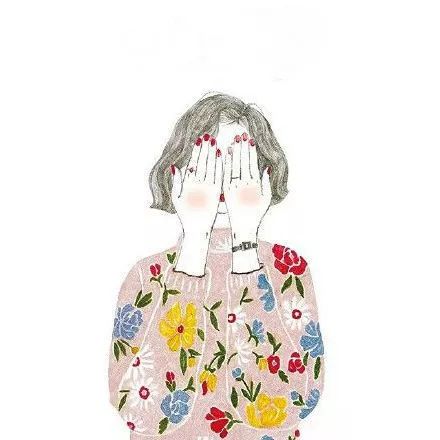众家言说|程巍:卡罗威的“盖茨比”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插曲“Young and Beautiful”

卡罗威的“盖茨比”

程巍
《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九二五年四月在纽约出版,评论界对之毁誉参半,且坊间忽有传闻,称女主人公黛西的形象塑造“明显剽窃了”女作家薇拉·凯切的小说《失踪的女人》(一九二三年九月出版)中的玛丽安·弗里斯特。深为流言焦虑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于是将这部小说最初的手稿片段(大致写于一九二二年七月至次年七月之间)寄给薇拉·凯切,以自证清白。他四月底就收到了薇拉·凯切的回信,信中称她酷爱《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时证明自己并未从其中发现任何剽窃痕迹。
寄给薇拉·凯切的初稿片段有两页留存了下来,现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其中出现了乔丹·旺斯(Jordan Vance)和埃达(Ada)两个女角色以及卡罗威(Caraway)这个男角色,从他们身上可清晰分辨后来正式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乔丹·贝克(Jordan Baker)、黛西(Daisy)和尼克·卡罗威(Nick Caraway),但在这些初稿片段中,卡罗威还不是故事叙事者,所拟的小说题目也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稿片段中根本就没有盖茨比这个人物,与之相仿的形象倒出现在菲茨杰拉德在创作这部小说的间歇所写的两个短篇小说中——而是“在灰堆与阔佬中间”。不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并非一气呵成之作,它经历了好几年的反复构思和不断修改,人物和情节多有调整和增删,而其间薇拉·凯切笔下的玛丽安·弗里斯特暗中影响了黛西形象的塑造,也并非没有可能,尽管这种“并非蓄意的相似”丝毫不会削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艺术原创性。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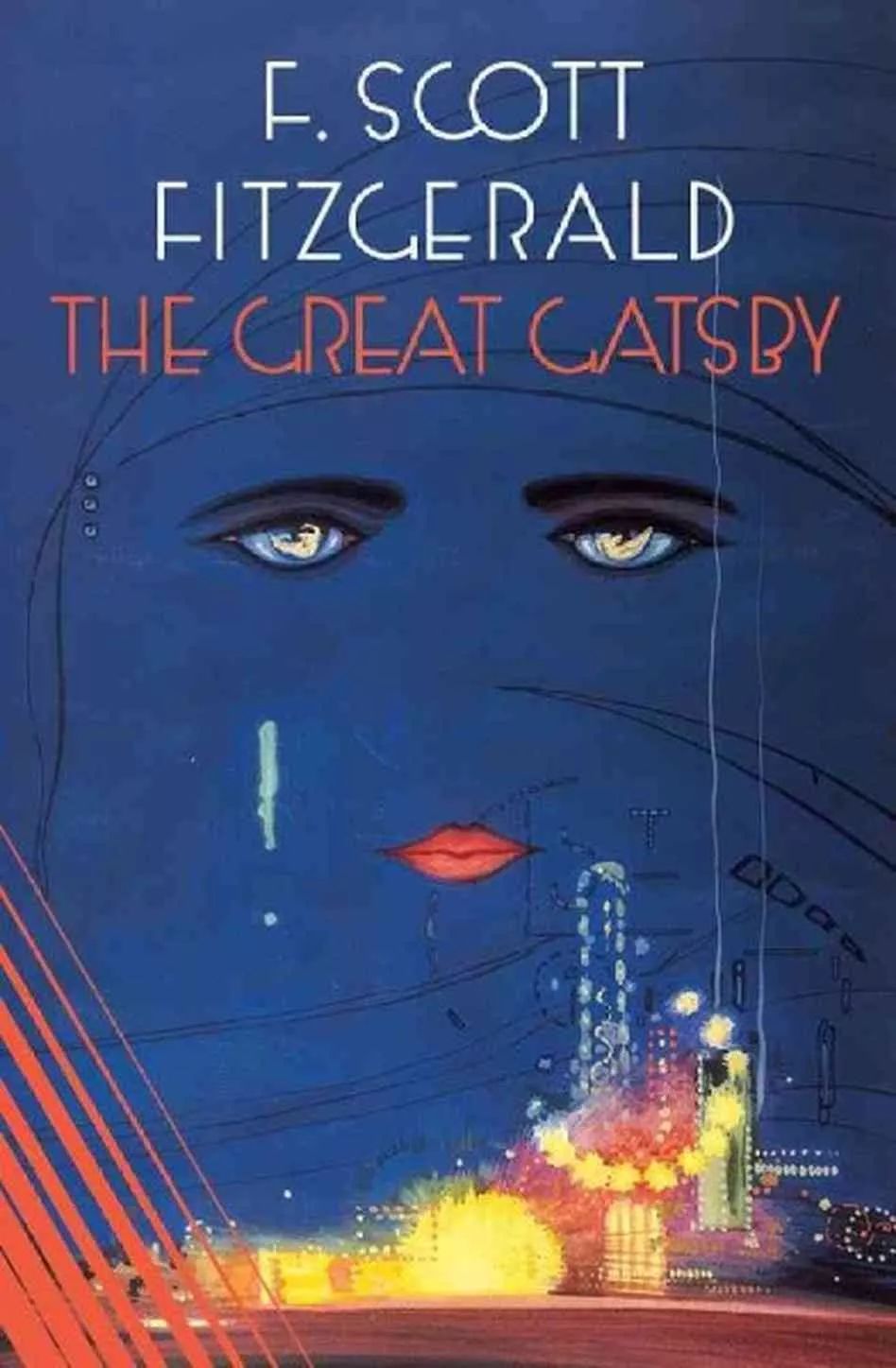
菲茨杰拉德反复构思和不断修改的过程,也是卡罗威渐渐成为故事叙述者的过程。哈罗德·布鲁姆说“菲茨杰拉德的美学是济慈渴望的消极能力的个人修订版”,又称“盖茨比不能讲述他的梦,每当他试图描述他对黛西的一往深情时,他的话语都坍塌为俗套之词,尽管我们不怀疑他对黛西的爱的真实性,就像我们不怀疑气息奄奄的济慈对范尼·布劳恩的强烈渴念的无比真实性。把可怜的盖茨比的粗俗的浮华用词与济慈的讲究的栩栩如生文体等量齐观,可能让人觉得荒诞,但盖茨比的深处是一个济慈”,不过卡罗威而非盖茨比才是故事叙述者,所以布鲁姆又说“在卡罗威的失落的、具有浪漫主义盛期风格的音乐的后面是低鸣的济慈的回声”。这就像芭芭拉·霍希曼所说,“作为一种分离或保持距离的方式”,“尼克这个角色被菲茨杰拉德用来传达自己的声音”。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尼克(左)和盖茨比
那么,“菲茨杰拉德自己的声音”或“尼克的声音”,到底是怎样一种声音?它与“济慈美学”或“消极能力”有何关系?其实,这种声音的特征恰恰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至少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肯定,以便让事物和人物呈现自己,而不是匆忙将它们强行纳入自己已有的知识范畴和道德评判标准。正如济慈在一八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一封家信中谈到“消极能力”时所说,“所谓消极能力,即一种能处在不确定、神秘、疑问的状态的能力”。我们关于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知识和据此进行评判的标准可能并不像我们自以为是的那样全面和公正,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真相是隐匿着的、半真半假的、真假难辨的,因而是神秘的,犹如黛西、汤姆、乔丹、盖茨比以及其他那些在书中出现的人物,他们的对话和关于他们的传闻是不可靠的,以致卡罗威对自己的“视觉”比对“听觉”更多一点把握,认为最好从人们表现出来的“姿态”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来判断一个人。唐纳德·哥尔尼希特谈到济慈的创造性的核心特征时,说它是“一种与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发生同情的奇特的能力,这与他的有关真正的诗人不执着于自身的观念密不可分”。实际上,《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开篇就赋予了故事叙述者卡罗威这种“消极能力”:
我年纪尚轻、易受影响的时候,父亲教我一条为人处世之道,我一直未敢忘怀。
“每当你感到要去批评他人时,”他说,“切记,世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你的那些有利条件。”
他没再说什么。尽管我与父亲之间一向话不多,但总能心心相印。我明白他话里有话。结果,我就渐渐习惯于保留自己的评判,这一习惯使众多离奇古怪之人向我敞开心扉,也使我成为许多纠缠不休的倾述者的牺牲品。心理不正常的人总能立刻从一个正常人那里察觉到这种品性,并抓住不放,于是,在我上大学时,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秘密与闻一些他们所不熟悉的人物的痛史。大多数这类隐私并不是我主动去打听的——每当我从某种确凿无疑的迹象意识到自己又将面临一场秘密倾诉时,我总装出昏昏欲睡、心不在焉或极不耐烦的样子,这是因为年轻人的私密,至少就他们表达这类私密的用词来说,通常是剽窃来的,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自己的判断意味着对人怀揣无穷的希望。正如父亲曾自命不凡地提醒的,也正如我自命不凡地重复的,人类生来就在待人接物的善意上分配不均——如果我忘了这一点,不能宽容待人,恐怕我在评判他人时就会因自己的先入之见而失之片面。
但卡罗威也可能将这种“保留自己的评判”的习性的形成部分归因于地理以及年龄的变化带来的一种迷惘的心理状态。他来自辽阔而寥寂的中西部的一个世家,“大战时”参军在欧洲打了几年仗,“享受着反攻的无穷乐趣,以致战争结束归来后感到百无聊赖。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倒似乎是宇宙的蛮荒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习债券生意”,这一年,他快三十岁了(面临着“三十岁生日的巨大冲击”),孑然一身,自以为此去就将与家乡永别。他当初在战场上享受着反攻的乐趣,但也目睹着昔日像大理石基座一样稳扎在西方人内心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其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化为废墟,而依然不紧不慢的寥寂的中西部就显得难以忍受了。“到东部去”,到纽约去,就是一头扎进陌生的令人兴奋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漩涡中。但那个“中西部人”并没有在他内心死去,而是与新获得的“东部人”身份——“我不再孤独……授予了当地人的身份”——形成一种交叉的目光,似乎任何事物都在其中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是非对错的界线变得模糊难辨,这就使他不得不更加“保留自己的评判”。
一九二二年春卡罗威到达纽约时,正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八条(即《禁酒令》,“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致醉酒类,并且不准此种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以及更严厉的《禁酒法案》(又称《沃尔斯特法案》,规定凡酒精浓度超过0.5%的饮料全在禁止之列,即一切淡酒和啤酒也被禁止)实施的第三个年头,但“禁酒运动”反倒促生了“私酒”这种庞大的地下商业的兴起。从英国非法走私来的各类红酒和苏格兰威士忌以及美国私酒贩子自酿的酒类通过各种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渠道(停泊在海岸的贩运私酒的船—接货的货车—四通八达的公路—作为零售点的加油站和药店)流向美国各个角落,公然出现在大大小小的甚至有警方官员参加的聚会上,而络绎不绝地来盖茨比公馆参加派对的纽约一带的时髦男女们在那里发现各种高档酒——“大厅里,设有一个黄铜围栏的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和烈性酒,还有早已不曾听说过的各种甘露酒……酒吧那边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同时,一盘盘鸡尾酒传送到外面花园的各个角落”——绝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感到难为情,而是开怀痛饮。实际上,不常在自己举办的这些通宵达旦的酒会上露面或宁可不引人注目地混杂在客人中间的盖茨比,就是一个大私酒贩子(这一点似乎谁都知道,也谁都不在意),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地下私酒帝国,靠这个成了一个令人尊敬的百万富翁,并在海边建起了一座宫殿似的庞大别墅。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
通过法律强制“禁酒”,从技术可能性上是徒劳的,按照当时政府禁酒部门的估计,要监控每个美国人每时每刻喝什么饮料,其中是否含有超过0.5%的酒精,至少得有一百万专职禁酒的警察。但技术可能性还是次要的,关键在于,“不饮酒”只是清教的教规,而“禁酒运动”通过禁止这种饮料来打击将此饮料视为宗教仪式或生活方式之组成部分的非清教徒人群,例如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天主教的领圣餐仪式就将红酒作为基督的血),而且,在其他一些民族的节庆仪式中,饮酒还被当做民族认同的仪式。“禁酒运动”致力于在美国这个各种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混杂的国家推行唯一的一种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即白种的、盎格鲁-撒克森人的、清教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具有压迫性,一开始就与美国宪法规定的个人自由原则相违。
与发动禁酒运动的中西部小城镇的清教势力将私酒贩子和饮酒者描绘成十恶不赦的罪犯和恶棍不同,那些将清教伦理视为过时的或者专横的道德意识形态的东部沿海大都市人(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移民浪潮中大量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人、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没有清教背景,恰恰相反,有着犹太教和天主教传统)将“禁酒”视为清教伦理对于其他文化传统的压制,也是盎格鲁-撒克森种族对其他种族的外来移民的政治压迫。谈到美国禁酒运动,丹尼尔·贝尔一九七六年在《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中说,它反映了“文化问题的政治层面”:“就此而言,美国文化政治学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是禁酒运动,它是小城镇的传统势力为向社会其他阶层强制推行其特殊的价值观(不准饮酒)而采取的主要一次——也几乎是最后一次——努力。”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海报
东部沿海大都市(尤其是纽约)接纳了大量欧洲新移民,也就接纳着大量非盎格鲁-撒克森的、非清教主义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来自欧洲的新移民也带来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乃至“欧洲式的抽象理论思维”,危及注重经验和传统的美国思想和学术以及看重经验和简单常识的美国生活方式。“反智主义”虽迟至一九五〇年代——也就是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才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以及政治压迫的形式,但它在美国生活中根深蒂固,它源自早期的清教徒对于欧洲“旧世界”的“精神腐败”的厌恶以及在美洲“新世界”的蛮荒之地创建一种“简单”、“纯洁”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但“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的中译容易引起误解,仿佛意味着对“理性”、“知识”的敌意。正如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所区分的,“反理性主义”并不等同于“反智主义”,“诸如尼采、索莱尔、柏格森或爱默生、惠特曼、威廉·詹姆斯等思想家,以及正如威廉·布莱克、D.H.劳伦斯或海明威等作家,其观念或均可称之为‘反理性主义’,但很难说这些人在生活和政治层面上‘反智’”,实际上,他们中许多人恰恰是“反智主义者”所敌视的那种知识分子,即追求超越“稳妥的常识”的边界的人。“我在‘反智主义’名称下所指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态度和观念,”霍夫斯塔德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对[复杂的]精神生活以及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知识分子]的敌意和不信任。”
这种社会对立同样具有地理和社会地理色彩,即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大都市之间、“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排斥抽象理论思维的“反智主义”传统在中西部根深蒂固,人们讨厌那种高度复杂的现代理论,提倡一种简单的“健康”的生活,而在中西部人看来,东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欧洲移民来的犹太知识分子——却将一些与美国经验主义思想传统相去甚远的高深莫测的理论术语以及同样高深莫测的繁复表达方式带入美国思想及其话语,瓦解了美国的国家认同的文化和心理基础,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小施莱尔辛格在一九五三年说“反智主义一直是一种反犹主义”。他说得有理,尽管有点绝对。
无论禁酒运动,还是反智主义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群体基础,即中西部的盎格鲁-撒克森的清教主义信徒。正由于禁酒运动具有这种文化政治学层面的压迫性,它就反倒为那些非清教人群的“违法”(饮酒)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即抵抗压迫。此时,饮酒就不仅不被认为“不道德”,反倒因为它象征着对一种“不得人心”的法律的反抗,而具有了某种英雄主义色彩。“禁酒运动”时期的许多美国人大量饮酒,比平时还喝得多,逼得那些大大小小的私酒贩子纷纷一夜暴富,并迅速挤入上流社会,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们趋之若鹜的衣着讲究、礼貌周全、出手阔绰的绅士。如果一项法律既“不得人心”,又无法真正追究层出不穷的众多违法者的法律责任,那么,享受着这种跨越法律而不被追究的快感,就成了一种时髦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盖茨比和黛西)
作为有着一半爱尔兰血统而且家里信仰天主教的移民后代,菲茨杰拉德自然不会像盎格鲁-撒克森的清教徒那样反感酒精(和他笔下众多人物一样,他经常狂饮),视之为危及美国社会道德根基的邪恶力量,而是在轻描淡写(或仅仅“隐蔽提示”一下)盖茨比的大私酒贩子身份以及他对庞大的地下非法商业帝国的操控之后,以浓墨重彩,将他描绘成一个似乎对谁都无害而且随时乐于提供帮助的绅士,一个永志不忘初恋情人并最终为之承担带来杀身之祸的责任的“情圣”。但或许是不想让读者联想到本来就受到歧视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菲茨杰拉德暗示盖茨比是北欧移民之后,而且通过小说结尾主持他的葬礼的“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暗示盖茨比是新教徒,即一个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森、新教”合一)。
种族主义是一九二〇年代流行于盎格鲁-撒克森人中的一种“危机理论”,它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一个代言人,即黛西的丈夫汤姆。他在卡罗威第一次在他家做客时就以一种“悲观主义者”的口吻激烈谈到“我们[白人]的文明正在分崩离析”,并问卡罗威是否读过“戈达德的《有色帝国的兴起》”。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说:“这是一本好书,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它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警惕,白种人就会——就会最终被淹没掉。它讲的全是科学道理。这已经证明了。”黛西试图打断他,讥讽他“最近变得渊博了,看了不少高深的书,里面有不少老长的单词……”但汤姆不理会,继续说:“这些书都有科学依据。戈达德这家伙把事情讲得明明白白。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种,我们有责任保持警觉,否则其他人种就会控制世界。”然后他环视在座的几个人,按照戈达德的人种分类法将他们一样分类:“说到占统治地位的种族,是指北欧日耳曼种族。我是,尼克是,乔丹是,至于黛西……”他望着黛西,“犹豫片刻,以轻轻点头的方式将她也包括进去”。
汤姆对“我们的文明正在分崩离析”的担忧与“戈达德”如出一辙。阿纳·伦德认为“戈达德”(Goddard)是菲茨杰拉德对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和洛思诺普·斯托达德(Nothrop Stoddard)这两个种族主义理论家的姓的合写”,这肯定如此,因为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洛思诺普·斯托达德一九二〇年出版的《冲击白人的世界统治地位的有色浪潮》(即《有色帝国的兴起》影射的那本书)就由格兰特为之写序,他们不仅区分了白人和有色人种,还对白人进行了细分,按高低等级分为北欧日耳曼人种(斯堪的纳维亚人种)、地中海人种、阿尔卑斯人种(斯拉夫人种)。汤姆是“盎格鲁人”,属于“北欧日耳曼人种”,而黛西出嫁前的名字是黛西·费伊(Daisy Fay),Fay是一个法语姓氏,暗示黛西是低一等的“地中海人种”。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
至于盖茨比,则其种族身份比较神秘。通过半真半假的履历,盖茨比一直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当时所定义的“真正的美国人”。安德鲁·戈登谈到当时流行在犹太、爱尔兰和北欧移民中间狂热的“同化梦”时说:“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在十七岁的时候通过将自己的姓由Gatz(盖茨)改为更盎格鲁化的Gatsby(盖茨比)而变成一个WASP。”乔治·皮特·利雷等人认为“‘盖茨比’(Gatsby)是日耳曼或瑞典姓氏‘盖茨’(Gatz)的美国化,故事发生的时间正当德国人和瑞典人依然被看做移民,是‘归化的美国人’,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属于纯正的北欧种族,而汤姆·布夏南担心这种纯正的北欧种族将被非盎格鲁-撒克森人所吞没”。卡莱尔·汤普森说:“Gatz这一姓氏字面上的意思在德语中是同伴或和平,它暗示杰伊·盖茨比可能是德国人或犹太人,从‘盖茨’改为‘盖茨比’意味着从犹太教改为新教。”的确,盖茨比庞大的地下商业帝国的成员及其关系人主要是犹太人(所谓“沃尔夫山姆的人”)。汤姆在对盖茨比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将他排除在“北欧日耳曼人种”之外,暗示他是犹太人,是“迈耶·沃尔夫山姆一伙的”。在与盖茨比的一次激烈冲突中,汤姆指桑骂槐地说他不能容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阿猫阿狗和你老婆胡搞”,“人们今天嘲弄家庭生活和家庭制度,赶明天就要抛弃一切,搞黑白种族通婚了”——对此,知道他与威尔士的老婆胡搞的底细的卡罗威只是讥笑,说这个酒色之徒自以为独自站在文明的最后堡垒上。
汤姆是格兰特和斯托达德的种族主义信徒。出于一种意味深长的对比,菲茨杰拉德让盖茨比的图书室出现一本“《斯托达德演说集》卷一”(“Volume One of Stoddard Lectures”),但这个“斯托达德”不是诺思诺普·斯托达德,而是“约翰·斯托达德”(John Stoddard),即诺思诺普·斯托达德的父亲。老斯托达德曾是新教徒,但后来改宗了妻子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并支持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建国,在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中间颇有声望。老斯托达德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足迹几乎遍及全球(来过中国),而且所到之处必将其山川形貌、自然美景、文明遗迹笔之于书,并细心体会其各自的妙处,《斯托达德演说集》卷一即对“挪威、瑞典、雅典、威尼斯”的描绘。他在另一本书的前言中说:“旅行的收获,不是来自你走了多远,也不是来自你看到的景色,而是来自它所激发的智性的灵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和阅读的多少。就像人的营养不是来自他所吃的食物的品质,而是来自他对食物的吸收和将其转化为自身成分的的程度……当意大利、希腊、埃及、印度以及其他地方成为我们心灵的永恒的和清晰的所有物,我们才谈得上访问过它们。”所以,他又将这种旅行称为“心灵之旅”,即摆脱自己的固念,向陌生的存在开放自己内心,并与之亲近。不过,这种带着深刻的同情去了解万事万物、芸芸众生的愿望,却不见于他的儿子——小斯托达德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父亲去世后,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种族主义理论家。父与子,才一代人工夫,美国就关闭了他的梦想与心灵拓展的精神,但它还保存在盖茨比的图书室里,尽管这本毛边书的书页没有被“裁开”,但菲茨杰拉德写道,如果这本书——“一块砖”——从书架上抽掉,“整个图书室就可能坍塌”。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
与盖茨比相比,黛西、汤姆以及那些隔三差五来到盖茨比公馆的酒宴的纽约上层社会男女,按卡罗威的说法,都是一些“无所顾忌之人,他们砸烂了东西,毁掉了人,然后就缩回到自己的金钱之中,退回到他们的麻木不仁之中,或者退回到能够继续维系他们的关系的什么东西之中,让别人来收拾他们的烂摊子”。这个“别人”包括盖茨比,望着他在篱笆那边的草坪上走远的身影,尼克突然有了一种兄弟之情,喊道:“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大帮子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
这个为他们收拾烂摊子的“别人”当然也包括卡罗威本人,他在盖茨比被威尔逊杀死后,操办了他的凄凉的葬礼:“下午五点左右,在霏霏细雨中,我们三辆车子组成的行列开到墓地,在大门旁停下来——第一辆是灵车,黑漆漆,湿漉漉,后面一辆是坐着盖兹先生、牧师和我的大轿车,稍后到来的是坐着四五个用人和西卵镇的邮差的盖茨比的旅行车,大家都淋得透湿。”这场凄凉的雨中葬礼令人联想到歌德笔下维特的葬礼,维特也是毁于他的强烈、持久而敏感得近乎病态的激情:“管家和他的儿子们跟在维特的尸体后面到了墓穴,阿尔伯特未能随他们一起来。夏洛蒂的生活彻底毁了。下人们抬着维特的尸体。没有牧师参加。”
维特是自杀,他的葬礼自然不会有牧师随往。但被杀或者说被误杀的盖茨比的葬礼还是有一位牧师参加的,在盖茨比的遗体下葬时,尼克在雨中站立的寥寥几个送葬者中“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着‘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那正是这个路德教会的牧师。这句充满感伤的诗意的祈祷语的英文原文是“Blessed are the dead that the rain falls on”,是一句自十七世纪流传下来的美国谚语,其他大同小异的说法是“Happy is the corpse on a rainy day”(雨天下葬的遗体是有福的),“Blessed is the corpse the rain falls on”(雨中下葬的遗体是有福的)等,但它最初来自古英语谚语“Blessed are the dead the rain rains on”或“Blessed are the dead,whom the rain rains on”。一七八七年F.格罗斯编纂的《外省词汇》(迷信部分)对这句谚语释义道:“如果遗体下葬时下雨,被认为是个好兆头。”雨中出殡的死者是有福的,因为,正如一八四九年斯芬克斯在一首题为《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的谣曲所唱:
哦,“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这悲伤、纤细、轻柔的雨,
上苍的无声的痛苦的眼泪
轻轻落下,直到死者的身体重生:
是的,“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
这雨,洗涤一切污垢的雨,
伴着“永恒之露水”,
使我们脆弱的肉身重生,
使我们的墓穴变成第二个子宫。
……
这些死者,在人间已死,
死后却获得了生命,
他们现在全在上帝那里,
耶稣是他们的首领。
可是,在小说开篇,尼克为何说“盖茨比代表了我所一直鄙视的一切”,而仅仅几行文字之后,又说“盖茨比最终是无可厚非的”,这正如在小说末尾,他在盖茨比走远时对他喊“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大帮子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之后,又说“我自始至终不赞成他”?批评家们从这里纷纷发现了尼克的“不可靠叙述”,例如查尔斯·华尔科特认为“我们习惯于赋予一个叙述者以某种全知的本领,因为毕竟是他在讲故事”,但“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尼克·卡罗威突破了这些常规……他习惯保留自己的判断”,这就像迈克尔·劳林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尼克允许不和谐音存在于他的观点中”。
但尼克只是在“更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从纽约返回家乡之前——才“习惯保留自己的判断”,而整个故事却是在他返回中西部家乡一年后追述的,此时,他对纽约的朝生暮死的花花世界已感到由衷的厌倦,似乎自己一下子沧桑了许多,急于退回到中西部的虽有些无趣却也安稳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中。曾经被他说成“宇宙的粗糙边缘”的家乡此时在他的一种充满诗意的怀旧感中变得“生动”起来,他重新认可“这是我的中西部……我是它的一部分”,“我现在才明白这其实是中西部的一个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和乔丹以及我,曾全是西部人,或许我们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弱点,使我们都不能丝丝入扣地适应东部的生活”。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
卡罗威没有具体说明中西部人的这种“共同的弱点”到底是什么——那可能是指缺乏“灵活性”、“巧智”和某种难以模仿得来的“自如”和“精致”。不过,尼可拉斯·特德尔阐释说:“东部是都市复杂性、文化与堕落的象征,而西部,‘俄亥俄河那一边的无趣、懒散、自负的城镇’,则代表着一种简单的道德。这种对比汇聚在小说题目上:当盖茨比代表着菲茨杰拉德所认为的与西部相联的那种简单道德时,他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而当他取得的显赫名声被东部当做成功时,他就差不多和巴纳姆[P.T.Barnum,以举办新奇的游艺节目和展览著名,同时还是一个多面手——如作家、慈善家、政治家等等,当时被认为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一样了不起了。”换言之,在他看来,当卡罗威判定盖茨比“了不起”时,是同时基于“中西部”和“东部”这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即本文前文所说的“交叉的目光”。
虽然同为中西部人,但汤姆、黛西和乔丹以及“我”之所以不及盖茨比,在于东部的经历使他们失去了这种“简单的道德”或者说“天真”,这种“天真”包含了一种对“梦想”的持之以恒、矢志不移的坚定性,而且浸透了爱和关切。这种天真的浪漫也片刻见于汤姆:当黛西正犹豫不决地在似乎已胜券在握的盖茨比与似乎快要一败涂地的汤姆之间进行选择时,气急败坏的汤姆突然记起他和黛西过去生活中的一些亲密片段,为反证黛西所说的“并没有真爱过他”,对她大声喊道:“在卡皮奥拉尼的时候也没爱过吗?”黛西回答“没有”,但容态已有一些勉强,汤姆又追问:“那天我把你从‘潘趣酒碗’[游艇]上抱下来,不让你的鞋子沾着水,你也不爱我吗,黛西?”黛西的意志立即就崩溃了,让盖茨比不要逼自己。但作为故事叙述人,卡罗威对自己与乔丹之间的爱情则轻描淡写,但他们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显得苍白,他和她同样老于世故,因害怕失败而不敢投入,对爱情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期待,而在这场还未怎么展开的爱情稀里糊涂地结束时,两个人似乎也不感到多么难过。不管怎样,卡罗威从黛西、汤姆、乔丹以及他本人身上发现的是那种无所用心、粗心大意的不认真(尽管卡罗威对乔丹说:“我最讨厌凡事不认真的人。”),缺乏盖茨比的那种认真、执着、对细节的无比关注以及将自己完全投入到一个想象情境中的敏感。他们失去的,在菲茨杰拉德看来,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敏感和热情。

《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
卡罗威从盖茨比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确定性,一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而不被各种粗俗的欲望所中断的激情和热烈的想象,这激情和想象甚至在其对象物最终被证明完全与之不相配的情形下依然不改初衷,就像盖茨比对黛西的爱——它超越了对象,在对象不在场或已远去的情形下依然如故:“当我坐在那里,沉思着这个古老、神秘的世界时,我思忖着盖茨比第一次认出黛西家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的惊喜之情。他经历了漫长的跋涉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他长久追寻的梦想此刻似乎近在眼前,他一定不会抓不住。他不知道他梦想的对象已被他抛在了后面,抛在了纽约城那一边无垠的混沌中,那里,共和国黑的田野在夜空下延绵不绝。盖茨比坚信那盏绿色的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行渐远的极乐未来。”
因此,当卡罗威说“盖茨比代表了我所一直鄙视的一切”和“我自始至终不赞成他”时,那绝对不是出于自己的一种道德优越感,相反,他认为自己远不及盖茨比。除了“消极能力”,菲茨杰拉德并没有赋予卡罗威另外的杰出才能,他多少显得有些平庸和“少年老成”(就像他谈到乔丹时一样),不会像盖茨比那样为一个不切实际而且最终证明配不上他的梦想而一直坚定执着,为之肩负责任,甚至因之丧命。在卡罗威看来,这太疯狂,太没有“理性”(“计算性”),也太可笑,他会鄙视或不赞成自己身上出现这种浪漫的激情(他与乔丹之间的恋情就是如此)。我们太容易赋予故事叙述者以一种“全知”的地位并对他的“评判”充满信任,但只有顺着卡罗威的自我描述将他降低到“常人”位置,才能理解他对盖茨比的似乎“矛盾”、“混沌”或者“双重”的评价:
当我去年秋天从东部返回家乡后,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起制服并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姿势;我不再需要内心的探险,探入人们的内心。唯有盖茨比,即我用其名来做本书题目的那个人,我不以这种态度对待他——盖茨比,他代表我一直所鄙视的一切。如果人之个性在于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不会屈服的姿态,那么,他身上就有某种异彩,某种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力,似乎他的神经与记录万里之外发生的地震的敏感的地震仪相连。这种敏感反应与通常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那种柔弱的感受性毫不相干,毋宁说它是一种永怀希望的非凡天赋,是一种我此前未曾在他人身上发现过而且大概今后也不可能发现的带有浪漫气质的时刻听从召唤的状态。不——盖茨比最终是无可厚非的;而正是那吞噬盖茨比的东西,那种在他的梦幻消失后从龌龊尘埃中升腾起来的东西,使我常常不再对人们的那些易逝的悲伤和片刻的欢娱感到任何兴趣。
正如前文所引,济慈将“消极能力”定义为“一种能处在不确定、神秘、疑问的状态的能力”。这不仅是指对他人的“不确定、神秘、疑问”,更指对自己的“不确定、神秘、疑问”。卡罗威之所以高度评价一个“代表着我一直所鄙视的一切”和“我自始至终不赞成”的人,是因为卡罗威更多地对自己固有的价值判断持着一种“不确定、神秘、疑问”的态度,却在盖茨比身上发现了“一种我此前未曾在他人身上发现过而且大概今后也不可能发现”的明确的一致性:他的每一步都走在通向“那盏绿灯”的漫长道路上。当卡罗威第一次看见盖茨比时,盖茨比正独自站在黑暗的草坪上,“我准备上前打个招呼”,尽管盖茨比没有发现离得不远的卡罗威,但“这时,他突然做出一个暗示动作,似乎他满足于独处——他双手奇怪地向黑沉沉的海水伸出双臂,尽管离他有些距离,但我敢发誓,我看见他在发抖。我也情不自禁地朝海水的方向望去——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一盏孤单单的绿灯,又小又远”。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1期,责任编辑:高兴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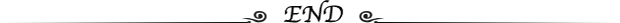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文娟
校对:静远 终审:言叶
世界文学
2018“中国最美期刊”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代号2-231
微店订阅

订阅热线:010-59366555
订阅微信: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qikanzhengding@ssap.cn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