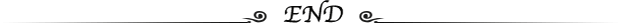切特·摩根是在蒙大拿州的洛根市长大的。那时候,小孩本不该再患小儿麻痹症,但在洛根,孩子们还会得这病。他两岁前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病好了,但是右屁股再也不能完全复位,他母亲总觉得他是养不大的。
十四岁时,他开始骑骄纵、不服调教的马,想向妈妈证明他是打不倒的。马会突然跃起,踢他,撞他,一次又一次。在这过程中,他渐渐认识到:马踢人或者怕生,不是因为性子野,它们踢踹、怕生,是因为千万年来它们已经形成了快速奔跑的本能,否则就会成为狮子的食物。“你等于在说还是因为它们性子野?”切特说出这种想法时,他父亲这么回应他。他没法解释,但他认为父亲理解错了。他觉得这有差别,人们通常说的“性子野”,根本不是他在没驯过的马身上看到的特质。他的小身板清瘦而结实,但因为屁股的毛病,摔倒时,他很难从马腹下爬出来,没到十八岁他就摔坏了右膝盖骨、右脚和左大腿骨。他父亲开车送他到大瀑布城,那里的医生把一根钢条安在他那条还没出问题的腿上,从髋部连到膝盖处。从此,他走路时就像要转身问问题似的。切特继承了母亲的体型,她有四分之三的夏延人(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为阿尔冈昆人的一支)血统;父亲是爱尔兰人,脾气倔强。他们对两个儿子的前途有些模糊的想法,却不清楚如何实现。哥哥参军了。看着他登上东去的列车,身穿军服,英俊挺拔,切特想为什么上帝或命运如此青睐哥哥。命运怎么能如此不公?他二十岁离开了家,往二号公路以北走,一直走到哈佛市。他在哈佛市外找了一份饲养奶牛过冬的工作。农场主一家人住城里,孩子们在上学。路面没有积雪时,他就骑马去最近的邻里打皮纳克尔牌,但大多数时候他都被大雪困在屋里,独自一人。屋里食物充足,电视信号也很好。他还有女子艳照杂志,杂志上的女子他看得烂熟于心,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一个相熟的女子。二十一岁生日时,他穿了两件法兰绒衬衣,里面套件秋衣,外面穿件短大衣,在炉子上热汤。那年冬天,他有点担心自己,他觉得若是再这么孤单下去,就会爆发点什么危险的事儿。春天,他在比灵斯找了份工作,在一间办公室里和友好的女秘书们一起工作,喝咖啡休息时和她们谈论牛仔竞技表演和各种运动。她们喜欢和他共事,还说要派他去芝加哥市的公司总部。他回到租住屋,拧着屁股在屋里走来走去,他想,若是一直待在办公室,三年后,他就一辈子要困在轮椅中了。他辞了职,整个夏天都在拼命打草捆子,也没挣到什么钱。屁股不痛了,除非迈步子不小心才会痛。那年冬天,他在格伦代夫市郊找了另一份饲养工作,那儿地处北达科他州边境。他想如果去东部而不是北部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雪。他在畜舍里隔出一个房间,里面有电视、沙发床、电炉和冰箱;他乘着畜力雪橇就可以给奶牛喂食。他买了些新杂志,里边的女孩对他来说很陌生;他看《警界双雄》和本地新闻节目。晚上,他能听到畜栏里马的动静。他算错了下雪的时间,十月份就开始下雪了。妈妈寄来的包裹和信件陪他捱过了圣诞节。一月份到来时,他又开始害怕自己。不是什么具体的恐惧。刚开始时好像脊柱周围有什么在嗡嗡作响,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安。
农场主留了辆卡车给他,车内装了个加热器,用电线直接连到蓄电池。一天晚上他把车预热好了,然后驶上积雪的公路,开向镇里。小餐馆还开着门,但他不饿。油泵立在发着蓝光的岛形加油站上,但车子的油箱还是满的。他知道这儿没人会陪他打皮纳克尔牌消磨时间。他绕开主街,环着镇子开,开到了学校。侧门有盏灯亮着,人们从停车场的车里出来,走进那道门。他放慢速度,把车停在街上,一直看着他们。他单手环着方向盘,扯弄着破旧皮套上松脱的一根细线。最后他从卡车里出来了,天太冷,他束起衣领,跟随那些人走了进去。
有个教室亮着灯,他跟着的那些人坐在小得可怜的课桌前,互相打招呼,好像彼此认识似的。墙上贴着美术纸标识和图片,黑板顶部有英语圆体字母表。大多数人和他父母年纪相仿,不过他们的面孔显得柔和些,穿得像是城里人,鞋子薄薄的,夹克干净鲜亮。他走到教室后面坐下来,仍旧穿着大衣,一件老式的羊皮内衬牛仔大衣。他检查了下靴子,看会不会粘上什么脏东西带进来,但靴子虽然从雪地里走过,却是干干净净的。一位女士——或者说是女孩——站在教室前边的讲台上,把文件从公文包里拿出来。她长着卷曲的浅色头发,身穿灰色羊毛裙和蓝毛衣,戴了副金丝眼镜。她很瘦,看起来疲倦而紧张。大家逐渐安静下来,等着她说话。“以前我从没上过这门课,”她说,“真不知该如何开始。要不你们先做自我介绍?”“你们可以给我说说你们所了解的学校法。”年轻教师说。小课桌前的成年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有人说。女孩不知所措,片刻后转向黑板。她穿着羊毛裙,臀部曲线流畅顺滑。她写下“成人教育302班”和她的姓名贝丝·特拉维斯,写到字母“h”和“r“时,粉笔发出尖锐的嘎吱声。课桌前的人们都惊得身子直往后缩。“如果你把粉笔竖起来,”一个年纪有点大的妇女边说边拿起一支铅笔示范着,“拇指握在粉笔的边上,就不会发出那种声音。”贝丝·特拉维斯脸红了,她改变了握粉笔的姿势,然后开始讲适用于公立学校体系的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切特在他桌上看到一支铅笔,学着刚才那位妇女说的握粉笔的姿势拿着它。他很奇怪为什么读书时没人给他示范呢?同学们在记笔记,他坐在后面听。贝丝·特拉维斯是个律师,看起来应该是的。切特的父亲讲过关于律师的笑话,但他说的那些律师都不是女孩。这个班的同学全是教师,他们问关于学生权利和父母权利的问题,都是他从未想过的事儿。他根本想不到学生也有权利。他母亲在加拿大圣西维尔大学教会学校长大,在那里,印地安孩子不说英语就得挨打,或者无缘无故地挨打。他还算幸运,一个英语老师用字典敲过他的头;一个数学老师在他课桌上敲断了码尺。但总的来说,他们没让他摊上什么大麻烦。一次,贝丝·特拉维斯似乎想问他点儿什么,幸好有个教师举手,他算是逃过一劫。九点钟下课,教师们感谢了贝丝·特拉维斯,说她教得好。他们商量着找个地方喝啤酒。他觉得他该留下来,为自己解释一下,所以就留在课桌旁。他坐得太久了,屁股又开始发僵。贝丝·特拉维斯小姐收拾好公文包,穿上蓬松的红色外套,看上去像个气球。“你要继续待在这儿?”她问。她看了看表,一块纤薄、金色的表。“什么地方有吃的?”她问,“我还得开车赶回密苏里州。”州际公路从他们所在的北达科他州边际穿过蒙大拿州,往西经过比灵斯和博兹曼,然后路过他成长的洛根市,还要翻过几座山才能到达靠近爱达荷州边境的密苏里州。“那是一段相当长的车程。”他说。她摇了摇头——并非表示不同意,而是表示惊讶。“我是在从法律学校毕业前接受这份工作的,”她说,“那时我什么工作都想要,生怕助学贷款到期还不完。我不知道格伦代夫在哪儿。看起来像贝尔格莱德,我是说这两个单词看着相像,贝尔格莱德离密苏里州要近些——我把这两处地方弄混了。后来我得到了一份真正的工作,他们让我干这份工作真是滑稽。我来这里要花九个半小时。现在还得开九个半小时回去,早上还得工作。我一生中从没做过这么蠢的事。”她看上去似乎在想是不是该怕他,然后她点了点头。“好的。”她说。在停车场,他为自己的步态感到难为情,但她似乎没怎么注意。她上了一辆黄色的达特桑小轿车,然后跟在他的卡车后,往主街的小餐馆开去。他估摸着她自己能够找到地方了,但他想和她多待会儿。他走进了一个小隔间,在她对面坐下。她点了咖啡,一份火鸡三明治,一份核桃仁巧克力圣代,请侍者尽快端过来。他什么都不想吃。侍者离开了,贝丝·特拉维斯摘下眼镜,放在桌上。她揉着眼睛,把眼睛都揉红了。“你在这儿长大的吗?”她问,“那你认识那些教师吗?”她把眼镜戴回去。“我才二十五岁,”她说,“别那样叫我。”他没说什么。她比他大三岁。她的头发在头顶灯光下呈蜂蜜色。她什么戒指都没戴。她打量着他,似乎又在想她是不是应当害怕。但房间那么明亮,而且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坏人。他不像个坏人,他对此非常确信。和一个他帮助过的人在一起——他不会觉得紧张不安。“星期四,”她说,“每周二和周四,要上九周。哦,上帝啊!”她又用手捂住了眼睛。“我做了什么呀?”他努力思索怎样才能帮到她。他得和奶牛待在一起,而开车去密苏里州接她也没意义。那么远,而且他们还得开回去。“我甚至都不懂学校法,”她说,“每次上课前都要学很多东西。”她擦掉下巴上的一点芥末。“你在哪儿工作?”他摇了摇头。她把碟子推到一边,吃了一口有点融化的圣代。她看了看表。“耶稣啊,差一刻十点。”她飞快地吃了几小口圣代,喝光了咖啡。“我得走了。”
他看着那辆达特桑小型轿车的微弱灯光消失在镇外,然后从相反的方向开车回家了。周二到周四时间并不长,而且现在马上就要到周三了。现在他突然饿得厉害,先前坐在她对面时,却没觉得饿。他要是吃了那半块三明治就好了,可他太害羞了。
周四晚上,他早早来到学校,学校还没人,他在卡车里等着,看着。一个教师拿着钥匙过来了,他打开侧门,开了灯。来的人越来越多,切特朝教室后面的座位走去。贝丝·特拉维斯进来了,样子很累,她脱下外套,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纸。她穿着绿色的高翻领毛衣、牛仔裤和黑色雪地靴。她在教室里分发讲义,还对他点了点头。她穿牛仔裤的样子很好看。讲义上方有一行字:“影响学校法的最高法院关键决议。”开始上课了,同学们纷纷举手提问。他坐在后面看,试着想象他以前的老师在这里的情形,但却想象不出。一个年纪比切特大不了多少的男人问关于涨工资的问题,贝丝·特拉维斯说,她不是劳工组织者,他应该和工会谈。教室里年纪大些的女人们笑了起来,打趣这男人煽动民心。九点钟,同学们离开去喝啤酒,他又和贝丝·特拉维斯单独在一起了。他已经盘算了四十八个小时要和她一起进餐的事儿,但现在他却不知该怎样做。他从未邀请女孩去过任何地方。中学时,有女孩同情他,但他太腼腆,或者太骄傲,没利用过这种同情。他在那儿尴尬地站了一会儿。在小餐馆,她请侍者把菜单里上得最快的食物拿过来。侍者给她上了可以外带的一碗汤、面包和咖啡,账单也一起拿来了。她点点头,好像他回答对了。“你知道城里有谁能教这门课吗?”这问题让他吃惊,但他觉得她问他什么都可以。他告诉她最简单的版本:小儿麻痹症,马,骨折。他说,如果不骑马,他最终只能坐轮椅或是进疯人院,或者在疯人院里坐轮椅。她点点头,好像那也是个正确答案,然后看向窗外黑漆漆的街道。“我以前很害怕读完法律学校还是要去卖鞋子,”她说,“抱歉我一直在说这个。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开车。”那个周末格外漫长。他喂奶牛,清洁畜力大车的马具。他用马刷刷马,直刷得那些马鬃毛闪闪发亮,一个劲儿地跺脚,一边看着他,疑心他有什么企图。在屋里,他坐在沙发上,心不在焉地切换频道,最后把电视关了。他想知道怎么追求一个比他大的女孩,一个律师,一个住处远得要横跨一州、脑子里除了那段路程就没有其他念头的女孩。他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但不是以前的那种烦躁不安。周二,他没开车,给一匹马装上马鞍,骑马去了城里。在奇努克暖风的吹拂下,在一月份,这算是个温暖的夜晚,夜空清澈无云。平原向各个方向平摊着延展开去,四下一片漆黑,只有镇子里闪着些灯光。他一边骑马,一边看着星星。到了学校,他把马拴在自行车停放架上,从侧门那边和教师们停车的停车场看不到这边。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塑料袋,解开袋子,里面装满了燕麦。马嗅着袋子,然后用嘴把燕麦捣弄了出来。“我只带了这么多。”他说着,把空袋子塞回衣服口袋。等半数的教师到了,他走进教室,坐到他的位子上。每人都坐在上周坐的位子上。他们谈论着奇努克风以及雪会不会就此融化。贝丝·特拉维斯终于来了,穿着那件篷松的大衣,带着公文包。看到她,他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快乐,她又穿牛仔裤了,真好看。他还怕她会穿那条细窄的羊毛裙呢。她站在那儿,显得疲惫不堪,郁郁不乐。教师们继续叽叽喳喳地说着。上完课,教师们都离开后,他问:“我可以捎你去小餐馆吗?”“不是坐我的卡车,”他飞快地说,同时心想着为什么卡车对一个女人来说更危险。他觉得可能是因为卡车像个房间。“出来吧。”他说。她在停车场等着,他解开拴马的缰绳,骑了上去。他从自行车停放架那边绕了一圈骑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看上去像个傻子,可是他又觉得自己的骑术不亚于任何人,于是就洋洋自得起来——他朝贝丝·特拉维斯骑去。她站在那儿,双手把公文包抱在胸前。“别想那么多,”他说,“把包给我。把你的手伸过来。左脚踏上马镫。再把另一只腿跨上来。”她照着做了,样子很狼狈。然后他把她拉上来靠在他身后。他把她的公文包抵着马鞍前桥拿稳当了,她紧紧地抓住他的夹克,腿贴着他的腿。他什么其他的想法都没有了,只感到她紧贴着他脊柱底部,是那么的温暖。他从后门骑出去,骑过黑黑的街道,快速朝主街骑去,在小餐馆后面突然停了下来。他先帮她下了马,然后在她身后闪身跳下,把公文包给了她,再将马拴好。她看着他,笑了,他这才意识到以前从没见她笑过呢。她的眉毛上扬,眼睛张得开开的,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笑起来眼周会起皱纹。她看上去是一副惊讶的样子。小餐馆里,侍者把汉堡包和炸薯条轻轻放到贝丝·特拉维斯面前,说道:“厨师问屋子后面的那匹马是不是你的。”贝丝·特拉维斯把椭圆形盘子长的那端转向他这边,然后拿起汉堡包。“吃点薯条,”她说,“你怎么从来不吃东西?”他想说在她身旁时他不饿,但若说出来,他又怕看她脸上出现那种回避的表情。她看着汉堡,好像答案在汉堡里。她眼睛的颜色几乎和头发是一样的,环裹着那双眼睛的是颜色浅淡的眼睫毛。他想她会不会认为他是个印第安男孩,因为他长着和母亲一样的黑发。“我不知道,”她说,“不,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母亲在学校自助餐厅工作,我姐姐在医院洗衣房工作,照理说,卖鞋子就是我这种家庭出来的女孩能得到的最好工作。”“不,没什么难过的,”她说,“这是件快乐的事儿。瞧,我是个律师,还有份这么好的工作,每隔一会儿就开车去该死的格伦代夫,直到我疯掉。”她放下汉堡包,用手背按住眼睛。她手指油乎乎的,一只手指上沾了蕃茄酱。她把手从脸上拿开,看了看表。“十点钟了,”她说,“早上七点半前我赶不到家了。路上有鹿,沿河开经斯里福克斯外边时,路面有光滑的薄冰。如果我能挺过这段路,还必须得冲个澡,八点上班,把没人愿做的所有破事都做了。然后明天晚上要多学些学校法的知识,然后在后天午餐前离开办公室,开车回到这边,眼皮一路直打架。也许,这还是比医院洗衣房好些,但也他妈的好不到哪儿去。”她用餐巾纸沾了点儿玻璃杯中的水,把手指擦洗干净,然后喝完了咖啡。“你真好,把马弄过来了。”她说,“现在带我回车子那儿好吗?”出了餐馆,他又扶她跨上马背,她用手臂抱住他的腰。她像一小片拼图与他的身体完美地拼搭在一起。他慢悠悠地骑马回到学校停车场,他不想让她走。到了黄色达特桑轿车旁,她爬下马时,他紧紧握住她的手,然后他也下了马。滑下马背时,她那件蓬松的大衣给扯得往上缩,她把衣服拉平整了,然后他们站在那儿,四目相对。他点点头。他想吻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做。真希望以前和中学女生或友善的秘书们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只要能为这一刻做好准备。她正要说点什么,但他在紧张不安中打断了她。“周四见。”他说。她顿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他把这当成了鼓励。他猛然拿起她的手来,亲吻着,因为他想那样做,那柔软而冰凉的手。然后他俯下身去,亲吻她的面颊,因为那也是他想做的。她没有动,一点儿都没有,然后他真正要和她接吻时,她像猛然从恍惚中清醒过来,躲到了一旁。她把手抽了回去。“我得走了。”她说,然后绕到达特桑轿车驾驶席那边。她开车出停车场时,他将马牢牢牵住,然后他踢了一脚雪。马往旁边一闪,躲开了。他恨不得狂跳一通,兴奋、紧张、苦闷。他吓跑了她。他不应该吻她的。他应该多多吻她才是。他应该让她说出她想说的话。他上了马,往家中赶去。周四晚上,他开卡车来的,不再像个牛仔;他有一项严肃的使命。他要真诚地回答她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他不吃东西。他要让她说出她想说的话。他不再等人们都来了才进教室;他早早地进去了,坐在后面的位子上。教室坐满了,然后一个穿灰色西服、肚子像个保龄球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来,站在讲台后面。“贝丝·特拉维斯小姐,”他说,“觉得从密苏里州开车过来实在太辛苦,所以我来接任这学期剩下的课程。我在这个镇里做律师工作。你们有些人知道的,其他人很快也会知道,我最近离婚了,所以手头有些时间。这就是我在这儿的原因。”这人说话时,切特从座位上起身,顺着过道走到门口。他站在外边,把冷冽的空气吸到肺里。他听任镇里的灯光在他的眼睛里游弋,直到他眨眨眼扫清了视线,然后爬上了农场主的卡车。他给车加够了油,这样发动机才不会罢工,然后卡车一阵咳嗽,等稳定下来后,就跑起来了。他知道贝丝·特拉维斯住在密苏里州,往西有六百英里远,要翻越几座山,但他不知道她具体在哪儿。他不知道她在哪儿工作,也不知道电话簿上有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他不知道是不是他吓跑了她,是不是那次骑马吓着了她。他不知道卡车能不能跑那么远,也不知道农场主发现他不在会怎么样。但他给卡车挂上档,沿着他三次看见黄色达特桑轿车走的方向驶出镇子。平坦笔直的道路仿佛在卡车下翻滚,黑暗、无声,就这样穿过了黑暗、无声、大雪覆盖的广阔大地。他在迈尔斯城外停了一次,在比灵斯城外又停了一次,他拧着那条发僵的腿一瘸一拐地到处走会儿,直到他又能开车了。到大廷伯城附近,平原到头了,开始翻山,在星光映照下,群山的黑色轮廓赫然耸立。他在博兹曼镇停下来喝了咖啡、加了油,然后经过斯里福克斯和洛根市时,在空旷的道路上他压着白线开车,这是为了避开路面的冰——路肩上结的一层硬如铁皮的冰已经漫延到了路面上。黑暗中,他右手方向的某个地方,他知道,父母正在睡梦中。他到达密苏里州时,天还没亮。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在电话簿里找“特拉维斯”。有一个“贝·特拉维斯”并留有电话号码,但没有地址。他记下号码,没打电话。他问看收银机的小年轻镇上的律师事务所在哪儿,小年轻耸耸肩说:“可能在商业区。”小年轻眼睛直盯着他。“那就是商业区。”说着,他指向切特的左手边。到了商业区,在黎明的微光中,切特看到身边都是店铺、老式的砖头房子和单向街道。他停好车,出来活动一下髋关节。群山靠得太近,他感到一阵幽闭的恐慌。这时他发现一块雕刻的木制标牌,上面刻着“律师”,就问来开办公室门的秘书认不认识一个叫贝丝·特拉维斯的律师。秘书打量着他那双扭曲变形的腿,他的靴子,他的短大衣,然后摇了摇头。下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秘书要友好些。她打电话给法律学校,问贝丝·特拉维斯去了哪儿工作,然后用手捂住话筒。“她在格伦代夫有份教书的工作。”律师在电话里把这条信息重复了一遍,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了点儿什么,把纸条递给了他。“就在下边的那个老火车站附近。”她用铅笔指着窗外说。八点半时,他把车慢慢开到纸上写的地址,正好遇上贝丝·特拉维斯的黄色达特桑轿车也慢慢开进这个停车场。他走出卡车,心里忐忑不安。她在公文包里找着什么,没有马上看到他。然后她抬起了头。她看着他身后的卡车,然后目光回移,注视着他。“我还以为自己弄错地方了。”她说,她的公文包自然地垂搭在体侧。“你在这儿做什么?”缓缓地,她点了点头。他尽可能地站直了身子。她生活在一个和他不同的世界。你乘飞机去夏威夷或者法国,都不如开车到她这儿用的时间长。她的世界有律师、商业区和山脉。他的世界里有饿得醒来的马和在雪里等他照料的奶牛,他要开十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去喂它们。“我很难过你不教那个班了,”他说,“我很期待你上课,期盼那样的夜晚。”“不是因为——”她说,“周二我本来想告诉你的。因为要开这么长路程的车,我已经要求找个人代替我。他们昨天找到了一个。一个穿黑西服的男人从一辆银色小汽车里出来,远远看着他们,审视着切特。贝丝·特拉维斯向他招招手,笑了。男人点点头,又看了看切特,然后走进房子;门关上了。切特突然希望她辞掉那份教书工作是因为他的缘故,希望自己对她还有点儿影响。他变换了一下身体重心。她把头发往后捋了捋,他觉得可以走上前,摸摸她的手,摸摸她的颈背——她颈背处的头发比别处要黑些。然而,他把手插进了牛仔裤口袋。她似乎匆匆扫视了一下停车场,才又看着他。“现在我得回去喂牲畜了,”他说,“我只知道如果我不开这趟车,就再也见不到你,我不想那样。就这点儿事。”她点了点头。他站在那儿等待着,觉得她可能会说些什么,可能会迎着他走近一点。他想再次听到她的声音。他想摸摸她,她的任何部位都行,也许就摸摸她的手臂,就摸摸她的腰。她站在他触碰不到的地方,等着他离去。他终于爬上卡车,启动了引擎。他的车开走时,她还在停车场看着他,然后他驶上高速公路,离开了小城。头半个小时里,他一直紧紧握着方向盘,直握得手指关节发白,他眼睛盯着公路,看着卡车将公路吞食下去。后来,他疲倦得连火气都消了,眼睛刚要合上,又猛地睁开。他差点就驶离了路面。在比尤特,他买了杯黑咖啡,站在卡车旁就把它喝了。他多希望自己在停车场时没有马上就看到她。他多希望自己有片刻的时间做准备。他把咖啡纸杯揉扁,扔掉了。驶过洛根时,他想着要不要停一下,但他没必要停。他知道父母会说什么。母亲会担心他的健康,开了一夜车,她这病歪歪的儿子在冒着生命危险。“你甚至都不了解这个白人女孩。”她会说。父亲则会说:“耶稣啊,切特,你让那些马一整天没水喝吗?”回到海登,他给马喂了吃的,喝了水,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没有哪匹马做过奋蹄冲出厩栏的事儿。他给它们套上马具,给雪橇装满干草,它们把雪橇拉出了畜棚。他用小刀将束绑每捆干草的橘黄色粗绳割断了,然后把干草从雪橇上扔下去喂牛。马儿迈着艰难的步子,毫无怨言,这时他想起那匹两岁的“滑头”,他浑身上下,被它踢得遍体鳞伤,当时他十四岁。现在他腹部的疼痛就像那时的痛楚。但他并没觉得贝丝·特拉维斯对他不公平;他不知道自己期待什么。即便她请他留下来,他也不得不离开。是那场谈话的终结,是那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看向她的那道呵护的目光,令他心痛、令他受伤。在畜舍里,他对着马说话,走到它们身后,靠近它们的后腿。它们是很聪明的马,对于意外变故具有免疫力,而他却让它们一整天都没水喝。他给每匹马额外加了满满一咖啡罐的谷物,黄灿灿的谷物滑溜而出,一层盖一层,倒进了饲料桶中。他走到屋外,在黑暗中,远望栅栏外平坦延伸的大地。月亮升起来了,原野是一片模糊的蓝色,一头头奶牛点缀其间。他的屁股仍然僵硬肿痛。他得去撒尿,于是走到离畜舍远一点儿的地方,眼看着雪地里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冒着热气的小坑。他想也许他在贝丝·特拉维斯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因为他已经向她展现了他的真挚。她不会回来的——无法想象她还会开车过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但她知道他在哪儿。她是个律师。只要她愿意,她就能找到他。但是她不会找他的。这才是让他心痛的事。他扣好牛仔裤的扣子,调整了一下屁股的姿势。他原本想做些练习,练习和女孩子相处,现在他有了,但他希望在感觉上这次体验要真的只像是一次练习就好。天气变得更冷了,他得赶紧进屋。他从口袋里摸出她的电话号码,在月光下细细看了一会儿,直到熟记于心,再也不会忘记。然后他做了他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掉了。
作者介绍

麦莉· 梅洛伊(Maile Meloy),1972年出生于美国蒙大拿州首府赫勒拿市,1994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小说艺术硕士学位,现居洛杉矶。短篇小说集《两者得兼》(Both Ways Is the Only Way I Want It, 2009)获当年《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十佳图书奖,并被《洛杉矶时报》评为年度最佳图书。2007年,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将麦莉·梅洛伊评为美国最优秀的年轻小说家之一。梅洛伊的创作生涯始于短篇小说,作品频频出现在欧美各类知名刊物上。梅洛伊的散文也别具一格,颇有建树。本文《贝·特拉维斯》(Travis, B.)选自其短篇小说集《两者得兼》。
载于《世界文学》2019年第5期,责任编辑:杨卫东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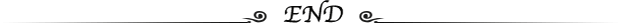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代号2-231
微店订阅

订阅热线:010-59366555
订阅微信: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qikanzhengding@ssap.cn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