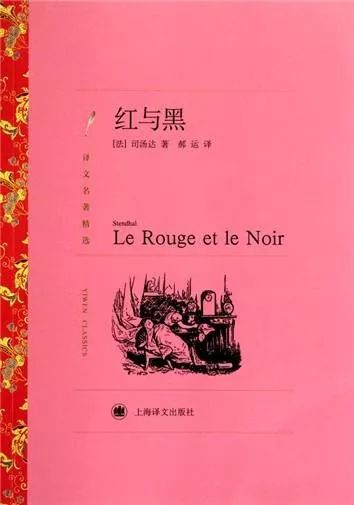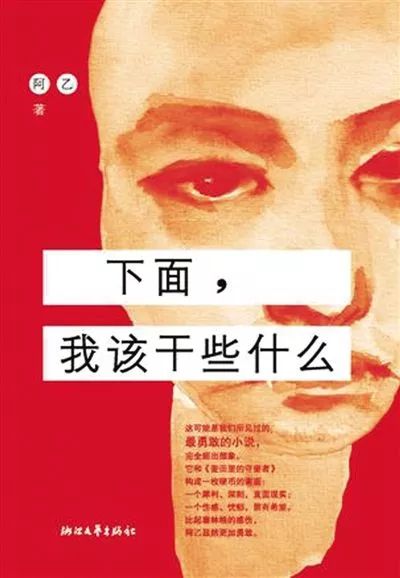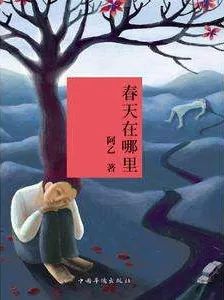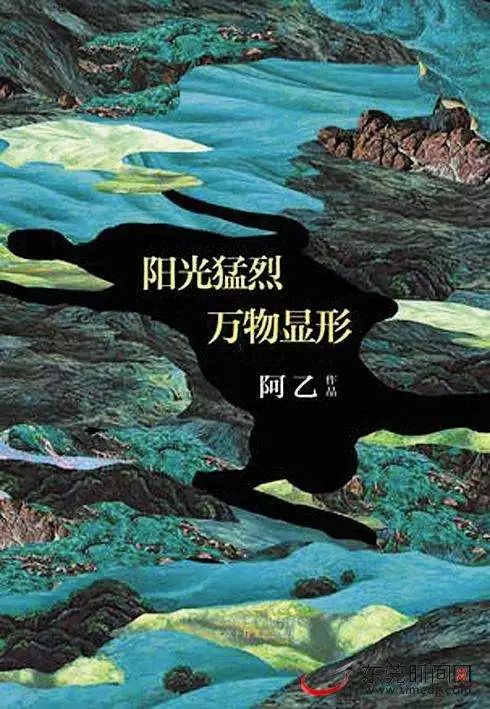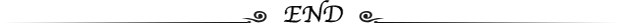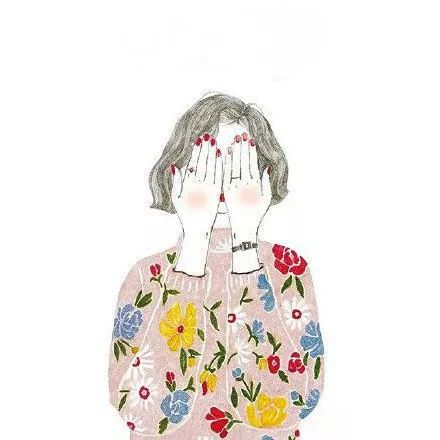阿乙
有几次在接受采访时,我说文学是无用的。这时我是一个知道羞耻并且在态度上有些暧昧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害怕手中的文学被引导和改造为外在意志的工具,一是害怕自己不能承担“教化他人”的使命,并且要为读者的行为负责。但在心中,我一直认为文学及文学家是有作用并且是作用巨大的,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一个人的父亲。我常在名著的序言里看见这样的话:“作为……,它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时至今日,它仍然在年轻人的心里发挥着它的作用。”和文学可谓近亲的哲学则对人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研究员迈克尔·坦纳在撰写牛津通识读本《尼采》时称:有一项出色的研究(阿舍姆,1992)致力于考察一八九〇至一九九〇年间尼采对德国的影响,该研究列举出了“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纳粹分子、宗教信徒、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先锋派艺术家、体育爱好者和极端保守分子”,他们都从尼采的著作中获得启示,而这个名单显然还可以继续延伸下去。我最近翻到一篇叫“故事如何塑造了世界”的文章,提到“荷马史诗不仅在文学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古希腊时期的图书馆和营火会。具体来说,就是它有助于塑造整个社会及其伦理”,“从这部史诗(《伊利亚特》)汲取无穷的灵感后,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把希腊语变成广袤区域的共同语言来回馈荷马”。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的话,那就请把我也算作一个深受文学影响的例子吧。在我的故乡,一个市区人口一度只有几万的小城市瑞昌,我曾经是一些人口中“头脑发热”的典型。有一次,一位在小城信访部门工作的高中同学来京,我请他吃饭。他和别人一样,对我在二十六岁时自摔铁饭碗到大城市闯荡的举动不吝赞美,说“这样的勇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说你有必要跟我这么客套吗?为什么不和我说说实话呢?我只是随口一说,未料他接下来说:“你知道家乡的人是怎么评价你的吗?都说小艾你是个妥子。”妥子在我们家乡话里是傻子的意思。那一刻我面红耳赤,为自己在人心中竟是这么一个东西而悲哀、愤怒。我在心中狠狠发誓,永远也不必回到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乡了。后来,我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去想,发现自己确实不懂得人生这门生意。做的事情可谓荒谬古怪。比如公务员编制,政府每增加一个都极为艰难,多少人为得到这个新增的编制而挤破脑袋。有的甚至采用行贿这样风险极高的办法。当时我年纪轻轻,已经借调到市委组织部,同时保留民警的身份,可以多领一份警衔工资。根据一种并非不靠谱的说法,来年我还有机会借调去更上一级部门工作。就是这样一份让人艳羡、并且使我在小城相亲市场变得极有魅力的工作,我将它搁在桌上,悄然乘车北上,到无亲无故的郑州当一名“打工仔”。你说这样的行为“妥”不“妥”。我记得在小城,一名大学毕业(虽然是毕业于成教部)的姑娘,作为警属,到公安局办公室当月薪只有一两百元的打字员。据说这样熬过十几年,她就有希望从临时工转为事业编。和她类似的是局里的司机、驯犬员,他们有不少是警属,都打算花费巨量的时间去等。也许会出现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一个人退休了,他的编制恰好也批下来了。我还想到一名邻县的干部,为女儿谋取到在类似乡财政所的地方上班的机会,将其设计为一名基层公务员,而他的女婿在欧洲留学。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我生于一九七二年的哥哥也曾受家族意愿左右,在矿业学院读完本科后返回小城矿产局工作。他先我一步离开了小城,去杭州当了一名程序员。他的离开对我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示范。不过,对我的出走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在这本定价十三元八角的书的扉页上,保留着我阅读时批注的日期: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那时我大专毕业刚好一年,在江西省最北边的一间派出所当内勤。在那个山谷里,马路上没有一粒柏油,所有店铺都没有招牌,因为几乎没有流动人口,没必要挂上一个招牌。我与其说是在那里工作,还不如说是在那里付出“必要的忍耐”。按照政府里存有的风俗,年轻人只有去基层锻炼,才能得到升迁。哈罗德·布鲁姆在分析于连时,认为人的不悦基于虚荣,“我们感到悲伤,是因为我们焦躁不安,无法在桌前坐下来”。在那个叫洪一的寂静乡村,我固然也像困兽一样焦躁不安,时常为如何用掉自己多余的精力发愁,但我认为只要调到县城,这个困扰就迎刃而解了。真正使我看清整个世界的轮廓、看到它的繁华与博大、看清我所在的瑞昌市只是一个悲哀的小地方并且不值得在此驻留的是《红与黑》,是一个叫于连·索雷尔的被判死刑的青年。它就像鞭子或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我脸上,使我一下具有了“地球人”“中国人”的意识,而不再是一个知足的“县里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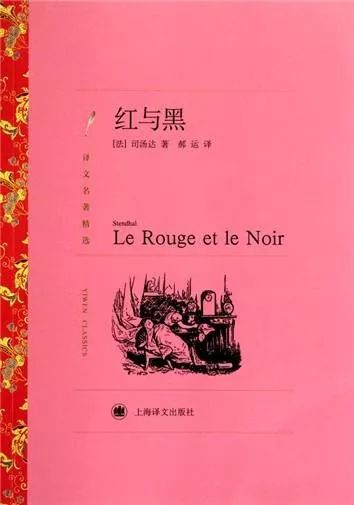
我无法忘记自己在乡村斗室做出的那些仪式感十足的举动:突然站起来、走来走去、将拳头击向桌面。我感到喉咙里堵着亟待导引出来的呼喊,我强烈想将它们分享给别人。发现自己的激情,就像发现大海、发现新大陆一样,让人感知到体内的血像一条粗蛇一样在扭动。因为血流加速而身体发热。我找到在洪一中学当老师的王辰以及在土管所上班的周小刚,手舞足蹈地向两位同龄人分享读后感,分享另一种人生可能。这种可能性不是距离遥远、纯属虚构,而是近在眼前,就在我们的手中和心里。“一个处在地理底层的身份低微的年轻人,他一样拥有对世界的所有权,”我这样说,“拿破仑拥有的人生,我们照样可以有。”然后仿佛是意识到这终归是大话,会使隐身在阴影中的鬼魂冷笑,我跟着别人一起笑话起自己来。我呀,其实还想举起书本,翻到第五十页,对着他们分享一段于连设法拉住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文字。我现在将它引用如下,诸位可以跳过去,也可以先来品尝它:……他指手画脚,碰到了德·雷纳尔夫人的手,她的手是搁在平常安置在花园里的那种油漆过的木头椅子的椅背上的。她的这只手很快地缩了回去。但是于连想,要使这只手在他碰到时不缩回去,这是他的职责。想到有一个职责需要履行,想到这个职责如果不去履行,他就会成为笑柄,或者不如说,会产生自卑感,他满心的欢乐顿时便完全化为乌有了。(第八章)最后大家终于坐了下来,德·雷纳尔夫人坐在于连的旁边,德尔维尔夫人挨着她的好朋友。于连一心想着他试图做的事,找不出什么话来说。谈话变得毫无生气。“将来我第一次参加决斗时,也会这样发抖,也会这样感到不幸吗?”于连对自己说;他对自己对别人都太不信任,因此不可能不看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在极度的苦恼中,任何别的危险在他看来都更为可取了。他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希望看见德·雷纳尔夫人突然有什么事,不得不回到屋子里去,不得不离开花园!于连不得不克制自己,他克制自己用的力量太猛,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完全改变了。很快地德·雷纳尔夫人的嗓音也颤抖起来,不过于连没有发觉。职责在和胆怯进行的这场可怕的斗争太痛苦,他不可能注意到自身以外的任何事。城堡的时钟刚敲过九点三刻,他还什么也不敢做。于连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气愤,他对自己说:“在十点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要做我在整个白天一直向自己保证在今天晚上做的事,否则我就上楼回到自己屋里去开枪自杀。”在等待和焦虑中度过最后时刻,于连心情过度紧张,几乎快要发狂了,接着,他头顶上空的时钟敲响十点钟了。这决定命运的钟声每一下都在他的心头回荡,而且仿佛在他胸中引起了一阵肉体上的颤栗。十点钟的最后一下钟声还在响着,他终于伸出手,一把抓住德·雷纳尔夫人的手,她立刻把手缩了回去。于连已经不很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再一次抓住她的手。虽然他自己很激动,还是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握着的这只手凉得像冰。他使足了劲把它紧紧地握住,她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手抽回来,但是最后还是让这只手留在他的手里了。他的心灵里洋溢着幸福,这倒并不是因为他爱德·雷纳尔夫人,而是因为可怕的痛苦折磨刚刚结束了。为了不让德尔维尔夫人发觉,他认为自己应该说话;他的嗓音又响亮又坚定。德·雷纳尔夫人的嗓音却相反,听上去她是那么激动,以至于她的好朋友以为她病了,提出回到屋子里去。于连感觉到危险:“如果德·雷纳尔夫人回到客厅去,我要重新陷入我白天的那种可怕的处境。我握这只手的时间还太短,还不可能看成是我得到了成功。”在德尔维尔夫人再次建议回到客厅去的时候,于连使劲握紧那只任他握着的手。德·雷纳尔夫人已经立起来,又重新坐下,有气没力地说:“我确实感到有点儿不舒服,不过外面空气新鲜,对我有好处。”这些话证实了于连的幸福;在这时刻他的幸福达到了顶峰……(第九章)司汤达《红与黑》,郝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50—53页。 我真想和他们分享我读到这段时全身仿若通电的经历。我发现司汤达复制的不单是伊泽尔省一名马掌匠儿子安托万·贝尔德(在现实中他杀害了自己的雇主兼情人米肖夫人)的心理,不单是他自己的心理,同时也是他死后将近一百六十年中国外省一名年轻警察的心理。我所有心思的活动——我那只有面对自己时才不加掩饰的幽微精细同时波澜起伏的心理活动——都没有逃出他的观察。司汤达不是在写于连,而是在写我。或者说,他是在写所有那些居住在外省、身份低微然而具有巨大想象力的青年。在我的欲念里,就是要这样去追逐女人。我渴望以这样的手段,或者,我被迫运用这样的手段。我们在追逐女人时,并不擅长使用油腔滑调的语言,不会过于奉承,我们为了负起自己的职责,往往会粗笨地去擒捉对方的手。高贵的女人是我们征服的对象,手是第一个堡垒。当时,在我的心脏深处,一定隐藏着一种道德上的无耻及残忍。对我们这些危险的奋斗者来说,道德只有一个,就是行动,就是占有,就是征服,就是获取。哈罗德·布鲁姆说于连这个小拿破仑“吸引我们,但却不会激起我们的喜爱之情”。我想这里的我们应该去除我。我不但喜欢于连,而且简直是崇拜。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张英伦先生在为这本郝运译的《红与黑》写译本序时,提到司汤达于一八〇五年一月十四日写下的日记:“我认为我是为最高级的社会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强烈地盼望这两种东西,而且配得上它们。”当时司汤达只有二十二岁,在一九九八年我恰好也是二十二岁。我记起在警校时持之以恒向一名貌美、温柔同时条件极佳的警督女儿发起追求的穷同学,我意识到,成功是对他行动的奖赏,也是对我们这些同学犹豫不决的惩罚和讥笑。合上《红与黑》后,我再也没有办法忘记一种屈辱的处境:我是在一个狭窄的远方毫无意义地生活着,我年纪尚轻,早早地就虚度人生。(后来我在北京见过编剧李樯一次,他来自小城安阳。他在作品《立春》中提到契诃夫的《三姊妹》,在焦菊隐翻译的这部话剧里,有这样一个片段:玛莎住在这个城里,懂得三国语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我甚至要说,这正和手上长了一个六指一样没有用处,是一个累赘。)我没办法接受这样窝囊的自己。我开始背着单位和家人,去天津《滨海时报》、南昌《信息日报》这样的媒体面试。我迎着朝阳出发,到达人家的大厦,挤在上百人的队伍里等待接见。看着那些竞争者一个个戴着眼镜,而我视力过好,我深觉羞耻。面试官们坐成一排,面无表情,冷冷地问几个问题,一会儿就打发走我。我记得在铩羽而归时,所乘坐的客车总是身披落日的光芒。被迫回到小城瑞昌,是对我的人生的巨大宣判,是一种镇压。我没有办法将这样的人生执行下去。后来我在写作中篇小说《意外杀人事件》时,将自己作为人物之一写进去,我写“我”试图这样回应来规劝自己不要出门的长辈:“你(出走)失败不代表我失败;即使所有人失败,也不代表我失败;即使我已失败过两次,也不代表会失败第三次;即使第三次失败了,那也比现在强,我不能在临死前追悔莫及。”
二〇〇二年秋,我终于将自己弄出去了。一个叫陈东的同龄人作为《郑州晚报》体育部主任打来电话:“小伙子,你这就过来上班吧。”我立即扔下在瑞昌市的工作,搭火车北上,来到郑州,开始当一名体育编辑。记得在走出郑州站时,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我展开双臂,“啊”地低喊着。这和拉斯蒂涅远眺巴黎时欲火炎炎地说“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是一回事。我是一个在自我相处时仪式感很强的人。在《郑州晚报》期间,我连专属的电脑也没有。作为一名有待转正的编辑,我得趁两名记者不在时,借用他们的电脑。他们一旦来到单位,我就得起身,走向员工抽烟的地方,倚在那儿发呆。在那里,我和当时还在郑州大学念书的实习生郑江波相处甚好。一天,在得知是郑江波负责查看应聘简历后,我问他,我是不是杀退千军万马才得到这么一个宝贵机会的?他这样回答:“招聘启事挂了十几天,只收到你一份简历。”后来我跳槽到北京一家报社上班,报社来过一位曾在小城广播电视报工作的记者。因为业务能力可能有欠缺,始终处在被开除的边缘。后来有人这么传说他,一天,他写的稿子(虽然只是豆腐块)终于被本报采用了。这一天他到得比谁都早,拿起新印好的报纸,抑扬顿挫地朗诵起自己写的报道,甚至不放过“本报讯(记者×××)”这样的字眼。今天,回忆到这个细节时,我心里像是被刀猛然擦了一下。在媒体工作九年途中,一天,我听说曾将我拒绝的《滨海时报》死了,是啊,死啦,心下不知为何兴奋极了。也正是因为知道自己以及很多像自己这样的青年深受《红与黑》的影响,我想到文学的一个源头叫拿破仑。有拿破仑以来,就有了无以计数的不再安分的人。这样私人的经历,我在好些场合讲过。有些人提醒我,一个作者应该处于零度的状态,应该忘我、无我。我有时想这样反驳:“我做不到这样,因为只要将我自己抽离,我的文学就失去一半。我若是死了,我的文学的房屋也就塌毁一半。甚至可能变为彻底的废墟。”不过他们善意的提醒还是使我认识到,我比较容易为自身经历骄傲和自豪,也就是小人得志、沾沾自喜。其实只要走到上海、广州、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就能见到大把的流动人口,他们都做了和我一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人到城市里发展,寻找自己理想中的职业,做自己理想中要做的事,在当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人们在使自己符合社会的同时,也在尽量使自己符合自己。但是,有时我又想,这样再正常不过的事,也许只是刚刚来到我们社会。也就是说,我,作为一名七〇后,恰恰处在转型的临界点上。在我以前,那些六〇后,因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多,并没有太多办法实践自己的意愿。要意识到面前有一个逐渐开放、允许人去自由流动的市场,是在九十年代,是在我们这些七〇后刚好成年的时候。现在的八〇后、九〇后应该对此困扰不多。我记得,我有一位表哥、一位表姐、一位堂兄,他们或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或出生于七十年代初,都使用了当时高考允许的极限次数:八次。除开堂兄终于考中省水产学校,剩余两人都悲惨地失败了。支撑他们这样做的,是对成为农民的恐惧。在一个市场远不开放的年代,农民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进而获得国家的分配,就只有到田地里干活,或者托人介绍到某个单位当薪水极低的临时工(这还是算好的)。我记得每当我读书不用功时,家中的大人就会过来恐吓我:“不好好念书,今后怕是要回九源乡穑田(耕田)哪。”
我是一个对存在主义倍感亲切的人。萨特在他普及性的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提到一个“裁纸刀”的概念。“我们在察看一件制成品时,譬如一本书,或一把裁纸刀,这件成品是由某个师傅根据某个概念制成的……裁纸刀一方面是根据某种方法生产出来的成品,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用途;很难设想某个人生产一把裁纸刀而不知道其用途。因此我们断言,对裁纸刀来说,本质——即旨在生产和确定裁纸刀的制法和性质的总合——先于存在;这样,在我们面前出现的这把裁纸刀或那本书是确实的。于是我们就用技术观念去看世界了,根据这一观念,我们可以说,生产先于存在。”他这样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室著名编辑艾珉在为他责编的《萨特读本》做导读时清晰指出:“和前辈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存在先于本质’和‘自我选择’论是萨特学说的基本命题。即人首先存在,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自身;生活本是一片虚无,全靠自己赋予生活以意义。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是人区别于物的最大特点。对于物来说,是本质先于存在,物在被制造出来以前,其性能功用早已设计好了;人却只能通过自我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确立自己的价值:‘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我对存在主义仍然理解很少,有时还存在极大的误解,但我认为它总是在不时地给我一些生命的汽油。我想到社会和父亲对我的设计和命名,我曾经有一个名字叫“国柱”,和别人的名字——“建国”“卫东”“爱武”“保国”“爱军”——一样,代表着一种安排。我之所以考进警校并且成为一名警察,渗透着父亲的强力意愿。有时,当我从梦中醒来,意识到父亲虽然已死了,他的意愿却仍旧试图逞到我头上。他在将我设计为一把裁纸刀。唯有我顺从,他才会感到和谐。自从在二〇〇二年秋天离开瑞昌后,我就开始稳固使用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阿乙。它像零一样无色无味、缺乏意思,可是我要使它发出光来。在一些深沉和聪明的人那里,容易手舞足蹈的我显得可笑。可是我常告诉自己:这世上有谁比你还珍惜自己呢。很多次站在窗前面对黑夜时,我都像足坛里著名的小人也是英雄若泽·穆里尼奥那样宣布:我是特殊的一个。原载于《世界文学》2019年第4期,责任编辑:高兴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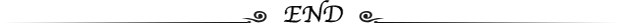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代号2-231
微店订阅

订阅热线:010-59366555
订阅微信: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qikanzhengding@ssap.cn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