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散文品读〡尾崎秀树【日本】:鲁迅与夏目漱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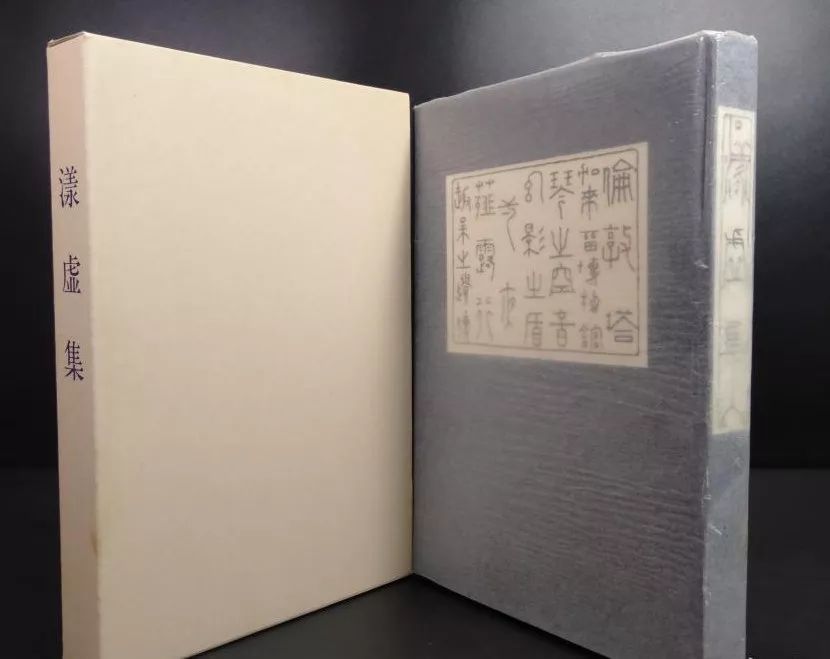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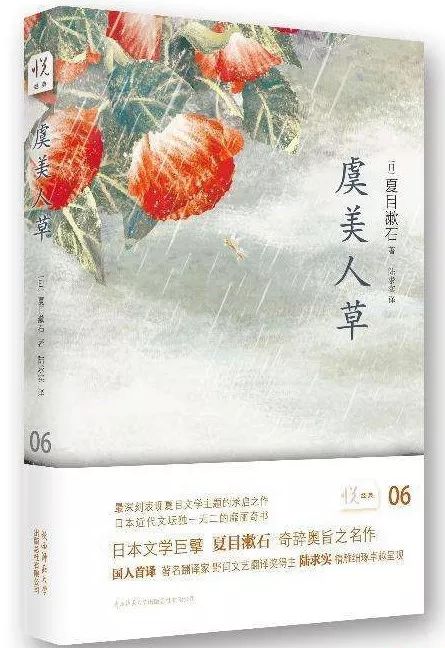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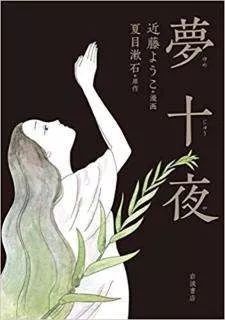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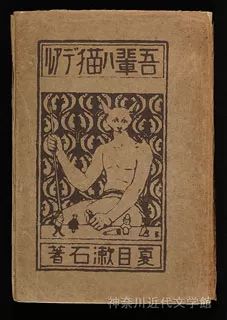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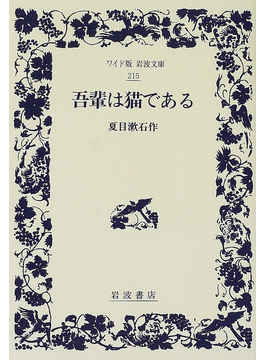
原载于《世界文学》1997年第2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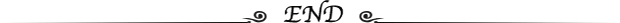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文娟
校对:博闻 终审:言叶
世界文学
2018“中国最美期刊”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代号2-231
微店订阅

订阅热线:010-59366555
订阅微信: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qikanzhengding@ssap.cn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