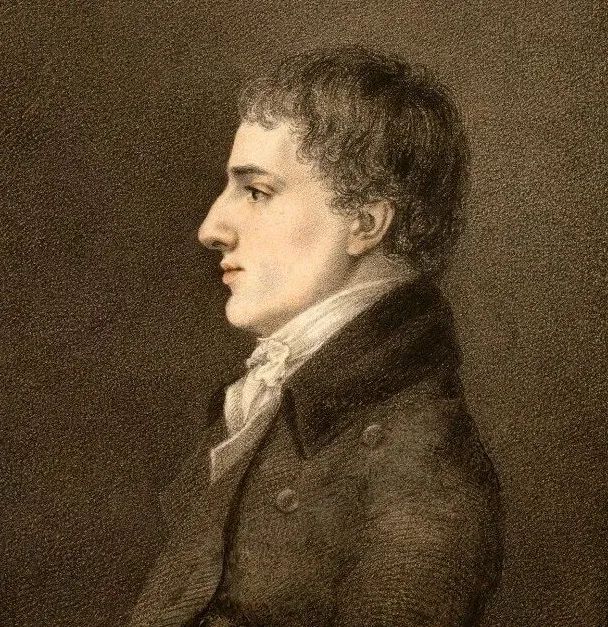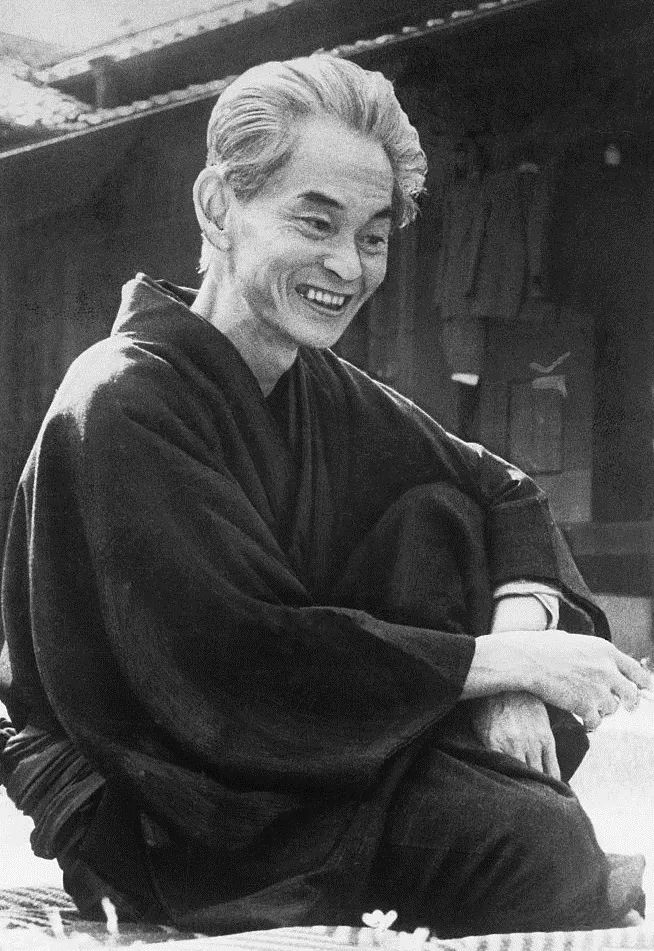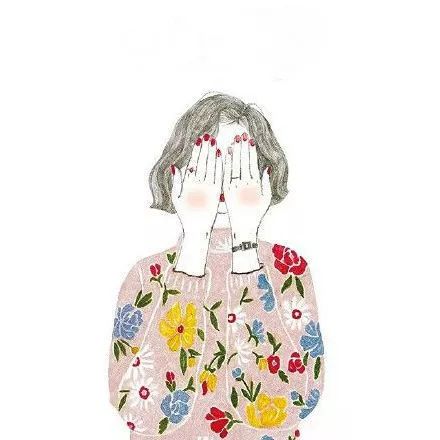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书香致远 |《世界文学》里的读书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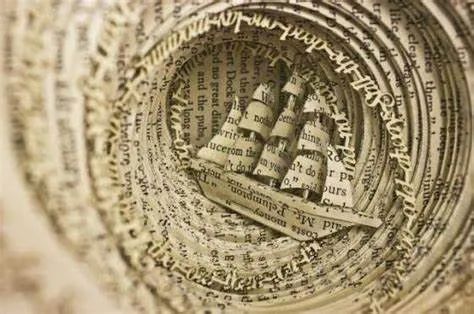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查尔斯·兰姆(英国)
朱利安·巴恩斯(英国)
大冈信(日本)
川端康成(日本)
阿兰(法国)
朱利安·格拉克(法国)
W. H. 奥登(美国)
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秘鲁—西班牙)
卡罗尔·希尔兹(加拿大)
黄金明(中国)
沙克(中国)
王小妮(中国)
赵荔红(中国)
海男(中国)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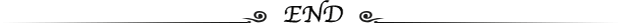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言叶 排版:文娟
校对:博闻
终审:言叶
世界文学
2018“中国最美期刊”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代号2-231
微店订阅

订阅热线:010-59366555
订阅微信: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qikanzhengding@ssap.cn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