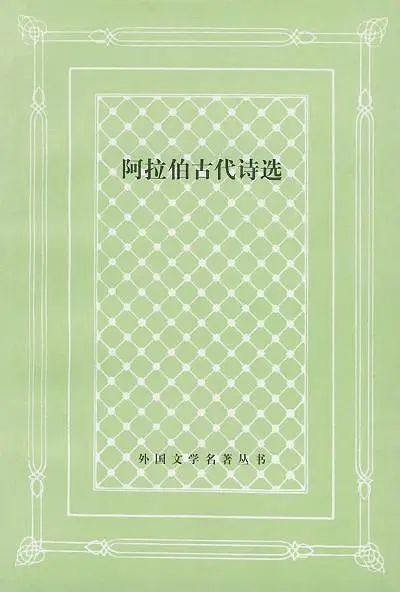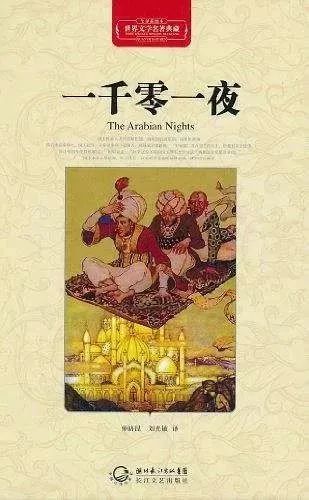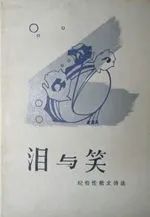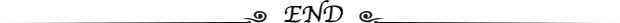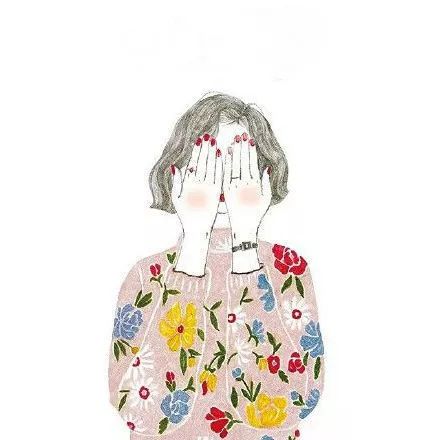“作为一个阿拉伯语言文学的教师, 翻译研究工作者,我又会时时觉得自己未能尽职、尽责而惴惴不安。喊不如干,向人呼吁不如从自己做起。这也许就是我在教学、科研之余,抽空译些阿拉伯诗歌的初衷。拙译《阿拉伯古代诗选》不久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总算是对全国广大的阿拉伯文学特别是阿拉伯诗歌爱好者有个初步交代,也算了却我一份心事。(……)我认为大部分诗还是可译的,只是觉得不好译,译不好。我只好尽力译得好一些。目的全在于抛砖引玉。我在翻译诗歌过程中,尽力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要对得起作者;二是要对得起读者。”
——仲跻昆
(摘自《世界文学》2001年第2期)

2020年4月13日,我国阿拉伯语文学届泰斗、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仲跻昆教授与世长辞,享年82岁。《世界文学》编辑部原本准备在今年的“译家档案”项目中前去采访仲老先生,如今这一愿望只能化作永远的遗憾了。
1961年11月,甫从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留校任教的仲跻昆先生以“中人”的笔名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叙利亚短篇小说《最亲爱的人死了》,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为我们的读者带来过曼妙的阿拉伯语诗歌和小说,也曾为《世界文学》组织的“外国诗歌翻译笔谈”系列赐稿,畅谈译事初心与苦乐。译路坎坷艰辛,却可建造起通天的巴别塔,在下面这篇数年前发表于《文艺报》的翻译之路自述中,仲跻昆先生回顾了阿拉伯语文学汉译的艰难起步与发展,细致地谈论了对诗歌翻译中韵律节奏处理的思考,并以琢玉人自比,发愿将不为国人熟知的阿拉伯语文学瑰宝通过翻译“雕琢成璧,献给中国人民”。今天我们重读此文,谨此向仲跻昆先生和他细密精诚的劳作之下硕果累累的翻译生涯致敬。 天艾
自1956年上大学算起,我与阿拉伯语言、文学打交道,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其间,除了教学、科研,也零零星星地翻译过一些阿拉伯古今的诗歌、散文、小说……
读过阿拉伯历史或是阿拉伯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年,中古时期,特别是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初期的文化、文学是何等风光,何等辉煌!它可与我国盛唐时期的文化、文学媲美。阿拉伯文化、文学源远流长,它承前启后:上承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迦南-腓尼基文明,下启欧洲文艺复兴。它贯穿东西:融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及其本身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于一炉,通过丝绸之路、香料之路,东接中国;通过西西里岛、安达卢西亚,西达欧洲。那时的阿拉伯语颇似今日的英语,是国际交流的通用语;求贤问业的学子也往往负笈云集于巴格达等地。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化、文学曾让西方的东方学者们为之倾倒赞叹。近现代的阿拉伯文学在传承经典、借鉴西方的基础上,渐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发展。一些诗坛巨匠、文坛巨擘,在我看来,并不比西方的一些著名诗人、作家逊色。但长期以来,阿拉伯文学在我国的翻译、介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却都远不够理想。
我常常为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境况、地位感到不安、不平:长期以来,受“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人们提起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似乎指的就是西方文学;许多冠以“世界”“外国”的文学工具书、文学史中,东方文学不是只字不提,就是只是点缀;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也大都是欧美文学作品。东方文学在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东方文学的译介远不及对西方文学的译介。而在东方文学中,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又远不及对日本、印度文学的译介。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工作虽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但只是翻译了《古兰经》部分章节和蒲绥里的《天方诗经》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仅限于《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片段故事,那是部分学者在20世纪初从英文或日文译本转译过来的。茅盾先生于1923年从英文译的纪伯伦的几篇散文诗,冰心先生于1932年译的纪伯伦的《先知》(原著为英文),是我国对阿拉伯现代文学最早的译介。多半是据英国学者约翰·德林克沃特的《文学纲要》编译而成的郑振铎(西谛)先生的《文学大纲》(1927),在上下两册共约2200页篇幅里,对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只占25页,算是当时我国对阿拉伯文学最全面、系统的介绍了。解放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为了配合当时中东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了表示对兄弟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当时在我国出现了介绍阿拉伯文学的第一次高潮,翻译出版了诸如《埃及短篇小说集》《黎巴嫩短篇小说集》《阿拉伯人民的呼声》《约旦和平战士诗歌选》《流亡诗集》等阿拉伯文学作品。但这些译作多半是从俄文转译的,直接从阿拉伯文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则是凤毛麟角。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年做教师的搞翻译似乎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是“追名逐利,搞个人名山事业,妄图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行为”,每逢政治运动一来,必定要受敲打,要深刻检讨,把自己臭骂一番才行。所以,我除了1961年毕业那年翻译了叙利亚一位女作家的短篇小说在《世界文学》发表后,直至“文革”,没再敢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文革”后,长时间的文化封锁禁锢使读者对文化、文学的需求如饥似渴,对外国(当然包括阿拉伯世界)文学的译著尤甚。因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阿拉伯文学译介在我国的新兴。为了打破“西方-欧洲中心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我国的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开设了“东方文学史”课,1983年还成立了“东方文学研究会”。众所周知,阿拉伯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学史”课的开设,引起教的人和学的人对阿拉伯文学的浓厚兴趣,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我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埃及开罗大学进修回国后,开始由教阿拉伯语言课转为教阿拉伯文学的。1987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我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任阿拉伯文学研究生的导师。在这种情况下,译介阿拉伯文学无论如何已经成为我一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事了。我常想起古代楚国那个为献玉璞被人讥笑、又被砍去双脚的卞和。他的悲剧主要在于所献的是璞,未经雕琢,难免被人误认为是石头。后经雕琢,成了璧,不就价值连城,为那个蔺相如成为英雄创造了条件吗?在我看来,阿拉伯文学也不啻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我们要想方设法把这块璞雕琢成璧,献给中国人民。这种雕琢过程就是翻译。歌德说过:“翻译家好比是热心热肠的媒婆,他们极口称赞那个半遮半掩的美人,赞赏她的姿色,以便引起人们对原著的不可抑止的思慕。”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其实我早就想做一个热心热肠的媒人,将自己眼中最美心中最爱的两种文学竭力撮合,联姻成亲;竭尽全力,把璞雕琢成璧。我最初是或独自或与同仁合作,译了一些小说,如黎巴嫩的《努埃曼短篇小说选》、沙特阿拉伯赛义德·萨拉赫的《沙漠——我的天堂》、埃及伊·阿·库杜斯的《难中英杰》《库杜斯短篇小说选》、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米拉玛尔公寓》《埃及现代短篇小说选》等;还译了纪伯伦的《泪与笑》《大地的神祗》等散文和《一千零一夜》的一些故事。但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它像一面镜子,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诗歌始终是阿拉伯文学的骄子:佳作珠联,美不胜收;诗人辈出,灿若星汉。在中世纪的世界,如同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可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媲美一样,也只有中国的诗歌可与阿拉伯诗歌相媲美:两个民族的文学都以诗歌为主体;诗歌又基本上是抒情诗,都讲究严谨的格律、韵脚;诗歌的内容、题旨也很近似。当年阿拉伯诗歌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周边国家、地区以及对西欧的影响,与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周边国家、地区(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影响极为相似。我先是参与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工作,负责撰写阿拉伯文学史部分,后又先后独自编撰《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与《阿拉伯文学通史》,这就免不了要介绍阿拉伯的诗人、诗歌,但如果只是笼统地、抽象地说那些诗人、那些诗歌是如何如何好,却毫不引述人家的作品作例证,或是引述时将人家的原诗译得一塌糊涂,那岂不忽悠了读者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我开始尝试阿拉伯诗歌的翻译。译事难,译诗尤难,犹如戴着枷锁跳舞。阿拉伯语与汉语是世人公认的两种最难学的语言,故而,如果我说翻译阿拉伯诗是难上加难,这大概不能算是危言耸听,过甚其辞。诗究竟是可译还是不可译,译界历来有争议。我认为大部分诗还是可译的,只是觉得不好译,译不好。但如前所述,对于我来说,这却是推脱不了的事。我只能硬着头皮去译,且要本着自己在翻译时的一贯主张——“既要对得起作者,也要对得起读者”,即译出的诗句既要基本忠实原意,还要中国读者读起来像诗,有诗的味道。诗歌讲究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古体诗尤甚,中阿诗歌皆然。译出的诗歌既然想要让中国读者读起来也像诗,那就得按这个标准去努力,去衡量。据此,我译出了《阿拉伯古代诗选》,其中选译了阿拉伯古代130多位诗人的400余首诗。此外,还在上述的《东方文学史》《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通史》中译出不少引述的诗。我自信在翻译过程中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因此结果也颇令我感到安慰。如译艾布·努瓦斯玩世不恭的咏酒诗:“酒袋摆一边,/经书共一起。/美酒饮三杯,/经文读几句。/读经是善举,/饮酒是劣迹。/真主若宽恕, /好坏两相抵。”“玻璃薄薄酒清湛,/两者相似难分辨。/好似有酒没有杯,/又似无酒在杯盏。”译艾布·阿塔希叶的劝世诗:“安在角落里,/乐把大饼啃;/一罐清凉水,/权当琼浆饮。/陋室虽狭窄,/幽然独栖身;/世外小寺院,/正好避世人。/依柱坐下来,/潜心做学问;/往事须反思,/亦可引为训。/胜似宫院中,/奢靡度光阴;/死后受惩罚,/身遭烈火焚。/此为我叮嘱,/谆谆且殷殷;/谁若遵奉此,/幸福享不尽。/劝君听良言,/悯世乃我心。”“人生在世皆会亡,/不分市井与君王。/纵然富有亦无益,/即使贫穷又何妨?”又如译伊本·鲁米描述一个清晨炸馓子老人的诗:“他坐那里颇疲惫,/不忍看他太劳累。/他炸馓子晨光里,/皮薄中空像芦苇,/锅中滚油何相似?/恰如传说炼金水。/面团如银手中出,/变成金网何其美!”这些译诗颇似我们传统的五言诗或七言诗。但我在译诗时,绝不想削足适履,单纯为了追求“五言”“七言”而以辞害意。因为有时诗句过短,意思表达不清楚,那就不如诗句长一些。如我译穆斯林·本·瓦立德的怨世诗:“他们既不清廉又不高尚,/纵然居于我上又有何妨?/烈火上面总是冒有黑烟,/尘土也常落在骑士盔上。”穆太奈比的矜夸诗:“活,不能碌碌无为苟活在世,/死,不能窝窝囊囊不为人知。/纵然在地狱也要去追求荣誉,/即使在天堂也不能忍辱受屈!”艾布·泰马姆的哲理诗:“真主若想宣扬不为人知的美德,/就为它安排好了忌妒者的口舌。若不是火能焚烧它近旁的东西,/沉香木的芬芳岂能为人们晓得?!”
当然,也不必每首译诗都要每句字数一样,长短一齐。如我译乌姆鲁勒·盖斯和祖海尔的《悬诗》,每首都长达100多联句,译成一韵到底已属不易,实在不能做到每句长短一致。现当代的自由体新诗,外表看起来似乎长短不一,也不太押韵,但实际上还是很讲究音步、节奏,且有宽松的韵脚。阿拉伯好的新诗诗人往往都有深厚的传统古诗的功底,因此,译起来也要倍加斟酌,马虎不得。如译尼扎尔·格巴尼的情诗:“你数吧!用你两手的十指:/第一,我爱的是你,/第二,我爱的是你, /第三,我爱的是你,/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我爱的还是你。”阿多尼斯的咏志诗:“先生,我知道断头台/在等待着我,/但我是诗人,我喜欢髑髅地,/我崇拜火……”虽是硬着头皮,我还是喜欢译诗的。译后总要反复读几遍,尽力让它琅琅上口。纪伯伦的《泪与笑》,原文是无韵的散文,我尽力把每篇译成有宽松韵律的散文诗,读起来更上口,更美一些。这大概与我自己自幼喜欢诗,并在中学时喜好朗诵有关。
原载于《文艺报》2012年12月10日。感谢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