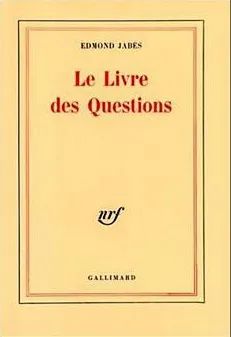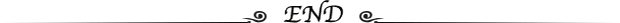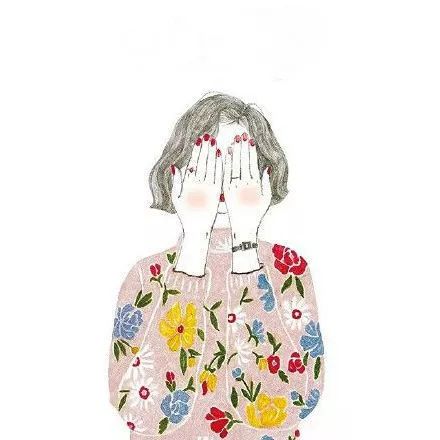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1912—1991)是法国诗人、作家。他出生于开罗一个讲法语的犹太家庭,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流亡法国,定居巴黎,直至去世。他将背井离乡的感受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品中充满了对语言的诘问和对文学的思索,并自觉地向犹太传统文化靠拢。针对阿多诺提出的“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的观点,雅贝斯认为,纳粹大屠杀的惨剧不仅有助于探索犹太人的身份及其生存的语境,也是反思文学与诗歌固有之生命力的重要场域。阿多诺将大屠杀视为诗歌终结的标志,雅贝斯则认为这正是诗歌的一个重要开端,是一种修正。基于这一体认,雅贝斯从1959年起,呕心沥血十余年,创作了七卷本《问题之书》(Le Livre des Questions,1963—1973),并于其后陆续创作出三卷本《相似之书》、四卷本《界限之书》和一卷本《腋下夹着一本袖珍书的异乡人》——雅贝斯著名的“问题之书系列”即由这十五卷作品构成。
沉默是雅贝斯文本的核心。“问题之书系列”所构成的轨迹,详尽地探索了语言与沉默、书写与流亡、诗歌与学术、词语与死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目的,正如雅贝斯在《问题之书》中阐释的那样,不是要屈从于沉默和语言内在的局限,而是要继续书写,对词语与意义之根源进行永无止境的探求。雅贝斯作品风格独特,难以定义和归类。美国诗人、翻译家保罗•奥斯特1992年在其《饥饿的艺术》一书中曾这样评价“问题之书系列”的独特文体:“(那些作品)既非小说,也非诗歌,既非文论,又非戏剧,但又是所有这些形式的混合体;文本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无尽地游移于人物和对话之间,穿梭在情感充溢的抒情、散文体评论以及歌谣和格言之间,好似整个文本是由各种碎片拼接而成,但又不时地回归到作者提出的中心问题上来,即:如何言说不可言说者。这个问题,既是犹太人的燔祭,也是文学本身。雅贝斯以其傲人的想象力纵身一跃,令二者珠联璧合。”
献给拉比诗人们,我藉他们之口道出了我的话语,而他们的名字在历经沧桑之后已化作我的名字;(“假如创造出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忍受同样的苦难,为了到头来让我们接受命中注定的同样的死亡,那为什么还要给我们嘴唇,给我们眼睛和声音,为什么还要给我们全然不同的灵魂和语言?”)
在书中存在。在问题之书中充当某个角色,成为其中的一员;担负起一个词语的职责或一个语句、一个自然段、一个章节的职责。
可以这样宣称:“我在书中存在。书是我的世界,是我的故乡,是我的家和我的谜。是我的呼吸和我的休憩。”我随着人们翻阅纸页而起,随着人们阖上纸页而息。可以这样回答:“我来自词语的种族,我们用词语构筑家园。”我确信这个回答依旧是个问题,确信这个家园仍不断受到威胁。如果上帝存在,那是因为他在书中存在;如果哲人、圣人和先知存在,如果学者和诗人存在,如果人和昆虫存在,那是因为在书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名字。这个世界存在是因为书存在;因为存在意味着与它的名字生死与共。书是书的作品。书是太阳,它生出了大海;书是大海,它发现了大地;书是大地,它塑造了人;否则,太阳、大海、大地和人就只能是无目标的聚焦,是无方向的奔涌之水,是广袤却无存在感的沙漠,是无人呼应的对灵与肉降临的期待,所有这些都没有应和,既无相似物,亦无对立物。于凯尔,你总是活得不自在,你从来不在此处,总是在别处;你不是超过自己就是落在自己后面,犹如秋天眼里的冬天或春天眼里的夏天;你不是在过去就是在未来,就像那些音节,从黑夜过渡到白昼时疾如闪电,与笔端的灵动融为一体。现时对你而言,就是这条迅疾得无从把握的通道。这条通道留给笔的只有或荣或枯的枝叶之词语,只有被投射到未来以求表达未来的词语。你阅读未来,你让我们阅读未来,而昨天,你不在,明天,你不再存在。而你已试图将自己嵌入当下,成为独一无二的此时,那一刻,笔支配着那个将会幸存的词语。你说不清自己的脚步想往哪儿走,也不知道它们会把你带往何方。我们永远也说不清奇遇会在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然而它肯定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开始,在某个更远的确切地点结束。于凯尔,你穿越了梦想和时间。对于那些看见你的人而言——但并非是他们看见了你;而是我看见了你——你是一个在迷雾中穿行的形象。我说“我”时,我非“我”。“我”指的是你,而你行将死去。你已心力交瘁。“我们与众生和万物之间的联系太过脆弱,它们屡屡断裂而不为我们所察。”“一缕气息,一次注视,一个手势,有时甚至是向一道影子吐露的秘密,这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联系之原初本质。”“若我们之间的联系是永恒的,那是因为这种联系是神圣的。”“你试图用写作解脱自己。真是大错特错!每个字词都会揭开一层新的联系的面纱。”你有一个未求而得之名,随着生命的延续,这名字将令你饱受磨难。但到哪个时刻你才会意识到这一点?
(若你的名字只有一个字母,你便站在了你名字的门槛。
若你的名字有两个字母,两扇门会打开你的名字。
若你的名字有三个字母,三支桅杆会带走你的名字。
若你的名字有四个字母,四条地平线会淹没你的名字。
若你的名字有五个字母,五本书会摘下你的名字。
若你的名字有六个字母,六位哲人会解释你的名字。
你有为脸备下的虚空。
“孩子,你名字中的每一个字母都相距甚远,因而你是星夜里的一堆篝火。你会在你的时刻感受到你的称呼的维度,那是你向虚无回应时的痛苦。”“一旦你占有了自己的名字,那些字母便归属于你;但你很快就将沦为这一占有的奴隶。”阿贝拉比的评论:
“作家的生命,要靠他所说、所写和一代代的传承才能显现。假如一句话、一行诗能比作品更长存,这殊遇并非作者以牺牲其他诗行为代价得来,而是拜读者所赐。真相在于,到头来,对谎言荒唐而不懈的追寻,却要我们付出泪与血的代价。”
(“你,相信我存在的你,
我怎好以
涵义多端的词语,
以如我一般
望即生变的词语,
以饱含异乡人
声音的词语,
他在为他的手、为他的笔而写,为抚慰他的双眼而写;如果不写的话,它们将会怎样呢?那么他的笔如今会无法使用,因生锈而窒息;他的手不会反映在任何地方、任何词语、任何字母中;也就无法用墨水即兴发挥出任何意象;至于他的双眼,则会因为面对着阖上的纸页、没有任何文字相邀而迷乱——只有写,才能让双眼在纸页上保持注视。他追随着双眼的历程。他在追问。他无暇回答。有那么多问题从他的舌尖掉头而去,沿着他的手臂冲进他的掌心。有那么多热望压迫着他的笔,给他手指以力量去运笔疾书。路在何方?路永远有待寻找。一张白纸上满是道路。我们知道必须从左向右。我们知道路还很长,知道还要历尽艰辛。而且永远要从左向右。我们早就知道,有时纸页一旦因符号变黑,这张纸就得撕掉。我们还要在同一条路上走上十次、百次;那是他鼻子的路,脖子的路,嘴的路;是他前额的路和灵魂的路。而所有这些路又都有它们自己的路——否则它们就不会是路了。面对眼前已开辟出的路——或可能开辟出的路——我们为什么总是要选那条离我们的目标最远、会把我们引向别处的路呢?我们并不在那儿——但是,或许,我们又在那儿?——除非我们处于心有灵犀或蒙受圣宠的状态,或是灵感在引导我们作出正确的选择——但这太罕见了,确实太罕见了——而那些蒙受圣宠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我是想说,他们在蒙受圣宠时一无所知。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蒙受圣宠往往意味着迷失自己的路,迷失自己熟悉的那条路而去追随另一条更隐蔽、更神秘的路。我们都有自己规划出的路,而在摊开的认知地图上,最长的路其实就是最短的路。对此他最近又有了新的体验。一天下午,他冒险去了荒漠,荒漠向东方延伸,越过了他父母曾经居住过的那个中东国家的边界。因为他需要用风景填补一下自己的寂寞。他驾着车四处乱闯。甚至越过了安全警戒线。在他四周,温暖的夜摘下了自己的手镯和项链——其中粉色的最迷人——他很惊奇,夜竟然可以出现又复消失,可以无限膨胀又遽然变小,小得可以揣进怀里。他很赞赏夜可以是个女人和女性的世界,可以玉体赤裸,又可以星辰为衣。风不时刮过,掠过影子和地表,像个探子似的来去无踪。没有任何征兆说明风会在日出前疯狂地攻击这一片虚空,而他正躲在这片虚空里。没有任何征兆,因为直到那时沙漠都无动于衷。正午时分,他再次发现自己正直面无限,直面一张白纸。所有线索、所有足迹都消失了。被湮没得无影无踪。从到达后搭起的帐篷里,他目睹了风即兴而玄妙的表演——不知帐篷为何没有被它吹走?突然,他听到了风在与沙大笑,在与沙共舞;风戏弄着沙,刺激着沙,又因自我嬉戏和无法尽数的沙粒而发怒,最终,它在自我欲望中变成了狂躁的沙神,驱赶着巨大的有翅造物去征服宇宙。他也许离出发地只有几十公里;但他却不知道。这里又有谁能谈论出发与抵达呢?到处都是遗忘,都是因为缺席而未铺就的床榻,都是灰飞烟灭的国度。对人而言,无论拯救什么,都必得有始有终,一如人的真身,可以重头再来。拯救是能止渴却又需求不止的水;是能充饥并让我们留有饥饿感的面饼,是为人而发芽、生长、成熟并与人相生相伴的那种东西。永恒,无限,它们是果浆和果皮的宿敌。当一切不复存在时,也依然会有沙、会有荒漠去与虚无聚合。在那个不再移动并且不再扎根的内心里,在那个自给自足并挑战理智与季节的内心里——因为荒漠之钥已交付了五大洲——在那个被迟缓逐渐征服而排斥了大海的干燥疆域的内心里——迟缓是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因为它富于静止的激情,早晚有一天,迟缓会在静止中溶化——在那个不可改变且拒绝存在的内心里,生存便意味着要确认极限,因为人就像囹圄中的囚徒,最终会意识到其损失——其损失的胜利。面对一堵高墙,除了推倒它还能做些什么?面对一扇铁窗,除了锯断它还能做些什么?但这堵高墙若是沙墙该怎么办?但这扇铁窗若是我们投于沙上的影子又该怎么办?总之,目标渐行渐远,便意味着停滞。无限拥有那种邪恶的透明。那超越我们之物睥睨我们。那逃避我们之物毁灭我们。每当低飞的鸟群想要观察一下沙丘的形状时,蓝天便会推开沙丘,让死亡占领阵地,用已死而谦恭的地标去迎接它们。不过他倒并没有身处险境。他只能走着去与大海会合,因为他的汽车发动机因沙尘暴出了故障,四轮深陷流沙,对他再无用处。他做出了决定。等太阳落山后再出发。但现在怎么打发呢?天气酷热。他决定先躲进帐篷。他的头很疼。他得每两个小时停下来休息一下。他得相信他自己对方向和捷径的直觉。三月的风很有鹰隼的做派,一旦成帮结伙,就会先啄瞎你的眼,再把你扑倒在地。他想象着一个失明的、一切都在它们摆布之下的世界。他还能找到海滩,找到他的家么?他的心脏有规律地跳动着,就像一泓泉水在他胸口引流架管。他紧紧抓住心脏,仿佛抓住泉水。他紧紧抓住一切征象,抓住生命所有原始的征象。这不幸的人,他丝毫也没料到他正远离自身而去。每次重创之后,就必须恢复生死之间的原始平衡;或向生祭献,或向死祭献,或按照顺序祭献;随死而死,随生而生,直至最后一息,但那并非死的凯旋,而是抛却皮囊:人的躯体。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3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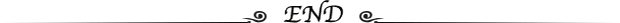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代号2-231
微店订阅

订阅热线:010-59366555
订阅微信: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qikanzhengding@ssap.cn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