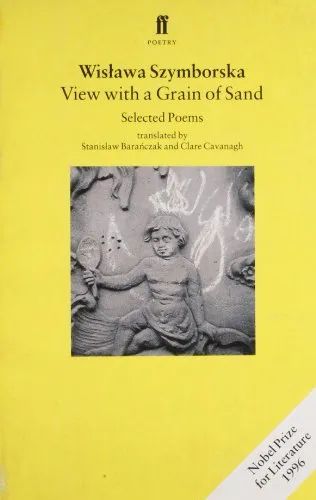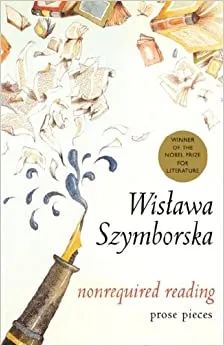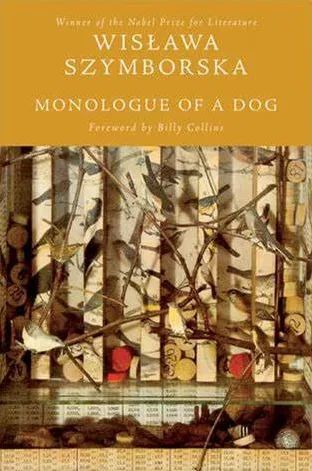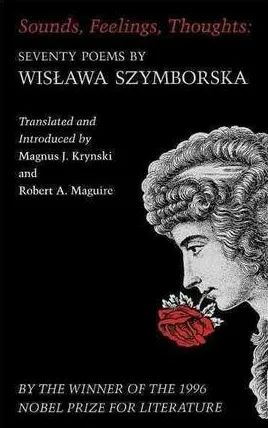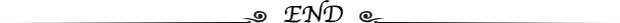但是在诗中,用每个字都要斟酌一下,这就不是普通和一般的了。任何一块石头,任何一片云彩,任何一天和任何一个晚上都不是普通和一般的。维•希姆博尔斯卡作 张振辉译
在演说中第一句话总是最难讲的,我算是已经讲过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话也很难讲,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因为我讲的是诗。这个题目我过去谈得很少,几乎从来没有谈过。我总觉得这个题目我谈不好,因此我的报告不会很长,只要报告不长,一些不精确的地方就会谈得少些。
今天的诗人都是怀疑论者,甚至——也许首先——对自己就表示怀疑。他不愿当众说他是个诗人,就像是这么说有点害臊。在我们这个吵吵嚷嚷的时代,如果缺点已经表现出来,要承认这是自己的缺点并不难,但要说出自己的优点就难得多了,因为它们隐藏得很深,连自己都不太相信……一个诗人在填写各种表格或者和什么人谈话的时候,他不得不说出他的职业,于是便笼统地说他是一个“文学家”,或者再添加一个他完成了什么著作的名称。不论是公务员还是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的旅客,一听到要和诗人打交道,总觉得有点信不过,有点感到不安。我料定,哲学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但他们的情况好些,因为他们常常可以给自己的职业装点一个科学的头衔。哲学教授——这听起来要严肃得多。可是没有诗的教授。这是否意味着,这种职业要求进专门的学习班,通过常规的考试,撰写理论文章,加上生平和注解,还要取得毕业证书?是否意味着,要成为一个诗人,光有几张写了诗的纸是不够的,哪怕上面写了最好的诗,而首先需要一张盖了印章的纸?我们记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俄国诗歌的光荣、后来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被判处了流放。他因为没有一份官方许可他当诗人的证明,被看成是“寄生虫”。几年前,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结识了他。我注意到,他在我认识的诗人中,是一个爱说自己是“诗人”的人。他这么说的时候,一点也不迟疑,而且还带有一种对自由的召唤。我想,这是因为他想起了年轻时遭受过的那些粗暴的侮辱。在一些幸福的国家,人的尊严没有被损害,诗人当然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发表,能够拥有读者,能够被人理解,但他们并不极力或者并不很极力要使自己每天都比别人显得更加突出。在不很久远的过去,也就是在我们世纪最初的那几十年,诗人们都爱身着奇装异服,做出一些古怪的姿态,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在当时对公众来说,是有好处的。可现在是诗人关起门来呆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了,他应当去掉身上所有的打扮,去掉那些美丽的姿态,也不必采用什么诗的道具,一个人静悄悄地等候着自己的发挥,等候着那一张没有写字的纸,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一件最有特征的事,就是现在产生了许多反映学者和大艺术家生平的影片。那些有雄心壮志的导演把真实介绍创作的过程当成是他们的任务,通过创作能够导致重大的科学发现或者产生最著名的艺术作品。在介绍一些科学家的劳动时,要指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实验室、各种不同的仪器、一些开动着的机器,过了一些时候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那种怀疑的时刻是很富于戏剧性的:重复了千百遍的实验只做一点小小的变动能否获得成功?一部关于画家的影片能够反映一幅画产生的全过程,从第一条线到最后一笔。一部关于音乐家的影片表现了音乐,从作曲家听到他创作的最初的一些节拍直到他写在乐谱上的一个完整的作品形式。这种形式虽然还不成熟,因为它没有反映奇特的精神状态,即人们所说的灵感,但它至少是一种人们能够看到也能听到的东西。诗人的情况最坏,他们的工作一点也不显露。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或者睡在沙发床上,两眼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墙壁或者天花板,有时写上七行诗,过了一刻钟后又划掉一行,再过一个小时还是那个样子,谁受得了?我在这里提到了灵感,灵感究竟是什么?如果真的有灵感,现代诗人也作不出明确的回答。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内心的冲动中从来没有得到过好处,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懂,就很难向别人讲清楚。我也一样,我有时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想回避它的实质。我的回答是这样:灵感并不是诗人或者广义地说艺术家们所特有的权利。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批人有过灵感,将来也永远会有一些人离不开灵感。这就是那些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一项工作,并且以对这项工作的喜爱和幻想完成了它的人,他们中有医生,有教师,有园丁,还有千百个其他职业的人。他们如果在工作中不断地遇到新的挑战,那么他们的工作就会永远成为一种冒险,在这种冒险中会遇到困难和失败,但是他们不会失去对它的兴趣。随着问题不断地得到解决,他们又会遇到新的问题。灵感,它究竟是什么?回答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我不知道”。像这样把工作看成是冒险的人并不很多。世界上大部分人工作都是为了谋生,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工作。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他们高高兴兴自己选的,而是生活环境给他们选的。他们不喜欢它,对它感到厌倦,他们之所以重视它是因为它是所有别的人都接受不了的。这是人类最大的不幸之一,而且这种不幸在以后的几百年会依然存在。因此我要说的是,我剥夺了诗人对灵感的垄断权,但我让他们加入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命运之神的选民集团。形形色色的刽子手、专制主义者、狂热分子和煽动分子为了夺得政权,往往借助于高声喊出的口号,他们也爱他们的这项工作,并且尽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去完成它,但是他们“知道”,知道,对他们来说,只要知道就够了。除此之外,他们对别的都不感兴趣,因为别的一切都不利于他们掌握的凭据。可是所有提不出新的问题的知识很快就会丧失它们的生命力和它们对生活的热情,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知识能够使社会遭到毁灭。所以我对“不知道”这几个小写的字评价很高。这几个字虽然是小写的,但它们却长上了坚强有力的翅膀,给我们开拓了新的生活领域,给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地球扩大了存在的范围。如果伊萨克·牛顿没有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一个苹果在他的果园里落地在他看来就像掉下一个冰雹一样,最多也只不过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下去。如果我的同胞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没有对自己说“我不知道”,她肯定只能当一个化学教师,教那些良家妇女,靠薪水吃饭,庸庸碌碌地度过她的一生。但她毕竟对自己说了“我不知道”,这几个字两次把她送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给那些永远怀着不安心情进行探索的人们授予诺贝尔奖的地方。诗人也是一样,如果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就应当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他在他的每一个作品中都想这么说,但是当他给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就犹豫了,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说法,这么说是绝对不够的。他只好再说一次,再说一次,然后提出一系列自己不满意的理由,文学史家于是给他的作品夹上一个别针,称为“成果”。我有时想到过一些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假如我曾大胆地幻想我和埃克列兹亚斯塔(传为《圣经·传道书》的作者。)谈过话,这也是一位哀叹人的一切行为都毫无价值的诗人,他是最重要的诗人之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因此我向他鞠了一躬。后来,我抓住了他的手对他说:埃克列兹亚斯塔!你说过,太阳之下决无新事。可你自己不就是在太阳下面诞生的一个新的东西吗?你写的那首长诗就是在太阳下面产生的一首新的长诗,因为在你之前谁都没有写过这样的长诗。你的读者也都是一些新的读者,因为他们在你之前没有读过这样的长诗。还有这株柏树,你坐在它的阴影下,但它并不是世界诞生时就生长在这里的,因为那时候这里还有一株柏树,它和你见到的这株柏树很相像,但它并不是这株柏树。埃克列兹亚斯塔!我还要问你,在太阳下面,你还打算写些什么东西呢?你是不是脑子里已经想好了?是不是还要否定其中的一些?你在前一首长诗中见到了欢乐,可这是不是昙花一现的欢乐呢?关于欢乐,你是不是还要写一首新的长诗呢?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笔记,或者已经写了一些段落呢?你大概不会说“我什么都写了,不用再补充”吧?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这么说,更何况像你这样伟大的诗人呢!我们对世界的巨大和我们自己的弱小都感到害怕,尤其是我们看到它是那么不关心人们、动物甚至植物的痛苦,更觉得它太残酷无情了,但我们为什么认为植物可以避免这种痛苦呢?我们想到了星星的火焰照亮的天空,在这些星星旁边还有一些行星,那么为什么这些行星是死的呢?难道它们真的没有生命?我不知道。我们既然得到了进入这个无限广阔的剧场的入场券,关于这个剧场我们就什么都可以说了,只可惜我们的入场券的有效期太短了,它只限定在两个日期之间。关于这个世界我们还要说些什么呢?那就是它令人惊奇。"令人惊奇"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圈套,因为只有那些脱离了众所周知而且得到了普遍承认的规范的东西,那些不符合我们的习惯因此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才是令人惊奇的。这么说来,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惊奇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它并不是和什么比较而产生的。是的,如果用一般的表达方式,就不需要仔细地考虑每一句话或每一个字,我们大家都用这么一个说法:“日常生活”“普通世界”“事物的一般顺序”……但是在诗中,用每个字都要斟酌一下,这就不是普通和一般的了。任何一块石头,任何一片云彩,任何一天和任何一个晚上都不是普通和一般的。首先,这个世界的存在不属于任何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又译辛波斯卡,1923—2012),波兰女诗人。主要诗集有《我们为此而活着》(1952)、《询问自己》(1954)、《呼唤雪人》(1957)、《盐》(1962)、《一百种乐趣》(1967)、《以防万一》(1972)、《大数字》(1976)、《桥上的人们》(1986)和《结束和开始》(1993)等。她的早期作品以战争和波兰战后和平建设为题材,反映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后期创作接触到了宇宙、世界、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题材,主要对世界从远古到现今的发展过程进行哲理的探讨。1996年,她以“精确和讽刺揭示了人类现实片段中的生活和历史活动的规律”获诺贝尔文学奖。
《诗人和世界》是希姆博尔斯卡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词。
2018-2020年《世界文学》公众号推送的波兰文学作品一览表:
两刊联动〡奥•托卡尔丘克【波兰】:房号
第一读者|奥•托卡尔丘克【波兰】:马
小说欣赏 |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波兰】: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时间(节选自《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小说欣赏〡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波兰】:世上最丑的女人
第一读者〡亚•扎加耶夫斯基【波兰】:轻描淡写(诗论节选)
诗歌回响〡亚•密茨凯维奇【波兰】:爱情十四行诗选
小说欣赏|波•普鲁斯【波兰】:一件背心
诗歌回响|莱·斯塔夫【波兰】:基础
小说欣赏|斯•姆罗热克【波兰】:实用的半身铠甲
小说欣赏|亨·显克微支【波兰】:奥尔索(上)
小说欣赏|亨·显克微支【波兰】:奥尔索(下)
诗歌回响|维·席姆博尔斯卡【波兰】:我太接近了
诗歌回响|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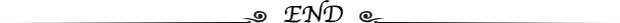

责编:文娟 校对:博闻
终审:言叶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