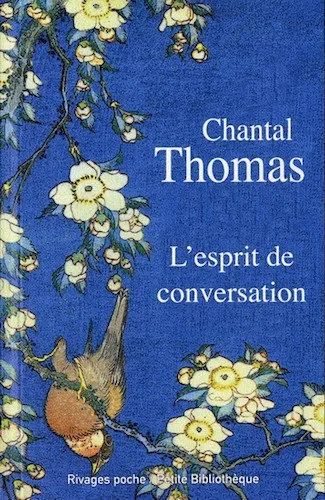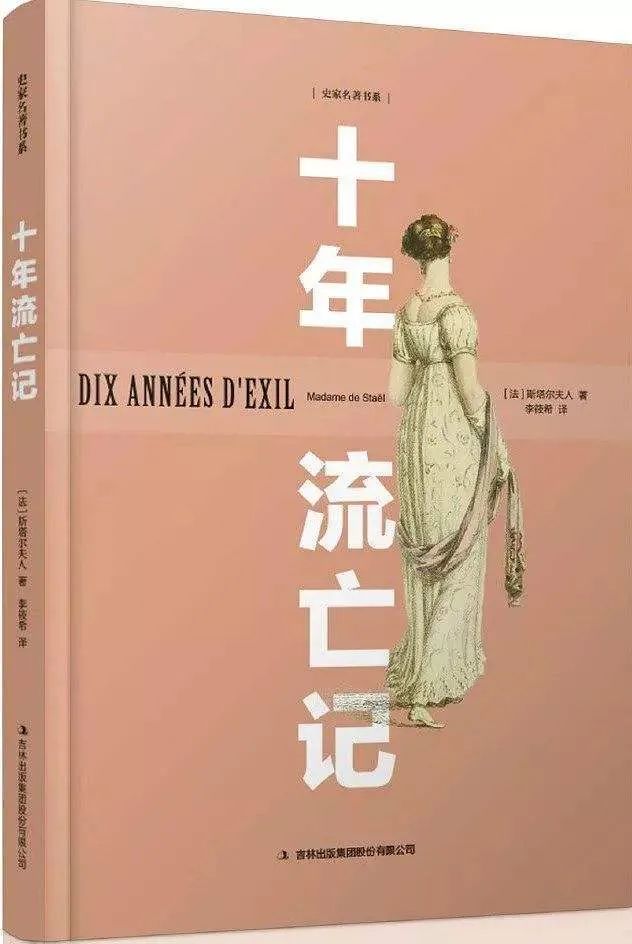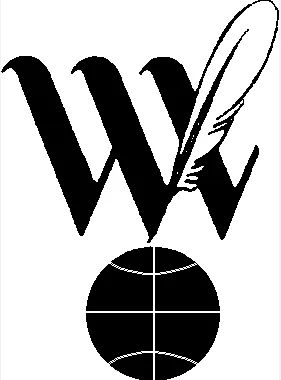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文学沙龙
“沙龙”这一独特的社交形式,在法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方面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历代法国文学对于“沙龙”的种种描述,也使“沙龙”蒙上了一层法兰西式传奇浪漫的面纱。
《谈话的精神》是沙龙的旧事,也是女性的传奇,更是一位历史学家对当今时代的质疑与反思。尚塔尔使我们看到科技的进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交流方式,我们却越来越丧失了表达与沟通的能力,缩略语和电报文体的信息充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香气的灵魂”变得越来越少,“我们甚至做不到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友好地交谈几句”。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使“沙龙谈话”这种交流的形式一去不返,然而斯塔尔夫人在18世纪所面临的女性的“两难窘境”,至今仍未改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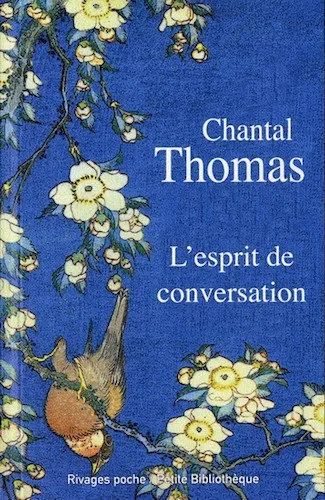
在“谈话的精神”背后,尚塔尔透过历史照进现实的沉思,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的交流方式与生活方式;更在“沙龙女主人”这一浪漫而使人充满幻想的称呼之下,让我们关注到时代变迁中女性命运未曾改观的无奈现实。
绝对的益处

凭借童年时代的沙龙经验以及卓越的语言天赋,斯塔尔夫人对有关谈话的诸多负面评价提出了反对意见:——对于爱情的孕育来说,谈话是一件枯燥且使人变得枯燥的事,百害而无一利。这是浪漫主义的观点。音乐和歌曲才会传递爱情。沉默——出于选择或是出于必须——也可以传递爱情,因为恋爱使人失去语言。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一切正相反,我们可以谈论爱情,爱情也会丰富谈话的内容。通过为谈话辩护,斯塔尔夫人也坚信爱情之愉与心智之悦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一种从肉体到精神的联系。——与哲学或政治相关的严肃谈话是男性的特权,女人们只会喋喋不休的唠叨。斯塔尔夫人本人极具语言天分的存在便是对这种观点的反驳,而她的政治才华也有效地打破了这种观点中的禁忌。女人不应满足于默默无语的角色(这种沉默很容易转向或反向变成总是被嘲笑的女人的唠叨)。女人不应惧怕掌握话语权和通过话语表达自己。斯塔尔夫人对平庸的资产阶级世界感到厌恶,因为在他们的家庭结构中男权占有统治地位。在《柯丽娜或意大利》中,斯塔尔夫人以辛辣的笔触描述了一个英国家庭的茶点时间。那是一个精神贫乏的清教主义小团体:“它[小团体]由七位最为严肃认真的外省女人组成,她们其中的两位是五十岁的老小姐,像十五岁少女一样羞怯,却远没有十五岁少女的愉悦。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亲爱的,你觉得水已经足够热,可以泡茶了吗?’‘亲爱的,’另一个女人回答道,‘我想时间还太早,因为先生们还没准备好过来。’‘他们今天会在餐桌上耽搁很久吗?’第三个女人问道,‘您觉得呢?亲爱的?’[……]每隔一刻钟,就会有个声音问起最乏味的问题,最终得到一个最冷漠的回答。内心涌起的厌倦之情,又带着一种新的重量落回到这些女人身上。如果不是始自童年时代的习惯教会了她们凡事忍让,人们会觉得她们是不幸的女人。”斯塔尔夫人捍卫某种自由,一种可以打破顺从和沉默——或者比沉默更可怕的某些东西:贫乏的话语、屈从的社会地位——的自由。柯丽娜从这样的地狱中逃脱了出来。她逃脱了在婚姻奴役基础上被缩减为品茶仪式的生活,逃脱了尊崇各种常规、憎恶天分的生活,这种对天分的憎恶,在经过反复灌输后,很容易导致对自我的厌恶。这种生活不是通过自身能力的发展,而是通过自身能力的“消除”而持续下去(这里我们借用了托马斯·伯恩哈德的题目。此外,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英国的外省和托马斯·伯恩哈德笔下的奥地利一样,是具有毁灭性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意大利都代表了自由、逃避、鲜活的空气。)柯丽娜选择了意大利或是自由,但是像德尔菲娜一样,这种自由是难以被容忍的。柯丽娜和德尔菲娜遭遇的不幸便是社会的惩罚。这种惩罚是因为她们(轻微地)超越了革新的程度,因为她们比普通女性多了少许的天分,因为她身上的激情会使她们与思想、政论、价值等领域直接产生关联。这样既热情又个性分明的女性是危险的。她们身上带有反抗的萌芽,对她们的姐妹们来说,她们都是坏榜样。因此应该远离这些会说话的女人。男人们被德尔菲娜和柯丽娜所吸引,同时又因为爱上她们而感到恐惧,因此德尔菲娜和柯丽娜最终都被恋人抛弃。对于当权者来说,这种女人是一种威胁。斯塔尔夫人总是将谈话与巴黎联系在一起:“我的沙龙又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我又寻回了谈话的快乐,我承认,在巴黎和大家谈话,对我来说曾是比一切都更有趣的事。”斯塔尔夫人被拿破仑判处流放,她试图在科佩重建巴黎的沙龙,最终她清楚地看到这是不可能的。布瓦涅伯爵夫人如是说:“这种重建,唯一不能替代的是,人们一旦具有了某种品味,便只能在法国,且只能在巴黎才能够寻回这种品味。斯塔尔夫人已经在流亡带给她的极度痛苦中提到了这一点。”
专制而厌恶女人的拿破仑,是一位审查大师,他只会拒绝斯塔尔夫人这样的女人:“波拿巴政府的特色,是对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深深蔑视。”斯塔尔夫人没有写过谈话教程。她本人对于那些需要遵守的规则都并不关心。她不仅会在犯错的时候自嘲,还特别欣赏灵敏的应答,这就会引出一个必然的后果——打断别人的话。她对德国式的礼貌习以为常,同时也慨叹这种礼貌使人厌倦。这是一种由语法规则强加的礼貌!“这样,在法国由于打断别人而使谈话变得妙趣横生的乐趣,抢先说出重要部分的乐趣,在德国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德语中的句子开头在没有结尾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必须给每个人留出他们所需的足够的空间,这对于事物的本质来说是很好的,也更有礼貌,却没那么有趣。”而邦雅曼·贡斯当却对这种缓慢表示赞许:“德国式的谈话,即便不是文人的谈话中,也有着某种情理和冷静,我觉得这是德国式谈话的优点,也是法国式谈话的不足。”斯塔尔夫人相信谈话的启发作用。她喜欢在话语中自失于虚空的感觉,喜欢边想边说的方式。写作对于她来说,需要某种精力与冲动。在话语中她以一种自失的方式去表达,却依然没有失去自我。卢梭曾在谈话中,尤其是在沙龙这个封闭空间的谈话中——更甚的是在巴黎沙龙的封闭空间中的谈话(如果想再越过一个恐惧等级的话)——感受到一个使人感到羞辱甚至致命的空间,尤其是,正是为了抵抗这种浅薄与软弱,他写下了著名的《新爱洛伊丝》,叔本华借鉴并夸大了书中厌恶女人的思想。普鲁斯特与他们并不相同,他选择了卧室而非沙龙,写作而非话语,但同样也以某种视角对沙龙与谈话进行了谴责。与卢梭正相反,普鲁斯特极具谈话的天分,他却退而选择了词句的沉默。他选择了深层的自我,与深层的自我进行对谈,而非表层的自我,即那个在维尔杜兰夫人家中浪费才华的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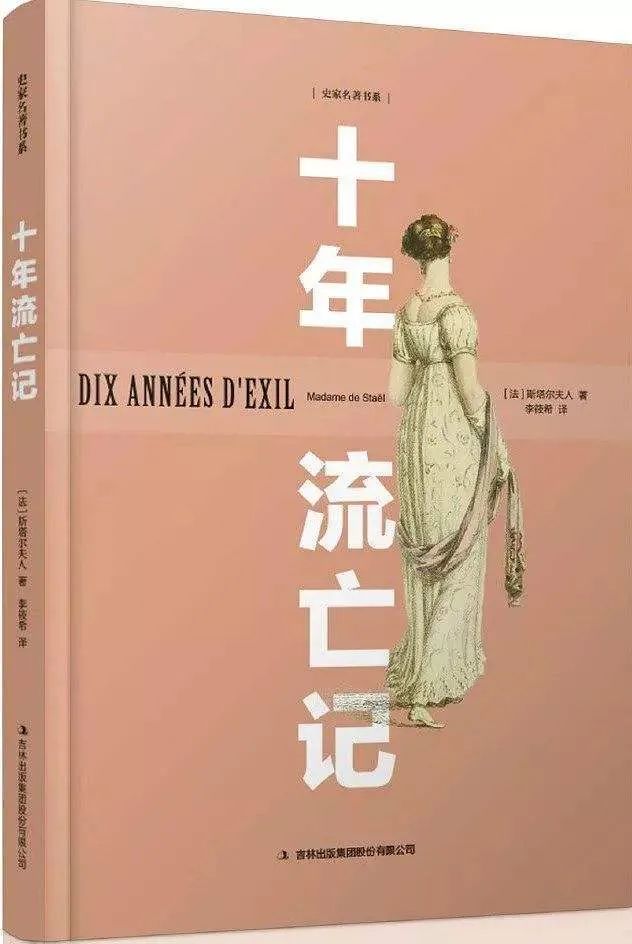
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这种区分与对立并无意义:谈话完全是有益的。您想要光彩照人,它便会令您万般迷人,充满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引导您超越自己。在《论谈话的精神》中,斯塔尔夫人描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升华:“一席活跃的谈话令人感受到的惬意,确切地说并不在于谈话的主题。我们在谈话中展开的思想或见解并不是谈话的主要兴趣点,谈话的趣味在于谈话双方以某种相互影响的方式,反应迅捷、相互愉悦的方式,不假思索、享受即时的自我的方式,不经意便得到赞赏的方式,通过语气、手势、眼神在各种细节中展现其精神的方式,总之,是一种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某种类似电流之物的方式,其火花的喷射,会使一些人从极度暴躁中解脱出来,也会使另一些人从恼人的情感淡漠中清醒过来。”谈话使人们不会发疯,不会成为灵魂的“囚徒”。对于很多人来说,斯塔尔夫人对疯狂的恐惧,是归因于她对孤独的畏惧。谈话并不是写作的敌人。在谈话与写作之间,有一种循环、激励和产出的关系。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一些趣闻的出现,据说斯塔尔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会聚在一起写作而非谈话。他们当时住在布洛瓦附近的城堡里。“晚饭后,我们打算围坐在一张绿桌子旁,一起写作而非交谈。这种变化多样的面对面的方式,让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有趣,我们迫不及待地离开谈话的桌子,过来写作。”他们玩起了“小邮局”的游戏,沉浸在短笺的写作中,且静静地相互传看。或者正相反,在《柯丽娜或意大利》中,有一个探访维吉尔之墓的精彩片段。维吉尔诗歌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就像一个声音正在和我们对话。柯丽娜和她的恋人一起在维吉尔的墓前沉思:“面对这个充满荣誉的墓园,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们回想着诗人的天分恒久贡献出的思想与画面。这是一次与未来人的绝妙交流,那是写作的艺术使之历久弥新的交流!” 尚塔尔·托马(Chantal Thomas,1945— )是法国当代作家、剧作家、历史学家,2002年凭《作别王后》一书获费米娜奖。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4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责编:文娟 校对:丹霞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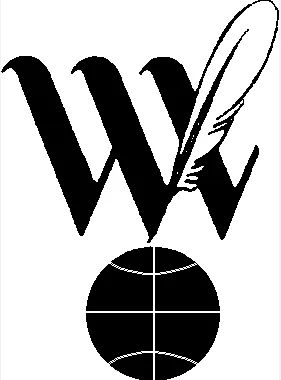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