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 | 史·海顿【加拿大】:亡者更惹眼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亡者更惹眼
史蒂文·海顿作 丁林棚译
上夜班意味着多拿半份工资,但在一月份这些天,即便不加工资,她也情愿在公园这边干活,给溜冰场喷雾制冰。她一个人工作,乐得个清净。在和冰场取暖室相连的狭小办公室里,她放了一个保温瓶,里面盛着咖啡,添了不少甜味剂。此外,她还放了一个新买的CD收音机、几本杂志和一本恐怖或浪漫小说。夜班结束时天还黑着,她会把这些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装在一个帆布包里带回家。朋友们常常问她会不会很寂寞。当然了,有时会这样,但如果你夜里别无选择,只能一个人待着,还不如有份活儿干,多挣一半的工资,总比一个人躺在床上好很多。
一个人工作省了不少麻烦——省得应付老板,也省得听同事们怨天尤人,还不得不表示声援。艾伦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但他们之间却常常感到不快,谁愿意和这样一群人待在一起呢?她总觉得,与人相处是件自然的事,不晓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烦恼。而现在,独处也许不是最佳选择,却让她常常备感轻松。事实上,在先前的几份工作中,老板们总是从她背后盯着她,不时地摸一摸她的肩膀。这种探摸几年前开始逐渐消失了。她不怀念那些亲密的手,尽管有时她确实怀念那种眼神,那一束束毫不掩饰的饥渴的目光,是那种目光定义了她的豆蔻年华和青春岁月。不过,她从来没有像她的一些朋友所说的那样感到独处有多么艰难。如果你和众人相处得好,你就和你自己相处得好。她认为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天生就很适合这个阶段的生活。以这种视角来看就对了。

在那根孤零零的荧光灯下看一两小时小说后,她会根据夜间的冷暖再次打开水,戴上羊毛手套,在外面套上一副工业用橡胶手套,然后出门第二次给冰面喷雾。在喷完第三轮或第四轮后,黎明降至,夜间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每个公园要把冰场铺好,准备就绪,至少要花上三个冰冷刺骨的夜晚,然后就是大量没日没夜的维护工作。这个公园的非官方名字叫骷髅公园,十九世纪时一直是城市的主要墓地。骷髅公园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她喜欢这里的办公室,比起其他更宽敞办公室里的踢脚线电暖器,她更喜欢这里的暖气机,像烤火一样。这里差不多就是她长大的地方。当然,一切都在变化。大量学生和年轻从业人员搬到了这里,租下公园四周的旧房子加以整修。漂亮的维多利亚红砖墙让公园有一种体面的假象,因为就在不远处是拥挤的街道,两侧林立着数百座没有院落的小房子,外层是铝制材料。此外,还有低矮的砖结构公寓楼,墙面像胆汁一样发黄。她就是在其中一所小房子里长大的,四十年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这里滑冰。
严格地说,她仍然有一个老板,但在这里,她从不需要和他打交道。不是说他故意找茬让她不好过。他们相处得很好。他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矮小,体格健壮,走起路来神气活现。他曾经是国家冰球联盟的选拔队员,不过究竟是哪一支冰球队,她从来没记得住。他对她就像对一个男人一样,甚至在和她说话时也总是以“哥们”相称,尽管他并没有真正叫她“男人”。当然,哥们。哥们,我真希望我能告诉你。今年冬天你想去骷髅公园,哥们,随你怎样都行。或许他认为,任何人只要比他块头大不少、强壮许多,怎么讲也应该是个男人。艾伦不仅体格结实——这是她前夫暗含讽刺的夸奖——而且身材高大。在她出生的这个小镇的另一片,大多数女人在三十来岁时都骤然变得五大三粗,体重很快就超过她们的丈夫。男人们则瘦得只剩一根筋,满脸皱纹,粗糙皮肤泛着红,好像用砂纸打磨过似的,他们的眼神如游魂般变得猥琐不宁、无所遮蔽。艾伦很幸运没有长出姐姐们那样臃肿的满月脸,只见她脸上的肉越来越厚,越来越男性化,而她的身材也更加结实,发福了将近一倍,就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勤劳农妇。

最近几天晚上,她并不孤单。在用低矮挡板围起来的简易溜冰场另一侧,一个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结满冰的柏油路旁的路灯下。他已经在那儿站了三个晚上。他背朝溜冰场,面对着石灰岩方尖碑。那石碑高二十五英尺,居高临下地俯瞰公园的这一侧。他没穿运动服,只戴了一顶棒球帽,上身穿一件棕色短皮夹克,下身套着蓝色牛仔裤,脚上穿着工程靴。气温大约在零下十五度。头一天晚上艾伦喷洒溜冰场时,他曾和艾伦说过几句话。当时她在溜冰场的西北侧干活,正好离他较近,稍稍抬高一点嗓音就可以彼此交谈。她不断地来回挥舞着喷头,在不断变硬的冰层上一层层喷水。他时不时地朝方尖碑走一两步,停下来,然后恢复僵硬的姿势。他好像在用眼测量那方尖碑。随后,他又后退了几步,向旁边跨出一步。她并没有特别留意,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这个公园以各种怪人怪事闻名,就是个露天旅馆,住满了吸毒者、假释犯、改造人员、精神病人。这里是形形色色怪人的流动站,只是他们大多不构成社会危害。
他飞快地把头扭过去看着她,就像一个投手在估量一垒跑垒员的速度一样。他的帽檐遮住了脸,不过她能看到他修剪整齐的浅色胡子。他长着宽厚的肩膀,身材挺拔。
“你见过奇迹吗?”他问。
又来这套了,她很宽宏地心想。然后,她用一种亲切友好的语气,也就是她在挑起话题时常用的那种语气说道:“这取决于你的意思。你在那里不冷吗?”
“必须把它移走。”他说。他的声音很温和,充满理性。
“什么,那个方尖碑吗?”
“这是一块墓碑。他们讨厌它竖立在这里。它总是压着死去的人。”
“你一直在跟他们交谈?”
他羞怯地歪歪头。“只能说,我听到他们谈论这事了。他们有两万四千个人。”
“这好像不可能吧?”她说,“在这么大一片空间里。我听说的数字是三万。”
“死人比我们更惹眼。他们对这片地有合法权利。他们共有两万四千人。他们讨厌那个墓碑,因为它违背民主意志。”
她第一次读到方尖碑上的匾牌是在六十年代,那时她还是一个孩子。一八二六年,教区居民就地选材用石灰石建造了这座方尖碑,以纪念“在生命第三十个年头”离世的牧师。艾伦从幼年到少女的那段时间,这座方尖碑一直是居民区的一个特色象征,人们可以用雪球砸它(如果你砸中尖顶得两分,砸中尖顶下的石球得一分)、拿它开玩笑(有点像一个勃起的阳具,匾牌上还刻着字,耸立在那里)或爬上方尖碑(每隔几年就有人从上面的三角墙上摔下来,摔断胳膊或摔出脑震荡)。现在,她猜自己明白那个男人说的是什么了——所有的墓碑早就没有了,一个多世纪前就被人从地里像拔牙一样移走了,而这座纪念一个人的石碑依然高高耸立在公园中,统治着挤满公园的那一堆堆无形的死人。

“我可以用意念移动物品,”那人说,“我常在厨房餐桌旁这样做。如果我使劲盯着这块墓碑的话,我就能移动它。我需要把角度调整对。它的重负死者无法承受。一旦我搬开它,我就会让它消失。我能让物体消失。”
在帽子遮盖下,他的脸黑黢黢的。“那些逝者想要这块墓碑移走,并让它消失,”他说,“要是像今天晚上这样,这可不是我乐意做的事。”
“是啊,太冷了。”她说。
他盯着她看了好久。
“好吧,祝你好运,”她对他说,“我是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现在得到那边去了。别冻着!”她往喷头端拉了几下软管,滑动着走到远处的挡板处,绕过刚刚浸湿的地方。
“我还能看出一个人的好坏,”他对她喊道,“我只要一看他们,就知道他们的一生!”
她回过头来冲他咧嘴笑了笑——谁能对这样的暗示置之不理?如果这算是暗示的话。
“那么,我是什么样子的人?”
她的目光与他相接。他眼神专注,仿佛眼前看到的是一片空白。她从来没有觉得与人四目相对会有多难,即使在孤独或受伤的时候也是如此。她没有负罪感。
“你是个好人。”
她又笑了笑,“谢谢。注意别冻着。”
现在是喷洒冰面的第三个晚上,凌晨两点。墙角和围板处还都有不少活儿要干,这些地方的冰总是起褶皱或者像卵石一样凸起。曲棍球场地的中间仍然是凹陷的,还需要用软管再喷一千升水。不过,两个场地一大早一定会就绪的。开始的时候,那个人还没在这里。大概半小时后,他出现了。她只能猜测时间,因为她没有听到或看到他来。如果这是她的恐怖小说里的一个场景,他一定是从旧墓地钻出来的一只厉鬼。她一直忙着在来回松动水龙软管,脑子里则浮想联翩。这是夜里特有的想象,和白天的想象不同。夜里的想象常常漫无边际,一会儿拐弯,一会儿入地,一会儿折返;而白天的思绪只会飘向那些更为现实的地方。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了,面对着方尖碑,只是今晚离方尖碑更近了些……第二天晚上,他们只是互相打了声招呼,仅此而已。她感觉到,他越来越认真,越来越专注了。或许他也越来越沮丧,或者说是越来越害怕失败。疯子是否会像理智的人那样害怕失败呢?她现在想到了加文。他的那些事都很短暂。他的离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让一个身不由己的男人感到自己很重要,这是一个没法完结的使命——不过她也想他。她想念那些夜晚。有那么一小阵子,她反复思考为什么自己晚上会想念加文。这时,她抬起头来,听到几声醉醺醺的嘶哑的叫喊声。三个小青年貌似正穿过巴拉克拉瓦街,朝这边的小路走来。她很高兴那个男人今晚不在这条路上。她在这里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一眼就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三个小青年看起来就像亡灵之神,穿得松松垮垮的,没有露脸,上身裹着一层又一层的黑色蓬松连帽衣。其中一个人的运动衫外面又套了一件摩托车夹克。不出所料,他们在离那人后面不远的小路上懒懒散散地停了下来。那人正背对着他们,显然毫无察觉。三个小青年中有一个又高又瘦,手里拿着一把铁撬。她趿拉着脚从围板后面走出来,站在冰场之间的空地上,让水喷到连接两处的冰面上,时刻注意着事态的发展。

他们开始奚落那个人,但声音微弱含糊,一开始很难分辨。那个人没有动,也没有回头看。或许他已经陷入了冥想,或者感觉自己成功在望。那个穿摩托车夹克的小青年正在慢慢靠近他:“喂,伙计。我早就听说过你。”他的声音比其他人更干脆、更清晰:“喂,不如盯着这个看,伙计。”他从背后推了那人一把,但并没有用多大力,那人开始慢慢转动起来,从腰部向上旋转。过了一会儿,他那张被帽檐遮住的黑黢黢的脸歪向了一侧,像一只迷惑不解的狗。
“别碰他。”她喊道。
连衣帽遮蔽的几张脸齐刷刷转向她,像动画片里一样。在别的场合下这情形会很滑稽。那个人转动的身体又恢复了原来的姿态。穿摩托车夹克的小青年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径直向她走来。她心里一阵恐惧。剩下两个人跟在他后面,动作松散而凌乱——他们到冰面上时会遇到麻烦。她转过身来面对他们,看着他们从昏暗的路灯下朝她冲过来。她把软管水龙带的控制环拧了半圈,以减少水流,让水冲到她面前的冰面上。软管头是钢做的,有半英尺长,它顶端变细,形成一个凸缘孔,直径为一英寸半。
“他是你的朋友?”为首的那个一边靠近,一边向她喊。
加文处理起对峙局面可是行家,他经常就如何处理这样的局面发表见解。你不要打口水战,他经常这样说——仿佛她真的很在乎他的意见似的。你让对手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让他说个够,泄掉他的威风。你保持冷静,沉默,和他对视。
“我想你们一定是朋友了,”为首的那个喊道,“你们两个都不说话。”
“你说什么?”高个子说。
“那个雕塑和这个人肉洗冰车,”为首的说,“他们是朋友。”
另外两个同伙笑了起来,那声音很粗俗,流里流气的。他们进入了冰场附近的灯光区。他们不是少年。从远处看,宽松的连帽衫使他们身材更矮小,更年轻。他们二十来岁。那个高个子拿的不是一根撬棍,而是木槌或雪橇的木柄。为首的那个继续向前走着,把双手从口袋里掏出,慢慢地把兜帽往后拉了拉,他的动作充满一种走样的仪式感。他闭着双唇微笑着。有那么一阵子,他的脸成为她目光的全部焦点。他出奇的英俊。一股心荡神摇的冲击波伴随着另一阵恐惧的痉挛直冲而下,击中她的子宫,这是一种孪生的震撼,它们彼此交融,共同作用于她。那张脸残忍而又英俊。浓密的眉毛,高高的颧骨,帽子遮住的灰色眼睛,丰满的嘴唇外面还有一圈胡茬,深色的头发剪得很整齐,头骨上有一块节疤,仿佛肌肉瘤。她在胸前慢慢地挥动着水龙带。三个人在浸湿的冰块边缘停了下来,就在水流来回冲刷的地方不远。他们的运动鞋和裤腿下部都溅上了水珠。
“你在和我们说话吗?”他的声音很深沉,但带着刺耳的鼻音,和那张脸很不般配。
“我说过,别碰他。”
“不管怎样,我们想看的是你。”那人抬起头来看着她。过了一会儿,他那平缓的眉毛微微皱了一下,眼睛睁得更大了。他明白了一切。他什么也没说。说话的是第三个:“这……她是个女人?”他是个矮个子,佝偻着身子,脸上长着麻子,看上去是三个人中喝得最多的那个。
“我不知道,”为首的说,“你自己问问她。那边那位,你是女士吗?”
“我他妈的从没见过女人在溜冰场干活的。”
“我见过她,”高个子说,“去年她让我离开冰面,叫我滚蛋。”
“去年我还没到这里来。”她说。
“在另一个公园里。沿巴里街的那个。”
“好吧,我想是因为冰还没有准备好。”她说。她满怀希望地朝疯子瞥了一眼。他根本没有在看这边。她应该撤回到小屋里报警。可是她做不到。她腿脚太慢,好几年都没有跑过一步了。在外面,至少有水龙带和湿冰把她和那些人隔开。
“看起来准备好了。”第三个说。
“什么,她?”那个高个子傻傻地斜着眼说。
“冰。”
“检查一下,扎克。”带头的那个说。矮个儿扎克试着在积水区另一侧的冰面上滑行。他的动作太快,双脚陷进冻结的冰水之中。他开始向前倾倒,胳膊乱舞,身子重重向后摔下去,到了肘部和屁股。你可以听到他的骨头撞击的声音。他翻过身来,趴在冰面上,用手和膝盖撑着身子,垂着头一动不动。
“好了,你现在可以起来了,”她说,“你们干扰了我的工作。你们应该离开了。”
“我们想先看看你的办公室。”为首的没有理会他受伤的朋友,接着说道。
“我不会让你看的。”
“我们已经到另一个公园的小屋拜访过了。就是在高地的那个公园。”
“那是肯定的。”她说。
“你认为我在撒谎?”
他的脸色苍白。他仿佛准备拔下头皮来为自己作证似的。沃尔特·昂格,那个说起话来很腼腆的矮个子烟鬼,就在里德奥高地的溜冰场当喷雾工。
扎克此刻已经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揉着浸湿了的肘部,一副受伤的小男孩的姿势。他愤怒地皱着眉,却怯生生地瞥了一眼冰面,好像它是个活物,只要他一动就会把自己铲倒。“臭婊子。”他说,不过似乎不是针对她。很好,她没有必要回应。
“我们走吧。”为首的说,有一瞬间,她以为他是在对同伙说话,要他们离开这里。可是她感到那冷酷的目光深深地刺进自己的双眼。
“带路。”他说。
“如果我进了那边的办公室,就得报警了。那里什么都没有。你认为我们有人会带钱来这里上夜班吗?”
他似乎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他说:“你那位朋友在另一个溜冰场工作,就是这样做的。”
“怎样?”
“带钱来。”
“我对此非常怀疑。”
他的脸色更白了。“让我来告诉你,”他皱着眉头说,好像刚刚得知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你真是个傻叉。”
“你说什么?”
“傻叉。”
扎克的笑声在寂静中回荡。傻叉。不是X,不是XX,也不是XXX。加文从来没有像他家里其他人那样服过刑——他相继经营过音像店和街角商店,尝试过特许经营,但都失败了——但他的一些儿时的朋友都进过局子,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里面的专家。傻叉,他对她说,用来称呼囚犯,是最糟糕的。操你娘的、丧家子、混蛋、狗屎,这套词都会让你惹上大麻烦,毫无疑问,但傻叉是最糟糕的。也许是因为感觉太傻了。如此轻蔑。毕竟,一个“操你娘的”可能会操你娘,操你奶奶,操你祖宗。一个傻叉才是真可怜的。也许对面那位帅哥也进去过。他一定进过牢。他知道怎么用这个词。但是这个词让她感到恼火,更让她气愤,她猛地把控制环完全打开,用软管对准他。她用戴手套的大拇指把管嘴拧小,这样就可以喷得更猛烈。她也许更喜欢“婊子”这个词。婊子至少是一个女人。即使是胖婊子。拉拉中的男人婆。任何这样的称呼都行。“傻叉”比被人忽略更严重,比被看穿或者无视更糟糕。这样的待遇她经历得太多了,不过,就这样吧,她都可以接受,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心理伤害而已,有比这更严重的。她从膝盖往上把他浇了个透,时间很短,但很彻底,最后她开始浇他的脸——她是多么讨厌那张如雕像一般趾高气扬的脸!然后,她把水龙带转过来对准那个高个子,不过他和扎克迅速后退,离开了冰面。

她与他短兵相接,但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麻木而迟钝。来袭者的脸猛地低了下去。软管水龙带好像卡住了。她惊慌失措地向后拉,他扔掉碎冰锥,跪到在地,伸手去摸他的脸。另外两个人停下来,僵在原地。
“夏恩?”高个子压低了声音说,“她把你怎么了,哥们?”
他发出嘶哑而尖锐的叫声。她蹲下身子,拿着又开始喷水的水龙带,抓起碎冰锥,放在外层衣服的口袋里,站了起来。
“夏恩?”扎克说。
“我的眼睛。”他说道,声音很沉闷。他放下双手,脸转向她,身后依然站着他的同伙。她喘着气畏怯地退缩着——这喘息是一种淑女的声音,电影里一个马上就要晕倒的淑女的喘息声。
她扔下水管跪在地上。“哦,天哪。”
“离我远点。”他说。
“你,”她对离小屋最近的那个高个子说,“进去,打911。”
“9—1—1?你他妈在开玩笑吗,女士?”
现在她是个女士了。
“我们需要叫一辆救护车。”她说。
“不能,他们会把我们送进去的。”
“赶紧叫救护车!”
“他不会有事的。怎么样了,夏恩?”
“我的眼睛!”
扎克朝她和夏恩走过来。
“别动!”她对他说,“你可能会踩到的。”
“你是说……”他半张着嘴,眉头紧锁在一起。
“我们得找找。拨打9—1—1吧,”她对高个子说,“小心点!”
他瞥了一眼扎克。扎克说:“我们打完电话就立刻离开。”
“我需要你们两个帮我找。”
“他们一般还会派一辆警车来。”高个子说。
“他们可以把它放回去的,”她说,“眼睛。”她对此很有把握。她看着小屋。她需要把水关掉。水龙带在她的膝盖旁噗噗噗地不停喷着,水四处乱溅,也许把眼睛冲到了黑暗中,但不可能冲得太远。夏恩侧身躺在冰水上,蜷缩着身子,翻来滚去地呻吟着,一只手捂着眼窝,眼眶外眼球的神经荡来荡去。她扯下四只手套四处搜索,使劲地检查,一只手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地上只有几处血迹。没有眼珠。
“求你了,”他小声说,“帮帮我。对不起。”
“我们会找到的,”她说,“让你朋友叫救护车!那个高个子。”
“我需要帮助,盖卜,快打电话!”扎克拖着双脚,几乎完全弓着身子在寻找。“这边太黑,很难看清楚。”他用酒鬼寻找跌落的硬币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说。盖卜朝办公室的门走去。艾伦在水坑的冰面上匍匐着,在夏恩周围留下了一圈波纹。她准备从里向外一圈圈扩大范围,直到找到眼珠。她瞥了一眼仍在方尖碑前的那个疯子,对这一切他浑然不觉。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光线洒到了冰面上。

“喂,我想这个是……该死。不是。”扎克弯下全身,在冰面上摸索着。她看着他慢慢地向前倒下。
盖卜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光线映出他站在门框里的轮廓。他气喘吁吁,仿佛刚刚接完付费长途电话跑回来似的。她新买的CD收音机在他手里。他有点窘迫地耸耸肩。
“我打过电话了,”他说,“我得走了。对不起,哥们。”
她不知道他说的“哥们”是谁。他像一个冰上溜石运动员一样,一只脚滑冰,另一只脚助推,飞快地溜向冰场另一侧的尽头,那里有一条小径通往海湾街。他一上到人行道,就开始飞奔,那速度出奇地快,对一个手里拿着大家伙的酒鬼来说几乎不可能。
扎克现在和她一样用手和膝盖趴着,他不再寻找眼珠。他在注视着盖布消失。她以为他也会马上离开,不过他又开始继续寻找。
她说:“扎克?”
“我是夏恩。”他透过颤抖的牙缝轻声地回答。他的夹克的黑色皮革上已经结上了霜。
“不,我是说你的朋友。”
“我?”扎克问。他有点狐疑地把头转过来。
“再往这边来一点,我觉得它不会滚到围板那边的。”
“小心点,”夏恩喘息着说,“他们可以把它放回去的。”
她从夏恩身边挪开,一圈圈向外摸索。这时,她觉得她看到了它。它滑了整整二十英尺,停在了冰水和雪堆相交的地方,那坚硬的雪堆是为了清理溜冰场空间而铲到一边的。眼珠就在雪堆的阴影里。她很肯定。她颤抖着向它爬去。那只眼珠似乎以一种不自然的警觉注视着她,甚至带着一丝愤慨,仿佛责怪她迟迟不肯来救助它似的。当她靠得更近一点时,它似乎不是盯着她,而是穿透了她,直视着她身后或者更远处的什么东西。
“我想我找到了!”扎克喊道。他一定在往她的方向看。
“进小屋去,”她喊道,“里面有一些袋子,放在纸巾盒里的塑料袋,在你进门后脚的右侧。拿一个出来,装满雪拿过来。不,拿过来就行。这里有雪。”
“好吧!马上!”
“你找到了。”夏恩在她身后说。
“你不会有事的。”她说。她伸手去探那只眼珠,然后停了下来,想把橡胶手套戴上。手套落在了夏恩旁边的冰面上。她没有碰眼珠。她可能会弄坏它。那眼珠令人畏惧,却仿佛有一种魔力。在恐怖小说中,脱离身体的眼睛偶尔出现,但那些通常是有意识的,充满警惕,是一种威胁。这只眼珠没有光泽,似乎失去了对世界的兴趣,可能已经结冰了。它看上去不像是真的,而像镶着灰蓝色玻璃虹膜的瓷器。它太圆了,一点不像真的。如果这是部电影,她一定会抱怨特效太糟糕。就像加文死后不久双子塔倒塌的时候那样,一切看起来都不像真的,而更像电影中的人造灾难。
她不确定一个眼珠会有多软——她的印象是,尽管眼球被一层膜固定着,但它的主要材料应该多少有点像布丁。她可以想象她留在眼珠上的指纹,这将是他余生一直要看的一个图案。她等着扎克把那雪袋拿来,然后用指节把它推进袋子里去。
警笛从远处呼啸而来,声音越来越大。她仍然跪在地上,蜷低身子,仿佛在护着眼睛不让它被冻着。她用颤抖的双手拢着它,但没有去碰,这样她就不用看着它了。她回头瞟了一眼。扎克在去小屋的路上来到夏恩身边并停了下来。他高高地站在朋友身边,浑身哆嗦着。
“你会挺过去的,哥们。”
“去小屋!”她大声喊,“我需要那个袋子!”
“好吧。”他继续蹒跚地往前走,差点又摔倒。这时,他的头歪了歪,就像一个醉汉突然间临时警醒一样。他听到了警笛声。他们正在靠近。他躲进小屋,又迅捷地出现了,仿佛猛然间头脑清醒了过来,在冰面上向她滑过来。她看着他的眼白越来越大。她伸出左手去拿袋子,而他则伸出右手把袋子递给她。
有一小会儿,他立在她身旁,仿佛被那颗眼球定住。他回头看了一眼夏恩。“我得离开这里。”他低声说道,但声音足以让人听到,然后踏上雪堆,朝着和盖卜相反的方向奔向公园对面。他的肩膀上下颠动,风帽也脱落了。他跑过方尖碑,那个人僵硬地转过头看着他。当警笛的呜咽声融成一声尖叫时,她用一把雪塞满袋子——这些袋子平时放在小屋里,用来捡公园里的狗屎。狗屎满公园都是,有时还会出现在冰面上。她用食指的关节轻轻推动眼珠,让它从边缘滚进袋子。眼珠滚了进去。她不知道是应该把袋子密封起来还是让它开着。她掉转身,爬回夏恩身边。她不敢站起来,因为这样会滑倒,让袋子掉落,甚至摔倒在它上面。她用膝盖和右手爬行,左手拿着袋子不让它碰到任何东西。

救护车和两辆警车闪烁着进入视野,沿着军械大街向东驶去。它们要绕一圈,从海湾街经过小屋进入公园。它们又消失了,但警笛声继续鸣叫着,撕裂了夜空。
“我想不会有事的。”她边说边伸手探他。
“如果我能保住眼睛的话。”
“你会的。”
“对不起。”
“他们很快就会把你的脸整好的。”
她不知道这会不会实现。她差点说英俊的脸。
“要是我必须回去坐局子,”他说,“我也能接受,只是我不想瞎了。我能看看吗?”他从冻得发紫的嘴唇里迸出几个字。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确认一下我们找到的没错。”她说。
他的身体抽搐着,仿佛因无法控制笑声而颤抖。她打开了袋子。“哦……天哪。”他说。那眼珠子正回视着自己的主人。她把裸露的手搭在他的肩上。他的身体在皮衣下瑟瑟发抖。他的低裆牛仔裤裆处的皱褶冻住了,隆了起来,看上去好像他勃起了一样。他没有畏缩,也没有看着她——他现在不会这样做了。
“你是不是在另一个溜冰场伤了瓦尔特?”
“不是现在这样。几乎算不上什么伤害。”
“最好是真的。”她抓住他的帽子,用力把它套在他的头上。
“一切都是为了二……二……二十块钱。没有人能相信我的生活。”
丁林棚的解析
史蒂文·海顿的短篇小说《亡者更惹眼》也是一个反讽的经典。这篇故事收集在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集中。海顿出生于一九六一年,曾一度被称为加拿大最年轻有为的作家之一,他的诗集《迟到的醒悟》获得二〇一七年总督文学奖。海顿一直聚焦孤独的人群和个体,描写生活的缺憾、意外、逃离等主题。对他来说,反讽的一个最有力的词汇就是“但是”,它是在表象的皮肤上划开的口子,刀锋直刺实质的血肉。“但是”是意义的支点,小心翼翼地维持故事的平衡,拒绝给作家和读者指明倾斜的方向。“但是”是海顿特有的反讽方式,所有的故事是从“但是”开始,并以一个隐身的“但是”结束,因为“但是”从来不是绝对的,它总是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生死未卜、变幻莫测。
作者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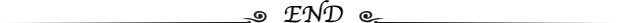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文娟 校对:博闻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