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色的庄严:首届中国·汨罗江国际诗歌贡献奖获奖诗人作品选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徐曼琳译
“快来 装点这朴素的桌子”
快来
装点这朴素的桌子,
用鲜红的番茄,
用茴香和卷曲的西芹,
用蒜,
用芳香的花椒和洋葱,
用长着小毛刺的黄瓜
和一块块西瓜——让黄油,
如琥珀般
的太阳在眼前,闪现
耀眼的光芒——是时候了
切几块黑色的面包,再撒满白色的盐,
千万别吝啬,
请拿出整整一瓶儿——
满瓶的葡萄酒
也不会碍事儿——多么愉快
如果能
消饥解渴,又能咀嚼品味!
那将至的秋天
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向你祈求,绝不祈求
你的恩典——
创造万物的上帝啊
淘气的情人
比阴郁的怀疑者更得你宠爱。
“我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
我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
在充满生机的大海死气沉沉的海滨,
海浪之上青铜色的天空在叹息,
因为诺托斯和玻瑞阿斯[1]相互争斗,
触动了空中的风铃,
那里时而酷暑,时而严寒,从未有过——温暖[2]。
金黄色,玫瑰色和青绿色的晚霞,
对脆弱的瞳孔十分有益,还有银河
给我庇护,让我远离疾病,
让我神志安宁,我敏锐的听觉
一点也不害怕大海深处的轰鸣,
它虽然涛声喧哗却和谐动听。
从童年时起它的每一声回响我都熟悉,
我是少有的通晓两种语言的人,
人类翻遍词典尽情铺展的
词汇都无法表达的旨趣,
天国的语言,稍加改变,
就能用歌唱的声调,将其呈现。
那我还剩下什么?——在大地上
这艰深的语言模糊不清,我的声音在空谷中
响起,虽已失去本意——一半自救,一半
活着,为那些有相似天性的居民,
为游弋的鸟儿或者飞翔的鱼儿,
在自己的房子里孤独地与时间为邻。
[1] 诺托斯和玻瑞阿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北风和南风。
[2] 按照基督教观念,受重视的是极端的状态:酷暑与严寒,而非均衡的温暖。
“比复杂的更复杂,比简单的更简单”
比复杂的更复杂,比简单的更简单,
时而动作迟笨,时而伶俐活泼,
堆叠成山,突入密林,
篝火猛烈的火舌
甜蜜地旋舞,嘲弄地摆动
从悬崖上快速地崩塌
又完整地站起,似乎
从未发生过什么,牢固而又通透,
她无所不知,却又一无所知,
只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一切。
以攻击威慑邻邦,
把和平赐给远方的国家,
诺亚方舟托起的她
在波涛之上云海之下,
展开宽阔的双翼[3],
那些关于未来、现在和过去的讯息
试图转变成一切存在的
充满诱惑的血与肉,
因为在各种各样的面孔和身影中
上帝最爱的是正直的她[4]。
[3] 双翼,类似俄罗斯的国徽。
[4] 诗到结尾处也没有表明这个“她”是谁。诗歌抑或是俄罗斯,或者其他什么?
徐曼琳


黑丝绸
赵四译
我站在路边
比一只瓢虫或飞蛾还小
比一滴乌鸦的眼泪
或杏仁还小
比一粒亚麻种子还小
比一根雌鹿的睫毛还短
惊恐地 我
抬起头
聆听
永恒
这匹黑丝绸
发光的声音
亚美尼亚舞者
赵四译
她一袭白裙跑进了画面
舞蹈 一片在半空中
旋转的湖水——
她精巧的手指自我安顿
渴望的密码
她精致的唇吻开启
沉默的花瓣
我目光流连于 她
像以闪光触角轻抚
串串葡萄的蝴蝶
她 耸肩叹息又像
在山中独自濒死的
无助牧羊人
我思忆起儿女
在纯洁与圆满之间
感受到关联之环的链锁
我变成了在永远失去
和始终与我们同在的
万物间那活的关联——
感受力自身
斯捷潘纳克特,2014
波兰诗歌
赵刚译
我与世界各地的作家们讨论波兰诗歌
一些人崇拜赫贝特另一些人崇拜米沃什和鲁热维奇
许多人赞赏希姆博尔斯卡的诗
但没人知道谁是诺尔维德、巴钦斯基、布尔萨
没人读过莱希米安、戈罗霍韦雅克、波希维亚托夫斯卡
对我们诗人的了解尚如此肤浅
我努力指出其他流派
鼓励人们去读克拉西茨基、莫尔什丁、雅尼茨基
还有萨尔别夫斯基,但他们只读诺奖获得者
和那个奇怪的扎加耶夫斯基
他们说他会是下一个
诗歌像生命有自己的巅峰和泥沼
阳光下闪耀的山脊和泛着甲烷气味的深渊
如果波兰诗人我只能选一个
我会选那位
尚未降生者
布拉迪斯拉发,2015
大流士·托马斯·莱比奥达(Dariusz Tomasz Lebioda),波兰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和出版家。1958年4月23日出生于比得哥熙。长年在“伟大的卡吉米日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客座教授(2002)。欧洲文化协会和波兰文学家联合会成员。语言艺术类季刊《主题》的主编。作品发表在《创作》《奥得河》《国际诗歌评论》(美国)、《当代国际诗坛》和《译林》(中国)以及十几个国家的数十种文学刊物上。曾获得波兰和国际上众多文学奖项。
赵刚


高兴 译
灵魂转生
我爱并坠落。雪下着。我蓦然醒来。
那些雪片让我生出永恒的感觉。
我用莫名的力量备好令人迷醉的
美餐,同魔鬼和新郎一起享用。
雪下着。雪下着。多么悲伤又理想的
盛宴,那是我朝向冬天的敞开,
在天空,平静,却又生硬一如珊瑚,
被寒冷逮住,急切地想要分辨
冬天的等级……它们会在哪里?
在世界的何处?跟随着谁人?
雪下着,就仿佛我将不再存在。
雪缓缓下着,仿佛有人惧怕我。
我坠落并爱。雪片蓦然将我唤醒。
永恒只是记忆,仅此而已。
感动
他没有肉身,也没有心灵。
他只用看不见的器官
哭泣,得到
最伟大的诗人的赞美。
他没有愿望。也没有开始。
我们永远信任他。他就是这样。
在人和天使,人和神中间
他没有区别。
他站在他觉得属于他的
地方。不幸,
欣喜,好运都无法向他靠拢。
我们知道他正用
内在的目光望着我们。
兴许,因此,天真地
我们从肉身逃往
我们梦想着属于
我们的心灵。
他在睡眠中生活。
不同于单纯的
那种生活。
他将秋天从大地搬到我们身旁。
他总是沉默。他的沉默本身
恰恰表明他的在场,
未被动词触及的在场,
未被名词玷污的在场……
每个早晨,他都死亡着
我们每个人的死亡,
但又无法描述
实际上如何死亡。
他总是自我死亡。
这是他唯一的一种比所有人
加在一起都更加充满活力的方式。
他大笑,为了保卫山峦。
他护佑我们,
用湿淋淋的悲伤。
他站在他觉得
属于他的地方——那里,疏离的
一切变成为了神、金字塔和蝴蝶
而制定的法则。
此刻,他在谁心里?在我心里?
在你心里?还是回到他自己心里?
我的祖国,一扇窗户……
我的祖国?一扇朝我敞开的
窗户,朴实而庄重,期待着
我献身于天空,那认得出我的
鸢尾花、手、迟疑和思想的天空,
不用问我:为什么?直到何时?
我的祖国?一个没有冬天的冬天的
日子,同熟悉的星辰,被怀疑激发的
命运一道,我走进……
一个我们无从命名冬天的冬天。
一个我只想在其中坠落的冬天。
我的祖国也许曾是一句诗,你的,我的,
一句上帝入睡前必读的诗。
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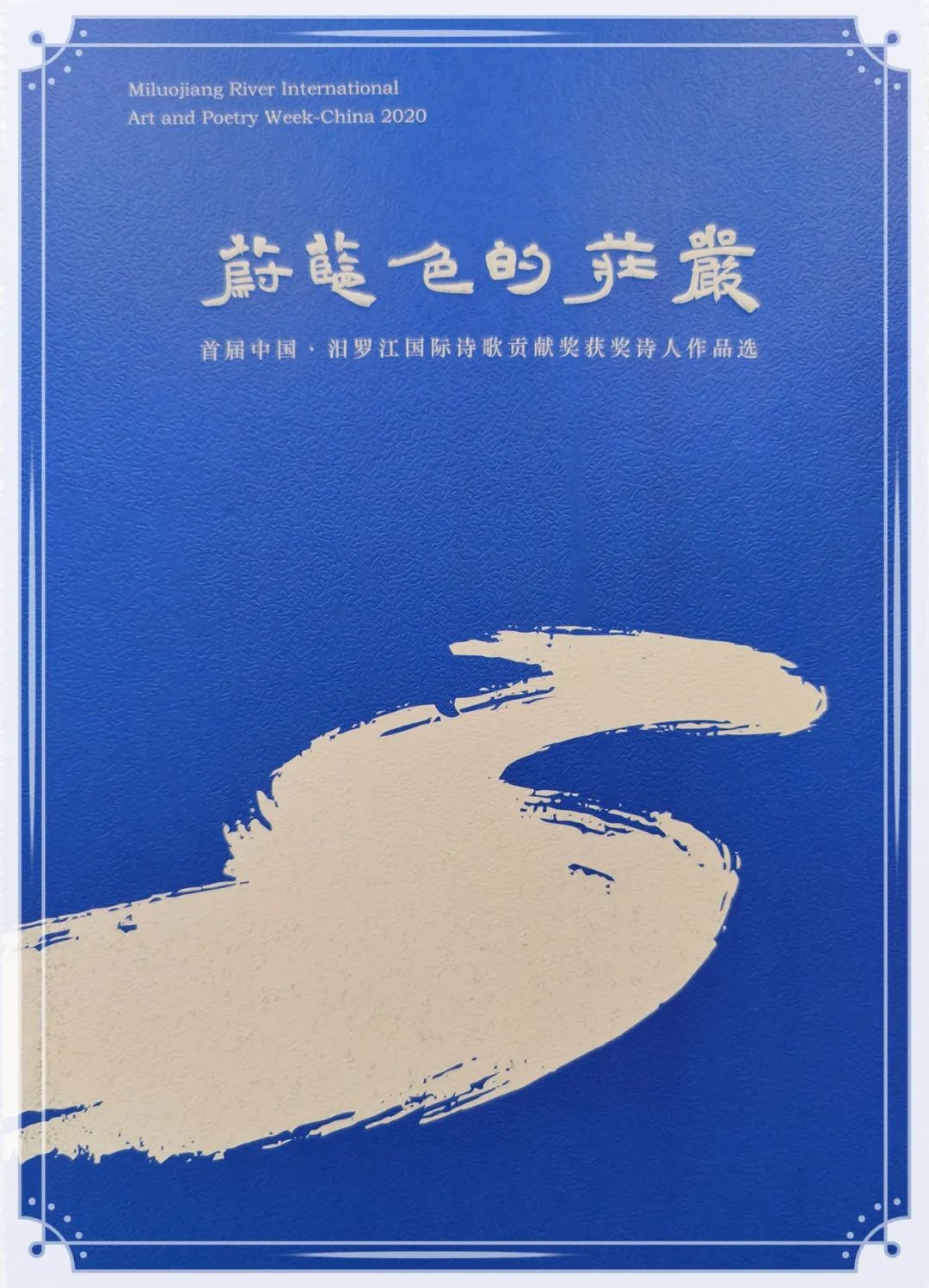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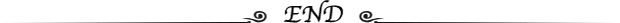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高兴 言叶
排版:文娟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