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专辑 |《世界文学》中的妖魔鬼怪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中的妖魔鬼怪





志怪小说:奇特的动物
这一组小说都是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前两篇来自法国女作家玛·达里厄塞克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行文的风格:怪异,细腻,善于营造非同寻常的氛围,通过细节交代来暗示情节发展的可能。
01
滑雪女人
在一个停电的暴风雪之夜,在与世隔绝的山顶居住的“我”忽然听到了敲门声。门外是一个来滑雪、却被恶劣的天气困住的女游客。“我”好心地请她进屋后,噩梦开始了。选段为“我”接待这个陌生的滑雪女人进家的场景。
我又向她走去,想给她点根烟——她的手在水里泡着——但我突然发现,窘迫中自己忘了拿火柴。她在斯特法内的浴袍上擦了擦她长长的手指,朝柜子走过去,一边对我说:
“您不用动。我包里的内袋里有。”
我赶快转回了身。就在她躬身拿包的时候,汉弗莱跳到她背上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那女人扭头勉强抓住了猫,把她钩状的手指甲插进了猫的脊梁。我刚巧来得及看到她的眼神:狂乱、骇人,和汉弗莱此刻的眼神一样疯狂。眼前的这一幕把我看呆了,意识一片空白,像一个大雪团。她直起身,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镇静地向我伸出手臂,给我点烟。
我惊了一下,恢复了常态。
“实在是抱歉,”我说,“这只猫怪得很。它没伤着您吧?”
她说没有,还好。她没事。让我不要担心。她也不招猫喜欢。我再次道歉,抓起汉弗莱上了楼,把它关到我的房间里。
我不忍心再责备它了,它完全被吓破了胆,我的手指能感觉到它砰砰的心跳。我坐到了床上。离开这个女人一会儿让我感到轻松。她的存在突然使我沉重。还有那个眼神……我试图说服自己刚才是有些恍惚。那黄色的眼睛。眼球凸出。她疯了,完全疯了。猫为什么要袭击她?为什么它也这样看她?查理怕的是什么?
……
她正叠着腿,坐在壁炉前抽烟。眼睛盯着火苗。我开玩笑地朝她晃了晃钥匙,说汉弗莱不会再来烦她了。她谢了我,眼光一直没离开火苗。我把钥匙放在了壁炉上,很不自在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再跟她说些什么好。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整个客厅的空气里都弥漫着她的存在。我动了动身体,到厨房去看狗儿们。它们一看见我就开始呻吟,在原地打转儿,连查理也这样。我觉得心中的不安在增长,不由得发起狂来。我呆呆地在查理头上敲了一记,又回到了客厅。
“您再来点咖啡吗?”
她缓缓地扭过头,两只眼睛依然盯在火苗上。然后,她的目光转向我,将两只像是由火光散射出的黄色的、被放大的眼球放到我身上。一个疯子的眼神,一个狂乱的眼神。
“好的。”她轻声说。
我拿起咖啡壶,将她的杯子倒满。墙后的厨房里,查理开始死命地叫了起来,那两条西班牙种猎犬立刻随声附和。滑雪女人的脸消失在了她的长发后面。我跳起来,跑到厨房:“住口!该死的!住口!马上给我闭嘴!”我低声吼道,慌乱极了。狗儿们呻吟着坐了下来。我恨它们。我又回到客厅,快要崩溃了。

02
猴子的认知
我打开门,屋子里悄然无声。我小心地走了几步。要是说有什么想法会让我不舒服的话,那就是想到黑暗的屋子里会突然跳出只猴子来。我轻轻地推开它的房门,它还在那儿,躺在黑暗里。它把被子推到一边,趴着睡,穿了一条背带裤。我好不容易分辨出了它的脸,皱巴巴的像一个握紧的拳头。它的手臂显得很长,可能是因为太瘦了的缘故。那双大手在黑暗中现出轮廓,像是用皮子给镶了边。它的大拇指关节怪怪地弯着,弯到了手掌下面。那手掌足有我们的两个长,生就是为了适应攀援的需要。
我悄悄地退了出来,把鸡放进烤炉,洗了生菜。在给运河边纤道上的绣球花浇水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人在注视着我。
马塞尔隔着窗户在看我。它扁平的鼻子贴在玻璃上,呼出两圈水汽,时聚时散。
“过来。”我对它说。
但是它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作了个手势。
“我不能出去。”等我进屋,把门从背后关上时,它对我这么解释说。
它揣摩着字眼,一字一顿地说着,嘴巴嘬成了鸡屁股状。它若是一个人,我就会觉得它太矫揉造作了。
“是我母亲不让你出去吗?”
“她允许我到后面的花园里去。”
背带裤穿在它身上晃晃荡荡的。它的毛色晦暗,肩膀上的毛还缺了好几块。耳朵是它脸上唯一有点肉的地方。它两腮凹陷,下颌因此显得尤其宽大,给人一种克制自我的感觉。它说话时,好像知道自己的脑袋很重,骨架太大,显得很难为情。
……
第二天,我把躺椅搬出来,给马塞尔放到丁香树下。我自己则想躺在草地上。
“坐上去吧,马塞尔。”
“我不能这样做。”它回答我说。
它长长的手臂垂下来,细得像两条绳子,手触到了地面。它站着,佝偻得厉害。
“您不能这么做?”
“如果您坐在地上,我就不能坐到椅子上去。”
天空一片澄蓝,丁香树在微风中摇曳,蜜蜂在忙着采蜜。
“马塞尔,我要求您坐到椅子上去,跟我说话。”
马塞尔勉强把屁股放到了椅子上。它好像陷入了片刻的沉思,低着脑袋,向它的长脚垂下去。它的脚趾扒在躺椅的边上,像是两只大手从它的背带裤中跑了出来。
“我不会谈话,”最后它说,“请原谅。”
“那您和我母亲说什么?”
“她给我讲她旅行的故事。”
我试图去想象马塞尔的生活。它在罗涅长大,一切观点、思考和痛苦都是我那位到处旅行的母亲给予的。在动物园的猴子笼前,我总是自忖到底是谁在看谁。栏杆后面,猴子的知识似乎无穷无尽。

03
老狐物语
比起猫咪、猴子,狐狸大概是亚洲志怪小说中最受欢迎的明星主角了。日本作家海音寺潮五郎的这篇《老狐物语》在古老的狐狸作祟故事的框架下写出了一番新气象。在传统的狐祟故事后面,作者次第安排进狡狯的利长、老谋深算的家康等多层背景,把传统志怪小说演绎为全新的篇章。在下面这个选段里,武士但马刚打狐归,就有狐狸为报复找上门来:
夜色深沉,但马一行才到家。带回来的狐狸让但马家所有人觉得珍奇。那些下层女佣用半好奇半恐怖的眼神远远望着死狐狸,很想向随从们打听打听这死狐狸的事情。
但马洗过澡,觉得神清气爽,开始喝起饭前酒,打猎的事已经画上了句号,对狐狸的哀怜——那一瞬的心情,现在,他想也不再想了。一天的疲劳和酒力一道发作,他很快就醺醺然了。突然,他听到远远地从什么地方传来一片吵嚷声,正想听个仔细的时候,随同打猎归来的一个随从一路小跑过来:
“殿下,出大事了!”
随从简直就是在喊叫,脸色铁青。
“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是哪里打架了?但马想。
“狐狸!狐狸!狐狸作祟了!”
即便是一身刚气的但马,心中也还是凉意骤起。他盯着来人低声说:
“镇静点儿!到底怎么了?”
狐祟这种事,在现代用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是可以做出充分解释的,但那个时代,无论谁都相信狐祟,丰臣秀吉活着的时候都说过宇喜多秀家的家里被狐狸附体的话儿。那位秀家的夫人,是从前田家嫁过去的。正因为和主家有关系,但马才记得特别清楚。
“走,去看看。”
他从刀架上拿起刀带在腰间。那刀长二尺八寸,鲨鱼皮鞘,美浓州锻刀名人关之住二代兼定所作,是他带着上过几次战场,用惯了的宝刀。
他领先一步走进了厨房。
宽敞的厨房中,麇集着男男女女的下人和武士,多数人都屏声静气、远远地围在窗旁灶龛边。被狐狸附了体的下女,光着上半身坐在灶龛的大锅锅盖之上。那坐姿非比寻常:大盘着腿,贴着两手,头直直地伸着,与稻荷神社神殿前的狐狸雕像一个样子。她不时地转头伸向灶龛去咬食什么,仰着脸闭着嘴,但看得见她的嘴在动。原来是那里有几尾干鱼。她的脸瘦瘦的且苍白,眼睛闪着异样的光,尖着嘴,活脱脱的狐狸神态。
……
女人专心地吃着,闭着嘴不停地嚼,好像一直没有注意到但马的到来。可是嚼着嚼着,突然,她面目狰狞地盯住了但马,眼睛闪出一道寒光,横叼在口中的干鱼簌簌地掉下来。她霍地一跃而起,叫道:
“好你个太田但马!残杀我妻我子!这仇如何能忘!我定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那声音尖细锐利,如锥穿耳。她头发哗啦一下滑落,遮住了半个脸,弯着小腰,两手缓缓地动着,比划成狐狸头的形状。
人们惊恐地叫起来。

魔鬼小说:人间事务所地狱分部代理人
志怪小说中的“动物”,或多或少带有民间传说或文化传统的影响。《老狐物语》尤其体现了日本的鬼狐传统。如果说东方志怪中的“动物”形象植根于民间传奇,充满了百姓生活的市井气息,西方文学中的“魔鬼”形象,则多与基督教传统相连,生长于“天堂—地狱”的圣经式语境。
01
魔鬼休假记
魔鬼X先生的存在对我们从来是一个谜。这会儿,他离开了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场所,硫黄色的火焰仍在他的周围喷吐着火舌。艰难地登上无穷无尽的层层楼梯,攀越过高无止境的座座扶梯,经过长途跋涉,他来到了上帝U先生的办公室。
X先生已经很久很久,无法想象有多么长时间,没有来这儿拜访他的上司了。这一天,他特意为此次极其重要的造访打扮了一番。当然,这是与他平时真实而自然的穿着相比较而言。众所周知,X先生在他那既不通风,又炎热无比的居所里成年累月地从事着他肮脏的日常工作,他的着装从来是不经意的。这会儿,在他瘦小的身躯上晃动着一件破旧的礼服,裤子刷得平平整整,一双手也洗得干干净净,只有指甲缝里还残留有洗不净的污垢,同样还有那张与我们大多数人想当然的印象截然相反的脸,充满了谦虚与诚恳,也打整得清清爽爽。终于,已经爬上通向U先生办公室那腐烂木门的窄小梯子了,忽然间他一下子失去了那一直激励他勇敢攀进的勇气,毕竟,瞬刻间他将要面对他的顶头上司。

如果说迪伦马特笔下的魔鬼亲切得让我们莞尔一笑,那么另一位魔鬼——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Stawomir Mrozek)的微型小说《伙伴》中的这位——则意外得让人哑然失笑。
02
伙伴
我决定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灵魂被看作人最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期望着此举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利益。
来与我接洽的魔鬼让我很失望。它长着塑料的蹄子,尾巴也断了,还是用绳子接起来的,一身皮毛像被飞蛾蛀蚀过似的,黯淡而又凌乱,连角也因过于短小而显得有些发育不良。这样一个可怜鬼能出得起高价来买我的无价灵魂吗?
“您确定自己就是魔鬼吗?”我问道。
“是的,您为什么会怀疑呢?”
“我期待着来的是位黑暗之王,可您长得如此……我想说,嗯,粗制滥造。”
“灵魂什么样子,魔鬼就什么样子,”它回答道,“那么我们来谈生意吧。”

幽灵故事:去而复返的亡者
每一类妖魔鬼怪小说都是从某种传统、某种特定背景中生长出来的。以动物为主角的志怪小说依附的是一个广博的、万物有灵的自然;关于魔鬼的奇幻故事勾连着宗教传统。另一类妖魔鬼怪故事——关于幽灵的故事——则让我们感受到人世的牵连和羁绊:不肯消逝的情怨、盘结于心的执念……某种心结让早逝的亡者们去而复返,再度回到人世,拜访他们无法忘却的“故人”。
01
第十九号
“您不让我进您家看看吗?温馨甜蜜的家。我跟您说了不会告诉您的家人‘我们的事情’,我一贯信守诺言。”
法里亚斯第一次有点警觉地看着他。他在十九号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点什么东西。
“好吧,您进来。”
“这才是我喜欢的。我看得出您让我进门需要点勇气。”
转即,十九号身处起居室,房间简朴整洁,但品味也一般。
法里亚斯喊道:“埃尔维拉!”埃尔维拉出现了,是一位还很年轻、有一定魅力的女人。
“这个朋友,” 法里亚斯多少有点结巴地说,“是你的同乡。”
“是吗?”女人的眼神里露出一丝喜悦,“您是土库曼人?”
“是的,太太。”
“你们在哪儿认识的?”
“这么说吧,”法里亚斯说,“我们有好久没见了。”
“是的,好几年没见了。”十九号说道。
他们聊了聊走丢又重新找到的牛。孩子们进来了。十九号亲吻每个孩子,礼貌性地问候。
“您结婚了吗?”她问道。
“丧偶。”
“哎呀,节哀。”
“五年前我妻子死了。淹死的。”
“太可怕了!是在海滩上吗?”
“离海滩不远。”
接着是冰冷的沉默。法里亚斯找了个借口。
“孩子们,来!去做作业,太晚了。”
“您,一个人住?”埃尔维拉问道。
她没有问他有没有孩子,唯恐他们也死了。
十九号用手拍了拍裤腿边,这是一个近乎机械的动作,只是为了要做点什么。
“好了,我不打扰你们了。另外,我必须在七点钟赶到意大利广场。”
十九号握住埃尔维拉的手时,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凑上前,吻了他的脸颊。
“您妻子的事情,我很难过。”
“我们走吧。”法里亚斯快要炸了。
“好,我们走吧。”十九号冷静地附和道。
男主人送他到栅栏边。在那里,他凝视着十九号,突然毫无征兆地哭起来。是难以抑制的抽搐。十九号不知该怎么办。这场泪雨并不在他的计划中。
很快,哭泣戛然而止,法里亚斯几乎是嘶吼了起来,不再用敬语而是直呼“你”:“你是鬼魂!鬼魂!你就是鬼魂!”
十九号笑了笑,非常理解,准备让步。他也用“你”来称呼对方:“当然了,孩子。我是鬼魂。你终于说服了我。现在擦干鼻涕,去靠着你妻子的肩膀哭吧。但你别告诉她我是鬼魂,她不会信你的。”

02
鬼恋人
死于战争的逝者因为执念而重返人世,这是现代鬼魂故事的一个重要主题。“现代鬼不再是血淋淋的。——但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对人的伤害。现在的伤害有更广泛的意义,那不必在肉体上,在精神上更使人痛苦。”这是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波温写在她的短篇小说《鬼恋人》前言中的话。而她的这篇小说也让我们集中感受到了战争作用于人的精神痛苦。主人公为四十多岁的杜路沃太太,回到老宅整理旧物,忽然发现一封写给自己的信。这封信来自她二十五年前在一战中阵亡的未婚夫。而此时正值二战,鬼恋人又回来了,在他的认知中,一切都不曾改变,他仍期待自己的恋人能信守承诺,前来赴约。
故事开始于一个鬼气森森的夏日午后:
楼梯的窗户钉住了,门厅里没有光。她只能看见一扇门半开着,便快步走过去,打开屋里的百叶窗。这位毫无想象力的太太看着周围,她看到的一切,以前长期生活的痕迹,使她感到困惑更多于熟悉。黄烟熏染了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写字台顶上有花瓶留下的圈痕。壁纸上的伤,是猛然开门时磁门柄碰出来的。钢琴已经送走保存,镶木地板上留下了爪子似的痕迹。虽然没有多少灰土渗进来,每件家具上都罩着尘埃的薄膜;而且只有烟囱通风,整个客厅里有一种不生火的炉膛的气味。杜太太把纸包放在写字台上,离开这房间上楼去;她需要的东西在卧室的箱子里。
她曾急着想看看这房子的情况如何——几个邻居合雇的兼职照料房屋的人这星期度假去了,不会回来。一般他不大进屋看的,她从来也不信任他。屋子有裂缝,上次轰炸留下的,她一直很留意。倒不是说会有什么办法修好——
一缕折射的日光横过大厅,她定定地站住了,瞪着厅中的桌子——上面有一封给她的信。
……
亲爱的凯瑟琳:

褪下妖魔的面纱:不能为人的人
01
墙壁里的妖精
韩国作家裴三植的剧本《墙壁里的妖精》,是一个读来令人潸然泪下的温暖故事。朝鲜战争之后,被判为“红色分子”的父亲为躲避政治迫害,不得不躲在家中墙缝中四十年,以“妖精”的身份来陪伴女儿的成长。选段为剧中开篇“女儿”的回忆。
我四五岁的时候,第一次遇见了那个妖精。
那时我得了水痘,满脸都是泡儿,裹着被子躺在床上。
那天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
[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的声音。]
迷蒙间传来妈妈在隔壁房间织布的声音,听着听着又睡着了。
不一会儿,突然感觉脸上像被什么扎了一下。
像是有人在我脸颊边呼气。
睁眼一看,有个东西突然闪过,我害怕极了。
使出浑身力气大喊妈妈。
—妈妈,快来呀!这里有人!
母亲大吃一惊,立刻奔了过来。
——做噩梦了吧?
——不是梦!真的有人!
母亲愣了一会儿,轻轻拍着我说:
——嗯,看来你是遇到了一个妖精。
妖精?
——对啊,一个非常疼你,喜欢你的妖精。
但是你千万不能和其他人提起这件事,绝对不行!
——为什么?
——就比如你做了一个好梦,但要是把这梦说出来的话,好运就没了呀。
妖精也一样。
如果你和其他人提起他,他就会飞走。
再也不回来了。
——我明白了。
——(伸出小手指)拉钩。
——(勾住小手指,晃动着)拉钩。
我睁大了眼睛,装出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听着妈妈说话。
就好像现在我女儿在听我说话一样。
不过这可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九五〇年初,我还只是个孩子。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时代去看看吧。
……

02
巫女图
意识形态的分歧让剧中的父亲不得不成为妖精才可以陪伴女儿,而在韩国作家金东里的小说《巫女图》中,宗教信仰的对立则让母子互相认为对方为魔鬼。信仰民间宗教的“巫女”母亲和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儿子,各自认为对方是被鬼神附体才“信了邪”。在偏僻的边镇,对立的信仰在一个家庭之中以一种最极端的悲剧形式呈现出来。选段为小说的开头:一幅成为传奇的巫女图,它神秘精美得令人屏息。而叙事主人公“我”正娓娓道来这幅画的来由……
远处是阴森森逶迤连绵的莽莽山岭,近处是黑黝黝宽阔深邃的浩浩大河。笼罩着这山岭、旷野和黑色河流的,是闪烁着点点蓝色幽光的星空。这是一个浓重的黑暗将人压得难以喘息的沉沉深夜。江边的沙滩上搭有一个硕大的遮棚,星光中,棚内密密地坐满了村镇上的女人们。她们已为女巫的咒语陶醉良久,一张张亢奋的脸上迷漫着凄楚和清晨劳顿困乏的神色。女巫自己也已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她的长衣无所凭依似地自由抖瑟,似乎已摆脱了凡世赘物的形骸而羽化,一个解放了的灵魂在自由地飘荡……
这是一幅画。
……
到我父亲长大成人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但是,祖父那间书房里,四方宾客你来我往,诗书名流挥毫唱和却依然如故。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一个春天的某一天,春风卷着尘土在街巷里翻飞,院子里的几株古杏已被催得烂漫如雪。傍晚时分,一个对我家来说极为罕见的陌生男人来到我家门前。他身材瘦弱短小,身着一件贫苦人常穿的短上衣,头顶竹笠,一条家织的手巾系在头上,看上去年龄约在五十上下。此人手牵一头毛驴,驴背上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姑娘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苍白里泛着青色。他们二人看上去似乎是男仆和东家小姐。
但是第二天他们站到我家厢房里时,那个男人却对我祖父说:“这个孩子是下人的小女,会画画,技艺不俗。因此,专程寻到府上为大人献技。”
姑娘通身白色,因此将其面色衬托得更加惨白。眉眼之间,聚拢着一团难以言状的浓重哀愁。
“你叫什么名字?”祖父向那女孩间道。
女孩没有做声。
“你有多大年龄?”
姑娘那双忧郁的眼睛望了望祖父,依然没有回答。
“她的名字叫琅伊,今年十七岁。”做父亲的代替女儿回答。接着,他用低沉的声音补充道:“这孩子耳朵聋。”
祖父点了点头。随后,他对那个矮小的男人说,那就在这里住几天,让她画几幅画看看吧。
此后,据说这父女二人在我家住了月余,女儿画画,父亲则在空余时间向人讲述了他们那段苍凉的故事。
在他们离去的时候,祖父给这对不幸的父女备下了贵重的绸缎和充裕的川资。但是,坐在驴背上的少女同来时一样,笼罩在一片阴云中的脸色忧郁惨白如故。
姑娘留下的那幅画,后来祖父名之为《巫女图》。这幅画,以及关于他们的故事,就由祖父传给了我。

啊,代代相传的鬼怪故事,天南海北的妖魔传说!关于它们的想象似乎永远也不会枯竭,只要哪里有人,哪里就一定会有妖魔鬼怪。
虚构是小说的本相。不同于旧时百姓或听书小儿,我们作为当代读者,大多在阅读妖魔鬼怪小说之前就已经知道它的虚构本质了。可我们读罢这些故事,依然会被精怪嬉笑怒骂中的真情重义所打动,会为鬼怪传奇所栖身的文化语境而着迷,或是因故事背后的世情冷暖而抚卷长叹。或许,这就是这些故事能够从迷信时代一直存续到今天、也将流传向未来的原因:它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妖魔鬼怪中重新发现“人”;它们引导我们从不同的歧路看向同一个终点,如何从虚构之中去发现另一种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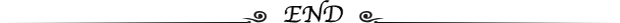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秋泥 排版:文娟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