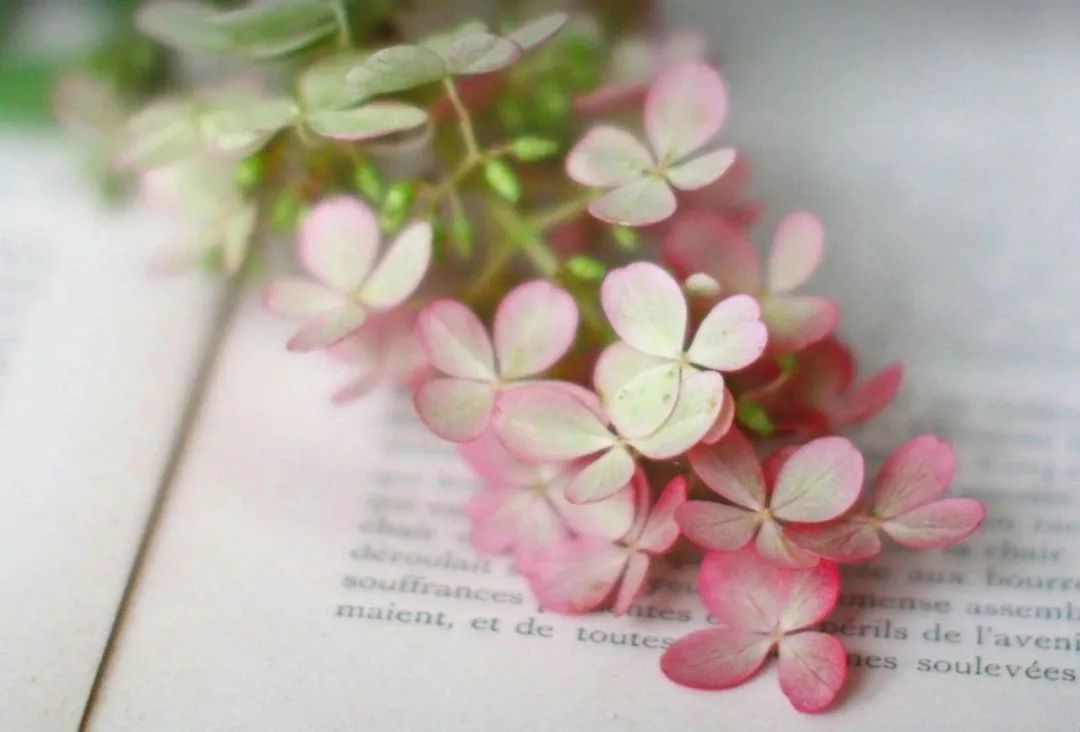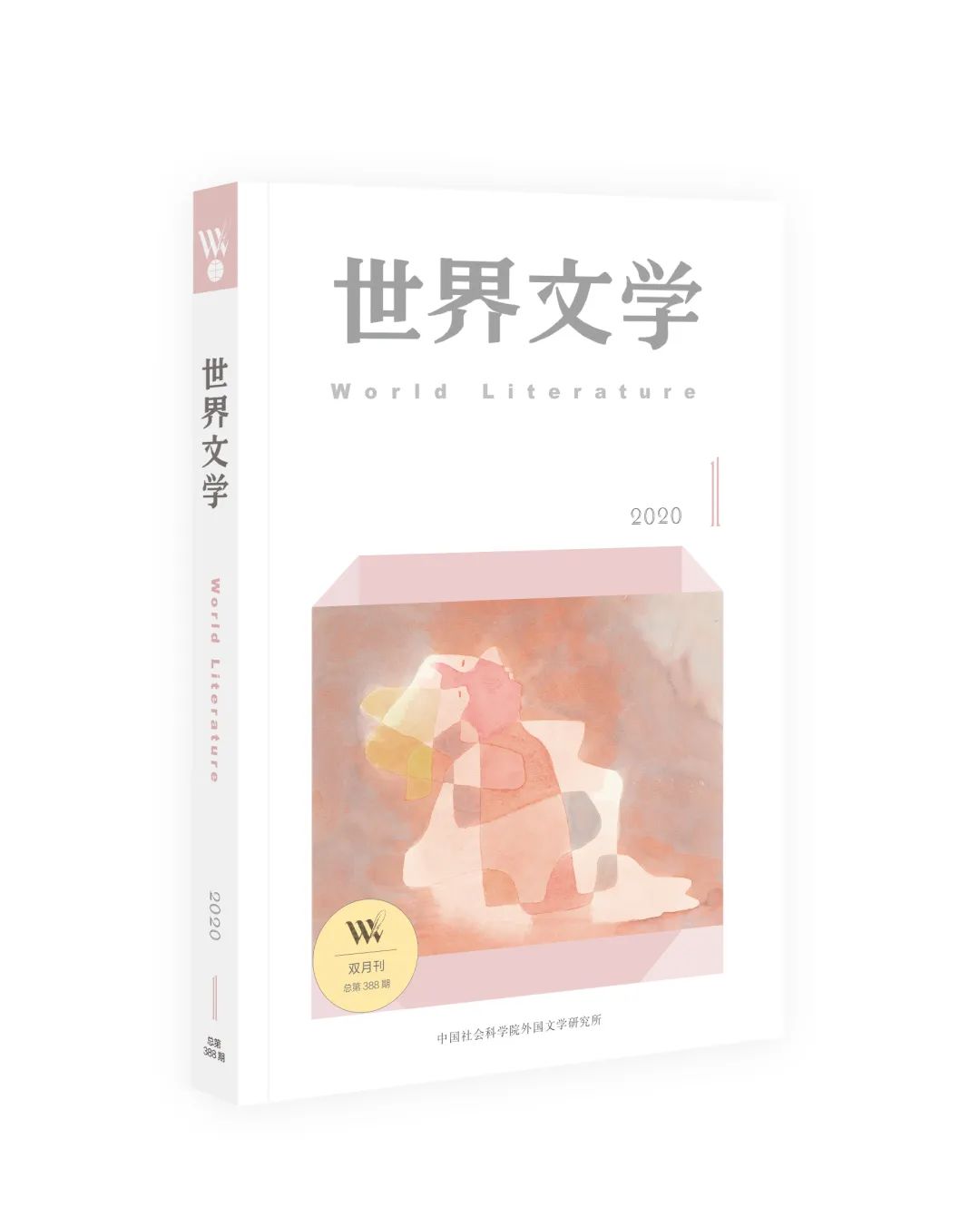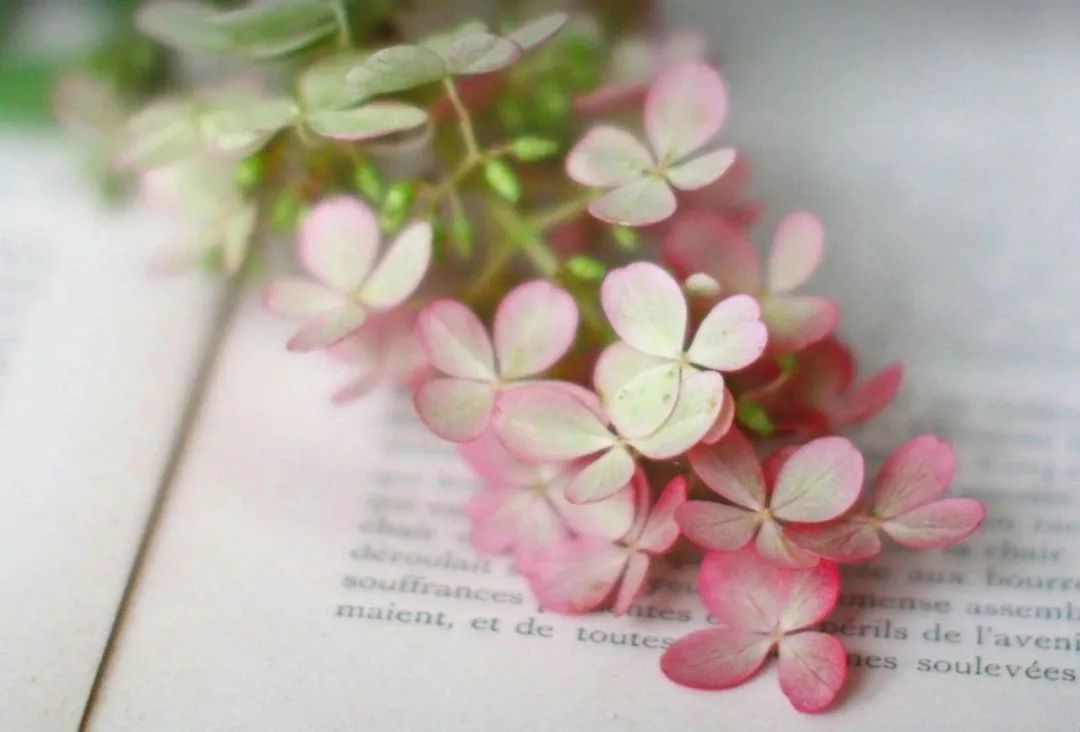
2月26日我们公众号推送了“2020年你最喜爱的《世界文学》小说”征文获选名单,转引了《世界文学》分享群两位朋友对今年第1期杂志上的一篇爱尔兰小说的讨论。从元宵节至今,我们分享群又有不少读者亮出了“隐剑”般的文本细读功夫,发表了不少细致入微、发人深思的评论,涉及新旧刊上的四篇小说:《媳妇再临》《三个黎明》《无形剑鬼爪》《贝恩斯》。我们从中截取了一些富有成效的互动以及精彩见解,分享给各位读者。欢迎进入《世界文学》线上共同体……
乾乾
如果说堕落是本文的一个主题,我倒觉得,叙事者是控诉“伊甸园”在商品世界里的沉沦。物欲的极大满足,与乐园的逐步沉沦,是并行的两条线。如果说主人公结婚生孩子,拥有一个幸福家庭,都是某种虚假的意识形态灌输所致,婚后又发现婚姻实相,那么这个解读是有道理的,但两人从少年时代就是恋人,结婚、买房、结婚后“生活不能变得更好,却偏偏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些不是虚假宣传,更不是意识形态灌输所致,而是因为赶上了爱尔兰历史上经历的黄金期,是真金白银带来的。家里那些摆设,品牌,叙事者近乎obsessively的对商品的描述,难道是一种虚幻的promise?温州—传记
为什么砸商场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主人公是个相对传统的人,他砸商场的标识,是否传递着这样一种潜意识——对“泛娱乐化”的控诉?另一层面,资本带来的美好生活是否真的美好?个人觉得作者在文中对此有一种反思,主人公他对妻子的冷漠是持怀疑的,妻子认为的合理、自然的是否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还有题目叫“媳妇再临”,想问一下有什么深意?是否隐含着作者对观念变迁的批判?德州—高兴
兰州 yingying
我读完《媳妇再临》这篇文章,第一感觉,作者写得还是人的存在问题。当一个人拥有了满足幸福的一切条件———美好的爱情、良好的事业、漂亮温柔的妻子、乖巧的孩子以及金钱地位等种种之后,他会幸福吗?没有!他的心理是“变态的”,就比如卡夫卡的格里高利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认为此刻诸神缺席,人的心灵是没有依靠的,人的灵魂缺乏归宿,我们都是失去了故乡的人。这其实是现代人的危机。这个主题在现代文学中很常见。生活是琐碎、乏味、无意义的,尤利西斯这个反英雄还在街上游荡,而我们的主人公爬上高处,砸了牌匾,做了一回伪“英雄”……我们该如何安抚我们的心灵?个人的一点拙见,因为没有读作者所有的文字,也没有读原文,只是就这篇文章说说,希望抛砖引玉。
温州—传记
有人分享下中篇小说《三个黎明》三个故事里的人物关系和时间跨度么?Zoe
同问。我只是觉得三个故事的女主是同一个:盛年时(便衣女警察)——少女时(小太妹)——迈向老年时(要退休的女警察)。但是理不清第一个故事里的罪犯,第二个故事里门房大叔和第三个故事里少年马尔康之间的关系(或者没有关系)。陕西 AEIOU
我还没看完,不适合说。我觉得作者给了某种联系,但又割裂了,又似没关系。温州—传记
我觉得第二个故事里的旅馆老柜员是第一个故事里的罪犯,他说他13年前杀过人,第一个故事就是他被逮捕的事。第三个故事我看到的和前两个联系不大,感觉马尔康像第二个故事女主角的孩子,跨度也是13年,女警察是第一个故事的女警察,再次13年后五十多岁,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听了@Zoe的说法,感觉挺对的,女警察第一个故事里说怕见门房,她到旅馆吐了,因为想起了从前,第二个故事的女主角更像她的少女时代。Zoe
有道理,13年这个细节我没注意到,这样好像就可以串起来了!

兰州 Yingying
《无形剑鬼爪》的译文真好,日本文学的味道全译出来了,读来每一句都是享受。感谢分享。杭州+地下室窥群老阿姨
师父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密传,是觉得要弟子自己领悟秘密所在,当时即使说了,男主也不会理解,深圳—张涛
《无形剑鬼爪》这篇小说最终讲的是一个人的品德修为,而非武力。宗藏符合我心目中的标准武士(侠士)形象:武艺高强,善良正直,嫉恶如仇,多情多义;狭间(这个名字取得好,似乎语义双关)同出名门,尽管身手不凡,却心胸狭窄,睚眦必报,难成气侯,最终导致美好家庭破碎并断送了自己性命;希惠是除男主外着墨最多的,她美丽温柔,勤劳体贴,善良贤惠,并深爱着男主,她和男主之间的关系仅隔了一层窗户纸。作者在开头写花,是不是为了铺垫烘托出希惠是像花儿一样的年龄,花儿一样的美?狭间妻的美,则不同于希惠,她娇媚艳丽,有成熟的风韵,但是善良而无脑,她的死令人怜惜扼腕。至于其他各色人等,作者寥寥数笔,既勾勒出个体鲜明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江户时代的黑暗官场。
哆啦A梦
中午抽空读了昨天的推送。藤泽周平这篇作品是第一次读到,读完特别想把电影也一起看了。我读时关注的点和张涛老师稍微不太一样。我的视野比较小,就是像《细雪》和《远山淡影》那样集中聚焦这几个人物的角度看,个人主观地弱化了时代背景。主人公里堀是唯一一位反面形象,让人特别反感的存在。其他几位,尤其是狭间及其妻子的行为都有非常好的合理性,尤其是前期越狱后的那段插叙,为狭间的误解及其后来与宗藏的比拼做好了铺垫。这也很符合日本的武士精神和普希金式的决斗。狭间妻的形象塑造得很丰满,是我理解的这篇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女主,因为宗藏和希惠后来的结合,其实是宗藏对狭间妻产生的难以言说的、冲动式的美好爱意被理性扼制后的替代性选择。当然前期邻居那段偷窥,也可以理解为宗藏在朝夕相处中有过对希惠的喜爱,但真正在一起的冲动还是源于狭间妻。尤其是后来在杀了狭间后遇到狭间妻听她讲的荒唐事时的那种愤怒和无奈。狭间妻的形象让我想起了《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不是蠢,而是为了狭间的义无反顾。不过狭间妻要比田小娥多了纯净和优雅的感觉。像极了日本的樱花时节,短暂而又绚丽。也有着「物の哀れ」的日本古典文学的审美特质。宗藏的成长和最终“复仇”都是因她而起。希惠更符合日本普通女性,平凡、淡雅、清丽,有她内在的含蓄和勇敢,也是日语文学中最常见的形象。故事读起来很曲折很引人入胜,这点倒是与一般的日本文学弱化矛盾冲突,平凡叙事的传统不太一样,有点像《春琴抄》中男主刺瞎自己前的那段的紧张心理描写。以上です。感谢译者和推送,这篇很喜欢。

沈阳—洪
@哆啦A梦@深圳—张涛受二位的启发,我也谈谈自己的感受。不知道这篇“鬼之爪”是不是“隐剑”系列的原文全本,跟电影的情节不太一样。电影里说女孩嫁过人了的。说是电影结合了两部小说,如此我倒还想读读那篇男女感情着墨较深的《白雪》呢。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精湛之处在于宗藏用暗杀术,也就是“鬼爪”除恶人。他为什么除恶人呢?就是恶人玷污了他心中的美好(狭间妻),而后者逢此不幸,也绝非简单的轻浮和愚蠢,自有其令人心痛和扼腕之处,然后宗藏对女性美好的情愫又借希惠得以纾解。试想如果没有希惠这个人物,宗藏对狭间妻的欣赏和怜爱便无了着落,继而最后逼他出手使用“鬼爪”绝技的对里堀的恨也不那么顺理成章了。另外,读到最后也理解了为何这门绝技一定要独门单传,因为实在是太厉害了,有点像代表神惩治人间的极恶,因此掌握这门绝技的人必须是正直的人。这是我对这篇文章思路的理解,至于说跨越阶级的爱恋,尤其是电影中展示出来的,应该是藤泽平周的《白雪》中重点阐释的吧?所以,了解那个故事情节的老师可以分享一下,我非常好奇呢。同一个作品,不同的读者读出不同的东西,有人看到了“侠义”,有人读出了“柔情”,还有人理出了所谓的“文思”。也许都是个人心理的投射吧?也许这就是好的作品耐得住推敲的过人之处吧?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个群存在的最大意义吧?畅所欲言,互相促进,共同遨游在文学的海洋,品尝小说带来的消遣和“甘露”。深圳—张涛
说到小说浓墨重彩的感情这条线,我想宗藏对希惠的爱一直是存在的,只是暂时停留在主仆或亲人之间的爱,未曾越过雷池。小说开头写到他飞快地跑回家,发现她不在,他感到“泄气”;而且母亲也曾为此担心过,“两个年轻人,朝夕相处”。这份懵懂的爱第一次被唤醒是在邻居告诉宗藏,有男人来找过他的时候。接着是宗藏的一系列心理活动描写,但是此时宗藏克制住了自己。正如群友们上述分析的,他第二次被唤醒,应是在接触了狭间妻之后,此时的爱显然已包括了情欲。于是在决斗前夜,宗藏捅破了那层纸和希惠结合,度过那难忘的一夜也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了。
深圳—张涛
谁看懂了这篇《贝恩斯》,我读完一头雾水。还有一个疑问是:为什么面包罐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笨马
我觉得小说写的是大师也是一个普通人,还可能有普通人都没有的缺陷。当然,就文学欣赏来说,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一篇小说的理解都不同,这就是小说生命力之所在。青岛—常春
玛丽唱的摇篮曲或许可以提示我们贝恩斯的人生状态(小说最后也以贝恩斯想听玛丽小姐唱歌结束)。 沈阳—洪
原文是awe-inspiring这个词吗?估计是“令人生畏”或者“诡异”的感觉吧,与前文“等着添油的”相对应。在我看来一个曾经的大师,离音乐和世俗生活很远了,但因为可能是一个“卖点”而被挖苦心思地联络和拜访。参与活动赚来的“钱”对这位大师来说应该不是很重要(因其极简的生活,不是挥霍),反之,如果未能出席,却需要支付一大笔违约金,这是大师所仔细关注的。大师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想要什么,比如对“冷熏肉”的品尝,以及对“唱歌”的欣赏。这个故事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强烈对比,能引发某种深思和讽刺的意味。深圳—张涛
集思广益,各位老师指点迷津之后,好像越来越清晰了。这个古怪的老头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经常描写的一位世外高人:通常住在孤岛或隐于深山,衣衫褴褛、骨瘦嶙峋却难掩仙风道骨、异于常人,寡言少语,行为怪僻,远离世俗,不问人事。他那布满灰尘的钢琴就像是挂在墙上的锈迹斑斑的剑,久未沾血却仍寒气逼人。谁都看得出他很爱惜他的剑,但从没人见过他使用过。北京—叶丽贤
这篇小说更像是人物素描,原型很可能是菲兹杰拉德认识或听说过的音乐家(有待进一步证实)。情节冲突不明显,走向是反高潮的,前面先通过各种逸闻或传说吊足读者胃口,让人殷切期待这位老音乐家的出场,后来慢慢把先前的印象打破,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位与社会脱节,与音乐绝缘,反应延迟,反复无常,但似乎又有点高深智慧的阿尔茨海默患者形象。因为这个人物是通过副艺术指导霍普金斯的视角来呈现的,所以有较大的理解和阐释空间。作家叙说中那种不动声色的、淡淡的幽默和嘲讽倒很耐人寻味。在回家地铁上写了一段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我不是这位作家小辑的策划者和编辑,理解不一定恰当。大家怎么看呢?很期待大家的回应和解读。深圳—张涛
他为什么要赶两个年轻人走,后来又为什么说喜欢玛丽的歌?这篇小说前面将一个素末谋面的艺术大师说得神乎其神,后来看到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场糟老头形象,真给读者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Kara
整篇小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其多重式内聚集的叙事手法,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可以控制对人物内心的透视, 从而达到有效调节叙述距离的目的。比如霍普金斯开头一段,那个“愿意,啥都愿意,啥都愿意” “我绝对需要搞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回来前,这是个好机会” “他受什么刺激了?也许......"还有那个”你这老家伙,你这老怪物,你怎么知道我弹了?“这些都是霍普金斯的心理活动,但下面又切入了内恩斯的心理——首先,他想,我要能交出他的名字才行......”最后的那段内心潜台词,“那你现在在想什么,你这老骗子,老坏蛋”简直神来之笔。这种视角的转换强化了作者对读者的阅读期待支配,读者会不知不觉进入到聚焦人物的意识。此外,这些潜意思独白貌似也应和了菲兹杰拉德作品中些许的幽默感。 一点点粗浅的感受。还有一点感受,通篇似乎弥漫着一种nostalgia的情怀,不管是对贝恩斯的回忆,还是对贝恩斯住所环境的描写,甚至玛丽的似摇篮曲的咏唱,以及最后贝恩斯对再次听到歌曲的向往,是否都是一种对遥远过去的回望?王中玉
我的感受是,这篇小说呈现的就是想象和真实,艺术与现实之间微妙的关系。贝恩斯之前只是活在霍普金斯头脑的想象中的艺术大师,而当霍普金斯见到本人时,发现大师也只是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普通老人,和别的老人没啥两样,这一度让他失落。最后小说又峰回路转,虽然看上去没啥两样的老人,临到末了还想要听女歌唱家的声音,好像从现实的烟火气里,又捕捉到了美好的灵光乍现。艺术是从生活停顿住的那个片刻,那个点滴中来的。小说揭示出来的这种现实与想象,与艺术追求的落差,是不是也是我们每个人,人生过程中,曾经体验到过的?北京—叶丽贤
我重读了一下原小说,从前后文推断,觉得“首先,他想,我要能交出他的名字才行......”这句话更像是在描述霍普金斯的内心活动(见到传说中的老艺术家,他脑袋短路了,一瞬间记不起老人的名字了)。“那你现在在想什么,你这老骗子,老坏蛋。“似乎也是霍普金斯的内心独白。前面也有类似这样未说出来的话:“你这老家伙,你这老怪物,你怎么知道我弹了?”大家觉得呢?沈阳—洪
对呀!他的视角写得很带劲儿,商人的狡黠和后生的敬畏,跟大师两个极端。至于说大师是心里真明白,都一清二楚,还是略有痴呆仿佛患了阿尔茨海默,这个有待商榷。Kara
@北京—叶丽贤,那些确实是霍普金斯的心理独白,但后面也有贝恩斯的心理活动。深圳—张涛
@王中玉您,提到了想象和现实的关系,这种体验确实有。打个比方说,心目中某个崇拜的大人物(名人或政要等),有一天应邀和我们共进晚餐,酒足饭饱之后,看到他坐在那里旁若无人的剔着牙。我们心里就会发出一声感叹:哦,原来他和我们一样,也是要用牙签的啊。
王中玉
艺术家名人身上的光环,会让我们容易陷入幻觉。而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破幻之后的真实,这也是文学常见的主题之一。温州—传记
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多大程度上先入为主的前提,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菲茨杰拉德的名声光环,在开始阅读前就预设了高雅作品这个大前提。换个人名地名,换个通俗作家的名字,是否很大程度上又将在低俗作品的大前提下进行阅读评价。沈阳—洪
不知怎的,我始终觉得哪位老人只是与人们的印象“差别”巨大,但并不算与先前的地位极大的“落差”。我挺理解老人后来选择那样的生活的。是个性的“选择”,不是“落魄”。王中玉
深圳—张涛
我觉得这个小说之所以耐人寻味,似乎就在于最后作者没有明确告诉读者,这位老人到底是真正的艺术大师,还是仅仅是一个沽名钓誉徒有虚名的平庸之辈。王中玉
温州—传记
嗯嗯,我感觉有时候看小说就像看一幅油画一样,远看很漂亮,凑近看发现只是一些粗犷的线条,再仔细看,这些线条看似无规律又有一定规律排列,连接,自然和谐地过渡。就像大千世界的奥妙一样。 Zoe
老人是不是喜欢玛丽代表的音乐类型?小说有这么几个细节:一开始说老人拒绝弹“第八交响曲”,是因为“太闹了”,后来小说从霍的视角介绍玛丽出场时,说她唱歌只会用“白声”,再到后来玛丽去见到老人时在鸡舍厨房哼唱摇篮曲时“声音文静,音量中等,没有对什么特别陪着小心”,“白声”是真实的,“摇篮曲”是安宁抚慰的,玛丽是安静的,可能老人追求的就是这种是和“太闹了”相对的真纯自然的音乐?他最后说“我已经好久没听到音乐了”,是在说玛丽的音乐才是他心目中的音乐?
鉴于《世界文学》分享会已近满员,新朋友可以通过底下的二维码(7天内有效)加入《世界文学》分享会plus:

如果无法直接入群,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的微信,邀请您进群。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