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欣赏|纳·赛阿达维【埃及】:她才应该是弱者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她才应该是弱者
纳娃勒·赛阿达维作 牛子牧译
他只能用右手的中指,其他手指都不行。小指不够长,拇指又太粗,食指自打被锄头砸伤后,就再也不长指甲了,而指甲可是精华部分,没准比手指头本身更要紧,因为指甲才是用来开路的利器。他曾经恳求母亲让他用个什么别的东西,锋利的东西,比如削尖了的竹棍,可是母亲用强壮的手指朝他一戳,他立马摔了个嘴啃泥,呛了满嘴的沙土,怎么都吐不干净。他眼见母亲一双大脚稳稳当当地走近前来,土地都在她结实高大的躯体下摇晃。母亲长长的手指握着锄头,将它高高抡起,就像举起一根风干的玉米棒一样轻松,然后又把它砸进土里,地面立刻像熟透的西瓜一样应声裂开。
母亲壮得像头牛。她能把比一头驴还重的包袱顶到头上。她驾轻就熟地揉面,打扫房间,准备饭菜,耕田犁地,怀孕生产,却从来不曾疲惫倦怠过。可是,身为他的亲妈,她用自己骨肉塑造了他,用自己鲜血喂养了他,却一点都没把自己惊人的力量遗传给他,他得到的只有丑陋的外表和懦弱的性格。
他总想要紧紧搂住母亲,把头埋入她双乳间,尽情呼吸她的气息,可这全然不是出于爱。他只想再一次融进母亲的身体,好让母亲重新把他生下来,给他强健的肌肉,让他脱胎换骨。当他亲吻母亲的时候,与其说是亲吻,不如说他恨不得一口口咬下母亲健壮的肌肉吞进肚里。可他不能这样做,他只能把头深深埋进两膝间,偷偷地怨恨母亲。有时候他会悄悄哭泣,有时候他会离家出走。有一次,他在傍晚时分从田里逃出去,把长袍下摆咬在嘴里一路狂奔,到了一处没去过的地方。夜幕降临,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远处阵阵狼嚎,他不寒而栗,只得赶紧往回跑。还有一次,他从母亲包里偷出五皮阿斯特,坐火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村子。在那里他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逛,不久便饥肠辘辘,脚底也火烧火燎地疼,只好又爬上火车回了家。又有一次,他从母亲包里偷出十皮阿斯特,偷偷跑到剃头师傅【埃及乡村的剃头师傅往往用土方为村民医治小病。】那里,站在人家面前直喘粗气。
“快说,小子,你来干什么?”
他口干舌燥,努力活动着黏在上颚的舌头,两手藏在长袍里。
“我的手指头——”
“你的手指头怎么了?”
“拿不稳锄头,不能像我妈那样。”
剃头师傅在他肩上推了一把,说:
“丢人不,小子。回去让你妈多喂你吃些肉,不就长得牛高马大了。”
于是他趴在母亲肥厚的膝头大哭大闹,终于闹得她弄了块肉来给他吃。他吃饱喝足,直打饱嗝,感到一股怡人的暖流延伸到手指间。他觉得两手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激动得一会儿握紧拳头,一会儿伸开手掌,一会儿屈起关节,一会儿绷直手指,渐渐地眼皮打架,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已是两天之后,随着那块肉被消化、吸收、排泄完毕,神奇的力量也逐渐消退了。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肌肉却软弱无力。时光飞逝,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步步逼近,他无法抵抗。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练习肌肉,他绷直手指,屈屈伸伸,关节咯咯作响。每天夜里他都这样练习,有时候他握紧十指,攥起拳头,还有的时候他用力过猛,手指扭曲错位,然后无力地瘫软下来。
他在门槛前呆立着,眼冒金星,几乎要失声尖叫,却发不出声音,只有一线口水从嘴角流出,像一条无毒蛇的尾巴,温热地在脸上滑过。
他感到有人伸出手指,像母亲一样有力地戳着他的肩头,让他坐下。臀部接触到刚刚擦过还有些湿润的地板,他好像感到安心了一点。他就这样呆坐着,闭着眼睛,半梦半醒,直到再次被人用力戳了一把,他一睁眼,发现那双分开的腿已经被送到自己跟前了。他回头一看,男男女女都聚集在院子里,敲锣打鼓,又唱又跳地等着他,他们瞪大眼睛,急不可耐地望向房门的方向。不,他绝不能让他们看好戏,他可不傻,他是全村最聪明的人——他都能给他们念报纸、写信,在伊玛目出门时做星期五的演讲。他必须昂首挺胸地走出这扇门,就像村里所有男人一样,甚至包括那个说话结巴,流着口水的傻小子。
他伸出右手,准备把手指扎入那两腿之间。可是他手臂突然一抖,手指跟着颤动了一下,便像死狗的尾巴一样无力地垂了下来。
他没有放弃,他继续尝试,继续垂死挣扎。他汗如雨下,顺着脸颊流到嘴里,他舔舔嘴唇,偷偷看了看那一左一右两个女人——她们每人拽着一条腿,同时扭过脸冲着墙壁,或者因为不好意思直视这种场面,或者因为看得太多已经懒得再看,或者不愿再揽上一项检验新郎性能力的职责,或者只是对当下的情况心领神会,所以替他感到尴尬。

于是他满怀信心地搓了搓手指。谁都不知道真相。那两个女人一直盯着墙壁,唯一一个真正关注事态发展的人已经由于担心自己的名声,紧张得神志不清了。
谁都不知道真相——除了她!她又是谁?他并不认识她,他俩素昧平生,他没看过她的脸,眼睛,甚至一根头发。今天本该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可是他看到的却不是新娘,甚至不是人,只是一团红面纱,下面伸出两条腿,被往两边拉开动弹不得,简直是待宰的牲口。可是即便如此,她还是来到了他面前,揭发了他的无能。她简直就是个圈套,捕获了他的懦弱和失败,他恨她,就像恨自己母亲一样,真恨不得把她碎尸万段,再泼上一瓶浓硫酸。
这怨恨让他豪情万丈,计上心来。他故作愤怒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鄙夷地咂了咂嘴。他得意无比地慢慢站直身子,转身出门,高昂着头颅,低垂的手里握着那条白手巾。他自信满满地踱着方步,居高临下地望向门口的老汉,突然把那白手巾扔到了他的脸上。白手巾干干净净,就像刚刚洗过,一滴鲜红的血都没染上。
新娘父亲羞愧地垂下眼睛,双肩骤然紧缩,头几乎碰着胸口。男人们从四面八方围过去,安慰他,鼓励他,然后齐刷刷转身冲着门口,严阵以待。
新娘出现在门口,红色面纱里小小的脑袋颓丧地低着,一道道指控的目光已经火辣辣地从四面八方刺过来。
(一九八七年)
作者介绍
由于对性、政治和宗教等敏感话题直言不讳,赛阿达维在阿拉伯本土争议巨大,作品常遭删禁,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她不仅为埃及政府所不容,也是宗教极端分子的追杀对象。她曾多年遭官方软禁,并于1981年被捕入狱,90年代被迫流亡美国。1996年,她结束流亡回到开罗。2011年埃及革命的浪潮掀起,老当益壮的赛阿达维在男女青年的簇拥下,走上街头。三年后,赛阿达维对埃及政治的失望依旧,但她仍未放弃对未来的信仰,也未放下她抗争的武器——笔。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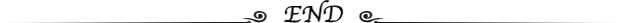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长按上图二维码,加入《世界文学》分享会plus

无法直接入群,可以添加《世界文学》
小助手微信,获邀入群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文娟 校对:秋泥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