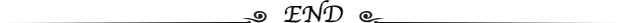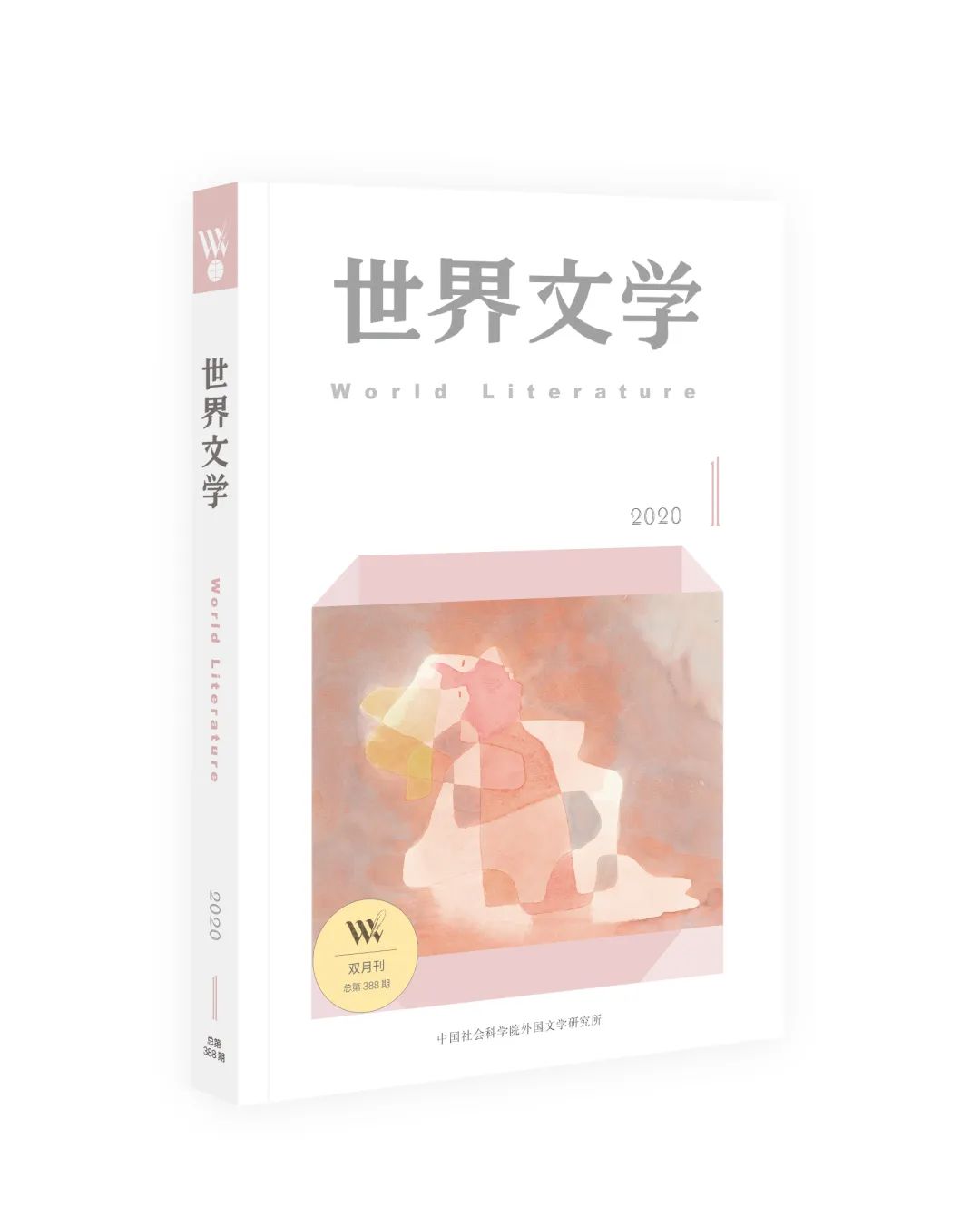2020年3月17日,巴黎因新冠病毒肆虐而首次采取了封城措施。法国各大报纸纷纷开辟“封城日记”专栏,邀请众作家记录自己在禁足期间的感受。每个作家被疫情和封城触动的敏感点都不同: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因封城造成的人与人的隔离而神伤的、为被禁足的读者开书单的、关心社会在非常时期的运行状况的、记录自己的隔离生活的……这些真切的思想和感受,可以见证当下,可以引起共鸣,或许更能够启发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此处所选作家日记,均来自法国《电视周报》2020年3月的“封城日记”专栏。
这是从痛苦和忧郁那儿偷来的一片柔情。照片里,一位老太太含笑将双手贴在一楼的窗玻璃上,窗户被白色纱帘遮去一半,老人们用这种帘子装饰自家老宅的做法由来已久。窗的另一边,街道上,一位女士——我猜她是老人的女儿——鼻子上扣着医用口罩,双臂交叉,将双手贴合在老人的两个手掌上。那双手倾诉了一切:爱、关注、强装的淡定和担心——“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张由帕斯卡尔·伯尼耶尔拍摄的照片上周六登上了《北方之声报》的头版。照片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让我恍惚间想到了自己。十四岁的时候,我隔着载我去夏令营的大巴车窗,望了父亲最后一眼。我挥别父亲,殊不知那是永别。今天,我们似乎碰上了同样的情形。最后的目光,最后的手势,也许吧。我端详着照片,生出疑问。窗玻璃真的把母女俩隔开了吗?她们的手指是不是永远也碰不到一起了?不要紧。她们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以至于那块玻璃,不管有或没有,都已不复存在了。它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想把自己的皮肤融进对方皮肤里的渴望,消除了一切隔离。剩下的是匮乏。我们无法抑制的渴望。熟悉的、遥远的、想望的、觊觎的、触不到的皮肤,我们的父母、孩子、朋友和爱人的皮肤。直到一个月前,我们能想象一个为了人类自身利益而禁止拥抱、亲吻和肌肤接触的世界吗?我想到了那些无法吮吸新生儿肌肤的父亲;那些分隔两地的恋人;那些双手经过一整天的刮擦而灼伤的收银员;那些在仓促的葬礼上未能亲吻母亲冰冷额头的姐妹;那些被人拦在楼外的医护人员。因为,你们明白,他们的手掌就是病毒的培养皿,从这些手掌到我们的电梯按钮之间,什么都可能在瞬间传播……我们待在现代的蜂巢中自我隔离,我们假装保持联系,视频中的微笑、照片、社交网络、通知、电话。屏幕加深了匮乏豁开的裂口——它什么都不能弥补,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填补人与人之间的分隔。拟像在我们之间额外设置了一道玻璃,上面映着可以防止我们发疯的幻像。但谁又真的相信呢?为了自保,人们强迫自己忘却甜蜜,忘却肌肤纹理,忘却身体颤动,忘却贴面的清凉触觉,忘却嘴唇的细柔包裹,我们强迫自己遗忘难忘,天哪,这是多么不容易,起床时一片空白,入睡时空空如也,这就是我,是你,是人类中所有脆弱的人。我想到了马拉巴特【库尔齐奥·马拉巴特(1898—1957),意大利作家、记者和外交官。】的一段话(出自其1973年出版的小说《皮》):“皮,我们的皮,这该死的皮。你无法想象,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皮囊【法语中“sauver sa peau”的字面意思是“拯救皮肤”,实则意喻“保命苟活”。】,能够干出何等的英雄业迹,能够犯下何等的无耻罪行。”这副双面皮囊,崇高又罪恶。作为秘密的停靠港,它传输着情感,以及病毒。我们终于明白,皮肤是我们唯一的防线。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大陆、边境、封禁:每个生物都是其自身的国土和岛屿。为了让我们觉醒,需要地球的这一下惊跳,可果然,我们是令人大失所望的动物。
于是,我看到了这张巨大的人皮,它像一张无边的犊皮纸,铺展在世界上空。一无所知的我们把自己的历史寄放在上面,把遭遇的意外铭刻在上面,把人类的集体传奇编织在上面。我们还身兼描摹时代的细密画画家,自以为掌握了时代全貌,但时代用它的鞋跟踩灭了我们的气焰。那些活在对炸弹、地雷、强奸和饥荒司空见惯的国家里的人民知道,皮肤是我们最珍贵的财产,而我们西方人才刚刚醒悟。可皮肤并不专属于我们,还有数百万的微生物在我们体内筑巢。意大利作家弗朗切斯科·佩科拉罗在法国不为人所知,但他早在一部很有预见的小说《和平年代的生活》中,就已经研究了寄生虫群体:“人类自诩为自然的主人是可笑的;把创世神话、外在于人的现实视作为我们服务的宇宙是可笑的。正是我们用自己的组织、皮肤和血液,为成千上万的物种、数十亿的标本提供了食粮……我们的不同在哪儿?我们的卓越在哪儿?”
这是一段皮肤的历史,一段脆弱的历史。但还不至于是万念俱灰的历史,不妨当它是一段张满我们的风帆、又从指缝中溜走的记忆。渴望重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但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看护好自己忧伤的皮肤【这一说法取自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驴皮记》。“忧伤的皮肤”是其直译名。】。卡·洛朗(Caroline Laurent,1988—),法国青年作家。著有《但突然,自由》《愤怒的海岸》等长篇小说,获得过玛格丽特·杜拉斯文学奖、报刊之家文学奖等奖项。

巴黎封城第八天。禁足令继续延长,每个人都投入到居家工作的义务当中,当自我产生抵触时——毕竟待在家里根本无法令人安心——我们选择通向外部的最后一道窗口:数字窗口。屏幕,一种数字形式的救赎,我们从上面读取信息。不管怎样,我们还能看到些好消息——尽管那些消息会时常遭到遗忘。《世界报》等一众媒体坚持这种鼓舞人心做法:他们没有否认当下局势的严重性,也没有掩盖会让一整周都陷入哀恸的沉重数字,但他们指出,与新冠感染和死亡的统计人数相比,被宣布为痊愈的人数也在增加。互助运动已具规模——其挑战将是运动的深度与可持续性,我们必须押注于此次应运而生的新公民精神:公民精神与防疫后盾的增强甚至赶超了新冠病毒的感染速度。这呼应了一位病人的话:“我们在检测病毒,病毒也在检测我们。”这句话在心理上给人以力量,病毒让我们有机会检验我们的团结程度,检验我们坚守的人文与人道的牢固程度。考验中固有失望,但也有美好的发现。《鼠疫》完美地阐释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暴露无遗,就像照片的曝光过程一样:本来不被察觉的东西,现在却显现出来,让人心生失望,或者反过来,让人重新获得此刻亟需的信心。让·格雷尼耶【让·格雷尼耶(1898—1971)是加缪在阿尔及尔上中学时结识的哲学导师,也是加缪一生的挚友。】读完加缪的小说后,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您的书让人产生一种沉重而深刻的共鸣……大家都会称赞这部小说的理念,即与恶对抗的坚持;以及看上去单调的叙述方式,我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品质,因为单调证明了心智的成熟。”
“禁足愉快”
我们的部分封城日记,讲述的就是这类“单调”。在史无前例的形势面前,单调成了反常的真理。人们以为,与旷古奇闻搭档的永远是紧张激烈,其实并不一定。每一天都是类似的,数字越来越糟糕,新冠病床和呼吸机的配给起初让人寒心,逐渐让人变得麻痹。加缪在小说中用单调与坚持对抗恶的辩证法,是集体在经受考验之时的典型做法。集体经验的结构是二元对立,每个人都在这一结构中各就其位,一些人过得单调,另一些人就过得饱和。
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在紧急状态下,占上风的、纹丝未动的,依旧是社会的运行状态,依旧是我们身旁的精英在没有万全办法自保的情况下接触他人的基本勇气:护工、收银员、公交司机、家政人员、送货员等,他们是基层中的伟大精英。辛·弗勒里(Cynthia Fleury,1974—),法国哲学家,心理分析师。现任法国国立工艺学院人文科学与健康方向讲席教授。著有《想象的形而上学》《照看是一种人道主义》等作品。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