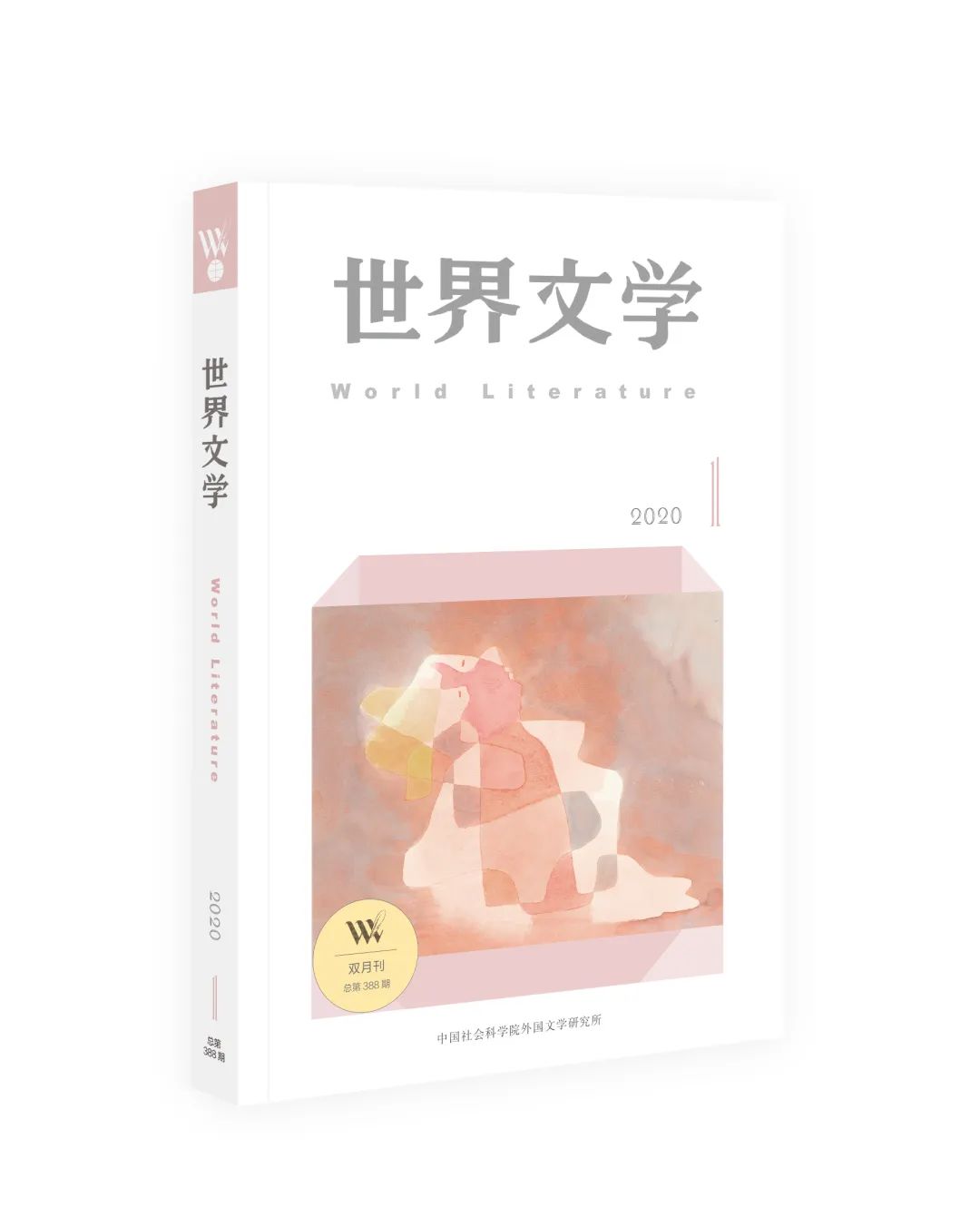文学专辑 |《世界文学》里的“汪星人”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养狗小记
〔捷克〕卡雷尔·恰佩克作 星灿译
在本篇散文《养狗小记》中,卡雷尔·恰佩克用饱含深情又不乏幽默的笔调,记录了与爱狗“敏达”相处的有趣日常。人虽是宠物的“主人”,可是爱到深处也难免会成为“狗奴”“猫奴”。恰佩克却自得其乐,并津津有味地把这一体验分享给我们。
至于谈到看家,这倒是名副其实。人之所以养狗,真的是想让它帮着看家。狗可真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主人,为他防贼防敌人。谁对它的主人有威胁它就扑向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便把狗看作忠诚和警觉的象征。可自从我养了这小狗以来,我却只能半闭着眼睛睡觉,因为得看着它,怕被人家偷走。它若想去散步,我就得跟着它,它若想睡觉,我就坐下来边写东西边为它当警卫,细心听着每一个声响。要是有一条陌生的狗朝我们走近,我便全身警觉,龇牙咧嘴地发出隆隆怒声。这时,敏达便瞅我一眼,摇着它那条小尾巴头,显然是在说:“我知道,你在这里保护着我哩!”
……
从一开始我就已经弄明白,养狗可以达到许多目的,其中包括充当这条狗的主人和指挥官。现在我倒觉得,更确切地说,敏达成了我的主人和指挥官。有时我就坦白地告诉它这一点,并直言不讳地说它是霸王,是折磨者,是滥用我的耐心和好意的任性而顽固的坏蛋。它好像压根儿不打算听懂我这些话,因为在我这么骂它的时候,它还热忱地直瞪瞪地望着我,摇着它那一小截尾巴,还伸着它那张粉红色的胡子拉碴的嘴鼻,冲着周围一个劲儿地乐,无声地乐,更有甚者,它还抬起那颗毛茸茸的脑袋,还想让我摸摸它。什么?你甚至把两只爪子趴到我膝盖上来了?去吧,去吧,敏达,我的丑八怪小㹴狗啊!让我把这篇文章写完吧!让我再说一下……
可是,还有一条不成文的狗规,那就是:热爱自己的主人。有些非常严肃的人把狗的忠诚看作为一种下贱的奴性表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按“奴性”二字我们想象不出能像狗的性格那样表现出如此饱满的热情。我从来没有过奴隶,可是我认为,它是,或者该是一只很守纪律、谨慎小心、沉着安静的活物。当它主人从编辑部,或别的什么地方回来时,它一见到他,不会高兴得汪汪直叫,不会往他手里咬,不会扑到他身上去拥抱他,总而言之,不会表现出放任不拘的热情和过于激烈的欢乐。而狗的大悲大喜情绪天生超过所有的动物和人。我无法想象一个绘图实习员会高兴得大喊大叫去搂住他顶头上司的脖子;或者一位神甫听到主教跟他说几句话便高兴得四肢朝天,在地上打滚。我说啊,人们跟他们的主人是一种皱眉蹙额的主仆关系;而狗对它的主人则是一种充满着热烈而无所顾忌的爱的关系。也许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古老的群体意识精神,一种活物的狂热的好群习性。它的灵魂深处仍然保存着手工作坊时期的那种天性。“人啊!”狗的这种目光对我说,“除你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可是你瞧,咱俩却是一个绝妙的狗的群体,不是吗?”
原载于《世界文学》1999年第4期


尼奇(一只狗的故事)
〔匈牙利〕德里•蒂保尔作 冯植生译
德里的中篇小说《尼奇》(1955)描写了50年代初匈牙利个人迷信时期一只小狗尼奇及其主人的不幸遭遇。在文中,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和极权落在个体身上的重压窒息着主人公,也窒息着小狗尼奇。不过正是在这样人人缄默、草木皆兵的高压环境中,安沙夫妇与小狗尼奇的爱与陪伴才更显得弥足可贵、温暖。文中小狗对被捕的主人的惦念、恐惧和无法理解的困惑,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可是,自从出了那桩事件以后,安沙的情绪变得迟钝了,尼奇也不像不久前的春天那样活泼而又直爽了。每当工程师轻轻叩门,它同样发出幸福的叫喊,紧张地跑到他面前,随后又跟随着他走进前厅,一次又一次地跳跃,可是仿佛情绪欠佳的人的气味也不同于往常似的,它很快也就放弃对主人作进一步亲昵的表示,垂头丧气地返回自己的睡铺去;有时,它甚至不吃晚饭,把鼻子搁在两只前脚中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一声不响慢慢吞吞吃饭的主人。夜里,工程师不止一次地高声呻吟或说梦话,这时,睡在隔壁房间的尼奇竟坐了起来,轻轻地发出抱怨似的叫唤声。安沙太太知道,丈夫又在做不平静的梦了。
尼奇已经进入它生活的第三个年头,假如以人的年龄作比较,我们可以设想,它正像一位20到25岁的年轻妇女。现在,它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充满着生活的乐趣。它行走、奔跑、跳跃,都充分显示出身心健康、快乐的特征;身体每一个部位的动作是那样匀称、和谐。它对什么都不在乎,显得落落大方。无论是冬天或者秋天,它总是干干净净,身上的毛白净光亮,眼睛炯炯有神,配上一只油光漆黑的鼻子,显得活泼而机智。显而易见,正像大自然为它准备的那样,尼奇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朝着可以预想的健康美的方向发展。
当安沙太太想起要照料那只狗时,最初那些令人烦恼的日子暂时过去了。最后,她决定把狗留在自己身边。她把丈夫最近穿的一件睡衣给了尼奇,把衣服垫在它的睡铺上。尼奇贪婪地围着衣服嗅着,然后又伏在它上面,继续嗅着。看样子,尼奇感到安心了。可是,每天晚上,尼奇还是等候着主人。晚上,楼房的大门关上以后,每当有人按铃叫门,尼奇就从睡铺上坐起来,侧着脑袋,这边歪歪,那边歪歪,神色紧张地倾听;有时,它还跑到房门那儿去,伏在地板上,用鼻子嗅着。来回几次以后,它竟可怕地倒吸一口气。呆了一会儿,它就慢慢地回到睡铺去,叹着气躺了下来。有一次,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大概是抱有的希望感使它的耳朵产生了幻觉,仿佛听出了工程师的脚步声,它像失去理性似地啜泣、甚至叫喊着,疯狂地抓挠着房门;主妇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奔到前厅去,打开门,狗也紧追在她身后。一个陌生的男人从她们房门口的甬道匆匆地走过。她和狗只好转身回到房里。夜间,主妇常常被狗轻轻地在地板上走动的脚步声弄醒。她拧亮床头柜上的台灯,发现那只狗就站在床边,耷拉着耳朵,低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面前的地板。
一天夜里,尼奇在梦中高声地呻吟,接着,它坐起身子,头往后仰,开始大声叫。主妇从床上起来,走到它的铺位旁边,蹲下身子,抚摸着它的脑袋。最后,主妇担心尼奇的叫声会吵醒邻居,便把它抱在怀里,带到自己的床上去。尼奇睡在主人的床上,这是头一遭。自从丈夫被捕以后,安沙太太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她,或者是她的狗走在街上,都没有人理睬。在这幢楼房的住户中,有些人明显地有意回避她;有些过去见面时总喜欢跟她聊上几句的人,现在相遇时也忘记跟她打招呼了;有时候,甚至会在她背后引来一阵惊悸的仇视的目光。安沙太太尽量克制自己,以便使自己的生活尽可能不为人觉察地适应这幢公寓房子的环境。她外出时总是有意避开人们,像影子一般走过甬道和楼梯。除了她那只狗紧张的吠声外,邻居们从她的房间里听不到别的声音。
德里•蒂保尔(Déry Tibor,1894—1977),匈牙利当代著名小说家,曾于1948年荣获第一届柯苏特文学奖(匈牙利政府设立的国家级大奖)。他出生于布达佩斯大资产阶级家庭,但由于受到进步思想影响,早年就背叛家庭,投身工人运动,曾积极参加匈牙利1919年苏维埃革命,同年加入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革命失败后,他被迫先后流亡维也纳、巴黎、柏林等地。30年代返回祖国,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坚持继续创作。


狗
〔俄国〕伊凡•屠格涅夫作 谌容译
本篇小说《狗》写于1865年,即写作《父与子》与《烟》的中间,体现了作家在艺术上的新尝试,因此风格迥别于其代表作。《狗》讲述了一个奇幻故事:主人公斯杰潘内奇产生了床下有一条狗的幻象,直到他真的拥有了一条小狗“特列佐尔”,床下之狗的幻象才消失。而后,特列佐尔忠诚地保护自己的主人,舍命救他于“虎口”之下。
这篇作品构思新颖别致,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曾对此篇颇为赞赏。1893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狗》太好了,语言惊人。如果您已经忘记了,那么请重读一遍吧。”
有一回,大约是六年前吧,那天,我回家已经很晚了,在邻居家打了会儿牌,——这时节,请诸位注意,正如常说的,我一点儿也没有醉;我脱了衣服,上床躺下了,吹灭了蜡烛。请你们设想一下吧,先生们!我刚刚吹灭了蜡,在我的床底下,立刻就折腾起来了!我想,是耗子?不对,不是耗子。它抓挠,乱动弹,蹭痒痒……后来,俩耳朵还扇得啪啪直响!
“毫无疑问,是条狗!可,哪儿来的狗呢?我自己不养;我想,难道是什么‘野东西’自己钻进来了?
眼看我的手已经拉着门把手了,突然,仆人的房后响起了脚步声、尖叫声、小男孩儿的喊声……我回头一看,我的天哪!一头巨大的红色的猛兽照直朝我扑来,我都没认出那是一条狗:只看见张着的大嘴、血红的眼睛、浑身竖着的毛……我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儿,这个怪物已经跳上了台阶,两条后腿直立,当胸朝我扑来——什么样的险情呀?我吓傻了,手都抬不起来了,完全昏过去了……我只看见数不清的白獠牙在我鼻子尖上晃,血红的舌头沾满了泡沫。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像个皮球似的在我的眼前腾空而起,这是我亲爱的特列佐尔在守护着我呢;它呢,像蚂蝗似的咬住了那个野兽的喉咙!那家伙低声吼着,喀喀地咬着牙,调头就跑了……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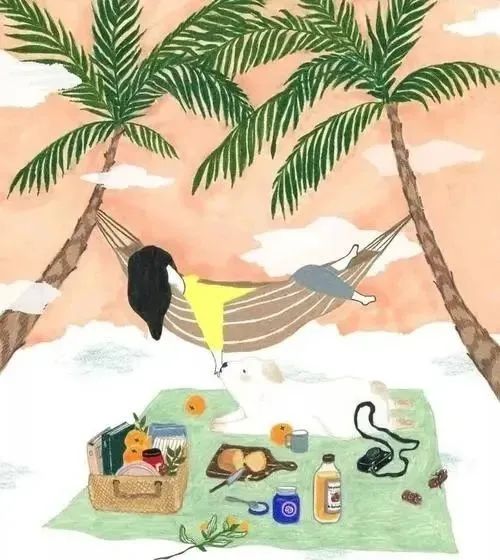

丁狗
〔英国〕弗•贝内特作 任学忠译
《丁狗》的故事发生在澳洲一个远离城市、人烟稀少的大牧场,丁狗(Dingo)是指澳洲野狗。主人公收留、养大了一只漂亮的小丁狗“幸运儿”。在她的身上,人类温暖情谊对她的驯化,与自然野性力量的召唤一直反复交替,让她不断地往返于牧场与野外之间。
全世界到处漫游的狗,我都不喜欢,都不想要。但我不得不将我的爱放到一只杂种的丁狗身上。这是一只澳大利亚内陆的普通野狗。这只母狗,后来成了我的狗,逐渐地用她刻骨铭心的方式、用她自然而然且很有技巧的爱赢得了我的心,在旁人看来她并不漂亮,但是在我眼里却是例外。她有一双松软且下垂的耳朵,四条长长的腿。一身从澳洲野狗和中型牧羊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又硬又黄的毛皮。作为她的双亲之一的那种牧羊犬竭尽全力地管理着那么多的大牧场。她的那双金色的眼睛弥补了她外形的不足,颇具特色。眼睛深处闪耀着智慧的光泽。因为是一只小狗,她还没有展示出作为丁狗本能的那种杀戮者的特色来。
我简直成了我的这个“幸运儿”的忠诚奴隶了。我把一个孤独男子所有的爱统统倾注到了这只黄色小狗的身上。我看着它从一个不起眼的烂毛团长成了一条瘦瘦的青年母狗。我喜欢她的那副长相:金色的眼睛,细长、苗条但肌肉健壮的身体,末端有一撮白毛的尾巴,总是竖起来,就像海上一面活动的三角信号旗。
远远地,丁狗们围成了一个运动着的圈。虽然我知道那些野狗们在饥饿时是如何的凶残,但我自己过去从没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丁狗们把我和牛群围在圈里,等待着进攻的有利时机。牛群在恐惧中跳跃着,抵抗着,吼叫着。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我的“幸运儿”。她更修长了,完全长大了。她奔跑在暴乱的狗群之中和它们纠缠在一起,咆哮在一起。她原来早已跑到它们一伙中去了!我思索着,猜想到这就是她消失的原因。我并且认为如果她想回到我这里来,她早就回来了。
我用劲吹着口哨。这昔日的哨声她是太熟悉了,哨声是那样的刺激,直戳人耳,命令她返回到我这里来。我从马鞍上跳了下来,张开了双臂,她一下子跳入我的怀抱,舔着我的脸。她跳得那么高,使劲地翻着跟头,向我表明了,对我们的见面她是那样高兴。
我爱抚地抱着她,低声向她诉说着钟爱的话语。我泪眼模糊,感到了她那黄色皮毛的温暖,又一次从她的双眼里看到了一缕金色的光。现在我再也不会让她走开了。
弗•贝内特(生卒年不详),当代英国作家,祖居英格兰南部城市哈斯丁斯,但多年和羊群、牛群在澳洲大牧场里度过。孤独的生活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


杂种狗“吉卜赛”
〔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作 杨静远译
《杂种狗“吉卜赛”》(Gipsy, the Mongrel,1940)是伍尔夫的晚期作品,创作于她逝世前一年。小说通过两对中年夫妻的冬日炉边闲话,描写了一只落拓不羁的吉卜赛狗(吉卜赛)和一只循规蹈矩的贵族狗(赫克托)的小小悲喜剧,并且借着对比狗的个性特色,反映人的个性特色。
“你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俩趴在那儿,”汤姆接着说,“吉卜赛在火炉这边,赫克托在那边。他俩天差地别,要多不同有多不同。这是个出身和教养的问题。赫克托是个贵族,吉卜赛是平民百姓的狗。这很自然嘛,她妈是个狗贼,她爹是什么只有天晓得,而她过去的主人是个吉卜赛人。你带他俩一道出去遛弯儿。赫克托严肃古板,像个警察,一门心思遵纪守法。吉卜赛呢,她蹦过栏杆,吓唬那些王家的鸭子,却总是护着那些海鸥,因为海鸥也是些浪荡子,跟她一样。我们带着她沿河走,人们在给海鸥喂食。‘吃你们的小鱼儿吧,’她仿佛在说,‘这是你们挣来的。’信不信由你,我亲眼看见,她用嘴叼着食喂一只海鸥。她对那些娇生惯养的富家狗——哈巴狗啦,膝上狗啦——可没好气儿。你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俩在炉毯上准是就这问题争论来着。天晓得,她硬是说服了那个老贵族,使他转变了观点。这一点,我们要是早料到就好啦。是啊,我时常为这自责。可事情总归是这样,事后聪明是容易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艺术先驱之一,代表作《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等。


狗过的日子
〔英国〕马克·斯特兰德作 龚容译
《狗过的日子》(Dog Life)初次发表于1985年,小说以男主人公向妻子讲述自己曾是一只狗的奇幻经历,来隐喻中年夫妇婚姻中的问题。
格洛佛·巴利特和他的妻子特蕾西,身上盖着淡蓝色的细薄布鸭绒被,躺在他们那张特大的床上,瞅着那片丝绒似的芬芳馥郁的黑暗。接着,格洛佛转过身子去望着他妻子。她的脸给一圈金灿灿的头发围着,显得比实际要小,嘴微微张着。他要告诉她一件事,可是非说不可的这件事也许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所以他犹豫着没有开口。私下里他已经琢磨了很久;这会儿他觉得非把它公开出来不可,不管冒多大的风险。“亲爱的,”他说,“有件事我一直打算告诉你。”
特蕾西忧心忡忡地瞪大了眼睛。“说呀,格洛佛,不过,要是这件事会让我不痛快,我宁可不听……”
“我只想告诉你,认识你以前,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什么意思?”特蕾西望着他问。
“我是说,亲爱的,过去我是一条狗。”
“你在骗我,”特蕾西说。
“不,我没有,”格洛佛说。
特蕾西盯着她丈夫,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房里冷清清的,一片寂静。正是讲知心话的时候;特蕾西眼神温和下来,显出很关切的神情。
“一条狗?”
格洛佛说完等着特蕾西开口。他后悔告诉了她这么多事。他感到很羞愧。他希望她能理解,当一条狗并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这种偏差,是因为他生来非这样不可,这倒也没什么可悲的。有时候一个人的狂暴本性,可以在对惊人的异化的期望中找到最美妙的表达方式。因为人仅仅在某种程度上才是他们自己。夜晚早些时候,格洛佛心里充满了悔恨,如今却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自豪的感觉。他看见特蕾西阖上了眼皮。她已进入梦乡。这种真相已经忍受下来,而且被一种把她安然引入另一个命定的夜晚的需要弄得无足轻重。他们会在早晨醒过来,彼此望着对方,就跟往常一样。他告诉她的这件事,他们再也不会提起,这并不是出于礼貌,或是怕使对方不快;而是因为,这种脆弱的表现,这种热情洋溢的失误,是每种生活中都避免不了的。
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1934—),诗人,生于加拿大,后定居于美国,曾在多所大学执教。他的作品主要有诗集《睁着一只眼睛睡觉》(1964)、《搬家的原因》(1965)、《我们的生活故事》(1976)、《诗选集》(1980)等。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2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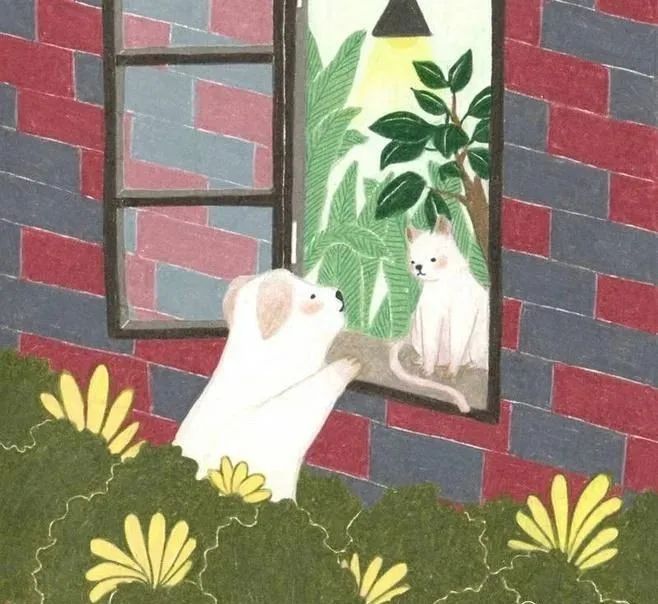

狗日子
《狗日子》讲述了两只失去主人的小狗在城市中度过的艰难时日。
小黄狗无意中走到了坐落在公园中心的游乐场中。它在这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它从敞着的门缝往哈哈镜厅探了探头,然后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但没走两步,身后的门就被一阵风“哐”地一声关上了。随着这关门声,大厅里耀眼的白炽灯立刻自动亮了起来。小狗突然间从四周的镜子里看到成千上万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小狗在盯着自己看,顿时吓了一跳。这么多狗!它吓得后退几步,想从这里逃出去,却再也找不着进来的门。四周全都是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狗……
小黄狗看着眼前众多的狗,“汪汪”地叫出声来给自己壮胆,但是面前的那些狗也同时向它吠叫着。小黄狗吓得浑身毛发竖起。此时此刻它想起了勇猛顽强、不畏艰险地与群狗拼死搏杀、舍身救自己的耷拉耳。这一次也许该它亲自上场了吧。它浑身热血沸腾,开始绷紧身体,集中精神,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它再一次对着群狗“汪汪汪”地吠叫起来。那些狗也如法炮制,齐声向它吠叫。但是这么多狗却没有一只胆敢靠近它、向它发起进攻。那些狗也效仿小黄狗的样子,吠叫几声后便安静下来。它对此无法理解。小黄狗惶恐地朝着对面的、身旁的、身后的狗连续吠叫……周围的狗也全都像它一样紧张地活动起来,纷纷向它吠叫了一阵。小黄狗此时已经感觉自己不可能轻易从这些和它一模一样的小黄狗中脱身。它想奋不顾身地冲向狗群决一死战,但是它发觉眼前那些狗也都有同样的想法,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向它发起攻击。群狗的疯狂嚎叫声已经响彻大厅,整个大厅炸开了锅,而这刺耳的吠叫声和群狗不断冲来的场面也让它惊恐万分。它越是焦躁不安、吠叫不止,大厅里就变得越混乱,吠叫声震耳欲聋。小黄狗力图咬住一条狗的腿,但这时却有无数只狗咬向它的腿。它勇敢地往前攻击,那些狗也同时向它发起攻击。小黄狗浑身发冷,感觉疼痛,不知哪一条狗会冲上来首先咬住它的腿。无论小黄狗如何疯狂地进攻,都无法阻止它们。但是它们尽管数量众多,却没有一个胆敢首先冲击它、扑咬它。这种状况确实让小黄狗感到无法理解。随着小黄狗的吠叫,群狗也开始狂吠起来,如同有成千上万条狗同时吠叫,几乎要把镜子厅的屋顶掀翻。小黄狗惊恐不已,感觉自己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狗围在了中央,危险也逐渐向自己逼近。不断逼近。
苏勒坦•热耶夫(1958—),小说家、剧作家,是吉尔吉斯斯坦新生代文学的代表人物,曾凭借富有实力的小说和剧作先后获得吉尔吉斯斯坦托合托古勒国家文学奖和列宁共青团奖,其代表作有小说《手握太阳的孩子》《洪水》以及剧作《女王的泪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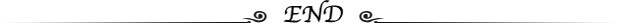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添加《世界文学》小助手,获邀进入《世界文学》分享会plus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秋泥 排版:文娟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