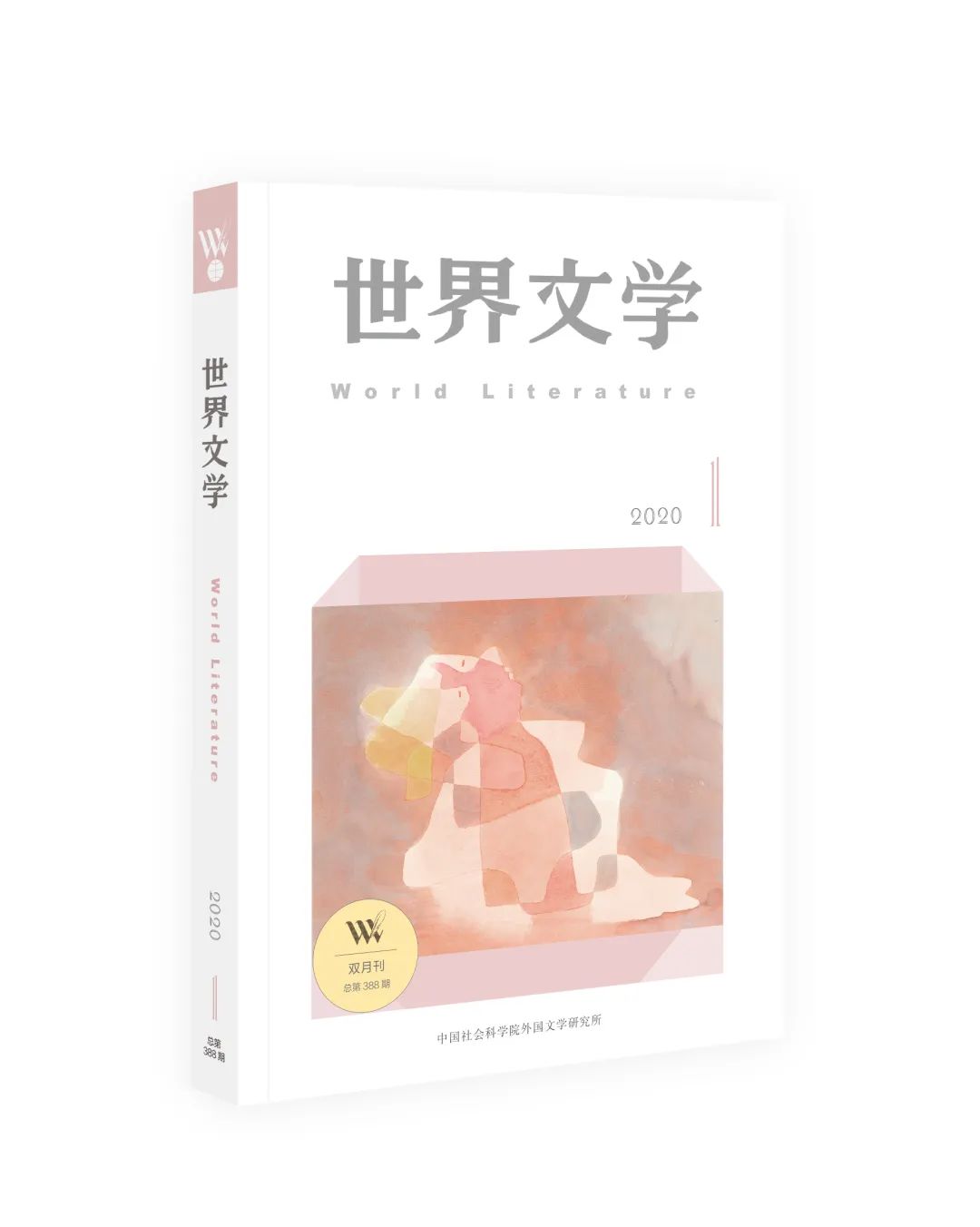劳动节专辑 |《世界文学》中那些五花八门的职业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五一劳动节
在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我们从《世界文学》往期刊登过的小说中,节选了五种不同职业的故事。这些主人公谋生方式各异,境遇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抱着巨大的执念或热情,每个人的经历也都称得上是有故事的人生。正如海明威所说,“任何人的人生,如实讲述,就是一部小说”。(Any man’s life, told truly, is a novel.)


采贝人
采贝人正在水槽边刷洗几只帽贝,蓦然间就听到水上计程船穿过那片海礁, 矻矻嚓嚓地开到了近旁。这声音听得他浑身发紧——船身剐蹭着指状珊瑚的杯盏和笙珊瑚的细小管枝,扯落花朵状或蕨叶形状的软珊瑚,还毁掉了好些海贝:橄榄贝、骨螺、蝾螺、密纹泡螺和巴比伦卷管螺,都被挨个儿凿出了窟窿眼。有人想要过来寻到他,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他拿起自己的采贝桶,给图麦妮扣好项圈,让她带领着他们从小路下去,再往海礁方向走。空气里有闪电过后的味道。
到中午时他们已经蹚水走出去一公里,到达了珊瑚礁巨大弯曲的中脊位置。身后的泻湖水面静静摇荡,前面是低低拍打的碎浪。就要涨潮了。图麦妮的绳圈已经解开,她半截身子露出水面,正站在一块蘑菇形状的石台上喘气。采贝人弯下腰,手指在铺满砂子的沟堑里聚拢、抖动、拂拭、寻找着海贝。他捏起一只破损的长旋螺,用指甲沿着它的螺旋凹线划过去。“纺轴长旋螺。”他说道。
没等到下一个海浪拍打过来,采贝人已经自动拎高自己的采贝桶,不让它被浪涛淹没。海浪刚退,他的两只手就重新插入沙砾,手指在海葵丛中的某个凹陷处摸索起来。他在一块脑珊瑚旁边稍稍停顿确认,然后继续去追一只挖洞逃走的海蜗牛。

一夜之间他的世界就变成了贝壳、贝类学和软体动物们的天地。在白马市不见阳光的冬季里,他学会了布莱叶盲文,开始邮购贝类书籍,等到冰雪融化后再翻开木料去寻觅丛林葱蜗牛。十六岁的时候,他心急火燎地想去先前在《大堡礁奇观》这类书里了解到的海礁,从此永远地离开了白马市。他在帆船上充当船员,途经整个热带地区!桑尼贝尔岛,圣卢西亚,巴丹岛,科伦坡,博拉博拉岛,卡恩斯,蒙萨,莫雷阿岛。在失明状况下完成了这一切。他的皮肤晒成了深棕色,头发变白了。他的手指、感觉、心智——他的一切——都痴迷专注于贝类外骨骼的几何形状、钙质造型,还有斜面、棘刺、壳顶结节、螺旋纹线和褶襞。
安东尼·多尔(Anthony Doerr,1973—),美国当代作家,曾获2015年普利策奖。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采贝人》《记忆墙》,长篇小说《关于格蕾丝》《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等。

候补宇航员
前排座位上穿着同一种式样的连肩皮上衣、戴着蓝色绒线帽的两个人似乎是疏远着大家,默默地坐在那里,像是有一堵透明的厚墙隔在他们与众人之间。那年轻的一个,脑后的黑发修剪得短短的,有时转过粗壮黝黑的脖子,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另一个,差不多已经满头白发,困倦而郁悒地望着窗外。他们是刚刚起飞了的两个宇航员的候补宇航员。年轻的那个,我不太熟……第二个,我们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我们初交的时候,他也跟他现在的搭档一样是个满头黑发的漂亮小伙子,可是他一直是一个候补宇航员。对这个年纪大一些的,背地里我们已经不称呼他的姓名了。谈话时,我们更经常地简单称他为“白头翁”。他,作为候补宇航员,到这里来过多少次了呢?他,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现在想什么呢?火箭升天的吼声不是还萦绕在他的脑际,他本来是可能飞向天外的呵,本来是可能的……
“下次就该您起飞了。您瞧着吧……”
白头翁显然早就猜到我的用心了。他笑了笑,请我坐下。
“问题是……准备呵准备——弄到最后……还得从头来,从零起。”
他弯下腰,拔下一根枯干了的野草,在手里转了转,又用长长的,像接出来一节的手指揉了揉,似乎用手的这个动作能够使心情平静下来。尽管这是枉然的,但是毕竟可以用它冲淡主要的话题,冲淡这次谈话势必要导致的毫无必要的推心置腹。
“我嘛,可以说是属于加加林那一批的人了……当然入队的时间比他晚。我经历了多少波折呵……生活,可以说,一变就是一百八十度。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这批志愿者,或者说同意接受体格检查的人,从各个飞行联队集合起来,像住疗养院似的闲住了一个半月,末了,能够通过体检全过程的,平均十五个到二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这样一来,让我们坦白地说吧,小伙子们可就耸拉脑袋了,因为对我们的活机体各个系统进行周密检查之后,有些人就干脆不能再飞行了。谁能保证你不会是那种被取消飞行资格的人呢?和我同屋的三个人就没等检查完毕,抬腿回家了。由于不愿意丢职业,就干脆拒绝继续检查身体了……常言说:宁耍到手的小山雀,不要天上的大仙鹤。”白头翁停了一下,似乎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说下去,终于又开了口。“我的体检顺利得出奇——一帆风顺。医生们只顾点头:好一个棒小伙子,简直挑不出毛病来,没说的……合格!……这是多么好的字眼呵!它代表着难以捉摸的幸福。可是,合格还不等于万事大吉。合格又怎么样呢?”

“以后可就像常言所说的,要靠命运了,尽管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白头翁又回到自己的话题上说,“我被编进宇航队。大概因为我是所谓的太合格了,所以被指派去完成降落伞系统的试跳训练。降落伞是新型的。我的一个同伴,在完成飞行任务之后,就准备用这种降落伞系统着陆。您明白吗?我坐在飞机上,在敞开的货舱门旁,穿着笨重的密闭飞行衣,背上是带有主伞和副伞的托架,架上有各式各样的仪器和着陆用的一整套自动起动装置。托架下面还有一个小箱子——安全备用器。这全套装备,足有一百多公斤重,让你站也站不起,坐也坐不舒服……活像一个安着一对活眼珠的模型假人。我自己从飞机上想跳都跳不下去,得由两个棒小伙子把我扶起来,推出机舱,难道不真的就是一个假人吗?我坐在货舱门旁就想:为什么他,比我先飞向宇宙的人,不去试跳这套降落伞系统,却偏偏要我来试跳?……当然,这是事后——现在我才发这通议论。事实上,如果你一味地感情用事,非探讨个究竟不可:为什么让他飞,不让我飞,那就干脆不要去当宇航员。那种生活你就过不了关。到头来还要一事无成。我现在这样认为:很可能在试飞降落伞系统的同时,也在考验我的性格。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有一件事不太好,其实也不是什么不太好,只是一想到你不是一线宇航员,而是候补宇航员,心里就万分不平……您是知道的,我那时候当候补宇航员,时间还不久。后来,我的时运也到来了,正像古代小说里所说的‘他的吉星也升起在天边’……”
从那时起过去好几年了。在塔斯社的电讯里,我一直还没有遇到白头翁的名字。
选自《候补宇航员》,原载于《世界文学》1980年第4期,【苏联】维·斯捷潘诺夫作,石言译。

发明家
“你不过是会画图,而我却会发明,七岁的男孩约翰对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尼尔斯说道。
“会打样描图是最要紧的。”
“画图我也会。”
约翰就在一个纸口袋上画出了一整台采矿机械,形状同他在赫特湖边的矿山里亲眼看到过的分毫不差。随后,他又在山坡上掘了一个三十来厘米深的坑道,算作是矿井。他造的这口矿井的各种技术装置一应倶备,就是井道太狭窄,细长得活象条小沟。等到他开始安装采掘机的时候,他哥哥忽然注意到这台机器上有些部件好像跟日常见到的大不相同。
“那些地方不对头,应该照着另外的那种样子造才对。”他告诉弟弟说。
“这些是我想出来的新东西。要是人家把机器造成这个样子,干活就会省劲多啦。”
“你把那些不对的地方叫做什么来着?”
可是,安•卡西迪对太阳能发动机那类东西不感兴趣:“上尉,最好还是发明一个捕鼠夹子吧。”
八十五岁的老发明家终于惊愕得抬起头来盯着她。这个红头发的娇小的爱尔兰女人如今也是老态龙钟了。旁的机器都可以运转不息,只有人这部机器里的零件在不断磨损,直到全部毁坏,却没有新的可以更换。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把手头上的工作都先撂下,而去发明—个捕鼠夹子吗?”
“我就是这意思。我从商店里买来了上百只捕鼠夹子,可是它们一点也不管用。”

他重新披衣下床——虽然在披上那件千疮百孔的晨衣时,手脚无力,都已经不愿再动弹了。他走到绘图桌旁,把所有的草图,还有已经画好的图样统统撕下来,重新钉上一张崭新的绘图纸。像往常一样,他开始吹着口哨,动手绘制一项他一生中从未想过的新发明。在这个最初阶段,没有人能够看得出它将来的形状。发明家正在绘制的每一份新的结构图样都还只是一种设想。
起初,他满以为这区区小事对他说来只不过是易如反掌。过了不久,他就发现这桩差使非但毫不简单,而且大为棘手。不过,他对克服困难已经习以为常了。唯其艰难困苦,方才砥励着他矻矻终日、百折不挠地钻研探索。他画出了一张又一张的图纸,但是随手又把它们撕掉了。直到破晓,他才终于画成了一个捕鼠夹子,一个常见的捕鼠夹子,不过大得非凡,光是诱饵就要用一块半公斤重的奶酪!
安·卡西迪走了进来。
“去叫人把这个制造出来。”他吩咐道,一面把图纸拿给她看, 上面各个竖切面、横切面、轮廓布局、尺寸座标等等都画得一清二楚。
小爱尔兰女人破天荒第一回仔细地审阅起她声名赫赫的主人绘制出的创造发明图纸来。
约翰·埃立克逊重新回到绘图桌上。他在没有把一个问题解决得至善至美之前是决计不肯罢休的。他相信自己的脑子是一部累积储存器,它能靠着自我充电来获得能源。他相信自己的思维就是一部永动机,是以活生生的人的模样出现的机器。除此之外,他对任何别的东西都不相信。
他抽出了整整一个星期时间为捕鼠夹子大伤脑筋,而不去搞他的太阳能发动机。他全身心都扑在了这项发明上面。但是,他感到精神不济了。他手下的人直率地要他卧床治疗。他听说他害的大约是一种什么白莱特氏症一不可救药的肾脏炎症。
为了要证明他们说得不对,他请来了一位名医。那是他从前还同别人来往时结识的老朋友——马尔凯医生。
“马尔凯,”他在床上坐得笔直,粗声大气地问道,“害了白莱特氏症的人还能够照常工作吗?”
医生一眼就看出了对方已病入膏肓,便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上尉,患有白莱特氏症的病人绝对没有做任何工作的权利。”这无疑是一份死刑执行书。发明家身子往后一仰,瘫倒在床上,就此咽了气,寿终正寝。他去世的这天恰好是二十七年前莫尼特号快艇出海驶向汉姆森停泊场的那一天。
在他的绘图桌上,仍然钉着那张尚未绘制成功的捕鼠夹子的构造图样。
伊瓦尔·鲁·约翰逊(Ivar Lo Johnsson,1901—1990),瑞典当代最享有盛誉的作家,多次获得瑞典各种文学奖金,是当代瑞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主张文学应该触及社会生活。主要作品有《莫娜死了》《只有一个母亲》等。

流浪画家
七月的一天,一位年轻漂亮的太太走进闷热的地下通道,想要花五百美元找一位流浪画家为自己画像。而当画像完成的时候,故事才刚刚开始……
“请坐,太太!”这个不负责任的画家指着空出来的座位说,
“我马上给您画。”
“不,您画不好,”莉季娅·尼古拉耶芙娜摇了摇头。
“我怎么画不好?我什么样子都能画!”
“您不会画。”
“我怎么不会?我是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毕业的。”
“问题不在于谁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而在于谁有什么样的才能。”
这时又有一个画家画完了,但莉季娅·尼古拉耶芙娜刚要走过去,他就摇了摇头,拒绝说:“您还是等瓦洛佳·利哈列夫吧。”
“他在哪儿?”
“他去什么地方了。肯定会回来的。但他只给他喜欢的人画像……”
“那你们呢?”
“我们谁给钱就给谁画。您先坐一会儿吧,那就是他的地方,”画家指着挂女中学生画像的三脚架旁的几把小椅子说。她坐了大约十分钟,边等边看着假塞尚画纸上出现的那个似乎有些相似但显然是美化了的瓦洛佳那张毁容的脸。
“您要画像吗?”
莉季娅·尼古拉耶芙娜应声转过头去。她面前站着一个瘦瘦的、几乎是皮包骨的年轻人,穿着一条破旧的牛仔裤和一件褪色的运动衫,深陷的两腮和下巴上长满短短的胡子,长长的头发梳成一个小辫。他目光专注、略带微笑地看着眼前的女人,神经质地搓弄着手指,就像音乐家即将登台演出前的样子。
“对,我想画一幅肖像!”
“您干嘛要在这儿画呢?请到我的画室去吧!我给您地址。”
“不,就在这儿吧!”莉季娅·尼古拉耶芙娜任性地抿着嘴回答。
“那好吧,就在这儿。咱们先试试……”
“就是说,您喜欢给我画像?”
“喜欢。但是我得警告您,我收费高。”
“这不是问题。您要多少我给多少,只要我也喜欢您画的画像。”
“就这么说定了。”

“您希望我画您戴着墨镜的样子吗?”
“当然不是!我只是忘了……”
“这么漂亮的眼睛怎么可以藏起来呢?”瓦洛佳笑了笑,“您的眼睛是傍晚时勿忘我的颜色。”
“为什么是傍晚的勿忘我?”
“因为太阳落下去后,所有的花都会忧伤。”
“莉季娅。”
“我叫瓦洛佳。”
“我知道了。您和其他人不一样……”
“这有用吗?与众不同的人往往生存艰难。”
“什么?”
“秘密。”
“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秘密……”
“我没有什么秘密,以后也不会有。您快画吧。” 莉季娅两颊绯红,仔细描过的眉毛愤怒地扬了起来。
“太棒啦!噢,您的眼睛现在好漂亮啊!”
“怎么漂亮?”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丁香花的颜色。”
“这都是您想象出来的。”
“停!请您尽量别动!”
半个小时后,那些艺术家都丢下自己的顾客,围拢到瓦洛佳马上就要完工的肖像前。
“你真是个天才,利哈列夫!”假塞尚赞叹道。
瓦洛佳脸色苍白,浑身是汗,小声吩咐了一句:“发胶!”
有人立刻递过一个上面写着“绚丽”二字的小瓶子。他挤出一小堆物体,空气中立刻漫起美发厅里独有的味道。
“这是为什么?”莉季娅·尼古拉耶芙娜问。
“怕画像时间久了脱色,需要固色。”
“为什么要用发胶?”
“为了漂亮。想看看吗?”
“当然想。”
瓦洛佳再一次认真地看了一眼画像,然后慢慢地转过画夹。莉季娅·尼古拉耶芙娜盯着纸上那张栩栩如生的脸看了好几分钟。画像画得惊人地相像,仿佛用无数条神经线编织出来的一般。这些线条似乎在纸上隐约摇动着,轻轻撞击着。最让莉季娅·尼古拉耶芙娜震惊的是脸上的表情,是女人那种忧伤犹疑,准确地说,就是绝望的表情。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波利亚科夫(1954—),俄罗斯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曾获果戈里文学奖、布宁文学奖等。小说《无望的逃离》《羊奶煮羊羔》和《蘑菇王》已有中文版,其中《无望的逃离》于2002年获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立的最佳外国小说奖。

健美大赛训练教练
若昂是健身馆里培训健美大赛选手的教练,说话干脆利落,笃信经过魔鬼训练可以开发出人类本身的巨大力量,一心想要给自己的健身馆培养出冠军学员。一天,若昂遇见了从未练过健美项目但是身体条件绝佳的沃特卢,如获至宝。
我们到健身馆时,若昂正同科尔孔迪纳站在单杠下。“若昂,这位是沃特卢,”我介绍说。若昂用犀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说:“我想和你谈谈”,说罢朝更衣室走去,我跟在他身后。“这样可不行,可不行!”从他脸上我看出他着实被我惹恼了。“看来你不明白,”若昂接着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如果你按我说的做,你能轻而易举地赢下大奖赛,然后大功告成。对我取得的成就你怎么看?就因为我赢过年度大赛。我可是下了大力气的,一组动作只做到一半是不行的,不行的。靠的就是整天不断地苦练,如今我成了名,拥有健身馆、汽车和两百名学生,正在购买公寓房。现在我想帮你,而你却不配合,真让人揪心。我这是何苦呢?就为我的健身馆里能有个学员夺冠?我有温贝托,有格玛莉娜,不是吗?我还有福斯托和唐塞拉——我从他们当中把你挑出来,你就这么报答我?”“你说得对,”我说着,一边脱掉衣服并穿上游泳裤。他又说道:“你要是有科尔孔迪纳的毅力就好了!他都五十三岁了,六个月前他来这儿的时候还得着一种可怕的病,背部肌肉萎缩,脊椎骨吃不上力,身子越发扭曲,挺吓人的,这你是知道的。他跟我说他全身都在萎缩和变形,医生们没他妈的一点办法,无论打针还是按摩都没一点儿用。健身房里有个家伙见到他惊得直咧嘴,他的鸡胸看上去就像海军上将的帽子,背部隆起,身子向前躬着,向侧面歪斜,怪模怪样的,让人看一眼就想吐。我对科尔孔蒂纳说,我会让你好起来,但你必须一切听从我的吩咐,一切,一切,我无法让你成为又一个史蒂夫·李维斯,但六个月后你会面目一新,跟换了个人似的。看看他现在的样子,我是不是创造了奇迹?历经惩罚、煎熬、流汗和吃苦受罪他终于创造了奇迹:人的力量是无限的!”

沃特卢穿着泳裤走出更衣室,像他平时走路一样。……
“你到这儿来上单杠,”若昂说道。“这儿吗?”沃特卢问道,已经站到单杠下方。“是的。等你把额头升到横杠时就停下来。”沃特卢开始在杠上悬垂,但在屈臂向上的过程中笑了起来,又蹦回地面。“别在这儿嘻嘻哈哈的,不是闹着玩的,”若昂厉声说道,“再来!”沃特卢重新上杠做引体向上并按若昂之前的指令停下了。若昂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现在慢慢地把下巴升到横杠上。慢慢地,开始下降,慢点儿!再回到原点,停下。”若昂仍盯着他的身体。“现在躯干保持不动,两腿伸直并拢抬起来。”沃特卢慢慢地把腿抬起,动作轻松自如,全身的肌肉形成合力,犹如一支和谐的乐队,既强健又漂亮,这想必已给若昂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的肌肉也开始绷紧,接着我发现科尔孔蒂纳和我同样如此,我们就像在合唱一首无比动听的歌曲。“可以下来了。”若昂说。他从没对哪个学生用过这样亲切的语调。沃特卢下杠后,若昂问道:“你练过体操?”沃特卢摇头否认。“从没练过,我知道你没练过;好吧,那我告诉你们,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一亿分之一,一亿!你多大?”“二十岁,”沃特卢回答说。“我能让你出名,你想出名吗?”若昂问道。“为什么要出名?”沃特卢反问道,他的确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真逗,愚蠢透顶的问题!”若昂说道。为什么?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就为了别人在街上看见我们的时候说那家伙很有名气吗?“若昂,那你说为什么?”我说。若昂看了看我,那眼神就像我骂了他娘似的:“嘿,你也问这个,这叫什么事呀!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呵呵?”若昂时常会失去耐心,我认为他想看自己的学生在大赛中夺冠都想疯了。……
“我来为你编排一组练习,行吗?”若昂问道,沃特卢回答说:“遵命。”我拿起我的训练卡片对若昂说:“我去做六十公斤杠铃弯举和四十公斤正握弯举,你看如何?”“好极了,好极了!”若昂露出满意的微笑。
我做完那组练习后,望着若昂指导沃特卢。起步阶段的练习非常枯燥,但沃特卢做动作时神态愉悦,这很不寻常;一般而言,人们不会很快喜欢上健美训练,沃特卢也没什么秘诀,他一切都按若昂的指令做。他不会正确地呼吸,那是真的,他还有许多要领需要掌握,但是,妈的,这家伙已经上路了!
沃特卢洗澡去了,若昂对我说:“我想培养他去参加健美大赛,你看如何?”
选自《人力》,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3期。【巴西】鲁本·丰塞卡作,丁晓航译。
鲁本·丰塞卡(Rubem Fonseca,1925—2020),丰塞卡出生于茹伊斯迪弗拉市,读过法学院,做过警察,从基层小警升至警监,这为他的写作生涯提供了丰富素材。196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囚徒》,后陆续出版短篇小说集《新年快乐》、长篇小说《伟大的艺术》《八月》等,奠定了他在巴西文坛的地位。2003年获“卡蒙斯文学奖”。至今丰塞卡已出版短篇小说集近二十部,作品特色鲜明,常以冷酷尖刻的语言直陈城市中的暴力及其它黑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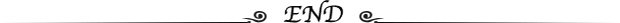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天艾 排版:文娟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