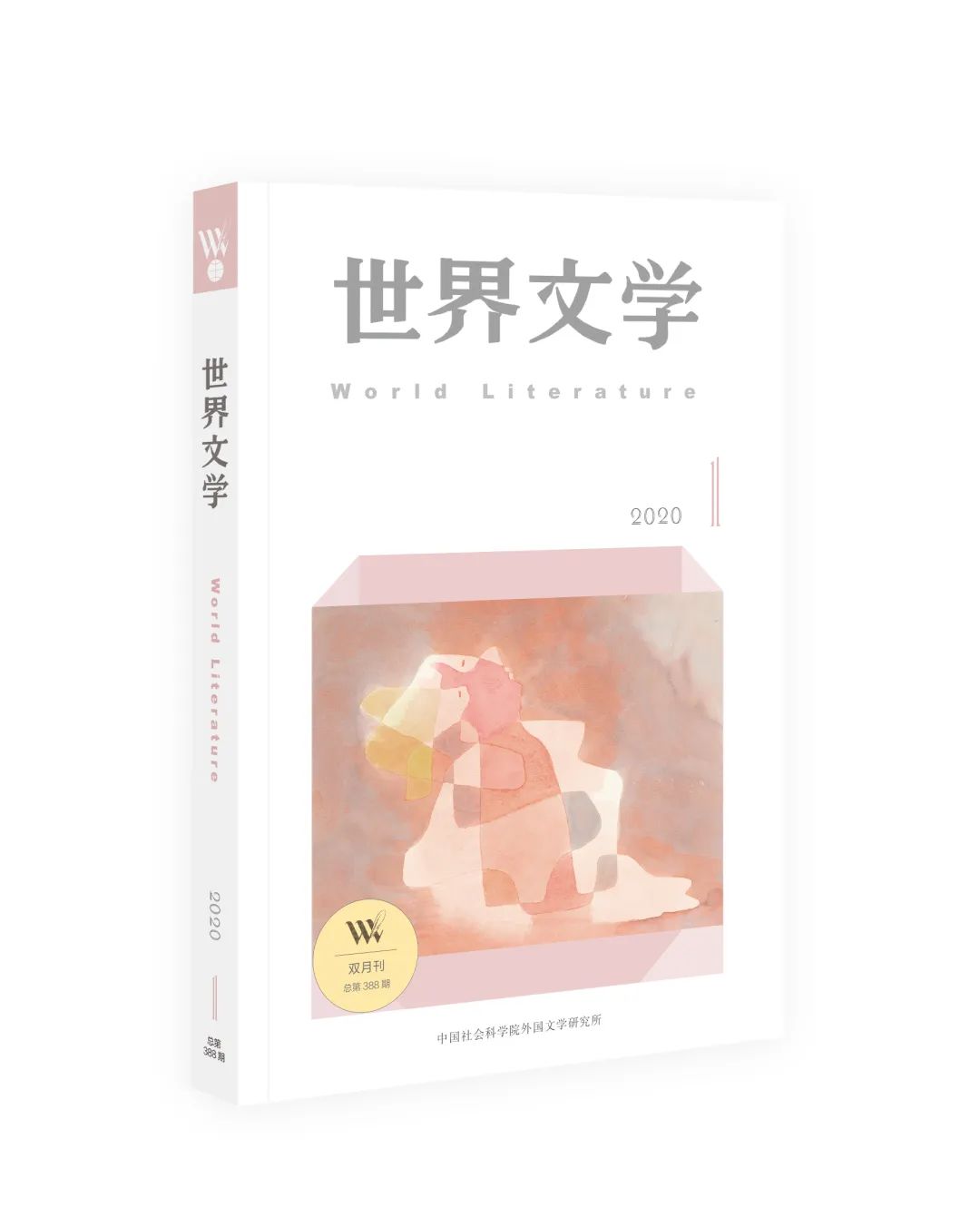第一读者|汗漫:在狮吼与熊舞之间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01
多年后,我们会说:一切都在庚子年或者说二〇二〇年春,发生剧变,从每一个人到全世界。
元月二十四,在上海至南阳新开通的高铁上,我周身充盈还乡过节的快乐。刚下车,就被次第传来的封城封省消息迎头痛击。在医圣张仲景长眠的这座小城里,一种空前的焦虑和迷茫包围了我。疫情猝然爆发、蔓延,像一个阴影中的蒙面者不宣而战——其战略目的是什么,支撑资源是什么,进攻路线与打击半径是什么?
我坐在母亲身边沙发上,像孤儿——孤独面对一瞬间天翻地覆的世界,发傻。终日握着手机,紧盯微信里苍茫的人间:无数空阔的大街、自闭者、忧郁症。十字路口,红绿灯在反思此刻的交替闪烁有何意义。高速公路上,一个驾车徘徊、没有出口能接纳的痛哭流涕者。雨中,手捏父亲胸部CT照片的孩子。阳台上敲锣呼救的女子。因隔离无法将蜂群转移到花期里去而绝望自杀的养蜂人。源源不断奔赴抗疫一线的军人、医生、护士。跨国采购抗疫物资的企业家。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演奏的交响乐团。电视、收音机中悲壮的合唱与旋律。迅速落成的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新闻发布会上语无伦次遭到撤职的官员。为疫区捐献白菜、土豆的农民。向被封锁的医院投送药物、食品的直升机。自发组织起来到工厂里生产口罩的画家、职员、编辑、学生。为医院免费送餐的餐馆老板。每天递增的确诊病例、死亡数字……

我在故乡紧盯远远近近的人们。担忧,感动,愤怒。尽管这担忧、感动与愤怒,仅仅能证明自己还不算是冷血的人。“无日不瞻望”“无夕不思量”。像白居易那样瞻望与思量,但眼力与心力一概匮乏、软弱。小弟从药店里买来最后十个口罩,成为全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储存了米、面、蔬菜和矿泉水,像进入战时状态。吃完最后一棵青菜,我才戴上口罩下楼采购,如同无脸见人、把柄多多的羞愧者。靠目光与菜场里寥寥几位售货员交流,嘴巴像加装上了弱音器,低哑,沉闷。回家,把口罩很怜惜地取下来,用电吹风灼热、吹拂、消毒,以便再次使用……
闷在家中时间长了,到李白多次来过的白河边晃荡。
这一条发源于伏牛山的河流,下通江汉、东海,是衔接南北的水路要道。中国南方北方之间的分水岭,就位于伏牛山顶峰。秦代修筑的一条“东南方驰道”,西起长安,经南阳直下襄阳抵达江南,唐代改建提速后定名为“东南大道”,大致上就是今天的G4等等几条高速公路的基础。南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悲欢的过渡带、华夏情仇的敏感区,无数诗词、戏曲、小说,从盆地传奇故事里获得表达的动力和资源,比如《三国演义》《南阳关》等等。在这场突然爆发的疫情中,南阳态势同样关涉全局。电视新闻中,一个高级别官员来到盆地与湖北接壤处,眺望着,脸色苍茫,像诗人。
“朝涉白水源,暂与人俗疏。”李白在白河边如此咏叹。庚子年,我与世俗人间的疏离很被动,很恐怖,远没有李白主动游荡的自在和舒畅。“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是他在白河边写下的另一句子,献给在南阳相别的友人崔宗之。浮云与落日,亘古如是,为人间情意的恒定永在,提供旁证和旁白。庚子年,同样在白河边,相识数十载的旧我,对一瞬间陷入“困顿和匮乏”的新我,又如何能挥手一别、“萧萧班马鸣”?

02
这是祖先们在冬春时节经常表演的驱疫仪式。疫情,大都在冬去春来之际出现。狮子与熊,是站在人类一边的吉兽。
南阳以汉画著称于世,卧龙岗下建设的汉画馆内,收藏有许多描述驱疫场景的汉画像石,线条简练、遒劲。鲁迅关注南阳汉画,收藏有众多画像石拓片。东汉时代,南阳冠以“南都”“帝乡”之名,达官贵人云集,死去,就以画像石装饰坟墓四壁,试图在石刻的景象里得到安慰、长眠。那也是一个瘟疫频发的时代。医圣张仲景在南阳出现,在东汉出现,是必然的。周围的伏牛山、桐柏山、秦岭,药材植物繁盛,是必须的。历代以来,本地中药作坊、制药厂众多,以“仲景”为品牌的药物众多,是必要的。“多病所须唯药物”,杜甫明白,我也明白。眼前疫情,何种药物可以根治、完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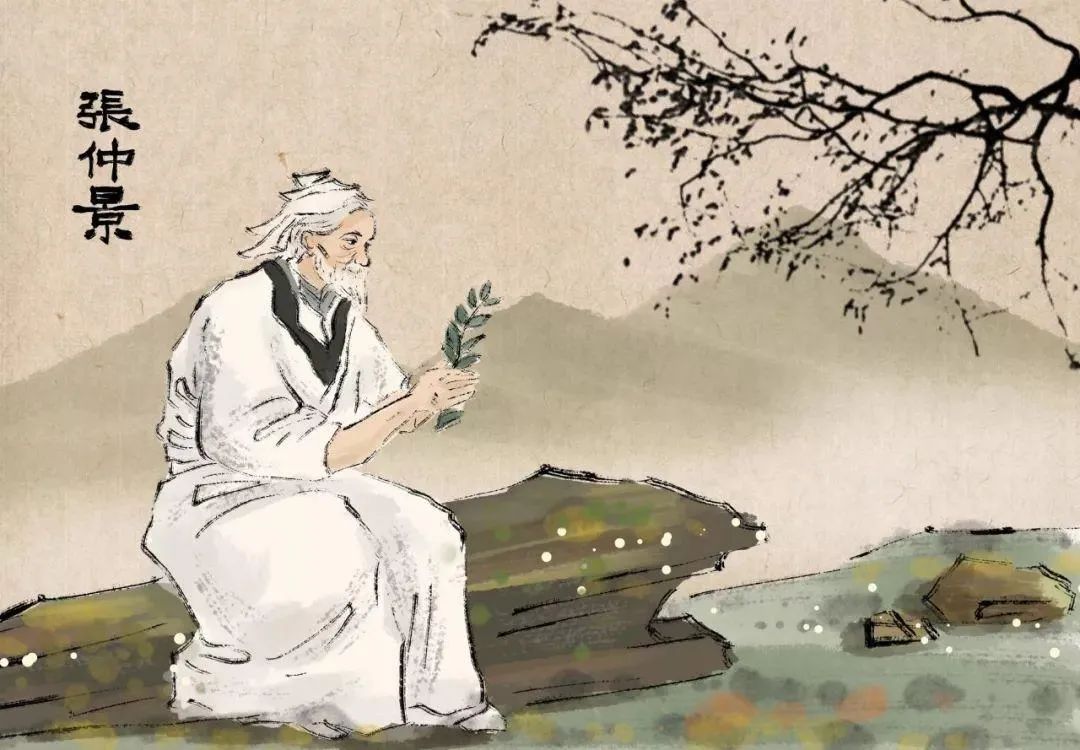
春节期间,专家、学者开始在网络、微信中,频频提及张仲景及其著作《伤寒杂病论》。国家推出一版又一版治疗方案,在各地实施,效果明显。其中,“清肺排毒汤”就来自张仲景的一个古老配方:麻杏石甘散,射干麻黄,小柴胡,五苓散……
南阳完全没有了过年的喜乐气氛。冷清。到处传来断路、封村、驱离探亲者的消息。若干远途出游的朋友,被迫中断行程,成为酒店里的流亡者?而巴黎,一个女子隔离在家把修长双腿搁在阳台栏杆上的照片,让我感觉,她依然在海岸线上晒日光浴。在不安中保持安定的力量,有多么难,就有多么必要。
“水饺还是要吃的。”母亲说。全家围绕在一起包饺子。餐厅里预定的一次大聚会取消了。北方人过节必吃水饺。为应对东汉频频爆发的瘟疫,张仲景在街头架起几口大锅,把羊肉和驱寒药材放锅里熬煮,捞出切碎,用面皮裹成耳朵形状,命名为“饺子”。煮熟后分给求药问病者,再端上一碗碗热气蒸腾的羊肉汤……南阳盆地有民谣广泛流传:“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迎客的水饺送客的面,天长地久人平安。”

03
《隋书》(成书于初唐)曰:“张机,字仲景,南阳棘阳人。”
《古今医统大全》(成书于明嘉靖年间)曰:“张机,字仲景,南阳人,受业张伯祖,医学超群,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凡医治诸症如神,后人赖之为医圣。”
“棘阳”,古地名,位于当下新野县一片田野。那里,是后来《三国演义》中“火烧新野”情节发生的地方,是诗人庾信、岑参相继萌发的地方。尽管身世抽象,毕竟有《伤寒杂病论》传世,张仲景因而获得无限的怀想与追思。
医圣祠内有张仲景雕像,《伤寒杂病论》扉页有张仲景线描肖像,瘦削,苍凉,关于“仁者爱人”的一种象征而已,不必考证是否酷肖其面貌。需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张仲景,像河流需要创造一个高拔的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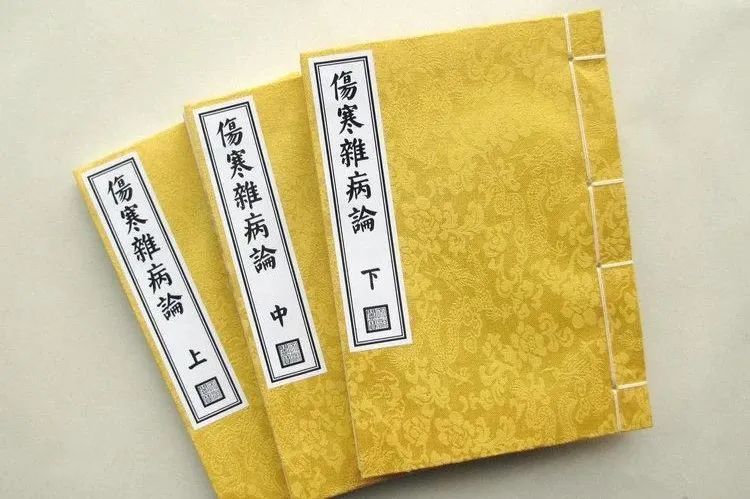
整个春节期间,看了二十余部电影,吃了若干碗水饺,以此转移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体重迅猛增加。屡屡走神。电影中所有人物对白,都能让我联想起疫情期的人类处境。因为,一切电影主题都是人性,都是生、死、爱、绝境、孤独。
法国导演侯麦的镜头里,有浓烈的阳光、葡萄园、女子,像梦境,遥不可及。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叙事中,关于家酿果酒,有这样的对话:“姐姐,要甜一点还是酸一点?”“酸一点。”“要浓一点还是淡一点?”“浓一点。”好电影,就是这样平和与日常,好生活也应该这样平和与日常。
在南阳盆地东侧,余冲村,祖父余孟光培植一个巨大果园。他喜欢酿制樱桃酒,逗引我去喝。醉了,一个小孩在树荫里睡了整个下午。蚂蚁沿着手臂这条长路,走上一张不平坦的、为未来开始储藏泪水的小脸……祖父死亡,美景早已消失。余冲村与我的关系,仅仅剩下四座祖坟,像拴马桩,让一个人的命运在奔腾中不至于陷入虚无。我有来路,就有归途,一个民族同样在来路与归途之间,永远不绝望。
疫情期,南阳市区乃至整个国家,大大小小的醉鬼和酸酸甜甜的醉意,都消失了。只有那寻常的醉意,才能灼热身心。

04
拥有类似羞耻之感的中国诗人,大约很多。抗疫一线那些大夫与护士,有情有为。试管与手术刀比一支笔有效有力。或许,阅读与写作的价值,仅在于自我治理与精神消毒罢了。为那些在医院或实验室一角沉沉睡去的人,写写“白衣天使像云朵”一类句子并能获得稿费?轻浮而可耻。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显然,他对酸腐文人持轻慢态度,赞赏高才者去选择“科学的考证”一途。用顾炎武的眼光看,我大约连被轻慢的才资也没有,以科学的考证去经邦救国,更无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旁观者?但旁观也是介入,辨认与见证同样是一种药品般的纠正。
我喜欢苏轼,在他身上看见理想的中国士子形象——立德、立功与立言,兼善并美。元丰三年,即一〇七九年,黄州瘟疫蔓延,苏轼正处于贬谪期。在研读《伤寒杂病论》《千金方》等等医书基础上,他拟定一个处方:肉豆蔻,木猪苓,石菖蒲,茯苓,黄,石药,白术……十年后,任杭州知州,再次遭遇瘟疫,苏轼在城中心的众安桥边,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传染病医院“安济坊”,拯救民众无数。
“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在南阳盆地里的邓州,写下《岳阳楼记》,这一收束全篇的句子,让人惆怅万千。他的另一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我对自己的小忧乐与天下之间的关系,缺乏信心。幸而有张衡、张仲景、苏轼、范仲淹这些巨擘俊彦不绝涌现,方使得华夏中国屡屡浴火而重生。

范仲淹
尚可自我安慰的是:一个写作者,若能在纸上自救,继而让阅读者获得勇气和力量,避免沦陷于共同或个人性的恐惧、困境,就是在维护语言的尊严、人的尊严。这一支笔,就能拥有铁锹、手术刀、针管的形状和力量。
05
来自异国或运往异域的抗疫物资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等诗句,传达着古老言辞里永恒的美意深情。各种“云朗诵”“云诗会”,使无数心灵在自闭与分裂中,得以整合与修复。

我的外祖父王恩惠是南阳有名的民间中医,研制出许多秘方,失传了。家族中,没一个人继承他的事业。遗物中有一本《黄帝内经》,繁体,封面已经破损,母亲珍藏多年。我找出这部医学书籍,随意翻读。抒情的段落比比皆是:“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张仲景应该研读过源于轩辕黄帝的这一经典。其中插图,点明一百〇六个穴位、十二路经络,像一百〇六个车站分布于十二条铁路线上,接纳着、输送着天地人间的种种规律与生机……
正确认识人类的身体与灵魂,是一项永远未完成的事业。需要医学院、中医院、心理诊所,甚至语言学院。庚子春,南阳盆地内外,许多小镇、村庄出现种种“硬核”抗疫标语,触目惊心:“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今年进门,明年上坟。”近似咒语和辱骂,充满凉薄和戾气。语言粗鄙,就是人性、人伦、人世的荒芜。这样的粗鄙和荒芜,是最隐秘最危险的疫情。
春节结束后,我从南阳返回上海的行程迟迟未定。对于乘坐高铁、飞机,充满疑惧。而高铁、飞机班次也压缩到极端。单位同事来短信慰问,对紧邻湖北的南阳疫情很关注。我明白,即便回到上海,也应在家中自我禁闭若干天,避免为周围带来不安感,这是我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年已八旬的母亲对我滞留南阳,暗怀欢喜,又觉得惭愧——毕竟这是大灾难背景下的小欢喜。但终于还是要回到上海,回到我的角色、台词、高潮与深渊。
临行前,我去医圣祠与张仲景道别,试图获得精神的内援。一棵巨大腊梅树,从医圣祠内探出围墙,像张仲景,探头打量春风与疫情并举的人间?这一颗灿烂头颅,向一个后生传递暗香和安慰,在冥冥中助力人间,纠正一个春天的脉象气色。我认识这棵腊梅树,每次到医圣祠内闲走,都会站在树下,看它开花或无花的样子。此时,医圣祠大门紧闭,像戴了木质的大口罩。
围绕医圣祠,寂寂然走一遭。往年春节,祠内都会有祭拜活动,游人云集,在张仲景墓前叩拜、献花、祈求康宁。这一刻,祠前汉阙上,两只浮雕的朱雀保持吉祥的飞姿,为全人类鼓舞勇气和信心。

06
在上海,我续写、修改这一篇起笔于庚子年新春的文章。疫情又呈复发之势,限制出行的举措在多地重新推出。某家医院建立“新冠科”,成为新闻热点:人类与不断变异的疫情长期共处互搏,这一概率很大。我能否顺利回南阳过年,有悬念,这篇文章又怎么能顺利结尾?无数未知与可能性,等待全人类继续辨析、判断、表达。
回顾这一年。四月后,境内秩序恢复。部分地区偶有病毒闪现于海鲜市场、酒店,但未有大面积恐慌重现。人流密度增加,堵车成为电视台热烈报道的好消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中国第一支新冠疫苗顺利完成三期临床研究,上市,为全人类带来福音。
这一年,人与人的距离感空前加强,握手、拥抱、亲吻,不再是寻常礼仪,而成为信赖、托付、生死与共的象征。隔离中的男女,加强爱情或者加深裂痕,打开门,直奔结婚证或离婚证。互联网行业获得重大机遇,热烈支持每个人在虚拟中热爱生活:网购,网恋,网游,网上论坛……大量实体店铺关门,橱窗里的木质模特,呆望行人,脸上细微的裂纹酷似泪迹,悲伤着,祈祷着?
这一年,在车站、航空港、宾馆、超市、小区,需要随时出示健康码,去回答“谁、从哪里来、在哪里、到哪里去”等等哲学性的拷问。若干感染者接受流行病学调查,暴露出私家侦探也无法捕捉、作家也无力想象的奇异路线:一夜间周旋于七个酒吧的女孩,公司下班后打了三份零工直到凌晨两点的中年男子,陪女友逛街、看新车、会晤客户吃大餐、去父母家蹭饭省钱还房贷的小职员……

这一年,最大的成就是保持体温正常,没有惊动随处可见、虎视眈眈的体温测量仪。去世纪公园看了两次荷花、菖蒲,补偿春天禁足期间的丧失。荷花映菖蒲,像灯火,照着某人一头乱发,安抚其种种的魂失魄散。草地上,少年少女们聚会、野餐、歌唱,口罩在吉他、指尖、发辫上迎风翻飞。这场景,让我流泪。一个人的老境和眷恋,因疫情而加速到来、加重分量。
这一年,全世界因新冠疫情去世者,日日递增,未来是否会逼近一九一八年爆发、历时两年、蔓延欧美的流感病毒死亡数字?那场疫情的伤害,超过了叠加于同时段的“一战”重创,死去的知名人士有诗人阿波利奈尔、画家席勒等等。目前,新冠疫情中的死者,有电影导演金基德、钢琴家傅聪……更多的人死于无名,更多人的悲伤,悄无声息。

07
自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到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十多年了,儿子从一个少年长大成人,选择了“科学的考证”一途。在那个充满异议与新意的国度里,承受怎样的重负与孤寂、忧伤与欢乐?他从未过多流露。对我纸墨间的抒情与思虑,抱持原谅、理解的态度。一月十八日凌晨,他破天荒发了一条朋友圈消息:接受检测时闭着眼睛的照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颁发的绿码,“回家”二字和一个惊叹号!
我能猜测他的喜悦和忐忑。不到飞机腾空那一刻,无法确定能够如期归来——既定航班,因各种情况会临时取消。他加入的一个多达数百人的“中国人回家”微信群里,顺利启程者,寥寥。其中一人,接受完检测、拿到绿码后,迅速辞职、卖车、退掉所租房子,拉着两个行李箱来到机场,却被通知无法成行,栖息于酒店又感染上病毒,嚎啕大哭……
在浦东国际机场降落后,儿子还将通过特殊通道被送入一家酒店隔离观察十四天,接受机器人的上门送餐与关怀,接纳核酸的持续质疑。这一类负有特殊使命的酒店,大都位于郊区。走廊里弥漫着浓烈的来苏水气息。地毯与地板,因天天消毒而褪色着、破旧着、忍耐着。

窗外,成群结队拒绝戴口罩的美国人,在游行示威、冲突、倒下。太平洋里,若干艘因疫情禁止靠岸的轮船,漂泊不定,缺乏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结尾处悬挂黄旗的那艘轮船的美感。“全球一体化”,在重重裂痕中显得虚幻而又真切——只要一个地域、一个国度病毒未息,谁都不能说自己是安全的人。人类进步表象下的种种病灶、隐疾,被这场疫情揭露。而灾难,也是一种启蒙和救赎。改善与大自然、他者、自我之间的关系,放弃自闭、傲慢、孤行一意,是一个不再抽象而异常紧迫的命题——
如何能够使亲爱的人,自由、无碍、欢笑着来到面前?
像异代前贤张仲景那样,在万千植物与暗伤之间,沉思、斟酌,让一纸最准确的药方、言辞,拥有狮吼熊舞一般祛疾、回春的力量。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喜欢明代诗人陈献章这一句子。庚子春,在故乡错过医圣祠内那棵腊梅、那个梅花满头的古人。辛丑春,乃至未来年年岁岁,愿天下人,都不再辜负玉兰、丁香、山茶等等所有好花枝。
2021年1月19日于上海
作者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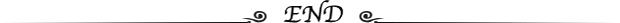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文娟 校对:秋泥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