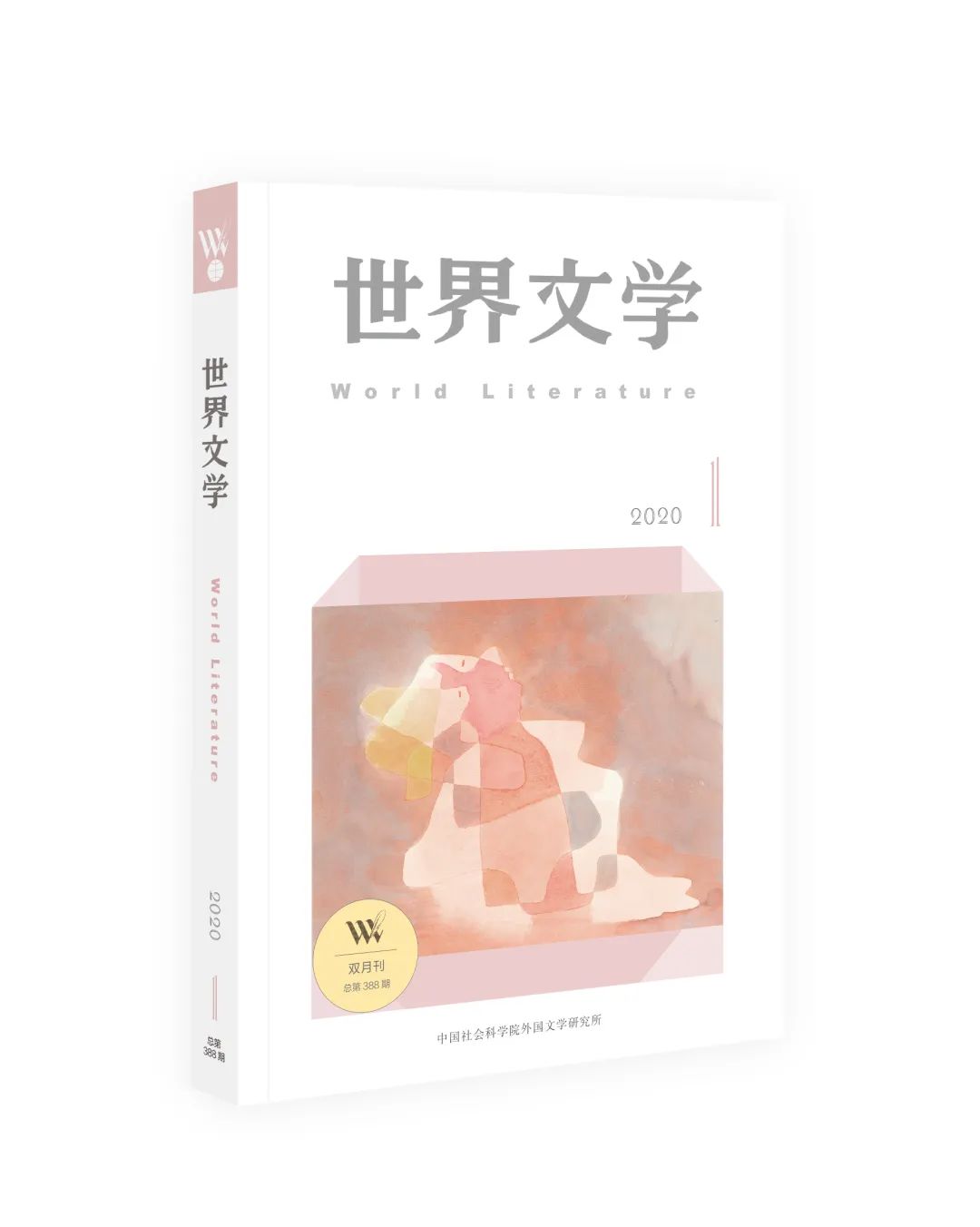六一儿童节 | 《世界文学》里的那些“黑暗”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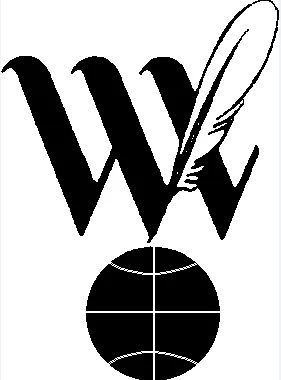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里的那些“黑暗”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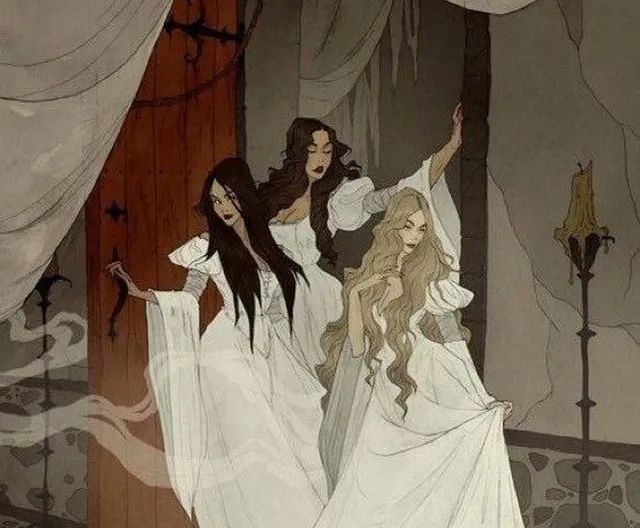

漂亮脸蛋

【波兰】莱舍克·柯瓦柯夫斯基作 杨德友译
尼诺是面包房工人,因为容貌漂亮而闻名。那确实是整个地区最最漂亮的一张脸;尼诺在街上一走,所有的少女都转目凝望:这个面包房工人一张俊美脸面真是魅力十足。
可惜,尼诺是在烤炉旁边工作,在又潮湿,又闷热的烤面包房干活:谁都知道,这种环境对俊美脸蛋儿的影响不良。除此之外,有时候他还有操心的事,和一切人一样;谁都知道,忧虑有害于美貌。结果,尼诺一照镜子,就在痛苦中断定,在他俊美脸面上生活正在慢慢地留下痕迹。尽管如此,这张脸依然美丽得不同凡响,而尼诺是很愿意保护这美貌不受时间的恶毒侵蚀的。于是他来到来洛尼亚城,因为这儿出售护脸专用的盒子。这种小盒子十分昂贵,尼诺必须向邻居们借钱才能购买。于是他买了盒子,把自己一张俊脸安全保护起来。
这个盒子除了昂贵之外,还有一个缺点:必须时时刻刻带在身旁,一分钟也不能放下,因为一旦弄坏,就连俊脸也要受损,可是尼诺对自己的美貌极为珍重,便下定决心承受一切不便。他保护脸,戴着盒子工作,散步,睡觉。他越来越操心美貌变相。起初几个星期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从脸上摘下盒子,在节日里还常化妆。可是他很快就发现,即使在节日里人也会遇到忧虑和麻烦,俊脸就可能遭到损害。所以,他决定一般不把保护盒从脸上摘掉;从此以后,谁也不能欣赏尼诺的俊美脸蛋儿了。少女们不再注目于他,因为不露出俊脸,尼诺一点也引不起她们的兴趣。原来用手指头指着欣赏他美貌的人,现在对这个不露脸的人是视而不见。而尼诺对自己的美貌的担心更加严重,连保护盒也不再査看,以免让漂亮脸蛋儿遇到潮气、阳光和风沙。
全城居民很快就忘记了尼诺的长相,而他自己,因为已经不査看保护盒,也不知盒子变样了没有。但是,每逢他想起自己是全城第一号绝美男子之时,便自豪得无以复加。他的的确确是美男子中的绝美,可是谁也不能亲眼目睹。
来洛尼亚一位著名学者克鲁先生途经该城,因为天气恶劣,不得不在城里客栈留驻数日。从旅客谈话中他得知尼诺的美貌,便想结识他。他找到了少年美男子住所,和他谈了起来。
“都说你是全城第一美男。”克鲁说。
“是这样的。”尼诺回答。
“你能不能为我证实一下呢?”
“当然可以。”尼诺答应了。但是他又立即想到,为此目的他必须化妆,还得把保护盒从脸上摘下;果真如此,小风和尘土很可能会损害他美丽的面容的。于是他立即追加一句:“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我的脸是受到保护的。”
“那就把保护面具摘掉,让我看看你。”
“不行啊,脸面要受到损害的。我必须节约我这张脸的美丽。”
“为什么你不适当地利用你的美貌呢?”
“为了保护它更长时间不受损害。”
“就是说,在将来用它?”
尼诺沉吟起来。他的确一直也没有细心考虑过这个情况。他认定必须节约使用美貌,但是不能确定将来是否还要把它包裹起来。他回答说:“不知道,的确不知道为什么要使用它。我的经验告诉我,不露出脸面也能生活得很好。”
“当然是可以的,”学者克鲁表示同意,“很多人活着都不必露脸。不过,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更好呢?”
“是,不太好,”尼诺回答,“可是脸不至于受损害。”
“你是说你保存你的美貌是为了将来用它?”
“我想让它永远漂亮。”
“为了谁呢?”
“不为了谁。只是让它漂亮。”
“你这个愿望恐怕是没办法实现的,”克鲁说这么一句,便和尼诺告别,点点头表示同情,走了。
与此同时,尼诺因为购买护脸盒而拖欠的债务偿还日期早已经到来。可是,面包房帮工挣钱很少,尼诺没钱。信任他的邻居坚决要求偿还借款,威胁要上法庭,把他投入监狱。尼诺急得没有办法。谁也不愿意再借钱给他,因为都知道上次的债还没有还。在来洛尼亚,谁不还债就会受到惩罚,被关进监狱。
经过长时间内心斗争和徒劳的筹款努力之后,尼诺决定把护脸盒退回去,再重新化妆自己的脸。他前往丽波丽城,找到原来购买护脸盒的地方。
“我想把护脸盒退给你们。”他说。
“什么时候买的?”店主问。
“十五年以前。”尼诺回答。此时此刻,他突然回忆起来,他脸上戴保护盒已经十五年了,而令他欣慰的是,他把自己的青春美貌成功地多保存了这十五年。
可是店主微笑一下,略表同情。他说:“十五年了。看看这盒子吧。全都破旧不堪,边角模糊,快要磨透,不成样子了。没有人再从我这里第二次买这样的护脸盒儿。连原价十分之一也卖不了的。尼诺,你是老主顾,可是我不能收购它。”
“可是,”尼诺惊呆了,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我没钱还人家买这盒子时候借的钱啊。可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我又不能替你还债。谁借钱谁还债;借债以前应该三思嘛。”
尼诺离开了,又压抑又害怕。眼前只有坐牢的前景,一点主意也没有。他回到家,一名警员正在等他,通知他第二天下午到法院出庭。尼诺胡思乱想了一整夜。清早起来做出决定,重新前往丽波丽小镇。
这一天他去的是当铺,用宝贵物件作抵押贷款。
“我要贷款三百帕特罗纳。”他说(“帕特罗纳”是来洛尼亚金币;三百是护脸盒原来的价格)。
“拿什么当抵押?”当铺老板问。
“我把……”尼诺回答说,“我把我这张漂亮脸蛋儿押给你,时间一直没触动过它——还有保护它不发生变化的保护盒子。”
“等我看看。”店主说。他从架子上取了一本书,书里记载着各种各样的人脸的价格。又打开保护盒子,还用放大镜细心观看尼诺的脸蛋儿。确实是年轻美丽,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连尼诺也感到有些激动,因为多年来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美貌。接着,店主又细看保护盒子,经过长时间计算后说:
“凭你的脸蛋儿和保护盒,可以给你二百帕特罗纳,多一个也不行啦。半年以后来赎取,交三百帕特罗纳。”
条件苛刻,尼诺犹疑起来:当铺的出价不够还债。但是这一地区内已经没有其他当铺,而且,即使有,也不一定出价更高。
“好吧,同意。”尼诺说,他还能怎么样?他留下了脸蛋儿和保护盒,取了二百帕特罗纳,返回原地,立即找到放债的邻居。他奉还了二百帕特罗纳,许愿很快奉还余额。他的确不知道怎么弄到这笔钱,可是又什么也不能说。邻居同意撤回诉讼状,但是警告说余额拖欠不得超过半年。
尼诺十分痛苦,郁闷之极。虽然短时间内可以躲过监狱,但是债务依然巨大,脸蛋儿又没了。
一个月过去了;在这六个月里,尼诺做出不间断的极度努力,尽可能多挣钱,全是为了还清邻居的债务,为了从当铺里赎回自己的美貌。一切都已落空。又过了三个月,邻居的耐心已经耗尽,便又向法庭上告他。经过开庭审判,尼诺因欠债被判入狱。
丽波丽城的当铺主人长时间等待着尼诺:他应该去赎回保护盒和漂亮脸蛋儿的呀。但是,到底没把他等来。店主已感到厌倦,便断定他不会再来。他从保护盒里抽出尼诺的脸皮,送给孩子们当玩具玩。孩子们用尼诺的脸皮做了一个球,当排球玩。很快,谁也就再也想不到这个旧排球曾经是少年尼诺的漂亮的脸蛋儿了。
但是,尼诺对此一无所知。坐在监狱里,他至少还有一件感到欣喜的至宝。他告诉一切和他谈话的人,说他有一张十分美丽的脸蛋儿,什么也不能损害,能抵挡一切损害。“我真的有一张全城最最俊美的脸蛋儿,”他说,“你们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我的脸有多么好看。现在保存在一个专用的盒子里,是一点也坏不了的。你们还能看见的。看看吧,看我的脸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虽然在监狱中,尼诺还以此为欣慰。他一直在那里坐着,确实深信他的一张脸在全世界都是最为俊美的。
城里有很多人为他惋惜。他们认为,尼诺是不幸的,虽然他自己该为这不幸负责;因为他应该知道,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能享有护脸盒子,亦即漂亮脸蛋儿在其中得以保存完好的保护盒。
与此同时,当铺掌柜的孩子们正在院子里拍打那个排球玩,那球的样子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不好玩了。
莱舍克·柯瓦柯夫斯基,1927年l0月生于波兰腊多姆市,逝世于2009年,是二十世纪波兰最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作家和翻译家。毕业于波兰罗兹大学哲学系。


雪孩儿

【英国】安吉拉·卡特 刘凯芳译
仲冬时节——一切都在严寒面前屈服了,大地洁白无瑕。伯爵和夫人出去骑马,伯爵骑的是一匹灰色母马,夫人骑的是一匹黑色的。夫人围着亮闪闪的黑色狐皮,足登雪亮的黑色长筒靴,靴上带有马刺,后跟是通红的。地面上本来就有雪,刚才又下了一场,等雪一停,整个世界一片雪白。“但愿我有个像雪那样洁白的姑娘。”伯爵说。他们骑着马继续往前走。看到雪中有一个坑,坑里全是血。他又说:“但愿我有个像血那么鲜红的姑娘。”他们又往前骑去,只见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栖息着一只乌鸦,“但愿我有个像乌鸦的羽毛那么乌黑的姑娘。”
他的话刚出口,就在他们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个姑娘,她皮肤雪白,嘴唇通红,头发乌黑,她赤条条地站在光秃秃的路边。这就是伯爵想要的孩子,伯爵夫人憎恨她。伯爵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在马鞍上他的前面,但伯爵夫人只是想道:我用什么法子来甩掉她呢?
伯爵夫人把手套扔到雪地里,吩咐姑娘下马替她捡起来,她打算策马跑开,将她甩掉,但伯爵说:“我给你再买一副新的。”话还没说完,伯爵夫人肩头的裘皮就跳了下来,围到了赤身裸体的姑娘身上。伯爵夫人又把钻石胸针扔进封冻的池塘的冰洞里,她命令姑娘道:“替我下水把胸针拿来。”她想这一来姑娘准会淹死。但伯爵却说:“她又不是鱼,天这么冷,怎么能下水呢?”话刚说完,伯爵夫人的靴子自动脱了下来套到姑娘的腿上。这一来伯爵夫人弄得上上下下光溜溜的像根骨头,而姑娘却围着狐皮,穿着靴子。伯爵有些可怜起他妻子来。他们来到了一丛盛开的玫瑰前。“替我摘一朵玫瑰。”伯爵夫人对姑娘说。“这一点我是没法反对的。”伯爵回答。
因此姑娘去摘了一朵玫瑰,她给刺扎了手,出血了,她尖叫了一声,跌倒在地。
伯爵流着眼泪下了马,他解开马裤,把阳具插入死去的姑娘的身体。伯爵夫人笼住了不断踢着蹄子的坐骑,在一旁仔细观察着,伯爵很快完了事。
接着那姑娘就融化了,过了一会儿,雪地上只剩下一根像是鸟掉下来的羽毛,一摊像是狐狸被杀死后留下的血迹,还有她刚采摘的那朵玫瑰。这一来所有的衣服又回到了伯爵夫人的身上,她长长的手抚摸着裘皮。伯爵捡起玫瑰,鞠了一躬,把花递给妻子。夫人一接过去,马上就把花扔到了地上。
“花扎人!”她说。
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生于苏塞克斯的伊斯特本,曾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毕业后当过记者,后来从事写作,创作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并翻译了法国十七世纪作家佩罗的童话集,成为当代英国文坛最活跃的小说家之一。


吹肥皂泡的男孩

【瑞典】彼尔•魏斯特贝 石琴娥译
从前有一个女人,她有三个儿子。孩子们的父亲早已亡故,他们的家境十分清贫困苦。打从孩子们懂事以来,他们不记得自己吃过一顿饱饭。他们住的那幢灰色小茅舍,屋顶上长满了蓬蒿,屋檐下燕子筑了窝,四壁倾斜,眼看要倒塌下来。这幢小灰屋只有一个房间,一扇窗户。窗台上放着一个花盆,门口长着矢车菊和山楂花。
紧挨着小茅舍有一大片森林,但是这片森林却同别处广袤无际的大森林不一样。只要穿过这片森林,就会来到这个国家的京城。母亲常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采撷草药。有个老妇人把草药拿到城里去卖掉,然后给母亲一点点钱。
大儿子和二儿子都长大了,身体结实茁壮,为人精明能干,看着都讨人喜欢。做母亲的非常疼爱他们,指望他们将来能很有出息,在生活中得到幸福。就像所有童话中穷人的母亲一样,她特别希望他们心地纯洁、善良,能够助人为乐。但是她一直不把这些话说出来,她觉得这是理当由他们自己来管的事情。
最小的那个儿子跟他的两个哥哥一点也不相像。他从小就比两个哥哥长得瘦小羸弱,总是落落寡合,独来独往。他最喜欢静坐在河边那棵枝杈伸出水面的柳树上。他用芦苇杆给自己做了一支小小的芦笛。他常常一边吹着芦笛,一边目送着脚下清凌凌的河水流淌过去。面对从高山群岭上一泻千里的滔滔奔流,他总是感到情趣盎然,心旷神怡。他侧耳细听河浪拍岸、水流击石发出的潺潺声响,觉得那是河水在跟他低语,虽说听不出在讲些什么。他看着映在水中的碧空,看着从河底翻泛上来的一串串珍珠般的细小泡沫,弄不清自己应该感到快乐还是惆怅。
有时,他平躺在树杈上,仰面观赏着夏日蓝天里你追我逐的行云。这一朵朵的白云宛如浩渺烟波的大海上的千舡万舸,扬帆竞发。他轻声地吹奏起芦笛,顿时,海鸟好像停止了翱翔,蜜蜂也不再在花丛中嗡鸣忙碌,而一齐来聆听他那清脆高亢的曲调。
他有时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深更半夜。母亲和哥哥们早都上床睡觉了。夜空黑魆魆的,繁星不断地眨着眼睛。最耀眼的一颗星星是金星,跟着这颗星星可以一直走到太阳以东、地球以北的那座巍峨的天宫。一钩新月很快挂上了夜幕,她把清冷洁白的光芒洒射到河面上。小男孩看到鱼儿摇头摆尾朝粼粼的亮光簇拥过去。他影影绰绰地瞥见水面上露出一张脸来,那必定是河仙水妖的脸。他又吹了一阵子芦笛,可是,他觉得蟋蟀的鸣叫更加悦耳动听,就放下了芦笛,竖起耳朵细听着蟋蟀的叫声。在熹微的晨光照亮了柳叶,河面上升起蒙蒙薄雾的时候,他才站起身来,返回到小屋里去。
但是他最心爱的游戏是坐在河边吹肥皂泡。那是有一回一个流浪汉教给他的:在一片折叠成匣子形状的树叶上或一块树皮里,放上一点点肥皂,掺上水,用芦苇杆蘸起一点来吹。他学会了把肥皂泡越吹越大的技艺。每当他看到吹出来的美丽的肥皂泡先在苇杆梢上粘一会儿,然后越涨越大,越涨越圆,悠悠荡荡地飘上天去,便会欣喜不已。他坐在柳树枝上,眼望那些轻盈透明的肥皂泡,陷入了遐想。他希望有一天,会有一位公主乘坐着挂有许多帆的大船,顺流而下,来到河边,叫他到她的船上去,把他带到京城的王宫里去过日子。
儿子们渐渐长大成人了。有一天,小屋里来了一个差人,他带来信息说,战争爆发了!邻国已经重兵侵入他们国家,国王命令征召所有体格健壮的男人入伍来保卫王国的疆土。就这样,老大老二上战场去打仗了。母亲放声大哭着说,她知道母子们今生今世再难见面了。两个儿子竭力安慰她,甚至还吻了她的脸颊,虽然如今他们已经长大,未免有点不大好意思。
不久,她得到通知说,她的两个儿子在战场上阵亡,为国捐躯,他们是所有士兵中最出色的勇士,她可以为他们感到骄傲。她又失声痛哭起来。她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最勇敢的人去送掉性命。她抚摸着小儿子的头发说道:
“现在我只剩下你在身边了,你想干点什么活儿呢?”
“我多半也应该去打仗才是,”小儿子回答说,“在童话里,小儿子总是应该比别人更有出息,说不定最后还能赢得公主的青睐,娶回家来,虽说我想,我不配有这份福气。所以我现在还是到外面去闯闯,见见大世面的好。”
他说做就这么做了。他出门上路,长途跋涉了许多日子。他每天在沿路的农庄上干几个钟点的农活,农庄主人供给他吃喝。晚上,他就在谷仓里睡觉。劳累不堪的时候,他就在沟边上坐下来憩息,吹奏芦笛,或是吹起他的肥皂泡来。
最后,他来到了一座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城市。人家告诉他说,这就是京城。男孩饥肠辘辘,必须找点活儿干来糊口。他在修鞋匠那里帮工学生意,可是,又不喜欢干这门营生。他后来发现,那还不如坐在门外吹肥皂泡好处来得更大,因为这一下招徕所有的过路人都停下脚步,观赏那些美丽的肥皂泡。修鞋匠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差不多是发了一笔财。城里其他的修鞋匠很快眼热起来,忌妒得很。他们把那个修鞋匠开除出了鞋匠行会。男孩不得不离开这个修鞋匠另谋生路,到别的地方去挣自己的面包。他不知道该找个什么职业。他自鸣得意的是,幸亏他没有任何要努力奋斗的人生目标,而且心情无忧无虑,任何事情都不会使他烦恼忧伤。
有一天,他坐在大街的拐角上吹肥皂泡。那些肥皂泡一个个又大又闪闪发光,路过的行人都看入了迷,觉得一生之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肥皂泡。街上熙来攘往,行人很多,他们许多人站在男孩边上不走了,看着他吹肥皂泡,因为反正他们有的是闲功夫。
住在深宫里的公主也来到人群之中,不过男孩认不出她,因为她穿着和大家完全一样的衣服。原来公主一连好几个晚上都在偷偷阅读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国王微服出访的故事,这位国王喜欢化装成平民,走遍巴格达的市集,偷听人家怎么在背后议论他。于是,公主也穿上了普通的衣服,悄悄地上了街。她从未见过芦苇杆能吹出这么圆大发亮并徐徐飘入天空的肥皂泡。忽然,有只小鸟飞过,停栖在一个肥皂泡上,于是这个飘动着的肥皂泡砰的一声碎裂得无影无踪,看起来真像是一次小小的爆炸。
后来,公主忍不住了,便走到男孩面前,告诉他,她是什么人,并且问他,愿不愿意跟她到王宫里去,教她吹跟这些一样的肥皂泡。他盯住她看了半天,怎么也不信一个公主竟然同大街上其他行人打扮得一模一样。不过后来,他又一想,大概是各个地方风土人情不一样的缘故。
“好吧,我跟你去。”他回答说。
人群目送他们走远。有许多人以为那个男孩准是个骗子—— 不过,人们偶尔会不辨是非、冤柱好人的。
王宫楼阁嵯峨,巍巍壮观,亭台错落,还有宽阔的大理石台阶,果然像童话里讲的那样,金碧辉煌,气象万千。他们先走过了御花园。园囿里长满了争芳吐艳的奇花异草,还有各种各样形状的喷泉在喷水。一个穿着华丽制服的侍从在石阶上恭敬地迎接了他们,并且一直伺候他们走进公主的寝宫。公主吩咐侍从去把早饭端来,让男孩同她一起吃。
“我每星期都要吃一次野莓子蛋糕,”公主告诉男孩,“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了。今天我们就吃野莓子蛋糕吧。”
男孩不禁觉得那野莓子蛋糕也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了,虽说他从来没有尝到过。他急于想看看野莓子蛋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刚坐到饭桌旁,公主的母亲,也就是王后走了进来。她一看到这个野孩子,不由得吓了一跳,用手一指,厉声喝道:
“这里岂是你坐的地方,不许你坐在这里!”
就在这一刹那,他觉得一只大手扭住了他的肩头,回头一看,原来是方才在大街上站在他身边的一个警官,正是他把这件事情禀告了王后。男孩心里非常难过,站起身来,走出宫去,离开了这座京城。他觉得,公主的出现是那么真切实在,而这一切又分明像是做了一场梦。
他萍踪飘忽,走遍了天涯,在外面流浪了很久很久。他到处吹肥皂泡,使大家快乐高兴。他越来越不大想那位公主了,但是又无法完全忘记她。后来,他回到了自己母亲住着的小茅屋。母亲已经很老了,可是仍旧天天到森林里去采撷草药。儿子回来,同她共享天伦之乐,使她感到十分喜悦。
男孩老是静坐在河边的柳树上,愣愣地望着河水发呆,把大部分时光消磨过去了。秋天来临了,树叶枯萎起来,变红发黄,一片片飘落到河岸上。一阵阵秋风把河面吹起了涟漪。有时候,河里还有一根根的圆木流放下来。男孩拿起他的芦笛吹奏起来,笛声是那样恬淡平静,如怨如诉,达到了一种过去从没有出现过的意境。小鸟都围到他的身边,静静地站在岸边岩石上倾听着,不再啾啁啭鸣。
他情不自禁地重温着往昔的梦:有朝一日,公主坐着大船顺流而下,把他带到王宫里去过日子。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了,一轮比平时更加鲜红的落日徐徐隐没在云霞雾霭之中。夜色那样黑, 男孩只能看到萤火虫的光亮在草丛中一闪一灭。寥落的疏星在天空中时隐时现。蟋蟀早就不像许多年以前那样高亢呜叫了。传到他耳朵里来的只有树叶的飒飒声和河水拍岸发出的哗哗声。
有一两回,他又到京城里去,坐在一家修鞋匠作坊门外,吹着肥皂泡。那些过去曾经看过他吹肥皂泡而现在还记得他的城里人,又停下脚步看他,因为尽管大部分人是为了修鞋才去的,可是总有一些人想看看肥皂泡。那位公主再也没有从那里走过。他想,她必定早已学会自己吹肥皂泡了。就在这时,他忽然在一个肥皂泡里看到了那位公主的倩影。这个肥皂泡也和其它肥皂泡一样,升过房顶,向着很远很远的地方飘去。他想,虽说肥皂泡里的只是转瞬即逝的反照,那也足够了,毕竟这正是肥皂泡的奇妙之处呀!
有的时候,他也喋喋不休地把在肥皂泡里看到的那个影子告诉过往的行人。因为吹肥皂泡的人就是他自己,所以,他讲到的那个影子其实多半就是他本人的影子,只不过因为肥皂泡表面受光线折射,他辨认不出自己的那副尊容而已。有一天,一个明智的长者路过,他捋着胡须说道:“这个人老是一门心思地把肥皂泡里看到的幻影信以为真,唠叨给大家听,岂不是活见鬼!他注定会白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耽误掉,结果弄得终身一事无成。”可是男孩听不明白那位长者讲的道理,依然故我地津津乐道他在肥皂泡里见到的那个影子。
彼尔•魏斯特贝(1933—),瑞典当代著名作家,瑞典笔会主席。魏斯特贝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在美国上过学,游历过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他写过小说、诗歌、游记和报告文学等。1949年,他的处女作《吹肥皂泡的男孩》短篇小说集问世。这个集子以优美洒脱的文笔描写了各种男孩子的性格,是当代瑞典儿童文学中深受欢迎的佳作。
原载于《世界文学》1981年第3期


黑色的土裙

【科特迪瓦】贝尔纳·贝·达迪埃 刘广新译
从前,有个姑娘叫阿依娃,母亲早已死了:她出生之日,就是母亲去世之时。
整整一个星期,母亲一直在难产中。好几个接生婆闻讯赶来,母亲依旧不能分娩。
婴儿哇哇地第一声啼哭,母亲也随之咽了气。
丈夫为妻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过了些时候,父亲又结婚了。从婚礼之日起,小阿依娃就开始受折磨。天底下的活儿,样样她全干过,没有她没受过的苦,没有她没受过的罪。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后娘见她微笑,就气急败坏地加倍折磨她。
小阿依娃长得很漂亮,超过村里所有的姑娘。她容光焕发,美丽得使后娘忌妒,使她生气。
后娘虐待她,让她干累活,罚她做苦工,可是阿依娃这个没亲娘的孤儿却笑得更欢,出落得更美。她爱唱歌,唱得那样动听迷人。她温柔可爱,待人和气,反倒常常挨打。后娘打她,还因为她生来勇敢。早晨鸡还没叫,她第一个起床;晚上狗已入睡,她才最后上床。
后娘真不知道怎样办,才能制服这个姑娘。早晨起来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晚上瞌睡的时候,她挖空心思地想啊想,想着怎样对付她。她的鬼心眼流露在目光里,闪出猛兽般的凶焰。她想方设法要姑娘不再微笑、不再唱歌、不再越长越美。
她死劲地耐着性子,最后总算想出了一个鬼计。一天早晨,她走出自己的小茅屋,对孤苦伶仃的孩子说:
“嘿!去洗洗这条黑色的土裙,去哪儿洗都行,不过要洗得跟高岭土一样白。”
后娘把黑色的土裙扔在她脚边,她依然笑眯眯地拾了起来。对于她,微笑可以代替叹息、埋怨、眼泪与啜泣。
优美的笑脸使周围的一切着迷,而在后娘心里燃起的却是妒火。这团妒火遇上笑脸,好比火上浇油,她用尽全力扑向这个没娘的孩子,孩子依旧面带微笑。
最后,阿依娃拿上黑色的土裙上路了。她足足走了一个月,来到一条小溪边。她把土裙泡在小溪里,可是裙子滴水不沾,怎么也泡不湿。小溪里长着睡莲,莲叶下面有鱼儿游动,河水不停地流呀流。河岸上的癞蛤蟆好像也想吓唬这个没娘孩儿,鼓起腮帮,齐声大叫,可她还是笑脸相迎。阿依娃再次把黑裙浸到水里,土裙还是不沾水。她唱着歌,又上了路。
那该有多好呀,阿依娃哟,阿依娃!
眼前的路上,横躺着一棵粗大的木棉树。树干上有个树洞,洞里有一潭黄色的清水。微风吹拂,水在沉睡。一大群蚂蚁,翘着螯齿,守卫在水边,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地传达口令。木棉树的主干上,有根枯死变白的干树杈,好像是木棉树伸出的一个指头,指向天空。树杈上落着一只与众不同的秃鹫。它展开庞大的双翅,遮住了这一方的太阳;明亮的眼睛,闪电般地闪着凶光。秃鹫的爪,像露出地面的大树根,一直拖到地上。瞧,它还有一张利嘴呢!没娘的孤儿,在黄色的清水里洗黑土裙,土裙还是不沾水。
阿依娃哟,阿依娃!
她来到黑猩猩村,对黑猩猩讲述自己的遭遇。听到她的经历,气得这群黑猩猩顿足捶胸。它们允许她在村边的水泉里洗裙子。可是,这里的泉水也不能把黑土裙沾湿。
没娘的孩儿又上路了。现在,她来到的这个地方可真怪:她所到之处,道路展开,走过之后,道路闭合;这里的树木、小鸟、小虫、土地、枯叶、黄叶、青藤、野果……所有的一切都能言善语。在这渺无人迹的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推她,又似乎有什么人在唤她:嘿嘿,小阿依娃哟!她走着,走着,不停地走,却不见移动。突然,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推着她走,她走了一段又一段,一直走到森林深处,来到一个幽静的去处,静得叫人害怕。
眼前是一块林中空地。香蕉树下,有一道宁静的流水。她跪在水边,嘴角挂着微笑。明亮的水面,粼粼细波,倒映着蓝天、彩云和树影。
阿依娃用手捧起清水,撩向黑色的土裙,土裙居然被打湿了。她跪在泉边,整整洗了两个月,裙子还是黑的,可她的手上却满是血泡。她还是洗呀洗,不停地洗。
阿依娃哟,阿依娃!
她刚刚唱完这支歌,只见妈妈来了,递给她一条白色的土裙,一条比高岭土更白的土裙。妈妈拎起黑色的土裙,一言未发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依娃回到家里。后娘睁大了眼睛,看到这条白色的土裙时,惊恐万分,全身发抖。这次她发抖不是由于生气,而是由于害怕。因为她认出来了,阿依娃母亲下葬时就穿着这条白色的裙子。
而阿依娃呢,小阿依娃笑了,她永远是笑容可掬的。
她微笑着,微笑着。今天我们还可以看见她那种微笑,那就是浮现在少女唇边的那种微笑。
贝尔纳•贝•达迪埃(1916—2019)是非洲著名作家之一。他早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戏剧创作,因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活动,1949年曾被监禁;1952年发表第一本充满人道主义的诗集《起来,非洲》1956年发表自传体小说《克兰比》。他的童话集《黑色的土裙》摈弃西方童话中司空见惯的仙女精灵和王子公主,取材于非洲现实生活,展示非洲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使人倍感朴实、幽默、自然、亲切。
原载于《世界文学》1982年第6期


傻孩子(选译)

【西班牙】安娜·玛利亚·玛图特 蔡潇洁译
01
煤灰
煤店的女孩儿额头、手和嘴里都有黑灰。她对着挂在窗户闩那儿的一截镜子伸出舌头,看着自己的上颚,觉得它像一间烟灰色的祈祷室。煤店女孩打开总是滴滴答答的水龙头,即使关着的时候,那里也总挂着一粒轻透的小珍珠。水流很急,像玻璃撞在石砌的水池上碎成千块。煤店女孩在有阳光进来的日子打开水龙头,好让水闪闪发光,让水在石头和那截小镜子上越变越多。一天夜里,煤店女孩醒了,因为她听见月亮摩擦着窗户。她急忙从褥上跳起来,跑向水池,那儿常常映着煤工黑乎乎的脸。整个天和地都被黑灰占满、涂黑,黑灰从门底和窗缝渗进来,杀死飞鸟,进入一张张大开着的像烟灰色祈祷室的傻嘴。煤店女孩满怀嫉妒地看向月亮。“要是我能把手伸进月亮里多好,”她想。“要是我能用月亮洗洗脸,牙齿和眼睛多好。”煤店女孩打开水龙头,水渐渐升上去,月亮落下来,落下来,直到没入水里。于是女孩也学它。黎明在池底看到了女孩,紧紧地抱着月亮。
02
树
03
旋转木马
安娜·玛利亚·玛图特(Ana María Matute,1925—2014),西班牙女作家, 2010年塞万提斯奖得主。玛图特自称她的一生是“纸生活”的一生。她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也正是“世纪中一代”驰骋西班牙文坛的时候。不过,虽然同样以战后的西班牙为背景,她的创作方式却从最初就在“主流”之外徘徊:比起客观白描,她更偏爱“主观世界”,叙事语言是抒情、隐喻和象征化的,叙事结构是片段化、场景化的,更有神话和奇幻成分穿插其中。虽然她的作品斩获了本国各类文学奖项,但当时西班牙主流评论界的态度却是审慎、犹豫甚至质疑的,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于玛图特作品中种种“现代性”的研究才开始大量涌现。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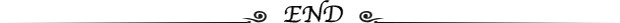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言叶 排版:文娟
校对:秋泥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