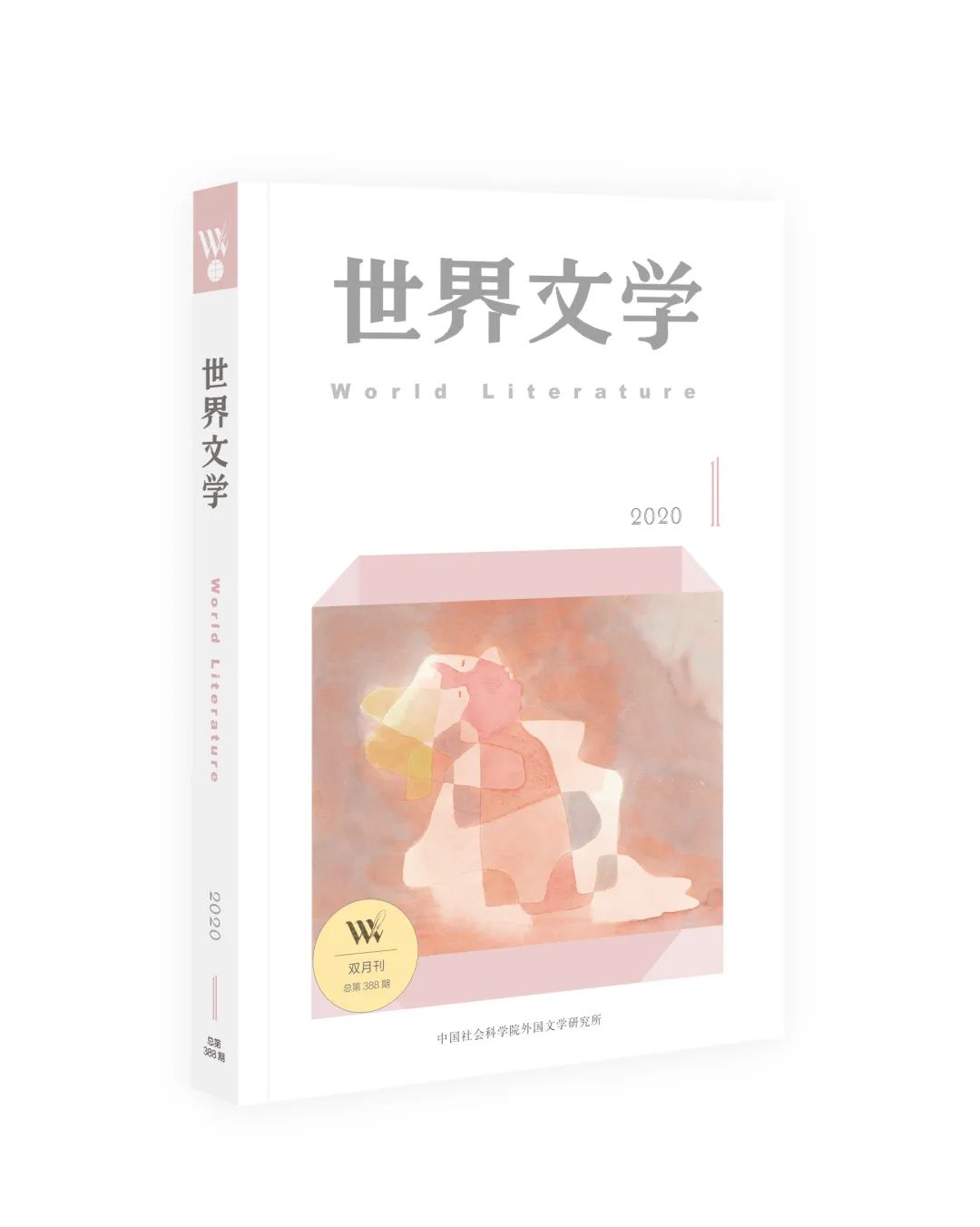众家言说|龚蓉:《劝导》中的“淡淡忧伤”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劝导》中的“淡淡忧伤”

龚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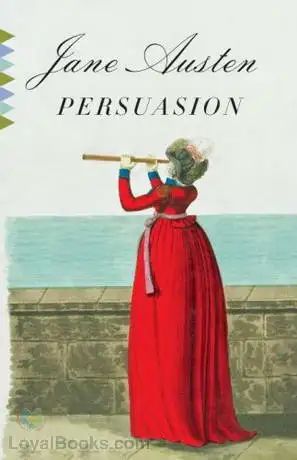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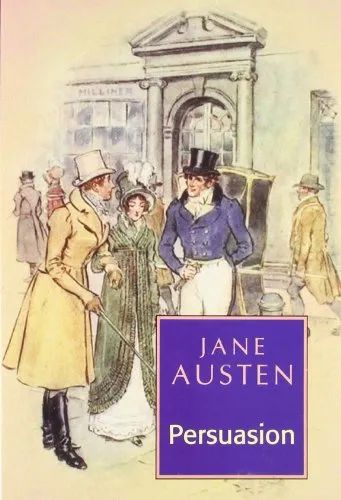

不过,一位匿名苏格兰评论者早在一八一八年五月就已经发现《劝导》令读者感到悲伤这个特点:他/她在肯定奥斯汀“善于观察,感情细腻,能精妙地运用幽默,动人心弦之处甚多;她的所有作品都贯穿着对人性的宽恕、平和而又纯真的笔调,几乎无人能及”的同时,还指出“作为故事,它们[两部小说]本身微不足道。第一部小说(《诺桑觉寺》)轻快活泼一些,第二部(《劝导》)则更为哀婉动人”。显然,这位苏格兰评论者并不认为《劝导》是一本足以传世的佳作,但他/她关于该小说“哀婉动人”的评价呼应了布鲁姆在二十世纪所描述的读者对这本奥斯汀遗作的整体印象。布鲁姆将《劝导》收入在《西方正典》所附录的经典书目中,认为该小说的“这种悲伤充实了我所谓小说的经典劝导性,它借此向我们显示了其非凡的美学价值”。布鲁姆对《劝导》美学价值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奥斯汀对女主角安妮·埃利奥特的人物塑造及其内涵方面,尤其是安妮如何体现了奥斯汀对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女主角克拉丽莎·哈娄所体现出的清教意志【关于清教意志,布鲁姆并没有明确对其加以定义,只指出“清教意志依赖于个人灵魂的自尊,以及精神领域中私人判断的相关权利,包括宣称自己内心的灵光,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这一灵光自行阅读与阐释《圣经》”。在提及理查森笔下克拉丽莎的清教意志时,布鲁姆则解释称:“克拉丽莎保持自身清白的强烈意志消解了她对生存的渴望。接受罗夫雷斯事后的悔过并与之结婚会损害她生存的本质意义,这就是说,她受到侵犯的意志必须得到尊崇。”】的修正。布鲁姆认为安妮“虽不引人注目,却必定是奥斯汀本人最情有独钟的创造……她在安妮身上确实是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天赋……安妮·埃利奥特很可能是所有散文体小说中感觉最敏锐、不曾错失半点细节的人物”。他还指出安妮“性格中的秘密就在于结合了奥斯汀的反讽和华兹华斯那种希望姗姗来迟的感觉”,而安妮这个人物的复杂与敏锐则是因为她“是奥斯汀笔下最后一个我必须称为清教意志的女主人公,但是在她那里,这个意志被其传人即浪漫派的同情性想象修正了(或许是完善了)”。于是,克拉丽莎“世俗化的清教殉道行为的强烈道德内涵”,在安妮身上得到了修正,这体现为在安妮心理中“因为自我的分裂而引起的伤感,记忆与想象结为了同盟,共同对抗意志”。

在一定意义上,《劝导》是一部颂扬坚贞并以善变衬托坚贞的爱情小说,但这种坚贞并不是山盟海誓的恋爱双方在历经磨难之后仍然忠于彼此的坚贞,而是婚约中断后,双方在分别多年后仍然在情感上忠于彼此的坚贞。不过,在安妮与温特沃思上校重逢前,他们都已下定决心不再与对方重续前缘,只是双方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十九岁的安妮出于责任感,听从了拉塞尔夫人的劝导,主动中断了同温特沃思上校的婚约,但却因仍然痴恋温特沃思上校而从此封锁自我,不顾拉塞尔夫人的劝告,先后拒绝了查尔斯·马斯格罗夫与堂兄埃利奥特先生的求爱,原因正如她在与哈维尔上校论辩时所坚称的那样,女性(或者是她本人)“爱得更长久,即便所爱之人已逝,即便希望已全无”。温特沃思上校对爱情的坚贞主要体现为他在与安妮别后的八年里未曾向别的女性示爱,但这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事实上,他一直因为心怀怨恨而下意识地排斥她:“她[安妮]辜负了他,抛弃了他,让他深感失望;更糟糕的是,她那样做还证明了她性格中的怯弱,那是他决断、自信的性情所无法容忍的……他那时是那么全心全意地热恋着她,此后也不曾见过任何一个可以与她相媲美的女子。但是,除了某种自然而然的好奇心,他并不想再见到她。她对他的魅力已荡然无存。”虽然他在写给安妮的信中强调自己一直都爱着安妮,“从未朝三暮四”,但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重返英国之际,他拒绝与安妮再续前缘:“他的目标是结婚……只要遇到了称心的女子,就立刻安个家……他那颗心已经准备接受他能遇到的任何一位动人的年轻女子,只要她不是安妮·埃利奥特。”于是,在寻求合适结婚对象的过程中,他先是沉醉于两位马斯格罗夫小姐对他的爱慕,然后又误将路易莎的固执与任性当作决断与坚定,对她另眼相看,直到莱姆发生的事故让他重新发现安妮的种种可贵之处,并在之后的反复回忆与对比中再次确认了自己对安妮的感情。对此,布鲁姆总结称:“婚约遭拒的温特沃斯重修旧好的愿望并不如安妮那样迫切,然而记忆与想象的融合战胜了他的意志。”
就此而言,安妮“世俗化的清教意志”体现为在忠于已逝情感的同时,与温特沃思上校保持距离。初次重逢之际,安妮深知自己当初的决定如何伤害了自信满满的温特沃思上校,虽然她因为自己八年前的决定而一直生活在痛苦中,但面对温特沃思上校的刻意冷漠,尽管她仍然对上校情根深种,出于自尊与自傲,她还是下定决心遵从意志,不再幻想与温特沃思上校再续前缘:
“变得都已经让他认不出来了!”这句话让她完全无法释怀。但很快她又开始庆幸自己听到了它。它能让她保持清醒;它平复了她的激动不安;它让她平静了下来,最终也定然会让她更加快乐。


《劝导》, BBC, 2007
在布鲁姆看来,《劝导》之所以不时显露出“优雅悲情”,一个客观原因“或许与简·奥斯汀不佳的健康状况有关,表明了她对自己英年早逝的预感”。的确,奥斯汀大概在开始创作《劝导》时就已感到身体不适,而到一八一六年初,她的身体状况就已经相当不理想了,有研究者认为她当时或已表现出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亦称艾迪生病)的症状,这使得她不得不在一八一六年五月二日中断《劝导》的创作,随后在姐姐卡桑德拉的陪同下前往格洛斯特郡的切尔滕纳姆进行水疗,同年六月十五日返回乔顿,之后不久,她便于七月十八日完成了《劝导》的初稿。因此,身体状况的恶化或许造成《劝导》匆匆结尾,仅以只言片语交代次要人物的结局,如克莱太太与埃利奥特先生的私情、伊丽莎白的失落等,也没有像其他小说一样安排女主角安妮定居在某处,令读者掩卷之时感觉意犹未尽。但除此之外,我们似乎还可以添加上两个严重影响奥斯汀情绪的客观因素,即针对奥斯汀三哥爱德华·奥斯汀及其乔顿产业产权的诉讼案(1814),以及奥斯汀四哥亨利·奥斯汀的银行破产事件(1816)。
一八〇九年十月,已继承了托马斯·奈特的三宗产业的爱德华·奥斯汀(他于一八一二年才正式更名为爱德华·奥斯汀·奈特)将选择权交给了母亲与两位妹妹,请她们在其中两宗产业——汉普郡的乔顿及肯特郡的瓦伊——上选择一幢房子居住,母女三人选择了新近翻修过的乔顿农舍。乔顿村是一个宁静古朴的英格兰乡村,距离奥斯汀的出生与成长之地史蒂文顿不过十七英里,而乔顿农舍则位于乔顿村中央,距离爱德华本人的都铎风格宅邸乔顿大宅仅四百米。对于自一八〇一年起便随父母与姐姐客居巴斯、父亲去世(1805)后更是四处搬迁的简·奥斯汀来说,乔顿农舍无异于第二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而对其作家生涯而言,她在乔顿村的安居生活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三年,她先后出版了《理智与情感》及《傲慢与偏见》这两部前期完成的作品;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五年,她创作与出版了《曼斯菲尔德庄园》及《爱玛》;一八一五至一八一七年,她完成了《劝导》,并留下了未完成的遗作《沙地屯》(Sanditon)。一八一四年初,爱德华养母的一个法定继承人起诉爱德华,声称自己才是包括乔顿农舍在内的奈特家族乔顿产业的合法继承人。在一封写给姐姐的信中,简·奥斯汀曾乐观地相信这桩讼案很快就会过去,但爱德华于同年十月收到了一份针对乔顿产业的逐出租地赔偿令,这使这桩官司的前景骤然黯淡起来。事实上,这桩官司一直拖到奥斯汀本人过世之后才有了了断,爱德华被判支付给原告一万五千英镑的赔付金。为了偿付这笔赔付金,爱德华甚至不得不砍掉并出售乔顿庄园林区的树木。换言之,自一八一四年起直至其去世,奥斯汀生活中的一大阴影便是,被迫离开乔顿,离开熟悉的乡村生活,重新过上居无定所的生活。在《劝导》中,安妮对巴斯的厌恶或许正是奥斯汀自己对巴斯印象的投射,而那个几乎就被拉塞尔夫人蛊惑的安妮形象,似乎也向读者透露了在病榻上完成该小说创作的作者的内心企望:在小说第二部第十章中,拉塞尔夫人为了劝说安妮接受埃利奥特先生,向安妮描述了一幅美好前景,即安妮以埃利奥特夫人的名义重归凯林奇,安妮听罢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渴望,她“不得不转过身去,起身走到远处的一张桌子旁边,靠在那儿假装忙着做点什么,竭力地压制住这幅图景激发起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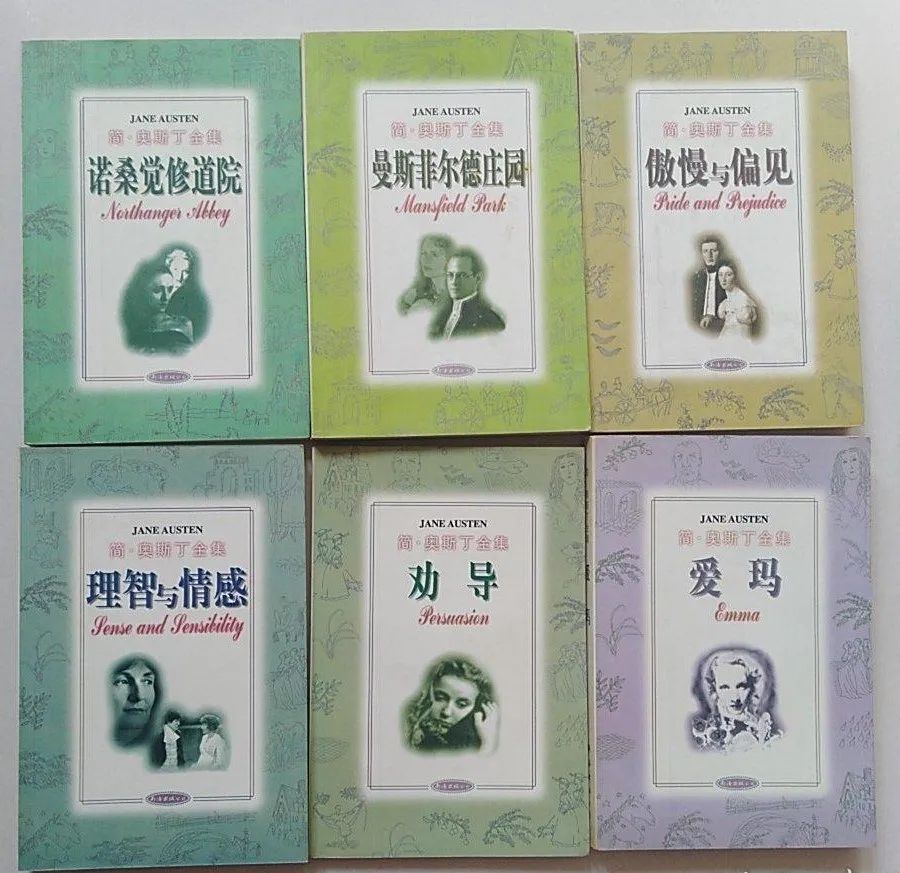
早在一八〇一年,亨利·奥斯汀便以银行家及军队代理人的身份移居伦敦,同友人一道开设了自己的银行,之后不久又成为汉普郡奥尔顿的一个地方私人银行的合伙人。一八一三年,在舅舅与弟弟爱德华·奈特的担保下,他又成为牛津郡的税务长,而两位担保人则分别支付了一万英镑与两万英镑的担保金。当拿破仑战争造成英国国内经济虚假繁荣时,银行业却繁荣昌盛,亨利的银行自然也受益良多。但在一八一五年滑铁卢战役后,英国经济迅速陷入低迷,政府骤然大幅削减从英格兰南部各郡购买食品、布匹及其他储备的订单。亨利在奥尔顿的奥斯汀、格雷与文森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合伙人、杂货商格雷首先陷入困境,迅速导致该银行在当年便倒闭。受其影响,亨利在伦敦的合伙银行也很快出现危机,并于一八一六年三月宣告破产。亨利的破产则导致他的舅舅与正处于乔顿产业讼案的弟弟爱德华的担保金荡然无存,损失惨重;两位在海军的奥斯汀兄弟也因亨利银行的破产而丧失了绝大部分存款与他们在战争中赢得的赏金,并因此无力继续支付各自每年提供给母亲奥斯汀太太的五十英镑赡养费。于是,就像《劝导》中的埃利奥特爵士一家一样,奥斯汀家族的众多成员也面临着经济压力,需要节俭开销以顺利渡过难关。奥斯汀与亨利的感情最为深厚,亨利深陷财务危机之际恰值奥斯汀身体开始出现严重状况之时,很难说奥斯汀对这位兄长前途的恐惧、对其他兄长经济状况的担忧、对母亲与姐姐及自己未来生活的焦虑【研究者指出,在此之前,奥斯汀母女三人每年的收入大概为450英镑,其构成如下:奥斯汀太太每年有210英镑的分红收入,卡桑德拉大约有35英镑,作家本人的收入则完全依赖于不稳定的小说版权收入;此外,弗朗西斯、亨利与詹姆斯(奥斯汀长兄)每年各自支付给母亲赡养费50英镑,爱德华每年提供100英镑。如果以1990年代的英镑对美元兑换机制计算,她们三人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她们的年收入将从每年约45,000美元降至近乎贫困线的约21,000美元。】没有影响到她的身体与情绪,并进而加深了《劝导》的整体阴郁氛围。当奥斯汀在小说中描写安妮对家道中落、身患重疾却又自强不息的史密斯太太的尊重时,她未尝没有借此表达她对破产后的亨利的敬意:坚韧的亨利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积极应对,选择担任神职以偿还部分债务,并于一八一六年十二月通过了温切斯特主教的考核,后受聘为乔顿教区的牧师助理。当奥斯汀在小说中安排温特沃思上校帮助史密斯太太收回其丈夫在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以确保史密斯太太能够生活无忧时,这或许既隐藏了她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亨利处境时的无力感,也包含了她对亨利未来生活的期望与祝愿。鉴于此,当小说结尾段落将史密斯太太的幸福与安妮的幸福并置时,这段表面上充满矛盾的段落似乎竭力希望其读者能够明白,尽管幸福充满不确定性,健康、乐观、真情对于幸福之必要程度完全不亚于金钱对于幸福之重要程度。

当奥斯汀着手创作《劝导》时,英格兰正在经历奥斯汀一生中前所未见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战时经济的崩溃、不加监管的银行制度、史无前例的国债、高失业率(军备物资需求直线下降造成供应链工厂纷纷倒闭)、为保护国内粮食价格而以价格手段控制粮食进口并最终导致国内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的一八一五年《谷物法》等,足以构成一股严重威胁中下阶层安稳生活的经济风暴。同时,议会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完全无视国债压力,任性地做出了立即取消收入税以讨好富有阶层的决定,这不仅将税负压力几乎平摊到了每个人头上,使得中下阶层的生活愈发困难,更加剧了国家的债务危机。《劝导》中埃利奥特爵士无视债务、继续以财务赤字维持奢侈体面生活的愚蠢行为,显然与英国当时正面临的财政问题同出一源。此外,战争结束后,军人纷纷退役,英国皇家海军更是减员百分之八十五。从军队中退役的这三十万军人除了推高失业率,还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有议员甚至因此抱怨支付给退役受伤士兵和海员的已减半退伍费开销太大,小说中哈维尔上校一家偏居于淡季的海滨小镇的生活,则无疑折射了同时代退役海员的困窘处境。【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国家债务已攀升至75亿英镑;至1819年,英国的国家债务已是国民收入的2.7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国家债务还要高。】


谈论简·奥斯汀所排斥的社会经济现状的做法已成为时髦,比如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部分地构成了她的人物们能享有经济保障的根本原因。然而所有文学巨著都建立在排除的基础上,也无人证明增强对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意识对于人们学会解读《曼斯菲尔德庄园》会有丝毫裨益。《劝导》结尾时对温特沃思在其中享有高位的英国海军表示崇敬……但是奥斯汀再一次显示出,她的卓越艺术是建立在排除的基础之上,英国海军令人不快的现状与《劝导》的关联并不比西印度群岛与《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关联大。
这样的小细节甚至可以与一八一六年的“无夏之年”建立起联系。一个晴朗的深秋午后,安妮与众人散步至温斯罗普附近。途中,安妮因留意到温特沃思上校对路易莎的热切赞许而情绪低落,当她随着众人“穿过一片片广阔的圈占地”时,她注意到“那里农人们正在忙着耕作……农人们正在对抗着那诗意感伤的情怀,一心想要带回春天”。珍妮特·托德与安特耶·布兰克认为,如果以后见之明来解读农人们的美好意愿,此处便具有浓厚的反讽意味,因为战争将在一八一五年重新爆发,农人们还将在一八一六年面临严重的歉收:一八一五年四月,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这极大地影响了北半球中高纬地区国家的气候,一八一六年的英国因此迎来了寒春与凉夏,奥斯汀在这年三月的一封信件中提到,乔顿农居她住处附近的一个池塘的水都快漫出来了,村庄里的道路脏兮兮的,农居的墙也一直湿乎乎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所写的信中描述了“无夏之年”对经济的影响:此时的麦子还是绿油油的,仅斯塔福德郡与什罗普郡就有两万六千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人面临着饥荒。

如此种种解读所指向的都是奥斯汀如何借助《劝导》来思考变迁中的英格兰社会、政治与文化,其结论不会抹杀布鲁姆关于《劝导》让读者心生悲切的描述,反而会促使读者进一步分析究竟是什么让自己在掩卷之余仍能体味到萦绕在小说字里行间的“淡淡忧伤”。温特沃思上校的爱及其家人的亲情,能够弥补安妮缺失的母爱与从不曾拥有的父爱与手足之情,却无法让安妮重返凯林奇、将其作为自己永远的家,而这恰恰是小说中安妮的想象与回忆差一点让她从自己的坚持中溃败下来的原因:“有那么一阵子,她的想象与内心都受到了蛊惑。想到成为她母亲那样的人,想到她将是第一个复活‘埃利奥特夫人’这个珍贵称呼的人,想到重回凯林奇,重新把它称为自己的家,自己永远的家,这种想法的魔力让安妮一时间无法抗拒。”作为海员的妻子,安妮注定要效仿克罗夫特太太,跟随丈夫四海为家,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一九九五年电影版《劝导》便以安妮坐在丈夫指挥的战舰中出海的镜头结尾。英国独立电视台所拍摄的二〇〇七年电影版《劝导》则在结尾处进行了重大改动,安排温特沃思上校带领被蒙着双眼的安妮乘马车回到凯林奇:温特沃思上校买下了凯林奇府,将它作为新婚礼物赠送给安妮,让安妮的人生从此不再有遗憾。这个让安妮不再有遗憾的改编,看似满足了读者与观众的期望,却在本质上消解了小说的阴郁色彩,小说在白马王子解救被困公主、让她重新拥有失去的一切的虚幻中丧失了其原有的美学意义。
龚蓉,1972年生,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编审,研究领域为早期现代英国文学,曾发表《自然与自由:北美森林林木热与十八世纪不列颠帝国政治》等论文,并参与翻译《贝克特全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1年第2期,责任编辑:杨卫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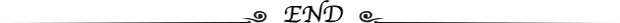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文娟 校对:秋泥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