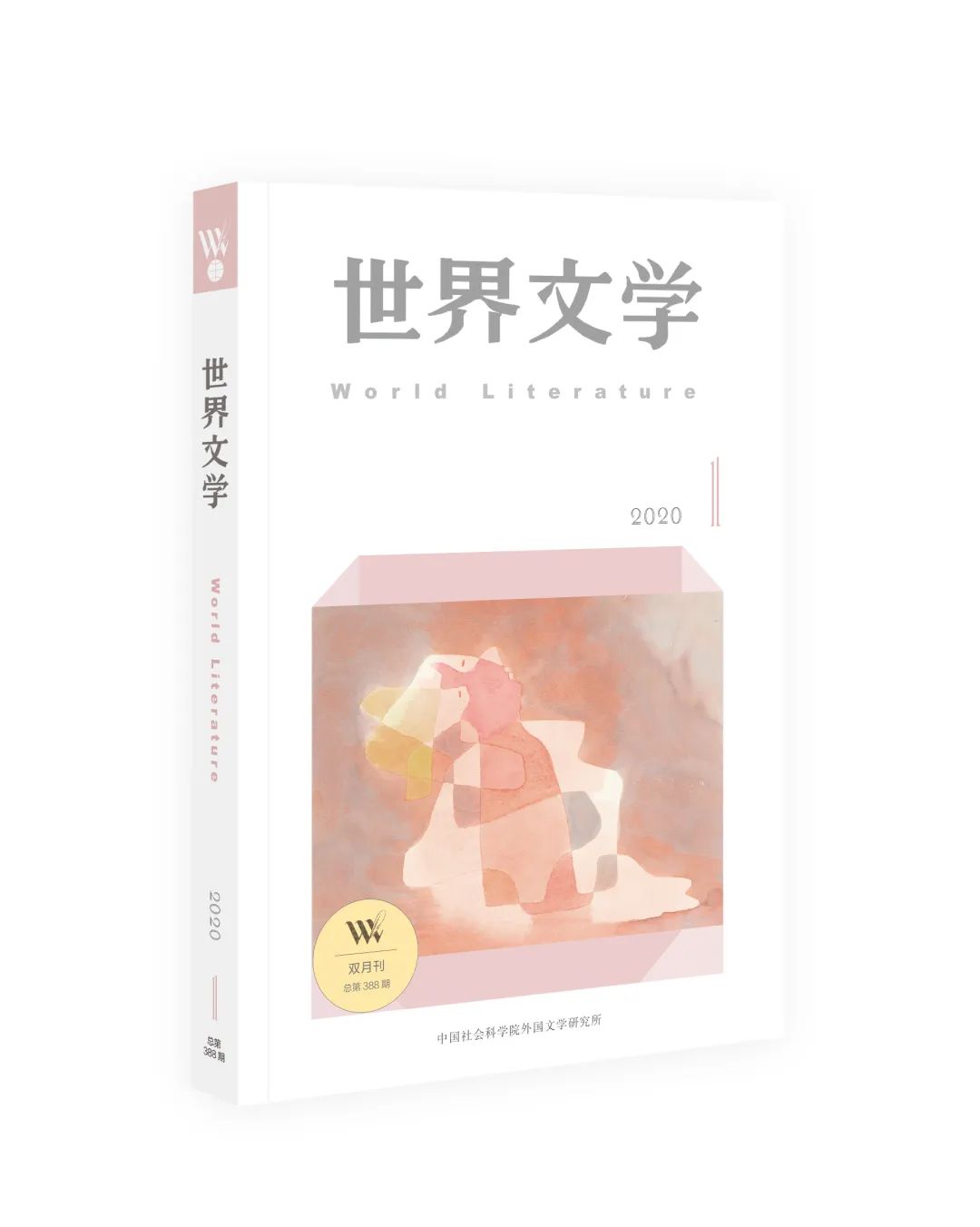父亲节专辑 | “你是世界的骨与肉”:《世界文学》中的父亲形象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致父亲(节选)
【奥地利】弗兰茨·卡夫卡作 张荣昌译
最近您问起过我,为什么我说畏惧您。如同往常一样,对您的问题我无从答起,一来是确实我畏惧您,二来是要阐明这种畏惧涉及到的具体细节太多,凭嘴很难说得清楚。在这里我试图用书面形式回答您的问题,内容只能是很不完善的,因写信的时候也是畏惧的,这就妨碍我对您畅所欲言,加上材料浩繁,远非我心力和智力所能及。
最初那几年中,只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有一天夜里我呜呜咽咽,吵着要喝水,当然并非真的因为口渴,多半是为了怄气,部分是为了解闷。您声色俱厉,几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后,您就将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儿站了很久。我不想说这样做不对,当时要保持夜间安静也许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不过是想用这例子来说明您的教育方法及其对我的影响罢了。后来,我大概也就驯顺听话了,可是我的心灵却因此带上了创伤。要水喝这个毫无意义的举动,我觉得理所当然。被挟到外面去,我大受惊吓。我天性如此,这二者我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儿去。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
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可是我常有的这种自悲感 (从另一角度看却也不失为一种高尚和有益的情感)却都出于您的影响。按说,我需要多少受点鼓励,得到点温暖,您应该替我多少清除点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才是,可是与此相反,您却拦住了我的去路,您当然是出于好意,要我走另外一条路。可是,那条路我走不了。譬如说,我敬礼敬得好,步伐走得齐整,您就鼓励我,而我却并不是未来的士兵。再譬如说,我饭量大,甚至还能边吃边喝啤酒,抑或我会哼哼莫明其妙的曲调,或者我会学着您的腔调唠叨您最爱说的口头禅,您也鼓励我,而这一切与我的未来均无干系。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在今天,也只有当您自己受到连累,当问题涉及到您的自尊心被我损伤(例如由于我想结婚)或因我而受到损伤(例如佩帕辱骂我)的时候,您才给我说几句勉励的话。在这种时候,您才会鼓励我,提醒我记住我的身份,指出我完全有资格挑选门当户对的配偶,而佩帕则大受谴责。可是且不说我如今这一大把年纪已不为勉励的话所动,这种鼓励并不是首先着眼于我,那么这对我又会有什么用呢。
想当初我是何等需要这种鼓励,而且是处处都需要。当时,只要一看见您的身躯,我心就凉了半截。譬如,我们时常一起在更衣室脱衣服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得。我瘦削、弱小、肩窄,您强壮、高大、肩宽。在更衣室,我就觉得我是够可怜的了,而且不单单在您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可怜,因为您是我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呀。后来我们从更衣室出来走到众人面前,我拉着您的手,一副小骨头架子,弱不禁风,光着脚丫子站在木板上,怀着怕水的心理,您反复给我做游泳的示范动作,我却一点也模仿不了。您原本出于好意,殊不知我却羞得无地自容。此时此刻,我的心灰冷了,在这样的时刻,我在各个领域取得的一切令人不快的经验显得何等的协调。要说起来,我最感到自由自在的,莫过于您有时候先脱好了衣服,我可以单独一个人呆在更衣室里的时候了,那时我就可以尽量拖延当众丢丑的时间,直至您最后终于来查看并将我从更衣室里赶出来为止。我是很感激您的,您似乎没有察觉我的困惑,我对我父亲的躯体也是感到骄傲的。再说,我们之间今天仍然还存在着相似的差异。
与此相应的就是,您在精神上也绝对占上风。您完全是靠了您自己的个人奋斗才这样飞黄腾达起来的,因此您无限自信。我小时候对这点还不太体会,到我长大成人后我才顿开茅塞。您坐在您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您的看法正确,别人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是偏执狂,是神经不正常。您是那样自以为是,以致您可以不讲道理,总是您常有理。有这样的情况,即您对一件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看法,而因为您没有看法,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所有可能存在的意见便统统都得是错误的。譬如,您会骂捷克人,接着就骂德国人,骂犹太人,您不仅选中了靶子骂,您还一古脑儿什么都骂。到头来,除您以外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性,他们的权力的基础是他们这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起码我觉得是这样的。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审判》《城堡》《变形记》等。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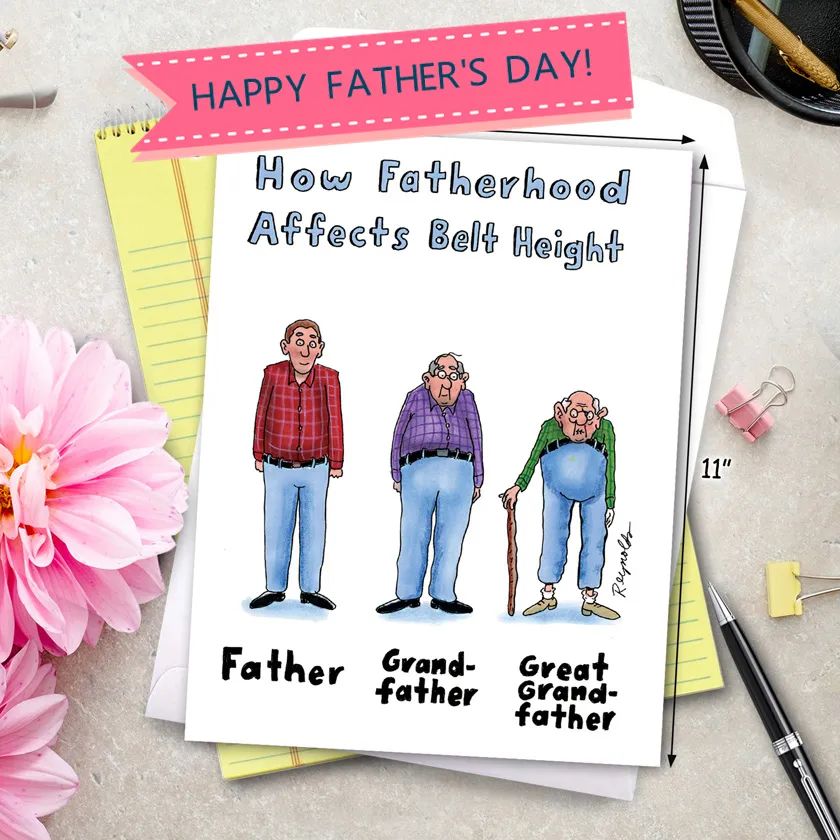

冥冥中的呼唤(节选)
和父亲在一起,我才感到安全。我追随他的脚步,那是他奋斗的回声。我们聚在一起时,我才觉得心满意足。每当天空乌云密布行路艰难的时刻,我便回忆过去,把一腔牢骚付与回忆,心情渐渐平静。只要想到过去,心儿便得到抚慰,人便增强了承受力,仿佛是向虚无求援。一路上我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上了年纪饱经风霜仍然如此。若心焦如焚,我便闭上眼睛。侍从见我闭上眼睛,都不敢靠近。这样,我又得了一个别号——沉思者。因为我是被迫朝向西方的,所以常常思念过去的东西。
杰马勒·黑托尼(Gamal Al-Ghitani,1945-2015),当代阿拉伯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先后荣获了1980年的国家鼓励奖、埃及科学艺术一级勋章和1987年法国骑士勋章,是整个阿拉伯文学文坛的一流名家。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1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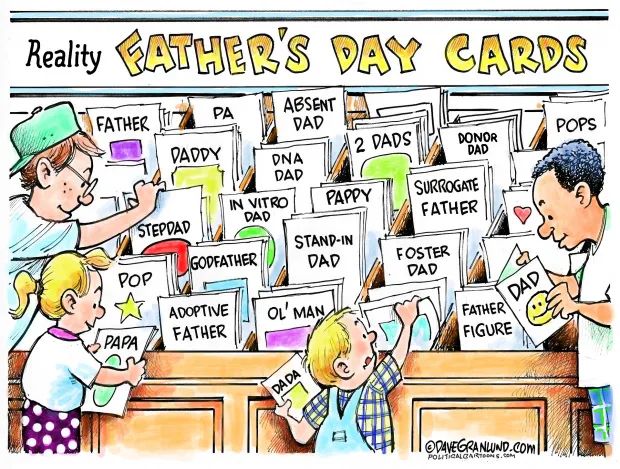

残日(节选)
【英国】石黑一雄作 白晓东译
但你会认为我有失偏颇,如果我说我的父亲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和这些人相提并论,而且我一直都在细读着他的事业,从中了解“尊严”的定义。可是我仍然十分肯定地坚信,在乐宝路庄园他事业的顶峰期,我父亲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尊严”的化身。
我意识到如果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一个人也许会承认我父亲缺少人们通常期待一位伟大管家所具备的多种素质,但我要重申,这些他所没有的素质总是一些表面浮华的东西。虽然它们无疑显得诱人,就像蛋糕上的糖霜,但却不是根本上重要的东西。我指的是诸如标准的口音、娴熟的语言以及例如对驯鹰和蝾螈交配之类话题的广泛知识——这些都不是我父亲所能夸耀的素养。另外,还必须记住,我父亲属于更早一代的管家。在他从业之始,这些素养对一个管家来说并不适当,就更谈不上值得羡慕了。对于流利的语言和宽广知识面的迷恋似乎始于我们这一代,或许是步马歇尔先生的后尘。当二流人物试图效仿他伟大之处的时候,误把表面的东西当成了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我们这一代太注重“修饰”;天知道多少时间和精力被花在了训练口音和语言上,多少小时被用在了研习百科全书和“测测你的知识”之中。本来,这些时间是应该花在掌握更根本的东西上的。
我坚持认为,尽管我父亲的英语水平和知识面都很有限,可是他不但通晓所有管理家务的门道,而且在他事业的顶峰,还取得了海斯社所谓的那种“与其身份相称的尊严”。那么如果我可以试着为你描述一下那种我相信使我父亲如此出色的东西的话,我将能够以这种方式向你说明我对“尊严”的认识。
石黑一雄(Kazuo Ishguro,1954一 ),日裔英国作家,生于日本长崎一个军人家庭。1960年随父母移居英国。毕业于肯特大学,在东英吉利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专门从事小说创作,成为英国移民作家中的佼佼者。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4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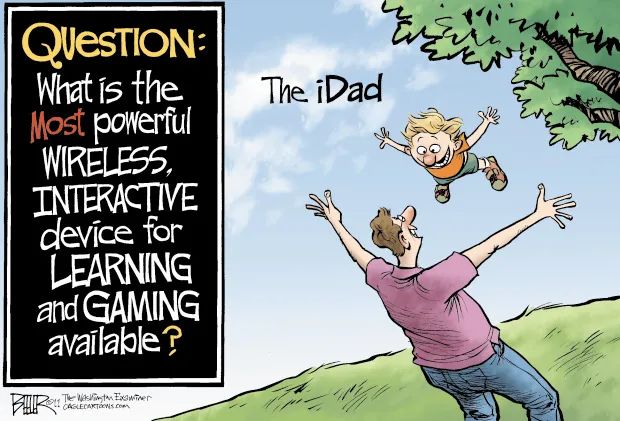

这个星球上的弃儿(节选)
这次也是如此,父亲为了超越“危机”而前往自己早已认定的树木所在之地加利福尼亚。最初像以往那样决定由父亲独自前去,可这时母亲开始发现,父亲即便如此也还是会深深地发怔……便考虑和伊耀一起随同父亲前往。但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在福利工场告诉我们,倘若存在智障问题,是难以取得签证的。就在这反反复复的过程中,一天早晨,母亲对我们表明了她的决定,那就是她一人随同父亲前往加利福尼亚。在早餐的饭桌上,父亲正好也在座。在这因自己而给全家添了麻烦的时刻,想要尽量予以补偿、把一切全都担在自己肩头的父亲,这天仍然在那里发怔。
对于陷入这种状态之中的父亲,现在细想起来,当时我怀有两种感情。一是生气的情绪,认为这个“危机”无论具有什么性质,眼前这个态度都是懦弱的;另一个,则是真切地感觉到父亲确实上了年岁。在以往得以独自超越的“危机”中——也不知是什么性格,母亲告诉我,在与父亲结婚之前就非常清楚这一切,可她却没给我提出任何具体启示——父亲一人闷居在避难之地,好像无论什么事都难以完成,惊恐与悲哀交织于内心之中。
在此前的文字中,我肯定已经有所表述:对于母亲,我可以很自然地将感情移入其中,可对于父亲,却总感到存在距离。
大江健三郎,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35年出生于日本四国爱媛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法文系。主要作品有小说《奇妙的工作》(1957)、《死者的奢华》(1957)、《饲育》(1958)、《人羊》(1958)、《我们的时代》(1959)、《个人的体验》(1964)、《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洪水涌上我灵魂》(1973),及大量的散文随笔。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6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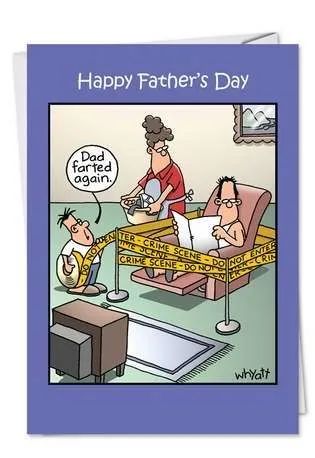

岁末(节选)
【美国】裘帕·拉希莉作 卢肖慧译
我没有参加父亲的婚礼。我甚至不知道有那么个婚礼存在,直到有一个星期天早晨,父亲很早打电话来,那是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我被门上一阵拳击吵醒,接着我听见隔壁寝室的人直呼我的大名。不用听电话,我就知道准是我父亲。没有第二个人会在九点之前打电话给我。父亲向来早起,他相信早晨五点到七点是一日之中的黄金时光。他在这段时间里读报,之后出去散步。我们住在孟买时,他沿着海边公路散步,在美国他就挑北海滨的小路走。尽管他竭力怂恿我和母亲与他同去,其实我知道他是喜欢独自散步的。后来情形就不同了,那些他曾经觉得回味无穷的孤独时光每日与他相伴,成了他的监狱。我知道,自从母亲过世之后,他几乎难以成眠,也懒得去散步。我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接到父亲电话了。他去了加尔各答,探望我的祖父母们,四位老人都健在。我拿起垂在电话线一端的听筒时,指望听到的只是他说他平安回到马萨诸塞,并没料到我现在有了继母和两个异父母妹妹。
他向我叙述了这些细节,好像在竭力回答问题似的,虽然我什么都没问。“我并不要求你在乎她,喜欢她,”父亲说,“你已经成人了,你生活里是不需要她的,可我需要。我只求你最终理解我的决定。”很显然,他准备好我生气——恶言、责难、挂电话。但他说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怎么愤怒,只感觉一种冲淡了的厌恶。当我第一次在孟买得知母亲得了绝症会死去的那天,我感到的就是这种厌恶,这种厌恶自那一刻埋进我心里,就再没有离开过。“她在不在你身边?” 我问,“要不要我跟她说话?” 我这么说话多半出于挑衅,而不是为了礼貌。我不完全相信父亲的话。自母亲去世后,我时常怀疑父亲在电话里讲的事只是为了搪塞我,比如他晚上去了我在家时我们常去的那家意大利饭馆吃了晚餐等等。其实他晚上经常是擦一擦杏仁罐盖子上的积灰,坐在电视前吃杏仁,喝尊尼获嘉威士忌。
他已经不再穿西装,他一身好像是周末打扮,深蓝长裤,奶油色毛衣。他的灰发比我记忆中的又多了,可他还是很帅。岁月爬上了他的脸,鼻子边的皮肉有些松垂,他的绿眼睛——因为这个特征,我母亲坚持认为他们家有爱尔兰血统——不再像以前那么不同寻常。我试图想象他几个星期之前穿着印度丝绸衬衫,披挂新郎圆头巾的样子。
我朝父亲看去。自从母亲走后,他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永远改变了他面貌的表情。那是一种哀伤,且更多是被触怒而又无可奈何,就像小时候他见到我打碎了玻璃杯,或者我们准备去野餐却碰上一个阴沉天气。我们在最后踏进母亲病房的那天早晨,他脸上布满这表情。后来每回我从学校回家,他迎接我时脸上依然挂着这表情,仿佛是冲着我母亲,怪她弃他而去,而现在这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了。
孟加拉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1967—),生于英国伦敦,幼年随父母迁居美国罗得岛州。拉希莉在新英格兰的学院氛围中长大,毕业于伯纳德学院,在波士顿大学深造文学创作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获博士学位。曾在多个大学教授创作课程。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0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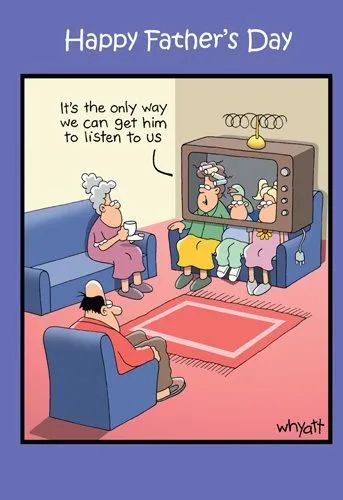

天国之门(节选)
【韩国】金劲旭作 韩梅 范钊颖译
听说打牌对治疗痴呆有效,女人也陪父亲打过牌。认真端详手中的牌时,父亲好像回到了过去。那时候,他在开车前总是认真查看地图,下班回家会确认鞋子是不是摆放得整齐。
父亲眼角下垂,嘴角微微上扬,分明是在微笑。父亲这一辈子总是神情严肃,就像个对自己的角色不满意的演员。这样的父亲竟然在微笑? 女人差一点就要喊出“父亲在笑”。
女人好像受到了意外一击,身体摇晃了几下。她有些恶心。父亲的微笑背后分明隐藏着什么,需要查明,那笑容里隐含着不平之处。身边的女护士想扶住她,女人摆摆手,摇摆着手臂走出了病房。
不见了父亲的微笑,女人依然一片茫然。父亲究竟经历了什么? 竟然露出那样幸福的表情? 那种幸福的表情,就像一下子打开了天国之门。
忽然,一段话像闪电一样划过女人的脑海。
“针灸高手们也会接屠宰场的活儿——为了摆弄出祭桌上用的猪头。在头顶心深深地刺上一针,猪就会微笑。其实这只是肌肉的机械反射,并不是真的在微笑。只有人会笑,笑才是灵魂存在的证据。人身上有个穴位,可以让灵魂脱离肉体,被称为天国之门。在这个穴位上深深扎一针,人就会陷入沉睡,微笑着去往另一个世界。”
金劲旭(1971— ) ,出生于全罗南道光州,本科毕业于首尔大学英文系,硕士毕业于首尔大学国文系。韩国当代著名作家,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戏剧创作系教授。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1期


祭父书(节选)
此刻,我坐在你的主驾位置上。想起曾经你教我的、我学会的东西。从前,我们沿石子路开着小货车,路上的大卡车和拖拉机,载着村民往来于田庄和山野。快到球场时,你把车停下,我们交换位置,从挡风玻璃那儿擦肩而过;你说,点火,我就踩下离合器,拧转钥匙,车发动了。在夏日漫长的白昼里,在黄昏的柔风中,我们缓缓前行。你教导着我。左手边,有麻雀从麦秸零落的田野上飞起,留下欢脱稚嫩的笑声。右手边,橡树给大地降下厚重的困意。车里,你说一句,我便依着做一步。在柔风中,我们缓缓前行。要是我哪里做错了,你就会说我开小差,然后假装生气;我不说话,只是听着,心里很自豪,因为你觉得我是学得会的,虽然老是心不在焉,但是学得会。你教导着我。你很严厉,教课嘛,本就该严厉一点。你用眼神给我指点着每个步骤,你说,挂一档,握好方向盘,慢松离合。你的动作,你握着方向盘的手;我的手,方向盘,我的动作。过去的场景与现在的我重叠交织,又尽数远去。我出发了。我出发,去往你遗留下的一切,一切都是你离去的痕迹。
若泽·路易斯·佩肖托,1974年生于葡萄牙南部小村庄高维亚什。27岁时凭借小说《无睛之眼》脱颖而出,成为萨拉马戈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至今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集和儿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26种语言,并荣获丹尼尔·法利亚诗歌奖、巴西“海洋”葡语文学奖、西班牙卡拉莫书店文学奖、日本年度最佳翻译作品等多个国内外奖项。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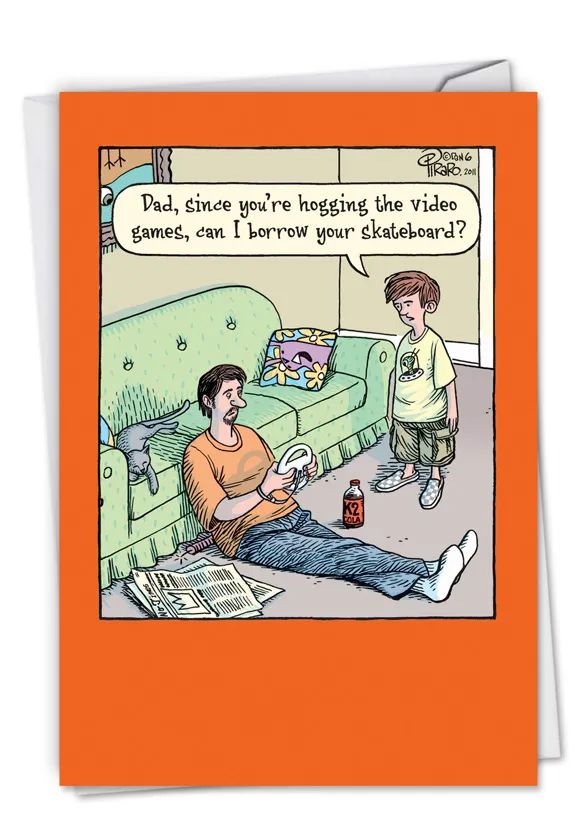

父亲(节选)
【德国】海伦·米勒作 马剑译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凌晨四点,我的父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部,被人从睡床上逮捕了。我醒来,窗前的天空一片黑暗,人声和脚步声嘈杂。隔壁的书籍被扔到地板上。我听到父亲的声音,比其他陌生的声音都响亮。我下了床,走向屋门。透过门缝我看到,一个男人打了父亲的脸。当我房间的门打开时,我感到很冷,躺在床上将被子一直拽到颌下。我父亲站在门口,身后是那些陌生人,高大,身着灰色制服。他们是三个人,一个人用手撑着门,我父亲背对着灯光,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听到他轻声呼唤我的名字。我没有回答,非常安静地躺着。然后我父亲说:“他在睡觉。” 门关上了。我听到他们把他带走了,接着是我母亲短促的脚步声,她一个人走了回来。
我父亲被捕一年后,我母亲被允许到集中营去探视他。我们乘坐窄轨火车直到终点站。上坡的道路蜿蜒曲折,途经一家散发着新鲜木料气味的锯木厂。通向集中营的道路在平坦的山峰上岔开。路边的田地尚未被耕种。然后,我们便站在装有铁栅栏的宽大的门前,直到他们把我父亲带来。我透过铁栅栏张望,看到他沿着集中营铺满碎石的道路走来。越是走近,他走得越慢。对于他来说,囚服过于宽大,以至于他看上去非常瘦小。大门没有被打开。透过孔眼紧密的铁丝网他无法和我们握手。我不得不走上前去,贴着大门,以便完全看到他瘦削的脸庞。他脸色苍白。我无法回忆起当时说了些什么。我父亲身后站着脸庞丰满、脸色红润的荷枪实弹的看守。
我父亲被释放了,条件是他不能再出现在原来的居住区。那是一九三四年冬天。离村庄只有两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在覆盖着积雪的空旷的公路上等待着他。我母亲腋下夹着一个小包,是他的大衣。他走来,亲了我和母亲,穿上大衣,冒着雪沿着公路向回走,弯着腰,仿佛无法承受大衣的重量。我们站在路上目送着他。在寒冷的空气中可以看得很远。当时我五岁。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夏洛滕堡一家医院的隔离病房里。我乘坐市郊火车到夏洛滕堡,沿着一条宽阔的街道走过许多废墟和枯树,走进医院里一条长长的、明亮的通道,走到隔离病房的玻璃门旁,按了门铃。玻璃后出现了一位护士,当我问及我父亲时,她一言不发地点点头,穿过长长的通道,消失在最后的几间病房中的一间。接着,我父亲来了。身穿对他来说过于肥大的条纹睡衣,他看上去很矮小。他的拖鞋在地砖上发出趿拉的声音,中间隔着玻璃,我们彼此注视着。他瘦削的脸上没有血色。我们不得不提高声音谈。他晃动着锁紧的门叫护士。她走来,摇摇头,又走开了。他把手臂垂下,透过玻璃看着我,沉默着。我听到,在一间病房里一个孩子在叫喊。我离开时,看到他在玻璃门后面站着,挥着手。在透过通道尽头巨大的玻璃射人的光线中,他显得很苍老。火车开得很快,经过废墟和建筑工地。外面是十月的铁灰色的光线。
海纳·米勒(Heiner Mueller,1929—1995),当代德国著名剧作家,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最重要、最有争议的剧作家之一。两德合并前,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米勒主要在民主德国从事戏剧创作和导演工作,曾先后在柏林高尔基剧院、柏林剧团等担任编剧、戏剧顾问、导演等职务,亲身参与了民主德国戏剧发生、发展到终结的几乎全部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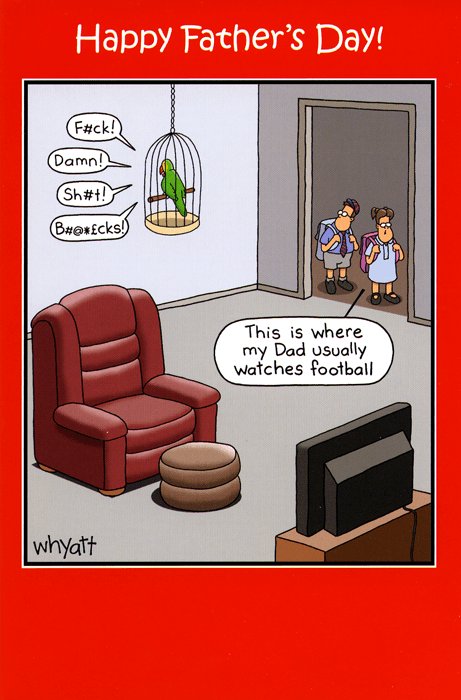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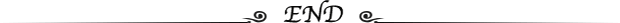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静远 排版:文娟
校对:秋泥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