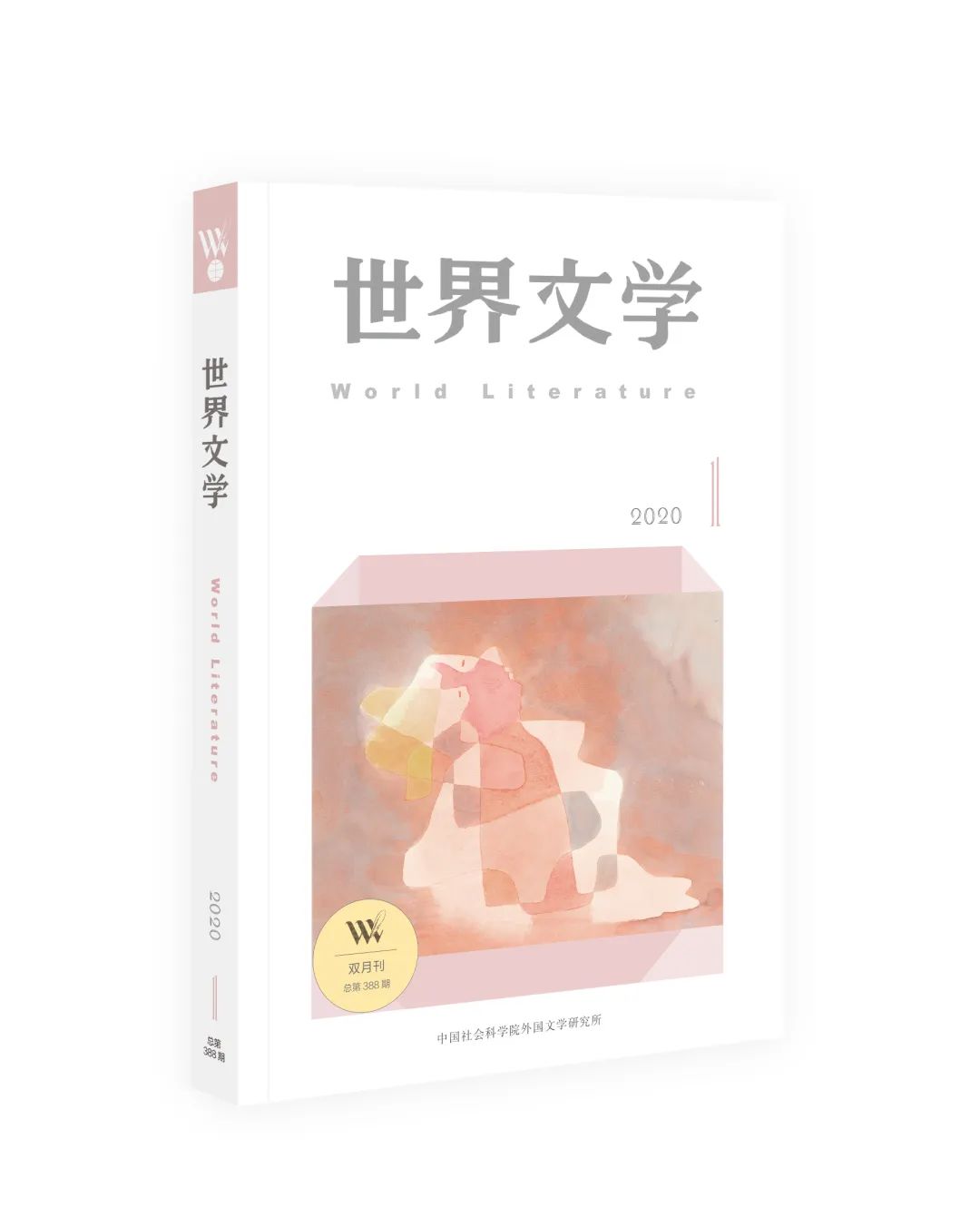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读者来稿|刘洪:“上方没有天堂”——《叫莱斯就好》读后感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一篇非常精彩细致的读后感。作者从主题到技巧、从背景到构思、从立意到语言等方面对《叫莱斯就好》这篇小说作了详尽透彻的解读,有感性的直觉和抒情,也有理性的逻辑和论证。作为作品的编者,何其有幸能碰到这么认真、这么用心去阅读和思考的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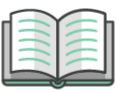
“上方没有天堂”:
《叫莱斯就好》读后感

格温·古德金





征稿启事
投稿一旦选用,将赠送《世界文学》文创、过刊、别册等小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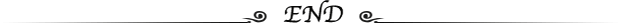
点击封面,一键订购本刊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责编:静远 排版:文娟
终审:言叶
征订微信:15011339853
投稿及联系邮箱:sjwxtg@126.com